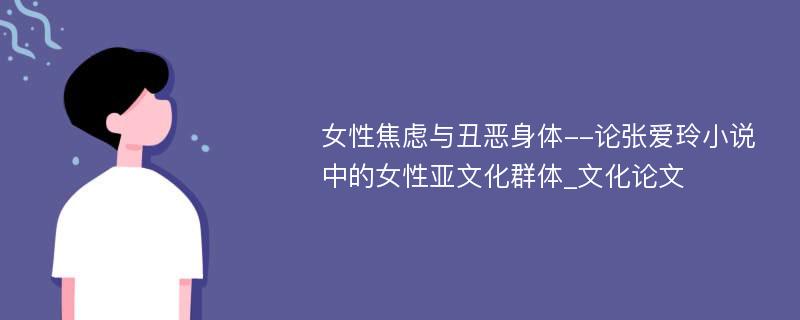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焦虑论文,群体论文,身体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论:张爱玲小说与女性亚文化群体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如何能够忠于她的生活、历史、文化现实以及她自身的性别特质。在这方面,张爱玲很少加以伪装或反串。此种忠于自身(女性)经验的书写模式,让张爱玲得以忠于自己的性别/经验而写作。不论是在女性压抑、焦虑或内囿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在张爱玲小说中挖掘到各种有关女性的沉默、匮乏、分裂、甚至疯狂的意涵和潜在文本。
大体上,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乃在于她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囿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这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事实上,在小说创作以外,她在影评中也曾经论及女性这方面的复杂心理和现实问题。例如她在《借银灯》中评电影“桃李争春”和“梅娘曲”时,便指出影片的浅薄在于:“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认为即使在礼教森严的古代,女性的心理也有其错综复杂之处(张爱玲,1995a:95—96)。可见在小说写作以外, 张爱玲亦十分重视女性心理和女性经验里的细节与复杂处。
男性对于女性心理的忽略,若非导致男性文本/电影中女性人格的扭曲,便是把女性视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作家对于女性主题的书写则表现了她对于女性经验遭受贬压的一种抗衡。在作家重视女性心理的复杂层面的基础上,张爱玲对于这些女性问题与心理的挖掘,特别是女性亚文化的特质,其深刻度往往令人惊异。
从女性主义视角而言,女性亚文化群体(female subculture )可被理解为:一种为了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设法将其永远置于此从属定位的一系列观念、偏见、趣味和价值系统。这使女性被编码在亚范畴地位上。简单的说,女性亚文化群体即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制度,一种和(男性)社会统治群体有着显著差异的生活习惯,包括社交活动、期望和价值等各方面。这使女性在家庭、社会、教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从属于男性主体之下。这种亚文化行为和思想,把生儿育女、家务工作、教育问题、宗教活动等视为女性亚文化群体的生活重心。这更被女性主义者视为一种被仪式化了的身体体验,其中包括了发育、初潮、性欲、怀孕、生育和停经等整个女性性欲与生活系统等方面,都在这意义上成为一种隐蔽的生活习惯(注:在此种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女性得以扮演合乎体统的淑女、或屋里的天使、贤妻良母等角色,而心安理得地生活在男性中心体制里。在西方,她们是所谓“家庭王国”的皇后,内心极为纯洁和虔诚(Eagleton 1986:13—14);在东方社会, 则是所谓的黄花闺女与良家妇女。)。
女性在亚文化群体的价值、常规和经历,使女性联系为一个统一体,并在阶级、生活方式和文化上和男性相背而驰。事实上,这和女性在父权体制中被定义为“他者”(the other)不无关系。在这背景上,此种负面的、非主体的、次等的概念使身为他者的女性往往陷于自我丧失的危机中,而不能像男性一样被理解为完整的主体,而构成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这正是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宣称的观点: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the Subject), 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the Absolute),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质论的现实状况之中(Beauvoir 1972:16—29)。
在张爱玲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以女性亚文化的特质去推演她们的匮乏、压抑、焦虑和丑怪等女性问题。许多女性人物在此从属位置中较难以找到自己的身分与主体。在《怨女》中,张爱玲写柴银娣在寻求自我身分定位的问题上就明确地提出女性的这种经验: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中间没有安置柴银娣的位置(张爱玲,1991a:97)。 这写照说出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中的他者位置:自我与主体的丧失(注:在中国传统男女两性秩序的文化编码中,由于儒家经典中的两性伦理观念扮演着重要的规范角色。因此,这里为了进一步区分中国的父权特质,提出“宗法父权”的概念。“宗法父权”一词在此含有双重的概念,意图结合中国宗法礼教和西方父权体制。此词相信颇能代表/讲述东方的父权文化体质,以期进一步标榜中国父权体制和儒家典籍中有关性别规范和道德礼教的特色。另见拙文《张爱玲的临界点:闺阁话语与女性主体的边缘化》,《中外文学》第24卷第 5期,1995.10。)。这正是张爱玲对从属女性及其亚文化处境最深刻的省思之一。
因此,一旦把张爱玲小说挪入庞大复杂的宗法教条、规范和禁忌交错重叠的传统宗法父权体制中,将更有助于勾勒潜藏其中的女性经验。而这里试图指出,这种讲述沉默与匮乏的女性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极为尖锐的问题。
二 女性亚文化群体:沉默与匮乏的意义
正如女性在整体父权体制的处境一样,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亦常被归化为亚范畴地位。 只有男性经验才被视作“普遍性”(universal)的根本,而把女性经验排除在外。在这位置里,女性经验亦被放逐于文学/文化中心以外(Donovan 1975:10)。然而,在张爱玲小说中此种亚范畴的女性经验,却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张爱玲的这种书写模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如何将边陲意义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其女性带进文本的中心舞台:以压抑与内囿性质的女性身体/文化,以及她们的沉默、匮乏、焦虑与亚文化特质等课题,去抗衡五四时期以来以男性模拟为主导的文学传统。
在这基础上,张爱玲书写女性自我经验的模式,除了可被视为一种女性文本的文学策略以外,亦可被视为作家一种文化的表态。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她很善于把隐匿在宗法性别秩序内的女性推上历史舞台,从而使她的文本也成为女性作家表现欲望、身分、语言和文化的剧场(注:有关方面的问题,甚至可以进一步牵涉到女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构成身体、欲望与权力的女性文本。参阅拙文《张爱玲的“闺阁政治论述”:女性身体、欲望与权力的文本》,《文史哲学报》第47期。)。
这里尝试从《散戏》一文开始谈起,先探讨南宫婳所表现的沉默与匮乏问题,进而在这基础上,才在后文探讨女性的焦虑与丑怪身体的主题。在张爱玲研究中,《散戏》一文的重要性普遍受到忽略。但事实上此文对于女性经验有颇为深刻的描绘,特别是南宫婳所表现的象征意义。在此篇中,南宫婳觉得她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张爱玲,1993b:12)。 实际上,南宫婳身为一个名演员,照理应比一般家庭妇女有著更为广大的生活圈子。但张爱玲却强调了南宫婳这方面的匮乏意义。
除了个人的私生活外,更甚者,南宫婳亦被塑造成一个沉默的女演员,连自身在公众场域的身分也被消除、默化。南宫婳这方面的内心现实体验很有启发意义,指出了她的现实生活和舞台表演的沉默意涵:
她(南宫婳)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她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韵节,因之,不论她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哑剧。(张爱玲,1993b:12)
这里的反讽直接了当:南宫婳的声音里充满一种奇异的沉寂。南宫婳虽然在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最终都落入“古装哑剧”的沉默之中。这正是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的匮乏、沉默的一种铭刻(注: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家庭和舞台两种场所中,南宫婳实际上具有更为复杂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有其从属性,另一方面,在舞台上亦含“女先知”的特殊身分。此种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的矛盾铭刻,笔者将另文探讨,此处不拟赘述。)。
在“古装哑剧”的象征基础上,叙述者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不论南宫婳在舞台上演的是什么戏,最终都要回到现实的家里,扮演传统的家庭主妇的角色。此种女性名演员被默化的喻意,除了直接讲出了她在舞台上的沉默与匮乏之外,同时也勾勒出她在现实生活中所将面对的沉默与匮乏,以及女性亚文化经验的生命观感。在这意义上,由于南宫婳的内心现实被舞台化和戏剧化了,再加上南宫婳在舞台上所象征的“古装哑剧”,从而也赋予南宫婳更为深刻的寓意。这使南宫婳在张爱玲小说中所演绎的女性哑剧,因而也具有更为广大的象征基础,使其更有能力指涉其他文本及广大的现实女性。
类似南宫婳这种女性亚文化群体的沉默与匮乏问题,普遍存在于张爱玲的小说之中。除了《散戏》外,《红鸾禧》中的娄太太同样有其无法避免的匮乏与边缘处境。当娄家状况愈发兴盛,娄太太却更进一步发现自身的匮乏,而变得更为沉默,觉得孤独无依:
他们父子总是父子。娄太太觉得孤凄,娄家一家大小,漂亮、要强的,她心爱的人,她丈夫、她孩子,联了帮时时刻刻想尽方法试验她,一次一次重新发现她的不够,她丈夫一直从穷的时候就爱面子,好应酬,把她放在各种为难的情形下,一次又一次发现她的不够。后来家道兴隆,照说应当过两天顺心的日子了,没想到场面一大,她更发现她的不够。(张爱玲,1994:40)
娄太太在家道兴旺中发现了她的不足,以及这些匮乏所带给她的羞辱与悲伤。她深知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屑于她的无能与不足。所有可能的意义都落入“妇者服也”的传统伦理/性别结构之中。在三纲三从的宗法规范下,娄太太的沉默、匮乏及其从属客体,为我们揭示了娄太太的女性亚文化身分的命运。娄太太的哀伤显示出她并没有随同家人的成长而成长。她丧失了与家人(家庭)共同成长的空间和条件。许多原可发展、提升人生境界的机会,都在亚文化处境中给剥夺了。娄太太此一角色,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成为这些儒家女性演绎匮乏与沉默的场所(注:这里采用“儒家女性”一词,主要因为在三纲五常的大主轴中,儒家三从四德的性别文化和尊阳贬阴/男尊女卑的道统,在文化层次上把中国传统女性贬为压抑符码。儒家的概念,在此因而不只是一种学说流派,也指涉一种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基本上,这和宗法父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两者互相指涉。这不仅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宗法父权体制中占有轴心位置,在儒家四书五经的典籍中,更大量传载着有关男女两性主从、内外、尊卑的宗法秩序思想,其所涉及的性别政治、象征秩序、男女主从等意识形态,更长久渗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深深影响女性的生活、心理与人格发展。)。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并不理解娄太太,不同情她反而同情娄嚣伯,替娄先生抱不平,认为娄太太不配嫁给娄嚣伯,是错配了夫妻:“多少人都替娄先生不平”(1994:40)。这层意义的揭露,再度显示张爱玲如何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儒家女性的亚文化困境。
在《红鸾禧》一文中,我们对于娄太太的阅读还必须进一步考虑到以下的问题:即张爱玲为何让娄太太钻回童年记忆中,一团高兴地为未来媳妇做花鞋的事件上。基本上,这不但是因为娄太太没有别的本领或长处,也是因为玉清和她一样是嫁入娄家的媳妇,而有同病相怜的感觉。然而,这里认为娄太太绣花鞋的行为可能有着更为重要的内囿意义:即是试图借助这行为去解除她内在的焦虑。在这迎娶媳妇的重大日子期间,深感匮乏的娄太太虽然努力表现自己的特长(绣花鞋),但她在家中的亚身分早已不被尊重。因此她的疏离感受仍是在所难免。娄太太对此亦有自觉意识。这表现在她对丈夫的反感上:
娄太太突然感到一阵厌恶,也不知道是对她丈夫的厌恶,还是对于在旁看他们做夫妻的人们的厌恶。(张爱玲,1994:48)
从这视角而言,本篇中的叙述者对娄太太内心的叙述显然要比文字表面更为深刻,说出了娄太太对自己、丈夫和社会的反感。娄太太的厌恶感,在暧昧的叙述语言中从丈夫身上转入生活圈子,连同其他知道她俩婚姻状况的人,即她俩夫妻的公众领域也都被指涉在这种暧昧不明的语言里。事实上,深感暧昧的是娄太太本人。她的婚姻关系所带给她的厌恶反感,甚至已为她带来羞耻。因而她对旁观的人们也感到厌恶反感。这里的反语用意相当简单明了,然而其中所涉及的厌恶、羞耻、自嘲等内心活动则复杂得多。因此我们必须把娄太太的女性亚文化身分纳入整体社会关系之中,才能进一步把握此中的主题讯息。
对娄太太来说,更反讽的是她在家中的低微地位,更可以从她无法自主处理家务上显现出来。虽然夫妻呕气吵架,第二天如果遇到意外事件,娄太太仍然必须忍气吞声打电话给娄先生向他请示、问主意(张爱玲,1994:43)。这充分显示出娄太太在家中的从属位置和亚文化特质。当然,这也透露出娄太太如何被边陲化为传统男性中心家庭中的他者的现实,从而暗中带出日后邱玉清亦将被他者化的命运。
此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孟烟鹂也是这般情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透露了孟烟鹂从属边陲的客体和被置之荒野地带(wildzone)的女性亚文化经验。此种富于沉默、匮乏与焦虑的女性亚文化经验,我们都可以轻易在张爱玲小说中找到,如《传奇》中大部分的篇章,以及日后的《小艾》、《色、戒》、《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半生缘》和《秧歌》等亦不例外(注:有关方面的问题,事实上亦包括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压抑与内囿主题。而这方面的考察,笔者已另文探讨。此外,亦可参考拙文《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第1期。)。
因此,女性亚文化群体的探讨需要较为全面的考察工作。在这方面,南宫婳的“古装哑剧”和娄太太的沉默、匮乏与哀伤等女性亚文化特质,除了显现在孟烟鹂和白流苏等人身上之外,亦同样落在其他女性人物身上,特别是《连环套》的霓喜、《金锁记》的七巧、芝寿与长安、《花凋》的川嫦与郑夫人、《小艾》的小艾与席五太太、《创世纪》的全少奶奶与潆珠、以及《等》中的各类太太,都在沉默与匮乏的意义上构成女性亚文化群体。在叙述复本(narrative double)的基础上,构成相互指涉、相互复写的叙述女体。这些女性在“传统恐惧”的心理背景上害怕被赶出家门、失去儿女或丧失丈夫/家庭所代表的经济和一切依靠的困境。一方面,这些女性亚文化群体已被宗法父权体制所内化规范,她们所共同面对的匮乏与焦虑在身分摆动间被视为常态。另一方面,这一层次的沉默与匮乏亦有可能外现为焦虑和丑怪荒诞的形式。
三 重读《花凋》: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的铭刻
从普遍意义来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和西方的父权体制一样,都把性别差异下的女性编码在体制内部之中,而又放逐到边缘位置:即在体制内、又在体制外缘的一种“内化外缘”处境(注:女性此种既被父权体制所归化收编,又在放逐中遭受压抑的状况,说明女性的性别编码原本即是在父权象征秩序内部所建构而成。用伊果顿(Terry Eagleton)的观点来说,女性既是被父权象征秩序浪漫地理想化了的成员,又是被放逐的牺牲者。她时而存在于男人与混沌之间,时而又体现为混沌本身(Eagleton 1983:190)。)。在此宗法体制社会里,儒家女性的“性”和“身体”不但被纳入宗法道德禁忌之中,同时,性与身体的差异亦被简化为压抑的手段,在体制内成为一种禁区,而使女性无法偏离从属、内囿或他者的亚文化定位。
从男女两性主从层面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伦理秩序显然充分表现了男性主体和性别政治的特质。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礼教律条中,以及在天、君、父、夫的规范下,女性往往被安置在“非正统”的从属位置中,藉以标志其亚文化身分的属性。这些传统女性因而在文化上成为男性“正统文化”及其“正统身体”所界定和规范的对象。
在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的概念中,两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权力关系,并视此关系为一切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原始模式。米勒(Kate Millett)从性别差异角度介入,指出父权体制如何借助性别差异的基础把女性置于从属的位置,以维护男性自身性别的利益与权威。这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性别与权力观念。在此性别政治中,不论权力形式以何种缄默的方式隐蔽自身的真相,亦将仍然是最具影响性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论是在公众场所(社会)或私人(家庭)场所,性别政治都是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两性关系基础。在这性别政治背后的真相是:上帝(天)站在父权体制的这一边,使之成为一种最具力量的压制机构。在这意义上,父权体制通过社会机制和经济压制而得以充分支配女性,把女性附属在男性中心底下。最后扩及社会、阶级、经济、种族、律法、语言、文化和性别等各个领域之中(注:米勒在《性别政治》一书中指出,政治概念不宜从狭隘的政治活动如政党、议会等角度定义,而应顾及人际权力结构关系(power—structure relationships)。因而视两性关系是一切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基础(Millett 1977:23—26:51)。)。
在探讨张爱玲小说的女性问题上,尤其需要从宗法规范与性别政治的角度去挖掘女性亚文化群体的压抑、匮乏、焦虑和丑怪的问题。以下三个小节即将进一步借助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特别是《花凋》、《创世纪》、《连环套》和《小艾》等篇去探讨这方面的女性亚文化群体问题。
在《花凋》中,郑川嫦逝世后虽有个华丽的墓园,但实际上则却只是虚假无实的表征而已。全篇故事以郑川嫦被粉饰的墓园和墓志铭为始,带出她那“美丽的悲哀”的真相,进而道出川嫦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她是一座没点灯的灯塔(1993a:431)。
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张爱玲,1993a:430)
正如叙述者的话那样:川嫦的一生的真相“全然不是那回事”。川嫦的墓志铭及其被美化了的墓园,成为郑先生为女儿所塑造的讽刺模型,一种违背真相的自我修正手法。这显示郑先生在川嫦死后,如何试图为女儿塑造一个美化的理想假象,以期替自己的父亲形象造势。但是,虚假的颂词一旦落到现实将宣告破灭。在这虚假的表象上,《花凋》里的叙述者在故事的开端塑立了一个大理石的白色天使,胸底环绕著一群小天使:“上上下下十来双白色的石头眼睛。在石头的风里,翻飞著白石的头发”(张爱玲,1993a:430)。白理石塑成的天使雕像在此成为川嫦生前丑怪的反写。像川嫦一样,那些被塑造为“天使”的大理石雕像,其背后正隐匿著丑怪的女性身体的真相。此处华美的墓园、白理石天使和情意绵绵的墓志铭都是虚假的表象。女性作家似乎企图借助少女成长与死亡的故事,及其纯真无瑕的女性形象,表达她对于郑先生的鞭笞和讽刺。川嫦生前死后的矛盾差异,即在儒家传统父亲的正统身分和儒家女儿的丑怪身体之间的差异中,反讽了川嫦的“美丽的悲哀”:女儿的身体在死后才变得真实美丽。死亡本身成为一种讽刺模拟,反讽了死者生前的悲剧。
川嫦死后的替身——石头天使,在小说故事一开始就托寓了她(隐匿)的抗议:反讽生前任她的身体病坏,死后才刻意安慰她的亡魂的父亲/郑先生。这是《花凋》一文的反讽核心。日后,我们从张子静对张爱玲的追忆中得知,郑川嫦其实乃是张爱玲年少的知心玩伴,真名黄家漪。“川嫦”谐音“穿肠”,此中柔肠寸断之意寄托了张爱玲的哀悼。郑川嫦的真实性,就像张爱玲小说中其他人物,如郑夫人、郑先生和曹七巧的真实性一样(注:据张子静所言,本篇所描写的郑家即张爱玲的舅父家,而《金锁记》的姜家则是李鸿章次子之家的真实故事。(参见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第九章)这些现实基础显示这些家庭中的女性人物和男性家长都有其现实意义。),有利于印证这些人物所代表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那些可以相互指涉的女性人物角色,在现实与文本的意义上,构成女性叙述中深奥复杂的文学策略。在此书写策略中,川嫦和她的母亲郑夫人的非正统身体,实乃共同处在同样的宗法性别政治和文化压迫之中,其差别仅在于郑夫人在郑公馆的位置比川嫦的女儿身分略为优胜,但却都受到正统身体(男性家长)的规范和性别政治的压迫。
川嫦生前卧病房中,正犹同被人软禁于“铁闺阁”里(注:大体上,“铁闺阁”概念和传统宗法礼教中的性别和伦理秩序有密切关系,特别是男外女内,男主女从,尊男贬女和崇阳贬阴等男女/阳阴尊卑思想。据此,铁闺阁的概念是一个较为广义的场所,有著更为深广的文化意义。在“女正乎内,男正乎外”的文化机制中,所谓“深闺固门”的闺阁场所,不再只是传统妇女生活起居的空间概念而已,而是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即儒家女性被规范于内囿机制中的一种概念。相关问题,可参阅发表于《译丛》的拙文:Reading "The Golden Cangue": Iron Boudoirs and Symbols of Oppressed Confucian Women.Rendition,1996,No.45.)。全家人以保护的名义使她动弹不得,自由被剥夺却又不提供她应有的医疗照顾。现实经验中,张爱玲少女时期被囚禁家中曾患痢疾而得不到充分治疗的经验,相信在此被转移到她的儿时玩伴黄家漪/川嫦的书写中。在《花凋》中,张爱玲相当能够将她的经验转移到文本中。作家篡改了现实往事,以川嫦的替身复写出一个女性临死前的绝望感:
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起,你坠著我,我坠著你,往下沉。
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张爱玲,1993a :448)
这里通过川嫦垂死的意识,反映出女性被迫害的经验。文中“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的写照,暴露出川嫦面对死亡所承受的焦虑。而这和郑先生的重男轻女和性别政治的压迫不无关系。在川嫦患病之后,她父亲抱著“不愿把钱扔在水里”的心态,并不尽心给她治疗,任她在病痛折磨中死去。在这意义上,川嫦的病体暗示了宗法社会中所忌讳的一种真相:女儿的死亡的根源往往在于家庭本身。在这些遭受性别压抑的女性身上,张爱玲实现了她在现实中所无法达致的反叛,指控了郑先生作为父亲的残忍。在坟前石碑上的墓志铭:“爱女郑川嫦之墓”等说辞,以及坟前白理石的天使雕像,因而都成了反讽的对象和媒体。
更进一层而言,在川嫦病逝前,她即深知她已成为家中的拖累。她的内疚加速求生意志的瓦解。她并没有要求家人为她付出更多可纳用的资源,反而为自身的不幸产生诸多的不安与愧疚,反射出家人所带给她的无形压力:“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张爱玲,1993a:447)。在这“拖累”的自责表象底下,隐藏著川嫦的丑怪身体和文化压抑的真相。川嫦的身体在这里显然正是父权文化压抑的场所。
临终前,川嫦在新来的李妈帮忙下,抱病走到街上漫步的描写最能说明女性“丑怪身体”的意义。川嫦注意到旁人的眼里没有悲悯的神色,反而将她视为人间的怪物:“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著她,仿佛她是个怪物”。川嫦从别人的眼神中窥探到自身的丑怪。此处的描写,显示出川嫦化身为“女性怪物”的特征: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张爱玲,1993a:448)。这种丑怪的体验令她陷入更深的沮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丑怪意象不但把她带到现实世界中,也把她带到人生的尽头,道出她临死前对于真实现实的内心幻灭感受。此处川嫦抱病走出病房的经历,使她最终看出人们只能接受戏剧化与虚假的悲哀,而厌恶真实的悲剧(张爱玲,1993a:448—49)。这也透露川嫦自己终于也体认到虚假的悲哀和真实的悲剧之间的真相。这打击也足以说明为何川嫦的病情在此次事件后即迅速恶化,而在不久之后与世长辞。
实际上,在此之前,《花凋》的叙述者早已指出川嫦病中的丑怪和焦虑。
她的肉体在他(章云藩)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了,她的脸像骨格子上绷著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了两只炎炎的大洞。越急越好不了。(张爱玲,1993a:443)
由此可见川嫦的丑怪与焦虑已经累积良久。相对之下,这种丑怪身体的铭刻,和川嫦生病以前那种“极其丰美的肉体”,“一双华泽的白肩膀”,以及充满深邃的热情与智慧的眼睛等写照(1993a:431),更可看出张爱玲这方面的书写策略。
此外川嫦死前的绝望、焦虑、病态与丑怪的写照,不妨借助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汀(M.M.Bakhtin)有关“丑怪身体”(the grotesquebody)的角度加以理解。在这问题上,廖炳惠在《两种体现》中即借用巴赫汀所提出来的“丑怪身体”概念,把儒家正统文化中关于身体的正统和规范化,和庄子哲学中巫者所表现的丑怪身体,及其象征反支配力量、不正统的潜存文化加以探讨。通过儒、道两者在身体与政体之间的价值体系差异,举出庄子丑陋身体和儒家正统身体的对话,以指出丑怪身体彻底震荡、破解儒家正统身体的可能性与颠覆性的意图(廖炳惠,1994:217—22)。
从巴赫汀关于丑怪身体的开放性角度来看,丑怪身体不但没有和现实世界隔离,而且还会不断成长,甚至超越自己的界限(Bakhtin 1984:26)。因此,这里不宜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丑怪身体视为封闭性质的概念,而限制了我们对于有关女性亚文化群体问题的探讨。
在此,张爱玲借助丑怪身体的铭刻,让川嫦在病中反省,最终让她看到了自身悲剧的真相。在这宗法父亲名义下的郑公馆中,她的闺房象征著封闭、怜悯、病毒满布的铁闺阁,把她隔离在繁华的人世之外。虽然如此,病中她内心仍旧充满美好的幻想:如花花世界中所充满的各种愉快的东西,橱窗里的,大菜单上的,时装样本上的,艺术格调的房间,高齐天花板的大玻璃窗,地毯单,软垫和她所盼望的成群儿女,还有供她使唤的奶妈等事物(张爱玲,1993a:447—48)。这种对比的布局,无疑加强了川嫦临终前丑怪形象的深刻度和讽刺意涵。
这些生活在深闺的女性亚文化群体,例如此篇川嫦的死亡,以及其他篇章中有关女性身体的病态与疯狂,实际上都和宗法礼教压迫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这不仅是政治和性别压抑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亦必须关注到此中多重复杂的伦理价值体系是如何界定母亲、妻子、女儿的身分、身体与原欲的问题(注:在这些问题之中,女性的身体观念被传统伦理意识所规范,并为女体建构一个封闭孤绝的世界,从形体与心理、外在与内在、主体与性欲等方面,将其制约成一种“文化符号”,而非真实血肉的人。)。再者,从文化社会层面角度而言,此种有关丑怪身体的女性书写,让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亚文化群体更能够展现欲望与权力运作的繁复意涵。“一座没点灯的灯塔”正好象征了川嫦的人生,明白道出川嫦的隐喻,直指空洞、无光、沉默、匮乏、焦虑与丑怪的女性身体内涵。值得留意的是,此篇中川嫦所象征的没有光的灯塔,正和《金锁记》中七巧所象征的“无光的所在”有著异曲同工之妙。
总的来说,川嫦死前的病态、绝望与丑怪形象,其实可以和七巧、银娣的疯女形象相提并论。同样的,川嫦苍白蜘蛛的意象亦可以和川嫦母亲那苍白、绝望的女性形象联系起来阅读(注:此点和将留待后文母女两代的复本中进一步探讨,这和《创世纪》潆珠母女等人所表现的焦虑母鸡和荒诞小丑等铭写相同。从中可见张爱玲如何深刻地刻划了这些女性亚文化身体的卑贱与丑怪的意涵。)。这里相信,在三纲三从之义、五伦教化的宗法礼教之下,女性亚文化群体的病态与怪诞现象,在此借助焦虑、歇斯底里和卑贱丑怪的形式而得到激化。因此,川嫦(及其母亲)的绝望、病态、焦虑和丑怪等描写,并不能单纯地被视为厌女症的表现。我们不妨将此视为川嫦处于从属处境之中,藉以表现女性焦虑的绝望情境,并以丑怪病痛的身体共同参与了破碎、疏离的深闺演出。据此,川嫦的死其实和她身为女儿身有著密切的关系。她的死亡,显示出儒家女性如何被置于亚文化身分的位置,并以从属化、病态化、疏离化、丑怪化去体现两性的差异和女性亚文化群体的悲剧。
四 女性身体论述:霓喜和其他丑怪身体的演绎
以上对于《花凋》的重读,使我们看到川嫦死前的丑怪身体,如何像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般偷偷地走出她的铁闺阁,走在她向往已久的街道上。但她却因此陷于哀伤痛绝之中。川嫦死前的丑怪,和她死后塑立在墓前的天使替身,正好前后参照出张爱玲如何运用川嫦的女性身体去书写女性内在的焦虑。这些女性的焦虑与丑怪,以至张爱玲其他小说中的女性身体铭写(如曹七巧和柴银娣的疯狂身体),在此都可视之为女性文学策略的标志。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来说,天使与怪物,甜美的女主角和愤怒的疯女,全是女性作家的表现手法,同时也是女性作家笔下富有背叛性质的书写策略之一(Gilbert,Gubar 1979:80)
张爱玲对女性丑怪身体的描写,除了直接书写女性身体的丑怪以外,也常用象征的意象表达。在此书写策略中,川嫦的丑怪与病态:即冷而白的大白蜘蛛,正和《半生缘》中顾曼璐那种“红粉骷髅”的病体写照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前文所提及的、川嫦那削瘦的脸庞,双眼仿佛是白缎子上被灯火烧成炎炎大洞的写照一般。这两者和张爱玲在《茉莉香片》和《金锁记》中关于“屏风白鸟”与“蝴蝶标本”的营造,实有相通的、讽刺模拟的效应。“白鸟”和“蝴蝶”取其丧失飞翔能力、失落自主空间的隐喻去表达铁闺阁中被形同幽禁的女性身体。“蜘蛛”的运用,则暗示恐怖与反抗力量的酝酿。而在后期《半生缘》的“红粉骷髅”铭写上,则又强调了女性的丑怪身体,直接以死亡的尸体鞭挞整个社会。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关女性内在心理和外在身体的从属、卑微、残缺、焦虑与疯狂,都在母亲、妻妾、女儿的身分上表露无遗。除了上述有关郑川嫦、南宫婳、娄太太、顾曼璐和冯碧落等人的身体铭刻之外,《金锁记》和《怨女》中曹七巧与柴银娣的疯狂与歇斯底里写照,都可视为女性丑怪身体的表现。其他第一、二炉香中葛薇龙、愫细和靡丽笙等人亦有不可忽视的焦虑与丑怪写照。其他写及病态女体的篇章,除了《多少恨》中的夏太太外,《小艾》中小艾子宫炎的病发使她下体血崩,血流不止的血淋淋的女体论述尤为深刻。这些《连环套》中霓喜捶尸、戳尸中满床血迹的铭写,都同样值得留意。
在《连环套》这篇作品中,这种关于丑怪身体的女性论述又有另一番不同的铭写。张爱玲在书写女性身体与心灵残缺上,将其和小孩的形貌身体结为一谈,以小孩纯洁单纯的心,带出霓喜作为母亲的内在现实。然后以反孩童特质的形象,把孩子的活泼可爱完全抹杀,替代以淡白的脸,“一双凸出的大眼睛”,如同“深海底的怪鱼”,“一块不通人情的肉”等负面形象去衬托霓喜的女体:“单纯的肉,女肉,没多少人气”,甚至是没有心灵的女体(张爱玲,1991b:65—66), 挖掘出霓喜被掏空的精神内涵与内心现实。从这种写照中,母亲照顾小孩时的焦虑心理也被带引出来。正如西苏(Helene Cixous)所言, 母亲的身体在此足以成为一种隐喻(cixous 1981:252)。这种比喻意象骇人,若非作家领略深刻,否则难以捕捉其中的女性焦虑。这种母女残怪的身体描写,在张爱玲的多篇范本中都具有同样的心理结构,强调了残缺荒诞的女性内在现实。即使像霓喜这样充分性感与肉感的女性身体,或七巧和银娣等赛比西施的女性形象,到最后都不能幸免于丑怪与焦虑的命运,同样被残缺化为丑怪与焦虑的象征。
在霓喜的版本中,那些被认为次等的女性特质:如女性的匮乏、焦虑、神经质倾向等,更进一步被激化为戳尸的歇斯底里行为,进而构成霓喜的丑怪身体的复写。在此,霓喜把花瓶砸向垂死的丈夫后,窦尧芳惊吓而死,霓喜则又出人意表地爬到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紧拳头,使劲捶床,腕上挂著的钥匙戳进窦尧芳的尸体里,染了血的拳头把床单与尸体弄得血迹斑斑(1991b:62)。这和霓喜当年被雅赫雅赶离家门, 被打得“浑身青紫”,被剪刀柄砸破头的写照正可前后映照:被砸与砸人,而带出受压与反抗的宗法性别政治。实际上,这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自我残害身体(卖淫养夫),以及曹七巧与柴银娣的疯狂写照等身体铭刻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差异点是:葛薇龙伤害自身的女性身体,七巧与银娣则伤害其他女性的身体,而霓喜则伤害男性家长的身体。这些差异点,各有其不同的意义。
这情况到了《小艾》中的席五太太身上,她对五老爷无条件的依赖则说明了一个传统女性自我否定的认命心态。事实上,除此之外,在其他篇章中,如这些女性亚文化群体还包括《等》的奚太太等人,《鸿鸾禧》的娄太太,《心经》的许太太,《琉璃瓦》的姚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鹂,《茉莉香片》的聂太太,《色,戒》的几个太太等女性人物,都和席五太太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化意涵。表面上,席五太太扮演女主人的身分,实则被附属在宗法象征秩序中。身为一个正室,席五太太知道自己在席家中身分的尴尬难堪;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的“弃妇”和“寡妇”又要比席五太太凄惨。她们的卑微、难堪、无能、匮乏、焦虑,都一再指向她们的女性亚文化身分。
有关女性文本中所蕴含的沉默、匮乏、焦虑与丑怪,其实亦存在于其他女性作家的叙述体中。例如萧红《生死场》的金枝和月英,前者“好像患著传染病的小鸡”(萧红,1988,28),后者则是“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叙述者更进一步指出:
(月英)白眼珠完全变绿,整个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萧红,1998,51—52)
更甚者,月英的下体被蛆虫所腐蚀了:“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萧红,1988,51—52)可见萧红对于女性病态和丑怪身体的铭刻,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同样骇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在不同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女性亚文化群体的表现各有其不同的写照与命运。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那转型、过渡的现实社会里更充满著女性亚文化群体的真实文本,其中不少即是此种焦虑、歇斯底里和丑怪的演出。例如五四时期的“李超事件”,李超为了反抗包办婚姻逃婚进入北京女师,最后在家庭的经济封锁中贫病交加地病逝。同年,另一位赵五贞亦为了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最后竟在婚轿中刎颈自尽。这些现实事件都能充分显示这些儒家女性的亚文化悲剧,以及她们在此中所表现出来的丑怪身体特质:贫病与死亡。
五 女性复本:母女两代与丑怪身体的复写
在张爱玲小说中,这些沉默、匮乏、焦虑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其所体现的丑怪身体,都无可避免地成为宗法父权社会中的女性怪物。这丑怪形象,可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找到不少的佐证。从曹七巧、郑川嫦、顾曼璐到柴银娣等形象,都含有“女性怪物”的异质文化。若从雅各布斯(Mary Jacobus)阅读女性的视角来说,女性文本中的怪物甚至可被视为是被压抑的一种性别摆动(vacillation of gender), 或是不稳定的身分属性。这说明在历史文本中,由于历史本身即是一种压制与排挤女性的阴谋,而使女性成为怪物或失常者的意象而出现(Jacobus 1986:4—8)。从这角度而言,郑夫人、郑川嫦、曹七巧、柴银娣、梁太太、葛薇龙、许小寒、顾曼璐等系列人物,都是宗法男性中心体制对于女性亚文化群体所做出的一种压制、排挤与扭曲的文化贬压,而使她们摇摆于性别之中,饱含丑怪与疏离的意涵。
由于女性亚文化群体的从属身分隐藏著庞大的内囿主题和焦虑能量,因此她们的身体犹如容纳性极大的“容器”,吸纳诸多隐匿与明示的从属与内囿意涵。这导致她们本身也成为一种内囿的器皿 (注:容器, “envelope”此一术语——在伊莉佳莱(Luce Irigaray )的理论概念里具有多重意义和指涉功能(Irigaray 1993:10)。 这里试图“盗用”有关概念,藉以理解女性本身其实即是用来装载男性利益的容器。)。
在一些女性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如何作为一种宗法社会的“容器”,她们的一生不断被女儿、妻妾、母亲等从属身分所裹覆。这些女性亚文化群体的非正统身分,被宗法父权社会诸多“服”、“扶”、“后”、“内”、“齐”等名目所裹覆或填塞(注:陈顾远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婚姻史》中即已表明,传统家庭中的夫妇地位,不论称其为妃、为耦、为俪,或为妃耦、匹耦、配耦、伉俪、合偶、配偶,表面上似未含有男尊女卑、夫刚妇柔的观念,实际皆为虚语,具有地位差等意义(陈顾远,1966:174)。)。在传统上,女儿、 妻妾与母亲的意义可被压缩成“物品”。更甚者,女性更被充当为一种此处所谓的、可供包装、裹覆、装载或容纳等意义的“容器”。道德规范一旦和性别主从挂勾,在意识形态上便加深了“妇人伏于人”的传统两性观念。女性在三从之义和七出之训底下,自古即被包裹于从属地位。这为夫妇两性的主从尊卑做了最佳思想指导与定位。此处女性亚文化群体的功能正好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提供资源,成为被父权社会运用、剥削、包装、裹覆和装载男性利益的最佳容器。
如前文所论,《花凋》中的川嫦在这意义上亦成为被父亲所界定的一种容器。川嫦自己无法决定自身所要装载的内容。她存在的意义归属于郑先生所给予的定义。正如她母亲郑夫人一样,川嫦并不能摆脱作为宗法父权容器的地位。从川嫦和郑夫人的描绘中可见,在体系庞大的宗法传统体制面前,作为女儿和母亲、妻妾的女性,一生中三个重要身分:母亲、妻子、女儿,都是宗法父权为女性设定的最佳容器,紧密包裹她们的一生。特别是母亲和妻子,更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去指称男性的身分与意义。她们都只是空洞的容器,其自身的意义等待男人去填补/供给。
此种女性身体作为宗法规范的一种容器,充分表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之中。这种阅读视角讲述著女性身体作为宗法社会的器皿,裹覆著她们作为从属身分的一种典范意义。因此,此种被包裹、被容纳的从属意义,不只是停留在某女儿或母亲的角色里,而往往被张爱玲进一步加以复写,成为母女两代的共同命运。这充分显示在郑夫人母女、全少奶奶母女,以及七巧母女的铭写中。这使张爱玲的成就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而大大不同于冯沅君与丁玲的新女性派、冰心的闺秀派或凌叔华的新闺秀派。
张爱玲对女性的书写,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显然要比这些女作家所书写的女性文本要深刻得多。她进入这些人物复杂的内心,比庐隐笔下忧伤消极的女性,如《海滨故人》的露沙等人,《或人的悲哀》的亚侠等都来得深刻;也比冰心、凌叔华、苏青等作家所书写的女性人物更为动人。
除了前文对于郑川嫦的阅读外,我们亦必须重视郑夫人的母亲形象。和川嫦一样,郑夫人也复写了女儿的悲剧,不同的是,川嫦的悲剧较短,而郑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
(郑夫人)总是仰著脸摇摇摆摆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凄冷地嗑著瓜子——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张爱玲,1993a:432)
由此可见,郑夫人和她女儿一样都扮演了绝望的女人与悲剧的角色。经由母女两代相互的映照,其所指涉的对象、范畴与代表性也相对增强。而此种绝望的女性形象,焦虑与丑怪正是她们的一种心理特质。
除《花凋》以外,此种女性亚文化特质亦在《创世纪》中匡潆珠母女身上显露无遗。潆珠的小丑悲哀及其母亲全少奶奶“焦虑母鸡”的描写,承载著大量的压抑语言。全少奶奶年纪不到四十,却已操劳忧苦,“像个淡白眼睛的小母鸡”:
焦忧的小母鸡,东瞧西看,这里啄啄,那里啄啄,顾不周全;现在不能想像一只小母鸡也会变成讽刺含蓄的,两眼空空的站在那里。(张爱玲,1991b:95—121)
全少奶奶在这里所表现的丑怪身体:焦虑母鸡的写照,显然是传统家庭妇女的普遍写照。她在厨房中忙得“披头散发”,说起话来常“举起她那苍白笔直的小喉咙……叽叽喳喳,鬼鬼祟祟”(张爱玲,1991b:100)。这造型正可以说明全少奶奶如何被描写为“像个淡白眼睛的小母鸡”的丑怪形象。
在《创世纪》中,全少奶奶的焦虑虽并没有令她发狂,而她的丑怪形象亦不同于七巧的疯狂,或郑夫人的绝望,或娄太太的匮乏,或霓喜的坚强,但是,其中的焦虑与丑怪却是共有的。在此篇中,作为女儿的潆珠要跳出器皿的定位已不容易,身为母亲的全少奶奶,自然更不容易摆脱既存的女性亚文化身分。她们和《连环套》的霓喜、《红鸾禧》的娄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鹂等人一样都共同面对著女性亚文化的命运。和川嫦的母亲相比,潆珠的母亲在传统大家族中更充满著为人媳妇的苦处。她在黑暗的厨房“怨天怨地做了许多年”,“忙得披头散发的”:
这些年来,就这厨房是真的,污秽,受气是真的,此外都是些空话,她公公的夸大,她丈夫的风趣幽默,不好笑的笑话,她不懂得,也不信任。(张爱玲,1991b:114)
此处“除了厨房就是厨房,更没有别的世界”,一语道尽了女性亚文化群体的内囿现实。更重要的,此篇中黑黯的女性私人领域:厨房/闺阁,连同《金锁记》中“没有光的所在”以及《花凋》中“没点灯的灯塔”等描写,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宗法政治所遗下的残余空间。从这些描写中可以挖掘到女性荒凉的意味。和女性身体一样,这些女性的荒凉与黑暗无光的领域,不只涉及女性的现实生活,同时亦蕴含欲望、文化与性别政治等问题。这种叙述体显示,潆珠可能也会走进全少奶奶的世界。此种女性亚文化群体命运的重写与复制永无终点。同样的,若川嫦不死,她可能亦将重复郑夫人的命运。
从潆珠的角度而言,母亲的丑怪形象给了她一种血肉淋漓的活例。而她自己,叙述者则给了她一副小丑的脸相:
下半个脸通红的,满是胭脂,鼻子,嘴,蔓延到下巴,令人骇笑,又觉得可怜的一副脸相。就是这样地,这一代的女孩子使用了她们的美丽——过一日,算一日。(张爱玲,1991b:121)
潆珠所演绎的丑怪身体表达出小丑式的悲哀,其实和全少奶奶的丑怪身体相仿。母女俩人的丑怪形象,其实正是以女儿/母亲的替身彼此对话。推而广之,从匡家母女、郑家母女至《金锁记》中的姜家母女,以至其他各个女性身体的写照,正可视为女性亚文化群体的各种复写。这“一副可怜的脸相”,被装载在多义、多变、矛盾的丑怪身体之中,彼此对话。
在这些写照中,潆珠显然面对著小丑式的青春年华。她在匡家的小丑角色,和全少奶奶、戚紫微一样徒有空洞的美,一家三代的女性都重写了女性亚文化的模式。在一种“华丽旧时代的美”的处境上,却揭示出“脸庞之内仿佛一无所有”的真相(张爱玲,1991b:122)。此种内在焦虑的心理背景,导致潆珠最终歇斯底里的与厉声叱喝她的祖母对峙起来:
(潆珠)兜头夹脸挣扎似地,火了起来,泼泼洒洒。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书也不给她念完,闲在家里又是她的不是,出去做事又要说,有了朋友又要说,朋友不正当,她正当,凛然地和他绝交,还要怎样呢?(1991b:121)
她不禁大声质问匡老太太:
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要我怎么样呢?(1991b:121)
这句问话,不仅是潆珠对祖母的质问,也应当视之为她向宗法家庭质问的一种口号。问话中充满自我的焦虑、不满与愤懑。潆珠面对了所有传统儒家女性的一切问题和诸多症候群:焦虑、悲哀、忧郁、不满和神经衰弱。她们虽不像七巧、银娣、薇龙、曼璐一般表露太多的歇斯底里症候,但在宗法象征秩序里,她始终处于被排斥和自我否定的位置里。这些被迫处于“父亲的女人”或“他的父亲的女儿”位置的女性,其肉体/物质性能不免成为受压抑的一种标志(周蕾,1995:29)。
潆珠的此处呐喊,显示她在内囿位置中,在爱情、学业、事业上都遭遇压抑。在这里,潆珠就和长安、家茵、愫细、薇龙、川嫦的女儿身分一样,承受著宗法父权对女儿进行权力行使的重量。除了这些女儿之外,她们的母亲,包括其他篇章中丧失自身姓名的女人,其身体就是一种容器,表征著宗法父权的一种裹覆。这些母亲和妻妾,连同其他女性(男性)作家笔下无名无姓的文本女性,如凌叔华《绣枕》中的“大小姐”和丁玲《夜》中不具名的“老婆”等等,都变成宗法体制下的一种器皿的象征。这种不具姓名的女性角色,自古就大量流传并互相指涉,在叙述复本的意义上构成意义深远的中国女性亚文化群体。这些女性身体不但成为文化与性别压抑的场域,亦成为女性文本的寓意所在。
以上这些亚文化身分的女性群体,无疑蕴藏了许多值得挖掘的问题。从上述的论述基础上,不论是席五太太、娄太太,或者潆珠、家茵、长安、川嫦、薇龙等女性的身体铭刻,都充满女性卑化、默化和丑化的意义。这些女性亚文化的写照,都是女性经验的表现。张爱玲的这种书写模式,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不妨被视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策略的标志”(Gilbert,Gubar 1979:79— 80)。通过张爱玲这种文学策略的解读,显示女性亚文化群体被反复表现在女儿、情妇、妻妾、母亲或婆婆等身上,显示不同身分的同一辞汇和同一意义。
从西方女性主义对于身体论述的视角思考,张爱玲所书写的女性身体亦释放了传统女性在宗法礼教中所面对的恐惧与焦虑。我们在她的文本中阅读到历史,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窥探到某些女性的身体和其内在世界的写照。她的书写,以及她对笔下女性人物命运的设置,实际上正是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格巴(Susan Gubar )所强调的观点:女性作家不但藉此寻找自己的故事,事实上也在寻找自我的定义(Gilbert,Gubar 1979:76)。 这层意义经常隐匿在某些女性文本的背后,而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读者的批评,我们自然有必要解开这些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隐匿故事(Rowland 1988:71)。在这方面,张爱玲书写了她所寻找到的故事,也说出一个女性作家对她笔下女性人物要说的话。张爱玲藉此女性亚文化群体的各种问题,去质疑男性中心社会下女性定义和女性自我的问题。此外,她也创造了她的女性文本。这些故事不但出自于作者个人的经验及其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也属于整体民族的历史。
从文学史角度来说,五四时期“父亲的女儿”的忤逆,而使这些女性的亚文化经验受到女性作家的重视。自五四以来,女性作家逐渐能在文化缝隙与松散零碎之处奠立自己的文学传统。陈衡哲、庐隐、白薇、冯沅君、凌叔华、丁玲、冰心、萧红等女作家,都曾经试图在性别与民族之间寻找某种出路或某种契合的可能性,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和语言去书写女性经验,并藉此将女性特质纳入文学史。这些女性作家藉此诉求各自所要寻找的故事和主题。在这方面,张爱玲尤能充分书写女性自我的经验,揭橥了东方女性的亚文化群体的属性。张爱玲这种注重女性亚文化经验和性别政治的书写策略,无疑为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开拓出一种女性文本的书写策略和表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