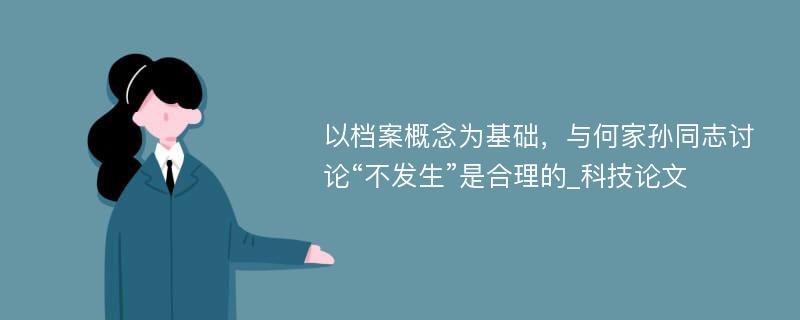
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与何嘉荪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同志论文,档案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界的认识应该说是较清楚的,从总体来讲,“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①],因此,在研究档案定义时,不少论者从来源角度出发,把文件作为档案的属概念。如果按文件的作用性质将其划分为现行文件与非现行文件(或称历史文件),那么档案概念应建立在现行文件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非现行文件的基础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过去也是一致的,在今天则不然。例如,《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2期发表的何嘉荪同志的《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合理吗?》一文就是一例(以下简称何文)。该文对档案界公认的关于档案概念是以非现行文件为基础的命题提出了质疑。档案概念到底应以何者为基础,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之争,它直接涉及到档案的定义、属性与范畴,正如《何文》所说,涉及到“档案概念据以立论的根基”,是一个应该讨论清楚的理论问题。据笔者拙见,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
一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首先是在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后又受到前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影响。尽管50年代末科技档案管理理论的建立,80年代末专门档案管理理论的兴起,使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有了较大发展,但这一研究历史的痕迹至今仍然存在。如在档案学的论著中仍偏重于文书档案;在档案与文件的关系上忽视对现行文件的研究,机械地理解档案文件的历史性,造成对档案的整体概念把握不准,等等。尽管如此,在档案的概念上以非现行文件或历史文件为基础却是合理的。理由有三:其一,在我国的档案中确有部分所谓的现行文件,但更大量的是非现行文件,且随着事物的发展,当前暂时为现行性的文件终归要变为历史文件。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历史文件是档案的主体,档案终究只能是一种历史记录。我们之所以认为把档案概念建立在现行文件的基础上是不合理的,是因为这不符合也不能表明档案的基本属性。同样,把档案概念建立在一般文件的基础上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不能表明档案与一般文件的区别,缺乏档案的时间特征。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文件或历史文件为基础,这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这正如我国目前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但主体是国有经济,因此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基础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其二,在谈及文件的现行性与历史性时,我们应当有一个广义的理解,并理解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历史”一词,《辞海》的解释是:“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②]显然,凡事物的发展过程即为历史,我们不能认为非到过程结束之时文件才能成为历史文件。例如,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会形成许多文件,这些文件在该人在世期间可以视为现行文件,因为它是人事管理过程中直接使用的材料。但是对一个人的今天与将来而言,昔日所形成的文件又是历史文件,因为它记录的是往事,是过去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认为历史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是基于事物发展的过程就是历史的观点。因而,不能因为产品仍在生产、设备仍在运转、房屋仍需维修,而把相应的产品图纸、设备文件、竣工图视为现行文件。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有相当一部分档案要从档案的范畴中除掉,其结果必然造成实际工作的混乱。例如,保存设备档案的目的是为了设备的使用和维修,其保存期限一般与设备实体同存,当设备报废时,相应的设备档案也就没有什么保存价值了。如果认为因设备还在运转使用,相应的设备文件就是现行文件,而不是相对地视为历史文件,那就无所谓设备档案了,因为哪个单位都不会花费人力和财力去保存管理那些实物对象已报废的所谓历史文件。总之,单纯以文件的使命为划分标准,那就不可存在产品档案、基建档案、人事档案等这类概念。我们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认定作为档案概念基础的历史文件的“历史”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能把历史文件理解为事物发展过程终结后的产物。其三,我国的档案工作与西方国家的档案工作有着不少差异,对档案概念的理解不同就是其中之一。西方国家一般把进入档案馆的文件称为档案,在此之前称为现行文件。把档案工作范围由档案馆延伸到基层单位档案室,是我国档案工作的一大特色,由此,档案概念的外延较西方国家有所扩大。如果用西方档案学的观点看,我国的档案中的确包括一部分所谓的现行文件,即“并不失其行政和法律效力”[③]的文件。因为按照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所谓现时使用完毕或办理完毕,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是指为履行当时的职责而直接使用材料告一段落,或完成了文书处理程序,并不是说以后不再利用,或文件内容针对的具体事务全部办完,该文件才算是‘处理完毕’”[④]。由此可见,我国与西方国家对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用西方档案学理论体系中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我国的档案概念显然是不妥的。事实上,我国对科技档案、专门档案的成功管理,证明了我国广大档案工作者对历史文件的理解是基本正确的,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把档案概念建立在历史文件的基础上,是符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的。我们没有必要用西方档案学的理论来规范我国档案学的建设,也没有必要用西方国家的档案概念来修正我国对档案概念的理解,因为这样做,既无视我国的国情和成功的经验,也不利于我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发展。
二
《何文》是从适应文档一体化管理的角度出发,对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否合理提出质疑的。文章把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所引发的矛盾归纳为档案起始点标准的双重性和归档制度上。但据笔者之见,上述矛盾并不存在,或者说并非是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所引发的。
关于档案起始点标准的双重性问题。《何文》引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把文件运动的全过程分为制作、现行、暂存和历史四个阶段,认为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导致档案阶段有的从暂存阶段开始,有的从现行阶段开始。归档关口“对有关文件而言设在文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而对另一些文件而言就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而且同一种文件在不同单位,其档案阶段的起始点也不相同”[⑤],即所谓档案起始点标准的双重性。对该问题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如果这一问题确实是由于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文件为基础所引发的,那么当档案概念改为以文件或现行文件为基础,是否就能解决这一矛盾呢,是否就能统一档案起始点的标准呢?假如档案以现行文件为基础,按照《何文》说法现行期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样也会产生是把现行阶段的起点作为档案的起始点呢?还是把现行阶段的终点作为档案的起始点的问题。即使档案以文件为基础,又该以文件的哪一个阶段作为档案的起始点呢?显然,否定了档案以非现行性为基础,仍然不能解决从那“一刻起将文件作为档案进行管理的问题”[⑥]。鉴于档案工作的广域性和文件类型的复杂性,在这纷繁多变的世界上,采用“一刀切”的办法硬要统一找出所有文件转化为档案的起始点是不现实的。正如人的特征是具有完全直立的姿态,解放的双手,复杂而有音节的语言和特别发达、善于思维的大脑,并有制造工具、能动改造自然的本领。但是,我们没有要去追求某个人或一些人何时刻具有这一特征,更不能因为某个人或某些人不具有或暂时不具有这些特征而否认他(们)是人,这里不存在人的划分标准的双重性问题。因此,就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问题,从我国档案工作的现实出发,模糊处理比精确界定可能更为适宜。至于《何文》中谈到“设备档案是在设备开箱时就先行归档”[⑦]的问题,并不能说是由档案起始点标准双重性所引起的。因为,这种开箱归档案的做法并不是档案工作中的普遍现象,而是在社会档案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为维护档案的完整性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如果能保证设备随机文件在设备调试安装后归档的完整性,设备开箱时随机文件不先行归档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有不少单位采取了将随机文件先登记后归档的做法,即使设备随机文件先行归档,也只是履行一个手续,档案部门立即进行复印,将复制件或原件交设备部门使用。另外,相对于设备的使用寿命而言,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因此,安装调试结束后随机文件的历史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何文》还提到科技档案修改与传统的强调非现行性的观念相矛盾的问题,对这一似是矛盾的表面现象应作深层次的分析。第一,科技档案的非现行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否则就无法解释对一些研制周期长的科技文件采取分阶段归档的做法,也无法解释科技档案可以更改的问题;第二,科技档案更改时有严格的更改原则、更改方法和更改手续,其中更改通知单是更改的凭证,必需归档保存;为保持更改前的原始面貌,原图作废但不销毁,仍作为档案保存。因此,从科技活动的发展过程看,这种更改仍属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继续,不存在按自己的观点与需要去篡改档案的问题。第三,科技档案与文书档案不同,文书档案所记载的活动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相应的历史记录当然不允许更改。科技档案则不然,它所反映的科技活动仍在继续之中。例如,一项产品研制成功了,还有产品的批量生产、产品的销售服务以及产品的改进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档案具有一定的现实使用性。
关于归档制度问题。在我国确实存在文件归档以后才能成为档案的问题,致使档案部门对部分未归档文件的失控,但这个问题的产生是不是由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所引发的,值得研究。由于我国档案工作延伸到行政管理与科技活动实践之中,在基层档案部门自然会产生文件归档的问题。在文件归档问题上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归档制度执行不力,或归档范围规定不细,或部分工作人员档案意识不强所致。既然问题出在归档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力上,就应该通过强化归档制度和提高人们的档案意识来加以克服。像《何文》中所举土地批租合同遗失一例,一是可以通过随时归档的方法解决;二是可以通过增强有关人员的档案意识来解决;三是可以通过加强归档制度执行力度来解决。因为这位总经理丢失合同之过,责不在归档制度本身,完全是自身档案意识不强所致。至于因这种情况发生在总经理身上而档案部门无法追究其责任,是归档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三
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正确的,但这并非说由此就不会产生矛盾了。比如过分强调档案的历史性,将非现行性的概念绝对化,都是不利于档案工作健康开展的。但因此而把档案概念建立在一般文件或现行文件的基础上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产生文件何时成为档案的问题,造成工作的混乱和思想的不一致。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文档管理一体化在基层单位已是大势所趋。如何实行文档管理一体化及如何设置归档关口等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只是鉴于这方面的实践尚处在初始阶段,有关理论的问世尚需一定时日。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档案是文件运动某一阶段的产物这个结论不会变,档案概念应以非现行性为基础这个命题仍然成立。正因如此,尽管《何文》中的有些论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文章的基本立论是值得商榷的。
注释:
[①][③][④]吴宝康等:《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②]《辞海》第146页。
[⑤][⑥][⑦]何嘉荪:《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合理吗?》,《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