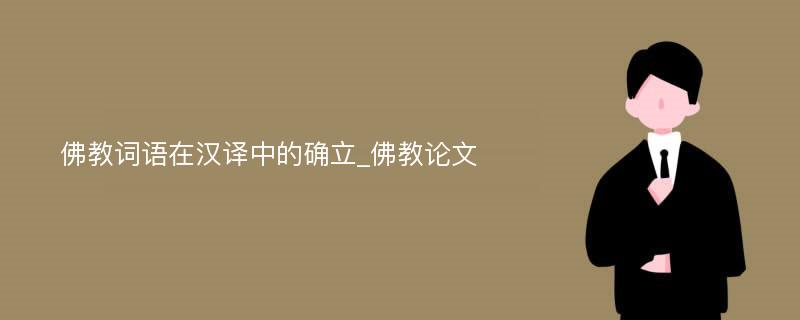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词语论文,汉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组成的“东亚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中国式律令、儒学和中国化佛教。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故东亚文化圈又称“汉译佛典圈”。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或者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如佛性、天堂、地狱、宿命、悲观、觉悟、境界、唯心、世界、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相对、绝对等等;或者融为大众俗语,以至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为佛教词语,如平等、眼光、刹那、缘起、手续、翻译、翻案、方便、大无畏、开眼界、门外汉、一刀两断、一丝不挂、一厢情愿、吉祥如意、对牛弹琴、盲人摸象等等。汉译佛教词语不下一万数千条之多,仅其成语即占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90%以上。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于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透过汉译佛教词语千余年来在印—中、中—日、日—中之间的跨国旅行,可从一个侧面展现“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在东亚史上的意义”。
一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为梵文Buddna音译,后译作“佛陀”,是释迦牟尼称号之一。据季羡林教授考证,汉语文中名词“佛”先于“佛陀”。“佛陀”译自梵文,“佛”译自中亚的吐火罗文,或龟兹文,或焉耆文。这种先后次序,正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先由中亚转折传来,后由印度直接传来。《浮屠经》约指《本起经》、《本行经》等讲述佛陀生平的佛经。从这一史料推断,中国人初知佛教及其经典,约在西汉哀帝(前27~前1年)的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还提到佛陀弟子的各种称号,如桑门(梵文Sramana音译,后译作沙门那,略称沙门,意为勤劳、功劳、修道,指佛教僧侣),比丘(梵文Bniksu音译,指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男僧)。以汉字音译西域或印度佛教词语,是汉译佛教词语的方法之一。
时至东汉初年,佛教逐步传播,人们将其视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71)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表明汉室王公把佛教与黄老术并列对待,楚王刘英还与沙门、居士一起斋戒,为囚犯赎罪,国相认为楚王有异心,上奏汉明帝,而明帝则对楚王的佛事活动取容纳以至赞许态度,其诏书还出现浮屠、伊蒲塞(梵文UpasaKa音译,后译作优婆塞,意为清信士、近善畏,通指一切在家的佛教男信徒,意译“居士”)、桑门(沙门)等汉字音译佛教词语。
佛教正式入华,通常以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为端绪。最早记载此事的是东汉时作的《四十二章经序》,内称:汉明帝遣使求法,并未抵达印度,只到了大月氏(中亚阿姆河上游),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回归。这段文献出现“佛”、“塔寺”等汉译佛教核心词汇。此后,袁宏(328~376)撰《后汉记》、范晔(?-445)撰《后汉书》都沿袭此说。而《法本内传》则另有述说:明帝派遣的求法使者所到地点,除大月氏外,还有“中天竺国”,即中印度,且有印度僧人摩腾(迦叶摩腾的简称)、竺法兰应邀赴汉,以白马驮经和佛像,于永平十年(67)至洛阳。翌年明帝建白马寺安置二僧,二僧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汉译全称《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经》,是辑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的“经抄”。
自东汉永平十年(62)《四十二章经》译出始,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胡僧及中国僧人译著大小乘经、律、论数以万卷。现存汉字佛典3360部,15000余卷,除少数由中国僧人自撰的经论(如《六祖坛经》)之外,大多为翻译作品。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其部数甚至凌驾中国古典之上,而它们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间译出的。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统计,历代翻译佛典的部数及卷数为:后汉永平十年至唐开元十八年(67~730),968部,4507卷;唐开元十八年至贞元五年(730~789),127部,242卷;唐贞元五年至宋景祐四年(789~1037),220部,532卷;景祐四年至元至元廿二年(1037~1285),20部,115卷。唐以后的零星译作,多为旧译佛经的补充,总数仅500卷左右。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将汉末迄唐末八百年间佛典翻译分为三期,一为外国人主译期,二为中外人共译期,三为本国人主译期。
“外国人主译期”多为来华的中亚僧人(如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支谦)、印度僧人(如鸠摩罗什、觉贤)凭记忆背诵梵语、巴利语的经义,然后译成汉文(或有中国人帮助)。这种口诵经文的方式,在古印度也很流行,故佛典的起始句皆为“如是我闻”(我听佛祖这样讲),是一种口诵句式,东晋法显《佛国记》述其状为“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这种译经的不确切处甚多,东晋至唐遂有中国僧人排除万难,西行取经求法。著名者如东晋法显(约337~约422)在印15年,历30余国,得《摩诃僧祢律》、《杂阿含》、《方等泥洹》诸梵文佛典,回国后自译《方等泥洹》;又如唐玄奘(602~664),出游17年,其中在印度15年,携大小乘佛教经律论520夹,657部回国,归唐后19年间译出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
晋唐间的译经事业还形成以某些寺院为中心的译场,设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总勘等职员,分工协作,久历岁月,始成译事。其译主兼有中国人、外国人,此为“中外人共译期”;后来,译主全为中国僧人,此为“本国人主译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译经,主要是后两种形态,所创造的汉译佛教词语,不胫而走,流行于庙堂之上、民众之间,晋唐以降各类文学作品(诗歌、戏剧、小说等)也深受影响。以唐代诗人王维(698~758)为例,其诗文大量采用禅语,他的《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便有“阴界”、“我人”、“趣空”、“因果”、“色声”等汉译佛语,阐发佛教“人我空”观念。王维还自号“摩诘”(“维摩诘”之节文),而“维摩诘”是佛经中一位著名大乘居士的名字。
二
汉译佛典数量在魏晋以降骤增。东汉译经者12人,译本292部,395卷(《开元释教录》卷一);魏晋南北朝译经者118人,369年间译经1621部,4180卷;隋初至唐贞元五年的208年间,译经者54人,译经492部,2713卷(同上,卷一至卷七)。
随着汉译佛典的大规模展开,东汉时以音译佛教词语为主的方法,到魏晋以降已发展为音译、意译并用,而且意译有后来居上之势。所谓“改‘胡音’为汉意”,如把《摩诃般若波罗密经》。意译为《大明报经》。有些译者还将道家术语比附佛学术语。鸠摩罗什(343~413)倡导以意译为主的译风,对这一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意译为主的译风,又与魏晋间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形上学的执着追求有关。倾心思辨的魏晋士人除从《周易》、《老子》、《庄子》等“三玄”中开掘形上之学以外,也注意于从形上学发达的佛学中汲纳思想资源;与此同时,佛教僧侣借助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及语汇,阐发佛学精义,以实现佛教的中国化。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结果之一,便是佛学的玄学化、道家化。玄学贵无,以“无”为中心问题,认为世间万物皆由“无”派生出来,老子的“无为”成为玄学的核心概念。中国的玄学之士和佛教僧人还以此诠释大乘佛教关于“空”的教义,用中国固有学术名词“格义”佛教概念。所谓“格义”,是用中国原有概念比附、翻译佛典名相,如安世高以“无”译“空”,以“无为”译“涅槃”,以“生死”译“轮回”。东晋僧人道安(314~385)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语汇注释《般若》、《道行》、《密迹》诸佛经,《高僧传》赞其劳绩:“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道安的释经之所以能“条贯既序,文理会通”,原因之一便是他善于以中国传统词汇阐释佛理。他宣讲般若学说时,便以“寂寥无言”、“恍忽无形”、“睹末可以达本”、“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等《老子》中的句式表述,从而用一系列汉字旧词意译佛教理念。魏晋以降,中国人对于佛教词语除以汉字音译(直译)外,又另辟意译一途。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种译经趋向。
被认作中国第一篇论翻译的文字,是三国人支谦所撰《法句经序》,内称: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节录自《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支谦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是一种直译主张,但他又有“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之说,这是追求通俗易懂与忠于原义的统一,为意译留下余地。该文以《老子》语句比拟经义,表现了用中国古典阐释佛典的意向。
隋唐的佛典翻译又自有特色:其一,改变魏晋间节译、选译之风,而多译全集,所据文本也不像魏晋时用西域胡本,而是印度梵本;其二,强调忠于经典本义,摆脱魏晋时译经的“格义”作法,其对佛教词汇的翻译,又由意译转向直译(音译),但因意译当时已深入人心,唐人译经往往取音译、意译结合的办法。
1931年,鲁迅在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曾将中国的佛教翻译历程概括为三段落;“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1](P381)。这里所谓“汉末质直”,指东汉译佛典尚直译(音译);六朝“达”而“雅”,译佛典走的是意译一途,唐代以“信”为主,则是以直译为基本,参以意译。
经过汉唐800年努力,汉译佛典成蔚然大观,其间创制了大量汉译佛教词语,仅以正史而言,汉译佛语便所载甚多,如《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中便有舍利、桑门、般涅槃、阿育王、须陀洹、斯陀含等不下数十百条;见于宋、齐、梁、陈、隋书及南北史者,更不可胜数。历朝所传别集,征引佛典甚多,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等人文集中,汉译佛语使用频率颇高。汉译佛语构成近代西学入华以前数量最巨大的外来语群体,人们张嘴说话,便自觉不自觉地讲出佛语,如世界、平等、现行、清规戒律、十字街头、少见多怪之类。赵朴初说:“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2]这是毫不夸张的平允之论。仅从创制汉译佛语而言,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便可谓大焉。
三
东汉以降,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间形成的汉译佛教词语,其翻译方式约分三类:直译(音译)、意译、梵汉合璧,它们各以自身的特色为汉字文化圈各国人民所采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赢得了生命活力,发挥出巨大的文化功能。其中音译与意译是基本的两种方法,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对两法作了颇精当的说明——“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此为意译;“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由旬’等”,此为音译。
甲、直译(音译)
翻译佛教词语时,汉字扬弃其意义,仅充作记音符号,此谓直译或音译。这种翻译方法,在东汉至唐代的佛典翻译中占重要地位。宋代法云的《翻译名义集》收词2040条,其中音译约2000条,占绝大部分。直译佛教词语又分全译、节译两类。全译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梵文mahaprajnaparamita),大慧到彼岸;波罗蜜多(Paramita),达彼岸;僧如蓝摩(Samghagarama),寺院;一阐提(IochantiKa),不能或不想成佛的人;比丘(BhiKchu),僧人;比丘尼(BhiKchuni),女僧;支那(cina),中国;悉昙(Sid-ha),梵文字母总称;瑜伽(Yoga),思维;菩提(Bohki),觉、智;头陀(Dhatu),行脚僧人。节译指对全译的简约,以适应汉语构词习惯,便于流传,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天上正等正觉),节为“阿耨三菩提”;摩诃衍那(大乘),节为“摩诃衍”;设利罗(佛的骨身),节为“舍利”;罗刹婆(恶鬼名),节为“罗刹”;阿罗汉(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节为“罗汉”;浮图(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节为“佛”;波罗蜜多(到彼岸),节为波罗蜜;僧伽蓝摩(佛寺),节为伽蓝。这些节译词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惯用词汇。
乙、意译
扬弃外来语固有语音,用汉语单字按汉语构词法构造新词,以表达外来语的词义,此谓意译。魏晋南北朝、隋唐间翻译的佛教词语,意译词甚多,其主要造词方法有比喻和汉词佛化二种。
其一,比喻造词法。比喻是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由于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往往有类似点,可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此即“比喻”。比喻的成立,包含三要素: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类似点。因此比喻在形式上就有正文(本体)、比喻(喻体)、比喻语词三成分。以这三成分的异同及隐显,比喻可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汉译佛教词语中的比喻造词法,主要用明喻、借喻二类,表明喻体与本体相合关系的隐喻很少使用。
(一)明喻,表明喻体与本体的相关关系。如以“法”为本体的意译佛词有法门,指通过习修佛法获得佛果的门户,《法华经·方便品》:“以种种法门宣示佛道”;法印,意谓印证是真正佛法的标准,佛教有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四法印(三法印加“一切诸行苦”)、五法印(四法印加“一切法空”)之说;法轮,对佛法的喻称:佛之说法,如车轮旋转不停,法雨,喻佛法如雨润万物,普利众生。以“心”为本体的意译佛词有心所,谓相应于心王而起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现象,为心所有;心田,人所行业(善或恶)的种子随各人之缘在心内滋长,如田地既长五谷又长稗荑;心花,众生本心清净如花;心眼,心如眼能洞察诸法。以“爱”为本体的意译佛词有爱火,情爱如火;爱河,情欲如河水溺人,《楞严经》有“爱河干枯,令汝解脱”之说。以“智慧”为本体的意译词有智慧剑,智慧犹如利剑,能斩断烦恼,绝生死绊。以“烦恼”为本体的意译佛词有烦恼贼,烦恼犹盗贼,能损慧命,伤法身。
意译明喻佛词的本体词,主要有法、色、身、见、染、空、性、业、缘、识、智慧、解脱、烦恼等,其喻体多为形象事物名词,如剑、箭、刀、鼓、雨、田、林、云、水、镜、花、海等。通过比喻,使本体抽象的佛教概念,经与形象的喻体结合,达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效果。
(二)借喻,喻体与本体的关系比明喻、隐喻更为密切,故不写本体,只用喻体来作本体的代表。如电影,以电光之影的神速、变幻,比喻“诸行无常”,“万法皆空”;兔角、龟毛,兔本无角,龟不生毛,以之比喻佛法“空”理;火宅,谓人世间之苦难如燃火之屋;火炕,喻指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众生于此受无量煎熬;根器,喻人之禀性各有差殊,故佛因人的类别不同采取不同手段说法。
其二,汉词佛化。藉助汉语的固有词汇,表述佛教术语的含义,即所谓“汉词佛化”。其方法有二。
(一)直接借取。如功德,原出《札记·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借指佛教的施善(“功”)得福报(“德”);寺,原指中国官署,如鸿胪寺、太常寺等,借指佛教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处所;天道,原出《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指自然规律,借用为佛教译词,指“六道”中最高妙的境界。
(二)引申。对原有汉字词的含义加以引申,或增其抽象义,如解脱,汉语旧词意为开脱、免除,佛教译词引申出解除烦恼业障达到自由境地的含义;思惟,汉语旧词原义思念,佛教译词引申出能造作身、口、意三业的精神作用,《观无量寿经》:“教我思惟,教我正受”,其“思惟”颇接近于现代心理学上包括分析、综合、推理等高级思想活动的“思维”。或增加比喻义,如羊角、羚羊角,在汉语旧词中本指具体事物,佛教译词则引申出烦恼义,以至坚的羊角、羚羊角比喻烦恼,可攻坏佛性。
关于音译、意译的选择,唐代玄奘发表过“五种不翻”的意见。即五种情况不得用意译,而必须音译。宋代僧人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十种通号》对玄奘的意见概况为:玄奘认为原词含义秘密,不意译;原词无中国对应事物,不意译;经师传承的音译,不再意译;原词含令人尊崇的奥义,不意译。这“五种不翻”之说,坚持了翻译的严肃性,使音译与意译得以并存互补。
丙、梵汉合璧
一个译词由音译和意译两部分组成,谓之“合璧词”。汉译佛教词中,不少是一半为梵音汉字,一半为汉语意汉字,此谓“梵汉合璧词”。略分四类。
(一)梵音字加汉字类名。如佛事,“佛”为梵音词“佛陀”节文,“事”,为汉字类名;佛经,“佛”为梵音汉字词“佛陀”节文,“经”原指五经等中国经典,转用于对佛教经典(梵文音译“修多罗”)的类称。
(二)汉字词加梵音字。如念佛、卧佛、法身佛、未来佛、现在佛、应身佛,参掸、坐掸、野狐禅,高僧、云水僧,等等。这些梵汉合璧词,都是后“梵”为主体,前“汉”作修饰。
(三)新造译字加汉字。如魔王,“魔”字为梵文Mara音译“磨罗”的节文,南朝梁武帝改“磨”为“魔”,指能恼人、害人的鬼怪。“魔”与汉字“王”合璧为魔王,指鬼怪头领。
(四)梵汉同义、近义连用。一类为梵汉同义复用,如僧侣,“僧”为梵语“僧伽”节文,意为“众”;“侣”为汉字词,意为“同伴”,也表多人,僧侣连用,意为“众僧”。此外,僧众、僧徒亦属此类。二类为梵汉近义相补,如禅定,“禅”是梵语“禅那”节文,意为“静虑”,“定”为汉字词,意为静定,二字义近互补,成“禅定”,指通过精神集中而获得悟解的一种思维修习。忏悔,“忏”为梵语“仟摩”节文,忍耐意,被误作悔过意,“悔”为汉字词,改过意,二字义近互补,成“忏悔”,指对人自揭其过,以求取宽恕,乞以悔改之义。
佛典既精于思辨,又长于形象,二者都深刻影响了中国语文。佛典中反复叮咛、高度夸诞、玄想的表现手法,倒装句、提缀语的大量运用,都成为中国语文的新因素。其集中体现,便是主要创作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译佛教词语,大大丰富了汉字词汇量和表达能力,而且为以后的汉译外来语树立了方法范例。中国近现代翻译西方词语的方法,也大体沿用汉译佛词的三种方法:音译(如华尔兹、布尔什维克、纽约、伦敦之类),意译(如革命、观念、价值之类),汉外合璧(如加农炮、香槟酒、雪茄烟、酒吧间之类)。这可以视作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在时间相度上的纵向深远影响。
四
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还有空间相度的横向广阔影响。其时的中国对于日本等东亚国家,是一个“文化输出国”,诚如唐玄宗诗云:“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全唐诗逸》卷上,第1页)
佛教在南亚次大陆创生,渐次由南传、北传两条线路播散到东南亚、中亚和东亚,成为一种世界宗教。北传佛教入华后,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融合,逐渐演变为中国化佛教,大量汉译佛教词语于魏晋南北朝隋唐间产生,并渗入中国学术和社会生活之中,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这些汉译佛教词语又传入其他国家,如缅甸语中的“南无”、“罗汉”、“佛爷”,印度尼西亚语中的posat(菩萨)、huisio(和尚)等,即借自汉译佛词。汉译佛教词语更重要的影响地区是东北亚诸国。中国化佛教在公元4、5世纪传入朝鲜半岛,继之又经朝鲜半岛传往日本列岛。撰于12世纪的日本史籍《扶桑略记》卷3称,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即中国南北朝时期,汉人司马达止抵大和,在坂田原建立草堂供奉佛像,此为日本民间奉佛之始,日本史学界则以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向日本朝廷进献金铜佛像、幡盖、经纶为佛教传入日本的开端,时间约在钦明天皇七年(546)。圣德太子(547~622)深信佛教,相传曾发愿往生极乐净土,他推行新政,诏令“兴隆三宝”(“三宝”为佛、法、僧,代指佛教),佛教在日本迅速传播。至奈良时代,《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等汉译佛典被尊为“护国”经典。随着大批汉译佛典传入,汉译佛教词语也在日本广为流行,构成日本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时人望月信亨(1869~1948)编纂的《佛教大辞典》收词35000条,多为汉译佛教词语,展示了主要创制于魏晋南北朝隋唐间的汉译佛教词语在日本语文中庞大的阵容。2000年4月,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佛教辞典》,其凡例称“佛教用语浸透了日本文化”,这“浸透”一语颇为传神。
汉译佛语大量进入日本语文,以至天皇诏书中多有“法恩”、“三宝”、“福业”、“法界”、“知识”等汉译佛词,一些贵族的汉文著作中也充满了此类词汇,如醍醐天皇的第16皇子兼明亲王所撰《供养自笔法华经愿文》不到300字,即有汉字音译佛词观世音、菩萨、释提桓因、毗沙门,有汉译佛典名称《妙法莲华经》、《开结经》、《般若心经》有意译佛语无畏道场、鸳峰之偈,梵汉合璧佛语须弥山、桑门之侣,佛化汉词有为之乡、无边之界、同应方赤、共期圆明等[3](P72)。日本的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也显示出汉译佛词的影响。《万叶集》卷五中的日本第8次遣唐使少录,著名歌人山上忆良的《思子等歌》便有“释迦如来,金口正说,等思众生”句式,其《悼亡诗》则有“爱河波浪已先灭,苦海烦恼亦无结。从为厌离此秽土,本愿托生彼净刹”句式,“爱河”、“苦海”、“烦恼”、“秽土”、“本愿”、“净刹”皆为汉译佛语,表明汉译佛词流行之广。
在西化盛行的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汉文学诗作仍多用汉译佛语,如小野湖山作于明治十一年(1879)的《华严瀑布歌》,由对日光晃山瀑布壮美的描写,引申出对“佛有诸宗,华严居第一”[3](P139-140)的赞颂,汉译佛语构成全诗的中坚概念。
日本僧人的佛学著作,当然更是以汉译佛语为基本词汇,日本天台宗大师原信(942~1017)的《往生要集》充满汉译佛语,如“净土极乐”、“浊世末代”、“利智精进”等。
汉译佛语在中日之间并非单向传播,而是双向互动的。汉译佛语由中国流往日本,已如上述;汉译佛语由日本逆输入中国,则发生在近现代。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成为学习西洋现代文明的“模范生”,其在译介西洋学术文化的过程中,用汉字佛语翻译西洋术语概念是方法之一,而这些以佛语翻译的西洋术语概念又传播到中国,衍为中国现代语汇的组成部分。例如,唯心,本为汉译佛语,出自《华严经·夜摩宫中偈赞品》:“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日本人借“唯心”一词作idealism的意译,后被中国沿用,成为一个基本哲学概念。又如知识、实体本来皆为汉译佛语,日本人借以作Knowledge、Substanti的意译,后逆输入中国,成为现代中国的重要新词汇。有些汉译佛词创自中国,但未在中国普及,传入日本方得流行,再由日本转输中国。如手续,一般以为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外来语,其实本为中国土产,见于佛教密宗仪轨抄本。密宗修持,重视次第(即程序),每一次动作次序谓之“手续”。“续”有继续、相继义,密法修持讲究“三密(身密、口密、意密)相应”,其中“身密”即结手印,手印(手势)的后续动作称“手续”。密宗于唐代从印度传入中国,不久由日本留学僧空海(774~835)、最澄(767~822)分别将密法带回,“手续”一词随密法流行而在日本普及。近代又由日本逆输入中国。汉文佛书在中日之间双向传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唐沙门慧琳著《一切经音义》(又名《慧琳音义》)在中日间的互动。该书录玄应、慧苑各家音义,编纂成书,博引古代韵书、字书及佛典,共解释1300部、5700卷佛经的音义,是一部大型佛教辞典,五代时期失传于中国。高丽国从契丹获此书,又传入日本,珍藏于西京建仁寺、东都缘山寺。江户时期日本僧人狮子谷徵上人、狮谷宝洲等将其校勘付梓,时在清乾隆二年(1737)。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佛学家丁福保(1874~1952)奉两江总督端方及盛宣怀之命,赴日本调查医学及养育院事宜,在东京旧书肆寻得中国已逸经典,获《慧琳音义》及其续编,这部佛教词语书方逆输入中国。而此书在中日之间的互动,是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传播的实证,同时也是隋唐文化在中、朝、日等东亚各国发生影响的实证。
主要完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汉译佛语,构成汉字文化圈的一大词汇来源,中国、日本均受惠无穷。汉译佛语因内涵丰富,表现力强劲而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不仅在千余年的历史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现代新语文的更张中继续崭露头角。关于这些论题的研究,有助于对东亚文化史认识的加深与拓宽,本文如能成为这方面的引玉之砖,则不胜欣幸。
标签:佛教论文; 日本佛教论文; 汉字演变论文; 汉字文化圈论文; 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南北朝论文; 释迦牟尼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佛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