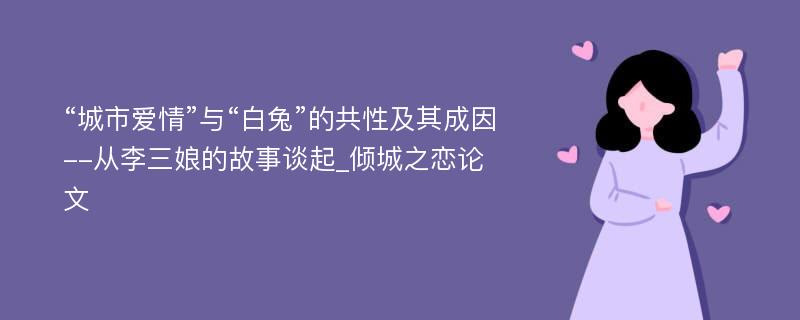
论《倾城之恋》与《白兔记》之间的共通性及其成因——从“李三娘故事”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通性论文,成因论文,白兔论文,之恋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年,张爱玲亲自将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当年12月16日,此剧在上海新光大剧院上演。上演持续一个月,共演80场,票房大卖,好评如潮。张爱玲对此剧非常重视,倾注了相当的精力,在《倾城之恋》排练期间,她曾前往排练现场观摩。在观看了“白流苏”一角的扮演者罗兰的表演后,张爱玲写下了《罗兰观感》一文。文中,张爱玲道出了《倾城之恋》的故事渊源,她说:“《倾城之恋》的故事我当然是烂熟的;小姐落难,为兄嫂所欺凌,‘李三娘’一类的故事,本来就是烂熟的。”① 张爱玲提及的“李三娘”,历史上实有其人,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妻子。欧阳修主持撰写的《新五代史》卷十八《汉家人传第六皇后李氏》中记叙了她的出身:“高祖皇后李氏,晋阳人也,其父为农。高祖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夜入其家劫取之。”②史笔是简略的,等到宋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出现,“李三娘故事”才得以完整。经过《新编五代史平话》的渲染增色,李三娘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目前已知的表现李三娘故事的戏剧作品有《刘知远诸宫调》(尚存残本)、杂剧《李三娘麻地捧印》(失传)、南戏《刘知远白兔记》等,这其中又以元代永嘉书会才人所编南戏《刘知远白兔记》(以下简称《白兔记》)最负盛名。此剧与《荆钗记》《杀狗记》《拜月亭记》并称“四大南戏”。自17世纪至20世纪,各地方剧种仍纷纷以《白兔记》为蓝本不断地将李三娘故事搬上舞台,至1939年,民国时期著名导演张石川还将李三娘故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李三娘》。 一 “落难—偶遇—团圆”:情节模式上的共通性 《白兔记》今存最早剧本是明代成化年间刊印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此剧在《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基础上强化了李三娘在刘知远离开后遭受种种磨难的情节,如“兄嫂凌逼,绝不改嫁”,“日间挑水无休歇,夜间挨磨到天明”③,“磨房生子,自咬脐带”,“思念孩儿,终夜难眠”等,这些“苦情戏”皆可以归入“丈夫离去,妻子落难”(以下简称“落难”)的情节类型之中。在元末明初产生的戏剧作品中,“落难”情节颇为常见,除《白兔记》之外,在《琵琶记》《荆钗记》等经典戏剧作品中也都有相似的情节,可见这一情节类型十分受当时观众的欢迎。除了添加了大量的“苦情戏”,李三娘故事的传奇性在《白兔记》中也得到了增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井台相会”这一幕中:一日李三娘正在井台打水,跑来一只带箭白兔,后有一小将追至,小将正是李三娘十六年前在磨房所产之子咬脐郎。咬脐郎在与李三娘搭话中发现眼前的妇人正是自己的生母。对于上述具有传奇性的情节,我们将之归入“偶遇”的情节类型。一般来说,“偶遇”给身处困境的主人公带来希望,实现了主人公命运从逆境向顺境的转换。李三娘与其子咬脐郎偶遇后,咬脐郎将母亲的不幸遭遇告诉了刘知远,并最终促成刘知远接回李三娘。夫妇、母子终得团聚。这段情节显然属于中国传统戏剧作品中常见的“团圆”类型。综上所述,《白兔记》戏剧的情节模式可以归纳为“落难—偶遇—团圆”。 当其幼时,张爱玲就已经将这一情节类型运用到自己的小说中了。在谈及儿时创作时,张爱玲回忆道:“我还记得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关于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便乘机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写到这里便搁下了,没有再续下去。”④显然,上述故事是一段典型的“丈夫离去,妻子落难”的情节。虽然这篇小说没有写完,但参照其开篇的“落难”情节,其通篇很有可能也将遵循《白兔记》中“落难—偶遇—团圆”的情节模式。 事隔多年,《白兔记》的情节模式完整地出现在小说《倾城之恋》中。在开篇处,张爱玲就叙述了一段现代版的“丈夫离去,妻子落难”的情节:作为弃妇的白流苏,离婚后久居娘家,年近三十的她日日被兄嫂羞辱欺负。和《白兔记》一样,张爱玲也以浓墨重彩描画了白流苏“落难”的景况,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都相当传神。张爱玲曾说:“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⑤“落难”情节之后便是“偶遇”:几近绝望的白流苏,在她人的相亲约会上邂逅范柳原——一位富裕的海外归侨,并得到范柳原的“垂青”,从此命运转变。《倾城之恋》中的“偶遇”情节更加复杂,可谓是双重的“偶遇”。一重是白范之间的爱情“偶遇”,一重是二人在即将分离之际与战争的“偶遇”。第二重“偶遇”极富传奇性,因为范柳原本不欲与白流苏厮守,恰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引出了二人最终“团圆”的结局,诚如张爱玲在小说末尾所说的:“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⑥综上所述,《倾城之恋》与《白兔记》一样,都采用了“落难—偶遇—团圆”的情节模式,具有共通性。 张爱玲为何要将《白兔记》中“烂熟”的情节模式运用到现代小说《倾城之恋》的创作中去呢?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吸引读者。张爱玲化《白兔记》的情节模式入《倾城之恋》,这实际是为了使自己的小说能更易于进入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对于这一点,张爱玲曾说:“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⑦可以说,“历代传下来的老戏”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感情的公式”,也留下了不少情节模式。和“感情的公式”一样,小说中出现读者因观看传统戏剧而熟悉的情节模式更易于引起他们阅读的兴味。另外,在阅读过程中,因为读者对故事的情节模式比较熟悉,其注意力也易于超越对情节的单纯关注,在古今故事的参照对读中从关注情节转而关注人物,并从对人物的关注中更深刻地领会张爱玲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感情。 二 逆境中的弃妇:人物形象上的共通性 在《罗兰观感》一文的最后,张爱玲写道:“流苏与流苏的家,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现社会里还是到处有的。就像现在,常常没有自来水,要到水缸里舀水,凸出小黄龙的深黄水缸里静静映出自己的脸,使你想起多少年来井边打水的女人,打水兼照镜子的情调。”⑧张爱玲以“古中国的碎片”形容“流苏与流苏的家”,这可以理解为她在提醒读者,将《倾城之恋》的人物形象及其生活环境纳入传统与现代的参照中体认领会。“井边打水的女人”是张爱玲推荐给读者进行古今参照的传统人物形象,而这一人物形象显然取材于《白兔记》中日日在井边打水的李三娘。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张爱玲在塑造《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形象时受到了《白兔记》的影响,而李三娘和白流苏这两个形象之间存在着共通性。 参考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人物类型划分,《白兔记》中的李三娘可以归入“弃妇”这一类型。中国文学中最早的弃妇形象出现在《诗经》中如《卫风·氓》《邶风·谷风》《邶风·柏舟》等作品里。在《倾城之恋》发表半年后,1944年4月,张爱玲在《论写作》一文中指出:“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诗上的。”⑨《邶风·柏舟》一诗的叙述者是一位被丈夫抛弃,又遭众妾及自己兄弟羞辱的弃妇。身处逆境的弃妇在诗歌中抱怨自己“亦有兄弟,不可以据”,终日“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⑩将《邶风·柏舟》的叙述者、《白兔记》中的李三娘以及《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相互对比,她们在遭遇和心理上呈现出不少相似性。由此可见,张爱玲确是基于弃妇这一人物类型来塑造白流苏的,而“逆境中的弃妇”便是《倾城之恋》与《白兔记》在人物形象上具有的共通性。 因为《邶风·柏舟》在叙事上的不完整性,张爱玲对这首诗的借鉴程度有限,只是“如匪浣衣”一句对于张爱玲体察弃妇的心理活动具有一定的启发。(11)相比之下,《白兔记》中的李三娘才是她塑造白流苏形象的重要参照。由于《白兔记》是一出戏剧,李三娘是戏剧角色,这使得深受《白兔记》影响的张爱玲,在白流苏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中揉入不少戏剧人物所具有的特征。试观《倾城之恋》中如此的描写:“阳台上,四爷又拉起胡琴来了,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12)在胡琴的伴奏下,依着曲调“飞眼风”、“做手势”,合着音乐的节拍“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这些动作描写明显取材于中国传统戏剧表演,而白流苏这一人物形象也因此散发出旦角的气质风范。 也许是为了让读者体会到白流苏人物形象与戏剧角色的共通性,在《倾城之恋》的开篇,张爱玲将《倾城之恋》定位成“胡琴上的故事”,并特意指出“胡琴上的故事,应当由光艳艳的伶人来扮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13)由此可见,在张爱玲的创作意图中,《倾城之恋》应是一篇富于戏剧性的小说,其中的女主人公应该具有戏剧角色的特征。为了提醒读者这一点,她还特意借范柳原之口对白流苏评价道:“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14) 张爱玲之所以在白流苏这一人物形象中灌注了中国传统戏剧中旦角的气质风范,戏剧文本的影响固然重要,另一影响当是源于她观看的《白兔记》戏剧演出。在欣赏了俗称“蹦蹦戏”的评剧所搬演的《白兔记》戏目《井台会》(又名《咬脐郎打围》《李三娘打水》)后,对于“评剧皇后”朱宝霞塑造的李三娘形象,张爱玲认为其中生动地展现出弃妇在逆境中特有的执着和韧性,她感慨道:“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15)在张爱玲看来,白流苏正是一个“蹦蹦戏花旦”似的弃妇,虽身处逆境,却最终“能够夷然地活下去”。为了让读者体会到她对白流苏形象的理解,1944年12月,在发表于《海报》的《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写道:“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16)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正是《白兔记》戏剧表演加深了张爱玲对于“逆境中弃妇”的感悟和思考,并让她在白流苏形象中增添了传统戏剧旦角的气质风范。 三 苍凉的意味:美学风格上的共通性 夏志清就中国传统戏剧与张爱玲小说在美学风格上的共通性曾有如是一段评析,他说:“她喜欢评剧……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17)的确,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上,张爱玲的小说当然是现代的,但是诚如夏先生所言,就美学风格来说,张爱玲的现代小说却与传统戏剧在“苍凉的意味”方面是共通的。 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文中,以西方悲剧为典范,傅雷高度赞扬了《金锁记》,他说《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最完满之作”,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8)与作为悲剧的《金锁记》相对,《倾城之恋》则是一出“传奇”。傅雷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作为“传奇”的《倾城之恋》,他说:“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至于《倾城之恋》中的人物形象,傅雷以悲剧人物为标准给予了轻蔑的评价,他说:“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总而言之,傅雷认为《倾城之恋》是一部“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的作品。(19) 同月,在《新东方》第9卷第4、5期合刊上,张爱玲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一文。文中,张爱玲首先将傅雷尊崇的悲剧的美学风格定位于“悲壮”,然后标榜“苍凉”的美学风格与之相抗。张爱玲表示:“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对颜色特具敏感的她就其对“苍凉”的偏爱阐释道:“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20)显然,这是张爱玲就傅雷说《倾城之恋》“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诸语提出的含蓄的反驳。对于傅雷认为《倾城之恋》的人物形象都是“浑身小智小慧的人”一语,张爱玲干脆明确表示自己的小说所欲描写的正是这些“不彻底的人物”,她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张爱玲说自己喜爱这些人物,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1)。 或许是因为早就发愿要为上海人写一本《传奇》(22),但或许更是因为不满于傅雷对于“传奇”的贬低,张爱玲最终使用《传奇》命名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1944年8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杂志》月刊社出版,初版四天之内便销售告罄,可谓大获成功。距离初版仅一个多月,《传奇》小说集再版,张爱玲为此写了《传奇再版的话》一文。文中,张爱玲用去近一半的篇幅叙述她观看评剧《白兔记》之《井台会》一出的感受。这一颇为反常的现象暗示了《白兔记》与《传奇》小说集之间存在着的关联。 《井台会》开场时胡琴演奏风格引发了张爱玲丰富的联想,她描述道:“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嘎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23)无独有偶,《倾城之恋》也是在胡琴的“伴奏”中开篇的,其文如下:“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24)分析上引段落,我们认为这是张爱玲在暗示读者,在美学风格方面,《倾城之恋》与评剧胡琴的演奏之间存在共通性,而她既然将《倾城之恋》视作一个“苍凉的故事”,那么这一共通的美学风格显然就是“苍凉”。在《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更明确指出作为“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倾城之恋》所欲表现的正是“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25)。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张爱玲在《传奇再版的话》中以大量的笔墨叙述对《倾城之恋》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白兔记》戏剧,其实质是含蓄地表达出整部《传奇》小说集呈现出的美学风格即是“苍凉”,以此再次回应傅雷对《倾城之恋》提出的批评。因为在张爱玲心中,《倾城之恋》是最能体现她“苍凉”美学风格的作品。 四 传奇文类观念:共通性的成因 在《传奇》小说集初版的扉页上,张爱玲以自己喜爱的孔雀蓝色印了两行题签:“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是张爱玲对于书名《传奇》所作的解释。这句话在日后的张爱玲研究中被反复征引,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主题研究的重要佐证。在这里,我们拟另辟蹊径,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剧的关系角度对于“传奇”之名作一番考证,以此探寻《倾城之恋》之所以与中国传统戏剧《白兔记》具有共通性的成因。 “传奇”一名由来已久。有学者指出传奇原是元稹创作的小说《莺莺传》的初名。(26)此后,裴铏又取其作为小说集名,传奇便逐渐成为了唐代短篇文言小说的总称,即唐传奇。自宋代至清代,传奇同时也可指称长篇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就曾被目为传奇。(27)小说之外,传奇又兼指诸宫调、杂剧、长篇戏曲等戏剧形式。可以说,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传奇是兼融小说和戏剧两大文学门类的统称概念。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小说概念自西方舶来,影响巨大,但中国文学传统中兼融小说与戏剧于一体的传奇文类观念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并未顿消。在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他们的小说文类观念实际与传奇文类观念一致。1897年严复、夏曾佑发表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一文,其中称:“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28)将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作为戏剧的《西厢记》、“玉茗堂四梦”等作品统称为“稗史小说”,这种分类法中折射出的正是传奇文类观念。 另外,在1902年《新小说》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梁启超也将作为小说的《水浒传》《红楼梦》和作为戏剧的《西厢记》《桃花扇》并举,以此论述小说所具有的“熏染刺提”功能。(29)直至1917年,在《告小说家》一文中,梁启超仍表现出对小说概念的“传奇”式理解,他说:“盖全国大多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西》;言哲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厢》。”(30)显然,在梁启超的意识中,小说即传奇,因此《红楼梦》与《西厢记》皆属同一文类范畴。另外,梁启超以“言情绪”为《红楼梦》与《西厢记》的分类标准,其中体现出的是“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31)这样的传奇文类观念。 时至20世纪40年代,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传奇文类观念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这一影响的发生,张爱玲应该是自觉的。秉持“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32)之念的张爱玲,深知只有“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才“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33)。对于自己的目标读者群——普通市民而言,张爱玲深知他们最喜闻乐见的便是传奇,她甚至不无抱怨地说这一读者群“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虽然,成名后的张爱玲曾表示“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戏无餍的欲望”(34),但是在初登文坛之时的她看来,“作文的时候要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35)在这样的创作思想主导下,面对深受传奇文类观念影响的读者群,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融入戏剧特别是中国传统戏剧的因素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作为现代小说的《倾城之恋》与中国传统戏剧之间的共通性也由此应运而生。 注释: ①⑧⑨(15)(16)(20)(21)(23)(25)(32)《张爱玲全集·流言》,张爱玲著,止庵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5、82、158、192、186、186、156~157、193、156页。 ②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页。 ③毛晋编《六十种曲》,第十一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3页。 ④《存稿》,《张爱玲全集·流言》,第70页。 ⑤(11)(33)(35)《论写作》,《张爱玲全集·流言》,第83、82、80、80页。 ⑥(12)(13)(14)(24)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倾城之恋》,止庵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167、160、183、160页。 ⑦《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全集·流言》,第11页。 ⑩《诗经注析》,程俊英等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3~64页。 (1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18)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阅读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气》,陈子善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9)陈子善编《阅读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气》,第9~10页。 (22)参见《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全集·流言》,第5页。 (26)参见周绍良《〈传奇〉笺证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1980年版。 (27)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题下注称:“传奇《红楼梦》八十回后,俱兰墅所补。”(见张问陶《船山诗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7页)由此可知,当时人也以“传奇”称《红楼梦》。 (28)(29)(30)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2~43、89页。 (31)《吴仪一批评本〈长生殿〉·自序》,(清)洪升著,明才校点,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4)《太太万岁题记》,《张爱玲全集·流言》,第278页。标签:倾城之恋论文; 李三娘论文; 文学论文; 白兔论文; 红楼梦论文; 张爱玲论文; 新编五代史平话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傅雷论文; 白流苏论文; 井台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