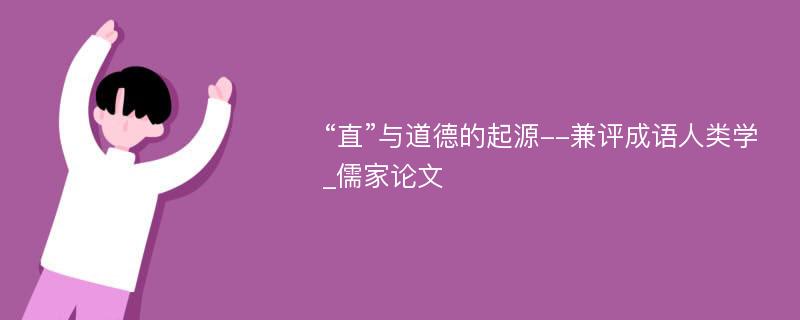
俗语“直”与道德的本源——俗语人类学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俗语论文,人类学论文,本源论文,札记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探索庄子的思想根源时,我曾这样推测,不仅庄子一书中的“许多奇异事物”,“还有庄子的‘道’……等我们以为高度抽象的概念,而在那个时代,可能也就是极普通的词语,很好理解”。里面并没有“玄之又玄”的东西,不过都是依据原始思维而做出的“忠实的叙述”。(注:参看拙著《中国诗哲论》,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页。)而这样推测的基本前提,就是原始思维抽象能力弱,直观性强,因此很难想象古人会进行比我们现代人更复杂的逻辑筹算。它们在今天之所以变得艰涩、精深,主要是思维方式不同而引发的,或者说是理性思维在以自己的原则去解释原始人的精神产物时,“把经念歪了”,否则很难想象古代哲人会那样有意识地把语言搞得如此不透明。
讲思维方式的对立,实际上主要矛盾发生在原始思维与文明人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因为后者的建构正是建立在对前者的破坏、革命基础上,不仅在社会形态方面,在精神意识方面亦如此。而我们现在所接受、所学习的古代文化遗产,恰是经过文明时代意识形态过滤、加工改造后的东西,古代文本所以变得不透明,与此直接相关。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古人沟通的困难,恰是文明的意识形态本身所造成的,而真正的交流,也必须首先越过这层精神障碍。如同心理学家认为个体的潜意识中沉淀着种族的集体无意识、沉淀着远古祖先的已无意识化了的“意识”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在文明时代中,在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那些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原始思维和文化之谜的正确答案。这个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领域,也就是我们平素所谓的民间文化。它在人类文化结构中的位置,正相当于潜意识在个体意识结构中的位置。
这种民间文化主要有两层,一是指尚停留在原始社会形态中,作为文明的异质形态而残存的原始部落文化,或与主流文化的发展并不同步的一些边远区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二是指已进入文明世界中的半氏族的、半农业的异质文化,这些文化与原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民间文化表现在文化模式上,则是人类学家所研究的种种仪式、图腾等,比如中国古代典籍上讲的一些婚葬仪式,至今还可从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中得到正确的解释。而民间文化表现在语言中,则是大量的俗语、方言,这些俗语、方言作为一种通过口耳世代相传、横越古今的“文化遗留物”,也与原始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使得我们所谓的“俗语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得以确定下来。许多古代重要的文字、概念、观念等,在意识形态中往往越讲越乱,越讲越糊涂,而其本源,却可能仍停留在民间的口语、俗语和方言中。本文拟从俗语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道德”这个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的本源。
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道德”在古代典籍中的本义。据文字学家的考证,春秋之前并无“道德”一词,“道”与“德”本是两个独立的词。“道”本义指“道路”。“德”的原始含义是指“人的具体行为”,“与巡视、选择道路的行为有关”。(注:张持平、吴震《殷周宗教观的逻辑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关于这一点, 还可参看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 —8页。刘笑敢正是依据是否出现合成词“道德”来区别内篇和外、 杂篇的。内篇中由于没有出现过合成词“道德”,而只出现过“道”或“德”字,故写作时代在前。)因此,道德的本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理性思维对“道”和“德”的分别解释。在理性思维中,“道”被当作一个哲学范畴,它既属本体论,又属认识论,关于其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我们兹举数例:
胡适认为:“道”是“一种无意识的概念”。冯友兰在30年代则认为,“道为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张岱年则认为,庄子“主张道是宇宙之究竟本根”。杨向奎则认为“道”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又是一种“根本法则”等等。(注:参看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103页。)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发生疑问,直观能力极高的古人思维真有如此复杂吗?而且,不难看出,这些解释都是试图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文明人理性思维最成熟的形态)来解释原始思维的一个命题。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则几乎从没有谁来做这样的分析。古代哲学家是凭着一种体验去认同“道”的存在的,这就是庄子所谓的“目击而道存”(《田子方》),然后再直接把它落实在日常行为中。所以古人称它为“本体明了”(《王文成公全书》卷三),无须言辩。
“德”在最初也只是一种“具体行为”,《说文》谓:“德,升也”,段玉裁注:“升当作登”,桂馥义证谓“古升、登、陟、得、德五字义皆同”,都与走路的行为有关,本身并无善恶之分。这一点还可从道家那里来看,庄子经常德、道不分,大德即大道,只是到了儒家手里,它逐渐变成一种伦理规范,并逐步有了明确的现实内涵。其内容如“让”、“恕”、“俭”、“敬”、“忠信”,以及“固、顺、孝、安”(四德)等(注:张荣明《“道德”小考》,《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我认为,这种转变,即中华文明在发韧期的理性思维对中国原始文化进行道德定向和阐释的结果。(注:拙著《文明精神结构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37页。)但这显然不是“德”的本源义,而是文明引申和附加给中国文明之初民的。
既然道德的本义不能从我们今天的理解(包括理性阐释学方式本身)中觅得,甚至也不能从学者们的考证中觅得,那么我们就试着到民间智慧中去探讨吧。只有当思路转变后,另一些材料才会派上用场。
从“道”和“德”的本义来看,它们都与人的行为有关,“德”已见前说,而“道”,在《说文》被释作:“所行道也”,两者都和行路有关。行路要依靠的人体机能,不是大脑,而是人的眼睛,所以从甲骨文“德”的字形来看,德的本源义并非《说文》所谓的“升”,而是如郭沫若所云:从直从心。(注:郭沫若云: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值(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但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范——后人所谓“礼”。礼字是后起的字,周初的彝铭中不见有这个字。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第336页。)“直”又“从十从目”,因此,“直”与人的眼睛密切相关。而金文“道”字中央部分为“首”,“也就是以人眼为象征的人头形象”(注: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531页。),所以“道”最初也直接与人的眼睛相关。这与前文所引对“德”的解释一样,它们都与走路或巡视道路的具体行为相关。这也是人们训“道”为“导”的原因。但这种通行的训“道”为“导”,与郭沫若训“德”为“礼”一样,(注:郭沫若云: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值(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但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范——后人所谓“礼”。礼字是后起的字,周初的彝铭中不见有这个字。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336页。)是“道”、“德”解释学的“下行”,是引申,而其本义,则需向上,溯洄求之。这里所以要把“道”、“德”与“目”的关系突出出来,其根据在原始思维中所特有的“人体式”的隐喻,这就是维科所说的:“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注:[意]维科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原始人“想象的玄学”,在今天的俗语中仍大量存在和使用。根据这种“人体式”的隐喻,我们可以断定,与“道”、“德”本义关系最为密切的字,既不是“导”也不是“礼”,而是人类的眼睛。关键问题只在于如何解释其内在关系。
三
根据我们提出的俗语人类学,有时我们不但不能相信古代权威典籍及其解释学,倒宁可更相信民间文化。这里的民间文化有几层,一是与当时的官方话语或正统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些文献中对“道”、“德”的解释,另一则是后代俗语中的东西,我们发现,“道”与“德”的本源义它们都与“直”有关系。
在第一层意义上,我们宁可相信在先秦大量使用口语的《论语》、《诗经》等文献对道德的解释,也不肯相信《春秋》、《尚书》、《左传》等文献有关道德涵义的记载,因为后者代表着当时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诗·小雅·大东》中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论语·卫灵公》亦云:“邦有道如矢”,“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抛开后代经学家的道德附会,道的基本意义与“直”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德”与“直”的关系则更密切。《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德”又作“德”其字形从“直心”。这一点还可参见《尚书·洪范》中讲的“三德”,“一曰正直”(此条注释虽出于《尚书》,但与《左传》等对道德所做的缜密的解释如“四德说”相比,仍有可取之处,它毕竟不象“固、顺、孝、安”那样意识形态化),所以郭沫若认为:德,从直从心,这是正确的;但他由此把“直心”引申为儒家经典中所谓“俗修身者先正其心”,引申为“礼”,则如前文所说,这是“下行”,是用已成熟的儒家哲学去解释中国原始文化中的伦理观念,这就犯了“越界”的忌讳。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直”与“礼”的关系,或原始人的“礼”与后来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学有什么本质不同。在此,我们先结合当时民间对“直”的理解来看。在《论语·宪问》中,孔子与弟子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段话也被看作是孔子赞同原始时代的复仇观。(注:参看王立《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 )古代复仇成风,孟子《滕文公下》讲商汤征葛伯的借口便是“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尽心下》亦云:“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这都表明先秦儒家是赞同复化观的,而反对老子的“以德报怨”原则。(注:《老子》七十九章“报怨以德”。这不仅表明老子深谙进退之道不象孔子那样“迂”,而且还表明了对儒、道两家不同的伦理学理想,我们过去可能完全理解错了,即以为讲自然的老子更倾向于直觉伦理学,由此看来,反而是以礼为中心的孔子伦理学更看重道德行业的直觉性。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从孟子到王阳明都特别看重“良心”和“本心”,反对“知行”两分的理论源流。此问题很大,以后再论。)由此可以看出,“以德报德”与“以直报怨”是同一个原则的正反两面,“以直报怨”即“以怨报怨”,也即“以德报德”的反义词,其中“以德”句的第一个“德”与“直”意同。但这复仇的标准是什么呢?王立以为“公正不阿,严循正义”,这里采用的是《广雅·释诂二》“直,义也”的解法,它没有注意到“义”在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巨大差异。我以为作为原始伦理学标准的“直”,它应该从直觉伦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直觉伦理学不同于文明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前者的生命本体基础是人的眼睛,后者的基础是人的大脑。前者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此即《大学》所谓的“十目所视”);后者看到以后,还要经过大脑的思考和判断(此即《广雅》释“直”为“义”的根源)。两者的不同还涉及到对《说文》释“直”为“正见”的不同理解上,从直觉伦理学角度,“正见”即“当下之见”,因为直觉活动与时间密不可分;而从功利主义伦理学角度,“正见”则被解释作“正义之见”或关于“正义”的正确看法。不弄清这层本质区别,我们就很难区分开原始伦理学与文明人的道德观,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道”、“德”的初文和本义都“从目”。它表明的恰是,原始人的行为规范是一种朴素的直觉伦理学。
这里应该谈一下直觉伦理学与思考、功利性或外在原则(他律)的本质矛盾。直觉伦理学认为人生而有一颗辨别是非的本心,它能本能地辨别善恶,从自己的直觉中就可以找到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和原则,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人之生也直”(《伦语·雍也》)。相反,恰是知识,尤其是依据非直觉伦理原则的功利性思考,往往使人的良知为了功利关系而遮蔽起来。它在碰到选择时往往“退一步讲”或“转念一想”,这一转念,往往就是功利的原则取代了道德直觉,使人的本心泯灭了,这就是孟子所谓的“失其本心”(《告子上》)。所以阳明学派强调“笃行”、“直行”而反对读书和知识,恰是因为功利性的思考,常会败坏道德的自发性、自为性,以及伦理意志的自由。
其实,这种以“直”为本源的“道德”虽然从学理上讲非常繁琐,但从俗语角度,它至今仍广泛地存活在口语中。在我们口语中,存在着一个以“直”为中心的语汇群,如“直来直去”、“直心肠”、“直性子”、“直杆子”、“直筒子”以及“直觉”、“直观”、“直感”、“正直”等口语。这些口语都是用来表示人的品德或行为方式的。它所表达的行为方式,也即可称之为“直觉伦理学”。这样讲原因有二,一是它们都与“知识”、“教养”相违背,正是缺乏知识与教养,使之常有一种“野蛮”或“不谙世故”的意义。而在这种道德基础上的选择,恰与孔子论“德”与“言”的矛盾相应。“言”就是措辞和思考,孔子说“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就是充分认识到人的道德行为的直觉性本质,而思考往往是用功利原则来牺牲道德直觉。所以孔子强调为政要“举直错诸枉”(《论语·为政》)。关于这一点,孟子《滕文公下》所讲的“枉尺直寻”中有更深入的讨论,委屈一尺,却可以前进一丈,从功利的原则,此即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主张,也即老子的“报怨以德”。但孟子却以为,如果“以利言”之,则不可为,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同样,这种“直”与“知”的矛盾,也可从康德伦理学那里求得证实。康德认为道德与知识无关,功利的因素会使道德的纯洁性受损。因为道德的原则是“应该”,这是无须借助知识的推理和判断(因为这种推理判断的根据是利益原则,而非道德本身)的直观能力,康德还认为,越是有经验的民族就会越失去道德的纯洁源泉。(注:拙著《文明精神结构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6页。)此处还可再参照费希特的名言:年龄愈长的人,自私愈甚;地位愈高的人,道德愈卑。这正是因为人的道德直觉被功利主义败坏的结果。二是它强调的是伦理判断的直觉本体,或直接性,这正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原始人行为的唯一规范。如原始部落复仇成风,“以直报怨”,自己的亲人被别人杀了,那么这里不须作任何功利上、知识上的算计,作为一种本能,他必须要血债血还,以牙还牙,这才叫做“有种”。而不以任何功利借口来干扰自己行为之纯正,如文明人所谓的卧薪尝胆,甘受胯下之辱,能曲能伸等。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只建立在能否胜利或成功这一功利计较上,为了最后的胜利,不惜以各种手段压抑感情,忍辱偷生,以便东山再起。而原始人的行为才是纯粹的“正其宜不计其功”,也不需作任何其他外在原则上的算计,如在一些武侠小说中经常可见到这样一种道德难题,一个坏蛋的儿子是否应为父亲报仇。在原始时代,也包括今天一些地方械斗中,根本没有这种理性的考虑(即父亲的好与坏),唯一想到的是,死者或受伤害者是一个人,是一个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那就该为他恢复名誉或复仇。由此可见,这种“直德”,在民间一直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虽然它一直是文明世界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因此,原始伦理学的出发点绝不是什么“正义”,或行动之前先考虑一下是否符合正义这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它完全依靠人的直觉来行事。而最能表现直觉的,便是人的视觉,而行为就是依据“直心”走该走的那一条路,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道”才是“道路”,而“德”则是“巡视、选择道路”的行为。而这恰表明,我们现在口语中的“直”,正是“道”和“德”的本源。此正所谓“真诗在民间”也。
以直觉伦理学为基础的“道”、“德”包括合成词“道德”,可以理解为行为与直觉的直接性和一致性(此即“知行合一”),中间没有任何思维的、语言的转换环节,也可译作“当下的行与当下的觉”,而且行与觉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可分性。理解了这一点,才会知道王阳明的心学所强调的“笃行”,以及他为何反对从语言和文献中去寻找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而要在直接、当下的行为中呈现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选择。
四
这就牵涉到两种伦理学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道德是一种直觉伦理学,文明道德则是一种功利伦理学。前者的基础是人的直觉,“直心”,这也就是俗谓的“良知”,在一个事件面前,良知无须反思,人心便能直接地作出善恶判断,如孟子讲的“不忍人之心”,这种良知在文明世界中并未泯灭,并且在许多场合仍起着选择机制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从“自欺”这一词在语义上的悖论来解释。自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人能有意识地欺骗别人,但在欺骗时,他自己却知道自己在“骗”,因此永不可能有“自欺”之说成立。这表明直觉伦理学的常在。而后者的基础则是知识和思维,也即俗谓的“经验”。在面临一种道德困境时,如看到坏人搞破坏,那么一个人首先的反应是这是不应该的或应该阻止的,这显示了良知的功能,但这种良知在将发未发之际,人又会转念一想,即把良知反应纳入大脑的理性思维中,这时人就离开了“应该”的原则,而依据“知识”或“经验”来反思:如这样做对我会有什么损益,这样做值不值等等,功利的考虑遂使良知被压抑下去。——这也才是文明人的道德概念,即文明人的行为不是依据直觉,而是依据某种知识范式或经验类型,当然这其中也可能有与良知相一致处,比如以英雄人物为榜样,但其目的却不是满足良知,而是满足人在社会中的荣誉感,这就使文明人的道德感靠不住,因为不是发之于内心,而是发自经验类型,那么他就既可能依照英雄范式,也可能依照非英雄的、大众的范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理学家非常重视“未发”前的本体建设,强调“忠”、“诚”和“毋欺心”等也是意识到这一点,即在道德的先验基础上排除功利性思考,以此来确保伦理行为的纯粹性。
从上述可见,知识与思维的作用,是道德本身区分为二的重要原则,这里我们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此转变机制再作一点分析。
从文字上看,“道”与“德”的初文都从“目”,这表明先民的行为选择更多地依靠人的视觉,无论是选择“道路”还是其他行为。而且可以说,“目”是直觉伦理学的生理基础,孟子《离娄上》谓“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不正,则眸子眊焉。”中国画论云:“传神之物正在阿睹中”,西谚云:“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都如此。而功利伦理学的生理基础是“脑”,它是一种“黑箱”或“灰箱”,其中的机关不是一下就能明了的,即非“直来直去”,而是“花花肠子”。但伦理学如何从“目”而转向“脑”的呢,这其中起关键的乃是知识(尤其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抽象”作用。
原始伦理学(道德本义)从“目”,其中伦理行为与人的直觉不分离,其行为的素朴性和思维的素朴性(或直觉性)是相统一的,知即是行,行即是知。此亦即王阳明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明儒学案》卷十)后者比前者不过是多一些说明、限定而已。但正如文明人中的“直筒子”、“大炮”常被他人当工具一样,原始直觉伦理学,也是在日益复杂的文明进程中,而饱经苦难中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甚至非常赞赏“直”的孔子亦云:“直而无理则绞”和“狂而不直”——《论语·泰伯》)原始人最初并没有“个人”,故“目”乃是一种人类学家所谓的“集体感觉”。这种集体直觉,在社会进化中逐渐失去其原始时代的统一性,为了保证集体生活的高度一致,又必须从中产生出一种能代表、象征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看法的“社会性器官”,这也就是氏族酋长的“目”。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道”、“德”两字形来分析。叶舒宪认为“道”字中的“首”,象征着人头,“道”就是“对祭头礼俗的直接概括”,它的本源指“后稷头”(注: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2页。),后稷为古代部落首领,它恰表明了,“首”中的“目”为酋长之目。而“德”字又从直,而“直”又“从十从目”,这里的“十”在上古有特殊的人类学含义,在一些表示太阳崇拜的“圆形”中,常有“十字”,(注:[苏]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这表明“十目”,也可能与太阳神有关。上古时代的氏族贵族,都自命为“太阳的子孙”,故德字中的“十目”(直字所从)也是指酋长之目。从对“道”和“德”的文字考释来说,“道德”中的“目”最初乃酋长之目,是一种高度统一的集体感觉的象征,是集体需求的抽象表达,而且最初酋长这双“抽象的目光”与氏族成员的“具体的目光”差别仍相当微小,所以原始共同体之中的“共通感”仍然存在。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私有制的产生,氏族部落成员的个人感官与酋长这双“抽象的目光”之间也就越来越难以取得一致的判断,以致最后个体的心智逐渐独立、封闭起来,中止了与集体(酋长之目是其象征)的共通感,社会开始出现第一次无序化,而为了使社会能组织起来,这便出现对秩序的需求,它使酋长之“目”的权威性越来越强化,这也就是道德从“直心”逐渐演化为“礼”的历史现实进程,礼在荀子《礼论》看来,即是“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的结果,于是一种对立于个体直觉的新的伦理学才开始产生。
从历史上看,这套新伦理学大都与酋长的存在相关。不光酋长之目,可作为“正见”,而且酋长的“手”、“足”也被用来当丈量土地、分配食物的标准,再进而言之,酋长根据自我或贵族阶层的需要,制定一系列原始社会必需的规范和标准,并用它们取代了最初的公社民主制,而在文字演变中,“道德”也就与“目”几乎没什么联系了。
在这种由“目”到“十目”、“直心”到“礼”的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直接性交往中断了,其中的转换机制即酋长的“目”、“手”、“足”和“思维”。这是原始人碰到第一次“抽象活动”,在这种抽象活动中,个体的直接性、具体性、实在性被剥夺了,一个人的“目”不再是个体行为的伦理基础,而是要根据“酋长”、“长者”或者他权威人物的“目”,在选择行为时体现的不再是个体的意志,而是与个体的意志相剥离开来的权力意志。(由此可理解一点,中国哲学心学一派,专讲“未发”与“已发”之统一,即强调行为的直接性,非间隔性,反对将已发和未发割裂开来,以此来保证个体道德行为的纯粹性的良苦用心)这个作为标准的意志,它开始以一种功利性原则作判断,这是理性最初的扩张形式,它能够把其他感性的存在当作表象,而把其功利、意愿、欲望强加给现实。这种理性扩张的结果,便是“礼”或“法律”,当道德不再依照个体的直觉,而是听命于外在的规范时,它就变得越来越不符合道德的原始本质,这就是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
关于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历史发展尺度的社会规范道德对个体道德直觉的“抽象”作用所致。它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为标准,为个体规定了一套规范,此即以“义”为“直”。由于这套规范在个体生命中并没有普遍性,所以它只能以压迫、改造个体的道德直觉为手段。这一点可从《吕氏春秋·贵直》中得到了解。虽然在表面上贤主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但这种“直”是任何贤主都无法容忍的。所以齐宣王虽以能意“好直”而招见他,但当能意真的“直”起来,指责齐宣王为“污君”时,齐宣王马上就要对他治罪。这也是庄子反对孔子“礼教”的原因。孔子虽也看重道德的自发性,但却为个体建立了一套抽象的伦理规范,这就使得它非常容易被统治者所窃取。正如庄子《胠箧》所云:“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所以庄子激烈地批判儒家,认为“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在宥》)。包括庄子在《齐物论》中强调没有一个可以仲裁的标准,都是因为他拒不承认这样一双“抽象的目光”的普遍性,但却抵挡不了这个怪物的生长。以至于到今天,作为道德本源的“直”,反而成为一个“没头脑”,“需改造进化”的贬义词,文明世界,有时就是这样颠倒一切是非、曲直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有些悲哀和无奈了。
标签:儒家论文; 伦理学论文; 道德论文; 人类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大学论文; 国学论文; 良知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