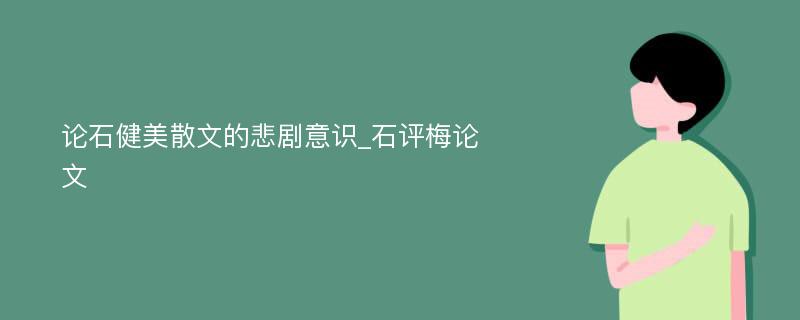
论石评梅散文中的悲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悲剧论文,意识论文,论石评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代以散文著称的女作家中,除了冰心和苏雪林之外,恐怕要数石评梅了。她以短短6年的创作时间写下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各体作品共几十万字,成为当时名躁京都的女才子。在各种文体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当数她的散文了。本文拟浅析她散文中表现出来的关于生命的悲剧性意识。
生命的悲剧意识,“包含着生命自身和宇宙的整幅概念,以及或多或少系统化的或多或少有意识的整幅哲学”(注:乌纳穆诺著:《生命的悲意识》。)。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现象,它来源于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生存与毁灭的矛盾冲突中,同时,焦虑、绝望、恐惧的心理始终伴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命主体。这使得历代许多文人都从他们心灵深处发出对人生的凄绝的呼喊。从品达的“阴影中的梦境”到卡尔德隆的“生命如幻梦”,以及莎士比亚的“我们是由幻梦织合的物品”,都体现了一种“厌世解脱”的悲剧意识。在石评梅的散文中,她揭示了人生的悲哀面,揭示了人生的悲惨和无价值。当她企图以自身力量去突破现实的、理智的、历史的制约而又明确认识到无法逃脱命运之网的制约时,当她在特定历史时期看见理想被毁灭、情感被囚禁、生命被毁灭时,就开始对人类自身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否定性的认识和评价,而这种否定性的认识和评价就是本文所指的悲剧意识的真正内涵。
20世纪初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民族审美意识,日益严峻的民族、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使“五四”作家开始认同尼采、萨特和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并形成了对现实人生的悲剧性认识。石评梅因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视角,接受了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的影响,并将其融入散文创作中,因此,在石评梅的散文中,处处充满了感伤体验的痕迹,处处充斥着悲观凄凉的氛围,处处表现着生命的疲劳和空虚。叔本华认为“一切生命的本质就是苦恼”“没有任何事物值得我们去奋斗,努力和争取,一切的财宝都是空无的,这个世界归于破灭……”“现实唯一的生存方式,只是所谓‘刹那的现在’的现象”,这种思想正好契合了经受失恋打击、在各种矛盾冲突中痛苦不堪的石评梅的心态。她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一朵“枯萎的残花”,她在散文中写道:“但是终日终年战战兢兢地转着这生之轮,难免有时又感到生命的空虚,像一只疲于飞翔的孤鸿,对着苍茫的大海”,当她面对“云雾的前途”时,石评梅“何处是新径?何处是归路地怀疑着,徘徊着”。这实际是石评梅在特定历史时代对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境况进行追问之后陷入的空虚心理,正如美国评论家西华尔在《悲剧眼光》中所指出的那样:“悲剧眼光将人看做寻根究底的探寻者、赤裸裸的、无依无靠的、孤零零的,面对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各种神秘的力量,还面对着孤独和死亡这些无可回避的事实。”这种对个体生存悲剧的焦虑,使石评梅把悲剧意识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悲剧性体验相融合,并且把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以长歌当哭、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在她的散文中,所以在她的笔下,即便是“锦绣似的花园”“美丽的姑娘”,在石评梅悲剧的眼光中,也不过是“荒冢灰烬”“腐尸枯骨”,即便是“花开红紫,叶浮碧翠,人当红颜,景当美丽”的时候,她也总是残酷而清醒地将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都分析成“秋风枯叶”。石评梅专心地、内在地执著于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注视,当她用这种心态去感觉周围事物时,所有的事物都呈现出它们痛苦而荒凉的神态,这是石评梅对人生根本境况、对生命本质既清醒又迷惘的认识,生命在此呈现出悲剧性的显著特征,而石评梅也因此而跌入来自于生命厌倦的深渊:存在的厌倦,最空虚的无底深渊。她认为一切幸福、欢乐都是消极的,永远不可能有永久的喜悦和满足,故而她常觉得“腐尸般活着无味”,希望把自己的生命“建在美的、泛的、静的”基础上,并且决定“不愿追想如烟如梦的过去,不愿希望那荒渺未卜的将来,只尽兴尽情地欢乐,让幻空和繁华都在我笑容上消失”,正是这种对生命空虚、转瞬即逝的本质的认识,使石评梅酷爱着冬天、冬天的雪和雪地中傲然开放的梅花,也使她对“寥阔而且凄清,萧森而且凉爽的陶然亭”格外青睐。对一切荒寒、凄清、寂静,具有颓废色彩的事物,她有一种特殊的嗜好。正如同刘烜所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主张、评价、倾向总是通过意象的不同组合体现出来的”(注:刘烜著:《文艺创造心理学》。)。这些载石评梅悲剧人生体验之“意”的客观物象的相互组合,便渲染出一种漫无涯际的悲剧凉气氛,而这种气氛与她那忧伤、愁苦、悲凄的心情相吻合,她把“白屋的空气”比为“淡月凄风下的荒冢”,把“小屋”喻为“阴森”的“深夜墟墓”,把陶然亭的月亮、晚霞、池塘芦花看成是“特别为坟墓布置的美景”,石评梅对描写意象的运用,对词句的斟酌选用,“都不可避免地将作者本人心灵中的无意识性呈现给了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注:(美)卡尔文·斯·霍尔等著:《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她的散文几乎字字血、声声泪,几乎觅不见温馨与明快,在这里,因了石评梅对自己的存在,生命的价值的痛苦思索,生活被剥下了华丽的伪装,呈现出它荒凉、空虚、痛苦的悲剧本质。
在人生苦短和离合之悲外,石评梅觉得人生的悲剧还在于人类永远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命运总是在左右着人们,把人牢牢地固定在一条充满忧虑、灾难、敌人、危险的人生之路上,尽管人类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却仍免不了遭受命运的残酷践踏,因此,在石评梅看来,人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生存本身和他的本质将成为人类难以负荷的重担”(注:(德)叔本华著:《叔本华论文集》。)。她写道:“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而且“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脱此罗网以自救”,当她发现“我们这四五年来被玩弄、被宰割、被蹂躏的命运醒来原来是一梦,只是这拈花微笑的一梦啊!”这种大梦初醒后对生命的大彻大悟正是对生命悲剧本质的真实揭示,当年意气风发地投入社会准备大显身手报效祖国的石评梅在爱情生活中遭受了致命的创伤,黑暗的现实又粉碎了她高昂的理想,石评梅发现自己无法逃脱命运之魔手的操纵,在散文中,她毫无隐讳地坦露自己的心迹,她的痛苦是直露的,她的抒情是大胆的,而当我们倾听到她在命运铁蹄下痛苦的呻吟时,又怎么能无动于衷?一切悲剧都具有感人、动人的审美特质,正如卢隐所言:“悲剧的描写,则多沉痛哀戚……所以这种作品至易感人,而能引起读者的反省。”冰心也强调悲剧“思力深沉,意味深沉,感人深烈,发人猛省”。石评梅写出了人类对生命体验的共通性、共感性,也正因为此,她的悲剧意识促使我们对自身生命及价值的思考和反省。
即便是关于爱情的描写,我们也时时能感受到那无处不在的悲剧意味,石评梅的爱情文字,大多写在其爱情悲剧的大幕落下之后,因而带有浓重的回忆和反思色彩,这种回忆和反思,使其抒情变得更缠绵悱恻而又深刻隽永。在她的散文中,我们分明可以触摸到一颗悲痛欲绝的心,在孤寂和凄苦中,她独自追踪着、演绎着、咀嚼着那美丽而又痛苦、不堪回首却又永远难忘的尘梦:“我觉着我写的那‘心珠’好像正开着的鲜花,忽然从枝头落在地上,而且马上便萎化了,我似乎亲眼看见那两个字于一分钟内,由活体立变成僵尸,当时由不得感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并且有了一种送亡的心绪,所以到后来桔瓣落地,我利其一双成对,故用手杖掘了一个小坑埋入地下,笑说:‘埋葬了我们罢!’”这种悔恨交加的情绪几乎贯串着石评梅所有的爱情文字中。乌纳穆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注:乌纳穆诺著:《生命的悲剧意识》。)石评梅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因为这种“富有悲剧性格的爱”,痛苦的石评梅并未寻找心灵以外的东西来代替、转移自己这颗受伤的心,反而将自己裹得更紧,这几乎毁灭了她以后所有的幸福,并直接影响着她后来全部的人生行为和创作心态。石评梅不再相信爱情,对爱她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爱情是盲目的小儿”,又说:“青年人唯一养料是爱,然而我第一怀疑是爱,怀疑的结果,我觉得这一套都是骗,自然不仅骗别人连自己的灵魂也在内:宇宙一大骗局。”石评梅看到人生所呈现的就是或大或小从不间断的欺骗。同时,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也深深地困扰着石评梅:“她的一生是永远在理智与情感的夹缝中挣扎徬徨,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下生活,她常陷于矛盾之中,欲爱不能,撒手不愿。”在这种冲突无法得到调和的情况下,焦虑、痛苦始终伴随着石评梅,她将悲剧的眼光扩展到了爱情领域,捧出了她那颗充满自我心理交锋的不安定的灵魂,表现爱情中个体与社会、理智与情感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冲突的悲剧性本质。
在《生存空虚说》中,叔本华指出:“生存之所以空虚,是因为,其一,在生存的全部形式中,‘时’与‘处’本身是无限的,而个人所拥有的极其有限,其二,现实唯一的生存方式,只是所谓的‘刹那’的现在的‘现象’,其三,世上没有常驻的东西,一切都是不停地流转,变化。”石评梅从自己对命运的真切体验和思索,接受了叔本华这一观点。在散文中她写出了人在时间之流中的转瞬即逝:时间以其变幻无常的空虚本质,使所有的东西在我们手中都化为乌有,万物也因此而丧失其价值,在我们的一生中,尽管做过许多事情,然而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人类个体投进空茫茫的空间和漫漫的时间之流中,是以有限之物而存在的,与时间、空间的无限相比,几乎等于零。这种对生存的绝对荒芜和空虚的本质的痛彻认识,表现在石评梅的散文中,就使她的作品“实在是主观的伤感过甚。满纸都是哀飒伤心的话”(注:林砺儒:《评梅的一生》。),并且“太Sentimetal——(伤感)!”(注:李健吾:《悼评梅先生及其文艺》。)当“生命之波滔滔地去了”,“一刹那,捉不住的秋去了”,当“一瞥的人生”原来是这样“无影无踪”时,石评梅发现“时间张着口,把青春之花,生命之果都吸进去”,和强大的时间相比,她认为“人世是宇宙藐小者瞬间的一转,影一般地捉不住了”,认为生命“更渺小了”,人生“在这大海中不过小小一个泡沫”,这绝不是一种无聊的无病呻吟之词。而是对生命现象的本质剖析,这种对生命的感觉体悟,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会有的,从某种程度来说,石评梅的悲剧性意识,已经超脱了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上升为对人类生命本质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尽管这份对于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沉思,将会引发我们极度痛苦的沉思,但是在最终处它却能增强我们心理上面对生活的勇气。正如曹禺所言:“悲剧的精神,使我们振奋,使我们昂扬,使我们勇敢,使我们终于看见光明的获得胜利。”
石评梅说:“我是投自己于悲剧性中而体验人生的”,“我愿做悲剧中的主人翁”。这虽是石评梅的心灵独语,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身处“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在冲出闺房走入社会后的真实心理写照,是她们走出深闺后面对无常人生和残忍现实的绝望无助的内心世界的反映。“五四”新文学先驱者充满激情地呼唤文学创作应灌注悲剧意识,卢隐强调:“创作家,对于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调描写出来,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在这个呼唤悲剧的时代,石评梅“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她的血和肉”(注:鲁迅著:《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在这片“崭新的文场”上, 她是“几个凶猛的闯将”之一。她的作品道出了生命的永恒悲凉,但又不把人引向悲观绝望,而使人站在较高的阶梯上俯视人生。巴金说:“生活本身就是悲剧”。石评梅正是用自己切身的感悟写出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并促使我们反省自身。
悲剧的效果,有着一种崇高的力量,能使我们超脱意志及其利害,而使感情产生变化。郁达夫认为:“悲剧比喜剧偏爱价值大,因为这世上快乐者少,而受苦者多”。正因为石评梅写出了“受苦者”的悲哀,才使她的散文得到了多数人的共鸣与喜爱。
真正的艺术决不是让人舒舒服服地享受,也不是让人昏昏欲睡的催眠曲。真正的艺术除了让你心情愉快以外,更多的时候是让你不舒服,甚至给你痛苦,因为它揭示了生活的真实,发现了世界的真理,解释着人生的真谛,从而给人以新的启迪。石评梅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的散文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