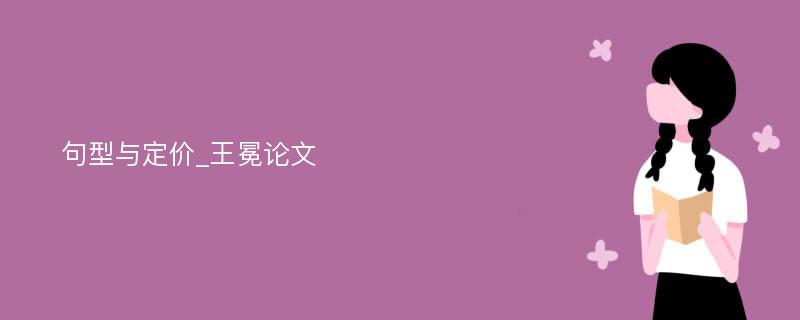
句式和配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句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评价“配价”系统的标准
“配价”研究的目的是从谓语动词和相关名词性成分组配上的限制来说明句子的合格性。例如:
(1)她送我一件毛衣。 *她织我一件毛衣。
(2)他们修筑公路。
*他们散步公路。
一句合格,一句不合格,用配价来说明:(1 )“送”是三价动词,能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而“织”是个二价动词,只能跟两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2)“修筑”是二价动词, 而“散步”是一价动词。如果再区分“价类”(施事、受事等),能说明的现象就更多。
评价一个配价系统的优劣,跟评价一部语法的优劣一样,应该依据三条标准:1 )总括性——说明的与句子合格性相关的语法现象要尽量广泛;2)简洁性——系统要尽量简单;3)一致性——不能有循环论证和内部矛盾。目前的配价研究在确定配价系统时具体标准提得不少,例如在确定动词的价数时,有的以动词的词义为依据,有的以句法形式为依据,也有的同时以词义和句法形式为依据;以句法形式为依据的,有的以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用不用介词引导为依据,有的以同现的名词性成分是不是必须出现为依据,也有的将两者同时作为依据。各人提各人的依据,但很少从上述三条基本标准出发来比较系统的优劣。配价研究要深入,似应注意这个问题。
2.以两个句式为例
下面以两个句式为例来说明建立动词配价系统时存在的问题。这两个句式一个是表示“予取”的双宾语句,一个是表示“得失”的领主属宾句。例如:
(3)A.他扔我一个球。 B.他吃我一个桃儿。
他斟我一盅酒。他抽我一支烟。
他搛我一块火腿。 他占我一间房间。
他介绍我一个朋友。他浪费我一只信封。
(4)A.王冕死了父亲。 B.他家来了客人。
他烂了五筐苹果。 他跑了一身汗。
他飞了一只鸽子。 他多了几分勇气。
传达室倒了一面墙。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3)是表示“予取”的双宾语句,以表“给予”的A居多,表“取夺”的B较少。(4)有人称作“领主属宾句”(郭继懋1990),这种句子的主语和宾语之间有“领有—隶属”关系,主语是“领有”一方,宾语是“隶属”一方,而动词与主语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句子的意义以表“丧失”的A居多,表“获得”的B较少。这两个句式在动词的配价分析中引起很多争论。从词义出发主张“扔”和“吃”这样的动词是二价动词的人无法说明为什么它们在双宾语句里能直接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如果从形式(同现的名词性成分)出发说它们就是三价动词,这又有悖于我们的直觉:从这些动词本身的词义来说不像是三价动词。有人用“兼价”或“变价”来解决,说它们既是二价动词又是三价动词,或说本来是二价动词,但在双宾语句式中是三价动词;拿“扔”来说,“作为二价动词没有给予义,作为三价动词有给予义”。(马庆株1998:284页)这样就得承认有两个“扔”,一个是二价的“扔”, 一个是三价的“扔”,至少得承认“扔”有两个义项,一个表示给予,一个不表示给予。这样做的代价比较大,因为这样的动词不是一个两个,为数还不少,(参看马庆株1983)一一标明有两个义项使系统的简单性受损。更重要的是这仍然违背我们的直觉,任何一部词典都不会在“扔”下另外列出一个表示给予的义项,或在“吃”下另列出一个表示取夺的义项。说“扔”这类词有两个义项还缺乏心理学上的证据,也就是没有心理现实性。(注:一个词如果有两个义项,就是多义词,含多义词的句子在理解过程中会出现“花园小径”效应,例如下面这个英语句子:
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fell.race 一词有歧义, 一作“跑”, 一作“使…跑”。 被试人在听到raced时可能先按“跑”理解为谓语动词, 到句子快结束时才意识到讲不通,再返回去重新按“使跑”理解为过去分词作修饰语,就像花园里沿一条小径散步,走到尽头发现不通,又原路返回重新找路走一样。这就会降低句子理解的速度,心理实验中反应时间会相对延长。然而实验证明, 英语中类似“扔”这样的情形并不产生这种效应(Carlson &Tanenhaus 1988)。)
如果不考虑动词的词义坚持“扔”可以是三价动词,那就有循环论证之嫌:说“扔”是三价动词的惟一根据是它能在双宾语句中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而要说明为什么“扔”能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惟一的根据是它是个三价动词。这势必导致“词无定价,离句无价”的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大家不愿接受的。(参看陆丙甫1979等)对于领主属宾句,“死”和“来”这样的动词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管说它们是一价动词、二价动词,还是有时是一价动词(无得失义)有时是二价动词(有得失义)。
问题还出在“内部矛盾”上。一些反对内部不一致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双宾语句和领主属宾句。例如用谓词的词义来确定配价时,一方面认定“他跑了一身汗”中的“跑”只是一价动词(没有获得义),一方面又把“他占我一间房间”、“他拿我一本书”、“他扣我十块钱”中的“占、拿、扣”说成三价动词(有取夺义),尽管这三个动词在词典中都没有取夺的义项。(见周国光1995,张国宪、周国光1998)另外,将“扔”等动词分析为三价动词,有不少人反对也有不少人赞成,但是将“死”等动词分析为二价动词,好像除了朱德熙(1978)几乎都反对。反对的人中有人认为“王冕死了父亲”中的“王冕”不是“死”的配价,而是一价名词“父亲”的配价;(袁毓林1994)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这又如何解释“他飞了一只鸽子”,“他死了四棵桃树”,“他烂了五筐苹果”,总不能说“鸽子”、“桃树”、“苹果”也是一价名词。还有人认为“王冕死了父亲”是由深层的“王冕的父亲死了”转换而来;(沈阳1995)这样处理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转换说还得说明为什么“他的孩子哭了”和“他的眼睛湿润了”这样的句子不能这么转换,不能说成“他哭了孩子”,“他湿润了眼睛”,尽管“哭”、“湿润”跟“死”一样都是一价动词。这也说明只研究动词的配价对句子合格性的解释范围有限,也就是缺乏总括性。又例如:
(5)我写给他一封信。
*我写给他一幅春联。(朱德熙1979文例)
(6)他来了两个客户。
*他来了两个推销员。
不管将“写”分析成二价还是三价,也不管将“来”分析为一价还是二价,总得说明为什么一句能说,一句不能说。再例如:
(7)他抢我十块钱。 他抢了十块钱。 他抢我了。 *他抢人十块钱。
他偷我十块钱。 他偷了十块钱。 *他偷我了。 他偷人十块钱。
“抢”和“偷”不管是分析为三价还是二价,总得说明为什么“他抢我了”能说,“他偷我了”不能说;“他偷人十块钱”能说,“他抢人十块钱”不能说。(注:有人认为“他偷我了”和“他抢人十块钱”能说,但这些人肯定也认为“他抢我了”和“他偷人十块钱”能说,而认为后两句能说的人不一定认为前两句能说。)目前对动词配价的分析还无法对这类现象作出相应的解释。
3.原因和对策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在研究动词的配价时没有考虑到句式自身还有其独立于动词和相关名词性成分的意义,二是没有认识到动词的词义不仅仅是一些“客观的”语义特征,更不是用目前的价数或价类分析就能充分说明的。
从动词出发,设法弄清每个动词的配价情况(价数和价类等),以此来说明句子的合格性,这种研究路向的基本假设是,整个句子的合格性是由其各组成成分(动词和相关的名词等)决定的,动词是核心成分,句子的合格性因此可以从动词的配价推导出来。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向,即通过把握组成成分的差异来把握句子之间的差异。然而,句子都是句式的体现,而句式有其自身独立于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这个整体意义是无法完全从组成成分推导出来的。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成成分的意义固然对句式整体意义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反过来句式的整体意义也制约着组成成分(包括动词)的意义。(注:马庆株(1983)曾提出“动词的意义有时要靠格式来限定”。朱德熙(1986)曾提出“高层次的语义关系”这个概念,指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另参看范开泰(1999)。儿童语言的研究证明,儿童习得动词词义极快,那是借助动词出现的句式(有其独立的意义)来推断动词的词义(参看Landau & Gleitman 1985)。 )从句式出发来观察动词和相关名词的组配关系,这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向。自下而上的研究应该跟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句子的合格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参看Goldberg 1995,沈家煊1999a,张伯江1999)
语义特征分析法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局限。例如“单身汉”一词,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可以定义为[未婚][成年][男性]三个特征,但我们却不会把教皇、同性恋者、隐士、人猿泰山、能娶四个老婆而只娶了三个的穆斯林男子等称作“单身汉”,尽管他们都符合这三个特征。按照Lakoff(1987),词的定义都要参照一个“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单身汉”的ICM 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世俗社会,一夫一妻制,有一个公认的适合结婚的年龄。跟这个ICM一致的未婚成年男子才是典型的单身汉。 这样一些背景知识是不能跟“单身汉”的词义完全分离开来的。名词如此,动词也一样。跟本文讨论的问题有关,拿“死”来说,“死”不仅仅是“失去生命”,还包括诸如“幼年丧父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等背景知识。同样,“吃”也不仅仅是“食物的咀嚼和下咽”,还包括诸如“吃是一种消耗、应该自食其力”这样一些背景知识。
为了更好地说明动词和相关名词性成分组配上的合格性,我们按照Goldberg(1995)的思路,提出如下的处理办法:将配价看作是句式的属性,(注:个别人提到“句式的配价”,可惜没有展开谈,主要还是在谈句式中具体动词的配价。)另一方面,动词的词义应该用“理想认知模型”来描述。具体说明如下。
4.句式配价
“句式配价”是指抽象的句式配备的、与谓语动词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和类属(指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为了与传统所说的“(动词)配价”相区别,可以改称为句式的“论元”(Arguments )。按照这个定义,“他扔我一个球”属于三价句式,跟“他送我一本书”一样有三个论元,一个施事,一个受事,一个与事,尽管动词“扔”的词义只涉及两个参与角色;而“(她结婚)你送什么?”属于二价句式,含两个论元,一个施事和一个受事,尽管动词“送”的词义涉及三个参与角色。同样,“王冕死了父亲”属于二价句式,跟“他丢了一枚戒指”一样含两个论元,而“王冕的父亲死了”则属于一价句式,只包含一个论元。“他们抢新郎”属于二价句式,如果意思是抢人当女婿,“新郎”是受事,就属于“施事—动作—受事”二价句式;如果意思是抢新郎的钱财,“新郎”是夺事,就属于“施事—动作—夺事”二价句式。
要着重指出的是,不同的句式有不同的句式意义。例如“王冕死了父亲”和“王冕的父亲死了”这两个句式,前一句强调王冕因父亲去世而损失惨重,而后一句只是表明王冕的父亲去世这一事实。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句中看出:
(8)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
? 王冕七十岁上死了父亲。
显然这是因为古稀之年父亡不像幼年丧父那样是个重大损失。上面( 6)“他来了两个客户”所属的句式,其整体意义有“获得”的成分,而动词“来(人)”的ICM告诉我们,来客户是有所得, 来推销员则不是,所以不能说“他来了两个推销员”。
句式的配价或论元主要是由句式的整体意义所决定的,“王冕死了父亲”所属句式的整体意义要求这个句式有两个论元,“王冕的父亲死了”所属句式的整体意义只要求这个句式有一个论元。
5.动词词义的“理想认知模型”
动词词义的“理想认知模型”中包括与动作相关的参与角色(Participant Roles),但不仅仅是参与角色。参与角色和论元的区别在于,句式的论元是比较抽象的,如一般所说的施事、受事、与事等,而动词的参与角色要具体得多,例如“抢”和“偷”的参与角色分别是:
“抢”[抢劫者,被抢者,抢劫物]
“偷”[偷窃者,失窃者,失窃物]
这样具体化是为了说明“抢”和“偷”的ICM不一样。 一个明显差别是参与角色“凸现”的情形不一样:
“抢”[抢劫者 被抢者 抢劫物]
“偷”[偷窃者 被偷者 失窃物]
黑体表示凸现的参与角色,对“抢”而言,抢劫者和被抢者是凸现角色,抢劫物相对是非凸现角色;而对“偷”而言,偷窃者和失窃物是凸现角色,被偷者相对是非凸现角色。这种区别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虽然都是受害者,被抢者所受的损害要比被偷者来得大。例如可以说“他偷走我一分钱”,但不大会说“他抢去我一分钱”,因为一分钱不像是重大损失,而“他抢走了我最后一分钱”就可以说了。在偷窃事件中,失窃物是注意的中心: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钱包,人们首先问他丢了多少钱。但是一个人在马路上遭抢劫,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人受伤害没有,抢走的钱财倒在其次。
区分句式论元和动词的参与角色,这样处理是否增加了层次因而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不然。其实一般区分动词的句法价和语义价,或区分动词的直接配价和间接配价就已经有了两个层次;袁毓林(1998)还把动词的价分为四个层次(联、项、位、元)。(注:分四个层次好像还不够。例如“元”是最低层次,定义为“一个动词在一个简单的基础句中所能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按这个定义“王冕死了父亲”里的“死”应该是二元动词,因为按袁文对基础句的测试方法,这个句子是基础句。(包孕测试:我听说王冕死了父亲;自指测试:王冕死了父亲的消息;删除测试:不能删略成“王冕死了”和“死了父亲”。)但袁毓林(1994)又坚持“死”是一价动词(不无道理),这样在“元”底下就还要加一个层次。)我们的处理相反能使配价系统简化,因为一种语言句式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句式的论元是确定的,论元的数目或类属不同,就成了不同的句式。至于动词的词义要作更详尽的描写,这是必然要走的一步,而且收益不小,能大大提高对句子合格性的解释力(下详)。
6.参与角色、论元、句法成分三者间的匹配
先来看动词的参与角色与句式论元之间的匹配。这种匹配遵循“语义一致原则”:如果参与角色可视为论元的一个实例(instance),则两者在语义上相一致。以表示给予的双宾语句“她送我一件毛衣”为例:
给予句式的论元 [施事与事受事 ]
│ │ │
动词“送”的参与角色[送者收者所送物]
送者是施事的一个实例,收者是与事的一个实例,所送物是受事的一个实例。
动词“扔”的参与角色只有两个,即扔者和被扔物,为什么能进入有三个论元的给予句式?因为动词的词义不仅仅是参与角色,而是一个ICM。只存在一个“扔”,这个“扔”的词义是一个ICM,在这个ICM 中包括这样一些背景知识:人们经常扔球给别人接,扔烟给别人抽等,但不经常扔铅笔给别人写、扔收音机给别人听:
(9)他扔我一只球。
他扔我一支烟。
?他扔我一支铅笔。
??他扔我一台收音机。
以上(5)可以作同样的解释,“写”的ICM包括我们经常写信给人,但不包括经常写春联给人。同样,动词“死”只有一个参与角色,姑且称为“死者”,之所以能进入有两个论元的领主属宾句,是因为如前所说“死”的ICM包括幼年丧父是人生的一大不幸这样的背景知识, 也就是包含一个“受损者”角色。这个“受损者”角色虽然不是“死”的参与角色,但是在语义上跟句式的论元“领有者”相匹配(受损者是受损的领有者)。这样,我们可以把“语义一致原则”的定义范围加以扩展:
如果动词的ICM 中有一个角色(不一定是参与角色)可视为论元的一个实例(instance),则两者在语义上相一致。
前面说动词词义的ICM中还包括参与角色的凸现(prominence )情形,这种凸现情形由于“语义一致原则”的作用也传递给了论元结构,仍以“抢”和“偷”为例:
他抢我十块钱 [施事 夺事 受事]
他偷我十块钱 [施事 夺事 受事]
黑体表示凸现论元。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把动词的词义看作ICM,就不可能有这种论元结构的区别。现在来看句式论元和句法成分(主语、宾语等)之间的匹配。这种匹配遵循有认知基础的“象似原则”: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对应于或“象似”论元之间的关系。(注:沈家煊(2000)指出这种象似是不完全的象似。)具体说明如下。要解释前面(7 )出现的合格性差异,可以建立如下的不等式:
凸现论元>非凸现论元
这个不等式可以解释为:(一)句式中如果凸现论元可以隐去,那么非凸现论元也可以隐去,反之则不然。(二)句式中如果非凸现论元可以作近宾语,那么凸现论元也可以作近宾语,反之则不然。具体说明如下:
(一)如果凸现论元可以隐去(他抢了十块钱),那么非凸现论元也可以隐去(他偷了十块钱),但反过来非凸现论元可以隐去(他抢我),凸现论元不一定能隐去(*他偷我)。 论元隐去就是不以句法成分的形式出现,这种象似关系在认知上的理据是:看得见的东西比看不见的显著。(二)如果非凸现论元可以作近宾语(他偷我十块钱,他偷人十块钱),那么凸现论元也可以作近宾语(他抢我十块钱),但是反过来凸现论元可以作近宾语,非凸现论元不一定能作近宾语(* 他抢人十块钱)。(泛指的“人”作“抢”的夺事不如受事凸现,参看沈家煊2000)。论元跟动词的关系越密切就越凸现,相应的句法成分离动词就越近。这种象似关系在认知上的理据是:近的东西比远的东西显著;两样东西挨得越近,关系就越密切。
7.动词进入句式的条件
动词进入句式,一般的条件是动词义须是句式义的一个实例。例如动词“送”的词义是双宾语给予句式给予义的一个实例,即送是一种给予,所以能说“我送她一件毛衣”。但是动词进入句式还不限于此。当动词义和句式义之间有一种“使成”关系时动词也可以进入相应的句式,常见的有两种情形:
(一)动词表示的是使句式义表示的动作得以实现的“手段”。例如“他扔我一个球”,实际是“他用扔的手段给予我一个球”,“他抢我十块钱”是“他用抢的手段夺取我十块钱”。
(二)动词表示的是使句式义表示的动作得以实现的“原因”:例如“王冕死了父亲”,实际是“王冕由于父亲的死而受损失”。“他来了两个客户”是“他由于有客户来而有所得”。
这种使成关系如前所说也是建立在ICM之上的,如幼年丧父的ICM,来人谈生意的ICM。这种使成关系是人类认识的基本关系之一。 在日常言语中,人们经常用原因转指结果,用手段转指行动,例如:
(10)——你今天迟到了没有?
——路上又堵车了。
(11)——面对歹徒你当时怎么办?
——我操起一把菜刀。
(10)是用原因(堵车)转指结果(迟到),(11)是用手段(操菜刀)转指行动(搏斗)。须知这类转指也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操作,(参看沈家煊1999b)同样是以ICM为基础的:因堵车而迟到,操菜刀而搏斗,都是I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