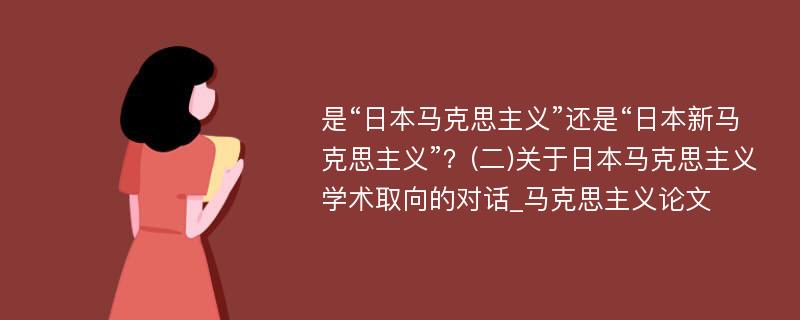
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下)——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术定位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立新:此外,我得为我的“学统”争辩几句,我是张老师批评的一桥大学的毕业生。一桥大学的确是日共的一个阵地,但它的学术并不仅仅是教条化了的斯大林主义。我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译者后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一桥大学是日本国立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如果近代的学问体系可以按照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框架来划分的话,那么,在日本具有深厚的法学和政治学传统的东京大学就是‘国家’,而以经济学和社会学见长的一桥大学则就是‘市民社会’。在相当于校训的《一桥大学宪章》中,第一句就赫然写着‘一桥大学是一座研究市民社会学问的大学’,在一桥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学好SMW走遍天下’,S是指斯密(Smith),M是指马克思(Marx),而W则是指韦伯(Weber),这三个人都是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缔造者。”
我把这段话拿出来,是想说明一桥大学在学术上是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它汇集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即使它的研究受到了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由于它的市民社会传统,它是不可能被等同于教条化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它应该被纳入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中来。举两个例子,张老师刚才提到的平田清明其实是一桥大学的毕业生;另外我花了两年时间来翻译望月这本大部头的著作这件事本身也说明我们并不都是教条化了的斯大林主义,我们的身上有足够的包容性。还有,关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学者,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编辑出了几卷德文版MEGA2,这是一项学术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如果没有对马克思手稿和经济学研究的积累,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的,他们的那一整套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果我不把他们的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也纳入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当中来,恐怕有失公允。我毕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的这一身份也要求我做到相对客观、兼容并蓄,使“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总之,我希望我们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的界定外延更大一些,因为这样做不仅会使更多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而且还有利于我国读者从各自的立场来接触他们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语言习惯上的原因。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确立起一个“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如果一下子使用“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读者会感到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用“日本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更顺。
张一兵:现在我对立新的发言做一个争论性的说明。第一,立新在回答地域性问题时,一上来就说错了一句话,就是他说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作。我们都知道卢卡奇的思想发展是呈一个Z字型的,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马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又臣服于斯大林主义,到了晚年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立新的第一句话就出了问题,这说明拿地域来划分马克思主义流派是不对的。
第二,我在论文里边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划,尽管立新也在讲“物象化论”和“市民社会论”的差别,但我认为他恰恰没有真正领会王南湜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即判断一个思想家的关键不在于观点上的异同,而在于方法论话语的异质性。按照我的判断,广松虽然自认为他区别于苏东,区别于人本主义的西马,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整个研究的基础实际上是科学实证论的,即马赫主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他把这样一种观念,就是经验性的描述本身和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与胡塞尔的意识研究结合起来,然后用这种观点来解读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我把他的这条逻辑称为不自觉的隐性科学主义方法论。他认为自己和人本主义不一样,他的哲学也的确表现出一种方法论上的实证倾向,但这个倾向跟阿尔都塞和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完全一样,它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因此,在广松的整个哲学思想中存在着二元的分裂。我在我的新书当中会非常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部分,另一方面是从马赫到广松哲学体系的部分,在这一体系中,“物象化论”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部分,他提出“物象化论”的目的是让马克思的观点为广松哲学服务。他有严重的认识论倾向,所以他把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转变成“物象化论”。而马克思实际上讲的是客观经济关系本身的颠倒,而拜物教当中的意识层面只是它的反映而已。广松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望月正好跟他相反,他实际上是隐性的人本主义。他虽然没有用人本主义这个概念,但他却把异化论看成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以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理论来解读全部后面的资本论手稿。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弗洛姆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但在文本研究上望月要比他们深入得多。所以我说望月先生是以非常精细的方式复活了人本学,只不过他同样是没有自觉到这一点而已。
韩立新:我只回应一下张老师批评我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即关于广松和望月的差异问题我将另撰文予以论述。我说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故意的,因为在我看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恰恰对这本书重视得不够。我们知道,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解读马克思理论,必须要研究经济学和辩证法以及二者的结合过程。而卢卡奇恰恰是在这本书中,依据当时刚刚出版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手稿,成功地论述了经济学和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的结合过程,而这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极具参考价值,因为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结合了经济学与辩证法,而且做得比黑格尔还好。可惜的是,我国至今还没有将《青年黑格尔》全译过来,这是一个还有待我们发掘的宝藏。
张一兵: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对二战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尽管我们在一些基本的概念定义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我们都认为,日本有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成果是值得我国学术界认真关注和借鉴的。我们相信,它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前沿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