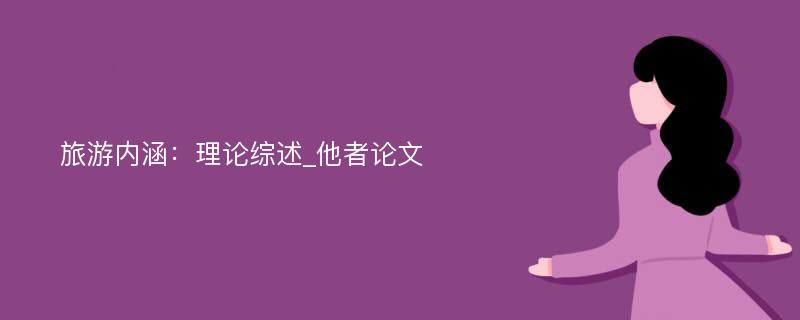
旅游中的涵化:一种理论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理论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李旭东认为“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和工作地前往目的地,在那里停留期间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以及为满足游客需要所建立的一切设施”[1]。这里提到的“目的地”,就是本文所论及的“东道主”地区。游客(客人)来到东道主(主人)的地区除了能够得到游客本身所关注的东西以外,还能体悟到与游客所属文化不同的异文化情调。当然,这种感受应该是双向的,由于游客来自五湖四海,东道主每天所面对的是不同的个体及群体,当然感受也会迥然相异。由于双方的文化接触,这里势必会引出本文所探讨的中心词涵化。
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1938年,赫斯科维茨在《涵化——文化接触的研究》一书中,给出了涵化的定义:“由个别分子所组成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2]P223显然,赫氏这里所意指的涵化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接触而引起的原有文化变迁。1954年,西格尔(B.J.Siegel)、窝格特(E.Z.Voget)和华琛(J.B.Watson)等以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研讨会的名义发表了《涵化——一个探求的表述》,认为涵化“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接而发生的文化变迁”[3]P225。关于这一理论表述,Nash也有相似的论述,“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4]P26。基于上述有关“涵化”概念的界定,本文着重论析的是:游客到东道主社会后,东道主(主人)文化与游客(客人)文化发生接触,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涵化。这种文化涵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关涉到东道主、游客以及旅游地等一切旅游要素,因而,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含义。
一、东道主的失语:地方性表述的困惑与文化边界的漂移
无论是作为一种策略上的表述,还是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分类,地方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5]P68也许,所有明智之士都会明白“地方性”是保留、保存和保持文化多元价值不可或缺的土壤。地方性文化不仅是文化多元赖以生成的基础,也是不同地域之间得以区别的符号,而且也是东道主文化可以彰显的招牌,更是大多数游客所寻觅之所在。然而,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传媒时代的迅猛来势及e时代的普及,也使信息传播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失去了具体的空间界限,使地域文化及人文文化逐渐趋于普同。那些原来相对静止的、小型的、封闭的部落、社区已逐渐被全球化、国家化的力量所渗透、连接,已不能完全代表原有文化的真实。如今,标榜的所谓纯粹的“地方性文化”或许早已成为“全球性的地方文化”了。
对于旅游中的东道主地区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空间坐落,也具有纷繁复杂内部结构。东道主社会文化不仅是一种动态存在的文化实体,而且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然而,随着诸如电视、广播、新闻、网络等现代传媒的介入,东道主地区旅游的策划者会情不自禁的受到这些媒介的影响,在其打造自己文化品牌的同时,难免会加入现代元素,主动迎合现代民众的审美需求,使其成为现代民众能够接受的审美体验。东道主地区的文化,在现代元素的渗透下,必然会发生过渡和转型(shifting)。在这种情况下,“东道主”的地方性表述,无非是在与外界互动和对话中逐渐建构出来的。换言之,旅游地的东道主,为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等游客的需要,会将这些人的声音加以内化,最终来完成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更有甚者,通过对游客进行想象来建构自己,也就是说,东道主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会充分考虑观光游客的观点以及游客对于异乡情调的想象,以此来修正和构建自己本民族、本区域文化更多的内涵,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游客到东道主社会所见到的地方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地方策略下的文化。
当然,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更应该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一体’与‘文化多元’是一对孪生子,如果贸然把自己的特色拿去作金钱交换,事实上是无法使这种交换长时间地继续下地去的,那么,悲剧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6]P264由此可见,东道主社会的地方性表述是苍白无力,没有其真正的实质内涵。
伴随着地方性表述的困惑,东道主有形文化的边界也将逐渐模糊。本文所指的“文化边界”是指东道主地区与其他地区区分的界限,通常与东道主民众居住区域的边界是重合的。当然,这种文化边界的模糊,对于东道主与游客来说应该是双向的。东道主为了走进他者(游客)的世界,希望具有异质文化的“他者”能够正视自己的文化内涵,领略其内在的文化真谛,根据对游客喜好的想像来建构自己。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东道主与游客之间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来面对彼此文化的互为异质的话,那么文化之间的传播就不可能是单向的。换言之,对于游客而言,东道主就是他们眼中的“他者”,游客要想真正走进“他者”文化空间,就必须放弃自己本文化的一些束缚,以东道主的身份领略其中。
或许,在现实旅游当中,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地位并不一定平等。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及发达地区的游客,自己本身就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到达东道主国或地区后对当地民众将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所谓“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主要指当地居民对外来旅游者的行为举止、态度和消费方式的吸收和接受”[7]P143。但这种示范效应并不一定具有毁灭性。从旅游跨文化交流过程的微观层面看,东道主地的民众行为也会对游客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在这样一个崇尚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更是如此。也许,当游客短暂的旅行结束时,也正是东道主服务行将结束之时,也许二者之间的主角不会再见面,但双方文化的碰撞或许还将继续。然而,在二者表层文化趋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隐藏在东道主民众心底的深层价值观念是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的差别。显性文化即表层文化,如:语言、服饰、饮食、生活方式等;而隐性文化即深层文化,如当地民众的心理、民众的感情、民众的信念、民群的意志和自尊心等。对于民众的隐性文化是需要细致体察和真切感悟才能领会的,在当地民众的意识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最为尊贵和神圣的。同理,对于游客的隐性文化来说,也具有同样的特性。
综上所述,传媒时代的来临,使东道主地方性表述发生了危机。在地方性知识本身受到异质文化层层叠加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发生异化。所以在现代语境下,需要对东道主的地方性表述作出新的评估与界定。与地方性表述相伴而生的就是东道主有形的文化边界开始漂移。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无形的文化围墙已经在全球化语境下慢慢倒塌。甚至,游客的文化边界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是文化的发展所使然,变是绝对的,不变才是相对的。
二、游客与东道主:凝视的“涵化”
1992年,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凝视的著述为基础,英国社会学家提出旅游凝概理论。有学者将旅游凝视理论概括为:“‘旅游凝视’是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是旅游者施加于旅游地的一种作用力,旅游者拍摄旅游地人文事象的摄影行为以及各类旅游广告图片等都是‘旅游凝视’的具体化和有形化,旅游地由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社会性地重新构建”。约翰·厄里(John Urry)认为旅游凝视的性质具有以下几点:第一,反向的生活性;第二,支配性;第三,变化性;第四,符号性;第五,社会性;第六,不平等性。”[8]P212从以上关于旅游凝视理论的表述,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凝视(gaze)也是一个涉及认识与被认识、支配与被支配等非对等权力关系的概念,是游客施加在东道主社会的一种内在作用力。
在旅游当中,游客是凝视的主体,东道主处在被凝视的地位,是被凝视者。当游客到达东道主社会时,对东道主社会的凝视对象无非是那些以图像、旅游广告等呈现出来的自然文化景观,通过对东道主社会的视觉体验及其对东道主社会进行社会性的重构,来达到自己愉悦体验的目的。这其中,游客对于东道主社会的凝视必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而东道主社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根据游客的审美要求来构建自己的文化。这其中其实隐含着游客(凝视者)与东道主(被凝视者)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具体来说,游客的文化往往对东道主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支配性。当游客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凝视时,一定会来到东道主社会来寻找这种旅游欲求,而东道主社会为了迎合游客凝视的需求,会根据游客的需要对自己原有的文化进行重新建构。东道主社会往往将那些承载着自身历史、文化记忆的景观,通过某种转换而脱离原来文化语境,使其更符合游客的需要,成为游客凝视的对象。
正是由于游客的凝视,驯服了东道主社会,而东道主社会在游客凝视所具有的压迫、强势之下,使其在自觉、不自觉地将游客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融入自身的行为、思想中。有的东道主社会的民众为了与游客产生亲近感,改变其自身的装束,来缓解由于双方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压力,相伴而来的,自身的文化特色也随之而削减。随着游客大量涌入东道主社会,那些异族、异地文化也必将大量随之侵入,再加上不同游客的凝视对象对东道主社会的文化和居民有着一定的规约作用,从而导致了东道主社会的文化特色也逐渐淡化甚至消亡。这些都是东道主与游客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所引发的凝视结果。
假使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是彼此互相欣赏的双向凝视,其结果应该有所不同。约翰·厄里(John Urry)将旅游凝视类型分为五种,但其中认为最主要的是浪漫主义的(romantic)和集体主义的(collective)。浪漫主义的凝视强调的是与凝视对象的某种孤独的、私人的和半精神性的关系。这类群体一般是指那些自助旅游、背包族以及探险家等。而集体主义的凝视是需要大量的和自己一样的其他游客在场,主要是指那些喜欢集体狂欢方式的度假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凝视现象,东道主与游客之间就没有强势与弱势的气氛,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基调。游客也许因为喜欢东道主的地方,而选择长期居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东道主与游客的互为凝视,可能会使东道主发现本文化的真正价值,顿悟到吸引游客凝视的真正所在及本地旅游业得以发展的根本,从而带来东道主文化的自省与自觉。在这股力量的驱动下,东道主社会会自觉地进行本文化回归,对原来被破坏的文化事象进行还原或修复。甚至,东道主社会将早已失传的文化表达方式纷纷挖掘出来,期望得到游客更多的凝视,当然这里有利益的怂恿。由此可见,当游客进入到东道主社会时,如果游客没有携带任何文化偏见,并且能与东道主民众进行真正的交流,这样不仅会让东道主民众对自身文化产生自醒,而且会诱发东道主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构认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游客与东道主的互为凝视,可以提升东道主传承与创新自身文化的内在激情。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游客对东道主社会的凝视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东道主社会发展本地旅游业的动力源泉,也是东道主社会迷失自己的根源所在。同时,它也又是东道主社会寻回文化本真内在驱动力。
三、变迁与固守:协商的涵化
文化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所谓文化变迁是指“由于民族的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9]P216引发文化变迁的途径可谓多种多样,如进化、发明、发现、传播或借用等。本文所提到的文化变迁,是由于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接触所引发的涵化,从而导致文化的变迁。当然,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至于东道主与游客之间是否按照“他者”的某些行为习惯来重构自己,则要根据彼此对异己文化的理解来决定。也就是说,双方都具有选择的权利。
在现代化语境下,旅游可以说是人们拓展生活空间一种现代途径。正如瓦伦·L·史密斯所言:“旅游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是“人类的探索行为,它使生命变得有意义”,旅游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可以使我们从这个枯燥的世界中摆脱出来,以获得身心上的恢复”。[lo]P22-23因此我们可以并不十分恰当地说,居家生活和广义上的旅游作为人类生活互补的两极,共同构成当今人类生存、发展与完善的图景。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游客来到东道主社会时,应该想得到的是:愉悦身心或是领略异域风情抑或享受“他者”文化的不同。那么,对于东道主社会而言,他们所提供的服务除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之外,就是满足当地居民在经济、社会及心理方面的需要。不难看出,东道主和游客都是把满足自身的需要作为行为动机的。现如今,旅游业已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性产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快的一个产业类型,对于全世界的资源、环境、就业以及文化交流等都会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发展好本地的旅游业,对于东道主社会来说,可谓意义重大。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东道主与游客接触后,如果东道主所求与游客所需之间没有一个利益上的平衡点,这一旅游活动是不能持续下去的。毋庸置疑,社会交换理论将会对此做出近似合理的解释。“社会交换理论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行为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11]当游客来到东道主社会时,表达出自己的需要时,交换就应该开始了。当然,双方的这种交换应该是一种理性的交换而非盲目性的,因为双方都明白自己在这次交换中所要得到的东西。当游客旅行结束时,一定会对自己的这次旅行做一下简单的梳理。衡量一下自己在这次旅行中的收获,是身心得到舒展还是精神得到饱餐。假使没有取得这些结果,本次交换的结束可能预示着永久的结束。反之,东道主也不例外,他们为游客所提供的一切,如果所得到的收益为负,那么下一次类似的交换就不可能发生。如果双方对本次交换作出的评价结果是收益大于付出,那么双方会尽最大的能力保持交换的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道主文化与游客文化接触后所引发的涵化现象,应该依双方的利益而定,将有利于本文化发展的东西吸纳进来,不利于本文化发展的东西将会遭到摒弃。对于游客而言,他们也许会从东道主文化那里得到某些启发,对自己的文化进行重新建构。同理,对于东道主社会亦会如此。因为“尽管各种文化对本身和对别的文化所做的表述远远不同,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却绝对不是互不了解的。它们在世界上非但不是孤立的,而且恰恰是其‘合作’或在特定背景下的‘联盟’才铸就了或长或短,成就不等的历史阶段,这种积累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命运。”[12]P7
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东道主文化与游客文化的涵化整合,所形成的文化创新问题。文化创新,对于东道主社会来说,不仅有利于自己旅游业发展,同时也能满足于游客的猎奇、愉悦身心的目的;也会对文化的真实地带不可进入的缺憾做出弥补。但是这种创新不是让自己原有文化面目全非的创新,而是要吸收“他者”文化精髓同时,以本文化为根基,加入现代的元素,来满足游客的追求。这种文化创新不仅使东道主社会的经济利益得到提升,还可以加强东道主社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当然,在这种传承与延续的过程中,应该始终秉有一种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因为任何文化的存在,都是该群体或民族的独特需要,双方不应该依自己的文化的观点,轻易地对“他者”的文化加以评价。
综上所述,旅游当中东道主文化与游客文化接触后,所形成的涵化对于双方来说,不是所有文化都被异己力量吸收或排斥,而是双方都有权利进行选择。他们将“他者”文化中有益于自己文化发展的部分,吸纳到本文化中来,然后加以调适整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从而满足“他者”和自己的需要。在旅游当中,如果东道主与游客之间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那么双方的涵化过程将会是一个“协商”过程。
四、结语
在旅游当中,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与东道主社会的接触,会引发不同的涵化路径。一方面是游客文化对东道主社会的多方面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东道主文化对游客文化的涵化,也是旅游场域当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面对旅游中的这一涵化现象,我们应该更多地保有一种宽容与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涵化,在使其地方性的表述发生困惑,文化边界发生模糊的同时,也使其能够吸纳游客文化的精髓而进行自我文化的创新,这是东道主社会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力量之基。而东道主对游客的涵化,可以使游客更深层的体会到异文化的不同,甚至对自己原有的某些价值观念开始重新定位,显然,这对于消除双方的理解壁垒将具有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