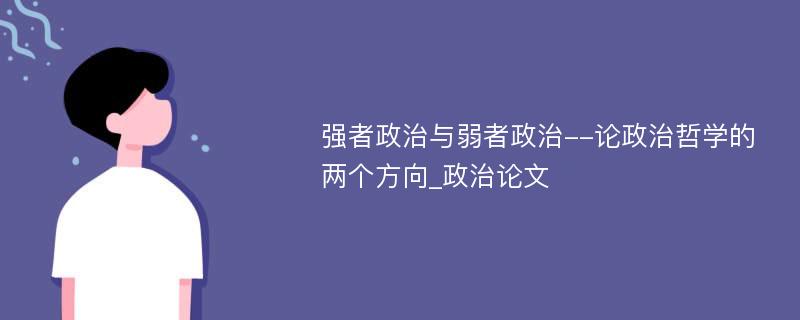
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试论政治哲学中的两种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两种论文,弱者论文,强者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罗尔斯以来,现代主流政治哲学的主题一直围绕着“正义”展开。发展者只是对正义的内涵(平等还是自由;以及何种平等、哪一类自由)进行争论与辨析,但是大多没有超出“正义”的范畴之外。即使是罗尔斯的批评者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具有类似凝聚力的总概念与其抗衡。这一点似乎正说明了“学术范式”的路径锁定力量。我们以为,突破范式的狭隘性的一种方式就是认真对待其他范式。在与现代性政治哲学范式差距很大的古典政治范式中,固然可以看到对“正义”的关注,但是我们还可以察觉到另外一个重要观念在发挥着统辖性目的作用,那就是“幸福”。
在此有人可能会立即提出异议:现代性政治也关心“幸福”,发展人民的福利正是现代效用主义政府的一个经常性任务保证(罗尔斯不是自称正是为了抗衡“长久占据政治哲学主流”的效用主义范式才提出正义论范式的吗)?但是,此“幸福”非彼“幸福”。如果说现代政治所讲的幸福是日常的、各人自由选择的利益目标的实现,那么古典政治中所集中关注的“幸福”就特指客观的终极完满至高的存在。这样的古典幸福概念,在现代性政治哲学诸门派看来,属于彻底“非政治”的私人旨趣,政治哲学对之只应表示沉默。
这样的疑点导致了我们提出一个理论假设:是否可以把整个政治哲学思考划分为两个十分不同的方向或维度:“强者政治学”和“弱者政治学”。它们无论在领域上、本体论上和目标上都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一划分将给政治哲学研究者带来许多富于启发的结果。
一 政治哲学的两种方向
让我们首先确定概念。政治思考的两种方向的依据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考虑是领域上的。“政治”的一般定义是“公共权力”。在这一定义中,已经可以识别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垄断暴力与公共事务。如果说前一个领域是“权力”(主权),那么后一个领域就是“权力的功能”(主权的行使)。这两个领域尽管有关,但是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它们各自面对一批问题。政治哲学史上不同的思想家的兴奋点经常只及其一,而不及其他。比如同样都是“社会契约论者”,洛克和卢梭等所热切关心的主题乃是“权力”:主权的来源、创制和制约等等。而罗尔斯却几乎完全不关心这一主题,只是成篇累牍地讨论政治应当维系何种“权利”才是公平正义的。这种区分绝非像罗尔斯自己所想象的是社会契约论在具体或抽象层次上的运用之不同,而是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领域(方向)的政治学的关注。
权力政治学属于强者政治学,而权力任务政治学属于弱者政治学,这几乎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但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正确”,西方政治哲学家避免这类语词。尼采对“弱者”的种种贬低说辞,更加使得有关概念牵连出了许多不合法的联想。① 然而此处之区分是一种严格理论上的领域特征描述,在价值上是中立的。“权力(power)拥有者”顾名思义就是“强者”(the powerful),而不拥有权力的平民当然是弱者。弱者期待于政治的,正是主权者为他们伸张正义,报复或抵御伤害。这从国家起源的国防说(比如修昔底德)和司法说(比如赫西阿德)中,都可以得到比较具象的验证。
第二,从本体论上讲,更能清楚看出“强者”和“弱者”的概念并没有任何褒贬羼杂其中。“强”意味着自足存在(巴门尼德),而“弱”意味着关系性存在。然而所有人包括自以为是强者的人,其实都是弱者;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独立“自足”的存在。人之在甚至在其自在存在中就已经被他者击穿,从而根本无法免除命运的摆布。政治权力可以被视为增强力量、超越私人、弥补缺陷存在的一种努力,但是终究无法完全达到自在自为之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智术师之口提出一种“弱者妥协”社会契约论时,确实是不无嘲讽之意的。但是现代社会契约论者高蒂耶在论证道德的必要性时援用了这一个例子,却是十分认真和肯定的:社会契约建立在人本质上是弱者的基础上。②
第三,从目标上说,强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终极“幸福”,这是一阶的或个人自己的生活价值;弱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正义,这是二阶的或人际道德价值。现代政治哲学由于“民主”、“平等”、“去政治化”等等启蒙观念的深刻影响和压力,把主权者仅仅规定为服务者,感到讨论强者的幸福有违“政治正确”,所以大多回避此种问题;同时底气十足地讨论权力任务领域中的种种目标——“正义”或者“福利”。然而,权力拥有者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独立人生目标?而且,作为强势存在者,主权者很自然会追求更为积极性的、舒张开展型的、美好高尚的目标。相反,无权力者自然会追求负面的、免灾性的、防卫性的目标,希望道德和权力保障安全、基本福利以及正义。
二 古典政治哲学对幸福的攀登
在政治哲学的两种取向中,不同的时代会选取不同的侧重点。古典政治总体来说是一种强者政治学。作为终极人生生活目标的幸福,在这个范式中是一个合法的问题,而且是吸引了人们注意力的焦点问题。是否存在“幸福的技艺”,谁拥有这样的高级技艺?是频频被人追问的问题。不足为奇的是,“幸福”的核心内涵主要被理解为“自由”——自足和自主。这主要依靠政治实现。这样的幸福不一定是权利拥有者占有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完全可能是更为高尚的公共行动追求。古代的政治领导人往往是个人(君主制)。不过,国家也可以是政治上的强者,这从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对强国雅典的赞词就可以看到。而且,这样的幸福在古代与“德性”这一强者概念又紧密不可分;有德性者才有幸福。这与古代政治中战争(国际政治)的重要性可能有密切关系。③
强者政治关心“幸福”,但是并不意味着认为权力拥有者必然能获得强者式“幸福”。实际上,古典政治思考的很大部分是在惊讶为什么所谓“强者”如此脆弱,幸福为什么永远如梦如幻。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历史、雅典的悲剧等等,如果有一贯“主题”在其中,这就是主题。古代历史并不是弱者的历史,而是强者(包括强国)的故事。但是从小亚国王克洛罗索到波斯大帝薛西斯,再到战败波斯大军的雅典和斯巴达领导人,无不体现了“强者不强”的史家洞见。悲剧更是如此。悲剧表面上看在争吵着“正义”,但是其更深刻意义是命运必然粉碎强者。④ 在人世间追求神才配得上的目标,失败才是更为自然的结果。
柏拉图继承了“强者政治学”取向的基本路径,同时又将其创造性地转换。《理想国》和《高尔吉亚》本来都是从讨论“正义”开始的,但是“正义”属于典型的弱者政治学议题。智术师在抨击正义时最终都抓住这一点:我们高贵强者难道甘愿受到弱者的险恶卑鄙诡计(正义)的束缚吗?⑤ 柏拉图无法回避这一挑战,于是他也诉诸主权者的“幸福”而捍卫正义。柏拉图论证的奥妙是将日常理解的“正义”完全转变含义,转变成“正义的原因”或“内心的正义”或灵魂的健康。这正是“幸福”。依托这样的转换,柏拉图可以主动出击,频频追问“谁是真正的强者?谁真正关心领导的幸福?”的问题,也就是强者政治学的问题。不明就里的智术师陷入其中,屡屡败落沉默。不过,把正义化为幸福,实际上是把弱者政治学彻底转变成强者政治学。对这一策略怎么看?赞成者不妨首肯柏拉图的机智和深刻。反对者则可以指出这样做在理论上的困难,比如“x的原因就是x”的思路是否合法;此外,还可能存在政治哲学本身的问题:把弱者政治学化为强者政治学,把二阶问题化为一阶问题,把主体间问题化为主体内部问题,这么做难道没有消解他人的重要性从而“正义”的真正意义?⑥
亚里士多德突出总结了希腊公民共和主义的基本精神,即作为所有公民整体的强者政治学。他在《尼格马克伦理学》一开始就明确他的思路是终极目的论的,而在《政治学》的开头又明确论证说按照这样的目的论,政治不可能服务于经济,相反,经济服务于政治。作为新本体的政治本体,必有其自身目的;而且既然调动一国之力追求,必是最高目的。作为“行动”的城邦生活、共同掌握自主之权力提供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人的政治类美德的最佳机会,意味着人之为人的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大序上的最高点——“幸福”或终极目的(Telos)——的达到。这一古典政治范式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进入充分自我意识之后,一直把握了许多人的思考。最为明显的当然是西塞罗和普鲁塔克的共和主义。西塞罗作为罗马共和主义者,确实更多地关心弱者政治学领域中的问题,比如保护财产权;但是他并没有忘却希腊共和主义的主题:政治家的幸福。⑦ 不过在此我们想指出的是,即使是被一般认为“反政治”的晚期希腊哲学也是以极端化的形式保存和光大着共和自由的强者政治价值理念。无论是斯多亚派还是伊壁鸠鲁派,其主导问题都渗透着这一意识:“什么是真正的强者,什么是终极幸福、亦即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足’”?“什么是奴役,什么是做自己的主人”?“什么是无法受伤的强悍”?⑧
三 “强”与“弱”的转化及其深入
与古典政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政治的主要关注点是弱者政治。从领域上看,政治的任务——无论是保护消极自由、人身和财产安全、福利还是“正义”——真正成为中心议题。“领导人的幸福”和帝国的荣耀几乎失去被提出来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加以讨论的合法性。从本体论上看,人类终于承认我们都是平等的凡人,必须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主体——主体间——主体的消亡,成为启蒙之后哲学本体论的逻辑发展路线。康德—罗尔斯传统的政治哲学也许凸显了这一趋势,其政治学背后的预设正是多元分立主体关系的独立重要性(而不是像在柏拉图那里把关系性正义问题变形为单个主体内部问题间接地予以解决)。所以,如果说古典政治的长处在于关心灵魂,所短在于不关心他人的真正独立地位;那么现代性政治所短在于忘却了灵魂的幸福,其长处在于关心他者。
强与弱的转换不是简单的,而是辩证性的;现代性的权力政治甚至也由“强者政治”转变为“弱者政治”,而这背后的原因却是弱者变强。洛克以来自由主义的权力政治学其实是权力制约学。现代政治在处理权力问题时预设了人民是权力的拥有者和委托者(trustor);而政治领导人却成了受托服务于人民的“公务员”。于是,本来超越于社会(关系)之上、保护正义的主权者也被纳入到“正义”关系之中。权力行使者在承诺为“神圣私人权利”服务的契约中得到权力的使用权。因此违背了这一契约就是“不正义”。可以想象尼采会多么痛恨这一“巧妙的奴隶道德技巧”。
强者的弱化还不止于此。一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发展到它的逻辑极端,最终指向自己。在一些新的批评者看来,社会契约论及其本体论还不够彻底,还没有真正打碎强者的硬核;所以应当继续“强者弱化”——把刚刚变强的新公民也变弱。这就是后现代学术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有的是被动的,比如或是提示人们在现代大国政治中个人其实拥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或是渲染现代生活的荒谬性和内心的非理性对人的摆布使所有人都脆弱无助等;但是,有的“弱化工程”则更为积极主动,论证应当选择弱者立场,开放自我,放弃自足,进入关系性存在,与他人命运共存。女权主义运动中不少人就可以作如是观。在她们看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包括权利正义和理性人之预设)体现的是“男性”本体论,它强化和扩展了西方政治传统中的强者的、主体的、征服性的倾向,而从根本上忽略或轻视了女性的感受。⑨ 女权主义的这一看法并不是孤立的。从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出发的德法现象学也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和相应的本体论。海德格尔对西方认识论传统的批判众所周知,而曾经从学于海德格尔的列维纳斯更推进了海德格尔,因为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说到底还是纯粹主体的,关心的是孤独个体的本真化,妨碍了我们对于他者的承认。
在列维纳斯看来,唯有夸张地强调他者的无比尊严,弱化自我的诉求,才能打破西方传统中的强主体意识,确立“正义”问题的独立地位。在作为列维纳斯的“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中,其基本命题就是他者优先于自我,而且构成了自我。自我屈从于他者的召唤,对其负有责任。很显然,这种不对称的关系甚至超出了“正义”关系。这种与整个西方政治伦理的主流格格不入的思想的目的正是为了打开强者政治学内化(消化)一切的强势把握力量,从而真正使得他者独立。列维纳斯反对西方的本体论,因为它用存在的同一性去统一一切,这意味着用自我征服一切。列维纳斯指出,从形而上学上说,“异”或“差异”先于统一,而且总是无法被“同一”所完全统一,所以是“无限”。这个差异,就是他者(的他性,alterity)。列维纳斯对此的最为著名的讨论可能就是“他人脸庞”的不可穷尽性。他者的脸上有悲哭、赤裸无助、对我的召唤,这质疑了主体的完全自由,宣告了不许杀人之道德诫命。明白了其中涵义之后的主体放弃了主权和统治,朝向他者的脸,成为一切为了他者的主体,对他者负责的主体,受苦受虐的主体。⑩
当然,“弱化主体”会不会在确立他者的尊严的同时抹煞了自我的价值?现代政治中的强者政治维度(权利自由主义)难道没有重要意义?对暴政的抵御难道仅仅靠贬低自己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是列维纳斯责任伦理学的出发点。前者的名言一直被列维纳斯引用:“我们对我们面前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有过错(有罪),我比其他人更有错(罪)”。这会不会导向道德自虐,给自己加上无法承受的重负,造成精神危机?圣徒总是不断责备自己无法做到高标准的要求(路德的觉醒)。有些女权主义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指出无限自我弱化的潜在危险。(11)
四、对新共和主义自由观的反思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学(方向)的存在是可以得到论证的。承认其问题域、本体论、气质、目标、德性的不同,将有助于人们的深入研究分析;甚至承认两种政治学维度之间在关联的同时存在潜在的冲突可能,也比回避和遮掩更能有助于解决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一节中将使用这一模型重新审视晚近共和主义发展中的一些争论。
我们知道,共和主义也是反对现代性的主流政治哲学自由主义而兴起的一种学术传统。开始时人们认为共和主义就是强调政治参与的重要,这是受阿伦特为代表的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影响的思潮(包括波考克等人);此外,由于麦金泰尔等人的努力,“美德生活”重新确立了自己在政治哲学话语中的一席合法地位。(12) 然而,最近以佩迪特为代表的一批“新共和主义”者又提出了一种“罗马式”的共和主义,其精神与“希腊式”的共和主义大相异趣,并不推崇统一的共同好(政治幸福)生活,而是突出一种负面抵制性的“共和自由”,即用立法的方式阻止“任意干涉”(支配)。佩迪特说自己的理论得到了斯金纳的历史研究的肯定:这一共和自由正是从意大利城邦到美国革命的现代共和主义者所追求的。然而,佩迪特的想法虽然机智,但是并不透彻,这从他提出这一理论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质疑就可以看出。(13) 他希望在柏林的“两种自由”之外确立“第三种自由”,但是他提出的这种共和自由与所谓“现代人的自由”——消极自由——十分接近,几乎难以区分。它也是否定性的而非积极性的,是免除干预。至于佩迪特分辩说“消极自由”观念中没有建立法律保护的自由的思想,则显得缺乏依据。
我们认为,新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及其困难可以从强者政治学和弱者政治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佩迪特等人之所以严格避开“希腊式共和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种共和主义属于典型的强者政治学的幸福诉求,它在现代性范式中一直被视为失去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合法资格。所以,佩迪特是从消极自由开始摸索“第三种自由”。尽管他后来把它规定为罗马式共和自由,但是其中的弱者政治基本特色依然明显:这种自由属于权力任务学的领域,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13) 佩迪特回避强势的共和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在现代性中直接宣传雅典共和生活,显得天真而梦幻,忽视了自由主义对直接民主的戒备的基本洞见,很容易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
但是在我们看来,现代政治依然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认真对待希腊式共和主义。换句话说,毋需回避强者政治学维度。至少,只有正视主权者的“终极幸福”问题,才能真正认识到主权者异化的诱惑的真实可能性。这种幸福的内核也是“自由”。正如佩迪特—斯金纳从“消极自由”中析离出了一种类似的、但是又相对独立的“第三种自由”一样,从“积极自由”中也可以析离出一种类似的、但是也与之不同的“第四种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正面意义的政治幸福,其根本内涵是人类征服障碍而舒张生命、充当命运的主人、实现真正的创造力本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不同的生活形式出面代表整个社会实现这种自由对命运的冲击。政治肯定也可以充当这种崇高代表者之一。如果只是像公共选择论那样理解政治的本质,人类将永远在猪的城邦中打滚,而这是人类的血性(thumos)所难以接受的。这种自由—幸福与所谓积极自由虽然有一定的亲缘性,但是有重大的不同:柏林讲的积极自由更多在强调“战胜自己”从而暗含了更多的自我压抑之危险,但是我们讲的共和自由更多地讲“战胜他者”,从而不必有如此不良的暗含。
如果对于“第四种自由”的规定有道理,那么我们可以据此回过头来重新反思佩迪特所提出的“第三种自由”。虽然佩迪特尽量把它说成是弱者政治中的议题,我们认为它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属于强者政治。第三种自由的核心是(政治所保护的)人格尊严,它其实是“第四种自由”的另一个面相,都是强者——主人的自由。从正面讲,是力量的充沛发挥;从否面讲,是不允许其他人的力量的充沛发挥侵犯到我的力量。从自由的价值上看,它与消极自由的区别在于:消极自由虽然也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选择和生活的非侵犯,但是这一自由只有工具性的价值,终极目标在于非政治领域中的其他事情。但是第三种自由却把法律保护的非侵犯状态(一种政治状态)当成具有目的性价值的东西而珍惜。佩迪特自己也看到:古典共和主义者在讲到“第三种自由”的时候多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进行说明:共和主义者最为痛恨的就是受到他人的任意支配,不得不卑躬屈膝、小心翼翼、拍马顺溜。(14) 所以立法杜绝这种状态。然而他应当进一步想到:谁会在众多“政治问题”中特别关注“支配”问题?(15) 谁有资格享有免除这样的状态的自由?谁有资格阻断他人的无限权力的侵犯?当然是主人、强者、王者。在罗马以及对于罗马人而言,完全的自由与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16) 马基雅维利认为,唯有强势阳刚的virtue,才能激励一个民族从奴役下解放出来;阴柔奴性的民族则不配享有这样的自由。(17)
注释:
①不过,这种语词的暴力在许多哲人那里不起作用:想想“主奴之争辩证法”和“卑贱者最聪明”之说。
②Gauthier,Morals by Agreement,Clarendon Press,1987,p.306ff.
③德性在古代主要是男子气的、英雄气概的、强者的。参看曼斯菲尔德:《马基雅维利的Virtue》,任军锋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118页;并参看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10页。
④人是神的玩物。强者遭受的伤害只会比弱者更多、更可怕。纽斯邦在其巨著《完美为何如此脆弱》中系统讨论了希腊文献对人间幸福的脆弱的深切反思;见M.Nussbaum,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但是纽斯邦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反思主要围绕强者展开。
⑤参看Plato,Gorgias,483B,491C—492C。智术师不懂强者不强的古训,他们在论证强者破坏正义时,诉诸的“幸福”显然是“生命力”(自由)意义上的强者幸福。
⑥有关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柏拉图的分配正义学说上,而且体现在其惩罚正义理论上,参看M.M.Mackenzie,Plato on Punish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94ff.
⑦参看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页;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⑧参看爱毕克泰德的《哲学谈话录》和伊壁鸠鲁等的《自然与快乐》。
⑨Virginia Held," Noncontractual Society:A Feminist View," in Hanen and Nielsen,eds.Science,Morality,and Feminist Theory,p.113.
⑩有关列维纳斯的思想,我们受惠于同莫伟民和孙向晨等的讨论。可以看到,这种“后现代弱者政治”其实在前现代就有类似的萌芽。塞涅卡和孟子虽然都有强势的一面,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主体的脆弱——他人的痛苦能够伤到自我,因为自我的本质是开放的、感受性的,他人的痛苦会使我受伤。不过,政治强者不必为之惭愧、蒙羞,反而应该感到珍惜,因为这一脆弱性恰恰标识了真正的人性。
(11)参看金利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714页。
(12)参看佩迪特:《消极自由:自由主义的与共和主义的》,应奇、刘训练编:《第三种自由》,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13)参看应奇:《论第三种自由概念》,《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4)(15)参看佩迪特:《共和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41页。
(16)参看阿兰·博耶:《论古代共和主义的现代意义》,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0页。
(17)参看佩迪特:《消极自由:自由主义的与共和主义的》,应奇、刘训练编:《第三种自由》,第205页。
(18)参看曼斯菲尔德:《马基雅维利的Virtue》,任军锋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第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