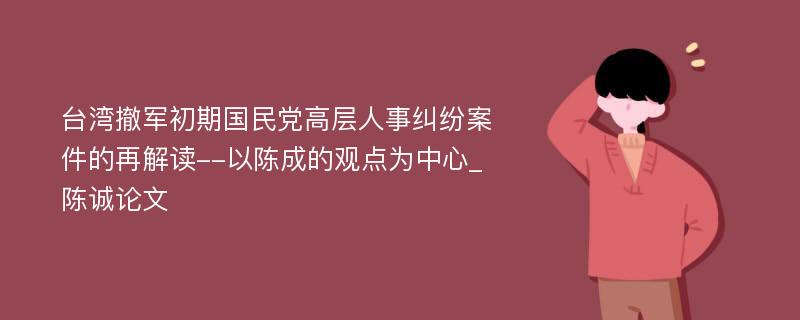
退台初期国民党高层人事纠纷几桩个案的再解读——侧重陈诚的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国民党论文,初期论文,纠纷论文,高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148-09
1949年1月初,受蒋介石重托,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年底因故离任,1950年3月初,又被蒋选中出任行政院院长。短短几年时间,陈诚为稳定在台湾的局面,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治台方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地方自治、生产建设等,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些情况,已有一些论著作了阐述,笔者在此不拟再展开讨论,而是想就这几年中发生的与陈诚有关无关的几件事情,提出来略作梳理,使我们可以大致感受一下,陈诚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什么样的政治氛围、政治处境下,来做那些事,从而了解到,这其中的难度和挑战,甚至超出了做这些事情本身。
一、陈诚是否不欢迎蒋介石来台
1949年5月初国民党军即将撤离上海前夕,蒋介石于6日上船,7日乘蒋经国让招商局准备的轮船“江静轮”离开上海,由蒋经国陪同,一路向南,9日到舟山群岛定海、普陀一带,巡游数日,盘桓至17日午餐后,由“江静轮”登岸,下午1时半自定海机场出发,4时50分飞抵(澎湖)马公降落,驻于马公宾馆。21日,陈诚、俞鸿钧、蒋鼎文到马公见蒋。26日,蒋介石自马公飞台南冈山,转高雄寿山,6月14日,又专程到离高雄100多公里的四重溪察看,“此地为恒春之风景区,四面环山,中有温泉,清甘可饮,更可涤身,周围景物,酷似江南。”蒋在此歇宿一晚。蒋介石在台湾南部走走停停前后近一月,于6月21日下午离开高雄,自冈山飞至桃园,转至大溪镇。“大溪镇有山有溪,风景与气氛很像家乡溪口”。24日上午,蒋离开大溪,到台北参加东南区军事会议,并于当日迁居台北草山。① 这时距从上海出发,已近50余日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蒋为何不直接去台北?主要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照吴国桢的说法,是因为陈诚未及时表示欢迎态度,引起了蒋的疑心。吴国桢说:“上海失守后,蒋乘一艘炮艇离开大陆,他给当时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和台湾省主席陈诚将军打电报说,他正向(台湾)岛驶来,蒋预料陈会马上回电欢迎,但等了24小时,陈仍未回电。外界对此事并不知道,蒋不得不让他的炮艇,绕舟山群岛转了24小时。我想蒋不会因此而原谅陈,以前他总是很信任陈的,我怀疑他这时是否还信任他。”“24小时以后陈诚的回电来了。蒋决定不在离陈诚的省会台北仅20英里的北方海港基隆上陆,而改在台湾的南港高雄”,原因是陈诚的部队在北部,南部主要是孙立人的部队,吴国桢称,“当蒋在高雄上岸时”,还问孙,“你对我在此上岸有何想法?”[1]
吴的回忆多有不确之处。1.蒋不是乘的一艘炮艇,而是“江静轮”;② 2.陈诚的职务还只是省主席;3.蒋在舟山群岛一带不是转了24小时,而是前后活动了八九天;4.蒋到台湾是乘飞机,而不是乘船“上岸”,也不是先到高雄,而是先到马公。
上述这些漏洞还只是技术上的,在实质内容上,在此之前,陈诚已为蒋去台做了许多前期准备,还发了好几封电报欢迎蒋去台。陈诚回忆,他接任不久,1月21日到杭州见蒋介石,25日返台。“我自京返台后,即在台湾准备八个地方,以供总统选用为临时驻用之所,计澎湖二处,台北、阳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各一处。于修葺布置完妥后,即迭电请总统莅台。”[2]在当时国民党大批军政高层官员退台,台湾住所极为紧张的情况下,陈诚的这些准备,虽有过事铺张之嫌,但就蒋陈关系言,不正是反映了陈对蒋的忠诚不贰吗?蒋离开大陆到台后,这八处地方,至少实地考察了六处,其中就蒋经国对四重溪、大溪两地的评价看,陈诚可谓用心良苦。3月15日,陈奉代总统李宗仁召到南京述职,17日,再飞溪口见蒋。和谈决裂,解放军渡江后,4月25日,蒋离开溪口到上海。这时,上海之失守也只是时间问题,故4月29日,陈诚即电请蒋介石直接退驻台北:“总裁蒋钧鉴:和谈决裂后,大局已告明朗化。今后剿共战事,势必长期奋斗到底。为号召国内外爱国志士,及联合国际上反共势力,钧座为自由中国之旌旗,驻节所在地点,亟宜早日确定。关于马公岛情势(蒋曾提出过要驻马公?——引者),职业已实施勘查,深觉该地交通通讯,颇为不便。职认为台湾,既为吾人革命复兴最后根据地,殊无其他顾虑之必要。拟恳早日驾临台北,长期驻跸,则指挥各方,皆多便利。或于穗沪渝等处,设置行辕,必要时,巡行指挥。除积极布置此间官邸外,谨祈早日命驾,无任企祷之至。职陈诚。卯艳叩。”[3]蒋离开上海乘轮南下后,5月11日,陈诚再有一电致蒋:“探呈总裁蒋钧鉴(蒋这时已成惊弓之鸟,连陈诚也不清楚蒋的具体行踪?——引者):卯艳一电计达。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国一切组织松懈,与限于法令,亦无法秘密也。”[4]11日正是蒋介石到舟山的第三天,吴国桢指的应该就是这份电报,但因为有十几天前的那份电报存在,吴的说法恐怕就不易成立。15日,陈诚再电蒋介石表示对李宗仁的不满,请蒋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总裁蒋:辰寒(14)电奉悉。读李之谈话,深感领袖受辱,干部之耻也。彼辈只知利害与力量,决不能以理喻与情动。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又职决铣日飞穗,最迟巧日回台,谨闻。”[5]18日陈诚返台后,21日到马公见蒋。
应当说,从整个蒋陈关系来看,一方面,应当不存在陈故意不回电、使蒋难堪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在当时离心离德的部属数不胜数、整个局势分崩离析那种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即使是对陈诚这种过去极为信任的部下,蒋是否也存有戒心,要观察、观望一段时间呢?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从陈诚任职头几个月蒋经国、宋美龄的往来电报中,似乎能窥到些许端倪。
到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内战形势的越来越恶化,若大陆不保后退居台湾,可说渐渐成为蒋家的共识。1948年12月27日蒋经国电告在美国的宋美龄,蒋介石打算下野返溪口暂住,宋美龄在12月27、28日连发两份电报,认为不妥,建议选择广东或台湾,电称:“奉化绝非安全居住之所,免得受人暗算,广东、台湾似较相宜。”“汝父在京如不能维持,则须赴台湾或广州,决不能回乡……如下野回乡,对内不能行使政权,对外不能代表国家,无法继续革命……故此举余绝对反对。”[6]在此前的12月7日,陈诚也上书蒋介石称:“惟默察大局,演变至此,决非枝节所能挽救,必须从战略政略上,作通盘之计划……目前战略,应以广州为中心,以海南、台湾为后方基地,争取时间,积极部署”。[7]因此,12月28日,蒋介石突然致电在台养病的陈诚,告以“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为要”。29日即将命令发表,并于1949年1月1日、2日连电催促:“为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必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何日就职立复。”[8]与此同时,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可以说,蒋家以台湾为最后庇护所之“全盘计划”主意打定后,对于具体负责实施者,陈诚成为其首屈一指的人选。
到1949年1月初,宋美龄甚至提议蒋介石为健康与安全起见,可以先到加拿大。22日,她致电蒋经国,让他“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不是美国——引者)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2月7日,宋又发一电:“父安全问题确须顾虑,余亦曾屡电提及倘能出国一行,亲自考察军事科学以备将来改进军队之张本最好……否则亦以迁往台湾为宜,总之,家乡实非安全之地”。[9]
对蒋而言,1月底蒋下野之后,局势进一步恶化,蒋氏父子处于越来越强烈的焦虑之中,这在蒋经国致宋美龄的电函中体现得十分清楚:2月3日:“时局正在恶变中,内心忧虑万分”;2月10日:“对于父亲之安全问题自应严加注意。人心之坏,出人意料,万分寒心。薛(岳)之态度暂无特殊之表示”;2月18日:“陈仪曾联络共匪谋和,幸早得发现,未成事实。时局不安,人心大变,前途殊堪忧也”;3月8日:“某方(指桂系——引者)正在计划作投降式之和平”,“内部不久恐难免分裂”,“某方积极发动李之正位运动,并要求父亲出国”,“江南军纪不好士气不振,难作坚强之抵抗”。到3月13日,蒋经国终于对陈诚都有点失去信心了:“(一)李已正式提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其目的似在利用何作为工具,而进行夺取全部政权之阴谋;(二)高级官吏多已脱离中央立场,而投向对方,吾人似益孤立;(三)粤薛(岳)之态度近来甚坏;(四)陈在台湾恐亦不能持久”。[10]
此处讲陈诚不能持久,是讲困难太大陈诚会顶不住,还是指对蒋的忠诚难以持久?从上文意思来看,我觉得指的是后者——是担心陈诚也不再对蒋忠诚!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国桢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但其起因可能不是陈诚不欢迎蒋去台,而是蒋介石担心陈诚不欢迎。
还有一种说法称,“在1949年5月蒋介石到台湾前,美国曾阻止蒋去台湾,但没有成功”。[11]据说,1949年3至5月,美国国务院两位著名高级幕僚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秘密意见说帖”,均有弃蒋考虑。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持人肯楠提出,“邀请孙立人将军参加(美国)占领军的新政权。如他肯接受此任,则我们分化中国驻台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通知蒋委员长,如伊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之身份相待”。美国国务院参事莫成德奉艾奇逊之命赴台考察后,主张以孙立人替代陈诚为省主席,其密电中说:“我们所需要者,乃一干练笃实之人,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亦不必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氏经验或有未足,但其他条件,却甚相合。”[12]与之相对应的说法是,蒋此时暂不去台,乃因顾忌美国:“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对美国多有顾忌,担心在国共内战失利且美国放弃援助的情势下,去台湾会对其不利,故多次对莅台踌躇裹足。”[13]因此,究竟是陈电中“殊无其他顾虑之必要”的话打动了蒋,还是陈未及时复电使蒋犹豫呢?
二、吴国桢取代陈诚省主席一职的前前后后
陈诚将省主席职务让出给吴国桢一事,起因于美国方面的一个动作。1949年11月初,曾任美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忽然电约时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赴美一行,台湾方面对此邀请寄望甚殷。郑介民应约赴美,归时带回一份重要文件,即美国海军上将白吉尔与郑介民的谈话记录,时间为1949年11月17日下午3时半,担任记录与翻译的为国民党政府驻美武官皮宗敢。其中最重要之点为,台湾如果对省政府进行改组,让吴国桢出任省主席,则美国将承诺恢复对台援助。
以下为白吉尔对郑介民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
关于防御台湾——我人(白氏自称,以下同)有以下之拟议:
(一)希望中国做到者,为改革台湾政治……希望台湾政府能代表各阶层各党派之利益,而非国民党一党专政……吾人认为陈诚将军之行政尚未成功,吴国桢先生在渝市及沪市之成就甚佳,美方认为彼为主持台政之理想人选……若吴氏主持台政,应给予彼完全之权力,以任用良好之干部……
(二)以上建议若能获得委员长之批准及支持,则美政府可以进行以下各事:
甲、派遣经济顾问团来台,协助台湾当局,计划办理工业、财政、商务、农业、行政诸事务,人数以不超过三十人为限。
乙、派遣非现役之军官,每军别约二十人及三十人来台,协助台湾海陆空军,策划办理补给计划、军队行政与训练诸项业务。但彼等不参加第一线作战指挥……
丙、物资方面
(A)陆军 供给台湾孙立人部防卫军六个师之装备。
(B)海军 供给海军巡逻舰十六艘。
(C)空军 供给必要之零件材料及修理设备。
(D)供给少数之雷达站及军用通讯器材……
本人所以告知阁下者,即欲阁下转达蒋委员长可以于此时向美政府提出类似以上之请求。以上拟议系美国社会知名之士向本人及其他军政负责人所提出,而由我辈向美国当局提出。当局对此已作极友善及极感兴趣之考虑。若再由蒋委员长向当局提出类似之请求,必可收取相当成果。③
对于当时惶惶不可终日,且将美国视为唯一救命稻草的蒋政权而言,④ 白吉尔开出的这个条件确实是很有诱惑力的。12月初,郑介民返台,将此上呈时在成都的蒋介石,蒋让王世杰与陈诚先行商议。陈诚表示,就他个人及整个大局而言,他可以让出省主席一职,因为当前“财政上的负担确是很重,开源节流,均极困难,尤其是要完成反共抗俄大业,势非争取国际同情不可。如美国确能改变态度,对我援助,则凡美方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应加以考虑,而予以接受。绝不可为了我个人的进退,而关闭了中美合作之门。”[14]
蒋自成都返台后,与陈商量,为不失去这一机会,又避免万一“上当”太失脸面,省主席一职还是陈诚担任,而由吴国桢以省府秘书长的地位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负责处理省政。但次日蒋找王世杰、吴国桢谈话时,吴拒绝接受。蒋又找陈诚谈,陈“坚决表示愿意将台省主席职务完全辞去,以便吴氏可以单独负责。但总统始终迟疑,又接着连说:‘太冒险,太冒险。’商谈至此,遂算大致达到决定阶段,即准我辞去台省主席,而由吴国桢接充。不过总统对于财政方面还是很不放心,对于财政厅长一职,不主张遽易新人……但吴氏因为预谋已久,故即此亦不惜以去就力争。我也向总统建议,吴氏既不信任严家淦,以后恐难合作,不如由吴氏另找替人”。[15]于是12月15日正式公布了这一改组方案,21日履行了新旧交接仪式。
吴国桢上任后,第一件事自然就是请美国兑现承诺。他会晤美国驻台总领事阿德格,托他转达美政府:台湾省政已依照美方意旨改组,希望美方履行诺言,从速援助。阿德格转电美国务院请示,美国务院“不独没有正面答复,且于23日秘密通令驻外各使领馆人员不得过问台湾内政”。1950年1月5日,美总统及国务卿相继发表声明,强调对华政策并无变更,没有考虑对台军援。“一时外电纷传,人心惶恐,恍如大祸即将临头,岌岌不可终日。”[16]
为探明真相,当局乃电驻美“大使”顾维钧,令其就近探明具复。顾维钧将此意向美国务院主管外次提出后,美外次答称,所云已办各项改革“皆贵国当局应作之事。昨闻新任吴省长告美副武官谓美政府所希望各项新政,均已照办云云,不无误会。美政府之关注,只在贵国自动改善一切,俾于保卫台湾……并无其他意见云云。彼又询台湾军事方面有何改革,归谁统辖,闻海陆空司令各自行动,征用人民房屋物品,骚扰居民,省长无权过问,而孙立人将军拥虚名而无实权,故亦无法控制。长此以往,仍难望所办之改革发生效验。吴省长前任极困难之上海市长,成绩甚佳,但亦因受军事当局之牵制,不能尽量发挥其能力。此次当予以宽大职权”。[17]
按照顾维钧的回忆,顾维钧见美外次,即“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是在12月23日下午。顾的回忆录所载相关内容比电报详细,但意思基本相同,其中关键的一段是:“吴国桢在同美国驻台湾助理武官谈话时曾说,美国政府期待中国进行的一切改革都已经办了。他(巴特沃思)不理解这一点,因为美国政府从未建议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具体步骤。它所感到关切的是中国政府应该为台湾人民谋幸福,以保证他们的忠诚,从而巩固台湾抵御共产党入侵的防务。”[18]见国务院的人这样说,12月27日,顾维钧又让皮宗敢去找白吉尔,白吉尔反问他,为什么孙立人将军没有充分的实权,并且还有比他职位高的人干预他的工作,也即台湾的政治调整并没有真正到位。1950年1月1日,美国各报登载了一条“显然来自”国务院方面的电讯,大意是杜鲁门总统不会改变其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他已裁决不派美国军队占领台湾;在向台湾提供一些政治和经济援助的同时,将不给予军事援助,但不会反对国民党政府雇用非官方顾问来帮助台湾。1月4日下午,在皮宗敢为白吉尔夫妇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白吉尔说,他在提出援华问题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他决定不再介入,以免在同政府的关系中陷于尴尬地位,并暗示障碍在于国务院的反对。[19]
实际上,白吉尔的建议仅代表军方部分人的意见,包括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人。军方的意见并不能左右政府,而以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杜鲁门总统以及前国务卿马歇尔等人对蒋介石仍十分反感,并未改变不在军事上援助台湾的政策。他们乐于见到蒋介石、陈诚等强人将权力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优秀、开明、清廉的吴国桢、孙立人等人手中,这一点与军方部分将领的意见接近,但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并没有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恢复对国民党军援的考虑。而且,美国政府一方面根本不承认有所谓承诺,二是包括军方在内对台湾当局政治调整的力度仍不满意,要求继续扩大他们所看好的吴国桢、孙立人的权限,极而言之,是最好能取代蒋介石的地位,以促使台湾政权进一步驶向符合美国人价值观的、也更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轨道。这是一个如意算盘,但其实也是对中国独裁政治本质的认识终究还存在着隔膜的表现。
据美国有关情报机构1949年9月间的判断,陈诚是效忠蒋的,孙立人并不盲目效忠:“福摩萨有大约50万人的军队,包括6万人的战斗部队。孙立人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并不盲目追随蒋介石,他现在是福摩萨战斗部队的总司令。毫无疑问忠于蒋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仍然控制着军事物资的供应,陈孙之间缺少合作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孙立人也不能从福摩萨的贮备中获取足够的物资供应。”[20]美国人制作了一份国民党残余武装情况表,其中“效忠对象”一栏,陈诚、胡宗南、张群是“蒋介石”,白崇禧是“李宗仁”,马步芳、马鸿逵是“自己”,卢汉、薛岳、余汉谋是“不确定”。[21]建立于这种判断之上,明确说陈不合适,让陈下来,要吴、孙上去的美国人,意图究竟何在呢?他们对蒋的再生能力,对蒋在台改革,从而稳定台湾局势,抵御共产党攻击的能力毫无信心,而急于要培植一种能制衡,甚至取代蒋的力量,以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并被苏联所利用,对他们在远东以致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
陈诚让出省主席一职,及蒋介石同意此事,并不是因为吴国桢比陈诚更合适,而仅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让美国愿意向台湾提供援助。这种安排,本来就说明吴国桢缺乏像陈诚一样的权力基础。吴国桢在实力、权位、资望等许多方面都逊于陈诚,虽然在外有美国人撑腰,在内却应当算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省主席。但吴却做得非常强势和张扬,⑤ 这样,蒋吴决裂是迟早的事。果然,半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虽然还不是国民党人所迫切期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已经足够刺激美国人的神经,原来似乎遥不可及的美援应声而至,蒋介石不必再为乞求美援而必须用谁、不用谁了。这样一来,本来蒋也很欣赏,但经过美国人一闹变得好像是美国人硬塞给蒋,甚至要以之压蒋的吴国桢、孙立人等人,在台湾政坛还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吗?
1949年12月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台湾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能够接受一个并非正式的美方提议,不惜将精心策划的退守台湾最为重要的人事布局之一加以更改,反映出其对美援的寄望与依赖之殷,也凸显了吴国桢出任此职所肩负的重任。如果美援因吴的出任如期而至,自然皆大欢喜,然而美援并未因此而来,吴却与当时台湾的主流政治游戏规则背道而驰,与当时台湾政坛最核心的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均有分歧,当利用他以钓来美援的作用基本失去时,吴的政治行情必然会低于他获得省主席职位以前,甚至更糟糕得多,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⑥
三、王世杰案是怎么回事?
蒋介石下野之后,作为其“私人参谋机构”的核心成员,一直随侍左右的主要是蒋经国、王世杰、吴国桢、黄少谷、张其昀、沈昌焕等。⑦ 蒋在台复职后,王世杰即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据说行政院院长一职先是考虑的他,他不愿接,才选了陈诚,可见蒋介石倚畀之重。但1953年底,却突然传来他被免职的消息。11月18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着即免职”。18日,消息即已传到美国,美联社的报道称,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已辞职,大概是因为津贴了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问题。
事情的原委据说是,原国民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为避免其在海外的资产落到共产党手中,由陈纳德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民用航空公司,将两航的股权出卖给这家公司。但此前两航有价值约125万美元的股权属于泛美航空公司,为购回这些股权,须先从中国航空公司在美国的存款中划出相应部分由民用航空公司给付。这笔款子已经移交给了民用航空公司,但在美国被冻结了,泛美航空公司并未拿到,台湾当局只得再拿钱出来给泛美航空公司,条件是待原来冻结在美国的钱解冻后,民用航空公司即将之归还给台当局,等于是台当局为赎回泛美航空的同一笔股份出了两次钱。⑧ 可是民用航空公司从美国银行取得这笔款子后,并未及时归还。蒋介石在责询行政院相关部门未尽职责,着手调查时,却发现此事的责任在总统府,是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拟了一个推迟催促民用航空公司归还这笔款子的签呈,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同意了。事情到这一步,蒋介石责怪是王世杰没有将事情讲清楚,否则他是绝对不会批准的。蒋发现王世杰的建议是根据一位姓端木的人的请求做的,便怀疑王世杰通过端木与民用航空公司有什么幕后交易,于是以上述措辞严厉的八个字免除了王世杰的职务。⑨
这里需要对该案的重要牵连者端木作点插叙。据《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此端木名端木杰,“是和陈纳德做那笔交易时的交通部长(?),后来又是民用航空公司的法律顾问”。(陈红民著《蒋介石的后半生》也讲是端木杰)经查,端木杰,安徽安庆人,陆军军需学校第1期毕业。1914年7月任陆军军需学校教员,后升任教官、教务主任,1928年12月任军政部军需署营造司司长,1933年任少将军需总监,1934年秋任交通部参事,1937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副部长,1945年2月任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6年6月任粮食部政务次长,同年底辞职,1947年春当选为立法委员,1949年3月任交通部部长兼中航公司董事长。11月端木杰在香港与中共取得联系,在两航起义后的诉讼中,作出不利于台湾方面的证词,1950年1月被免去交通部部长职务,1950年12月返回广州,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72年1月11日于北京病逝。
但据《徐永昌日记》,此端木名端木愷,1953年11月19日“九时许,伯聪(魏道明——引者)来,谈蒋先生因陈纳德民航公司欠政府美金一百二十五万,该公司现因赔累不拟再还一事,怒王雪艇秘书长何以不早催其还……前日突将陈辞修王雪艇一起叫去,责王腐败官僚与端木愷有勾结(端木现执律师业,似负某造辩护之责,曾有签呈陈总统,王则择由注意见转总统,总统批可。现在总统以其择由有避重就轻、有意蒙蔽云云)。王言敢以人格担保其无,并反指长官不应如此出言。陈从旁劝解,蒋责陈无能误事,国家所以至此……王归即上辞呈,蒋掷地不理,径下条以不尽职责,着即免职……余谓,就个人观察,觉王对蒋先生很忠,亦颇顾大局,人亦学者。伯聪谓,不然,王很阴谋揽权,结党贪污。是则出余意料之外”。[22]端木愷,安徽当涂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留美,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任过法学教授,1934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1941年任行政院会计长,1947年8月任粮食部政务次长,1949年8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同年去台湾,任总统府顾问,并执律师业,1969年起任东吴大学校长,1987年逝世。[23]
笔者以为,此端木是端木愷的可能性大。以端木愷留美法学博士、法学教授的资历,容易与王世杰接近,1949年任总统府顾问,时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关系也吻合;有留美经历,易与美国人打交道,执律师业,符合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法律顾问的身份;端木愷去了台湾,而端木杰1950年就投向了大陆;徐日记是中文影印本,顾回忆录是英文译本,我怀疑有可能是顾维钧回忆录的译者将“端木愷”译成了“端木杰”,前者似可靠些。
以王世杰在国民党内的历史与贡献,尤其是退台前后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就算这125万未收回王世杰有责任,蒋介石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台湾高层当时即有人议论,此事“前因很多,此次发作之事件恐系表面”。陈诚、吴铁城出面为王说情,蒋或在日记中骂陈诚,或对吴铁城发火,⑩ 其症结何在呢?一种说法是,王世杰被免的真正原因,是背后谈话不慎,被情治单位的人员监听到并上报,蒋一怒之下将其免职:“总统府前秘书长王世杰于去年12月间,突被免职……台湾来人告桢谓王之免职,实因其谈话不慎,为特务所密设之录音机录出,报告钧座,是以有此结果。特务之在各处,甚至私人住所,密设录音机器,桢固知之。但王案之是否如此,桢不敢必。惟在钧座未宣布王案真情以前,桢不能不认为此种说法,有其相当根据。”(11) 如果说,位高如王世杰者,都会受到监听,此时二蒋的手段,实在了得,只是不知蒋经国有没有用这种手段,对付陈诚、彭孟缉等人。(12)
四、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
蒋介石退台初期,在高层权力斗争方面,实际上很快即面临一明一暗、前后相续的两个战场。明的是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争斗,但随着桂系的实力在大陆丧失,李宗仁由港到美,蒋介石复职,桂系的威胁渐趋消失。暗的却是一文一武、渐成气候的吴国桢、孙立人,成了对蒋介石权威构成挑战的新势力,这两股势力的冒头都离不开美国人的操纵,都有以之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意图。尤其是李宗仁渐渐淡出后,美国政府和军方都在为吴国桢、孙立人向蒋介石要实权,多次通过不同管道传递这类信息,压蒋就范。(13) 这时的台湾要生存,唯一的希望是美国,杜鲁门对蒋介石又很不客气,蒋介石不得不耐着性子。但美国人越是抬高吴、孙,蒋的心里就越是嫉忌吴、孙,套用一句中国的老话,爱之,适足以害之。到美国民主党一下台,进入艾森豪威尔时代,形势一变,吴国桢、孙立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这是这两个案子发生的背景。
吴国桢靠着美国一个未能兑现的承诺上台,已属尴尬,上任之后,军、政、台湾地方均无深厚背景的他,却十分强势,不与陈诚、严家淦合作,又明与彭孟缉等人,暗中实与蒋经国争高低,甚至公开向蒋介石叫板,说什么“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的硬话。[24]胆识,胆识,笔者佩服吴国桢的胆量,但不佩服他的见识。吴以受过美国教育、具有民主信念自许,号称“民主先生”,要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威权相抗衡,纳台湾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也不看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的手下。他追随蒋介石这么多年,在国民党内浸淫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自信了,或许他以为自己可以是个例外,以为蒋介石在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会彻底改弦更张,放手让他施展,甚至不惜束缚住蒋经国的手脚,事实证明他错了。又或许他以为,蒋介石要保台湾,就必须靠美国,要靠美国,就离不开他。如果说,朝鲜战争之前,他这样想想还无妨,朝鲜战争之后,他还这样想,就未免迟钝了。所幸他脱身得快,比之稍后的孙立人,还算幸运得多,吴国桢出事了,同样是美国人看好的孙立人,没看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不思急流勇退,还想着该他来做参谋总长,结果输得更惨。
在国民党军队中,孙立人是少数有美国军校背景的高级将领之一,在中印缅战区有上佳表现,深受美国人欣赏。但抗战胜利不久被调到台湾任陆军编练司令,不受重用,国民政府退台初期,却因其美国背景突然走红起来,1949年底被任命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3月出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俨然台湾军方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与吴国桢相似的是,他与军中其他高级将领关系很差,“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了三票对一票的否决。”他的一位老部下评价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另一点与吴国桢同样的是,他也抵制蒋经国的特务政工人员对军队的渗透,“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他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和小蒋为敌”。[25]这种局面,二蒋不拿他开刀才怪。
吴国桢事件告一段落,1954年6月,孙被调离陆军总司令职位,改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5月即发生了所谓孙立人兵变案,指控孙的部下要乘蒋介石到南部屏东阅兵时以武力要挟蒋介石重用孙,接下来更抖出孙的部下郭廷亮等一批官兵通共的“匪谍案”,6月间起,孙即被长期软禁,郭廷亮被判死刑,后经蒋特批改判无期,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共谍”案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让人惊愕的是,30多年后,1988年3月23日,台湾《自立晚报》独家发表了郭廷亮关于此案的“陈情书”,其中写道,郭廷亮在1955年5月25日被秘密逮捕后的最初10天,不停地被严刑拷打,强迫其承认是“匪谍”,“有谋叛之意图”,以及与孙立人将军有“非法”关系。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公然要求郭廷亮“扮演假匪谍自首”。7月14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郭廷亮接到其公馆谈话,说“为了使这次的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使郭廷亮不再抗拒:“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主任等所杜撰编造。”为应付陈诚、王宠惠、王云五等九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核查,9月9日晚,毛人凤再召见郭廷亮,对他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如果郭廷亮的陈情书属实,那么当年孙案的性质何堪再问。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去台仅仅几年时间内,在发生了这几个看似孤立的事件后,蒋下野时所倚重的为数不多的大员中,又有几名要角出局。从此,台湾政坛基本只剩下了两种人,一种是绝对效忠蒋氏父子,尤其是追随蒋经国、对蒋经国的继位不构成任何威胁者,如彭孟缉、俞大维、严家淦之类;一种是地位与实力均较有限的台籍人士。在这种被蒋家日渐净化(恶化)的政治生态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鹤立鸡群的陈诚,实在是个异数。其实,越到后来,陈诚越是显得突兀,而且,台湾政坛的容量就那么大,要做点事,就要有权,要有权,就难免与别的掌权者发生碰撞,谁还能与陈诚发生碰撞呢?那自然非蒋经国莫属。还在1950年8月,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正儿八经地谈论此事了:“如今,福摩萨行政集团内部存在很多重大的内部张力,这些矛盾正在削弱政府的统治。较为显著的矛盾是:(1)聚焦于省政府内的陈诚与吴国桢之间的政治分歧;(2)在中央改造委员会和国防部之间的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私怨。”[26]在稍后蒋经国的权力进一步上升之后,美国人认为,“蒋经国目前的权力根基并不完全能够确保他继承大位,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依靠他的父亲……他倡导使用极权主义的手段来击败中国共产党,这使他成为那些主张采用更为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国民党中国未来问题的人的敌人。蒋经国的首要对手是陈诚,他是目前的行政院长和蒋介石的忠诚副手。”[27]1954年2月魏道明对徐永昌也谈到,“辞修年来很布置势力,此为蒋先生所不喜……今辞修与经国已摩擦甚”。[28]陈诚这样敏感的地位,二蒋能不对他大大地睁着眼睛?各种真假传闻、蜚短流长能不包围着他?在这样的环境下,陈诚能够从从容容做那么些事,除了陈一直对蒋表现忠诚、肯做事敢做事能做事、身有痼疾肯定熬不过蒋经国等因素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在捧吴、孙压蒋的同时,将他划在蒋的一边一并打压,反终于使他能够在位高权重的情形下得以善终,阿弥陀佛,真不容易。
注释:
① 此段据蒋经国日记《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5月5日至6月24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实践出版社,1985年,304-333页。
② 5月8日蒋经国致宋美龄电所用“总统府文电稿”的信笺左下角就加盖了注明发电位置的“江静轮船”章,这批文电加盖的同类印章有溪口、普陀山、马公岛、高雄、草山等。参见《蒋经国书信集——与宋美龄往来函电》(影印本)(上),台北“国史馆”,2009年,110页。
③ 《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台北“国史馆”,2005年,84-85页。《顾维钧回忆录》则称这次会谈的时间是11月19日,所记白吉尔谈话内容大致相同,惟个别细节有出入:援助海军的军舰是12艘而非16艘,并提到援助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替换已经证明为不适应局势的陈诚,人选最好是吴国桢……要给新的省主席以充分的权力”。(《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530-531页)否定陈诚的意思更明显。
④ 读这段时间的《徐永昌日记》可以感受到,当时退台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对台湾到底能否守住十分关心,且大多抱悲观态度。1950年1月2日,徐晚饭后访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询其对保守台湾有无把握,谓,毫无。余以为应提供一守台必须之办法请蒋先生执行,不行即辞职,毋恋栈,自败而败国。渠以为应先提辞呈,不准时再提计划。答以更好。”(《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10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页,1950年1月2日)“美国劝告台湾美侨速撤离台湾。”(7日)白崇禧对徐永昌谈及李宗仁“谓渠极不赞成其出国之举,询余李应如何是好。答以最好开诚团结,归做副总统,不然只有待万一台湾失败,期做将来之戴高乐。”(13日)
⑤ 在1950年3月初蒋拟任用陈诚出任行政院院长的问题上,吴国桢竟以辞职来要挟,“吴国桢以辞修出掌行政院,其心不安,坚求辞职”。在陈“组阁”过程中,吴国桢坚持不合作态度,蒋介石再三规劝,有意让其担任副院长兼省主席,吴仍“坚执不允”。蒋又邀吴国桢夫妇聚餐,宋美龄也出面调解,“劝告其强勉忍耐,与陈合作”。3月11日,蒋陈最终确定名单后,吴国桢又突然“以财政部长不能与其省府合作,要求其自兼部长相胁”。“余以名单已定,而且已提常会,不能改动告之,而彼仍要求不置,美使馆也间接表示支持国桢,心滋不怿,最后仍照原定名单提案通过,不管美国之态度如何也”。(参见陈红民、赵兴胜等《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29-32页。引号中内容为蒋介石1950年2月22日、3月4日、3月11日日记)此处的“财政部长”是严家淦,即吴国桢数月前非要从省财政厅厅长任上拿下者。美国政府明确其拒绝对台军援的立场已近三个月了,吴国桢的分量并不像此前所传的那样重,用了吴,美援也没有来,不事事迁就吴,美国又能怎样呢?这是蒋介石“不管”的理由。其实,白吉尔“神话”落空之后,蒋介石这样对吴,已算够客气的了。这时,陈诚辞了省主席,摇身一变,成了行政院院长,恐怕也反映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可惜吴氏不察,还沉醉于有美国人撑腰的幻想中。
⑥ 据吴国桢回忆,陈诚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就“公开指责我用欺诈手段猎取省主席一职。按他的说法,我在美国掀起了对我的个人宣传,并骗使中央政府任命我为省主席,借口说任命之后美援就来。他这么说,我当然怒不可遏”。“从那以后,尽管他是行政院长,但由于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省政府,所以不管我制定什么计划,我就自行其是,不同他商量。”《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31页。
⑦ 参见《吴国桢口述回忆》,83、86、93页。另据1949年11月6日司徒雷登与郑介民在华盛顿谈话的备忘录,郑介民告诉司徒雷登,现在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是这四个人:王世杰、吴国桢、唐纵、黄少谷,蒋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CC派已失去影响。这与吴国桢回忆的名单虽有出入,但均包括王世杰在内。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The Far East:China Volume IX/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Formosa (Taiwan).pp.412-413.
⑧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512-514页。
⑨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0册,514-515页。
⑩ 参见《徐永昌日记》,第11册,225、227页,1953年11月19日,26日。《蒋介石的后半生》,270页。
(11) 吴国桢1954年在美国发表的致蒋介石公开信,见《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429页。
(12) 吴国桢即说陈诚最信任的一个仆人也被蒋经国收买,“我们所有的电话都被窃听”。《吴国桢口述回忆》,175页。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中有大量此类记载,此处不一一征引。
标签:陈诚论文; 吴国桢论文; 孙立人论文; 王世杰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蒋介石论文; 国民党论文; 蒋经国论文; 李宗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