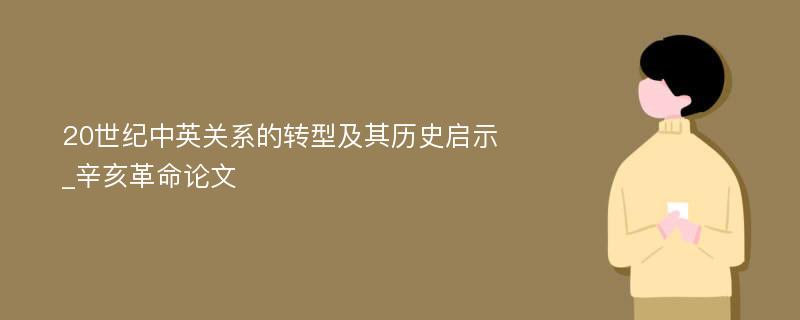
20世纪中英关系的转变及其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英论文,启示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我国经历的三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中,中英关系也几经转折。本文拟从我国对外关系的角度,集中探讨中英关系转化的原因及影响。
一 英国对辛亥革命的粗暴干涉和决定性影响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侵华方面和方式的增多、程度的加剧,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遽然兴起,中国开始步入谋求成为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并且力争改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不平等地位的历史阶段。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根本愿望就是要最终废除列强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挣脱外来控制的枷锁,实现民族独立与自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未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但是“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一部分。)。
辛亥革命前,英国在华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十分可观。英国向以商贸立国,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华商贸利益较其他列强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以1870年中英直接贸易额合计为100的话,1910年则骤升至168.5,而且我国被置于严重的入超国地位,1913年中英贸易仍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左右(注:C·F·雷麦《外国在华投资》(C.F.Remer,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纽约1968年版,第354-355页。)。 中英贸易在各通商口岸间的贸易中占的比例也最高。直到辛亥革命前,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各项不平等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达69处之多,其中英国占28处,居首位,其次是日本占25处(注: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6-21页。)。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表明, 英国在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与通商口岸间贸易中所占的总值,均高于日、德、法、美诸国所占的总值。(注:《1911年中国海关部署贸易收益与贸易报告》(China:The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911),上海1912年,第42页。)。 鉴于英国在华主要利益是商业和经济方面,因此英国当局最关切的必然是在华权益。
我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方面,英国也始终占有绝对优势。英商太古、怡和两公司排挤我轮船招商局,长期把持我沿海及内河航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控制着我国对外、对内航运的41%(注:C·F·雷麦《外国在华投资》(C.F.Remer,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纽约1968年版,第354-356页。)。 长江流域是英国攘夺的“势力范围”,当然英国更看重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筑路权、筑路借款权,以及掠夺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等。1898至1914年间,英国在华争得的铁路筑路权为列强之冠,当时我国有限的已筑和待筑的铁路中有2 万余公里与英国有关,受英国控制的已建成的铁路达8千公里以上。在此期间, 英国对华铁路投资合计1800万英镑以上,我方仅损失回扣即不下140 万英镑,年付息达900万元(民国初年折合90万英镑),迄1922 年已累计欠英方各项款额1600余万英镑,与其对华铁路投资总额已相差无几了(注:束世徵《中英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37-139页。)。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 在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总额为600万英镑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过程中,英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既借巨款,清政府为将路权从商民手中收回出卖给借款诸国,颁发了“干路国有”上谕,遂激起四川商民的保路运动并涉及全国各地,酿成武昌起义的诱因。
清末民初,英国外交代表对中国政府具有特殊的影响力,是英国在华享有可观的政治利益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任期最久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早与袁世凯私交甚笃,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被举为北京公使团领袖公使,可见他在崩溃的清王朝及北京公使团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了。总之,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华拥有巨大的、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权益。因此,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必然是继续保持和扩大这些既得的权益。
英国利用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从外交、军事、财经等方面干涉辛亥革命,扶植政治野心家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英国对武昌起义爆发是有准备的,而且也准备采取相应的外交和军事对策。尽管当时武昌爆发的反清革命并无排外性质,甚至革命军政府做出了“不反帝”的对外承诺(注:《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153 页;第227页;第2册第58页。),然而英国当局仍增兵京津做好了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同时,调遣英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巡弋,并获得清政府保证其镇压革命的军事行动不会危及该地区租界及各国利益。为阻遏革命烈焰由长江中下游向各地蔓延,英国当局还精心策划由其控制的沪宁、津浦(南段,北段归德国控制)等铁路的“中立化”,一度派军占领上海北站,阻挠革命军光复南京,起了阻碍革命军北上推翻清政府的作用。1911年10月17日,英、日等国驻汉口领事发布“严守中立”布告(注:《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 152 —153页;第227页;第2册第58页。)。因为, 列强如果采取直接武装干涉,介入革命军政府或清政府任何一方,都可能立即引起另一方排外,当然首先是反英。英国对武昌起义的政策是排除动用武力,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保护其在华利益。 11 月14 日,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Sir Edward Grey)在致朱尔典电中表明的外交立场最能表现其“中立”政 策的动机和目的了。他在谈及指望得到英国的“友谊与支持”的中国政府应是“不受外力的干涉而执行其政务”的政府后,强调“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来保持贸易上的门户开放。至于由何人组成政府,对我们并无关紧要”(注:《英国外交部档案》,F.O.302/10032, 格雷致朱尔典,1911年11月14日。)。
武昌起义爆发后,惶悚万状的清政府不得不请权倾一时又备受满人官僚忌视的袁世凯再度“出山”,藉其资望影响以国内争取外援。11月中旬袁世凯晋京组阁,格雷立即电示朱尔典,提出这是一个“能与各国公正交往”,“维持内部秩序”,“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注:《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153页;第227页;第2册第58页。)。其实, 颇获列强青睐的袁世凯政府何止得到英国的外交支持,还有财政和军事的支持。经朱尔典等人在清政府与革命军政府之间斡旋,南北双方于12月18日开始停战议和,议和地点设在上海英租界,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证人是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Goffe)。朱尔典指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傅磊斯(E.H.Frazer)在议和期间与清政府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保持接触,尽力促成双方达成协议(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9页。 )。朱尔典则在北京帮同袁世凯策划密商,凡议和之事一一与闻,俨然是袁世凯的最高顾问和决策人,对辛亥革命进行公开的干涉。议和期间,袁世凯施展政治阴谋,翻云覆雨极尽欺诈之能事。他一方面藉清政府要挟革命派就范,另一方面又藉革命势力恫吓清政府,以期篡位夺权取而代之。在内外势力勾结的胁迫下,革命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只能让步,最后接受了君主立宪的国体。
当时,鉴于国库如洗、需款孔亟,清政府仅半月内即向朱尔典和四国银行团提出4次借款要求,却未获明确答复。 在长江流域拥有庞大利益的英国担心革命烈火的蔓延不仅会影响其在华商贸利益,而且一旦列强发兵干涉甚至酿为对华武装争夺,受损最大的必将是英国。因此,英国当局认为这时向任何一方提供借款都不符合其既定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金融中立”是外交上“严守中立”的衍生物,相辅相成互为因应。如果说,“严守中立”实际上是呼唤和支持袁世凯复出的话;那么,“金融中立”简直就是明示清政府再请“强有力”的袁世凯组建足堪维护英国在华既得权益的“负责政府”了(注:《美国对外关系·中国部分1912年》(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China 1912),华盛顿1956年版,第103页;第843页。)。12月初,摄政王载沣被迫下台,朱尔典立即要求汇丰银行向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提供300 万两借款。但是,由于革命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光复后的上海也毕竟是在革命势力的控制之下,上海汇丰银行和傅磊斯总领事才未敢贸然行事,英国只好暂时继续维持着“金融中立”的虚势。直到1912年2月, 清帝逊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虚伪地赞成共和而被举为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终被其窃夺。于是,袁政府很快便 获得四国银行团5 次临时性垫款的第一批垫款200万两,1913年4月袁政府又获得五国银行团(日、俄加入,美国退出)巨额的“善后大借款”。这样,“金融中立”的虚势已经毫无意义了。
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财政上通过国际银行团的巨额借款扶植袁世凯,政治上通过强权外交为袁世凯窃国篡权扫清道路,胁迫清帝退位,胁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南北议和”正是这种妥协的产物。英国在辛亥革命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二 英国是率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不仅需要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而且还需要排除美、英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英、苏在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中宣称:“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渠等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注:《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126页。)。美、英既然标榜“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却又只“同意”中国在“国民政府下”,其虚饰与矛盾赫然纸上。其实,战后真正有力量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只有美国。战后英国对华政策追随美国,彼呼此诺,立场十分明确。战后英国背信弃义强行重占香港,1945年8 月起两年内协助船运10万国民党军从九龙到北方反共内战前线,直接插手“克服”华北的“骚乱”是必然的(注:《美国对外关系·中国部分1912年》(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China 1912 ),华盛顿1956年版,第103页;第843页。)。
英国在二次大战中蒙受重大损失,国力式微,国内经济的恢复不得不仰赖美国的援助,自然外交方面也只能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然而,战后英国对华政策决不是消极地追随美国,更重要的是体现英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是根据其经济利益的需要制定的。战后,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贸易部以及各官方与非官方部门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总是着重研讨中国的经济形势,显然因为这是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战争结束前后,英国实业界的巨头们便开始越来越关注战后对华经济政策了。英商中华会社(China Association)总干事古尔(E.M.Cull)、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即“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麦高恩(Mc Gowan)等都认为对中国采取中短期(例如10年)的展望是比较合适的。鉴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是英国在华进行完整的工商业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中国没有不动产占有权的安全保障和一个健全的政府,就很难设想英国对华大笔投资会取得有效的回报。不过,他们期望英中首先“恢复相互换货和贸易”。麦高恩尤其看好中国东北地区和台湾省在未来中国经济恢复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表示他的公司有兴趣参与政府将中国“从迄今尚在盛行的混乱中拯救出来”的工作,因为“中国经济的恢复有助于全世界”(注: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英商中华会社1946年年度报告中,多处强调恢复一个多世纪以来盛极一时的由英国转口销往欧陆为主的中国茶叶贸易是大有可为的。此外,蚕丝、猪鬃、驼毛、锡和钨等多项中国传统出口产品也是英国及欧陆各国大量需求的。报告还批评政府未及早派遣一个旨在保护英国的利益和资产,熟悉中国情况的代表团赴华(注:《中华会社文件·年度报告》(China Association Papers:Annual Report),1946年5月15日。)。 其实,早在1944年底英国贸易部在一份关于派遣一个商业代表团访华的评议中,已显示出“对华贸易是有兴趣的和积极的”,英国政府从未忽略过中国市场。
不仅如此,1947年8月7日,英国贸易部官员胡珀(H.O.Hooper)备忘录的出台,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英国朝野渴望重现战前英国在华极具优势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然而对于英国来说,旧梦重温、再现“辉煌”又谈何容易,已是力难从心了。因此,如何才能保护至少是不太多地失去战前英国在华既得的经济地位,当然是英国政府也是实业家和商人们殚思竭虑的难题。为此,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必须有和平的环境、健全的政府、稳定的经济和完善的法规。也就是说,战后英国支持的中国政府只能是有足够的实力控制中国的局势,至少是能够间接体现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利益的政府。战后,英国伙同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克服”所谓“骚乱”,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的曲折反映。不过,由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独裁遭致中国人民日益激烈的反对,英国当局也并不相信这个政府真的有力量控制混乱的中国局势,当然更不相信这个政府足堪间接体现英国的利益了。然而,英国当局的反共心态根深蒂固,一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与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大体保持一致。
英国当局经长期观察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1945年2月,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Seymour)在向政府提出的一份建议中认为,如果战后中国分裂成共产党政权在北而国民党政权在南的话,政府应执行传统的政策。也就是说,“当中国分裂时,英国只承认当时的中央政府。即使这个中央政府反对英国在华利益,英国也要支持它。但是同时,英国政府应该通过在中国各地的领事与各地割据政府保持事实上的关系”(注:《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46166,薛穆致艾登,1945 年2月28日。)。该项建议被英国政府采纳,后来成为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原则和政策。当然,英国当局决不会喜欢中国共产党人,更不会为新中国的成立欢呼,但是以英国的现实利益为重,较少受无实际意义的因素制约和干扰,是其不变的外交传统。
3年后,1948年2月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Sir Ralph Stevenson)在向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递交的一份报告中,确认中国共产党是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共产党。他通过大量事实肯定中共统治区成功地运用新的经济政策后,指出中共得到人民的支持,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已经攻占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方。关于英国在华利益,史蒂文森强调指出,英国对华贸易即使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也决不会比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更糟。他认为:“除对美国外,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英国不会比对其他外国更坏(注:《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69527,史蒂文森致贝文,1948年2月2日。)。史蒂文森最后建议政府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起初,贝文认为这位大使的报告无助于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英国外交部中国处的官员也对新中国抱有偏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形势已完全明朗,英国今后只要想保护和扩大在华利益,就不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交。贝文很快转变了观点,但是在冷战初期英国要承认中共政权却也不能不搪塞美国,用贝文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而且永远是中国人”(注:转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现代民族主义者,一直渴望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亦即取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尤其是希望得到西方大国的了解和尊重。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1949年4月30日,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注:《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开国大典时,周恩来致函各国政府,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英国贝文外交大臣与美国艾奇逊(Dean Acheson)国务卿就承认新中国问题多次进行磋商,未获一致。美国坚持在其自定“标准”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认新中国。贝文虽在一份送交美方的备忘录中声称英国准备承认中共政权,但是不久又在下院表示政府“要以谨慎的方式、合理的速度,怀有产生最佳结果的信念行事”(注:《下院辩论集》(House of Commons Debates)第469卷,1949年11月16日,第2013栏。)。不过,英国国内舆论要求承认新中国的呼声日盛,尤其工商界人士更为积极。他们指摘美国人的“恐共病”,反对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敦促政府加快“承认”的步伐。英国工党艾德礼(Clement Attlee)内阁原则上取得共识后,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国法律上之政府”,并“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注:《外交公报》1950年第1卷,第1期,第18页。)。同日英国舆论界欢迎政府的决定,《泰晤士报》高度评价“政府采取了明智的行为”,《曼彻斯特卫报》强调政府的决定是“合适而慎重的”。
尽管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决定主要旨在确保其在华经济利益,然而毕竟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当时,英国在华投资高达10.3亿美元,英国工商界为保护其投资安全,当然普遍要求政府与我国建交。不过,从战前到建国前夕,英中贸易额却呈急剧下滑的趋势。这时美国不仅不愿承认新中国,甚至认为考虑这个问题的时机都还未到来(注:E ·卢亚德《英国与中国》(E.Luard,Britain and China),伦敦1962 年版,第78页,第82页。)。美国既然甘愿退出中国市场,英国岂能坐失重新占领中国市场的良机。此外,英国为维护其在香港的地位和利益,也只有与新中国建交才有可靠的保证。面对中国大陆的形势已不可逆转,战时首相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 )声称:“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并不一定是一种赞同之举。……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是表示恭维,而是要获取便利”(注:E·卢亚德《英国与中国》(E.Luard,Britain and China),伦敦1962年版,第78页,第82页。)。由此可见,英国承认新中国并不表明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的赞同和肯定。况且,中英两国政府对“承认”的理解和立场也存在差异。这时,英国尚未断绝与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关系,因而尚不具备正式建交的条件。我方坚持先谈判后建交,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英方接受了我方的正当要求。1950年3月起,中英正式开始建交谈判, 不久因爆发朝鲜战争而中断。几经波折,直到22年后的1972年3 月两国才正式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三 谱写建设性的中英关系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性质和特点是中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互相抵制和排斥。中国与国际社会间这种互斥局面的出现,自然是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过程的产物。60年代中后期,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苏联摆出争夺全球霸权的态势,发动对华战争的危机四伏。中国与深陷越南战争泥淖的美国为对付苏联的威胁而趋于不再将对方视为心腹之患,从而为中国与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准备了基本条件。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尊重现实讲求实效的,并不总是以革命的行为模式对待国际社会。在对实际事务进行抉择和处理时,具体利益和现实需要也往往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出发点。例如,1972年2月, 中美《上海公报》是规范此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文件之一。同年3月和9月,中国又相继与英、日正式建交,实现了与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在外交上重返国际社会的最大动力是国内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说过:“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与让娜·索维的谈话》,《人民日报》1987年3月20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外交方面的最主要表现是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将斗争视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唯一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基本判断。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如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性成就博得了全世界的喝彩。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是中英双方共同谱写两国建设性关系新篇章的前奏,为此后双方建立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锁钥。然而,西方国家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喜欢以他们特有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功。例如,90年代以来美国相继出版的麦古恩《背信弃义的英格兰:1997年放弃香港》(William Mc Gum,Perfidious Albion:The Abandonment of Hong Kong 1997),马克·罗伯蒂《香港的陷落:中国的胜利与英国的背叛》(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注:参阅余绳武、 刘蜀永主编 《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3页。)等。他们将中英《联合声明》与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诬为“1984年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将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及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在中英谈判的关键时刻毅然作出明智的抉择,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由疑虑转为理解甚至欣然接受,从而推动谈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诬为“背信弃义”。他们将中国政府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通过和平谈判成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诬为香港的“陷落”。
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既坚持主权与治权不容分离又采纳了英方的合理建议,充分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促成香港问题顺利解决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保证。撒切尔夫人在签署《联合声明》后承认,“一国两制”构想“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注:《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0日。)。应该说,作为谈判对手,这位首相的评论是公正客观、恰如其分的。在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领导人本着务实的精神,都表现出充分的诚意。英方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与中方合作的基础上,寻求香港问题的园满解决,才是维护英国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表明,只要双方本着相互信任和谅解的精神,和平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最正常、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也是中英双方内部和外部条件逐渐具备和不懈努力的结果。邓小平说过,香港问题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的确,中国国力的日趋强盛和国际信誉昭然于世,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提条件,而“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决策的正确为此提供了重要保证。战后英国执政达11年之久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堪称是战后英国最有作为的首相之一。她的政治外交手腕强硬闻名于世,并善于审时度势,行事果断,内政外交政绩卓然。撒切尔夫人懂得必须“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为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找到了较合适的位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英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历史形象。正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对世界形势和英中两国的清醒认识,才会在解决香港问题时做出明智的抉择。虽然英国和西方某些人对实现英中关系正常化又多次访华的前英国首相希恩(Sir Edward Heath)和撒切尔夫人总是颇有微词,指斥他们为“叩头派”,但是他们的外交成就毕竟赢得了绝大多数英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赞许和欢迎。
四 一点启示
中国的先哲们说过:“以史为鉴”、“鉴古明今”。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也说过:“史鉴使人明智”。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 )在《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一书中写道:“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 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历史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对于过去以及对于现在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注:[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页。)。卡尔深刻揭示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深入理解”中英关系的现在,就需要了解中英关系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延续,不了解中英关系的过去,就很难“深入理解”它的现在。
中英两国的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一个多世纪以来,一方面中英两国发生了多次难以避免的撞击,历史伤痕难以抹去;另一方面英国在中国与欧洲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汇的漫漫历史长河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逝者如斯,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稳定和发展,凡具有远见卓识的各国政治家均致力于建立国家间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英两国均注重务实外交,以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1997年香港顺利交接的历史性成就为契机,两国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寻求到越来越多的结合点。英国工党政府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应中国政府总理朱镕基的邀请于1998年10 月6日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布莱尔首相访华的重要成果之一——《中英联合声明》向全世界昭示,中英关系的新篇章已经揭开。两国领导人同意面向未来,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即包括经贸、财经、议会、国企改革、环境、军事、刑警、文化、学术、艺术和体育诸方面的对话、交流及合作。中英两国商贸关系的发展前景当然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英国已经是仅次于德国的中国第二大欧洲贸易伙伴。两国政府首脑还同意启动两国高层专家为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献计献策的“中英论坛”,促进两国非政府组织间的高层接触,加快商业、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中国国家元首江泽民主席应邀将于1999年下半年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必将为新世纪中英关系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共同面向新世纪的挑战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世纪中英关系的转变启示我们,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摒弃前嫌、求同存异,不仅可以通过和平谈判顺利解决久悬不决的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而且可以从关系冷漠转向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中英关系的转变向全世界有力地证实了解决有历史宿怨的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关系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标签:辛亥革命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清代论文; 袁世凯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