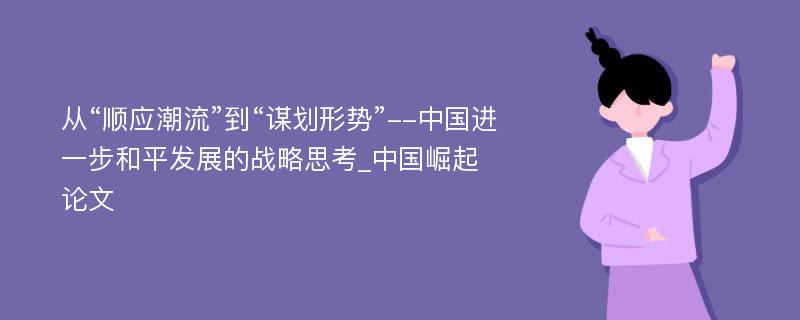
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和平发展论文,战略论文,随势论文,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2-0004-15
一 导论
建国60年,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成长为国际影响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书写了当代历史上最成功、最传奇的和平发展故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和平发展,无可辩驳的事实为相关争论给出了确切的肯定答案。
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可能缺少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但不乏各种软硬指标。中国崛起的首要指针是经济的强劲增长。在经济总量、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中国均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已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紧随美德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①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②正是鉴于中国的贡献和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06年9月决定将中国的基金份额从2.98%提升至3.72%,中国的投票权也相应地从2.98%提升至3.72%,排名由第八位升至第六位。③中国在主要国际经济机制中的话语权因此得到相应提升。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新一轮投票份额的调整,这将进一步使中国受益。
得益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大力开展多边外交,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提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已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不仅加入了1945年以后成立的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世界上大多数多边国际公约,而且还参与创立了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在首都北京设立秘书处的多边国际组织,即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对外关系实现历史性、跨越式发展,同外部世界已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框架。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依赖和借重明显增多,国际事务中的“中国因素”日益突出,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威胁的努力均离不开中国。中国已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边缘行为体,而是成为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和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④
相对于各种客观指标,外界的主观认可可能是评判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更为重要的根据。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频频见诸全球各大媒体,“中国崛起”不仅成了当今最时髦的政治术语,而且认可中国崛起成就的评论渐趋成为主流。中国在世界上已成功树立起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美国华盛顿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认为中国软实力与日俱增,已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源泉。⑤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联合推出政策报告《欧中关系的权力审视》,也强调中国实现“历史性崛起”,“由新兴国家发展为全球大国”。⑥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已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家形象,被大多数亚洲国家看做“好邻居、建设性伙伴、认真的倾听者和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⑦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和平崛起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开辟了一条大国崛起的新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很好地融入了国际社会,成为其中的“好公民”。⑧
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和国家形象都说明中国和平发展不再是神话,而是事实。现在,中国可以非常欣慰地述说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并非常坦然地总结和平发展的历史经验。需要回答的问题已不再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而是为什么能够实现和平发展以及能否和如何继续和平发展的伟大进程。鉴此,本文的重点不是总结中国60年的发展业绩,而是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能否延续和平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为实现进一步和平发展而应采取的战略选择。笔者认为,中国60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随势”,中国可以进一步延续和平发展进程的保障在于“得势”,为此而应采取的战略选择是在随势和得势的基础上不断为自身发展“谋势”。
二 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随势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是一个历史奇迹。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预设的和平崛起战略。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概念是在2003年,⑨但和平崛起进程却可以追溯到1978年。而且,中国提出崛起概念的初衷是为了化解“中国威胁论”,而不是为国家发展提供某种宏图伟略。中国崛起之路也远非平坦,如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都是有可能颠覆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重要路障。中国启动和平发展进程,并不断突破各种障碍确保这一进程不中断,固然得益于各种有利的主客观因素,但其中至关重要的法宝,并在今后进一步和平发展过程中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在于随势。
所谓“势”,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静态的总体格局,即局势、形势、气势;二是指动态的主流趋向,即情势、态势、趋势。静态之势蕴涵动态之势。势既表现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体现行为体施加控制的主观能动性。《孙子兵法·势篇》云:“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孟子·公孙丑上》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在中国文化中,势向来被看做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用势的概念来分析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博弈,可以得出颇具启发性的结论。
在国际政治中,所谓“随势”,就是顺应国际格局的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趋向,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历史机遇,维护和拓展核心国家利益。势虽可控可塑,但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弱小行为体而言却往往是不可忤逆的,只有随势,才能发展,逆势只能丧失机遇,甚至被势所淘汰。随势并不是简单的逆来顺受,而是顺势而动和借势而为的有机结合。随势要求一国必须对具体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形成准确判断,在正确世界观的指导下,对本国进行合理定位,确定并据情及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随势还要求一国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围绕核心国家利益,有效应对各种战略难题,化挑战为机遇,变劣势为优势。
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实现和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随势的结果。从本文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奉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前,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国策是逆势而非随势。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国际体系中扮演“反对者”和“革命者”的角色。新中国诞生之初,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与美国对抗的“一边倒”战略。随后中苏同盟走向破裂,中国又选择了同时与美苏对抗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理论,现在回过头来看,虽不乏远见卓识,但把美苏划归同一个世界,在淡化美苏矛盾的同时,又长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既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又不符合冷战的历史事实。不论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地位的误判,还是因为国力的过于脆弱,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行为都带有鲜明的逆势印记。中国这一时期明显趋向于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拒绝参加各种国际组织,排斥除主权原则以外的大多数国际规范。尽管中国卷入国际冲突都是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1953年朝鲜战争)或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中印、1969年中苏、1979年中越三次边界战争)时做出的迫不得已的抗争之举,但军事参与而非外交参与使中国成为两极国际体系得以最终形成的“推动者”,⑩并以“受害者”的身份成为美苏对抗的牺牲品。即使对于主权原则,中国的内化程度也很低,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乏与西方对抗和消极防御的寓意。(11)
中国改革开放前总体上既没能很好地顺应和利用历史发展大势,有效地为自身拓展国际空间和提升国际地位,也没能很好地化解各种困难和障碍,为自己谋得国家发展的机遇。在中国60年的发展中,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成就、国际影响和国家形象均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与体系抗争的对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迫不得已,那么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对内自残却绝非不可避免。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发展战略界定为逆势,绝不是要否定中国的内外成就,而只是想要说明中国为什么这个时期没能启动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有效的随势战略,从而顺利地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行得益于中国世界观的改变和对自身发展的准确定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12)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并据此提出了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既朴实又宏伟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的启动使中国迅速将国内议程由以军事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上既充分利用了长期和平的有利环境,又改变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不利形象。
邓小平提出并为随后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创造性践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以及有关国内发展的所谓“猫论”和“摸论”成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进程中实施随势战略的典型写照。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外交,先后实现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苏之间构建起稳定的大三角格局。这个战略布局使中国不仅摆脱了此前仅仅充当两极对抗牺牲品的被动状态,而且成为冷战后期美苏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重要支点。冷战结束后,中国更是根据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形成“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借助国际体系和平转换为中国发展赢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3)积极构筑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新的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为中国开创全面和平发展的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再充当坚定的反对者,而是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务实的利用者。与建国初期强调不惜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后,中国越来越重视通过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中国已在冷战后时代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了大部分领土争端,并为以同样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奠定了重要基础。(14)即使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一向被中国人看做国内争端的台湾问题上,中国也表现出了和平解决的强烈意向。此外,继重返联合国之后,中国先是从服务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加入世界银行(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0年)、亚洲开发银行(1986年)以及申请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始会员国地位(1986年),最终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又进一步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安全等各个领域广泛参加多边国际机制。(15)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令人信服地说明,“在一系列国际规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表现得比以往更能够与现存国际社会(依据其现实状况)保持一致”。(16)
正是基于随势战略,中国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经济市场化等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树立起崭新的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也正是基于随势战略,中国才得以有效应对危机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没有因此发生逆转。其中,对当前最具启示意义的当属中国在处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形成的化挑战为机遇的历史经验。在席卷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没有逆来顺受,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采取袖手旁观的对策,而是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对主要受害国出手相助,不仅推动亚洲经济很快走出困境,而且顺势成为亚洲其他经济体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重要经济伙伴。中国负责任的稳定作用赢得了亚洲邻国的赞誉和信任,并为自身在地区层次上拓展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打开突破口。(17)不少评论自此把中国视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认为中国正取代日本成为新的地区发展模式中的“领头雁”或“火车头”。(18)事实证明,中国具有极强的随机应变、化解战略难题及变挑战为机遇的适应能力。随势战略确保中国完成了在很多人(包括部分中国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实现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三 中国和平发展可以延续的根本在于得势
2008年全面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个经济体,对中国延续和平发展进程提出了迄今最为严峻的挑战。金融危机导致中国进出口大幅下滑,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严重缩水,外来直接投资锐减,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金融危机在抑制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和实实在在的,给中国延续和平发展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质疑中国和平崛起的怀疑论者提供了某种佐证。国际已有评论认为,金融危机将使中国无法续写和平崛起的篇章。(19)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实现和平崛起的布赞也感到,中国过去30年相当成功的政策在接下来的30年将不再有效,中国崛起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点”。(20)持相似看法的人士不在少数,但在前瞻时把30年作为历史周期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尽管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远非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能比拟,但从中国处理前次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来看,把此次金融危机看做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似有过分夸张之嫌。中国能否延续和平发展进程,最终答案仍在于事实。但在中国用事实作答之前,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将是中国和平发展可以最终跨越的另一个路障。支持乐观判断的根据可以列举很多,从本文的分析视角看,其中最根本的在于中国得势。
所谓得势,就是在国际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发展道路与历史潮流一致,拥有更多的有利契机,便于化解各种挑战和难题,维护和拓展核心国家利益。得势即得道,占据天时、地利与人和。得道多助,因此更能借势而为。得势者往往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解决原本可能难以解决的困难,实现原本可能难以实现的目标。得势要求一国必须善于审时度势,在判断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确定和调整国家发展战略时不能过于保守,否则就会荒废因得势而赢来的战略机遇。得势还要求一国善于用势,积极运筹,在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巧妙化解难题,确保核心国家利益不受损伤。
之所以认为中国目前得势,主要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在对中国和平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维持经济增长、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家形象等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至少以下四个因素可以说明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处于得势地位。
第一,全球经济普遍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更为突出。据各种经济预测,受金融危机影响,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均为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其中,美国可能达到-1.4%。相比而言,“金砖四国”经济总量虽也呈下滑趋势,但平均增长率可维持在4.7%左右。其中,中国可达到6%-8%。从本文起草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来看,“保八”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较危机前明显放慢,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优势更为突出。判断谁在经济竞争中得势,相对增长比绝对增长更重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撰文指出,重要的不是绝对实力,而是相对实力。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美国经济增长率已呈下滑趋势,从克林顿时期的4%减少到小布什时期的2%,GDP在世界总量中的比例从2000年到2008年大幅减少,降幅为7.7%。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以年均10%的增长率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金融危机只是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济的这种不平衡增长状况。据佩普计算,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相对实力下跌32%,而中国相对实力却增长144%。(21)中国与欧、日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也存在类似的增长落差,而优势同样明显在中国一边。因此,国际上不少评论认为,中国不仅在金融危机中直接受损最小,而且还会因其他国家受损严重而相对受益。即便经济增长率为8%,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中国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中国崛起已成定局。
第二,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日益上升。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被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看做近代以来继欧美崛起之后的第三次世界权力大转移,更是非西方、非民主国家的首次崛起。其直接后果就是,结束了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引发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重大转变。(22)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推动国际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多极格局的轮廓更加清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多极化进程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一向敌视、讳言多极化的美国,也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开始转变态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琼斯公开承认,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不少学者更是坦言,冷战后的美国单极时代已走到尽头,金融危机使“全球多极体系”提前到来。(23)中国既是多极化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世界正处于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明显在走“下坡路”,而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塑造能力却呈上升之势。从解决金融危机到应对气候变化,从防止核扩散到打击海盗,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到创立二十国集团机制,在多极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几乎世界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任何全球性多边机制的有效运作都需要中国参与。随着中国在处理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在贸易、金融、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塑造国际规范和完善国际制度的能力越来越突出,各国普遍预期中国将成为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中的关键“玩家”。
第三,各国对中国借重增多,中国化解国际制约的空间显著扩大。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处于史无前例的衰退之中”,“美欧遭受重大地缘政治挫折”,国际权力对比加速“东移”。(24)曾经“独领风骚”数百年的西方国家正处于历史发展的低点,与冷战后初期相比,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可以“包打天下”、“一语定乾坤”的时代正一去不复返。美欧在甚至无力解决自身难题的情况下,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和借重其他新兴力量,以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成为各方竞相借助和拉拢的对象。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把同中国的战略合作看做摆脱危机、重建实力优势的关键。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政要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学者纷纷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中美轴心”、“中美命运共同体”和“中美国”等概念。(25)尽管“中美共治”的提法缺乏根据,也不现实,(26)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该更多顾及中国的呼声和诉求。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把摆脱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期盼中国经济尽快复苏,并带动世界和本国经济回暖。各国对中国的借重增多,使中国可与不同类型的国家找到共同利益,充当协调各方关系的桥梁,从而有助于在进一步崛起过程中分散国际压力,化解国际制约,降低与他国发生战略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外界“中国观”趋于理性,中国提升国家形象的软环境更为有利。和平发展使中国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世界各地普遍兴起“汉语热”和“中国热”,渴望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引发国际社会深入反思“中国观”。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甚嚣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明显淡化,继之而起的是“中国责任论”和“中国机遇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定,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阻挡。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在接受《卫报》采访时,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作用,并表示中国正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大国”。(27)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甚至价值观念因金融危机而广遭非议不同,“中国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和追捧。“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北京共识”则崭露光芒。尽管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28)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东看”并主动借鉴“中国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与以往一味怀疑、批判和贬损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现在能够更理性地看待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模式”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解和认同有一定程度的增强。国际社会“中国观”的积极变化以及对中国认可和期待的上升,显然有利于中国提升国际威望,增强软实力,缓解外界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疑虑,并进一步牢固树立开放进步、稳定崛起、和平合作、诚信负责的国家形象。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对中国和平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明显加快的多极化进程使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成为各方竞相求助和借重的对象,国际社会“中国观”的理性化更为中国化解国际压力、改善国家形象营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中国得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占据得势地位,获得续写和平发展篇章的历史机遇。正是由于中国现在比以前实力更强大,地位更有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像化解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成功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推进和平发展进程。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断,如果中国用势得当,金融危机会使中国加快崛起为世界强国。(29)
四 中国进一步推进和平发展需要谋势
说中国和平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处于得势地位,并不是说中国可以高枕无忧地渡过难关,更不是说中国已经最终完成了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往回看,中国已经实现了和平发展,但往前看,中国崛起的路仍然漫长。和平发展就像一次未竟的长征,现在中国实现的只是阶段性的和平发展。中国可以说是大国,但还称不上强国。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只是最近几百年才成为主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重新走上了崛起之路,再度确立了大国地位,并为重新返回世界中心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的中国不仅没有必要回避大国定位,而且应把构建世界级强国作为继续推进和平发展进程的目标。为此,中国不仅需要为应对眼前的各种挑战、延续和平发展而善于乘势、积极用势,更需要着眼长远,为进一步崛起为世界级强国而善于造势、积极谋势。
所谓谋势,就是能够有意识地、前瞻性地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格局,掌握和控制历史发展潮流,为维护和拓展核心国家利益,不断创造有利契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古语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谋篇重于谋子,谋势重于谋篇。善于谋势者往往能够在竞争中长期占据得势地位,提前锁定胜局。不善于谋势者则难以将得势地位维持长久。谋势要求一国既要审时度势,更要着眼大局,围绕国家发展目标,积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确保本国可以持续在重大战略博弈中占上风。谋势要求一国不能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不在细枝末节问题上过于纠缠,而应在确保核心国家利益不受损伤的前提下有取有舍,先予后取,有时甚至只予不取。
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既得益于随势和得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谋势的结果。中国在冷战后期构建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并在冷战后时代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打造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重要舞台的对外关系框架,皆为谋势之举。正如布赞所言,与历史上德国、日本和苏联崛起不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挑战国际秩序,不与其他大国发生直接对抗,正在开创一条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的崛起新路。(30)这意味着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崛起经验可供中国借鉴。随着和平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搭乘历史便车的机会也会相应减少。要开拓性推进和平发展进程,中国必须在随势和得势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势。
第一,谋经济增长之势。长期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依然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由于全球经济最终摆脱危机,并走出衰退阴霾,即使按照最乐观的预期,也要几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因此,处于得势地位的中国有机会在力争率先走出危机的基础上,为危机后的可持续增长早打基础、早谋思路。要谋经济增长之势,中国首先应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保增长”过程中实现经济转型,借危机消除发展模式中的痼疾,使之更能适应危机后的全球经济竞争。其次,中国应深入研究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的发展大势,既要借机进一步“走出去”,更要为接下来打造经济强国、贸易强国、金融强国和投资强国,加强战略谋划和部署。再次,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改革方向施加影响,力争在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重建中占据有利地位,并充分利用G20等新机制,塑造于中国有利的国际规则和议程。此外,鉴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应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抢占诸如“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中国在确保本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有必要增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31)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得势地位,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离不开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第二,谋战略地位之势。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因金融危机而处于失势的不利地位,但金融危机尚不至于从根本上终结其主导角色。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美国仍将维持一超霸权地位,仍是决定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32)而且,鉴于美国一向具有令人吃惊的适应世界变革的能力,不能排除美国在“大落”之后“大起”的可能性,(33)多极体系还未成定局。因此,中国要谋战略地位之势,首先应继续推进多极化进程,加大力度塑造国际体系向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化解西方牵制和阻挠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和巩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其次,中国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会如何同现有霸权相处,既要进一步推进多极化进程,又要避免因此被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预设为敌。多极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国际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与美国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也是美国与其他大国分享领导权的过程。但美国仍然实力超强,如何避免与美国发生战略碰撞,是中国谋战略地位之势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最后,中国应继续以国际体系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角色深入参与国际机制和体制建设,加大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改革的影响力度,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发言权。在国际贸易、金融、能源、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积极参与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创设,争取及时进入,早做工作,施加影响。
第三,谋国际影响之势。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剧烈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中国参与解决。尽管中国已成各方竞相求助和借重的对象,发挥国际影响的空间不断扩大,但总体上,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仍远远超出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要借助当前的得势地位,谋国际影响之势,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中国已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练好内功”的同时,也要把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处理好。中国在国家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的时代,如果不把外部世界的事情处理好,已很难做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为此,中国需要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意味着中国在必要时应进行必要的“建设性干预”。同时,中国应勇于承担国际责任。责任与权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大国影响与大国责任相辅相成。中国只有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包括在一些看起来与己无关的问题上进行战略投入,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筹码,为自己“揽牌”,以便在大国折冲中获得更多主动权,拥有更多修订国际规则的机会。中国既要防止陷入西方的“责任陷阱”,也要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照顾国际社会关切,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物品。
第四,谋国家形象之势。西方国家普遍不愿接受中国崛起,把中国崛起视为“异类”,担心中国挑战其国际地位,破坏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削弱其民主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因此,美国要塑造中国的战略选择,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34)欧盟则希望中国成为像它那样的“规范性行为体”。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担心中国复活传统的“朝贡体系”,并因此求助外界对中国进行防范。(35)因此,中国要促使外部世界更快接受中国崛起,首先必须继续推行安抚战略,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时机,积极谋国家形象之势。其次,中国应主动转换国际角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多元国家身份虽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但也给中国争取更多国家认同带来一定困难。中国在发挥影响时强调大国身份,在回避责任时突出发展中国家地位,已引起国际社会不满。为进一步赢得战略主动,中国应在定位自身角色时,减少机会主义色彩,体现国际主义精神,致力于成为负责任的新兴强国。最后,中国应发展普世性的国际理念。在继续倡导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互利共赢等思想的基础上,中国需要针对外界的核心关切,回答中国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希望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怎样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等问题。中国应设法在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国际理念上消除国际疑虑、误解和偏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占领道义高地,使国家形象更可亲、可敬、可信。
如何进一步实现和平发展已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从应对挑战、化危为机和打造世界级强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战略地位、国际影响和国家形象等方面积极谋势。(36)只有主动谋势,中国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所形成的严峻挑战,将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化为进一步推进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在逐渐成为世界级大国的基础上更加顺利地迈向世界级强国。
五 结论
经过60年的不断探索和努力,中国不仅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而且取得了历史性成功。随势而不逆势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30多年的随势战略为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可靠保障。阶段性和平崛起的历史积淀使中国得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面前处于相对得势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提升以及国家形象的相对改善,为中国赢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得势,成为中国可以续写和平发展篇章的重要源泉。但要真正把得势变为得分,中国还必须善于乘势和用势,并在此基础上围绕更远大的打造世界级强国的战略目标,从经济增长、战略地位、国际影响和国家形象等方面积极造势和谋势。为进一步和平发展而谋势,要求中国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更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与时俱进,锐意进取,逐渐将战略重点从“务实”过渡到“务势”。
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大挑战和大机遇,预示着中国和平发展将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如果说在此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解决的是中国如何拥抱世界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便是世界如何拥抱中国的问题。正如国际社会所普遍期望的,中国已经并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和内化各种国际规范,实现国家的社会化。但中国和平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期,世界既没有准备好接受,也没有来得及适应。针对外界有关中国崛起之后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的疑虑以及出于为中国将来发展为世界级强国谋势的战略需要,中国应主动在观念塑造和规范建构方面,通过反向社会化,让世界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接受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曾让中国无所适从,现在中国不能让世界无所适从。积极创造和推广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世意义的国际理念,加深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同和适应,将是新时期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收稿日期:2009-11-05]
[修回日期:2009-12-31]
注释:
①Dan Ciuriak,"The Laws of Geoeconomic Gravity Fulfilled? China's Move toward Center Stage," 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31,No.1,2004,pp.3-28.
②C.Fred Bergsten,Bates Gill,Nicholas R.Lardy and Derek Mitchell,China:The Balance Sheet: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6,p.116.
③"IMF Agrees to Increase China's Voting Power," China Daily,September 19,2006.
④潘忠岐:《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48-54页。
⑤Carola McGiffert,ed.,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9.
⑥John Fox and Francois Godement,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London: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9.
⑦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2005,pp.64-99.
⑧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an 'Peaceful Rise' Succeed?" Montague Burton Chair Inaugural Lecture,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March 10,2009,http://www2.lse.ac.uk/PublicEvents/events/2008/20081203t1625z001.aspx.
⑨2003年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讲演《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时,首次提出“和平崛起”概念。
⑩代兵、孙健:《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第29-33页。
(11)Pan Zhongqi,"China's Changing Image of and Engagement in World Order," in Sujian Guo,and Jean Marc F.Blanchard,eds.,"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New York/Lexington: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pp.39-63.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页。
(13)潘忠岐:《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第41-44、35页。
(14)Jianwei Wang,"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Asian Security:Sources,Management,and Prospects," in Muthiah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380-423.
(15)Justin Hempson-Jones,"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ian Survey,Vol.45,No.5,2005,pp.702-721.
(16)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17)David Shambaugh,"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1-47.
(18)Trish Saywell,"Powering Asia's Grow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August 2,2001; "Why Europe Was the Past,the U.S.Is the Present,and a China-Dominated Asia Is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22,2003.
(19)Joshua Kurlantzick,"Twilight of the Autocrats:Will the Financial Crisis Bring down Russia and China?" The American Prospect,March 16,2009;另见Jianyong Yue,"Peaceful Rise of China: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5,No.4,2008,pp.439-456。
(20)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an 'Peaceful Rise' Succeed?" March 10,2009,http://www2.lse.ac.uk/PublicEvents/events/2008/20081203t1625z001.aspx.
(21)Robert Pape,"Empire Falls," National Interest,No.99,2009,pp.21-34.
(22)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pp.18-43; 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W.W.Norton,2008.
(23)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November 2008.
(24)Roger Altman,"The Great Crash,2008: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Vol.88,No.1,2009,pp.2-14.
(25)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3,2009; 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Vol.87, No.4,2008,pp.57-69; Niall Ferguson,"Team 'Chimerica',"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7,2008;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 and Global Asset Markets,"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0,No.3,2007,pp.215-239.另见David Shambaugh,"China and Europe:The Emerging Axis," Current History,Vol.103,No.674,2004,pp.243-248。
(26)Elizabeth C.Economy and Adam Segal,"The G-2 Mirage: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Affairs,Vol.88,No.3,2009,pp.14-23.
(27)Julian Borger,"David Miliband:China Ready to Join US as World Power," Guardian,May 17,2009.
(28)相关争论可参见Minxin Pei and Jonathan Anderson,"The Color of China," National Interest,No.100 2009,pp.13-30。
(29)参见Roger Altman,"The Great Crash,2008: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pp.2-14。
(30)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an 'Peaceful Rise' Succeed?" March 10,2009,http://www2.lse.ac.uk/PublicEvents/events/2008/20081203t1625z001.aspx.
(31)潘忠岐、黄仁伟:《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16-122页。
(32)Nicholas Burns,"The Ascension," National Interest,No.99,2009,pp.53-62.
(33)Robin Niblett,Ready to Lead? Rethinking America's Role in a Changed World,London:Chatham House,2009.
(34)U.S.Department of State,"Fact Sheet:U.S.-China Relations," April 18,2006; Robert 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September 21,2005,http://www.ncuscr.org/articlesandspeeches/Zoellick.htm.
(35)David Shambaugh,"Introduction: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in David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pp.1-25.
(36)有关地缘层次上的谋势,参见潘忠岐:《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21-39页。
标签:中国崛起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