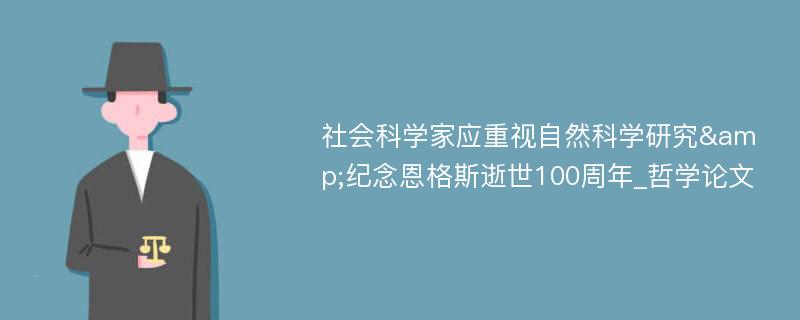
社会科学家要关注自然科学研究——写在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写在论文,科学研究论文,科学家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8月5日是马克思逝世之后当时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无产阶级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正直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会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历史伟人。这位历史伟人曾经逊称,马克思在世时他拉“第二小提琴”,但他拉得如此精妙、出色,以至使他们的协奏缺一不可。在他们共同创立的学说中,恩格斯有着重大的贡献。除了同马克思一起完成的那些研究以外,他自己还有一些卓越的发现。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极为关注自然科学研究的话,那么恩格斯比之于马克思则将更多的精力投诸自然科学研究,并由此作出哲学的概括。当然,这样说,只是在比较的意义上。从总体上看,他们都作为社会科学家而关注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关注和深刻了解,那么,社会科学家就很难站在划时代的高度上;如果对自然科学渺无所知,那么,社会科学家就只能是冒牌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站在了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时代前列而取得他们的重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
我们今天纪念恩格斯,就应当从恩格斯那里汲取这样一个有益的启示:社会科学家要关注自然科学研究。
一
直观地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人们常常把它们当作并列的、既定的存在,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而指出两者的相互关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停留在这样一种观点上,而是看到和指出了它们之间的更为复杂的深层关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一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而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树立其上的社会的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社会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根据于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的发展,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而社会科学作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对这些意识形态形式的研究则最终根据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社会意识形态放诸社会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考察,并在这一考察中精确地指出了自然科学发现和相应的技术应用对它们的影响。先进的自然科学发现和相应的技术应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作为建立于新的自然科学发现和相应的技术应用基础之上的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们便提出相应的新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哲学的观点。但是,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相应的技术应用并不只是通过社会经济基础的这些变化、转换,而是还以更直接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这些观点,并进而影响社会科学的研究。例如,恩格斯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同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恩格斯还具体阐述了18世纪形而上学与19世纪开始的唯物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基础,说形而上学是直到18世纪末以搜集材料为主的关于既成事实的自然科学的产物,而唯物辩证法则是19世纪开始的以整理材料为主的关于过程、关于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自然科学的产物。恩格斯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著作中,都探讨了自然科学问题,揭示了它对人们的哲学世界观并从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影响。
当然,我们此文特别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是自然科学的消极的产物。恰恰相反,在肯定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基础作用、先导作用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是由两条途径实现的:其一是通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环节,例如由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革命性变革施及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其二是通过新的哲学世界观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关于前者,恩格斯指出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而一定经济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自然科学研究推向前进;关于后者,恩格斯则指出:“自然科学家可以采取他所愿意采取的那种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并因此而主张自然科学家要掌握辩证法。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反作用,都要求社会科学家关注自然科学研究。
于是我们看到,恩格斯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作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着广泛涉猎和重大成就的社会科学家,就极为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做了大量的笔记,记录了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大成果,甚至从细微之处考察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并从哲学上作出高度概括。例如他对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引起的世界观方面的变革的意义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估价。同时他也看到诸如达尔文、赫胥黎、丁铎尔等人思想方法的片面性,看到他们“渴求一种解救的哲学”的状况,因而关心这些自然科学家们哲学方法论的改进,以唯物辩证法指导他们的自然科学研究。例如,他同马克思对肖莱马的化学研究的指导,就使肖莱马颇受教益。
二
事实上,历史上一切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都有着非常浓厚的自然科学兴趣,有的甚至同时就是自然科学家,例如法国的笛卡尔、德国的莱布尼茨和康德等等;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除马克思(他的《数学手稿》公认有独到的贡献)、恩格斯外,其他诸如列宁、毛泽东,虽然由于领导革命战争,没有更多的时间研究自然科学,但还是非常关注自然科学研究,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每一重大发现,都满怀兴趣和热忱了解它。他们既关注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哲学世界观的重要作用,也注意运用先进的哲学世界观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因而他们虽然作为社会科学家而著称于世,但仍然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着重要贡献。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且不说迄今为止的100年间,人类已从恩格斯时刚露头角的电器时代转入今天的电子时代,其间无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飞跃,就是与恩格斯同时稍后的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相对论原理,也足以引起人们许多观念的变革。例如,恩格斯时代的时空观,基本上还是批判地借鉴黑格尔,强调时空是物质的运动形式和它们的无限性。在时间观念上,恩格斯没有涉及时间与物体运动速度的关系;在空间观念上,虽然在恩格斯的时代已经有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即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和黎曼几何学,但由于它们的空间意义还没有被认识到,并因而被称为虚拟的几何学,所以恩格斯并没有论“无限空间”的不同形式,没有讨论弯曲空间等等。也许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当伯恩施坦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送爱因斯坦征求是否付印的意见时,爱因斯坦写道:“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02页)在这里,爱因斯坦是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不存在对恩格斯的贬抑,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评语是对全部手稿而说的。我坚信,要是恩格斯本人能够看到,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后,他的这个谨慎的尝试竟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好笑”(同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作了卓越的哲学概括,但我们今天不能继续停留在恩格斯的材料和结论上,而应该从新的自然科学材料出发对他的某些结论作出修正。
但是,爱因斯坦之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怎么样呢?尽管他依据相对论原理解决了水星近日点进动问题,预言了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和引力波的存在(这都为后来的天文观测所证实),并因此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但是社会科学家没有能够及时地从哲学世界观上作出与此相应的概括,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样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无动于衷。在哲学教科书上,在哲学课堂上,常常重复着一些在爱因斯坦时代就已经应当修正的观点。例如,在时空观问题上,虽然也批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经典力学的观点,但具体解释仍然没有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自然科学基础,虽然是唯物的,但并非是充分辩证的。又例如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与转化等定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天经地义的,它甚至被作为唯物主义的证明,但是,自那之后,科学发展竟也证明了它的相对正确性,爱因斯坦的质能相当性定律(E=mc[2])如果成立,就打破了物质守恒与能量守恒的界限,使二者具有了统一性。但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课程所讲的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和相应的哲学观点。这就不可能使哲学与时代同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现代科学的哲学意义,提出了比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综合与发展了的观点:“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引自于光远《毛泽东与自然辩证法——值得重温的一次谈话》,载《了望》1995年第6/7期)又例如毛泽东从哲学角度说明了世界的无限性后说:“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同上)在毛泽东这一无限可分性思想的启发下,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了关于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毛粒子”也由此得名。毛泽东的见解,从哲学上说,具有时代的高度,并为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所证明。可惜,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没有充分注意从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就着眼,因而常常停留于《实践论》、《矛盾论》和它所征引的材料上。这样,无论说他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是具有某种空泛性。而这,应当归咎于社会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疏远。
三
如果说以上所及还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较高层次上说明了社会科学家关注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那么,以下所及就从一般人的思想观念和哲学世界观上说明了社会科学家关注自然科学研究的迫切性。在一般人的思想观念上,甚至在一些跻身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员的哲学世界观上,常常见出缺乏起码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危害。例如,前几年有人连续撰文宣扬“一分为三”论,据论者说它是一种辩证的新方法,要以此“纠正”和“补充”“一分为二”的不足,但是,恰恰与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他是背离了辩证法而修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他在此、彼之间加上了“亦此亦彼”。直观地看,论者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论,而深层原因,还在于他没有从恩格斯所例举的事物的运动过程去理解,并因此而曲解恩格斯。这里,都有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的背景。如此讲辩证法,讲新世界观,不仅是空洞无物,而且还恰好背离了他的初衷。又例如,在我国久热不凉的所谓“特异功能”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心理暗示作用,或者干脆就是运用物理、化学或其他技巧的戏法,但偌多人载欣载奔,受骗上当而不自知。对这种新时代的迷信现象,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如能及早引导,那将避免多少荒唐以至灾难。遗憾的是,有些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都为这种新时代的迷信推波助澜,而究其底里,也是缺乏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
这里涉及我国社会科学界人员素质情况。据对几处高等院校的了解,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缺乏起码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有相当多的人的数理知识达不到牛顿时代已经达到的高度,更不了解自恩格斯之后的许多重大发现。反映在科学研究上,要么是古典的量的积累;要么是新形式的“转注”;要么是人云亦云,重复叨念;要么是贩卖洋货,贴自己的标签;即使有一些涉猎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的,也常常不是从哲学方法论上作出概括,而是套用个别概念,如熵、场等等,结果还是新名词,老货色。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关注自然科学研究,站到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高度上来。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象他那样,摘取自然科学的果实,酿造社会科学的酒浆,以期在新的世纪之交,造就出新的划时代的哲人、社会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