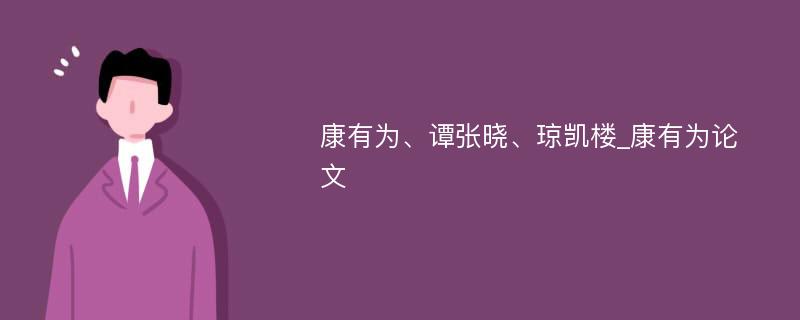
康有为、谭张孝与琼彩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谭张孝论文,琼彩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899年7月20 日联合一批加拿大华侨创立保皇会,“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注:1900年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页。 )为旨趣。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保皇会发动上书请愿、军事勤王、募集捐款等活动,并许以“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的承诺,申明“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注:1900年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页。)。广大华侨身居异邦,心系祖国, 积极支持保皇会。保皇会收到的海外捐款数目相当可观,康有为等用部分资金投资实业,经商赢利,以期获取更充裕的经费开展保皇活动。但是,事与愿违,投资实业大都以失败告终,康门弟子因利益纷争而离心离德,很多华侨也走上了支持革命的通路,保皇事业受到极大的挫折。康有为、谭张孝等人开办琼彩楼,后因债务纠纷而互相指责、谩骂、争斗即是这一段历史的缩影。本文依据一些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注:此档案材料系指由美国谭精意(Jane Leung Larson)女士提供的康有为、保皇会资料, 共三份,其中《征信录》现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美籍亚洲人研究图书馆,另两份现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为行文方便,这两份资料下文称为“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这三份资料的节选本即将出版。),对琼彩楼事件作一综述,揭示该事件对保皇会的影响,并试图从兄弟阋墙的角度说明保皇会是如何走向衰亡的。
一
谭良(1875—1931),字张孝,广东省顺德县甘竹乡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与梁启超、徐勤等同学于万木草堂。1899年赴美后,对保皇会事务颇为支持,任洛杉矶地区保皇分会会长,曾主持《文兴日报》工作(注: 参阅谭精意“An American Baohuanghui Leader:
TomLeung's Life,Politics and Papers”一文,1993 年“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和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03年,梁启田、梁启超先后游美归国,徐勤恐怕美国保皇会员变卦,要求谭“时时提倡之,勿使事败垂成也”(注:1903年12月23日《徐勤致谭张孝书》,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可见,保皇会对之甚为倚重。1905年春夏之间,谭陪同康有为遍游美国东北、西北各地。10月15日,两人在波特兰分别。之后,谭函请康开办酒楼,以赢利资助保皇会派遣留学生。其时,谭奉康命致力于选送保皇会员的子弟留学欧美事宜,以备将来党、国两用。对这一请求,康一口答应,即将暂存于谭处的七千多元(美元,下同)保皇会公款拨作开办酒楼之用。后来,康陆续增拨资金。谭身为总办人,为该酒楼倾注了不少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选定酒楼地点即费尽周折。他起初选在洛杉矶开办,但因该地铺租昂贵,资本有限,故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铺位,焦急异常。康频催尽快办理,称“此事为兴学育才大举”,“太谨慎畏葸则迟误失事机矣”,指示谭“速办速办,无复多迟疑以误事”(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905年11月7 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催办酒楼原信》。)。恰在此时,忽得芝加哥同仁言该地有铺位,谭就决定在芝城开办酒楼。在选址的同时,他着手拟定酒楼招股、派息章程,向各埠散发,吸纳股份,扩大经营。康接到章程后,甚表满意。地点选定后,谭密锣紧鼓地进行操办。康主张店面要以雅丽为主,不必讲求奢华;色调以蓝白色相衬最佳,花式讲究相配。康认为酒楼取名“琼彩楼”“太劣”,以“华严”、“华粹”、“馔玉”之一为名更好(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日(1905年12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入股琼楼及初办时函商各事及电》。)。不过,“琼彩楼”的招牌已经做好,最终没有更改就定了下来,并于1906年6月开张营业。
在筹备琼彩楼开张的八个月里,谭放弃洛杉矶医馆的许多生意,事必躬亲,满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建功立业。但是资金短缺严重阻碍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招股章程发出后,响应者寥寥,即使入股,亦是小数目。康有为于1905年11月命谭从七千多元中提取五千元借与李美近,剩余的二千多元更不敷使用,不得已,谭频向康请求拨款。康除亲自拨与有限的数目外,便命香港华益公司纽约分公司支援琼彩楼,于是,纽约方面的冯镜泉、汤铭三、康有霈、陈继俨等就直接参与琼彩楼拨款事宜。康同璧、康同荷、梁启超等人也卷入琼彩楼的财务运作中。期间,康不断催促谭尽快派息,还清借债,以应墨西哥各项投资之急需。由于事前并未商定各笔拨款性质(是否借款)如何,以致数目混乱,相互拖欠,纠缠不清,终于爆发了康、谭二人关于琼彩楼债务的纠纷。
二
发生琼彩楼债务纠纷的直接原因是康、谭二人对经营琼彩楼的资金用途有着不同的理解。康有为认为:商场中资金往来是有偿的,用公款开办酒楼,必须加计利息,本息俱还;谭则认为康经营琼楼是学生为老师办事,店员给老板打工,与借钱纳息是两码事。尤有甚者,康以琼彩楼资金乃保皇会公款,身为会长的他有权调拨(包括调出和拨入)这些资金,由此,引发收支不均,账目出现了混乱。帐目混乱,应从李美近借款开始。李美近何许人不得细考,他曾担任保皇会美国西北四省的“代表员”(注:1907年3月23日《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88页。), 被康赞为“义士”(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905年11月11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委借李美近商款原信》。)。对于李五千元的借款要求,康交由谭与之洽商,嘱咐谭从七千多元中“暂拨以应之”(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905年11月11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委借李美近商款原信》。)。1906年3月,李美近还了四千元,尚欠一千元。 谭函询康措置之法,康复云“美近款,吾已复书担之,汝可勿问”(注: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1906年5月10日)、十一月十五日(1906 年12月20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但是,康一直没有“担之”,后来还替谭写信催李还清余款及利息。李敷衍拖延,康以“借与李美近之款五千元乃拨为芝楼之股本”(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康有为的信。此信由汤铭三转给谭张孝,《征信录》中未录写作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谭于是日收到此信)前。)为由,要求谭追清余款。从现有资料来看,李美近始终未偿清借债。实际上打乱了谭筹办酒楼工作的正常进行,又因拖延较长时间,一千元的资金缺口一直无法填上,琼彩楼的帐目统计出现了混乱。
琼彩楼帐目混乱加剧是从香港华益公司纽约分公司拨款开始的。康有为“令纽约直拨(款)芝埠”(注:《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着纽约分局拨款入琼楼原信》,未录日期。),该分公司便负责琼彩楼资金的大部分。但是,康始终没有指定谁专职此事。从《征信录》中可知,康有霈、汤铭三、冯镜泉、陈继俨等均曾经手划拨款项与琼彩楼。康有霈直言其兄(康有为)未曾指定他专司拨款之事,“不知首尾”(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康有霈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桂宇拨款来琼楼及数目原信》。)。专责乏人,不仅没有达到使谭张孝与纽约直接往来、节省汇费的预期目的,反而造成了“人人管,无人管”的混乱局面。据康有霈统计,他经手注资琼彩楼达三万一千六百元(注: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907年12月22日)《康有霈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桂宇拨款来琼楼及数目原信》。),加上冯、汤等人经手数目,款项巨大,分红派息却不准时,康有为及一些股东甚为不满:“美中存款为张孝等借支,致不能拨,及我来美,则有数大事相近而来。”(注: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907年4月8日)康南海《与任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文简称《梁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页。 )缺乏充裕的资金用于墨西哥投资的周转,康非常被动,急于了解琼彩楼运作详情,一方面指派康有霈、汤铭三与讲“会同督办”(注: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1906年5月10日)、十一月十五日(1906年12月20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一方面派出林兆生、陈继俨核查琼彩楼帐目,“整顿改良一切”,令谭“一切听宜甫(陈继俨字),并将一切内外数目告之示之,俾宜甫有把握办理”(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907年4月2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 《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派陈、林二君查琼楼数目原信》。)。查数完毕后,康指示:“兆生随我,决无暇来理事,已派定铭三来,孝为总理,孝行,铭为代办总理可也。铭因股票事,非半月后不能来,孝必须待之。”(注:《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派陈、林二君查琼楼数目原信》。《征信录》中未录日期,其中提及陈继俨已查数完毕,估计此信写于1907年5月。)如此一来,无疑架空了谭张孝, 其总办之职有名无实。两人关于琼彩楼经营、管理的分歧意见与日俱增。1908年初,康声称“张孝前后借去十六万(华数),……至今利息本钱分文不能交”,又发现琼彩楼1907年的结算单上少了二万四千元,怀疑为谭“私吞”。他震怒无比,决计对当事人采取不留情面的措施:“铭、雨二人擅借巨款而置之不理,可恶已极,若谭盗则更不必言,刻拟布告,又拟控追,拟作欠公学款而抄其家。”(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七日(1908年3 月9日)康南海《与任弟书》,《梁谱》第443页。)1908年底至翌年初,琼彩楼内部混乱情况和康、谭的争执渐渐公开化,保皇会会员和股东们均认为谭混水摸鱼,靠一笔糊涂账发了大财。为了自辩,谭搜集有关信件(包括康有为的信件),辑成《征信录》一书,公开出版。透过《征信录》我们得以较为清楚地了解两人争执的内容、结果,从而判断谁是谁非。
康、谭二人的争执,焦点是十六万元(华银)问题。十六万元华银(当时约合八万美元),主要包括琼彩楼股本、四千元借款、养五十(注:“五十”何许人,康、谭二人的信函中均未详载,故不得详考。)之款及资助一些保皇会留学生的学费、生活费。
琼彩楼资本,主要有华益分局股份、洛杉矶股份、中国内地股份、芝加哥股份及各埠散股共七万多元(注:见《征信录·付琼彩楼股份芳名》。)。双方争议最大的是华益分局的股份。康有为将自己替保皇会注入的股份与华益的拨款分开看。他亲自投入的有一万二千五百元(注:在同一封信中,康也曾提及入股共一万四千五百元,见《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康有为的信。),汤、冯等人股入的四万一千多元是未经他同意,“专擅误拨”(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康有为的信。此信由汤铭三转给谭张孝,《征信录》中未录写作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谭于是日收到此信)前。)的。其言下之意,华益拨款非股份,实系琼彩楼借款,谭应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息。谭认为,华益拨款中的二万九千五百元是康指令参股的,与康亲自入股无异,其余则系借款。股份和借款应区别看待,前者只在每年赢余中分取红利,后者应按规定清还本息。其次,关于借款数目,康开列的一万六千元是他亲手借予的,尚未将其他人的借款合算,并非总数。谭的说法并不一致。在致康的亲笔信中,他称琼彩楼“前后共借四次,系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一元”,而“旧年一年(按指1907年)共还本银八千八百元二毛(截至旧年西十二月卅一日止)”(注:《谭张孝致康有为信》。此信未署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廿二日(1908年8月18日, 康于是日复信与谭)之间。此信删增涂改之处颇多,并无署名,似为未完手稿。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征信录·付琼彩楼还华益公司揭项数目》显示,从1906年3月至1907年2月,琼彩楼借款四次共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1907年还本银七千二百四十九元二角。两相对照,差距甚少。但数目虽小,却令人疑惑不解:究竟哪一笔数是对的?出现差别的原因何在?琼彩楼股份和借款各有几许?两人说法不一,又囿于资料有限,笔者虽反复计算,仍无法得出确切数字,也无从剖析个中缘由,姑认“悬案”视之,暂且搁置。需要强调的是,康、谭二人之争是从这两笔款项开始的,这两笔款项的准确数目至关重要,是透彻了解争执的因由的“钥匙”。
四千元借款与四千多元学费、杂费的问题。《征信录·历年进支数目》中有“(丙年)四月廿三进鸟约来银四千元”一条,谭并未说明其用途。康谓此款乃谭“自私借款,有单立限,一二月交清免息”,过期不还,则计息(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康有为的信。此信由汤铭三转给谭张孝,《征信录》中未录写作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谭于是日收到此信)前。)。谭指出借款时确曾立单,康收列四单后即着康有霈回信,谓此款“仍作来往数,将来再计,弟(按指谭张孝,下同)有还款时,将弟代支之数扣之可也”(注:转引自《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谭张孝的信。此信未署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廿二日(1908年8月18日,康于是日复信与谭)之间。)。 谭将信寄还康察阅,康“允如前议”,只作为来往数,不算是借款,但如今康否认“前议”,谭只有如法炮制,将代支出的四千多元学费、杂费与四千元借款抵消,信中说:
“今银已支去,数亦拨妥,先生始偏其反,而在弟本无不可。但弟代先生支出之款亦有四千四百余元(各数皆在学费、集〔杂〕费两项内),先生亦当先拨还与弟,方能向弟追取借项。若止知弟借去之款本息追究,而置弟代其支出之款不议不论,作无是事,自忘前约,目人为‘诱骗’、‘棍盗’,是失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今作来往数,则比对两讫,二家清楚,两无受亏,亦情理兼尽之至也,况先生有前约乎?”(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谭张孝的信。)
面对有据有理的辩驳,康强硬的语气稍有和缓,他复信云:
“惟四千所借乃商款,非公款,两年不清,息无从出。当时孝所清者是一二月,故免息,亦无作未往数计语。若季两(按指康有霈)写,可将两笔缴来两验。……考欠公商者,孝清其本息;我或公款欠张孝者,亦由我与公款清还张孝,庶几清楚,亦省嫌之道也。”(注:《征信录·总长驳数后以数原信》。 此信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1908年8月18日)。“非我数”三字系据康的手稿补入。)
很明显,四千元是拨作股份之用而非借款,之所以引起争端,是与康有为转托康有霈办理而不够重视有关的。
养五十之款的问题。培养五十为刺客,在康有为1905年游美前已开始。从1905年10月开始,其培养费用由谭支付。约在是年底,康催促五十执行刺杀计划,五十以“学问未成,家有老亲,暂未能行”为词,拒不行动。谭告以实情,康认为五十无用,令谭停止供应学费。谭为五十术情,康回信云:“□□(原文如此,似是隐去‘五十’二字)性行孤高,如冷月梅花,留此清芬以对冰雪,别有风趣。吾爱之至极,恨不能置之左右为忘形之交也。前云樵(按指欧榘甲)荐来时,多有议其不行者,此大事,吾固不信,然无论如何,事甚欲保存此人,认为一佳事。吾党力虽困乏,然吾既爱之,今决停前议而仍供养之,弟仍为我日夕备清水,陈古瓶,供此一支梅花也。弟得无谓我癖爱梅花耶?我无求于梅花而仍养花,此何情耶?亦不解。”(注:转引自《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谭张孝的信。此信未署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廿二日(1908年8月18 日,康于是日复信与谭)之间。 )依康之意,谭继续供养五十。 他算出至1906年12月养五十学费共五百七十四元(注:在《征信录·历年进支数目》中,五十及谭张孝的学费一同记账,从1906年7月起单独记账, 每月二十元,之前五十学费应与此相同,故依此得出其学费、杂费总共为五百七十四元。),康认为此数过多,谭妄自开数。接悉谭细述整件事始末的信后,康才觉有失,一方面承认应该供养五十至当年署假(查两人先前未曾如是说),一方面坚持“今至冬后,则非吾意,引吾信亦谬”,表示“养五十一事,所费有限,……今无大差,亦可无庸议”(注:《征信录·总长驳数后认数原信》。)。养五十之款大多是从琼彩楼款中支付的,养五十之款的争执是两人账目之争的内容之一,对于认清由于琼彩楼资金被派往不同用途而引起账目混乱无疑具有一定作用。
关于康同璧、康同荷、梁启超与琼彩楼的来往数目问题。琼彩楼付款与康同璧有两次,第一次在1906年1月20 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支付一百元,第二次在1906年3月20 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廿六日)支付一百五十元。对第一次付款,康声明:“此非我命,璧未清而张孝未告,……我不知不能认。”对第二次付款,康声明:“此非我命,我不知两人私交,由两人自追取,我不能认,……私借则我不管。”总之,不负任何责任,“不论何人,凡非我命私借,私支,与我无与”(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康有为的信。此信由汤铭三转给谭张孝,《征信录》中未录写作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谭于是日收到此信)前。),此两数由谭追回。此外,谭曾先后三次汇款与康同荷、梁启超,但康同荷与康有为言分文未收,康令谭如果确曾寄出款项,追回交梁启超;否则,追还与他。谭解释说,三次汇款都寄到横滨《新民丛报》梁启超处,有收据和汇单为凭;如果尚未领取,当可追回原银,若已取去,则他首尾清楚,“亦不能不认帐”(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谭张孝的信。)。
这场争论,康有为要么失于折理,要么失于折义,不仅反映出他对琼彩楼不够重视,缺乏亲自参与,对一些来往资全的数目,用途糊里糊涂,未能做到专款专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缺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领袖品格。谭张孝理、据俱在,事情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康不得不承认错失,提出了结办法:“一,琼楼本息虽与孝(数)无关,惟前借二万四千后,冯手交数万必应照原立单清息;一,孝前经手七千,后多养五十,其息勿问。五十及卓如、同荷学费认之可也。璧借款,孝自追。宜侃数未(有)交到,可罢论,其余孝收过公款代支公事者扣之。商款则必须纳息,与公不同。学款归琼楼清之。”(注:《征信录·总长驳数后认数原信》。“宜侃数”指陈继俨交与谭张孝的八百元,谭否以曾收到此数。括弧内的字系据康手稿补入。)对照上述诸问题的争执,这无疑是一个对症下药的办法,基本上能起到息事宁人的效果。但是,综观整件事始终,康之所作所为、所言所说,确实过分,尤其是对谭张孝的态度,与经营琼彩楼前相比,截然两样,其家长或的处事待人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挫伤了谭张孝的雄心。谭始终自鸣不平,既要抑制满腔愤闷,顶住闲言碎语,又得解释事情因果,保全名声。因此一事,两人的师徒关系出现裂缝,而且是越来越大,以致无法弥合。
康有为收到1905、1906两年的琼彩楼账目清单后(谭张孝前后两次抄寄账单与康),认定为“极欺谬不清之册”,他发现两次账单的一些数目不相符合,斥责谭“真是乱束”,“今所开数,不论拨充股本、张孝借款、付充支数,一概不分,但开来往数,擅收他款,借支他事。以十六万元之巨款,三年而无分毫之息而认妄支他事,擅扣拨充股本之款,事同诱骗,实属任意欺乱,谓之棍盗可也,岂复成数乎?”声色俱厉,跃然纸上。他条分缕析,驳斥各条账目,声言一切“亟当澈底清查”,方能罢休(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康有为的信。此信由汤铭三转给谭张孝,《征信录》中未录写作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6月5日,谭于是日收到此信)前。)。对账单的评价,表明康对谭经营琼彩楼成绩的评价,即毫无成绩可言。
接获乃师信后,谭震惊之极,不知所措,“思之感情既深于昔日,今以钱银交手之故而出激烈之言”,实属意外。万般滋味在心头,痛定思痛,他回顾三年来为琼彩楼所做的一切,所牺牲的一切,致被称为“诱骗”、“棍盗”云云,认为是康“言不由衷,唾骂之惯技”,不足为奇,不足取信。他这样写道:“先生谓十六万巨款两年存弟,无分毫之息,尤为离奇,不可思议。故无论无此巨款,即或有之,亦承上发下,随手经过之款,并非存弟,又非弟私借,能责弟纳息也?……试问代先生做生意之款应责弟纳息否?借与琼楼之款,亦有琼楼是向。……凡此皆承先生之命,而认弟为傀儡者,能责弟纳息否?各款以琼楼为大宗,而琼楼之股,借款多由鸟约拨往芝埠,并未到过罗生存弟处一日者。先生不直接交涉,弟为其间接代理,遂至往来芝三次,丧失医业利权无算,而买得今日之结果者也!今谓商会出入之款皆计息,则主动者为先生,应纳息多少,还问诸先生可也,弟岂能代任其咎?……而先生存弟之款,今日拨东,明日支西,款无停贮,支无定候,又安有息可生、有息可扣?……又如华益诸人,凡代收入支出过手之款,一切责该人纳息,能行之否?如可行之,何认不责他人而独难弟也?”(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谭张孝的信。)他觉得,汤铭三、冯镜泉、康有霈等均与琼彩楼数目有涉,“共知共见”,且“一切均有信据”,不容赖账、希望“清白之躬,还我本来”(注:《征信录·总长驳数来往原信》中谭张孝的信。),并请康派人核查清楚,“勿轻听谗人之言,认叛离其亲众而失知人之哲”,致师徒“因财失义”(注:《谭张孝致康有为信》。此信未署日期,应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908年 6月5日)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廿二日(1908年8月18日,康于是日复信与谭)之间。此信删增涂改之处颇多,并无署名,似为未完手稿。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
虽然彼此已撕破脸皮,但谭仍希望财既失,义还存。这愿望是善良的,却又是一厢情愿的。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康、谭之争渐为人知,流言蜚语纷至沓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谭发表《征信录》,表白真相,从而将事件推向新的阶段。
三
《征信录》于1909年1月在美国出版, 目的是对整件事“澈底澄清,辨析毫厘”,以“明心迹而折流言”(注:谭张孝《〈征信录〉小序》。)。全书共有七个部分,即历年进支数目、总长驳数来往原信、总长驳数后认数原信、抄白各项信据、付电影原信墨迹、付琼彩楼还华益公司揭项数目、付琼彩楼股份芳名,再现了琼彩楼从筹办、集资、开办到争数的原因、过程、结果等诸多细节,使整件事的始末基本得到还原,尤其是“抄白各项信据”部分,节录康有为、康有霈等有关琼彩楼的资金的来源、性质、用途的信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项,无异于揭了康有为的老底,在保皇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对于琼彩楼账目之争和《征信录》的发表,保皇会内部出现不同的反应。据现有资料来看,绝大多数人站在康有为一边。他们从维护保皇会的角度出发,申明谭应尽快清还借款,谴责他发表《征信录》蛊惑视听;少数人则出于保全名誉的需要,对康的所作所为大表不满,间接支持了谭张孝;也有一些人借此“倒康”,站到康有为的对立面,加剧了保皇会的分崩离析。
杨灵石是属于对康有为极其不满的一类人的典型。他在1905—1906年间为保皇会事奔走于美、加之间,曾奉康命协助谭办理商务,对琼彩楼倾注颇多心力,熟知一些“内幕”情况。康叮嘱谭“万不可放(杨灵石)出外”(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905年11月10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催办酒楼原信》。)。及至杨赴波特兰料理去世的华侨梁鸿轩身后事,康又斥责杨“坏极”,在波城“生许多风波”(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906年8月 1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征信录·抄白各项信据·着纽约分局拨款入琼楼原信》,此信又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23页。)云云, 视杨与内奸无异,千方百计地想控制他,以防他泄露琼彩楼的情况,节外生枝。这些事实的真相一经披露,杨“愤怒殊甚”(注:1909年7月8日《龚强立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28页。), 指斥康“道德丧地”(注:1909年6月22日《杨灵石致康有为书》,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23页。),要求康查清此事, 澄清当年对他的种种诬蔑之词,恢复其名誉和清白。此外,叶恩、欧榘甲、刘章轩等一批保皇会员为开办振华实业公司,于1908年底开始在美洲筹款,恰值琼彩楼经营混乱的状况不断外泄和康、谭之争渐趋白热化以及《征信录》发表之际,他们便以此为把柄之一,大肆攻击康有为及其亲信,揭露他们经营商务的诸多弊端,引发保皇会“十年以来未有之变局”(注:己酉年十一月初四日(1909年12月16日)芝加哥保皇会伍鸿进等《请看叶恩、欧榘甲、梁少闲诸贼之罪状》,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又,关于振华实业公司的前因后果,参阅贺跃夫《刘士骥被刺案与康有为保皇会的衰落》(载《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康有为与振华实业公司》(载《岭南文史》1959年第1期)等文。)。
上述两方面情况皆因《征信录》而起,当事人基本上与康对立甚或对抗,可见,康与一部分保皇会员及支持保皇会的华侨的关系是较为紧张的。同时,大多数保皇会员支持康有为,起而顶住形形色色的攻击,展开还击。副会长梁启超虽对康、谭之争不甚知情,对谭“骗去十余万”“绝未闻知”,但仍望有“挽救办法(注: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8年1月26日)《与夫子大人书》,《梁谱》第431页。),另一个副会长徐勤斥责“谭张孝以诡谋诱纽(约)局诸人”,认定琼彩楼的资本“全为谭张孝所据”(注:1909年6 月《谭张孝致徐勤公开信》,《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23—424页。又见于美国保皇会资料未刊稿。);有的认为谭拖欠借款及利息“非顾大局”,必须清偿(注:1909年6月19日《骆月湖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19页。),有的认为谭在叶恩、欧榘甲等发难时发表《征信录》,无疑是落井下石,火上添油,“可恶之极”,声明日后掌权“必须报此阴谋”(注:1909年3月25日《游师尹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94页。重点号为原文有。)。
除发表《征信录》外,谭张孝还于1909年6 月发表致徐勤的公开信,对徐所言琼彩楼事纠偏正误,以表抗争。但无论如何,《征信录》的发表,表明他与琼彩楼的缘份到此为止,之后,他实际上退出了琼彩楼的领导班子。但直至1911年,还有股东如何家本(国内)、黄处达(新加坡)向他查询有关情况,而接管该楼的周国贤、游师尹却乏回天之力,琼彩楼的经营每况愈下。此后,曾为活跃分子之一的谭张孝也就逐渐退出保皇会的活动。
平心而论,保皇会投资经商是无可非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时势使然。随着保皇会组织日益扩大,会众日多,经费捉襟见肘,保皇活动的开展颇有难度。他们正是想通过开办实业,能对杯水车薪的资金情况有所补益,推动保皇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其次,康有为流亡期间,对崇尚实际、讲究利益、注重金钱的西方社会风尚耳闻目睹,自然而然地有所接受、有所仿效;一些华侨的致富也树立了诱人的赚钱示范效应,所以,重商观念的影响无疑也促使他们开展商业活动。康有为们经商是内因、外因联合作用的结果,是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投入社会实践,努力改造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有益尝试,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转型思想的影照,因之,康有为们经商体现了进步的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毕竟受时代的、阶级的和个人的桎梏束缚太重太深了,对现代经商理论和实务不甚了了,虽然制定了有关章程如《中国商务公司缘起附章程》、《商会改良章程》等,明确规定了各任职人员的职责权限,但在生意场中具体操作起来却有章不依,违背了“先明权限,次清报数”(注:1906年6月6日《商会改良章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87页。)的商业准则,人为控制取代了市场原则, 章程竟成一纸空文,不起丝毫作用,所以,多数实业投资难逃失败、破产的厄运。尤其要指出的是,康有为们没有摆正保皇变法与经商赢利的关系,不仅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实业投资中,保皇变法的“正经事”被撂在一边,颠倒主次,不分轻重,而且到后来竟把二者截然分开看待,忘掉它们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联动关系,这样,实业投资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作用,保皇事业势力走向穷途末路。当发生矛盾冲突时,他们并没有采取积极的、稳妥的办法解决之,而是往往归咎于某一两个人,以致裂缝不断扩大,矛盾愈积愈深,覆水难收,最后引起矛盾的大爆发,一些人因此纷纷离弃康有为和保皇会,严重削弱了内部团结。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1905—1907年革命派在大论战中战胜保皇派,革命思想风起云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已成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保皇会的海外投资和保皇活动不能取得实效亦是当然之事。
总而言之,保皇会经营琼彩楼有得有失,失多于得,得不偿失。康有为们失去的不是一间琼彩楼,不是一个谭张孝,而是人心的向背。琼彩楼的历史是保皇会式微的真实缩影,是一部分康门弟子和海外华侨摈弃保皇信念,投奔革命和回归革命的如实反映。琼彩楼的失败,标志着康有为神农救国理想的幻灭,加速了保皇变法实践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