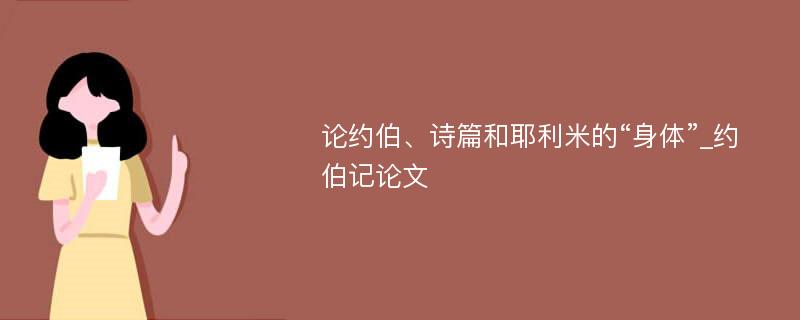
论《约伯记》、《诗篇》、《耶利米哀歌》的“身体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哀歌论文,诗篇论文,身体论文,约伯记论文,耶利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品集似乎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具有宽容心的一部分,许多具有异样思想的作品各自在这里找到了安居之所。作品集属于圣典的第三部分,其希伯来语词“纪土毕姆”(Kethubim)即意谓“一组文稿”(Writings)[1]420。或许这个语词特有的意义弹性可以使编订者依据自己的阐释将许多非正统文本纳入圣典,而对其他可能的阐释心照不宣。我们将要讨论的三篇重要作品——《约伯记》、《诗篇》、《耶利米哀歌》即出自作品集。然而我们将三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并非由于思想意义——应当承认,至少《约伯记》和《哀歌》具有某种“非圣经化”[2]116的倾向:《约伯记》当然是对上帝的理性化怀疑,《哀歌》也透露出对上帝的一定程度上的不满甚至愤怒——而是试图从文学表达角度进行一次崭新的探讨。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受造物,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7)人作为被造的存有,并非没有身体的灵魂,而是具备身体的存有,“人就是一种‘没有肉身便没有自我’的存在,”[3]46人类存在可以看作“一种通过肉身作用于世界的存在,这个存在同时通过肉身所提供的感官直觉来理解存在物的形式。”[3]66-67吉高认为人的主体性不单由独处的自我意识构成,也由人的身体构成,身体的结构让人成为行动的推动者,身体的行动表达人作为位格的存有。人的身体表达人的内在性,意识与自决皆不能脱离身体。[4]
身体标志着人的存有,并且表达着人之为人的特性,因而在哲学上和神学上身体都是不可忽视的。在圣经中,它进入了神学与文学的表达。所以,将神学与文学联系起来而侧重于文学表达对身体进行研究将是一种新颖的思路。由于身体在《约伯纪》、《诗篇》、《耶利米哀歌》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提出三篇作品的共同特性:身体性。身体性可以大致表述为经常性地回到身体来表达与描述神人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状态。在这里,身体首要的是指人的身体,而把动物或者植物的身体排除在外,因为如果将它们纳入考察范围,身体就会有扩大为笼统的意象的危险,这样就丧失了研究的意义;另外,这里的身体不但包括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各种器官——当然这些是最为主要的——也包括基本的身体需求一衣食住行,以及基本的身体行为一吃喝拉撒睡,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人的切身感受。下面就会看到,这种切身感受对于我们的讨论是多么重要。
一
身体性在三篇作品里面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修辞层面和非修辞层面。后者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然而前者仍具有重要意义,它显示了古犹太人对身体的关注已经达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身体简直构成了文字表达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细胞。
《约伯记》中,提幔人以利法在说到一种神秘体验时说:“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约伯记》4:12)约伯在诉说自己的遭遇时说:
“我的眼晴必不再见福乐,
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
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
——(《约伯记》7:7-8)
那些“不以舌头谗谤人”(《诗篇》15:3)的正直人才能得居圣山,而那些恶人总是“用口说骄傲的话”(《诗篇》17:10);毁灭耶路撒冷的“敌人伸手夺取她的美物”(《耶利米哀歌》1:10)。
极为明显的是,耳朵和听、眼睛和看,舌头(或嘴)和说、手和夺取等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一般的表达是不会将相关的身体器官予以点明的。在我们看来,古犹太人的这种表达不但是哕嗦,简直是赘余了。然而他们乐此不疲,在三篇作品中这样的表达是如此的频繁以至于成为了一种结构模式。如果说这种情形只是偶然出现,从而我们完全可以一笑而过的话,那么当它成为一个经常性现象时我们便不能不加以关注。那时的人们似乎习惯于将某一动作或行为直接与发出器官或部位相联系,而不仅仅笼统地看作整体的人或整个的身体的活动。当需要讲述这一动作时,相关的具体器官总是形影相随。这里就显示出身体对于表达的极端重要性与不可或缺性。
另外的一个普遍情形是身体及其相关行为被赋予了隐喻功能,或者反过来说,对与上帝的直接关系的表达总是通过身体来完成。祈求上帝实行拯救时,诗篇呼告:“求你起来……求你举手”(10:12),“你不要掩耳不听”(《耶利米哀歌》3:56),而信靠耶和华即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倒”(《诗篇》17:5)。从神学上讲,犹太教赋予上帝以位格,上帝具有与人相似的形体与动作,人与上帝的交往就同人与人的交往具有相似性,上帝以一种人格存在创造并参与历史,因此,上帝的“身体”以及人的身体出现在作品中便是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仍然折射出我们探讨的身体性的问题。身体成为隐喻的基点,从而被提升到神圣性层面了。
另一种修辞性层面的身体性就直接构成了修辞的一部分: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承他们的项上,
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诗篇》73:6)
下面一句诗仍是将抽象性的东西作为身体的覆盖物看待:
“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
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
像油入他的骨头。
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
当他常束的腰带。”
——(109:18-19)
另一处也这样描述咒骂的力量:
“我的敌人辱骂我,
好像打碎我的骨头。”
——(42:10)
抽象事物通过具体而独特的身体感受而成为了具体可感的东西。身体以及身体感受总是他们表达抽象事物的首要手段,骄傲或者咒骂总是被引向身体来进行描述。这里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对身体性的非修辞层面的界定。我们马上就要进行这项工作了,上面的探讨应该说都不是典型的身体性,典型的身体性,即非修辞层面的身体性,总是与身体感受紧密相联。
二
三篇作品中最为触目的是对身体的非正常情况以及对身体的侵害过程的描绘与叙述,并且许多时候都是大面积的集中出现。《约伯记》第30章中约伯痛苦地悲鸣:
“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
疼痛不止,好像啃我。
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
又如衣的领子将我缠住。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
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
《诗篇》第38章受苦者受到上帝的惩罚:
“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脓,
我疼痛,大大拳曲,
终日哀痛。
我满腰是火,
我的肉无一完全。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我就唉哼。”
《耶利米哀歌》第4章:
“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
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
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
枯干如同稿木。”
上帝对犹太人的惩罚引致的首要的是身体的巨大痛苦;相应地,他们祈求上帝惩罚恶人时,首要的是祈求上帝对他们身体的毁坏:打断恶人的膀臂,敲碎他们口中的牙齿,使他们喝醉以至于露体;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水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以至最终的死亡。人的身体是分有神性的,“然而人的身体又是十分脆弱的,极容易受伤害,包括被他伤害,利用或禁锢,又或自我伤害。”[4]犹太人将身体的损害看作一种严重的事件,它带来的痛苦不但是真切的,也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比外在的丧失更为重大。约伯在丧失儿女和财产后,仍然歌颂耶和华。撒旦在上帝面前评论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他进一步向上帝建议:“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约伯记》2:4-5)且不管撒旦的预言是否准确,作出这种预言本身即可反映出当时的犹太人把身体放在首要的地位予以珍视和保护。因而身体受到破坏对人而言是最具有破坏性和威胁性的。或许约伯的一句话即可作为这个问题的注解:
“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
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
——(19:22)
因此,在他们看来,上帝的惩罚最残酷的是伤害身体,相应地,在他们的意识中,最恶毒的诅咒是诅咒恶人身体的相关部位遭受打击;也因此,他们描述恶人对自己的攻击时总是围绕他们对自我身体的残忍击打: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阉。”
——(《诗篇》22:16-18)
在这里,性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前面的身体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主体性、感受性的存有,所有的刺激都落实到身体这一层面加以把握,身体去感受刺激感、烧灼感等等。而这里的叙述已经从身体抽离出来,身体成为被观察、被审视的对象。当然这是对身体关注的又一必然结果,关注身体自然会从外部凝视身体,观察身体动作。犹太人悲悯的、愤怒的、或者恐惧的目光不时会投视在身体之上。因此,他们会讲述身体的主动行为或者身体承认外部行为的过程。《约伯记》第16章第4-16节以及《耶利米哀歌》第3章的许多地方是上帝击打自己的记录,《约伯记》第20章第23-29节是上帝攻击敌人的描述,它们构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血腥场面,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这时已经是极具文学意味的场面描写了。的确,对身体的外部的细致书写很容易获得文学性。这是一种近距离的、迫近似的追踪,文学中让人着迷的细节就在这里产生了。《诗篇》第133章这样描述了亚伦的受膏: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又到他的衣襟。”
膏油经过身体时的那种缓慢的,似乎有些滞重的,然而又有淋漓之感的状态被到位地传达出来了。扩展一下的话,《雅歌》也是对身体的欣赏和赞美的绝妙诗篇,不同的是它是对身体本身的审美。前者是动态的,而它是静态的。
当然,当他们祈盼上帝的重新降临施行拯救时,他们也把身体的康健、舒适以及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放在突出位置。他们对上帝的颂扬也总不忘记提到上帝对人的身体的创造之功。
在所有这些关于身体的诉说里,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部位几乎都被包括进来了:头、脸、眼、口、鼻、舌、耳、脖颈、上膛、肺腑、心脏、骨头、腰、肚、腹、腿、脚以及血液、头发、眼泪、精液等等,可以说,在他们生物学的认识范围里,人体的各个部位一同进入了文本。应该说犹太人对身体是极为关注也极为熟悉的,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的身体也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神圣性的,人理应认识和珍视自己的身体。《圣经》里比比皆是的是关于人的清洁卫生、性生活、生育等规范,而且,犹太人将割礼作为民族的族类表记,“把‘肉体的约,与文化的‘约’联系在一起”。[5]16将肉身符码化。[5]18应该提到的是他们对动物身体也是感兴趣的。《约伯记》中对河马、鳄鱼的描绘远比对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的描绘详尽,也更富有激情。那么,对人的身体的难以割舍的表达情缘便不足为怪了。另外,将这种对身体灾难的反复诉说看作源于他们深刻的历史记忆也不会失当的。民族的多灾多难,以至惨无人道的巴比伦之囚事件,给他们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心灵震撼简直太大了,那是他们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梦魇。可以看到,被掳之前的作品虽然包含身体性因素,但只是偶尔出现的,远没有这里的集中和复杂。
必须指出,在圣经里,身体性与神圣性是不相冲突的,相反是有机统一的。身体感觉愈是强烈、愈有助于我们感受到神圣性:身体遭受灾难,是背逆上帝的后果,它警醒人们只有坚定信靠上帝才能解除这一切的痛苦。尼尔逊就敏锐地指出,神学反省不能停留于抽象,却必须从生活中的身体经历入手,而非只着眼于那些人认为是“属灵”的经历。[4]埃里希.奥尔巴赫在讨论犹太—基督教传统文体时指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高雅文体,这种文体决不轻视日常事物,对感官性的现实,对丑陋、不体面、身材猥琐,它统统纳而不拒,或者,如果用相反的意思表达的话可以说,出现了一种新的‘低级表达方式’,一种低级的、本来只用于喜剧和讽刺剧的文体,它现在大大超出了最初的应用范围进入了深邃和高雅,进入了高尚和永恒。”[6]81前文我们讨论了身体的隐喻问题,不妨这样认为,三篇作品中整个身体性表达即是一种庞大的隐喻:体验上帝的神性。
三
进一步的问题是,身体性在文学、美学上意义是什么?这才是我们从文学角度提出身体性的指向所在。上文已经提到了对身体的外部描述带来的文学性对文学的启示意义,这里感受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梅格·庞蒂在理解躯体时指出,“尽管我们总是把每次提供给感觉经验的事物看作某个对象的表现,但这种通向感觉的表现本身却总是通过躯体作为媒介。躯体确实是在对象性的世界内部与其他事物一起被发现,但是这种通向感觉的表现本身则只有通过躯体这一媒介才能被体验到。”[7]73身体在犹太人那里即是对于感觉的巨大意义。身体感觉是拥有肉身的人的普遍能力,肉身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最为真切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身体感觉在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一方面,相对于需要想象力参与的其他感觉来说,身体感觉是最为强烈的,尤其是身体受到损害时的疼痛感。我们常谓的“切肤之感”即意在传达切身的强烈感觉;另一方面,它又是最具有普遍性、可传达性的,肉身受到刺激时直接通过神经系统为我们所感知,具有完好的神经系统的人面对同一刺激时就会有同样的感觉,比如针扎指头时,我们都会有尖锐的痛感。因此,当《约伯记》、《诗篇》、《耶利米哀歌》聚精会神描述身体的受损害状况时,它们意在传达受损害时的痛感,从而传达尖锐的宗教体验。
感觉应该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人是一种肉身的存有与文学即是人学这样两种观念也向我们提示身体对于文学的重大意义。在现代,文学艺术完成了从“义”过渡到“感”的位移。[8]192单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讲,它经历了从感觉纯化到感觉复苏的发展过程。[8]192只是这里的感觉已经不限于身体感觉了。而同时,女性写作却在身体感觉内部拓展了身体感觉的领域。她们“紧紧抓住自己生命历程从出生、初潮、初吻、交媾、怀孕、生育等阶段的切身经历,从生命哲学的层次上体验生命的奥秘探索神秘的女性之谜人性之谜,开拓出每一个女人都要经历的生命现象和平凡的世俗生活中那诱人的生命之美。”[9]283然而由于身体本身的歧义性,有些时候身体成为被展示的对象,写作沦为堕落的下半身写作。对她们来说,也许重读圣经将会是一场庄严的文学洗礼。
另一方面,在着重表现身体损害的三篇作品里,“审丑”问题也相应凸现出来了。在那里,充斥我们眼目的,是从脚掌到头顶的毒疮,是破裂的肺腑,是发臭流脓的伤口,是干瘪的眼睛,枯干的皮肉,是锡安城的腰束麻布、尘埃满发的长老,是垂头至地的耶路撒冷的处女……,即使祛除身体性的隐喻指向,作品对“丑”的审视的目光也是宽阔的和敏锐的,具有震撼力的。而在传统的美学中,审丑总是被忽视的。因此,审丑需要我们重新关注。当然审丑是一个庞大的问题,既非本文论题范围,又非笔者力所能逮。值得指出的是,人们已经开始将审美与审丑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笔者所能做的只是试图引起人们对圣经尤其是《约伯记》、《诗篇》、《耶利米哀歌》中的审丑倾向的注意。
标签:约伯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