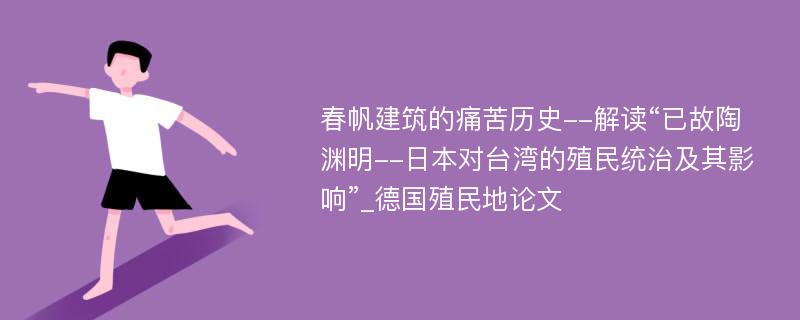
春帆楼痛史——读《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日本论文,楼下论文,殖民统治论文,春帆楼痛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4-0261-09
日本下关的春帆楼是甲午战后日本逼迫清朝政府签订割让台湾等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处。1911年,梁启超在此写下了《马关夜泊》诗,末句为“春帆楼下晚涛哀”。1955年,台湾著名学者黄静嘉先生首度赴日,凭吊于斯,发愿撰写一部其十年前业已开始研究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法制方面的著作。嗣后,又步梁任公原诗谱出新章,末句只改梁诗原韵一字:“春帆楼下晚涛急”。从“哀”到“急”,生动地表述了中华民族这一世代难忘的国家之辱、民族之痛。现在,黄静嘉先生又以“春帆楼下晚涛急”为书名出版他六十年来研究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的学术成果——《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注:《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黄静嘉著。繁体本,台北商务印书馆,2002年4月初版;简体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第1版。)下简称《春帆楼》,把这辱和痛又清晰地展示给了国人。都说“痛定思痛,其痛更甚”。这辱和痛的回忆对于每一代中华儿女却是必须的。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有忧患感、有危机感的民族才能有出息。据说那个被中华民族视为“伤心地”(梁启超《马关夜泊》中句)的春帆楼已挂起什么“日清讲和纪念馆”的匾牌,在当年日本军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势下,有什么“讲和”的氛围?!而今,面对日本当局对侵华侵亚死不道歉的态度和诸如年年张扬地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劣迹,以及两岸情势,深感黄静嘉先生大著写得及时,出版得也及时。尽管他是以科学理性精神来撰写的,但却深深地揭开了这层巨创大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宁愿视之为是一部痛史——春帆楼痛史。
一
在中国大陆,“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公认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将“半殖民地”置于“半封建”之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权或主权和人民基本人权受到列强侵夺戕害有多么严重。按我个人的理解,“半殖民地社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神州大陆而言,能够体现这个“半”字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列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控制国内政权并垄断财政、金融、商业、关税、文化、宗教等领域,达到资源掠夺的目的,同时以领事裁判权的方式攫取了我国的司法权,从而直接损害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另一方面,在神州的边疆领土则存在着实实在在的殖民地状态,其中,无论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台湾都是这些边疆殖民地中最大的。它以清王朝一个行省的建制于《马关条约》后脱幅而去!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回归祖国时,其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间已长达51年之久。宝岛的沉沦,曾经是亿万华族难以吞咽的奇耻大辱。百余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头颅和鲜血都抛洒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几个字上。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只要一日不归,华夏儿女的热血就一日不能停止沸腾。
今天,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然而,正因为它成为历史,才值得我们在这里认真地回顾和审思。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学界,少见有对台湾殖民史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带来的隔阻,资料阙如。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因为大陆学者缺乏对“殖民地”这个概念的切身感受。须知,对于神州大陆而言,或许用“半殖民地”四个字就可以概括近代中国,然而,对于台湾人民来说,则只有“殖民地”这三个字,才可以准确地言说那半个世纪的沉痛。这“半”字之有无,安可以道里计?!惟其如此,黄静嘉先生的《春帆楼》一书的简体版在大陆的发行,对大陆学界来说,就不仅仅是填补了日本殖民台湾史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将“殖民地”这三个字如此近距离地拉到了大陆学者的眼前。
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殖民地的剥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然而,当今天台岛中出现美化日本殖民台湾历史的论调时,除了一些空泛的评论外,大陆学者似乎较难切题应对。究其原因,不能真切地了解日本的台湾殖民史,特别是沦为殖民地的台湾人民曾经经历的苦痛和心路的变迁,便是一个重要的缘由。 《春帆楼》一书从制度层面全面考评了日本在51年间是如何利用政治法律手段压制台岛人民的。无疑,要想了解“殖民地社会”,制度分析是最直接的角度。它为大陆学界所重正在于此。
婊子最斤斤于给自己立贞洁牌坊。日本统治台湾也不忘披上一件合法外衣。根据《马关条约》第五条:“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出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徒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这个条文,貌似温情地赋予了台湾人民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脱离台岛的选择权,据说是符合国际法原理的,它也曾成为日人统治台岛的最强依据。然而,正如黄静嘉先生指出:“实际上,则台湾人民珍惜其先人开发斯岛的历史,且身家性命财产均在台湾,基于对土地的爱恋及实际困难,他们虽非出于甘愿,但其接受日本的国籍(臣籍),在当时情况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第22页)。这点说明非常重要,指出了所谓的“选择权”不过是在没有自由选择条件下的权利。就像传统资本社会中的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却被告知有商品交换的自由,但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哪还有别的什么自由?这还不算,当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它还要求你在一份格式契约上签名,让你承认是自己选择,并且承担一切责任。这哪里是什么“选择”?!如果这也叫做合法,那只是殖民的非法之法。这样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最适用的定义就是“专制”。我们以前往往重视专制的非人道性、苛严性、残酷性,其实,应该还加上一个特征,那就是虚伪性。我们知道,国民选择权理论的产生是基于社会契约原理,其本意是通过假设国民享有选择权来赋予统治的初始合法性。这一选择权的前提是,国民已经享有与统治者平等协商的地位,并且在现实中享有多项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它本是为了逻辑推理的必要而通过理论加以纯化的权利,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这种选择权一直是个值得怀疑的命题。以假设的、纯化的权利理论作为现实统治的依据,不但不合乎情理,反而极易为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提供依据。退一万步说,即使依据这种理论,根据《马关条约》或任何其他因战争结果而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统治权,都不可能获得初始的合法性。这是因为,统治的本质是对人口的统治。无论拥有多大面积的土地,如果没有人口,都只是私法上的财产权问题。因此,统治始终是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从契约原理上讲,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建基于双方之间的合意,这里的“合意”,也可以说成真实意愿的表达与合和。也就是说,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契约的达成。否则,其统治即丧失了合法性。从契约原理观察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即可发现:一、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权来源于战争和暴力而非合意,除了强盗逻辑以外,根本谈不上达成契约所须具备的“真实意愿”这一要件;二、由于统治权来源于侵略战争,因此,所谓的“条约”是违背契约双方必须平等自由这一原则的,一方面,被侵略的战败者没有平等协商的地位,另一方面,被侵略一方也没有意志表达自由和选择自由,缺乏这两个因素的契约,任何一个具备法律常识的人都可以断言,这是一个非法的契约。然而,本来是强盗的作为,却偏偏喜欢扯上文明社会中的契约理论作为遮羞布,这样做的结果,证明的是这个强盗不仅凶残,而且还极其虚伪,是真正值得善良的人们需要认真防范的强盗。只有在认识到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不具有合法性之后,我们才能对台湾人民的反抗行动之正当性获取真切的认知和同情的理解。在这里,“统治”与“统治的合法性”是需要加以严格区分的概念。
二
《春帆楼》一书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笔者在阅读中,不时地为黄静嘉先生那独到的视野和历经八旬苍霜的智者才具有的见识所叹服。如他在第十八章“殖民地人民之觉醒及抗争”和第二十章“余意”第二节“华人浩然之民族志节”中所表达的思想,即充分肯认台湾人民采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意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别是在“华人浩然之民族志节”一节中,作者在部分肯定林熊祥先生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看法后,明确指出,熊祥先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在于,只是肯定殖民统治时期的义举,而忽视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价值。作者的观点是:“这些非暴力抗争,正是符合当时现代性社会之主流价值的。其规模、深度及影响之广被及渗透,殊不亚于此前之誓死抵抗及奋举义旗”(第446页)。作者将这样的观点作为全书的结尾,足见其对这一观点的重视。作者的看法确有深意。经过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血腥镇压后,后期的暴力抗争在规模、数量上都有所减弱。然而,是否没有暴力抗争就表明日本的殖民统治已经获得了台湾人民的认同,从而因“统治”而获取了“统治的合法性”呢?这一问题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大多数论者停留在一种朴素的认识上,只承认“誓死抵抗”是一种否定统治合法性的表现,而忽视或无视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如果后一种认识能够成立,那么像拉.甘地在南非组织印裔同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哈维尔在捷克组织的《七·七宪章》运动,岂不都成了与统治者合作的运动?从反面来说,难道只有让人民去蹈死赴难才能算是守节?这种看法,如果说可以免于“以理杀人”之讥,至少也有迂腐之嫌。实际上,即使被统治者沉默,甚至不得己的屈从,也须分析这沉默和屈从的性质,并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何况,在那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从来没有沉默过,这只要看看《春帆楼》第十八章的考述,即可全面的获知。这一点对我们大陆读者尤为要紧,相比之下,我们所受到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的赞美教育要多得多,容易忽视非暴力抵抗的意义。
此前,一些人到处散布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后期认同日本文化的观点,已经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殖民统治者在物质方面予殖民地人民以“恩赐”,就可以渐次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应当指出的是,很可能正是殖民统治时期生长过来的“斯多哥摩症候群”(“斯多哥摩症候群”,“即事主遭绑架并长期与绑匪共同生活后,遂有认同于绑匪倾向之情形”,见《春帆楼》第439页)的成员希望人们产生这种错觉。这一错觉又导出一个实际层面的困惑,即是否经过日本51年的殖民统治,台岛人民的确已被“日化”或“驯化”,或至少是认同了日本文化而疏离华夏文化呢?在此方面,黄静嘉先生关于非暴力抵抗意义的观点及相关论析所作的澄清工作就显得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三
《春帆楼》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第一次清晰地再现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地制度的全貌。
殖民地制度曾经是这个星球上喧嚣过的社会制度。原始的殖民地制度已经被历史死死地钉在了耻辱柱上,然而,这并不能代表殖民地制度的幽灵就从此远离人间。事实上,“后殖民制度”正在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善良人们的关注和忧虑。它也是中国在将来必须予以警惕的物什。然而,不能认识那种原始的殖民地制度,就不可能对所谓的“后殖民制度”的性质有真切的认识。而对不知道“殖民地制度”为何物的人来说,《春帆楼》或可作为进阶之书。
揭示日本在台岛施行的殖民制度,是《春帆楼》一书之用力所在。其中关于日本式殖民地制度特征的阐析尤为精彩。
需要申明的是,认识这一殖民地制度的特征,可以暂时排除1931年至1945年时期。《春帆楼》一书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殖民统治前期和后期。前期从1895年至1914年,后期从1914年至1945年。前后两期又各分两个阶段。其中,后期以日本“处于准战争及战争体制下”为分段标准,以1931年为界,将整个后期分为两个阶段。该书的第十九章“殖民统治落幕之前夕——军部法西斯威权下之殖民地人民”,就是叙述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为战争需要,如何对台湾采取进一步严苛的统治。显然,利用这段时期的资料,对于殖民地社会的附庸性,以及殖民地制度向极端方向发展的型态特征等问题,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但如果利用这段时期的资料,却容易使反面论者可以此阶段并非殖民地制度之常态提供藉口。故为了说明日本在台湾实施的殖民地制度的常态特征,我们权且排除此一时期。
那么,1895年至1931年这36年间,日本统治台湾的殖民地制度具有那些重要特征呢?根据《春帆楼》的考述,试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唯一的意识形态。具体表现在,政府垄断教育和信息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将日本文化和“皇民”文化确立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意识形态“驯化”台岛华族。在这方面,首先表现在剥夺本岛人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这一点是被黄静嘉先生认为“最显著而突出的一点”,他指出:“台湾殖民地统治者自始即坚决地自小学教育起严格推行日语,而剥夺殖民地人们学习及使用本国语文之权利,其‘坚决’与‘勇气’,被认为是世界任何殖民地上所没有的”(第324页)。其次,“积极建立大小神社并推行其神道国教”,“促使各家庭供奉神宫大麻”。甚至一度毁坏佛像、佛具,“唯因此举引致佛教团体强烈反弹,并受到日本佛教界之出面支援,始趋缓和”(第307-308页)。最后,教育制度上推行愚民政策。在1895-1919年间,“只有临时性而时有变动个别学校之规则,而没有整体性的基本制度”,而“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在普及日语,和养成驯从殖民地统治秩序的‘臣民’”(第261页)。在这约25年的时间里,殖民地政府不但不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甚至限制本岛人参与中等教育。此后,虽然设置高等教育,但实际上,越是高等教育,就越是为日本人子弟独占。
第二、无所不在的恐怖。日本殖民地政府之所以能够推广上面那些禁锢人类心灵的措施,最大的工具是在整个台岛社会散布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怖。对此,我们只需以前期对台湾民众的镇压以及殖民地警察组织为例就足以说明。在前期的镇压中,则只需来看看殖民地临时法院对于“西来庵事件”的审判。在这个案件中,共拘捕1957人,“审判结果处死刑866人,有期徒刑453人,行政处分217人,不起诉处分303人,判决无罪96人。”(第205页)。你听说过司法审判处死866人的案件么?这是司法审判还是屠杀?“西来庵事件”后,台湾本岛人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正面抵抗,而维持台湾社会秩序的警察机构,则成为殖民地政府控制台湾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重要工具。对此,让我们来审视曾任总督府通信局长的持地六三郎的告白:“台湾的警察,实为台湾殖民政策的重心所在。台湾的警察,除其本身固有的事务外,而几乎辅助执行其他所有的行政。”因此,他还赞叹这是“警察国家”的理想“在台湾已成事实”(第222页注2)。台湾的警察势力能够遍布社会每个角落,又因为它直接控制了“保甲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保甲民负有连坐责任,使之互相监视”。对此,黄静嘉先生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控制了保甲组织之警察,遂成为无所不届无所不能之统治权力之代表。在现实生活上,民间所熟知者,保正虽为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但日籍的警察大人震怒时,可随时命其当众跪下,保正只有遵从,足见民族压迫之甚及警察权威之大。”(第226页) 而日本学者盐见俊二的结论也可作为黄先生论述的佐证:“警察既然掌握了保甲,警察力就渗透了行政的底层,因此,反又增加了警察的力量,提高了警察的地位。总之,讲到统治台湾,不能忽视警察。讲到台湾警察;不能忽视保甲。”(第227页)
第三、全面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这方面涉及极宽广,篇幅有限,只说两点。其一,台湾殖民地一直以总督府为最高权力机构,总督既是最高行政长官,又行使立法和司法大权(可集中参看第312-317页)。至于殖民地的官吏,则“由日本人垄断甚至独占”。当时的民众党领导人蔡培火在其《给日本国民书》中曾提到,在“日人据台二十五年之后,高等官中,本岛人的任用是极罕见之事,仅五名而已;判任官的有俸者,亦只三十余名”(第219页注1)。其二,经济资源的掠夺方面,仅以所谓“林野调查”为例。日本据有台湾后,立刻开始进行土地林野调查和登记。1895年,即日本据台之初,即发布《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其第一条规定:“凡无证明所有权之地契或其他确证之山林原野,皆属官有”。接着根据这项规定予以贯彻,其结果是“查定官有为916775甲,民有仅56961甲,不及官有十分之一”。这样,林野调查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林野调查整理之结果,“使殖民地政府由而掌握了大量之林野,以官业经营或以各种‘合法’之方式交予前来殖民地之日人‘事业家’们”(第125-126页)。
第四、在以上三个主要的统治特征下,产生一个反面的特征,即台岛华人丧失政治权利和部分私权。一、直到实施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即将日本国内法施行于台湾)以后,殖民地政府仍“明文将其中有关行政诉讼规定,一体均予删除,即仍不承认殖民地人民有以行政诉讼防卫其不受行政处分之权。其中,尤以治安警察法之排除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最为令人瞩目。盖殖民地统治者为镇压殖民地人民之集会结社,最常动用者即为治安警察法。铲除行政诉讼规定之结果,使殖民统治者得以就此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第289页)。二、在地方自治权利方面则更无论矣,“除厅、街庄协议会纯属咨询机关,根本未实行自治外,即设有所谓议决机构之州、市,其执行(理事)机关之州知事、市尹仍为官派。”(第240页)这样,本岛人不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在公权力侵犯公民权的时候,也不具备任何防御的能力。换言之,本岛人已经整体性地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另外,在语言自由、宗教自由、就业平等、平等接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也受到剥夺。在私权方面,一直到1923年才有商法在台湾适用。之前,则用罚则的方式限制本岛人采取现代化的公司组织企业。“因此,拥有数百万资金之林本源制糖只能按照旧惯上的‘合股’组成。在这里,殖民地统治者的目的,系在束缚殖民地人民经济活动的自由,抑制殖民地人民民族资本之抬头。本岛人如欲采取公司组织,只有把资本交给日本支配(与日人合组公司是可以的)或以日人为头,这是为了便利建立日人之支配地位与独占。”(第116页)。
至此,或许无庸再举例说明日本殖民台湾的制度特征了。实际上,所有这些殖民地制度,无非为了满足日本的两个目的:一是资源掠夺:二是为进入南亚做准备,从而实现更大的掠夺。正如作者所言:“以台湾殖民地而论,日本之获取台湾,一方面,固系以台湾殖民地之经营并直接获取利益为其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之作为南进扩张之根据地,此目的毋宁是更重要的”(第46页)。应该说,日本通过其殖民地制度有效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至于台岛人在这一制度中,则自始就没有被视为殖民地社会的主体加以看待。在殖民地社会中,他们是失去了人格尊严的人群。
四
在读完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后,每个读者对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性质都会得出一个自己的判断。笔者在看完黄静嘉先生以“余意”为题的末章之后,确实清晰地感受到先生未尽之“余意”。对那些尚未尽吐的“余意”,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笔者对自己的理解也设有把握。然而,因为这一番阅读深受作者的启发而有了“如鲠在喉”之感,故不避续貂之嫌而有以下讨论文字。
综观日本在台的殖民地制度,或可先以一言蔽之,该制度属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统治类型。
诚然,作为现代意义的“极权主义”概念,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它首先用于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其后的明确指向则是二战时期意大利和德国等法西斯统治。日本殖民台湾的初始时间发生在19世纪末,因此,要将日本殖民统治作为极权主义统治,在时间认同上似乎存在差异。其实,“极权主义”尚缺乏统一的定义。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的说法,极权主义包括这样一些特征:“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党制的国家,秘密警察统治以及政府垄断社会的经济、文化和信息结构”(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9页。)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来看,在某些方面与极权主义统治的特征确有不符之处, 如“一党制的国家”和“秘密警察统治”。然而,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权威学者汉娜·阿伦特强调说,“极权主义”的实质归根结底只是一点,即“极端的”、“无所不在”的恐怖。从这一总的描述来看,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是极为相符的。我不清楚《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作者在定义“极权主义”时是否研究过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情形,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更不可囿于一书一家一说。鉴于此,从极权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的常态,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有理论上的根据。
更重要的是,殖民地统治与极权主义统治之间原本有着内在联系。实际上,在人道主义、宪政、民主和法治观念勃兴并大行于现代国家之时,并不妨碍一些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上实施反人道、反宪政、反民主以及反法治的统治行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未完全从封建君主制脱胎出来的新兴军事资本国家,其国内的极权专制色彩尚很明显,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实施极权主义方式,更是不难理解的事。所以,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实施的种种劣政,包括以一种意识形态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在司法审判外衣下进行大规模屠杀、剥夺被殖民民族的基本权利,以及用无所不在的恐怖政治威慑人民的正常生活,和通过普及谎言来腐蚀一个民族的道德良知等等,都不过是作为常态的极权主义统治的表现罢了。这些统治行为的实施,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殖民统治者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却因此而公然地将殖民地人民作为客体加以奴役和榨取。其更深层的效果,则是摧残人的普遍尊严和践踏存在于文明社会中的公理。殖民地的存在,为维持某些恶的制度提供了温湿的土壤,使某些反人道的制度在此土壤上渐以发展,并为成熟的极权主义制度提供了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支援。可以说,日本对台湾实施的极权主义的殖民统治是上个世纪早期尚不成熟却很典型的极权主义统治形态。
今天,当有人无视殖民地统治者的恶行,无视这种极权主义殖民制度的丑恶性质,而公然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美化为“良心的殖民统治”。真不知道,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良心何在?赞美日本殖民统治者有“良心”的人的良心又何在?其居心又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