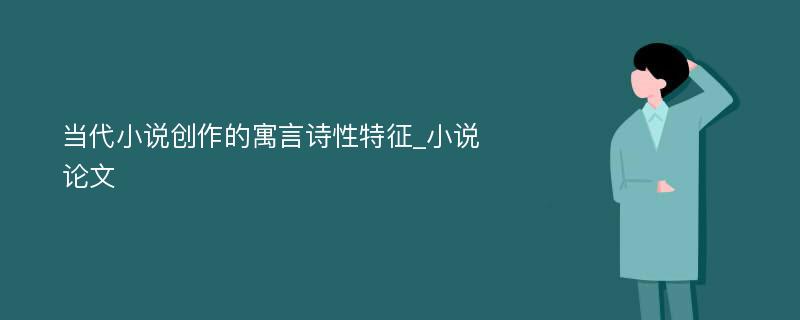
当代小说创作的寓言诗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言论文,特征论文,当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文学写作,无不追求以一种独到的文学叙述表达历史和现实、人 生与世界的存在及其联系,也就是努力以“历史地”、“美学地”呈现,“说”出一个 时代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精神性的存在状态。那么,在对世界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表 现及把握过程中,如何摆脱和超越以往文学表达、文学想象的局限和传统艺术模式的束 缚、制约,从而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达洞穿具体的社会生活表象,而直指人类、人性的 心灵内蕴,使叙事文学达到理想的境界,成为一代代作家努力追求的方向。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当代小说创作,不仅呈现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种 种特征,而且其感悟、表达生活的审美方式、美学趣味,特别是那种介于写实和虚拟之 间的意象性、寓言性表达,使中国文学冲破了以往“纪实性宏大叙事”规范长期造成的 形式匮乏和平面叙述的浮泛,为文学创作和阅读开拓了一个颇为宏阔的艺术空间。无疑 ,文学叙事表达的万千气象使当代中国小说呈现出深广的文化诗性特征,寓言模式的表 现形态经由中国当代作家之手趋于成熟,而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生活观念 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与世界文化、文学的一次成功“整合”。
1985年前后至今,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充满寓言诗性的小说文本。在“寻根文 学”思潮中,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王安忆的《小鲍庄》,以明显的寓言 力量,显示了不俗的实力;“先锋作家”苏童、格非等人以自己的写作表达了对超越时 空的文学永恒性的求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刘震云、阎连科以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 朵》、《日光流年》震动文坛;余华则以《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的深刻寓意展现 出文学叙述的巨大魅力和人文力量。以上作家们的写作表明着人们对文学的深入理解和 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
下面,我试从几个方面具体论述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寓言诗性特征。
解构时间:实现主体对现实的超越
当代小说的寓言化倾向,首先表现为作家们试图通过小说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结构性把 握,以小说的叙述结构建立起全新的寓言结构,从而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超越,艺术 地创造出永恒的时间结构。而透过现实世界与生活表层结构,使文学表达出能体现生活 内在本质的本体结构,则需要诗与时间的和谐呈现,那么使两者完善与和谐的途径仍然 是创作主体对于世界结构的清晰把握,说到底,创作主体只有充分地体验时间,即与人 的生命及其价值相关的时间,才能诗化时间,诗化生活和人生,使生活的结构诗化。因 此,结构时间,将客观物理时间转化成充分体验后的心理时间、文学时间,也就可以实 现创作主体对表层现实的超越。
结构主义学者霍金斯认为:“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一 思维方式中,“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 那种关系”。(注:霍金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作家余华也曾反复强调人作为创作主体同现实世界及时间的“结构关系”,他认为 ,“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时……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 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 ,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注:余华 :《虚伪的作品》载《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可见 ,只有创作主体对时间重新进行结构,捕捉或寻找“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 ”或取消“时间固有的意义”,才能在小说文本貌似封闭性的文学时间中,获得我们对 世界新的认知和理解,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这时,我们还会发现,我们在小说 的叙述语言和结构中,时间最终消失在阅读中,消失在叙述的空间中,抽象出寓言性的 关于世界的某些真理,给我们以审美的愉悦和发现的满足。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则是一部刻意解构时间的经典之作。它正是通过对于 现实表象时空的叙述和颠覆,即以创作主体的审美思维、审美观照方式重新编排生活, 建立起自己的小说本体寓言框架。生活被“颠倒”着进入小说的叙述,形成“时光倒流 ”式的结构模式。因此,从艺术史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说《日光流年》是当代极具形式 感的典范作品。
作家选择了“寓言结构”来结撰小说,创造文本独特的描述氛围,进行精致缜密的构 思,试图通过对一个完整故事的“寓言化”处理,来蕴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整 个人类的命运。小说以三姓村村长司马蓝为叙述线索,贯穿小说故事时空。小说第一卷 《注释天意》中,司马蓝便没能超越40岁的生命“大限”,以殉情方式自尽。第二卷《 落叶与时间》叙述司马蓝身体力行,带领全村人进城卖皮,拼命修渠改变水源,以延伸 生命之“时”限。在三至五卷中,司马蓝回到青壮年时代、童年时代、直至在母体里对 外部世界的感知。在全书的叙述中,主人公的生命时间被逆向叙述,叙事逆着正常时序 溯流而上,形成一种新的叙述时间、叙述语法。这种对文学时间的刻意解构,使文本产 生了开放性的寓言结构。文学时间一方面刻上了作家体验的印记,因为作家通过体验和 孕育设置了小说文本的潜时间,这是改变了物理时间之后的心理时间体验;另一方面, “作品的文学时间又是读者参与创造的结果,不同的读者以各自方式投入文学阅读而使 作品的文学时间以读者个人方式生成”。(注:马大康:《论文学时间的独特性》,《 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1期。)在这里,作家显然受到乔依斯、普鲁斯特、蒲宁的影响, 有意地打破文本的外在时间,在文本中创造出一种内在时间,这种内在时间赋予了作家 自身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和把握,时间的虚拟与实在化并存,体现出人的生存状态性, 人们在诗化的时间与人生中,捕捉、感悟到一种迷离、模糊的瞬间感受,从而生发出对 人生的价值、意义、永恒、失落诸问题的哲理思考。《日光流年》中的“40岁大限”意 象性地强调了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个人时间体验的有限性,我们在司马蓝的有限时间中 感受着一种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一生命个体的终止和时间的 终止。既然人的时间性就是人的生存性,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去把握有限时间 ,去创造和充实有限人生,打破客观世界为生命设定的边界,最终实现主体对现实的超 越,成为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之一。小说以表现主人公“死亡”起始,也就是将死亡作 为终结开始叙述,死亡是终结的现象,同时又是现象的终结。这种叙述方式冲击着我们 的思想,激发我们对生命的沉思。生命的终结对表现的时间性来说是什么?死亡对时间 来说是什么?生命的必死性本身是什么?对时间而言死亡的意义如何?小说引发我们关于 存在的遐想。
由于对时间的刻意解构和处理,对于《日光流年》这部小说来讲,被颠覆的时序使时 间成为小说结构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小说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主题。使司马蓝及三姓村 惊心动魄地恐惧的时间,成为走向死亡的隐蔽的叙事密码,成为整个人类生存的极限坐 标,成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困境的永久象征。
刘震云用八年时间潜心写作的二百万言四卷本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无疑也是 作家通过“解构时间”制造的高超文本。小说叙事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过去、 现在双重时间多次任意重叠,故事、场景不断变幻、转接、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 作家显然借鉴了福克纳式的叙述结构,其中现实与幻觉、死亡与新生、历史与未来、纪 实与虚拟杂糅交汇,除去几个贯穿性人物和游移飘忽的叙述人“小刘儿”,没有完整清 晰的叙述线索,时序的颠倒,历史与现实因果关系的迷失,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出多层次 、多视角、多场景、多隐喻主题的放射状结构。不同于《日光流年》,它几乎没有叙事 的焦点,庞杂的人物、庞杂的情节、纯粹的叙事欲望,拆解、解构着时间,造成看似支 离破碎的结构,形成“刘震云式叙事圈套”。
现实不仅被叙述架空,历史也变得捉摸不定,游移于鸿篇巨制中惟一可以辨析的只有 强烈的时间意识。比起马原在叙事中注重显露叙事过程本身,让叙事行为凌驾于故事或 陈述对象之上,刘震云则利用小说庞大冗杂的规模和繁复的叙述视角,即没有任何固定 视点,以及近乎“意识流”、“黑色幽默”的表现,叙述在多重层面上滚动、发展。并 且叙述以“时间”为纲,随心所欲地收束和展开、提起,扑朔迷离的独特文体“逼迫” 读者面对这一文本做寓言式的体悟。时间在这里被空间化、抽象化的叙事理念又使这一 空间形式获得文本的稳定性,最终写作和阅读同归于超时间性的寓言范畴。正如有评论 者所指出的:“《故乡面和花朵》极大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传统关系,赋予文本以现代 性的艺术旨趣”。(注:程光炜:《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文学评论》1999年5期 。)而除此以外,刘震云的主要写作意向恐怕还在于对“历史”、“故乡”等精神历程 进行整合,实现对历史、民族、社会、心理和人的生存境遇做诗性的追寻与求证,“还 原”那种隐含缠绕于创作主体灵魂深处的心灵真实。可以说,刘震云完成的是对生存批 判的寓言表达。
此外,其他许多当代小说家在运用“解构时间”的结构策略上也屡试不爽。格非在其 长篇小说《敌人》、《欲望的旗帜》和短篇《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中,将自我 意识融入文本的自然时间和叙事时间,造成文本时间上的模糊性空缺和重复。其中,《 锦瑟》采用破坏叙事里的时间顺序来破坏人们对世界与人生传统、秩序的理解。小说的 叙事不在时间里展开情节,而是在空间里呈现为一种新的叙述结构。由于故事在这里已 不再是作家所感受到的“情感载体”,因此,叙述便指向了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辨,这样 ,也同时拓展了叙事空间,增大了叙事容量。《锦瑟》让一个人在一篇小说中死亡四次 。主人公冯子存分别在考试落第,经商成功,做皇帝被诛杀,隐居等四种生存状态中或 自杀或被杀,表现出作家对人与世界关系、人的欲望的感受与思考。小说陌生化的、独 特的结构方式造成的寓言效果达到了极大的警示意义。苏童的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也都表现出时间意识的开放性 ,造成“现实与幻觉的双向转换”。(注: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 993年版,第92页。)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带来了叙事方式、小说结构意识、方法的革 命,而且,加强了小说的寓言化情境,即小说整体的寓言性、符号化,拓宽了小说叙事 的诗学范围。形式取决于一种写作思维方式,从而衍生出新的小说结构美学。那么,在 这种寓言结构小说的写作和阅读中,作家与读者不仅走向了形式的新颖,而且进一步体 验到思想内涵的丰厚。
象征营构:民间叙述与审美寓意化
从某种角度讲,许多小说故事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寓言性质,而故事的结构方式、讲述 方法、表现方法则会提升寓言的文化底蕴和更深层次的内涵。因此,我们说,文学深邃 的审美魅力实质上取决于表现。正如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所说:“在一切表现中,我 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 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 东西”,“用‘表现’这个名词表示表现力所促成的事物的审美变化。因此,表现力是 经验赋予任何一个形象来唤起心中另一些形象的一种能力;这种表现力就成为一种审美 价值”。(注: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2页。)桑塔耶纳在这 里所说的第二项,与我国传统文论中讲的“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弦外之音” 有相通之处。文学作品对第二项的追求,即象征化表现,体现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及 生活表象的穿透力,是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和把握,它使文学作品既呈现出多义性和无定 性,又有严肃性和哲理性,使人们超越生活的表象,从更深的背景和层次去体悟生活、 人生。所以,象征成为一种审美方式,在其对世界的符号化过程中,穿透作为表象的现 实世界,使审美产生寓言和神话的品质。关于象征的品质,黑格尔、克罗齐、卢卡契、 卡西尔、苏珊·朗格等有诸多论述,这里不做深入探讨,我们要阐述的是当代作家在其 写作实践中如何通过对象征世界的营构,在对生活的象征化表现过程中,以创作主体对 现实世界的真切体验,使象征所包孕的寓言表达方式克服其主题的单一性和定向性而走 向多义和深邃,使审美不是走向观念、理念的牢笼,而是以一种平实的民间叙述形态表 达对现实世界和人性的包容、体察、感悟,为人们提供一个进一步反观现实的艺术参照 系。实际上,其构造的是一个诗意的世界,而且,其中沉淀着叙述的魅力和极高的人文 含量。对此,作家们选择了不同的叙述方法。
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便是在写实的层面下进行象征营构并 产生巨大的寓言力量。
具体说,余华是通过对生活的整体性象征使审美走向寓言化的,而且,他选择对民间 生活形态的写实和白描的传统手段来完成生活诗化这一审美过程。从《活着》的故事表 层上看,他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败家子”的故事。这个小说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沿用了 传统的范式和路数,如同《围城》之于“流浪汉小说”,人物的行为方式,活动范围与 线索、人与人关系的规定都有一定的发展套路,也不难找出与其故事特征相近的文学史 上的诸多“原型”。福贵这个人物作为一个纨绔子弟,早年“不务正业”,浪荡鬼混, 致使命运发生巨大转变,从富阔少爷沦为一介草民。小说用力最多的是,福贵没有沉沦 ,而是开始了新的漫长的积累并在这过程中不断地遭受一次又一次新的变故。令人惊奇 的是,福贵都能够一次次地承受下来。余华在这部10万字的小说中,将人间的苦难铺陈 得淋漓尽致。而且,他对苦难的叙述竟又异常冷静,无论是作为小说文本中的“我”, 还是承担叙述功能载体的福贵的隐形“替身”叙述人,在文中都有效地控制其情感的流 动,接近于所谓“情感零度”的写作状态,他让人物、场景、世事沧桑的人间图景自我 呈现。可以说,作家表达了对生命的感悟,福贵、家珍这些平凡生命的生存与死亡、生 的悲观与死的宁静,与大自然交融一体的和谐,都在余华充满内在人道温情的平静叙述 中流溢而出。另一部同样表现人物命运的生存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使余华的写作走向 更深沉的民间叙述的空间。主人公许三观每在生活的关键处卖血,用生命本身的能量或 人自身最后的能耐解救自己,摆脱或暂时地改善生存的困境。我们看到,余华对许三观 的叙述,保持着与叙述福贵时大体一致的感觉。这两个人物都在社会的最底层生存跋涉 ,他们没有绝望,他们的苦难与世俗密切相关,他们能够“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实 际上余华是以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生活史为线索写出了“所有的中国人这几十年是 如何‘熬’过来的——不是‘活’过来的,而是‘熬’过来的”。(注:杨少波:《忍 受生命赋予的责任》,《环球时报》1999年3月12日。)可以说,余华对苦难的叙述中, 表现出小说的思想含量立足于作家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和想象的广度和深度上,而作品 巨大的深厚性则建立在余华对人的本能、行为和结局平静的提示中,小说道出了有关人 的命运与存在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内在欢乐与痛苦景象,是对灵魂与精神的诗性表达。 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这是不以写作技巧甚至写作机智取得寓言效果的寓言小说,是可 以多层面解读的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这是充满了现代主义意蕴的写实主义小说。 (注:阎晶明:《欲把小说比寓言》,载《文艺报》2000年2月1日。)这也实践着余华的 文学宣言:“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 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无疑,这种小说文本的内涵体现着一种 哲学境界和历史深度。
贾平凹的《怀念狼》选择了最具民间性的物象——狼展开叙述,形象地阐释对世界的 理解。这部小说围绕商州仅存的15只狼铺陈开来,以“保存、保护”其存在和赶尽杀绝 作为人的抉择,并以此表现人性、人的存在状态的作品。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讲,他写作 《怀念狼》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狼以一种凶残的形象存在于人的印象中,人是在与狼的 斗争中成为人的,而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惶恐、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 。因此,怀念狼是怀念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世界的平衡。上帝创造了人的同时 也创造了众多的生命,若包括狼在内的上帝众多子孙都死了,上帝也不会再保佑人类。 人的生存中不能没有狼,不能没有对立面,人不能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否则,人将会 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变成“人狼”。小说将人置于人性善恶 的临界状态,不同的人在狼面前的不同心态和取舍,呈现出人类的浮躁、清醒和麻木。 特别是当野狼近乎灭绝的时候,捕狼队的队员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他们的生命力在 不断地萎缩,人性的光辉和激情趋于暗淡,人使世界出现了失衡的危机状态,生态环境 的恶性衰变的同时,人自身也陷于一种尴尬、迷乱和不知所措的境地。作者反复强调, 这部小说,他选择最具民间性的狼,就是出于隐喻和象征的写作需要,隐喻和象征是人 的思维中的一部分,它最易呈现文学的意义。(注: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关于< 怀念狼>》,《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无疑,小说从表层的对民间生活的叙述 把读者引向一种精神沉思,在一个阔大的文化范畴中,作家试图完成对中国文化传统、 对人类的品性进行深入的批判和反思。在这里,具象与喻象、典型与象征互渗,对生活 的具象描述是对生活的有限把握,喻象的创造也即桑塔耶纳所说的“审美的第二项”则 是对生活的无限把握。其象征功能的运用,使小说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的限 制,达到了拥有现实、洞悉人生的哲理高度。
象征是对生活进行的诗化处理,是作家扩大自己作品容量的有效方式。王蒙的论述可 以准确概括余华等作家在这方面所做的追求:“一篇成功的小说,好的小说,往往具备 这样一些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不是分裂的:它既有直观性,又有思辨性,既有具体性, 又有抽象性,既有纪实性,又有寓意性;它好像暗指着什么东西,又不是非常明确的。 ”(注:王蒙:《关于小说的一些特性》,《创作是一种燃烧》,《漫话小说创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进一步说,当“宏大叙事”的洪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渐 趋消解之后,小说的诗性开始以一种深沉厚实的民间叙事形态和立场完成着作家的真诚 叙述。在文学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尽管文学的象征看似以弱化的形式继续承担着 神话的功能并以此张扬着理想与精神,但象征的营构仍以启示的方式支撑着审美的家园 ,把文学引向质朴和深邃的哲性诗学。
戏仿文本:寓言走向新的叙事空间
美国叙事学研究者华莱士·马丁在回答“小说是什么?”时这样陈述:“‘小说’意味 着词与物之间的错误联系,或者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文学可以被设想为对于言 语行为即语言普通用法的模仿,而非对于现实的模仿”。(注:华莱士·马丁:《当代 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多年来,有关小说和叙述的内涵争论 不已,但小说虚构的本质越来越不容置疑。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来,无论小说理论抑 或写作实践,小说习惯的那种秩序和等级已受到颠覆。特别是在先锋小说家的大量文本 中,“真实”、“现实”和“虚构”成为颇有兴味的现象,陈晓明对此所做的概括较为 精到:“真实的现实消失之后,叙述仅只是虚构的游戏——写作和阅读双重快乐的虚构 ,小说不是让你认识和重建现实,而是给你提示一次虚构的想象经历。写作和阅读不过 是面对虚构的游戏”。(注:陈晓明:《仿真的年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 页。)从另一角度讲,现实不过是人们对现实秩序的幻想而已,现实没有本源性的存在 ,它实质上是话语构造的产物。那么,无论是我们对现实的幻想,还是对历史的想象、 理解都可以被重新建构和虚拟,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审美规约和修辞策略使“现实” 或“历史”再度复活,进入一种全新的叙述和阅读境地。现实性、可能性和传奇性构成 的文学叙事形成一种符号化的审美功能。这种艺术表达,不再是僵死的词汇堆积的“现 实”故事载体,而是借助于对词语的歧义性想象,复活心灵,激活事物。这样,叙事便 创造了现实和生命,叙事成为主体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当代作家被视为较为先锋的 叙事选择就是“戏仿”文本。
“戏仿”文本实质上是对传统经典文本的破坏性颠覆,它采取反叛的姿态,对经典文 本进行夸张和变形。经典文本中的主题话语、情节、细节、人物心态均被改变既定形态 和叙事走向,这种放大镜或哈哈镜式的艺术处理,使经典文本遭到瓦解,叙事将文本象 征化、意象化、寓言化,文化含量增大。
李冯的两个短篇《我作为武松的生活片断》和《另一种声音》是典型的“戏仿文本” 。新的叙事成规、新的美学观体现了对“真实”的新的理解、体悟以及大胆的叙事追求 。前者选择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作为叙事基本框架,但叙事重心和角 度已发生了位移。《水浒传》中全知全能叙事在李冯的小说中变成了行者武松的内心自 述,尤其是作为深入民间民众根深蒂固的打虎英雄,其严峻、崇高、挺拔的强者气质和 气概荡然无存,而被一个酗酒成性、内心烦躁无聊的形象所取代。武松在这里不过是文 人施耐庵编造的富于神奇、传奇色彩的虚构人物,真正的武松则是喜欢暴力、浑身充满 蛮力的平庸者。《另一种声音》是以《西游记》作为戏仿对象,作家同样是借用这一家 喻户晓的古代神话故事作为结构本源,但在处理孙悟空这一盖世英雄、智勇化身时却把 他并入庸常之辈,让他走下神坛圣地,剥离其光环,以现代人生活经验和方式“武装” 人物,固有的经典人物仅仅成为小说构成的一个因素而已,孙悟空不再成为传统经典中 的孙悟空,而成为常常能变过去却变不回来、嗜睡懒散、东游西逛、深受物欲影响的闲 人。“取经”这一历经千难万险和人格磨炼的宏大主题被消解殆尽。《西游记》在李冯 笔下被篡改成“戏仿”文本,隐喻着另一种内涵,英雄和庸人都是创作主体根据自己叙 事的需要制造的事实,任何文本都是一种文化拟古、语言行为,都指涉为某种寓言、警 示;真正的英雄和庸常之辈都是审美创造,都是一种审美断言,即使是历史事实,在叙 述中也是讲述者重新阐释和臆想的一种寓言和神话。作家的权力就是进行寓言写作,诗 性生成,表现人物及其精神环境。
显然,这是一种新的“审美形式结构”,是个人的经验、自由的虚构、叙事策略的合 谋。如果仅仅说这是对技术的追求是不全面的,它还是对传统文体的一次革命性挑战, 是价值多元化时代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世界的寓言设计和“语言狂欢”。我们可以 透过文本的艺术意象挖掘其深厚丰润的寓言、文化意义,在对文本的审美体验中进行二 度创造,体味、把握世界的不同表现形态和特征,这样,才能诗意地接近和拥抱世界。
我认为,小说写作是对“非现实世界”的诗性描述,是作家心灵和想象力的体现,是 作家虚构的“有价值的生活”。审美创造的过程和审美接受的过程最终都指向象征和寓 言,指示着一种文化。当代小说写作已从单纯追求“意义”价值中走出,走入语言诗学 的审美层面。许多作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文本能包蕴更宽广丰厚的内涵和寓言诗性价值 ,探索艺术表现生活和世界的可能性,这正是当代小说写作日趋走向成熟的标志。
标签:小说论文; 余华论文; 当代小说论文; 寓言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许三观卖血记论文; 读书论文; 活着论文; 日光流年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