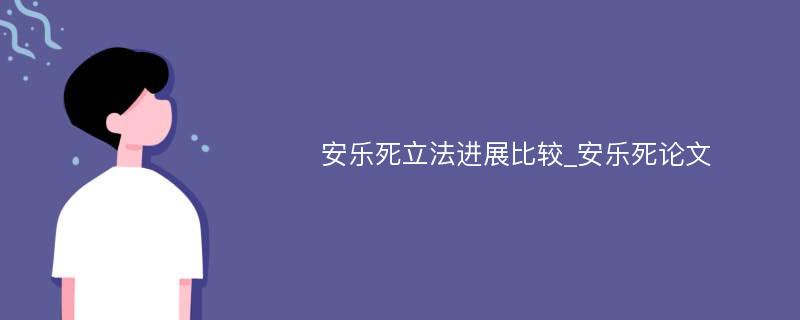
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乐死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安乐死,用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从怜悯出发,把身患不治之症和 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或做法。”西方医学界将安乐死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安乐死 是指采用积极的措施去结束垂危病人弥留在痛苦之中的生命,具体做法是给病人注射毒剂, 或 者给服毒性药品等等。而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对垂危病人的治疗措施,停止对病人的营养 支持,尤其是指停止使用现代医学设备和手段抢救病人,让病人自行死亡,这种做法往往被 认为更不人道。通常所讲的安乐死,主要指积极安乐死,在英语中又叫做“怜悯杀人”,即 某人以所谓不痛苦的方式,将身患不治之症而即将死亡而又希望死亡的垂危病人立即处死的 积极行为。
一、美国安乐死研究及立法
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安乐死状况的,当属美国人基非尔(Kiffer)。他早在1979年就在大 量 的收集、调查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名为Bioethics:A Textbook of Issues,U.S.A的书。在 书 中,他罗列了大量调查报告,尔后分析美国各阶层对安乐死的公众态度及认同情况。书中介 绍说:早在1950年,美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就对民众支持安乐死状况进行调查;后来分别在 1973年和1977年,又对普遍民众和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意见进行调查。这些调查表明,在美 国支持安乐死的人在逐年增多。(注:1950年,美国盖洛普民测验结果显示,36%支持不分类别的安乐死;1972年,美国《生活 》杂志进行民意测验,有41000人投票,90%相信临床病人有权拒绝延长生命的人工手段(Kif fer,GH.1979);1973年,已经上升到有53%支持安乐死。)1977年,美国医学会调查结果,59%的医生接受被动安乐 死观点;90%的四年级学生肯定这种观点。仍然有大量的医生表示要尊重病人的愿望,不再 使用 特殊手段以延长生命。只有5%的医生不愿探讨这个问题(Kiffer,1979)。
为什么有的医生赞成而不愿执行呢?据调查,有2/3的医生说担心被诉诸法庭,而且为了避 免麻烦;50岁以下的医生对临床病人近在眼前的死亡问题十分有兴趣,但50岁以上者则不感 兴趣。
基非尔书中还载有美国医学会的宣告:“在有确凿证据证实病人已经接近死亡时,医生建 议或决定停止使用特别手段延长病人肉体的生命,病人的家属可以自由地采纳。”
美国第一个关于安乐死的立法诞生在1976年9月30日,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小布朗在该 州死亡权利法上签字,1977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实,这是一个消极安乐死法。这项法律允 许成年病人在制定所谓“活遗嘱”(living will)后,授权医生关掉维持生命的人工设备; 只要根据医生的判断,该病人已经毫无疑问即将死去,以及生命维持系统的唯一作用只是在 延缓死亡的到来时刻。此外,该法还规定:“活遗嘱”的生效,必须至少有两名见证人,而 充当见证人角色的不得是当事医生或病人家属;而且,近亲家属并不拥有对于安乐死的申请 权 。在这一系列规定之下,医生才能根据病人的“活遗嘱”取下维持生命的辅助系统,这样, 对病人的死亡就不再负有任何责任。病人授权医生摘下人工生命维持系统而死亡,也不再被 看作是自杀,并且不影响其家属领取人身保险费。
出于对危重病人无法表述或者出现措辞不当的考虑,美国的“安乐死教育基金会”(Ecitha nasia Educational Fund)还起草了一份“活遗嘱”(living will)参考样本:“如果我不能 参加决定自己未来的这时刻的来临,我愿让我这一声明作为表达我的愿望和遗嘱。如果不存 在使我从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中恢复的合理期望,那么我要求死亡,不要求用人工的方式和 极端的方式,维持我的生命。死亡与出生、成长、成熟和年老一样是一种现实——一种必然 ,我害怕因每况愈下、依赖和毫无希望的痛苦所带来的屈辱胜过害怕死亡。我请求从怜悯出 发为我的晚期痛苦用药,即使这些药物会加快死亡的到来。”
看了这份“活遗嘱”,许许多多的人都会为这种对死亡的豁达而真诚地感动。因为他们认 为,安乐死可以减轻垂危病人的痛苦,当病人感到生不如死时,死亡比生存于他们来说就 是人道主义的行为;而且,这样的安乐死对社会有利,不必要浪费更多宝贵的人力、物力和 财 力来维持即将死亡的生命,同时也减轻了病人家属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况且,现代人对 生命价值的考虑,首先是生存质量;当病魔的折磨使人即将丧失尊严的时候,应该为自己的 尊严而乐观地选择——尊严地死亡(death with dignity),这也是人所应享有的“死亡权利 ”。
美国第一部消极安乐死立法,是受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著名个案影响的,其中最引人注意 的两个案件都发生在新泽西州。第一个案件发生在1973年,被告人是23岁的男性公民勒斯特 ·泽格曼尼克。在一次车祸中,他的26岁的哥哥乔治·泽格曼尼克颈椎高位性损伤,以致于 从 颈部以下形成高位截瘫,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精神上十分痛苦,便有了但 求速死的愿望。乔治反复请求自己的弟弟勒斯特·泽格曼尼克帮助自己结束他痛苦的生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帮助解除哥哥因高位截瘫所带来的身心上的极度痛苦,按其吩咐结束 了他的生命,但因此被送上了法庭。然而,1973年11月5日,陪审团最终认为“被告人患 有神经暂时失常”,而没有裁定为故意杀人罪。
其实,这是一例典型的积极安乐死行为。在当时,美国尚没有任何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直 到现在,美国医学会仍然反对积极安乐死。而世界上真正承认安乐死为合法的国家很少。瑞 典虽然承认援助积极安乐死,但却很少实行。
而1975年4月发生在新泽西州的另一例关于消极安乐死的案件,当时在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国 家 都得到了广泛报道,还促成了美国许多州对“自然死亡法”(Natural Death Acts)进行立法 。整个案件是因为误食饮料而引起的。
1975年4月14日,凯林·昆兰小姐在无意中将巴比妥酸盐(一种毒剂)加在酒中作为饮料饮用 而导致昏迷,被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在依靠人工呼吸器的情形下,处于长期的昏迷状态达 7个月之久。她的父母在确信她再也无法康复地醒来之后,请求医生撤去人工呼吸器,恢复 其“自然状态”。在遭到医生的拒绝和向法院起诉被驳回之后,继续提出上诉,最终于1976 年3月14日,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对昆兰父母有利的裁决:“如果医生和医院 道德委员会认为其绝无恢复的可能,那么挂在昆兰小姐身上长达11个月之久的机械呼吸设备 可以摘除;而且,摘除人工生命辅助系统与非法杀人之间存在着真实而绝对的区别。任何参 加者,无论监护人、医生、医院其他人,都不因此而负任何民事和刑事责任。”
时隔一年半之后,美国的第一个“消极安乐死法”在加利福尼亚州生效。自此以后,美国 又有3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自然死亡法。然而,各州对自然死亡法的 规定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主要存在于拟制“活遗嘱”的时间和某些细节上。最后,为了统 一各州的自然死亡法,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于1985年8月通过一项“统一重危病人权利法”( Uniform Rights of the Terminally ill Act)。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只有华盛顿和纽约两 个州的法律禁止安乐死行为,而俄勒冈州通过了唯一的允许医生辅助自杀的法律,但却在州 法院阻止下被暂停生效。
1997年1月8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华盛顿联邦最高法院内进行有关“临终的危重病人是否有 权向医生提出‘安乐死’,而这种医生辅助的自杀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的一场大 辨论听证会。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辩论,引起了全美各界的关注。当然,听证会由于支 持和反对双方各执一词,最终未能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但根据最新调查统计,在全美公众 ,包括医生当中,支持安乐死的人已经占了多数。[1]
顺便指出,世界上真正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是荷兰,而且荷兰也是最早实施安乐死的国家。 日本也承认积极安乐死,并由名古屋高级法院于1960年列举了合法安乐死的六大要件:(1) 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有不治之症,并且死期已经迫近;(2)病人痛苦异 常,令人惨不忍睹;(3)夺去病人生命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4)如果病人神志 清醒,并有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和同意;(5)夺去病人生命原则上应 由医师去做,如果不能由医生去做则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6)夺去病人生命的方法在 伦理上应该是适当的。
二、在半年内立而废止安乐死法的国家——澳大利亚
1.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的制定和废止
1997年3月25日凌晨,澳大利亚参议院以38票对33票,通过了中止《垂危病人权利法》的提 案。从而使安乐死立法仅仅生效了半年。这部在1996年5月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并 在7月份正式生效的《垂危病人权利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它使“安乐死”在澳 大利亚北部地区合法化。这项法律规定: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以上,而且患 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必须由本人递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书,要有本人签字;法 律同时还对医生履行“安乐死”作了详细规定,并规定在病人提出“安乐死”要求并且获得 医生签字同意后,分别要有七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
这部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是由时任北部地区首席部长的马歇尔·佩隆提出的。他曾亲眼看到 一位亲密的政友患癌症死亡时的情景,更感受于生母垂危之际的极度痛苦。所以,他建议北 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以便让没有生还希望的患者安然去世。该法 的 倡导者是一位名叫尼奇克的医生,他从该法5月份在北部地区正式生效之后到12月份的半年 时间里,已经帮助了四名患者接受“安乐死”。其实,这部“安乐死法”通过以后,澳大利 亚各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最后,由澳大利亚众议院保守派议员凯文·安德鲁向联邦 议会提交议案,要求废止“安乐死”法,并在当年(1996)的12月在澳大利亚众议院以88票对 35票,首先通过中止《垂危病人权利法》的提案。[2]
2.澳大利亚第一位接受合法安乐死者的情况
《垂危病人权利法》5月份通过,7月份正式生效;两个月之后,即1996年9月22日,鲍勃· 邓特(Beb Dent)接受由一台电脑控制下注射过量的巴比妥酸盐毒剂而死亡,从而成为世界上 在第一部安乐死法生效后接受安乐死的第一人(终年66岁),具体是由澳大利亚医生尼奇克实 施的。
鲍勃·邓特生于1930年,他一直是一个很坚强又很有主见的人,年轻时曾是英国圣公会传 教士,后来对基督教产生怀疑,因此离开教职。此后,在北部地区做过木工和估量员,认识 了妻子朱迪,并于1976年他46岁的时候结婚。1991年,61岁的鲍勃·邓特被诊断患了前列腺 癌,先后在布里斯班、柏斯和达尔文市做过三次手术,为防止扩散,双侧睾丸被切除。然而 ,即使如此,术后仍然常常出现反应,尿道堵塞,不得不使用导尿管。由于气候原因,感觉 十分不好。1995年8月,再次进行手术以疏通尿道,但是几个月后,癌细胞的浸润又使尿道 发 生堵塞。1996年3月,鲍勃·邓特特别邀请菲利普·尼奇克医生为之出诊,到家中为其看病 ,二人由此相识。1996年6月,他再次接受尿道疏导手术,术后健康状况骤然恶化,体重迅 速减轻了25公斤。经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髓,在其本人的要求下,医生告诉了他 的实际病情而且说明已经无法好转。
在鲍勃·邓特患病期间,夫妻二人开始笃信佛教,相信轮回学说。当病情进一步恶化,疼 痛加剧时,鲍勃开始想到了安乐死。当时澳洲北部地区的一些政治家、医学界人士和绝症患 者 一直在议论安乐死立法问题。1995年2月,在北部地区首席执政官马歇尔·佩降(Marshall P erron)的倡议下,通过了有关自愿安乐死的法案,这就是著名的——《垂危病人权利法》。 法案规定,寻求安乐死的绝症病人必须得到3名医生的签名——1名家庭医生、1名专科医生 和1名精神病医生。法律正式生效日期是1996年7月1日。
1996年6月以后,鲍勃·邓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腹部剧烈的疼痛使他难以忍受,只有靠不 断增加止疼药的剂量来缓解。因为同时服用大量的多种止疼药物,又引起了一系列毒副作用 ,更加使之痛苦不堪,夜里经常性大便失禁,妻子担任护理工作,从清晨到夜晚,不停地换 洗。在这样的情况下,鲍勃口述了一封长信,并由他的妻子朱迪代为记录成文作为遗嘱。在 信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他的痛苦状况:“这几个月我一直处在剧烈的疼痛之中。假如我有枪 ,我真想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我本来是一个很活跃、精力充沛的人,然而现在我几乎什么 也不能做,我需要他人24小时的护理……当我看着我的妻子为我受罪时,我的痛苦就更加重 了。”从这份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出,鲍勃·邓特即使在剧烈的病痛之时,意识还是十分清 醒的,他富有同情心,仍然体贴妻子。他是不愿再痛苦、不愿再增加他人的负担;同时,也 希望尊严地活着,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很活跃精力充沛的人”。如今的状况,实在使他无论 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和精神上都无法接受自己的生命状态。所以,他要选择安乐死的方法 ,来减轻自己和家人的精神负担,减轻痛苦。
当时,围绕安乐死的争议十分激烈,鲍勃决心在自愿安乐死法案通过后,就结束自己痛苦 的生命,而且他的妻子朱迪也理解他的心情,对他的选择表示支持。尼奇克医生也愿意作为 其家庭医生签字。鲍勃和朱迪对久争不下的“安乐死”立法之争忧心忡忡,每天关注着报纸 有关安乐死的报道。在鲍勃焦虑而痛苦地等待过程中,7月初,新南威尔士州的胃癌和前列 腺 癌者马克斯·拜尔(Max Bell)千里迢迢赶到北部地区,希望使用安乐死来尽快结束自己的生 命。然而,除了尼奇克大夫为他签字外,找不到第二位为他签字的医生,所以,只能绝望地 回到新南威尔士,并在一个月后在痛苦和遗恨中死去。这件事给鲍勃精神上的刺激很大。然 而,苍天不负,在几经艰难的周折之后,一直到1996年9月7日——即安乐死法生效后两个月 ,他才征得了除尼奇克医生之外的另两位医生的签字:一位是要求保密的前列腺医生,一位 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精神病学权威约翰·艾勒德(John Ellard)。
1996年9月22日,星期天午饭后的14点30分,鲍勃冷静地对医生说:“你到这儿来,是完成 一项工作,我们开始吧!”几分钟后,他安详地死去,而且指令键由他本人按下,他的妻子 朱迪也一直在场。
他的实施安乐死,在澳大利亚使对安乐死法案的争议更加激烈。在他之后,又有三位临终 病人接受了安乐死行为,但没有多久,这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就在澳大利亚众议院保守派议 员凯文·安德鲁的反对和提议下,经过辩论,最终于1997年3月25日,通过参议院决议而被 废除。
这部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自1996年7月1日生效到1997年3月25日被废止,总共才实行了八 个月。如果减去1996年12月众议院通过中止法案后三个月时间,那么,真正生效时间还不到 半年,其间实施合法安乐死者有四人。
三、中国的安乐死研究及立法进程
早在1987年,中国法学界、医学界和哲学界就开始了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其中很直接的 一个原因,是缘由陕西省汉中市的一家医院为一位女性肝硬化病人实施积极安乐死。
1986年6月23日,54岁的妇女夏索文因患肝硬化、肝脑综合症而住进汉中市医院;6月27日 晚,患者出现烦躁不安症状,时发惊叫,经安定处理后入睡。第二天,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 在得知母亲已经再也无法康复后,向该院院长请求为免除其母的痛苦,结束其母的生命,但 遭到了院长的拒绝。随后,其子及小女儿又转向住院部肝炎部主任濮连生反复提出同样请 求,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在濮开具处方并注射之后,患者于6月29日凌晨5时死亡。1986年 9月,汉中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将两位直接责任医生及夏某的儿子和女儿收容审查。检察 机关在审查此案时,对两位医生的行为形成了三种不同看法:①认为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②认为其行为构成过失杀人罪;③认为其行为没有构成犯罪。由于对该案的意见发生分歧 ,公安机关将两位医生解除收容审查,改处取保候审。同时,汉中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3 ]
1987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 京组织召开了“安乐死”讨论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8年1月22日在《午间半小时》节 目时间里,播出了讨论会的实况录音,节目组后来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她在信中表示 支 持安乐死,并写道:“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了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 物 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方法。”[4]
1987年,池连信对内蒙旗(县)级医院中32名中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调查,其中要求继续治疗 的有15人(占46.87%),除1人为牧民外,其余均为干部。而有13名牧民知道自己患有癌症以 后,只准备住院几天,而后自行带药回家。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自愿自行实施了消极安乐死。 而赞成积极安乐死的有一半以上(占53.13%),其中大多数是牧民(占76.4%)。在住院治疗的1 3名干部中,有4人在得知真实病情后,拒绝治疗,并于停止治疗3-4天内死亡(占总人数12.5 %),占干部人数的30.76%。而13名牧民得知患有癌症后要求带药出院,主要是出于经济费用 上的考虑,他们认为病情已无法好转,再继续治疗实在是浪费。[5]
1988年7月5-8日,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医学界、法学界、医学伦理界的近百名学者,在 上海医科大学讨论了安乐死问题。到会学者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却达到了一 致 看法——安乐死既是一个极复杂的医学、法学问题,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伦理学问题 ,因此应该持慎重态度。
1989年,应一等人对北京644名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安乐死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进行调查, 其 中包括75名医学,调查结束出人意料。见图示:
赞成积极
职业人数赞成%反对%
安乐死%
干部75 98.7 1.3
58.7
大学生 145 95.9 4.1
62.1
医生75 94.9 5.3
65.3
教师75 93.3 6.7
45.3
军人73 90.4 9.6
54.2
工人64 86.0 140
46.9
农民93 84.9 15.1 43.4
售货员 64 53.1 46.9 44.4
合计664 88.6 11.4 52.6
我国对安乐死问题的专题著作还没有,多是在关于有关论著中开辟一个章节来论述。[6]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然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 生存权利,而没有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积极安乐死在我国还是意味着不合法,因为没有对安 乐死的合法性进行规定,那么,与传统的故意杀人罪性质相同的事情都被解释为非法。根据 我国刑法规定,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构成故意杀人罪。而积极安乐死行为是故 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这一点十分明显。
在我国,合法地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由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二是在符 合正当防卫条件之下的自卫杀人。在我国的刑法学里明确地注有:经被害人同意而剥夺其生 命的行为也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这仍然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应构成故意杀人罪 。如果查明杀人的行为确实基于被害人的要求,而且是为了解除被害人的病痛,这也仅仅说 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可以作为法院量刑时从轻或减轻的理由。由此看来,我国法学界 将积极安乐死仍然视为故意杀人罪。
然而,消极的安乐死在我国不会引起法律问题这一点,自古至今一直地被国人在文化心理 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而且似乎大多数人都在自觉地遵守着这个原则,因 为这一现象与我国的实际状况有着极大的关系。1987年,由池连信对内蒙旗(县)级医院中晚 期癌症患者32人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中13名牧民在得知自己患有癌症之后,只准备住院几天 便带药回家,其实是自动地接受了消极安乐死。这个事件是中国人对消极安乐死默许并自觉 遵循的最生动说明。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物质资源并不丰富,医院医疗设备及医务人员都十分有限,人民的经 济负担能力差,因此,对晚期病人不予以积极治疗的情况时有发生,医院经常会拒收垂危病 人。对于这种消极安乐死的行为,普遍心理都能够接受。同时,在现实中,也不会将这种行 为 视为犯罪。
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地解释执行条 件和步骤,但又因为安乐死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复杂,一时尚不可能如愿地阐明。安乐死立法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面广。也正因此,不可能依人的意愿加以速成。这也是在世 界上真正为安乐死进行立法的国家极少而且还出现了澳大利亚随立随废现象的重要原因。
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普通民众的看法要比学者们的观念开放得多,因为他们只是依靠个人 的所谓良心和思想感情作为判断标准,而很少顾及到其它的社会问题,他们所考虑的只局限 在自身和家庭,至多是周围的关系和影响,而对于相关社会心理、伦理、法律、医护等问题 ,则很少考虑。
安乐死立法应体现以下特征: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个人意愿;而在实施对象、实施手 段和方法、实施程序等方面,都应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规定。
安乐死,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神秘的。虽然有时我们也能主动地选择死亡,然而, 当真正地因为自然的死亡脚步临近了生命之时,却无法面对和接受这个自然的生命法则,对 死 的恐惧、对生的向往和对世间人事的眷恋,融合成了临终者复杂的精神氛围。而出于这种精 神氛围的同情和设想,在中国的文化里,则形成了人文的情感拒绝,尤其在当事者面对自己 的至亲至近的人的时候。这种情感和理智充实的人文积累投射到社会环境之中,则形成了社 会抉择的诸多障碍,即使这种做法有利于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为此我们必须忍受诸多心 理和情感上的阵痛,整个社会应该做好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因为,有价值的生命——无论 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都有权利降临人间,而我们都应该以宽容和欢迎的心态等待她的到 来,而后再安祥地接受她、拥抱她。然而,她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吗?
倘若安乐死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又由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监督和约束其行为呢?又由 谁来付诸实施呢?谁又有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呢?是法律吗?法律只能通过社会的共同准则来 约束人的行为;但决不能在没有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对人进行裁决,剥夺其正常行为的权利; 因为宪法不曾赋予它这个权利,一切社会因素也不可能谅解地许诺它拥有这个权利。病人, 作为一个处在垂危之际的临终病人,被动地为自然生命规律所牵系,使生命衰弱地呈现在此 过程的最后最艰难的时期,本该是最值得同情;然而,他并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也不曾触 犯 法律的尊严。人有生存的权益,自然也有生病和死亡,以及接受治疗和关怀的权益,临终是 每一个生命个体所不可避免的。
所以,法律对于一个处在垂危之际的病人,也同样地没有剥夺其生存的权利。但是,法律 有什么权利可以行使呢?那就是充分地保障生命个体,保障每一个公民在临终的艰难之际, 可 以自由选择,以自己的愿望选择解除自我的无法康复的痛苦的权益,并对其实施进行有效地 监督和裁决,主持其公正。
历史和传统是由人谱写的,前人为我们塑造了过去的历史和传统,而我们的所有行为也必 将 作为历史沉淀下来。然而,其所形成的社会惯性是否成为良好的人文传统呢?我们有责任为 后人作出合理的解释,为后人建立一个良性的人文环境,而此沉淀作为能适应于将来社会 的惯性而存在,成为优良的文化传统。即使在现在的社会心理上可能会留下暂时不适的情绪 ,但是,我们必须作为抉择,必须忍受这种阵痛,在情绪上养成包容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