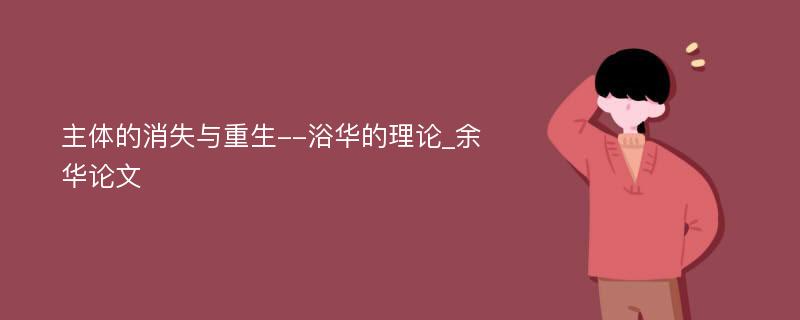
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华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余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6-0021-05
解读余华的小说,其叙事话语对旧有叙事陈规的改造是关键。但“先锋”或“新潮”,乃批评家着眼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概括;作家本身自有其念兹在兹的主题。对余华来说,主体的痛楚、苦难,主体的生存方式,乃至主体的存在与否(主体是否是一个人类自欺的幻相?),是一个纠缠不去的心结(complex)——如何在语言的牢笼里开辟出另一片切己的语言,以表达源自个体生命的经验,是驱策其不断进行叙事实验的动因。从早期处女作阶段的忧伤、惊惧,到“无情世界”的冷漠、超然,再到《在细雨中呼喊》隐约透露的温情之光,《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民间视野,余华的主体,历经了一个从泯灭到重生的过程。
一、创伤性记忆
我把余华初登文坛的三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下午》、《四月三日事件》称作他的“处女作阶段”。这三篇小说中,有两篇明确标示出主人公的年龄——十八岁。这个年龄提供了一个进入这批小说的入口。
十八岁,是一个少年初长成人的标志。这三篇有关“成人式”的小说,我相信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验,那些巨大的哀伤与失望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成他日后苦难世界的完整图景,忧伤、惊恐的情感像烟雾一般弥漫在文本里,构成了这一阶段小说的基调。与此同时,他日后小说中的重要主题:肉体与语言的施暴,蠢蠢欲动,预告燎原之势。
《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西北风呼啸的下午》都描绘了暴力所代表的成人世界馈赠给少年的见面礼。无论出外(前者),还是在内(后者),没有哪一个处所是可供荫庇的所在,“我”终至要被成人世界裹挟而去,接受它强行赋予的秩序。《四月三日事件》中,“四月三日”则可被视之为发挥着超常威力的先验能指“菲勒斯”,它的所指并不重要(臆想和现实在文本里密布疑云,勾画着“四月三日”暧昧的轮廓)。关键在于,当主人公试图以出逃来规避“四月三日”的诱捕时,恰恰完成了作为事件一种的“四月三日”,别无选择地进入了“菲勒斯”所代表的父亲、语言、权力之网。
这三篇小说都包孕了暴力的因子。但之所以把它们划归为“处女作阶段”,倒不在于风格的成熟与否,而是这一阶段的写作与此后“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经由叙述者和聚焦方式所把握到的写作者的感情脉络。
在这三篇小说中,前两篇的叙述者都是戏剧化叙述者,叙述者“我”活动于故事中,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布斯:《小说修辞学》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聚焦者也是“我”,聚焦与叙述同时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四月三日事件》的叙述者虽是非戏剧化叙述者,聚焦却严格控制在“他”以内,这个“他”的感知、心理完全可以用“我”来重写(注:“有一个验证的办法可以区分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那就是用第一人称‘重写’特定的片断。”参见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13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这样一种戏剧化、内聚焦的写作与他此后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形成了鲜明对照:外聚焦的叙述处于一个旁观的位置上,内聚焦的“我”却卷入了事件当中,猝不及防地与事件撞上,愕然、吃惊、伤心、恐惧,所有的人事都和“我”有关,“我”被抛入了世界当中,世界非“我”能把握。——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受伤的、惊恐的“我”仍然是一个主体,即使这个主体是一个弱小的,没有力量的主体。
《一九八六年》将主体的惊惧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这篇小说削弱了人物的心理深度,在人物的内聚焦中,小说大量充斥的是“他看到街上整天下起了大雪”,“他听到屋外一片鬼哭狼嚎”等诸如此类的感官的现象描述;但是,这篇小说依然保留了适当的心理活动——幻觉。幻觉的存在证明了主体的存在,只不过这个主体是一个精神分裂式的主体。
一般所说人物的心理深度是指人物有感情、看法、思想,幻觉则是丧失正常的心理反应,思维停留在事物的表象上,产生扭曲和变形。停留于表象说明人物的认知能力被破坏,但是产生扭曲、变形,尤其是《一九八六年》中疯子具有惊人一致性,朝着一个方向变形的原因、策动力何在,仍然可以追溯到人物的潜意识或无意识——这即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心理深度”。
《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幻觉总是固执地朝向杀戮、血腥,文革的创伤性记忆不断萦回在疯子的意识里,挥之不去,引导他一次次将现实的事物认作阴森恐怖的尸体、白骨、鲜血、脓液,引导他一次次将日常的世界变成残酷惨烈的梦魇。这种在精神分析学上称为“固置”的心理痼疾甚而至于使他一再地“强迫性重复”杀戮行为——刑罚。对他人臆想的砍伐与对自己真实的自戕交织一起,历史的刑罚研究与现实的杀戮行为互为指涉,正常与非正常,历史与非历史,各种界限开始模糊,小说的末尾“疯子死了”、“疯子又出现了”,生与死的界限也开始摇摇欲坠,生人与死人殊难分清,疯子是他,是你,是我?这时候,小说中蓄意描绘的春天、夏天、每一天,忽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恰应了鲁迅先生说的“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注:《鲁迅全集》第五卷193、194页。)。
我认为这一篇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书写文革达到少有高度的不多篇章之一。这与余华所采用的叙事话语有关。新时期的“伤痕”、“反思”小说大都立足于单一的叙述主体,叙事话语的类型多半是“控诉”、“追悔”、“悼亡”,主体在这场浩劫中只是一位被骗者、受害者、暂时性癔症患者;浩劫过后主体迅速恢复“正常”身份,过去的盲信、狂热、打倒与被打倒,做神、做人、做鬼,一概自动从记忆清除,人们若无其事地在苦难的废墟上搭建起幸福的新乐园。余华的叙事话语戮破了新一轮历史书写的假象。在《一九八六年》里,疯子不再作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被“现实主义”地描绘成有血有肉、有性格深度的主体;他作为一个无名无姓、文革中具体遭遇不详的人物登场,丧失了“控诉”、“追悔”的能力,而只是一次次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行为上重返恐怖的历史,乃至“误”认现实为历史。这样一个“正常”身份无限延宕,精神分裂式的主体,也许更切近文革、前文革、后文革“似真似幻亦真亦幻”的主体境况。
二、无情世界
巧合的是,《河边的错误》又写了一个疯子。但此疯子已非彼疯子了。
可以说,《河边的错误》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小说前半部分精心铺垫,渲染了一篇侦探小说应有尽有的氛围,然而故事行走到中途,却像一个饱满的气球被戳了一个洞,突然漏了气,侦探小说严密的因果逻辑和环环相扣,被置换为一个疯子的无意义的即兴行为——再没有比这更让人扫兴的结果了。在旧有的侦探小说文类中,凶手总能被送上正义的审判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的智力与能力终归能让暂时失序的世界恢复正常。可是在这一个戏仿的文本里,常规话语制造出来的人类信心遭到了摧毁,人们在这样一个无可理喻的世界里,只能枉费心机,束手待毙,结局不是死就是疯。作为故事发展原动力的疯子,不再是《一九八六年》中可从历史、社会追根溯源的心理学意义上的疯子,而是一个抽象的生理上的疯子,一个无人称、无性格、无心理的“物”。就是这样一个物,驱动着人们盲目的、虚枉的追寻。
就这样,余华彻底摒除了人物的心理深度,踏上他无情写作的长旅,开始构造起一个逻辑井然、富有秩序感的世界。这里我所说的逻辑,并不是指余华开始编造有头有尾、富有因果关系的故事,而是指余华这一阶段的小说呈现出来的一种共同的倾向。
这一倾向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小说中触目可见的死亡。死亡的给定事实,对死亡的预感,预告,成了他小说叙述推进的动力。《现实一种》以一个婴儿的死亡为开端;《世事如烟》则预支了司机的梦与少女4对命运的满怀忧虑作为死亡出场的先声;在《难逃劫数》中,叙述者甚至已不耐烦隐于文本之后制造隐约闪烁的预兆,而是在叙事话语中肆无忌惮地插入这样的句式:“后来,就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她不可能知道这种心情其实是命运的阴险安排”等等。这些让读者心中格登一下的句子出示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叙事者,这个叙事者似乎已将他的人物的命运牢牢握于掌中,随他的喜好他将安排他们逐一走上死亡、坐牢、自杀的道路,他已经不需要说明死亡的理由,只需一两个死亡通告,人物就将“难逃劫数”。这个真正的主宰者在《偶然事物》中终于堂皇登场:语言。这篇小说基本上由两个人的通信构成,一位有着偷情妻子的丈夫与一位经常周旋于已婚女性的男子,共同探讨咖啡馆里的一起凶杀案,两人在纸上展开如火如荼的对话、辩驳,讨论如何面对已婚女性外遇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最后的结果是,那位嫉妒的丈夫杀死了那位风流的第三者。文本并没有说明这位第三者是否就是勾引通信者妻子的第三者,而是突出了这一切的“纸上”性质:语言入侵现实并最终制造现实。
到目前为止,余华的主体走过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路线。他的叙述从个体面对庞然世界的惊恐开始,然后是创伤性记忆对个体的侵损与伤害,接着,个体的命运越来越被抽象为人类的苦难图景,人们毫无希望地在这个世界里存活,死亡成为人们无可规避的命运。随着他写作风格的确立,这个世界也越来越趋向稳固和形而上。这其间最富吊诡的是,写作者从面对世界的惊惧与惶恐出发,变成了稳操胜券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看透与阐释。余华的探索,一方面破坏了此前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所习于勾勒的、昂然向上的进化论式世界图式,同时又不自觉地滑向了另一种神话或迷思(myth),一种阴惨的、盲动的,主体束手待毙的“现实”。写作者的精神立场从起始的直面、惊恐到步步为营的旁观、超脱,最后只剩下一副颓败的抽空了历史与社会的世界图景:主体面对这个世界无所作为,只配拥有“物”的命运,被抛进、被杀戮、被抛出,激动、痛苦、受伤、恐惧的“人”失去了,主体沦为物的结果只能是盲目地、盲然地杀人(物?)与被杀,这一切在语言的快意驱遣下,小说中的人物与小说外的写作者一同卷入了这场能指的死亡嬉戏与狂欢。
三、温情的微光
在分析被认为是余华的“转型”作品的《在细雨中呼喊》之前,我想先厘清两个词语:苦难与痛楚。在我的理解里,苦难更多地与“人类”这样一个省略了无数个体的范畴联系在一起,它代表一种总览的概述,给出的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而痛楚则更多地与个体相关,个体的喜悦、哀伤、甜蜜、迷茫,像细雨一般绵长地、无声地将个体网织在里头,那些在细雨中压抑的、悲切的呼告则成了生命艰难成长的回声。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并不认为《在细雨中呼喊》标示了余华的转型,相反,我认为他回到了他最初写作的源头——生命的痛感。
阅读《在细雨中呼喊》,最强烈的感受是:写作者的感情回来了。此前余华的写作在驶上了风格成熟的轨道之后,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词语狂欢的趋向,技术漂亮的同时,写作者的脉搏越来越难以触摸。在叙事话语对旧有成规的改造上,余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当然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于写作者来说,如何表达出他自身真实的经验,如何完成他对生命的摸索与追探求,却是一个需持续一生、努力接近诚实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叙事话语类型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能否从常规话语所夹带的隐蔽的意识形态中突围出来,在不断入镜与破镜的镜城突围中,困难地说出自己那“无词的言语”。
《在细雨中呼喊》一共四章,重新启动了“我”作为叙述者,叙述的节奏时而不安,时而舒缓,笼罩其上的则是一种酸楚的叙述语调。正如流泪是出于伤心,或是因为幸福,《在细雨中呼喊》的酸楚同样有两种:悲凉的与安慰的。相对来说,第一章与第三章更侧重前者,第二章与第四章则偏向后者。有趣的是,第一章、第三章所描述的父亲与“我”,祖父与父亲,都是一种“内”的关系,而第二章、第四章的“我”与朋友苏宇、鲁鲁、养父母王立强、李秀英则是“外”的关系。“内”是亲属、血缘,但是并没有多少血浓于水的感情,相反充满着遗弃、侮辱、斗争(想想“我”祖父与“我”父亲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所焕发的智慧);与苏宇、鲁鲁,与养父母并无原生的关系,却有短暂的、极可珍贵的温暖。苏宇与“我”成长中理解的同情,在鲁鲁幼小的身上所显露的生活的不幸与他执拗、幼稚的抗争,王立强有些粗暴但真挚的父爱,李秀英对“我”诚实品质无保留的信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成长生涯中温情的微光。余华否认了爱一定来自生理、血缘(《现实一种》中,余华曾提供了兄弟相互残杀的景象),这种爱的根基并不牢靠,相反,对他人的体恤、关心、尊重、信任,才是真正的、支持人们活下去的理由与依凭。
应该说,这些温情有如夜晚的萤虫,光芒微弱地明灭在整篇小说中,痛楚仍然是整篇小说的主调。余华并没有就此提供一个乐观的人生图景。但是在经历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恐惧、惊慌,到“现实一种”的残暴、冷漠,现在,我们看见余华在这个令人越来越窒息的主体的牢狱里,凿开了几扇温情的窗子。
四、民间形态
个体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呢?也许设问的方式可能不同,但只要是有一点生存感触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或多或少会触碰到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庞大的知识体系给出了各个层面的解答,现世的政治意识形态更是提供了众多可供仿效的人生楷模与榜样,但是如果我们把眼睛转向民间,从他们的视线看去,他们是如何看待“活着”,又是如何“活着”呢?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余华在他对主体的思考上又跨出了一步。在“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中,余华用抽象的类代替了活生生的个体;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他复苏了带着痛楚与温情的主体,再接着,余华把他的主体放到了“民间”的背景上。
《活着》的叙述两部分,主体是福贵讲述他的一生,另一位叙事者“采风人”则起了串场的作用,他的职责准确地说是聆听。“采风人”的叙述袭用了余华过去的话语方式,描写、抒情、议论,各种错落的句式仍然保留了知识分子的语体习惯。相形之下,福贵的叙述则平白如话,余华将福贵的语汇、句法严格地控制在一位农民的文化水准之内,他过去的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特有的出人意表的余华式比喻消失了。我这里随意抽取他过去的一个文本为例:“她拖在地上的影子如一股水一样流入了茅屋。”“那堆火轰然倒塌,像水一样在地上洋溢开去。”(《鲜血梅花》)。
一位普通农民想象不出如此复杂、本体与喻体之间有着奇异联系的修辞。福贵的讲述中仅有的三次比喻均不需要精致的联想,直截了当,带着农民朴拙的表情。例如:“爹说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刀、盐”是农民生活里不可缺的物什,这两个经过生活及主体触摸过的比喻放在福贵的讲述里,呈现出了贴心贴骨的面目。
有必要在这里比较一下余华前后两类不同风格的比喻的功能。在第一类中,比喻作为强行连接在横组合上的纵聚合,扩充了能指链。这些完全可删去而不影响句子进展的比喻,像一颗颗诡异的石子硌在文本里,提示了小说的“叙述”性质,叙述话语不容忽视的存在,意味着主体不过是语言制造出来的一个文本中的“道具”(注:余华曾公开表示:“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5。)。《活着》的比喻则恢复了主体与比喻息息相关的联系,农民自身的生活经验引发了农民的比喻。这样一种充分尊重人物自身的比喻,表明了写作者的叙事姿态的一百八十度转变——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开始让位于民间的话语方式,写作者收敛起自己的语言,开始谦虚地倾听民间的声音。
应该说,这样的写作并不是原地倒退:重新回到现实主义模仿论所谓对人物的真实模仿,事实上,“语言只能模仿语言。”(注: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194页。)因此,民间话语在余华作品中的启动,实际上意味着写作者思维方式的位移——一种民间朴素的人生观开始进驻到写作者对主体的思考中。
这种民间话语方式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这部小说没有复杂的故事与故事结构,整部小说依顺时序展开,借助了民间说书与戏曲中常用的叙述方法:省略与有意重复。省略类似于民间故事里经常出现的“许多年过去了”。在这种叙述学上称为“省略”的叙述方法中,叙事时间一笔带过了事实时间,事实时间在文本里被压缩为零,叙述一下就进展到若干年后(注:参见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社1990年版。)。《许三观卖血记》中频繁使用了这样的省略,像荒年一家人躺在床上睡觉的情节,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许三观一家人从白天睡到晚上,又从晚上睡到白天,一睡睡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一日。”这些省略除了推进叙事速度外,还表示了民间日常生活的稳定或停顿,平静或苦闷——“无话可说”说明了民间生活形态的停滞。
另一类有意重复,则反复书写了人物的某一类经历。许三观卖血的事迹类似于著名评剧《杨三姐告状》中为姐姐的屈死哭冤上访、百折不挠的杨三姐;当许三观一次又一次面临着卖血,当命运一次又一次扼住许三观的咽喉,杨三姐、许三观们的坚韧、顽强,他们无可作为的作为(杨三姐的告状经常要先承受一顿责打才可允许其“发声”,许三观的卖血则使得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焕发出了底层民间对命运的抗争与对生命的守护。即使他们采取的方式经常是弱势的,不得已自我毁损的。在这里,重复产生了辉煌,单纯孕育着伟大,这些有意重复的叙述使得民间平日隐而不彰的可贵品质凸现出来——那些埋藏在凡俗生活里的坚毅与温厚,在重复的动作里,显露出了它广大包容的光辉。
但是,《许三观卖血记》与《活着》不同。前者讲述的是坚韧,后者则是忍耐。忍耐,是对世界不抱有看法,不对命运发出怨言,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当福贵的儿子、女儿、老婆、女婿、外孙一一地死去,福贵和一头老牛仍然扶持着继续人生的长旅,余华描述的这一幅景象有地老天荒的味道,生命的顽强也借此体现。但我对于这种完全受动的、主体在世的方式,心有疑窦。许三观的卖血是出于对生命的守护(尤其是他的多次卖血是为了一个非亲生儿子——乐)。福贵的活着却止于活着;活着,就是接受“活着”那无可奈何的悲怆。余华在《活着》里再一次流露出他抽象化(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犬儒)的倾向,在“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里,他抽空了历史与社会,同样,在《活着》里,“活着”又一次变成形而上的主体本体。
民间是一个包罗万象、瑜瑕互见的世界。我们现在还难以判断余华是否找到了他主体的立足点。民间对生命的坚韧与温厚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根基,但是民间也还具有退缩、保守与犬儒的面目。将主体交托予民间,并不意味着主体就可一劳永逸地避开权力的入侵与破坏(《活着》中老全死于战争,庆余死于为官僚的太太抽血,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乐要表达对许三观的爱时,也必须借助政治话语的掩护:第一爱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其次才是许三观),主体的命运仍然面临不虞之保。
民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只能在他者的参照下不断予以定位(注:参见南帆《民间的意义》,《文艺争鸣》1999,2。)。它并不存在一个恒定的,足以与权力(政治、商业、知识)相抗衡的本质力量。它如同土壤一样,但却无法保证其能开出鲜活的花。活着本身绝不只意味着活着,种族、阶级、性将毫不留情地将主体卷入各种各样的权力场中,为了主体更美好、更丰富的生命,抗争、努力、奋斗,也许还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主体在世的根基,他的生活与思考、爱与愁、泪与笑、耻辱或骄傲,一切的一切,探索的路远未终结。在这里,我愿意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送给余华,作为他继续前行的见证与鼓舞:“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