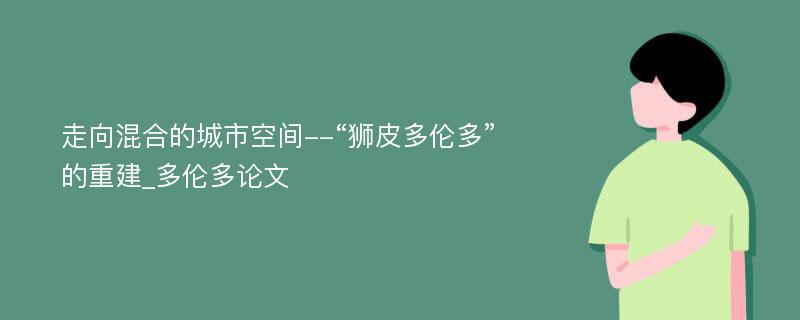
走向杂糅的城市空间——《身着狮皮》对多伦多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伦多论文,重构论文,走向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如何在政治独立之后争取文化独立,这是加拿大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面临的问题。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似乎给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然而,这一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消除文化隔阂和不平等现象,这一点不断受到质疑。迈克尔·昂达奇(Michael.Ondaatje,1943-)提出的杂糅也许可以成为加拿大文化发展的另一条可能途径。在其小说《身着狮皮》(In The Skin of a Lion,1987)中,昂达奇对移民城市多伦多①在20世纪初的发展进行了重构,表现了不同文化在城市空间的遭遇和冲突的过程,指出了新的文化生成的可能性。这个新的文化既不是对英国文化的延续,也不是多元文化的拼盘,它具有杂糅的特征。
“杂糅”一词源于生物学,19世纪中期之后,这个词被借用于种族和文化研究。根据克劳狄·奥赫恩的定义,杂糅是指“双方或多方相互混合生成第三方的过程”,这个第三方的“起源难以确定,与生成它的各方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②。文化杂糅最初是指在殖民征服过程中,殖民者文化和被殖民者文化“相互联结、融合、交叉并最终发生转化的现象”③。但是,杂糅并不仅仅发生在殖民者文化和被殖民者文化之间,而是贯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杰里·本特利认为“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常见现象”。④爱德华·赛义德进一步指出:“没有任何文化是单一的、纯洁的,所有文化都是杂糅的”。⑤霍米·巴巴则明确提出:“正是两者之间的空间承载了文化的含义”。⑥《身着狮皮》所关注的,是加拿大的英国殖民者后裔所坚持的英国文化和欧洲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杂糅的可能性。
昂达奇笔下的20世纪初的多伦多,正经历着巨变。第一次欧洲移民浪潮席卷而来,不仅改变了这座城市有形的物质空间,而且改变了这座城市无形的文化空间。一方面,移民工人日夜不停地建造两项十分重要的市政工程——布洛尔大街高架桥和东区水厂。前者使城市可以越过唐河河谷向东延伸,将东区和城市中心联结起来;后者则通过网状管道向城市居民提供干净的用水,从而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联系在一起。一座现代化的加拿大城市正围绕着这两座建筑显露雏形。另一方面,这些移民“使得多伦多人口的文化结构变得复杂起来”。⑦他们的到来“增加了加拿大的文化多样性”,却也“造成了种族和文化的冲突”。⑧他们在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位置,与英国殖民者后裔冲突、斗争、走向和解,使多伦多从一个二元对立的空间向一个杂糅的空间发展。
在《身着狮皮》中,多伦多首先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空间。英国殖民者后裔和移民在城市有形空间的位置是对立的。以市政工程局局长罗兰·哈里斯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后裔竭力控制城市的有形空间。哈里斯负责布洛尔大街高架桥和东区水厂的建设。按照他的计划,在他的严厉督促之下,高架桥“在梦中架了起来”。⑨同样,“为了他老做的一个……梦”,他“为自己”建造了水厂。⑩这两座建筑帮助哈里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帮助哈里斯实现梦想的移民工人却身处城市的边缘。《身着狮皮》用黑暗的空间比喻移民在城市中的边缘位置。在这部小说中,移民最经常出现的地方是黑暗的空间:安大略湖底黑暗的隧道,夜晚的高架桥,黑暗中的起居室、酒吧间和面包坊。昂达奇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帕特里克指出:“如果你看不见你就无法控制任何事情。”(11)黑暗中的移民无法控制城市空间,城市不属于他们。
英国殖民者后裔和移民在城市无形空间中的关系起初也是对立的。高架桥和水厂不仅使哈里斯实现了改变城市有形空间的梦想,而且给了他控制城市无形空间的权力。因为“城市具有可塑性”,所以谁可以“决定一座城市的空间如何塑造”,谁就可以“在这座城市打上自己身份的印记”。(12)哈里斯给高架桥命名为“爱德华王子”,给多伦多打上了英国文化的印记。以哈里斯的名字命名的水厂更给了他控制整座城市的能力。达芙妮·斯贝恩指出,要成为城市的主宰者,“可以通过控制空间来控制城市资源”,从而达到“左右城市现状,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13)。哈里斯深知“哥特人本来可以通过摧毁罗马城的沟渠占领这座城市。切断水源或者在水里投毒都可以让城市屈膝投降”。(14)控制了水厂,就控制了干净的水源,从而可以控制城市,让他所代表的英国殖民者后裔成为城市的主宰者。
相反,身处城市有形空间边缘的移民,在城市的无形空间也处在边缘。戴维·哈维认为“城市空间的塑造象征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现行的社会秩序”。(15)多伦多是哈里斯按照自己的梦想塑造的城市。在这座城市,移民面临着被抹煞历史存在的危险。市政府的摄像师给建设中的水厂隧道拍了照片,却没有拍隧道中的移民工人。在高架桥建造过程中,哈里斯让人在不同的施工阶段,从不同的角度,给高架桥拍了4000多张照片。可是,没有人给移民工人拍过一张照片。因而在有关多伦多城市建设的历史档案中,没有移民的身影。昂达奇在谈到《身着狮皮》时说,他为创作这部小说曾经做过大量调查,“我可以告诉你建造布洛尔大街高架桥用了多少桶沙,因为这是多伦多的历史,而建造了这座该死的桥的工人却无人提及。他们不是历史!”(16)哈里斯等人“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移民建造的高架桥和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上,抹去了移民在多伦多存在的痕迹”。(17)移民没有被城市官方历史所记载,隐没在历史边缘的黑暗之中。
移民还面临着丧失文化身份的危险。他们无权继承自己的文化,甚至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英语是唯一合法的语言。警察局长德雷珀强行通过了一条法规,规定如果他们在公共场所使用英语以外的其它任何语言,都会被监禁。因为不懂英语,移民工人在上班时间不能互相交流。要发出声音,只能学习英语。在英语学习班上,“一个操纯正英国口音的声音说我叫欧内斯特,接着许多男声也接二连三地跟着说自己叫欧内斯特”。(18)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也失去了自己的姓名。更有甚者,当他们到职业介绍所去求职时,那里的人“给他们都取了英文名字。……他们记住这些陌生的外国音节,就像记住一个数字”。(19)被剥夺了使用自己本族语言的权利,被剥夺了真实的姓名,移民处在城市的社会文化边缘,只是一个个数字而已。
此时的多伦多,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延续英国文化,移民继续生活在城市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边缘;或者以另一种文化取代英国文化;或者提升移民地位,多种文化平等共存。
昂达奇不愿意看到移民受到排斥和压制。他在小说中对移民工人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的描写,充分体现了他对移民的同情;关于多伦多城市建设调查的谈话,则明确表达了他对移民被官方历史边缘化的愤怒。但是,他并不赞成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他认为,二元对立的模式可能造成双方对立的紧张关系,甚至导致暴力对抗。在小说中,伐木工人卡托因为罢工计划泄漏而惨遭杀害;换过几个工作的帕特里克为了发泄对城市主宰者的不满,纵火焚烧马斯科卡旅馆,因此被投进监狱。在这两起事件中,移民的反抗并没有成功,自己却受到了伤害。可见,昂达奇并不认为对抗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昂达奇也没有为小说中的多伦多设想一个多元文化的发展前景。事实上,多元文化政策(20)自1971年出台之日起就不断遭到批评质疑。多元文化社会被比作一幅马赛克拼图:“以单一的主流文化为背景,由几个名称各异、各自具有内部同一性、边界清晰、无法融合的非主流文化拼接而成”。(21)更有人指出,“强调非主流文化应当受到尊重、保护、支持”,其实是“暗示不同文化之间是无关联的,每一种文化都是经久不变的,永远不受外界影响,并且内部没有任何分歧”。(22)换句话说,多元文化政策只能在对于文化的本质和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框架内调整文化关系。
《身着狮皮》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创作而成,而昂达奇却在这部小说中为多伦多设想了另一条发展道路,让城市的不同文化群体朝着相互沟通、和谐共处、融为一体的方向发展。小说在描写哈里斯排斥移民的同时,描写了另一位英国殖民者后裔帕特里克融入移民群体的过程暗示虽然英国殖民者比其他移民更早来到加拿大,但是他们也是移民,他们与加拿大空间上的相互从属关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与其他移民相互融合,才能使加拿大成为他们共同的家。
帕特里克出生和生长在多伦多以北的林区小镇,可是在这个他本应熟悉的地方,他却感到孤独和陌生。他的孤独感与早期英国殖民者的孤独感是一致的,而这种孤独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与加拿大空间上不确定的关系造成的。在北美这片寒冷荒凉又美丽壮阔的土地上,他们既渴望开始崭新的生活,又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受到大自然的漠视和威胁,不知道如何把陌生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23)。在帕特里克经常翻看的地理课本里,“彩色的染料绘成的加拿大地图”上有大片“没有命名的地区”(24),说明殖民者还不完全拥有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对他们来说仍然陌生。
在《身着狮皮》中,哈里斯通过建桥造厂和给建筑物命名,把原本陌生的空间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又通过排斥移民,确保自己在这个空间的主宰地位。和他不同,帕特里克渴望通过与镇上移民工人的交流,来摆脱孤独感。在晚上,他看见伐木工人在结了冰的河上滑冰,向空中跃起,再重重地落下,让坚硬牢固的冰层托住他们。移民工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他们对空间的把握让帕特里克着迷。白天,这些移民在镇上居民的眼里是陌生人;晚上,他们却使他的世界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变得陌生,让他成了小镇上的陌生人。“他渴望握住他们的手”,却因为“对自己和这些说另一种语言的陌生人都不够信任”而“不能大步走上前去,加入他们”(25)。因为他不能和这些移民交流,就无法摆脱陌生和孤独感。
多伦多和小镇不同。昂达奇把帕特里克也称作“移民”——从林区小镇到城市的移民。言下之意,在这座新兴的、还在变化发展中的城市,每个人,包括英国殖民者后裔都是移民。所以任何文化,包括英国文化,都不是必须遵循的传统。正如罗伯特·弗雷泽所说“《身着狮皮》中的多伦多没有任何传统,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可能”。(26)在这样一座城市,帕特里克逾越了语言、民族、文化等界线,了解了移民的生活和情感,融入了他们的群体,和他们一起找到了归属。多伦多在经历了对立和冲突之后,面临着杂糅的前景。
帕特里克刚来到多伦多时,对说另一种语言的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仍然存在。他默默地工作,不与身边的移民工人交流。但是,他对这些和他一起干活的移民的观察,让他了解到他们对待空间的方式,从而改变了他对移民的态度。与哈里斯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可以通过沟通和协调使空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不是强行划分空间界线;他们允许和邀请他人分享空间,而不是排斥他人。
行窃高手卡拉瓦乔对自己所在的空间非常了解,可以自由地在黑暗的空间里拆散和组装家具和电器,也可以越过界线,在他人的空间里行动自如。但是,他越界的方式不是使用暴力,而是改变自己。越狱时,他把自己漆成蓝色,和天空一样蓝,和监狱的屋顶一样蓝,于是在狱警的眼皮底下逃走了。特梅尔科夫负责在半空中检查高架桥的铆钉,他对自己工作的空间也了如指掌,却从不强行进入这个空间的任何角落,而是借助风势在半空中来去自由。他随时准备接受他人进入自己的空间。因为这样,他不可思议地在半空中接住了黑夜里被风吹落高架桥而闯入他空间的艾丽丝,并且把这个陌生人带回朋友的酒吧。
作为移民,特梅尔科夫和卡拉瓦乔被排斥在城市边缘黑暗的空间。他们顺势而为,是保护自己的聪明做法,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和他们相比,盲人伊丽莎白对空间的看法更加积极。对她来说,黑暗和光明并没有区别。哈里斯等人“将移民推进黑暗的湖底隧道,那里是被排斥的人的空间”(27)。空间界线也成为身份的界线。然而,如果光明和黑暗之间没有界线,那么“被排斥的人的空间”和城市主宰者的空间也就没有了区别。伊丽莎白与特梅尔科夫、卡拉瓦乔一样,并不企图控制她完全有能力控制的空间,但是她比他们更进一步,主动邀请他人和她分享空间。她带领帕特里克参观盲人的花园,告诉他自己对花园的了解,让这个看得见的人,这个和她不一样的人,了解属于她的空间的秘密,在这个空间里自由行动。
卡拉瓦乔等人对待空间的方式表明,空间是开放的,可以包容不同的群体;空间的界线可以模糊,被空间的界线所分隔的群体,可以消除对抗,相互妥协、沟通和融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了解,帕特里克跨出了融入移民的第一步。他越过语言的界线,进入移民的群体。移民在公共场所不可以说自己的语言,而在马其顿人聚居的社区,帕特里克却学会了用他们的语言说几个词,因此被他们所接纳。少年帕特里克因为对说另一种语言的芬兰伐木工人不够信任而无法加入他们,因而无法走出孤独,而现在他在说另一种语言的马其顿人中间找到了温暖。打破语言的界线之后,他进入他们的空间——墙壁上挂着欧洲风景画的家和巴尔干风情的酒吧,通过他们结识了芬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了他们的痛苦、恐惧和渴望。那些“说另一种语言的陌生人”对他不再陌生,他成了移民相互联系的网络中的一个环节。
随着语言的界线被打破,民族和文化的界线也被抹去。帕特里克了解到,移民在多伦多城市建造的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刚刚来到多伦多时,他受雇成为一名“搜寻者”,寻找失踪的百万富翁安布罗斯·斯莫尔;进入移民群体之后,他对这位城市的主宰者之一失去了兴趣,转而搜寻移民过去的历史。他了解了他们在高架桥上和隧道中所做的一切,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缝入历史”(28)。在帕特里克眼中,这些建造多伦多的移民也是这座城市文化地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制革厂里,染色工跳进满是“红色、赭色和绿色”的染料池里,“就像跳进了不同的国家”;当他们从染料池里出来时,“一直到脖子都染上了燃料的颜色,他们拖着湿漉漉的皮,因此看上去好像他们剥下了自己的皮”(29)。这样的描写“把移民彩色的‘皮肤’和他们的文化身份联系在于一起”(30)。这些不同颜色的移民工人,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代表,站在雪地里休息时,他们沾满了染料的身体组成了一副彩色图画,就像帕特里克少年时翻看的彩色染料绘成的加拿大地图。受到哈里斯排斥和压制的移民带来的文化走出了边缘,构成了多伦多乃至整个加拿大无形的文化空间的一部份。
帕特里克和移民的相互了解和接纳甚至抹去了他们之间身份的界线。第一次参加移民在隧道里的集会,看到哑剧表演中扮演移民的木偶因为受到当权者的侮辱而伤心,因为无法用语言表达而伤心、无助,他不自觉地走上台去,想要结束这令他痛苦的场景。这时,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移民中的一员。在后台,半明半暗的灯光、管道和仪表之间的道具箱、悬挂的木偶间偶尔走过的演员,让帕特里克仿佛走进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他感到自己“在像一个木偶一样走路”,并且无法分辨在他眼前闪过的影子是木偶还是真人,“一切现在似乎[都]在变形的过程之中”(31)。真人与木偶、观众与演员、英国殖民者后裔与移民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身份界线的模糊意味着不同的文化群体不仅可以和谐共存,而且在相互影响下开始发生转化,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小说结尾,哈里斯和帕特里克之间的身份界线也趋向模糊。面对放弃了炸毁水厂计划的帕特里克,面对帕特里克对他排斥移民的指责,哈里斯意识到城市的发展与移民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压制和排斥移民可能会让隧道里的集会发展成集体的暴力反抗,摧毁城市和他的权力。他还回忆起自己和母亲在这座城市的奋斗,顿悟自己和帕特里克、卡拉瓦乔、特梅尔科夫一样也是移民。他看着睡着的帕特里克,“看见他周围的狮子因为生命而自豪,然后他手拿斧子,从皮带下面拔出剑来,像离弦之箭一般扑向它们”。(32)在故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国王吉尔伽美什十分勇敢,曾独力杀死狮子。他像哈里斯一样,梦想建造一座城市,以此展现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帮助他实现梦想的恩基都来自森林,就像帕特里克一样。吉尔伽美什和恩基都最终成了亲如手足的兄弟。现在,在哈里斯眼里,帕特里克成了吉尔伽美什。哈里斯承认了帕特里克和他是城市的共同建造者,帕特里克和哈里斯这两个人物发生了重合、交叉和转化,他们之间的身份界线变得模糊。
虽然,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物之间身份界线的模糊只发生在特定的情景之下,在某一个瞬间里,但是,杂糅的前景已初步显现。多伦多不必遵循英国文化的传统,而应该有自己新的独立的文化。这个独立的文化由不同的文化构成,因而具有包容性,但是构成新文化的不同文化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不是多元文化的拼盘。这个新文化是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转化的结果,它不断发展变化,是具有活力的、杂糅性的文化。
注释:
①长期以来,加拿大人一直认为“多伦多”在当地印第安部落的语言中意为“聚集的地方”。这个意思使得多伦多成为移民国家加拿大的象征。虽然现在有语言学家发现这一解释有误,“多伦多”的原意是“树木在水中生长的地方”,但是多伦多的象征意义并没有改变。
②Claudine C.O'Hearn,Half and Half:Writers on Growing up Biracial and Bicultural,New York:Pantheon,1988,p.xiv.
③Yvonne Spielmann and Jay David Bolter,"Hybridity:Arts,Sciences and Cultural Effects," in Leonardo,Vol.39,No.2,2006,p.106.
④Jerry Bentley,Old World Encounters: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vii.
⑤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1994,p.xxv.
⑥Homi K.Bhabha,"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in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209.
⑦Glen A.Lowry,After the Ends:CanLit and the Unravelling of Nation,"Race" and Space in the Writings of Michael Ondaatje,Daphne Marlatt and Roy Kiyooka,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Simon Fraser University,(May 2001),p.140.
⑧Peter S.Li,The Making of Post-War Canada,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7.
⑨⑩(11)(14)(18)(19)(24)(25)(28)(29)(31)(32)迈克尔·昂达奇:《身着狮皮》,姚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4,105,92,218,134,127,7,18-19,144,126,115,239页。
(12)Jonathan Raban,Soft City,London:Hamish and Hamilton,1974,pp.1-2.
(13)Daphne Spain,Gendered Space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17.
(15)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p.31.
(16)Barbara Turner:"In the Skin of Michael Ondaatje:Giving Voice ot a Social conscience",in Quill & Quire,(May 1987),p,21.
(17)Mita Banerjee,The Chutneyfication of History:Salman Rushdie,Michael Ondaatje,Bharati Mukherjee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Druck:Betz-Druck,2002,p.111.
(20)加拿大政府于1971年正式出台多元文化政策,以期消除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并于1988年通过《多元文化法案》,旨在“保存并促进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传统,同时努力争取全体加拿大人在国家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参见The Multicultural Act,
(21)Stephen Vertovec,"Multiculturalism,Culturalism,and Public Incorporation," 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19,No.1,1996,p.5.
(22)Tariq Modood,"Anti-Essentialism,Multiculturalism,and the 'Recognition' of Religious Groups",in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eds.,Citizenship in Diverse Socie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75.
(23)很多早期加拿大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矛盾的情感,其中最典型的是苏珊娜·穆迪的作品《丛林中的艰苦岁月》。
(26)Robert Fraser,"Postcolonial Cities:Michael Ondaatje's Toronto and Yvonne Vera's Bulawago," in 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Vol.26,No.1 (January 2001),p.46.
(27)Marie-Louise Stening-Riding,How Newness Enters the World:Hybridity in the Intercultural Novels of Bharati Mjkherjee,Michael Ondaatje and Salman Rushdie,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Dalhousie University,(May 2004),p.165.
(30)Gordon Gamlin,"Michael Ondaatje's In the Skin of a Lion and the Oral Narrative," in Canadian Literature,No.135 (Winter 1992),p.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