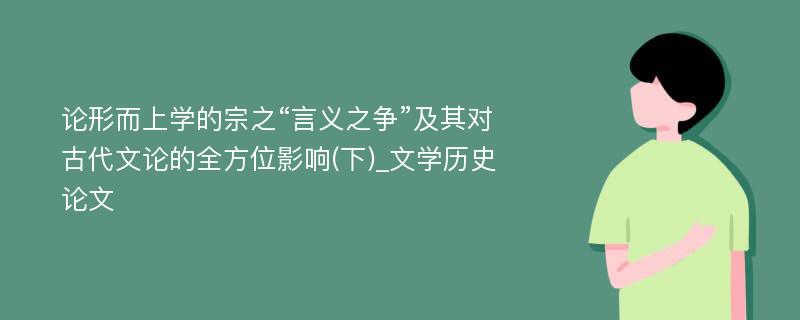
论玄学“言意之辩”的宗致及其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玄学论文,之二论文,其对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立象尽意”论的理论机制
在“言意之辩”中,以王弼为代表的“立象尽意”派,声名最著。王弼关于言、意的认识,分三个层次:“立象尽意”、“寄言出意”、“得意忘言”。其中,“得意忘言”论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观。
王弼是在注《易》时与“言意关系”正式遭遇的。王弼《易》学,夙称“新学”。“新”,仅仅是就其对沉湎象数迷信之汉《易》学的颠覆而言的。若就其对《系辞》中明而未融的玄智的呼应与发现而言,王弼之《易》倒是向“十翼”的忠实回归。(注:《易经》有“经”(六十四卦)有“传”(十翼)。离开《易传》,《易》仅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旧有筮案的汇编。正是“十翼”,发掘出筮占中零星包蕴的玄智,并把它们系统化为一套玄理,《易》才成为“经”。迷信象数的五经博士的《易》学,从本质上说是巫史之《易》,传承的更多是筮占知识。王弼“新学”,以“传”释“经”,坚持高扬《易》中包蕴的玄智,王弼才称得上是思想家。其在《易》学上创新处,集中见之于其所树立的迥异于两汉《易》学的“大衍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80页)在王弼“大衍义”中,本体与万有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统一关系:即“体”发“用”,不存在无“体”之“用”,凡“用”必有“其所由之宗”;即“用”见“体”,不存在离“用”之“体”,“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本末相即,体用一如。王弼关于言、意关系的讨论,就建立在“本末相即”、“体用一如”的方法论基础上。) 王弼对意-象-言关系的讨论,集中见于其《周易略例·明象》章。[10] (P591—621)《周易略例》的撰述目的,是试图通过对《周易》体例、卦爻结构的研究,把象数形式改造成义理传达工具,树立《易》学新范式,在精神上向《易传》回归。要树立新范式,首先要破除两汉《易》学中弥漫的“象数迷信”,重新激活被两汉《易》学消解了的《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鼓之舞之以尽神,变而通之以尽利”的解释能量。要激活《易》的解释能量,就要对“象”(卦象结构)进行重新认识。《周易略例》第四章《明象》承担的就是这个任务。
《周易略例·明象》章首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象”是一种模拟,《释文》:“象,拟象也”。《易》中之象也具有模拟性。《系辞下》云:“易者,象也。象者,像也”。不过,《易》“象”模拟的不是具体事物,而是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一类事物。由于《易》“象”是某一类事物的集合,例如“乾”像是“刚健”一类事物的集合,“坤”像是“柔顺”一类事物的集合,故而,凡是与“刚健”有关的事物(例如,天、马、首、君、父、玉、金等),都可以用“乾象”来表示;凡是与“柔顺”有关的事物(例如,地、牛、腹、臣、母、布、釜等),都可以用“坤象”来表示。这就使《易》“象”具有相当大的包蕴性。王弼把《易》象的这一特征称之为“触类可为其象”。《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立“象”的目的,是为了借“象”这个媒介来表达他们所领悟到的意义。例如,乾卦用“天行健”之象为媒介来表达“君子自强不息”之“意”,坤卦以“地势坤”之象为媒介来表达“君子厚德载物”之“意”,蒙卦以“山下出泉”之象为媒介来表达“君子果行育德”之“意”,等。从意义传达的诗学性上说,《易》“立象尽意”和《诗》“比兴言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篇强调:“易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圣人之所以能如此这般地“拟诸形容”,是因为在圣人特殊的视野中,“象”(“天行健”等)和“意”(“君子自强不息”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关合处。(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皇甫湜拈出的比喻的基本原则:“比喻也,凡喻必以非类”(似是而非)、“凡比必于其伦”(似非而是)。《答李生第二书》、《答李生第三书》,见《皇甫持正文集》卷4,四部丛刊初编。) 因而,相对于“象”来说,“意”是“象”之“体”;相对于“意”来说,“象”是“意”之“用”。王弼《周易·乾·彖》注说:“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乾]也者,用形者也”。《周易·坤彖》注:“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形者也”。[10] (P213,226)王弼把《易》象的这一特征称之为“合义可为其征”。“义”即“象其物宜”之“宜”:“意”和“象”之间“似是而非”的关合处。因而,王弼强调,“象”只是“出意者”,而不是“意”。王弼《周易·乾·文言》注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时义而取象焉”。[10] (P215)所谓“象之所生,生于义也”之“生”,只表示逻辑上的先后,并不表示因果上的生产或者产生。《系辞上》有云:“见乃谓之象”。凡是“象”,包括卦象(具象的抽象符号结构),皆有形可睹,有实可名,故而是可以言说的。因而,相对于“言”来说,“象”是“言”之“体”。没有“象”,就不需“系辞”;相对于“象”说,“言”是“象”之“用”。不用“言”,“象”就无以自明。因为“言生于象,象生于意”,“言”和“象”、“象”和“意”之间,是“体用”关系,故而只要坚持“即用见体”,就可以“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言”虽然不可能直接地去“尽意”,却可以通过“尽象”去曲折地“尽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衍义”中“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的“体用相即”的本体论立场,在“立象尽意”论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立言明象,立象尽意”,仅仅树立了一个原理。正如《系辞下》强调的,《易》虽有“与天地准,弥纶天下之道”的巨大思想威力,能“极天下之赜”,可“鼓天下之动”,但“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尽意”,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个“寻言观象、寻象观意”,人对“言”、对“象”、对“意”是否能做到“神而明之”的问题。这样,王弼就把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尽意”问题,转换成对“言”、“象”、“意”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方法论问题。
《周易略例·明象》章接着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筌蹄鱼兔”之喻,见于《庄子·外物》篇。[4] (P725)王弼借用“筌蹄鱼兔”之喻,旨在突出“言”在“明象”中、“象”在“尽意”中的工具(中介)性质。工具有它适用的对象,如《考工记》所言:“铄金为刃,凝土为器,作车行陆,作舟行水”。[9] (P908)不同的对象要求不同的工具。“明象”需要用“言”、“尽意”需要用“象”,正如“得鱼”需要用“筌”、“得兔”需要用“蹄”一样。无论多么精致的“言”,都无法实现“尽意”目标,正如无论多么灵巧的“蹄”,都无法“得鱼”一样。因而,在“尽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事是恰如其分地认识“言”、“象”的功能范围,只让它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发挥,而不对它们心存非分的奢望。宁可“守株待兔”,也不“缘木求鱼”!工具运用强调效应。工具的价值和意义不在工具自身,而在对工具的有效使用。何谓“有效”?恰到好处就是有效。如何“恰到好处”?掌握分寸才能恰到好处。因而,在“尽意”的时候,其次要考虑的事是恰到好处地掌握“言”、“象”运用之度。“象,出意者也”,舍弃“象”,当然就无法“出意”。但是,假如在用“象”去“尽意”的时候,一味地对“象”苦思冥索,“意”反而被“象”所遮蔽,仍然在一片黑暗中伏而不出。就像携一张好弓出门射猎,却把箭握在手中,只是赞叹“好箭!好箭!”就是不射出去,再好的弓箭也射不中猎物一样。“言,明象者也”。舍弃“言”,当然无法“明象”。但假如在用“言”去“明象”的时候,一味地对“言”精雕细刻,“象”反而被“言”所遮蔽,仍然在一团混沌中隐而不明。就像“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一样。王弼强调“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在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在忘象”,真意就在这里。“忘”不是“悬置”,更不是“舍弃”,而是在“观言中”对“言”、观象“中”对“象”进行解构。解构就是要拆开“言”、“象”僵硬的外壳,让“明象”主体冲出“言”的“牢笼”去“寻象”,让“尽意”主体冲出“象”的“牢笼”去“寻意”。“忘言”、“忘象”的理论机制是什么?王弼没有明说。但“忘象”中有对王弼“象”的深刻洞见,“忘言”中有王弼对“言”的深刻洞见。王弼“忘言”、“忘象”的理论机制及王弼洞见的深刻性,借助西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的“话语转义”理论,可以得到说明和印证。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批评家海登·怀特。怀特在其文化批评文集《话语的转义·前言》的一条注释里说:“言语/词汇或表达方式与意义之间的分歧,当然是现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一个根本信条。该信条产生于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任意统一的观念”。[11] (P1)索绪尔以严格区分和深入分析语言的“能指”和“所指”著称,其论域接近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引发了西方思想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对西方思想传统产生的震撼、强度和深度,犹如魏晋玄学对两汉思想传统产生的震撼。海登·怀特通过这条注释暗示,“言意关系”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关注的中心,他的“话语转义”理论,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基础上向纵深挺进,或者说是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提供一种原理性分析。
按海登·怀特的定义,“话语是一种文类”,其最重要的任务是赢得这样一种“说话的权力”:相信用一种方式明确表达的事物,同时还被其他方式隐蔽地表达着。这一言说“权力”的根源,就在“话语的转义”性上。怀特认为,“转义”是一切话语的灵魂,是所有话语建构客体的过程。(“一切”、“所有”,未必真贴合“后现代”的立场。)没有转义的机制,话语就不能发挥作用,就不能达到目的。所谓“话语转义”,就是把要去认识的“未经分类的陌生领域”,移入“已被编码”的经验领域,使之获得理解和认识。就像诗学中经常有意偏离语言的常规用法,在“言-意”之间创造一个联想空间,生成比喻和思想一样。怀特从西方传统诗学和现代语言学中识别出四种转义方式:隐喻(再现的,强调事物的同一性)、换喻(还原的,强调事物的外在性)、提喻(综合的,强调事物的内在性)和反讽(否定的,在肯定的层面上证实被否定的东西,或相反)。并认为前三种是语言自身的运作范式,第四种“反讽”是语言为思维方式提供的一种范式。“转义”特别是“反讽”式的话语转义,就是通过解构“比喻”,来激发对事物性质认识和描写不充分性的思考。怀特强调,话语转义是“反逻辑”的:其目的是要对一个“特定经验领域的概念化”加以解构,以来新知。话语转义是“前逻辑”的:其目的是要标识出一个经验领域,以供此后“由逻辑引导的思想”进行分析。怀特把话语转义形象地描绘为“在经验的既定编码与一连串待理解的现象之间的‘往返’运动”。并指出,话语转义“似乎有一个原型结构”起作用,他把起作用的“原型结构”归之于“相当于心理防御机制的语言防御机制”:话语“既批评他人又自我批评”的本性。[12] (P2—7)所谓“话语自我批评的本性”,大概类似于庄子所谓的“以言去言”。“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突出强调了历史书写的阐释性,认为历史书写是“通过情节编排”,“识别所讲故事的种类”;通过不同形式的(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语境论的)“话语论证”,把从历史中识别出来的全部事件与线索编织成一条意义链,以表达书写人对历史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采取的立场:无政府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关怀。[11] (P383,393)
因而它既关心构成话语主题的客体,又关心阐释活动本身。“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最鲜明的理论特色,是将历史“文本”化,把历史叙事的“修辞性”放在中心位置,从而颠覆了西方现代历史学一贯标榜的“客观性”。因而海登·怀特又把“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追求的目标定位为“元历史”,把“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性质确定为“历史的诗学”。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代表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向历史研究的移植。其对历史编纂学的作用还有待时间来验证,其“转义理论”却对读者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可以成为我们审视王弼“忘言”、“忘象”洞见深刻性时的参照系。
按海登·怀特的说法:“转义是所有话语构建客体的过程”。准此,当“圣人见天下之赜,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的时候,已经对“客体”进行了两次“话语转义”:把从客体中发现的“天下之赜”(意),比拟形容为现实中的“象”,这是第一次话语转义;给“象”一个固定的符号化的外形(言),这是第二次话语转义。按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话语转义”是一个把陌生事物表现为熟悉事物的过程:把陌生事物从“未分类”因而不可言说的领域(“天下之赜”),移入另一个“已被编码”即已被反复言说的经验领域(“立象”、“系辞”)。然后“拟诸形容”,通过“隐喻”,发现两个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间隐含的“似非而是”的共性;通过“换喻”,借助“二者之间互相还原的关系型态”,比较两个不同的客体,解释二者现象上“似是而非”的差异;通过“提喻”,把两个现象“似是而非”的外在关系理解作具有“似非而是”共性的内在关系。再通过“反讽”(“观言”、“观象”),激发如是操作对事物性质或描写本身“不充分性”的思考,对“言”、“象”进行解构,把“言明象”、“象出意”的能量释放出来,从而使不可言说的陌生事物得到言说和理解。《系辞》中“拟诸形容”四个字,惟妙惟肖地道出了“圣人立象尽意,系辞尽言”时的修辞性质或诗学特征。由于“言”、“象”皆是话语转义的成果,故而在“立象尽意”、“立言尽象”的时候,毫无疑问地要对“意”、“象”、“言”皆有所取,皆有所舍。例如,当立“天”之象去尽“乾健”之意的时候,取(肯定)的是“天”那“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可见的“行健”之形。为什么立此象不立彼象?因为“天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可见的“行健”之形中,有与“乾健”有着某种“亲和”关系的“行健”之“神”;舍(否定)的是“乾健”玄理的不可名言性。当用符号化的“言”去“明”“天行健”之象的时候,取(肯定)的是“天行健”这三个字“控名责实”的概括力量,舍(否定)的是使“天”有“行健”之“象”的“四时行焉,百物兴焉”之“神”。如是,在“言”和“象”之中,就同时辩证地存在着如怀特“转义理论”中说的“亲和”(肯定而“不即”)和“紧张”(否定而“不离”)两种关系。“天行健”这三个字(言)字面上直接肯定的是一个僵硬而抽象的观念,语言不得不如此,因为任何语言都是在抽象,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天行健”这三个字想间接印证的却是它字面上否定的使“天”有“行健”之“象”的“妙而不可知”的“四时行焉,百物兴焉”之“神”。立“天”之象直接肯定的是“天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可见的“行健”之形,想间接印证的却是它否定的不可言说的“乾健”之理。换句话说,“言”和“象”皆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综合体。当然,正如黑格尔《逻辑学》里说的:“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但是,由于“圣人立象尽意,系辞尽言”时“拟诸形容”的自觉修辞意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对立,在“言”和“象”中表现得特别尖锐和紧张。正是这种紧张,才把“观言”、“观象”问题推向前沿。由于“言”、“象”皆是话语转义的成果,所以对“言”、“象”的理解接受,必须坚持“转义”的诗学立场:始终把它们作为“拟诸形容”来对待。“忘言”、“忘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就根源于此。“忘”是为了“得”:解构“言”、“象”直接肯定的东西(能指),捕捉“言”、“象”想间接印证的东西(所指)。为什么能如是“解构”?因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间的统一关系是任意的。这就意味着,用一套语言表述的东西,同时还可以用另外一套、几套语言隐蔽地表述道。王弼所谓“义苟在健,何必马乎?义苟在顺,何必牛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黑格尔把这种前逻辑的语言中的诗性因素在人文科学话语中顽固的无法删除性,戏称为“概念的多元决定暴政”。“忘”-“得”之间的辩证转换,海登·怀特按西方修辞学的术语称之为“反讽”:“在肯定的层面上印证否定的东西,或相反”。中国智慧称之为“正言若反”、“言未始有常”。“正言若反”或“反讽”,正是“圣人立象尽意,系辞尽言”的刻苦用心,同时也经常是人文学科用语言去陈述一个陌生世界时的刻苦用心。不“忘”就不能“得”。佛典《大智度论》里的有一则比喻,最能形象申明此理:“惑者不识月,以问识者。识者以指指月,惑者视指不视月”。“视指不视月”的“惑者”由于不能“忘”指,永远是“不识月”的惑者。王弼所谓“象生于义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者,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破的正是类乎“视指不视月”的《易》学意义认知中的象数迷信之惑。
依持对“意”、“象”、“言”的洞见,王弼引导着对语言功能的理解和意义传达的认识,从激进主义的根本怀疑(例如荀粲)和保守主义的盲目乐观(例如欧阳建),攀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尽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完全可以通过“忘”-“得”之间自觉的辩证转换,激活言-象、象-意之间的张力;凭借这种张力,在言、象、意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像穿梭一样“往返”运动与过渡,无限接近那个不可名说之“意”。经王弼“意以象尽—忘象得意”、“象以言着—忘言得象”的洗礼,中国传统的语言观经历了一次“技进于道”的“哥白尼革命”。
五、“言意之辩”对文论的全方位影响
玄学“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不仅指玄学“言意之辩”的“言不尽意”、“言尽意”、“立象尽意”派全方位地影响了古代文论,而且指在玄学“言意之辩”影响下,古代文论对语言功能的认识、对语言运用境界的企盼获得全方位的更新和全方位的提升。粗略地说,“言不尽意”论唤起了文学对语言局限性的警觉,使如何准确掌握语言运用之“度”,成为魏晋南北朝文论的新课题。“言尽意”论坚定了文学“立言不朽”的信心,使文学语言形式的锻造问题,成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关注的重心。“立象尽意,得意忘言”论提升了文学运用语言的境界,使艺术论上的“形神”问题,在古代文论中逐渐凸显出来。
玄学“言意之辩”更新了中国文学对语言抒情达志功能的认识。经“言不尽意”论的冷峻提醒,文学猛然意识到惯常赖以安身立命的“言”,实际上是不应该寄于更多希望的粗糙工具。“言”既是人离不了又让人信不过,是文学必须接受的事实。于是,如何让粗糙的语言尽可能地产生出细致的效果,便是经过玄学洗礼后魏晋南北朝文论面临的新课题。如何恰如其分地界定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恰到好处地发挥语言的功能,成了文学焦虑的中心。一时间,“巧”(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巧言”、“巧构”、“巧喻”、“巧思”成了文论中的关键词。
从陆机起,魏晋南北朝的文论大家,就有一种从宏观上把握语言在文学中确切地位的理论兴趣。陆机从历代作家积累下来的艺术经验和自己文学实践的切身体会中,提炼出文学理论上的一个中心主题:“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并以“物—意—文”为最基本的贯穿线索,组织起他那篇结构恢宏的文学专论《文赋》。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里,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建构了文学发生学和文学价值论的基础模型:“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依此基础模型,在“上学下达”:“论文叙笔”,追溯“道沿圣而垂文”的历史轨迹,和“下学上达”:“剖情析采”,彰显“圣因文而明道”的价值意义的辩证运动中,有条不紊地探讨了文学理论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陆机那个“中心主题”和刘勰那个“基础模型”,在方法论上受玄学“言意之辩”影响的痕迹相当明显。例如,如同玄学“言意之辩”把“言”、“象”恰如其分地界定为“圣人之意”的中介一样,陆机和刘勰也恰如其分地把“文”界定为文学要“逮”之“意”、文学欲“明”之“道”的中介。再如,如同玄学“言意之辩”把“意”、“象”、“言”之间的关系,“恰如其分”地界定为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样,陆机和刘勰也把文要“逮”之“意”与“逮意”之“文”间的关系、文要明之“道”与“明道”之“文”间的关系,恰如其分地界定为不即、不离的关系。又如,如同玄学“言意之辩”总是辩证地对待“意—象—言”一样,陆机和刘勰也总是辩证地对待“物—意—文”和“道—圣—文”。在玄学“言意之辩”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文论在对文学语言的根本认识上,取得了两项积极成果,引发了文学语言上的“革命”。
陆机发现,尽管可以把文学实践的全部问题,从理论上划分成“意称物”和“文逮意”两大层次。但无论哪一个层次里的成果,最终都要由“文”来体现。因而,文学实践的最高目标,是锻造出既能“称物”又能“逮意”的语言形式。最高目标的实现,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用语言去“称物”、“逮意”之人,既要有高明的艺术素质:“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又要有敏感的艺术心灵:“遵四时而叹逝,赡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既要有聚精会神的艺术心态:“罄澄心而凝虑,眇众虑而为言”,“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又要有高度活跃的艺术想像力:“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既要有驾驭全局的整体眼光:“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以效绩”;又要有整合局部的系统观念:“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既要有遵守艺术规范的自觉:“虽区分之在此,亦禁邪而制放”;又要有创意造言的艺术果敢:“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既要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又要有公共的美学趣尚:“和悲雅艳”、“穷形尽相”。陆机这一系列话语,实际上是把文学中的“称物逮意”问题,转换成作家如何通过文学语言形式的锻造,去“鼓而舞之以尽神”的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和玄学“言意之辩”最终把“言意”问题,归结为如何去“神而明之”地“立象-观象”、“系辞-观言”问题遥相呼应之迹,清晰可辨。《晋书·陆机传》称,陆机与其弟陆云赴洛途中,于逆旅曾“梦与王弼谈《易》”。对《易》的玩索,已渗入陆机的“潜意识”。而《易》是玄学“三玄”之一。陆机与玄学的思想呼应,可谓渊源有自。陆机这一系列话语,在追求体系严整的理论家看来,似乎有点“巧而碎乱”。但陆机以其“碎乱”之“巧”,把文学创作全过程的各个领域匆匆浏览一遍,不仅有效地巩固了曹魏以来文学自觉的成果,而且成功地为后世自觉的文论勾画出应该致力探索的理论坐标。
如果说陆机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得益于对“文、意”不即不离关系中“不离”一面的省察的话,那么,刘勰所取得的成果,则主要得益于对“文、道”不即不离关系中“不即”一面的自觉。刘勰在《原道》、《宗经》诸篇,从自然界“动、植皆文”,“无识之物,郁然有彩”的经验事实中,引申出精神界“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有心之器,岂可无文”的结论。“文”在“政化”、“修身”、“事迹”即人活动的各个层面都是须臾不可离的。“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就必须“雕琢情性,组织辞令”。因而,刘勰断言,一个有教养的人(“君子”)是从来不以质朴自限的。相反,经典表明,“情信而辞巧,志足而言文”,乃是运用语言去“鼓天下之动”的有效途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言”是明“心”的,“文”是饰“言”的。“言”和“文”在运用实践中,就存在两种而决非只有一种可能性,如《情采》篇所言:“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就如同“观象”可以“寻意”、执“象”必然迷理一样。因而,刘勰最关心的是语言运用之度。《文心雕龙》的“文学语言”论,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运用“经济学”。他关注的重心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益。刘勰从大量的语言运用实践中,辩识出四条最“经济”的语言运用途径。无论哪一条,都受过玄学思想智慧的启迪。
(1)实事求是地确定文学语言的活动范围。《夸饰》篇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难以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既然形上之道非文学语言所能尽,那么,在语言运用实践中,就不要让文学语言作这种劳而无功的无谓努力。既然文学语言只能与感性世界打交道,那就让文学语言在它力所能极的范围内尽情驰骋。文学语言在达到自己活动范围的极限时,应该谦恭地停下来,就像《神思》篇说的那样:“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实事求是确定文学语言的活动范围,是为了正确认识文学语言自身的特性,杜绝文学语言运用上的无谓浪费。让运用文学语言的心思,经济地运用到它该用的地方。“知止”是庄学中的智慧。在庄学中,“知止”是保持精神澄明的基本前提(《人间世》“心斋”),是保证物我和谐发展的首要条件(《逍遥游》“至人无己”),是消解“成心”、获得全面、辩证认识的有效途径(《齐物论》“言非吹也”、“休于天钧”),是对人精神意志的深刻反省(《齐物论》“非彼无我”),是对人精神活动范围的层次区分(《齐物论》“道未始有封”),是对存在困境这一焦虑中心以外问题的有意悬置(《则阳》“大公调曰”)。在庄学中,在这个地方“知止”,是为了在那个地方精进。“止/进”之间存在一个辩证转换。把握住其间的辩证转换,得其精髓;把握不住其间的辩证转换,矇于皮毛。刘勰“笔固知止”论,得其精髓。黄庭坚“夺胎换骨”说[12] (P5),就为“皮毛”所矇。黄庭坚“夺胎换骨”法“止”非所当止,“进”非所当进,先失庄学精髓。当然,山谷诗学自有其一片精光,非“夺胎换骨”所能掩。但其误已远播境外,致使王若虚《论诗诗》有云:“戏论谁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13] (卷45)影响所及,致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对黄庭坚诗学理论的处理,经常是“买椟还珠”。这是题外话。
(2)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学语言的活动水平。树立“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坚定信念,激发在语言上狠下工夫的信心(《原道》);学习经典运用语言的高超技巧,体会经典语言运用的高明境界,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语言运用观(《征圣》、《宗经》);领会神话中“元语言”的永恒魅力,认识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正纬》);兼收并蓄四言诗“比兴言志,雅润为本”、五言诗“怊怅切情,清丽居宗”、骚“自铸伟辞,惊采绝艳”、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诸子“越世高谈,气伟采奇,辩雕万物,事核言练”的艺术经验,丰富语言运用的手段(《明诗》、《辩骚》、《诠赋》、《诸子》);熟悉各种文体对语言的独特要求,实现“即体成势”的理想(《文心雕龙》上编《乐府》以下各篇);通过深化艺术构思,解决“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矛盾(《神思》);选择和自己才性最贴近的风格类型,为自己创造性运用语言创造条件(《体性》、《定势》);不倦地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度,提高语言的情感强度,给语言灌注饱满的生气(《风骨》、《夸饰》);在古今、雅俗、质文、奇正、刚柔之间往返穿梭,强化文学语言的张力,使文学语言成为“辞已尽而势有余”的开放性结构(《通变》、《定势》);树立整体观念,“乘一总万,举要制繁”,坚持在系统结构的“上下文”关系中处理字、句、章、奇偶、宫商、旧新,实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的理想(《镕裁》、《声律》、《章句》、《丽辞》、《事类》、《练字》、《附会》)情、文并举,“隐”、“秀”兼综,使“情在辞外,状溢目前”(《隐秀》、《比兴》)。可以说,《文心雕龙》的全部篇章,皆是为最大限度提高文学语言活动水平做出的努力。这里既有“言不尽意”论的反面提醒,又有“言尽意”论的正面推动。
(3)坚持“含章司契”的立场,在“神与物游”中锤炼思维,在锤炼思维中锤炼语言。《文心雕龙·神思》篇里有个基本观点:“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语言是人与陌生世界打交道的手段。语言的熟练使用,当然需要一定的知识作支撑,一定的训练为基础。但用语言去反映世界,却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神与物游”的复杂过程。其间有“心”有“术”,有“道”有“技”。依《原道》篇所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基本原理,言、意之间的“密”或“疏”,从本质上说,是“心”与“物”的“密”或“疏”的问题。对世界观察细密,体贴入微,虚静玄览,思维透脱,心、物“合”则言、意“密”。观察粗,体验浅,思维乱,与物隔,心、物“离”必然导致言、意“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刘勰突出强调“含章”(感性世界及对感性世界的体验)在文学语言运用中起“司契”(主导、决定)作用的立场:语言表达上的混乱是思维混乱的表征,锤炼思维是锤炼语言的可靠途径。在“含章司契”说中,不难看到刘勰与欧阳建《言尽意论》援为立论基础的荀子“名以事验”思想的联系。“含章司契”的语言立场,决定了刘勰独特的“不必劳情,无务苦虑”的文学语言运用境界观。
(4)以“反本”为文学语言运用的最高境界。“贵乎反本”不仅是《文心雕龙》一以贯之的文论策略,同时也是刘勰的文学语言境界观。也许是受“文之枢纽”部分“原道”、“征圣”、“宗经”等标题的暗示,中国文学批评史常把刘勰“贵乎反本”的文论立场,看作是荀子思想立场的一脉相承。其实,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皮相判断。的确,荀子最先标榜“原道”、“宗经”、“师圣”。但那只是为意识形态纯洁化而斗争,属于刘勰说的“励德树声”的范围。而刘勰是从“建言修辞”上宗经师圣的,按刘勰自己的说法,从这个角度宗经师圣,是前人从来没有涉及过的。文学语言运用上的“反本”,有不同的层次。其一,从“为文造情”向“为情造文”回归,从创作方向上正本清源。文学是一种高级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体性》篇云:“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物色》篇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学发生学要求“为情造文”。《神思》篇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艺术构思要求“为情造文”。《镕裁》篇云:“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艺术表现要求“为情造文”。《知音》篇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学鉴赏要求“为情造文”。语言是精神的家园。无“家”可归的精神是“游魂”,所以文学活动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上,都不可能离开语言。但正如《章句》篇说的“设情有宅,置言有位”。“联辞结采”仅仅是为精神构建一座供精神棲居的“宅院”,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文造情”却把“手段”颠倒为目的,文学成了毫无精神目的的语言工艺制作。结果只有两种,或者是“强奴欺主”,把本是主人棲居的家园霸占为己有,在里面肆意妄为;或者是建造一个无人居住的鬼宅空屋,给鬼狐活动提供空间。“为情造文”使文学的精神旨趣丧失殆尽。“反本”就是要把被“为文造情”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重新赋予文学语言运用以饱满的精神旨趣。其二,从“采滥辞诡”向“要约写真”回归,从艺术操作上疏通引导。《情采》篇里对“文采”和“情性”之间的本末体用关系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为文造情”者必然“采滥辞诡”,因为只有用“淫丽烦滥”的词藻堆积,才能掩饰他们精神旨趣上的庸俗和贫乏。就像袁枚《续诗品·葆真》品里挖苦的:“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征典求书。古人文章,俱非得已。伪笑佯哀,吾其优矣。画美无宠,绘兰无香,揆厥所由,君形者亡”。“反本”就是要树立“要约写真”的艺术信念,消解艺术操作上的“淫丽烦滥”。“要约写真”中的“要”,指的是对文学语言运用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文采”和“情性”之间不容颠倒的本末体用关系。“约”即对文学语言恰如其分的运用。得“要”才能行“约”,唯“约”才能“写真”尽意。由于“约”是恰如其分,故而“约”只是“淫”的对立物,“约”决不排斥“丽”,也无意提倡质朴。以真、善、美为对象的文学,需要赏心悦目的形式:“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因而,“要约写真”不仅不排斥文采,相反,它还要通过“要约”操作去“振采”,即把文采“饰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也只有坚持“要约”,才能够把文采“饰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其理就如袁枚《续诗品·振采》品里喻示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胡洁?匪熏何香?若非华羽,曷别凤凰?”刘勰在对语言运用之度的把握上,态度是十分严谨的。其三,从“兢今疏古”向“还宗经诰”回归,从文学语言本色上正末归本。《文心雕龙·通变》篇云:“文运律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是使文学活力永存的源泉。按刘勰的看法,“通变”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恰到好处地处理“质文”、“雅俗”关系,使文学语言在运用中永远保持饱满的“气”和“力”。“变”就是要“隐括乎雅俗之间”,“望今制奇”。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辩骚》《明诗》《诠赋》等,就是“望今制奇”的体现。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术语表述,“变”就是使“亚文学样式文学化”。“通”是“斟酌乎质文之间”,“参古定法”,让文学“存在于成规之中”,永远保持本色。《原道》《宗经》《师圣》即是对“通”的原理性论证。“通”就是通过“还宗经诰”以“反本”。“还宗经诰”是针对文学发展中暴露出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兢今疏古,风末气衰”问题制定的策略。刘勰在《练字》篇引述过一则神话:“仓颉造字,鬼哭粟飞”。这则神话的文化人类学意义是,语言创造使人从自然中脱颖而出,成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元语言”具有极鬼神之幽、夺天地之化的永恒魅力。刘勰从文学发展轨迹中却发现,“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丽,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14] (P520)随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语言在运用实践中越来越趋于精细化:由质而辨、由辨而雅、由雅而丽、由丽而绮、由绮而新。伴随着语言精细化而来的,却是“元语言”中极鬼神之幽、夺天地之化本色的不断流失:由淳而辨、由辨而侈、由侈而浅、由浅而讹。“元语言”中的会通天、地、神、人的“诗性”,不断被理性污染,一步步丧失其丰富的意蕴、绮丽的联想、广泛的沟通、诚挚的情感,几乎要沦为冷冰冰的工具。文学语言必须“反本”。“反本”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到“去古未远”的“经诰”中,领会“元语言”极鬼神之幽、夺天地之化的永恒魅力,还文学语言以“诗性”本色。《正纬》之所以列在“文之枢纽”,用意就在于此。假如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术语表述,“还宗经诰”、“反本”就是“再野蛮化”:通过更新语言更新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反本”求“通”,一直是中国古代文论提高文学语言活动水平的沿用不替的策略,唐代“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具体做法,宋代严羽“取法乎上”,通过“推原汉魏”来定近体诗之宗旨的理论视野,明代如“礼失求诸野”一样到民歌中求“真诗”的“自赎”行动,莫不贯穿这一精神。在西方现代诗学中,例如英国批评史上的华尔华兹、象征主义者叶芝、“新浪漫派”中的批评家、意象派诗人庞德以及号称“20世纪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诗人”艾略特的批评实践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反本以求通”的意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建立,就是从对“诗性的语言”在人文学科的无法删除性的体察开始的。其四,从“钻砺过分”向“率志委和”回归,从艺术心态上根本调整。刘勰从前人的语言运用实践中,识别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自然的”立场遵循“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让“言”随着“意”之曲折、情之起伏自然流淌。由于“自然的”立场坚持“以意为主”,故而精神(“意”、“志”、“情”)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率志”)。由于精神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故而能够做到“入兴贵闲”:无诱于利害,无慕于毁誉,用志不分,伸展自如。由于“自然的”立场坚持“辞以情发”、“以文传意”,故而“言”除“传意”、“申情”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完全地把自己交给了自由的精神(“委和”)。由于“言”除“申情”、“传意”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要求,故而能够达到“析辞尚简”:不雅不俗、不浓不淡、唯意所适、恰到好处。“非自然的”立场恰好相反。“心缠机务,鬻声钓世。言与志反,苟驰夸饰”。由于“心缠机务”,故而于现实利害,锱铢必争、于世俗毁誉,斤斤计较,不“虚”不“静”。由于“不虚不静”,精神完全被“机务”牵引,不能自主,故而左右失据,劳心日拙。由于“言与志反”,故而语言成了遮掩其庸俗精神旨趣的虚假外衣。“言”非“志”之言,“志”非言之“志”。由于“言”除了制造虚假之外再无更健康的精神旨趣,故而如脱缰之马,只能“苟驰夸饰”,无目的、无节制地修饰自身。钻砺过分,劳而无功。劳作开始的地方,经常是艺术停止的地方。如果希望文学语言把自己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就必须“率志委和”:修辞立诚,重树“真宰”。虚静其心,遵顺“自然”。在这里,“自然”既是运用文学语言的基本立场,又是文学语言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自然”这一概念源出《老子》。但在《文心雕龙》语境中,“自然”并非如在《老子》里那样,仅是万有“莫之为”的存在状态。《文心雕龙》里的“自然”,是一种精神旨趣,精神活动的最佳方式,精神向往的最高境界。是人“妙造”出来的“自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自然”指这样一种境界:在“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的基础上,以“从容率性,优柔适会”的方式去“为情造文,要约写真”。文学语言上“自然”境界,就像黑格尔说的,让旨趣在“心灵宁静的氛围中伸展出来,在精神的清彻之流中锻造成形”。或像歌德说的,最好的文学形式是让人完全被形式所传达的精神旨趣所征服,一点也意识不到形式存在的形式。正如《文心雕龙·情采》篇引述的贲卦“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之理显示的,文学语言的“自然”境界,是在浮艳中打过滚、超越浮艳之后达到的自由境界。
刘勰以实事求是认识文学语言活动范围为前提、以坚持“含章司契”立场为基础、以全面提高文学语言的活动水平为动力、以“反本”为文学语言运用的最高境界的文学语言论,涉及层面虽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准确掌握文学语言运用之度,引导文学语言“进技于道”,使文学语言真正成为精神的家园。
在玄学“言意之辩”思想智慧的启迪下,陆机、刘勰等文论大家,在理论上成功地预见了文学语言“进技于道”的境界。但魏晋南北朝文学语言运用实践却尚未达到“进技于道”的水平。中国文学语言“进技于道”境界的真正实现,是一代盛唐之音的劳绩。一代盛唐之音之所以能成此“正果”,应该归因于“言意之辩”中“得意忘言”智慧的进一步点拨,归因于随着主流文学样式从“古体”向“近体”转换而导致文学语言运用实践的进一步积累,归因于文学对其他艺术门类(例如山水画)艺术介质运用实践经验(例如笔墨运用实践经验)的有意识借鉴,等。在文学语言“进技于道”问题上,魏晋南北朝人为什么“力行而未致”?“得意忘言”论如何提升了唐人的语言观?“近体”律绝的文学样式,为什么会加速推动文学语言运用实践的进一步积累?绘画艺术的笔墨运用实践经验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融入文学的?“丹青精神”对文学境界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饶有兴趣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列范围。“鸿风懿采,请寄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