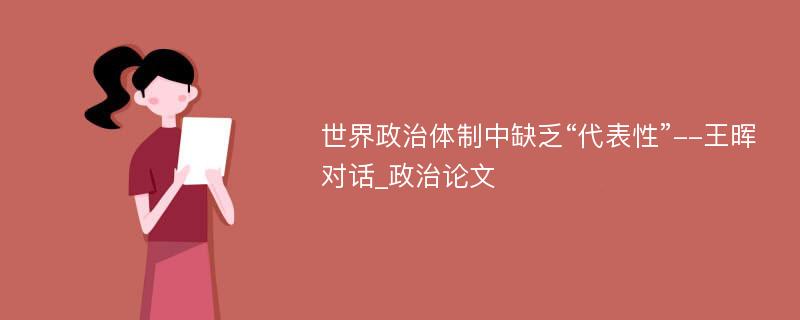
世界政治制度中“代表性”的缺失——对话汪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代表性论文,政治制度论文,世界论文,汪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总部威里·勃兰特大厦会议厅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哲学与政治”的圆桌会议,由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进行对话。汪晖教授发表了题为《代表性的断裂:再问“什么是平等”》的演讲,加布里尔主席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与正义》的演讲作为回应,政治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前联邦德国议会议长沃尔夫岗·蒂尔舍(Wolfgang Thierse)、德国哲学协会主席朱里安·尼达-胡姆林(Julian Nida-Rümelin)参加了圆桌讨论。在演讲之后,汪晖教授应托马斯·迈尔教授的邀请接受了《新社会》杂志的访谈,讨论演讲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本文为该访谈的中文翻译稿,汪晖教授本人对译稿进行了核对和修改。
○您曾对在西方民主制度中和在中国国内缺失民主以及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发生“代表性”断裂这种现象作出评论。就缺失民主的性质而言,您认为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在政治家们的讨论中,人们多半强调两种社会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别,当然这是不无道理的。可是,近1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了某种转变,西方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同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相似之处,这当中包括:中国版的社会分裂、社会国家的破毁,以及尚不具备社会政治维度的新工人阶级的产生,还有欧洲版的贫富分化和民主危机。
事实上,这种转变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某种专家政治取向。专家政治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如今已十分突出,如在金融部门中就是如此,而且这种现象在两种制度中是极为相似的。这就是说,“民主”这一课题无论在西方世界或特别在中国,都一如既往既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法治国家这一属性而言,同样可以这样说。现在所有的社会都面临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新的挑战。19世纪和20世纪所产生的所有政治制度,现在都发现自身正面对各种新的问题。
○在您的分析中,您强调两种发展趋势,一个是“代表性”的退化,另一个是社会阶级和政治阶级日益扩大的分裂。社会利益在政治制度中是否已不再被充分体现?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和在中国同样都具有压倒优势吗?
●我指出两者具有相似的趋势,并不是否定两者的差异。中国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革命阶段,从1911年开始,直到7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有70年的时间是处于革命之中。自然,这也意味着,政治制度必须把极不相同的各种成分整合在社会形式之中。中国的状况同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存在重要的区别。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主要发端于农村,其政治构成和社会发动力植根于农村结构之中。在革命时期,政治机制深受阶级斗争的影响,而党就立足于这一意识形态之上,但这个阶级政治是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并不像欧洲那样明确的社会里。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政治代表性并不直接等同于阶级的直接代表性。我曾将这个阶级概念描述为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在50年代,政权被认为是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代表95%以上的人民”,而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依据的。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对象是以阶级敌人的名义出现的政治敌人。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阶级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政治斗争解释为围绕阶级代表性而展开的政治斗争。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同东欧各国的情况也很不同,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显示出某种相似之处。1989—1992年,苏东体系瓦解了,但中国共产党依然强大有力,并且使政治形式得以呈现出某种连续性。通过对外开放和逐步采取市场取向,以及迈入全球化进程等等,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形式的这种连续性当然只是表面现象。如今我们看到,这里发生了某种根本的转变。不仅就民主化而言是如此,而且就政治价值发生转化而言也是如此。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经江泽民,直到胡锦涛时期,政治口号是:党要代表社会的最重要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结果就是共产党的代表性的本质发生了某种转变。邓小平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江泽民的口号是“三个代表”,如今的口号是“和谐社会”。共产党尝试摆脱旧的意识形态。但是,现行体制下的日常实际生活表明,普通的民众、处于下层的社会阶层,从而工人阶级,在公共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声音。
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们很难找到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我们也难以在相关的政策或法规中找到代表他们的政治取向。因而,政治进程越来越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且颇具资本取向。
○虽然情况如此,但是您不认为西方民主形式仍不失为一种选择而值得中国效法吗?您对西方民主的现状有怎样的评价?
●借鉴不同的制度,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一直是中国改革的内容之一。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与西方,甚至俄罗斯与印度,虽然政治制度很不相同,但为什么如此不同的政治制度却面临着十分相像的危机?从政治的层面看,危机的核心在于政党体制。在欧洲,从政党政治的两个方向来看,政党都越来越趋向中间。典型的左翼政党变成中左政党,传统的右翼保守政党变成中右政党。各政党在选举运动中虽然竭力向选民展示各自的不同之处,但是选民却越来越发现,各政党的社会经济纲领几乎不再存在什么差异。这种情况无需实际民主进程的助力便大大有利于专家政治,意大利最近的新总统上任并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也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我们从中便可看到这种情况。
按照经典的政治学理论,一种多党制的议会制度是建立在某种经过谈判调解冲突的机制之上的。各种利益的不同代表通过议会框架进行谈判,导致某种共同意志。这就是民主决策的根本机制。但是,如果政党发生了代表性危机,这一框架的运转也就发生了困难。在美国,茶党运动可以视为共和党的政治代表性危机的产物,占领华尔街运动则与左翼政党的危机有关。德国实行的是一种社会民主制,它比其他制度更为有效和更为牢靠,但代表性的断裂问题未必不存在。在西方,形成公共意志的这一基本结构——也就是民主形式——未必会发生改变,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传统的政党政治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中国的政党体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欧洲的民主制度不同,但无论是政党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性危机方面的症候都很明显。越是想把自己变成全民党,传统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就越深刻,其结果是两种现象的替代性出现,一种是民粹主义政治的升温,另一种是专家治国式的精英政治的登台。在法治基础薄弱和政治参与较低的社会,还可能产生政治的“密室化”。借鉴民主政治和新型的群众路线,都是避免后一种危险的途径。
○西方民主的一项承诺是其多元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政党竞争。然而,政治产出、社会结构和平等却往往遭到忽视。现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开展公开讨论的多元主义,存在着各种流派。一种日益深化同时日趋广泛的言路多元主义看来正在抬头。这种广开言路的多元主义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政治领导层产生影响了吗?各流派彼此是怎样沟通的?
●这些流派正处于转变之中。在80年代初,中国政治运行于两极之间,一极先前颇为团结一致,他们推崇旨在体现广大民众意志的“群众路线”;另一极为先前的官僚主义者和专断者。在80年代,大部分政治讨论是在政治机关和公共机构的框架下展开的,这也导致了政治机关的相对开放性,如党内的公开讨论变得多了起来,虽然也并不稳定。90年代以后,一些根本不同的利益集团开始抬头,并且这也是在社会日益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初,这些多样化的讨论首先是在知识界的讨论中出现的,它们并非像80年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那样由党的领导层推动。这种讨论起初多半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但自90年代以来,由于触及现实问题而激化起来。这些问题包括:农业危机、卫生医疗保障问题、国有企业及其私有化、收益的分配、地区间的差距以及政治改革等等。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种讨论后来通过大众媒体扩散开来,并最终为当局所关注,且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消化。实际上,现在在政治精英中间,甚至在党内,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就是当局和公开的政治讨论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效果的一个实例。在朱镕基总理任职时期,有关三农问题的公开辩论曾迫使政府面对问题,实行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并推行新农村建设。讨论最初发生在知识界,逐渐地扩展至大众媒体,最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关注;而政府最终不得不被追认真看待农业中的危机,并修改发展农业的改革纲领。
不久前,有两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政治讨论的视野,这就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有关两种模式的辩论或多或少夸大了两者的差异,但这也反映了党内和社会上的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
○在平等和民主参与方面,中国在发展中最近可望采取哪些步骤?
●就大众媒体而言,中国需要更加开放,需要更多的公开性。但这是一件麻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媒体可以对政治制度进行“殖民化”。这一点托马斯·迈尔您本人就曾进行过分析。这种发展在中国恰好已经发生。中国现在实行的固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但是媒体的影响较之从前已大大增强,如南方传媒集团,以及十分强大的四大门户网站。如果把温家宝总理同媒体之间的互动当作一种标准来看,那么可以发现,与江泽民或朱镕基时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大众媒体上亮相的机会大大增多了。我认为可以将当代世界的政治危机概括为如下方面,即政党国家化、国家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
公共性问题依然是一个问题。政治干涉仍然十分突出,并有碍于讨论空间的持久发展。此外,还有媒体日益屈从于市场取向这个问题。实际上,媒体在许多地区都实行地方性垄断,例如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南京,都是如此,在那些地方,所有可供利用的报纸都属于同一家出版集团。这种地方性的媒体垄断必然导致新闻报道的片面性和易操纵性,不仅从党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而且从利益集团对于媒体的控制来说也是这样。
○请允许我们再谈一下社会民主问题。甚至温家宝不久前也使用了这一概念。究竟中国传统中的哪些特性使得人们对社会平等、民主化社会以及多元民主制持有与我们不同的观点?
●在中国,就西方政治模式而言,许多人宁愿选择“社会民主”这一概念,而不赞成右翼的、保守派的政治观念。这或许是因为社会民主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之间多少有些重叠的关系,虽然两者的政治形式极为不同。许多老一辈人习惯于使用“群众路线”这一革命概念,即吸收全社会参与政治,讨论政治参与的必要性。群众路线的纲领赋予来自群众运动的政府以合法权力。在这一制度下,干部直接同农民、工厂工人对话,同时吸收工人、农民代表参与管理,以消除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会使人们同政治领导者疏远。这一实践在过去30年中很少再被提及,但最近许多地方又在做新的实践。我以为,这样一种基层实践如今再也不可能有效地恢复“群众路线”时期的状态和机制了,因为现今的政治制度已深陷官僚主义之中。当然,这一试验也许可以导致进一步的实质性的政治试验和制度试验,但现在的社会条件和制度框架都不利于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实施。这也正是危机所在。
我们首先要推进的是政治进程的更大的透明性。一些公共管理机关已经这样做了;所有的政治发展事项,如倡议制定新的法律等等,都应在相关的网站上予以披露,不管这涉及的是地区性的事情,还是全国的事情。
○在西方世界,我们正围绕普世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或分立主义进行一场大辩论。欧洲左派主张建立一种以平等和参与制民主为特征的社会。在中国的文化界中,是否有人忍受不了关于平等和参与制的普世主义概念?
●并非如此,文化传统有助于改进关于平等的旧观念。这里不一定必然存在分立主义。我们之间的价值和观念依然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可以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甚至历史差别,总是有意义的。不过,这和特殊主义或分立主义不是一回事。
民主对我们来说是某种积极的东西。甚至文化界中的保守派都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们并不习惯于民主程序,但是他们也指望政治参与的某种更有力的制度化。文化界的保守主义并不一定要反对民主制。中国和西方存在差别,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借鉴政治制度和法治国家的原则等内容。但即便借鉴这些制度和原则,也仍然需要处理它们与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历史遗产的关系。例如,中国的农业机构同欧洲国家是不可比较的。这部分是因为,土地产权是由昔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财产继承而来的。中国借鉴了市场导向的农业改革,固守旧的土地关系变得不可能,但即便是为了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容,也不等于说非得完成土地私有化不可。公共产权在使用权方面的变通,未必采用私有化的形式。维护公民的权利与保卫土地的公有制原则并不是对立的。我们知道,贪污受贿多半是由公有财产买单,而很少由私人财产付账。问题在于,农村改革是否可以使全体居民受惠,却又不一定与社会民主模式完全一致。这种模式是立足于很高的税率之上的。中国减免了农业税,实行了更加灵活的土地关系,土地的公有产权能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分红,是一个正在探讨中的问题。
○2008年年底,中国领导层颁布了一份农业改革文件,宣传扩大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最初,曾出现了大量赞同的声音。但是,后来逐渐听到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在当前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民如果把他们的土地出租,将会丧失他们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网。这项政策确实符合农民的心意吗?为保护农民,政府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这份文件本身是某种妥协的结果,推出的是模棱两可的举措。在文件发布之前,中国政府内部是有意见分歧的。随后政府急忙进行澄清,说明此举是为了促进所谓土地流转的灵活性。这样做无非是加强市场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把他们的土地使用权转租给其他农民。可见,其实这涉及农民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而不涉及改变产权本身。今天,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郊区,特别是在南方,几乎已见不到小农的踪影。到处工厂林立,城乡的明显差别已难以辨认,而农产品多半是从邻近的省份运进来的。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原因之一是土地价格的上涨。因为土地已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是用于城市的商业目的。因此,土地获得了某种附加值,这种附加值不是来自生产。基于这一原因,对农民的必要补偿可以区分为两个类别:首先,涉及个体农民家庭的土地,只有农民才有权使用土地从事农业。这样的农民家庭当然应当获得补偿。而用于商业目的所获得的土地增值,在我看来应归于整个社会,并用于共同的福利。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要求对福利状况进行测算,而不是去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他建议应更加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福利状况的指数,这包括财富的均衡分配、生态指标以及参与水平。这一争论在中国今后几年会产生影响吗?
●胡鞍钢谈到“绿色国民生产总值”。他尝试对“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本原则作出界定,他把社会保障、生态问题和良好的政府管理等列入其中。关于幸福指数也存在争论,这涉及福利、教育、卫生保健体系的质量等等。
中国的经济试验的一个极富成效的侧面,就是各种经济规划都是由地方首先发起试验的。在大多数场合下,这种规划不是囊括整个社会。现在我们知道,在有一些地区,这种试验未获成功并被放弃。这种地方性发展规划的试验,开始只实施于颇为具体的区域,因而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只有那些在地方上行得通的规划,才被推广于相应更高的各层次,最后才确认是否具有全国性的价值。这样,某一全国性的步骤失效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如果政府行政、公开讨论、社会参与能够有效结合,从实践中总结提高,我们就会确信,这样的实验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这里的政府也表现为比许多别的政府更加负责。这倒未必取决于政府形式,例如是民主制的,还是非民主制的。如果你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你就会发现,日本实行着一种远为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对社会需要或新形势的应对能力却受到很大的限制。
○2008年,中国遭到一场可怕地震的袭击。但只是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中国的行政当局就做到了使一个面积相当于整个比利时的地区完全重建起来。我们曾访问过四川地震灾区的一些人,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中国政府迅速做出的救助深怀感激之情。
●这就是我所说的超常的应对能力。西方世界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应当怎样判断这种应对能力?我读过弗朗西斯·福山的一篇文章。他访问过中国并且对于中国内地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福山对中国政府的反应能力有所评价,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个方面来看,中国大陆的工作效率高于台湾地区或韩国,甚至高于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他又批评中国政府缺少分权制。同时他承认,中国政府有能力了解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问题在于,关于这种应对能力或反应能力,从理论上应怎样界定其政治前提?事实上,从某些方面看,中国政府的反应能力很强,但从另一方面看,又存在着高度官僚化的特征。如何将这种反应能力日常化?在我看来,这种反应能力产生于某种民主的潜能,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之更加稳定。
[夕昆:中央编译局]
标签: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