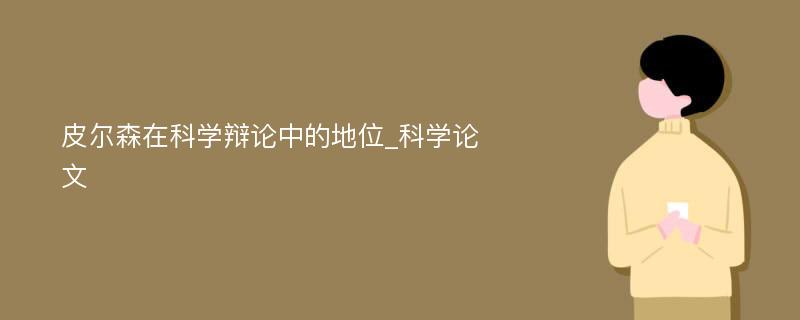
“科学论战”中的皮尔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科学论文,皮尔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同哲学派别和思想流派关于如何看待科学以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之大论战〔3〕。1923年2月,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一篇人生观讲演。该讲演把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中国宋明理学调和在一起,主张自由意志和内心修养,宣称“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4〕。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1887—1936 )面对张君劢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遂本着为捍卫真理而战之目的起而宣战,在《努力周刊》(48、49期)撰写长文“玄学与科学”〔5〕予以批驳。其后, 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诸多名流纷纷参战争论,形成了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论战的文章当年底就被编辑成册,以《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6 〕刊行。
丁文江在英国留学七年(1904—1911),1908年入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在英时对凯因斯(J.M.Keynes)的经济学书每本必读,也熟悉边沁、穆勒以及达尔文、赫胥黎、高尔顿、皮尔逊的著作和思想。丁文江回国后,曾用统计学研究过人体测量学、古生物学和中国历史,可见他与皮尔逊的科学进路亦有合拍之处。据傅斯年回忆,他本人常谈的通论科学方法的书是彭加勒、马赫、皮尔逊和罗素的,此外还有普朗克、爱丁顿和金斯的,丁文江说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书是他读过的。由此可见,丁文江十分熟知皮尔逊,他在论战中也确实是以马赫、彭加勒,尤其是以皮尔逊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观锻造自己的思想武器的。
在“玄学与科学”一文中,丁文江揭示出,张君劢的议论的来历,一半由于迷信玄学,一半由于误解科学,以为科学是物质的机械的。针对张君劢等人附和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的观点,丁文江强调说,纵使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玄学家,这些人仍然是不科学的。而他们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们是“务外逐物”岂不可怜。他义正辞严地斥责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
如果说丁文江的上述言论继承了皮尔逊的反形而上学和为科学的精神价值辩护的思想进路的话,那么他在阐述科学本性和科学知识论时,基本上沿袭了皮尔逊的科学哲学。他在谈到科学的范围、材料、方法和目的、价值时说,我们所谓的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定律〕〔7〕。 不过若是所谓事实,并不是真的事实,自然求不出什么秩序公例。他还说:
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凡是真的概念推论,科学都可以研究,要求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的最大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地分类,然后求它们的秩序关系,想一句最简单明瞭的话来概括它。所以科学的万能〔8〕,科学的普遍, 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
丁文江完全赞同皮尔逊关于科学的教育价值的观点。他表示,科学不但无所谓张君劢所说的“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逻辑〕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在这里,他也赞同皮尔逊的优生学思想,认为近年来生物学上对于遗传性的发现,解决了数千年来性善性恶的聚讼,使我们恍然大悟,知道根本改良人种的方法,其有功于人类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在论述科学的知识论时,丁文江用书櫃子代替皮尔逊的黑板为例,阐明何谓物何谓质。他和皮尔逊一样,也借用了摩根的术语“思构”〔构象〕称外部客体。他用刀子削铅笔削破手指代替皮尔逊的膝盖碰到桌子尖棱为例,阐明“觉官的感触”〔感觉印象〕过程。他得出与皮尔逊相同的结论:无论思想如何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直接的是思想的动机,间接的是思想的原质。我从我们自觉〔意识〕现象推论起来,说旁人也有自觉,是与科学方法不违背的。科学中这样的推论甚多。他进而表示:
心理上的内容至为丰富,并不限于同时的直接感触,和可以直接感触的东西——这种心理上的内容都是科学的材料。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
丁文江在这里显然借鉴了皮尔逊的感觉论以及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并无严格的界限、科学的范围也包括心理现象等见解。而且,他像皮尔逊一样认为,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觉官的感触相同,所以物质的“思构”相同,知觉概念推论的手续无不相同,科学的真相才能为人所公认。藉于此,他借鉴皮尔逊的合法推理的准则,提出概念推理的三个原则。
丁文江把上述科学知识论概括为存疑的唯心论(skepticalidealism),并认为凡是研究过哲学问题的科学家,如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詹姆士〔詹姆斯〕、皮尔生、杜威以及德国马哈〔马赫〕派的哲学,其细节虽有不同,但大体无不持这种哲学。因为:
他们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识物体的唯一的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觉官感触的外界,自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认为不知,应该存而不论,所以说是存疑。他们是玄学家最大的敌人,因为玄学家吃饭的傢伙,就是存疑唯心论者所认为不可知的,存而不论的,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
他接着(重复皮尔逊的话)说,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伯克莱〔贝克莱〕叫它为上帝,康德、叔本华叫他为意向〔意志〕,布虚那〔毕希纳〕叫它为物质,克列福〔克利福德〕叫他为心理质〔心理素材〕,张君劢叫它为我。它们始终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方法,各有各的神秘,而同时强不知以为知。旁人说他模糊,他自己却以为玄妙。他引用皮尔逊的电话局和接线员的例子评论道:“存疑的唯心论者说,人之不能直接知道物的本体,就同这种接线生一样:弄来弄去,人不能跳出神经系统的圈子,觉官感触的范围,正如这种接线生不能出电话室的圈子,叫电话的范围。玄学家偏要叫这种电话生说他有法子可以晓得打电话的人是什么样子,穿的什么衣服,岂不是骗人?在这里,丁文江的评论也与皮尔逊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用存疑的唯心论〔怀疑的观念论〕概括皮尔逊的哲学也是可行的,只是皮尔逊的怀疑哲学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方法:它不仅怀疑感觉背后形而上学的物自体,也怀疑一切神学、迷信和教条乃至陈规旧说。
面对丁文江的挑战,张君劢随即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长文应战。他接过丁文江责备“今之君子……以其袭取之易也”的话题,反唇相讥丁文江的“所谓科学的知识论,无一语非英人皮耳生之言,故君子之袭取,正在君之所以自谥也”。他列举了七条,逐一与皮尔逊的言论进行比较。
(一)在君曰,玄学是无赖鬼。又是诅咒玄学家死完之语。皮耳生〔10〕曰,玄学家为社会中最危险之分子〔11〕。
(二)在君引冒根〔摩根〕氏《动物生活与聪明》一书中“思构”之语。皮耳生亦引冒氏《动物生活与聪明》一书中“思构”之语。(皮氏书四十一页)
(三)在君云,推论之真伪,应参考耶方思(丁译戒文士)〔杰文斯〕《科学原理》。皮耳生曰,关于推论之科学的效力,应参考耶方思《科学原理》第四章至第七章,第十章至第十二章。(皮氏书五十五页)
(四)在君曰,此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伯克莱叫它为上帝,……〔12〕。皮耳生曰,官觉背后之物,唯物主义名之曰为物质,伯克莱名之曰上帝,康德、叔本华名之曰意志,克列福名之曰心质。(皮氏书六十八页)
(五)在君所用譬喻,曰书櫃,长方的,中间空的,黄漆漆的,木头做的,很坚很重。皮耳生所用譬喻,曰黑板,亦曰长方的,黄色的,很坚很重。(皮氏书三十九页)
(六)在君说明觉神经脑经动神经之关系,以刀削左手指头,乃去找刀创药为喻。皮耳生说明觉神经脑经动神经之关系,以脚膝为书桌之角所撞破,乃以手压住,乃去求药为喻。(皮氏书四十二页)
(七)在君以电话接线生比脑经。皮耳生以脑为中央电话交换所。(皮氏书四十四页,四十五页)。
我们之所以冗长地引用上述对照,其意在于说明,丁文江在论战中所持的哲学立足点(观点乃至例证)是皮尔逊思想,同时张君劢对皮尔逊的名著也认真地作了查阅和研读。张君劢与丁文江在见解上针锋相对,他当然不会同意丁文江的“后台”即皮尔逊的哲学和进路。于是,他把批驳的矛头转而对准皮尔逊——皮尔逊垮台了,丁文江也就无立足之地和不攻自破了。
在张君劢看来,皮尔逊的科学的知识论其重要之点有三:(一)思想内容之所以组成,则在官觉之感触。(二)因知觉或经历之往复不已,因而科学上有因果概念。(三)科学之所有事者,即将引官觉之感触,分类而排列之,以求其先后之序。他在批评皮尔逊的感觉论时首先引用了其一段言论:
就科学就吾人言之,此在外的世界之实在,即形、色、触三者之结合,换言之,即官觉的印象而已。人类所得之印象,犹之电话接线生之所得之叫号。彼之所知者,但有叫号者之音;至叫号者之为何如人,非彼之所知。故脑神经它一端之本体如何,亦非吾人之所知也。吾人拘束于感觉之世界内,犹之接线生拘束于叫号之世界内,而不能越雷池一步。(《科学规范》六十三页)
张君劢也许是出于他本人的观念论立场〔13〕,他并未像物质论者或朴素实在论者那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皮尔逊感觉论的要害——物质实在或对客观实在的否定。他只是说:“皮氏以为分析世界之事物,其最终不可分之元素,必归于官觉之印象。除官觉之印象外,无它物焉。然依我观之,苟人类之始生,若其所得于外界者,只有感觉,则并感觉而亦不可能。何也?”他接着引用德国《思想心理学》之言论证说,名此为甲感觉,名此为乙感觉,此甲乙之分,已有一种论理〔逻辑〕之意义。此意义也,甲乙感觉所由以构成之分子也。吾人居此世界中,若所谓感觉仅有色之红白,触之刚柔,味之辛酸,形之大小,则所谓辨别性者安从而起?惟其不仅有色形触三者,而尚有与觉俱来之物。譬之红色,一至简之感觉也,然与红俱来者尚有二事:一曰红色如此,二曰此真是红;此二者,即所谓论理的意义也。惟其有此二者,而后有彼此之分,而后有真伪之辨,此则推理之所由以本也。一切感觉不能脱离意义,则皮氏纯官觉主义〔感觉论〕何自成立耶?”
张君劢得出结论说,盖人类之于世界,既已以辨真伪求秩序为惟一要义,则与生俱来者,必有一种辨真伪求秩序之标准。此标准为何,即论理的意义也。他在赞同地引用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学说(伏于官觉接触之后者,必有理性之作用)后断言:
科学家推本人类知识于感觉之说,无自而成立。然此类言论屡见而不一见者,皆自忘其立言之本也。譬之在君师法皮耳生之言曰,事物之实在,皆感觉而已。不知此一语中已含有非感觉的成分。何也?赞成感觉而排斥其他各物,则已有一种是非之标准。是非之标准非感觉也。
在这里,张君劢显然没有完整而准确地把握皮尔逊的知识论。皮尔逊虽然没有明确强调感觉或感觉印象——他的感觉论的基石和科学素材的源泉——中的意义,但是他在界定即时的感觉印象和存储的感觉印象、记忆、联想、意识和思维、知觉官能和推理官能的共济时,已隐含了张君劢所谓的意义和心智之作用,更不必说皮尔逊看重逻辑和理性在科学和知识中的功能、意义和价值了。
针对皮尔逊最爱用的中央电话交换所之譬喻,张君劢引用美国人罗杰斯(Rogers)的话评论说:“苟接线生之全世界,仅以叫号者之声音为限,则所谓电话交换所,将如空气之腾于虚空中,不移时而化为乌有。”他接着阐释道:
罗氏之意,接线生不仅与声音接触;且尝与世界实在相接触,故交换作用之依据,不仅限于声音。诚如是,人类之所接触者,决不限于感觉。而岂感觉之后,必另有它物在,虽其为物之本体如何,为哲学争论之焦点,然吾人之知识世界,决不仅以感觉充斥;则可以断言。人心之辨是非也,别真伪也,即为实在之一点,而岂感觉之所能尽哉?
其实,皮尔逊并未把人类所接触者乃至科学限于感觉,他甚至认为感觉未达至概念或至少未达至知觉水平,都不能作为科学的材料,他只不过是要把超感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排除在科学之外而已。这怎么能说皮尔逊的知识世界为感觉充斥、被感觉所能尽呢?诚然,人们能够通过感觉及其基于其上的推理和猜想,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实在,但是这种实在的本来面目则是他无法断定的——这正是皮尔逊比喻的本意和价值之所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企图借助外观、通过概念理解实在,这无异于一个人想了解无法打开外壳的钟表的内部机构;他永远不能把他的答案与实在的机构加以比较,而且他甚至不能想像这种比较的可能性或有何意义〔14〕。作为实在论者的爱因斯坦的比喻和作为观念论者的皮尔逊的比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是发人深省的,罗杰斯和张君劢显然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张君劢说:“世间事物之‘真’者,皮氏曰惟有感觉。我以为苟无辨别真伪之思想,则并感觉之彼此而亦不辨。故所谓‘真’者,除感觉外必认思想,或曰论理的意义,此乃学术上之天经地义,不容动摇者也。”关于第一句话,只是张君劢本人对皮尔逊思想之理解,皮尔逊似乎没有说惟有感觉为真的话。至于后面的议论,我们在上面已作了厘清。同样地,张君劢指责皮尔逊在知识起于感觉抑起于理性问题上执一方(感觉),未辨明感觉和概念同为知识构成之分子,这简直无异于唐吉诃德和风车博斗了。事实上,皮尔逊只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认为感觉是知识之源泉,而从知识构成上则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十分看重理性在科学中的巨大功能。
关于因果概念和皮尔逊的因果观,张君劢是这样评介的:英国学派以经验或感觉为出发点,然反诘以感觉之中并无无形之因果概念在,则彼必答曰,是由其事之屡屡出现,成为一种往复不已之态,此因果之概念所由来也。惟如是,有因必有果者,非必然之真理也,乃心理上之信仰或习惯为之也。此说也,出自休谟,今已成为传统的学说。他进而表明:
科学之所重者,厥在因果律之必然性。自马哈〔马赫〕以来,以因果律必然性之说,不便于说明物理学一切现象,乃为因果律重下一种定义,曰:因果律者,无所谓必然性也,不过记现象之先后,且以至简之公式表示之,以图思想上之省事〔思维经济〕。如数学上甲为乙之函数,则乙亦甲之函数。故因果之相依,亦犹甲乙之相依,此外无他意焉。皮耳生之书,其论因果,一本马哈之说。故其言曰:“科学上之公例〔定律〕,乃以心理的缩写法,记述知觉的先后之序。”“科学之不能证明现象之先后中有内在的必然性。”
张君劢接着评论说:“然以吾人观之,力学上之现象,如一物件上左右各加一力,则其所行之路,为平行方形之对角线。夫物件路线之方向,且能为之算定,则必然性之强可以想见。马氏皮氏辈为维持其唯觉主义〔感觉论〕故,乃擅改定因果律之定义。实则唯觉主义本无成立之根据,而因果律之本意,初不以一二人之点窜而动摇也。”诚然,皮尔逊在因果观上借鉴了休谟和马赫的思想,但并不等同于他们二人。张君劢似乎不了解皮尔逊立足于概率论和统计学,提出了比因果律更为广泛和精致的缔合或相关概念,传统的因果概念只是其一个极端即绝对依赖;他也不知道皮尔逊关于必然性属于概念世界而非知觉世界的命题。他仅凭道听途说来的一点常识,就凭空妄发议论,怎么能不无的放矢呢?其实,无论是马赫〔15〕还是皮尔逊,都对因果性概念的发展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张君劢即使看到二氏的有关文献,依他的科学知识水平,恐怕也难以弄懂或领悟。
张君劢根据上述分析和批驳,断定皮尔逊的知识论是“脆薄”的。他进而揣度皮氏亦自知仅恃唯觉主义之不能自存,乃有所谓推理之说,而其标准则有三:概念不能自相矛盾;以非反常的人的知觉为标准;各观察者所得推论之一致。在张君劢看来,皮氏之承认此三标准不啻自弃其感觉一元论,而走入唯心派之先天范畴说矣。他还以牛顿持绝对时空概念而爱因斯坦持相对时空概念,马赫不承认有所谓我而詹姆斯承认之等对立为例,反问到底谁算正常,谁为疯子?在这里,张君劢又显露出对皮尔逊思想把握不确。其实,皮尔逊既未抛弃其感觉印象之基石,也未堕入先验范畴——他持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至于张君劢的例举,他显然没有弄清:哲学家的无休止的争论属形而上学,早已被皮尔逊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科学家的分歧在于概念层次的不同或概念进化,并非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知觉官能和推理官能不一致,而且具有相同官能的人也会承认爱因斯坦的时空概念比牛顿的高明和进步,而且爱因斯坦的概念也只是暂定的而非最终的。
张君劢还批评皮尔逊关于知识和非知识的划界观点。他在引用了皮尔逊的有关论述后断言,皮氏毅然划一条界线,凡科学方法所适用者,名之曰知识,并指斥皮尔逊眼界“狭小”,把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知识和乐之美不美的审美知识都排除在知识之外。诚然,皮尔逊认为用科学方法获得的都是知识,但是他关于知识的界定则是宽泛的:知识是对人的心智内容作理性分析所达到的结果,只是知识一词不能用于不可思议之物或不能成为心智内容一部分的东西。他甚至把宗教定义为有限与无限之关系的知识,并认为科学知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不用说,张君劢对皮尔逊的知识之内涵和外延一知半解,而他对后面的观点则全然无知,因为他根本未读皮尔逊的《自由思想的伦理学》(1888)〔17〕。张君劢在文中还引用或转述了皮尔逊关于社会变迁和科学的教育功能的论述,并指明丁文江所言与皮氏同一精神,唯不如皮氏之简单明了。对此,我们就不一一评说了。
在对张君劢的答辩中〔18〕,丁文江又多次引用和发挥了皮尔逊的思想和言论。他批评张君劢对科学的最大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他在引用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中的四条推理法则〔19〕后说:
牛顿这种精神,真是科学精神,因为世界上的真理是无穷无尽,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只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科学上所谓公例,是说明我们所观察的事实的方法,若是不适用于所发现的事实,随时可以变更。马哈〔马赫〕同皮耳生都不承认科学公例有必然性,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科学同玄学根本不同的地方。
丁文江在文中又涉及到他的科学万能论:“我说‘在知识里面科学方法可能;科学万能,不是在它的材料,而是在它的方法。’我还要申说一句,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结果,是在它的方法。”在这里,丁文江把皮尔逊的“科学统一”用“科学万能”置换了,显然超越并违背了皮尔逊的本意。不过,他对皮尔逊的怀疑论的理解则是深中肯綮的:
所以存疑主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奋斗的,不是旁观的,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用比喻和猜想同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论断,什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
针对张君劢指控他的知识论与皮尔逊一样是唯觉主义〔感觉论〕,丁文江辩护说:我说它是“科学的”,并不是说已经“有定论的”——这是张君劢自己对“科学的”下的定义,与我毫不相干——是因为这种知识论是根据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感觉印象〕与正统派哲学的根据不同。新代的经验主义是用经验来讲知识的,用生活手续来讲思想,新唯实主义〔新实在论〕用函数来讲心物关系,惟与唯觉主义的人地位不同,然而都可以说是科学的,因为都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知识论的。
丁文江还倡导用科学教育和科学方法改造宗教,这与皮尔逊的思想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我们极力提倡科学教育的原故,是因为科学教育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功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功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功分析的。我们不单是要使宗教性发展,而且要使它发展的方向适宜于人生。唯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它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作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他进而表明:
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谁也不能放弃谁。我现在斗胆给人生观下一个定义:“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
在这里,丁文江的发挥和议论是很精彩的,是对皮尔逊思想的合理引申和发展。不用说,我们从中也不难窥见到皮尔逊关于科学的教育功能、科学与宗教、情感与知识、知识即道德诸观点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丁文江的论述已超出了《科学的规范》的内容,由此可以推断他还读过皮尔逊的其他论著。
其他有关参战人物也涉及到皮尔逊及其思想。例如,站在张君劢一边的张东荪〔20〕(1887—1972)指出,丁文江的调调本于皮耳生,但却太无抉择了。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乃是对于杂乱无章的经验以求其中的“比较不变的关系”。这个即名为法式和法则(也许是暂定的)。所以科学并不十分注重于内容,而注重于方式,即是关系,即是关系的定式。他还认为,科学对于所取对象可以取名的方法,只由一个所谓的科学方法(即分类与归纳等)高悬于其上,决不能统一。科学的特殊方法虽是二次的,却非常重要。若抽取各别的二次方法以成根本的方法,势必愈普遍而失其独到的精神。在这里,张东荪关 于科学即关系定式的观点也本于皮尔逊,但更多地则是本于彭加勒〔21〕。至少所谓的二次的方法,皮尔逊虽未明确强调,却也没有否认其存在和意义。
科学派的王星拱〔22〕(1888—1949)论述说,我们承认,在感触的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世界,罗素把它叫做形式的世界,皮耳孙把它叫做概念的世界。他俩的意思固然不同(皮耳孙的概念世界是有描写作用的,而罗素的则无),然而有一点却相同。就是这个非感触的世界是由感触的世界构造起来的,而且这个非感触的世界是绝对地有规则的,这一点却与玄学家所主张的超物质的自由的玄学世界,大不相同。所以皮耳孙说,概念世界是用感触世界建筑起来的。王星拱接着恰当地发挥道:
现在,我们就用皮耳孙的名词概念的世界来陈述我们的意见。类的性质,是存在于概念世界的。科学事实,就是个体性质之表现。科学定律,就是类的性质之表现。类是不能脱离感触世界而独立的。科学定律也是不能脱离科学事实而独立的。所以概念世界中有同因必生同果的定律,感触世界中也必定先有同因必生同果的事实。
唐钺〔23〕赞同皮尔逊和丁文江的有关见解,认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科学中的未知部分在京垓年代以后,或者可以望其渐近于零;但是,要使它等于零,恐怕是万劫作不到的事。然而吾人的知识却是日有进步的,可以不必因此灰心,更不应该因此说科学方法不适用于研究某类现象。如果说唐钺的这些言论是对皮尔逊思想介绍和引申的话,那么他的下述议论则是明显对准张东荪(当然也是为皮尔逊辩护)的:“有人以为各种科学,各自有各自的方法。既然各自有各自的方法,那么科学方法的种类繁杂,当然不能说用科学方法的研究,都是科学;因为一种材料不能适用许多方法的缘故。我的浅见以为各科学固然有各科学的方法,而同时有它们的共同方法。就是心理学同物理学也有共同的方法。……所以不能说一切科学没有唯一共同的方法。既然有唯一共同的方法,那么当然可以说凡用这种方法的研究都是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