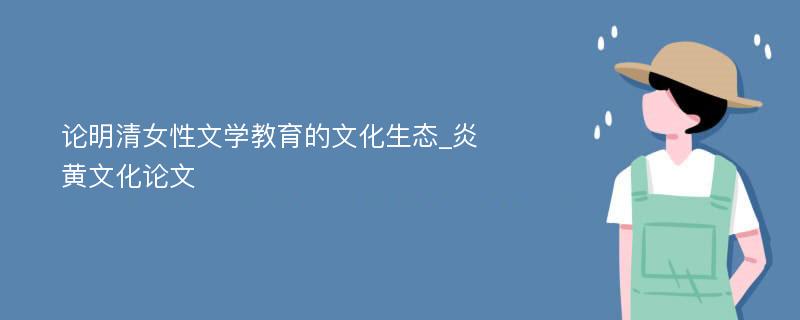
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文化生态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时期论文,生态论文,女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5-0021-09
没有教育就没有文学。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与文学传播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海内外对此多有论著涉及,可谓详备细致。但是除了少量论著简略提及以外①,尚无学人着力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审视这一文化现象,这一状况显然不利于全面考察和深入探索明清时期女性文学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本文拟讨论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文化生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简释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本文所说的“文学教育”,在内容上既包括专门的诗文歌赋教育,也包括一般的蒙学教育与经史教育对文学素质的养成;二是本文所说的“文化生态”,概指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文化生存状态,亦即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与制度、习俗、舆论等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明清时期,与男子相比较,女子的文学教育面临何种特殊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有何基本特征?这种文化生态给女子文学教育造成了何种特殊的效果?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殊途同归:女子文化知识教育的“德本论”
要讨论中国古代女子的文学教育问题,不能不先从女子的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说起。
作为中国教育家的鼻祖,孔子并不太看好女子教育。他一面说“有教无类”②,认为人不分贵贱,都应受教育;一面又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③,隐然把“女子与小人”排斥在教育之“类”的行列以外。
然而,从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的权力话语却大都对女子教育给予高度重视。那种“但教男而不教女”的做法,早在东汉时就被班昭(约49-约120)《女诫·夫妇》斥为“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④?北宋郑侠(1041-1119)《谢夫人墓表》引述郑氏之语云:“予常怪世之人,生子女不知教,豚彘畜之,肥其躯干而不美以德。……是则教子之所急,莫若女子之为甚。”⑤清初陆世仪(1611-1672)也说:“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而教女子尤为至要。少读《内则》,怪其多载酒浆笾豆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⑥人们甚至认为“教女之道犹甚于男”,因为幼而不教,长而失礼,“在男犹可以尊师取友以成其德,在女又何从择善诚身以格其非耶”⑦?
不过究其实,人们肯定女子教育,并非看重教育对女子养成自身独立人格价值的重要功能,而首先是看重教育对女子养成依附于男子的道德人格的显著效用。人们认为,“妇人所以有师何”?不过是“学事人之道也”⑧。女子之所以得以“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无非是要求她们学习“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⑨。清李晚芳(1692-1767)言简意赅地概括“女学之道”有四:“曰事父母之道,曰事舅姑之道,曰事夫子之道,曰教子女之道”,四者自少至老,“一生之事尽矣”,舍此别无他途⑩。
就中国古代理想的家庭关系而言,女子的一生一直是从属于男子、依附于男子的,她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更缺乏独立的人格价值,因此,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始终注重女子伦理精神的培植和道德人格的养成。人们认为,与男者学业于外,志于四方”不同,女子为学,只是“正洁于内,志于四德”(11)。因此,所谓女子教育无非就是:“四德与三从,殷殷勤教汝。婉顺习坤仪,其余皆不取。”(12)
那么,除了伦理道德教育以外,女子是否应该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呢?对此,在中国古代一直流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教育观念。
一种教育观念认为,为了培育女德,防微杜渐,女子不应该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至少不应该接受过多的文化知识教育。如东汉和帝邓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13)三国魏文帝甄后,“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14)时至明清,认为女子不应识字读书的教育观念仍然相当流行。如明温以介(后改名璜,1585-1645)之母认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15)周亮工(1612-1672)之父提出:“妇女不识字,《列女》、《闺范》诸书,近日罕见;淫词丽语,触目而是。故宁可使人称其无才,不可使人称其无德。”(16)
在这种文化生态中,明清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女子勿使之学书,勿使之观史”(17),“禁女子不得识文字”(18)的情形,女子识字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清贺龙骧说:“男性识字解义者十有七八,女能识字解义者百难一二”(19)。在清代已是百分之一二,在明代亦难以高于此数。即使到了文化高度发达的清朝末年,“举国女子,殆皆不学,甚至士夫世家,礼法森然,文采有曜,而叩其女学,则花貌蓬心,瞢无所识。……故一家之中,男子则文学彬彬,妇女则鹿豕蠢蠢,虽被服相近,有同异类”(20)。
与此相对,明清时期另有一种教育观念认为,女子应该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甚至应该接受较为高深的经史教育。如明徐皇后《内训》云:“夫女无姆教,则婉娩何从?不亲书史,则往行奚考?”(21)清蓝鼎元(1675-1733)主张:“妇人终老深闺,女红之外,别无事业。然耳口见闻,不能及远,则读书明理,其大要矣。”(22)陈弘谋(1696-1771)甚至质疑:“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23)
其实,比较上述两种教育观念,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因为禁止女子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固然是为了使女德纯正,身心不受污染;而提倡女子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性。如明许相卿(1479-1557)主张:“授读女教、《列女传》,使知妇道。”(24)清蓝鼎元强调:“女子读书,但欲其明道理,养德行,诗词浮华,多为吟咏,无益也。必有功名教之书,乃许论著,不然,则宁习女红而已矣”;因此,“若通经学古,著书垂训,有关名教其大,则君子贵之矣”(25)。李晚芳指出:“读书则见礼明透,知伦常日用之事,责备无穷,自当着力事事而不敢怠惰。”(26)周赓业(1730-1798)说:“女子不知书,他日无由尽妇道。”(27)章学诚(1738-1801)说:“故女子生而质朴,但使粗明内教,不陷过失而已。如其秀慧通书,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诗礼渊源,进以古人大体,班姬、韦母,何必去人远哉?”(28)
即使在西风渐盛的清末,女子文化知识教育的这种“德本论”观念仍然占据上风。如郑观应(1842-1922)批评当时“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主张仿照西方社会,在中国建立女子学塾,让女子进学校接受教育,以便培养学问高深、道德高尚的“贤女、贤妇、贤母”(29)。
因此,我们可以说,“德本论”是明清时期女子文化知识教育的核心观念(30)。要之,女子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目的,不是识文断字,而是明道育德,这就形成明清女子文学教育的文化生态。
若有若无:女子文学教育的边缘化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中,女子的文化知识教育已呈现边缘化状态,而女子的文学教育更处于边缘之边缘。文学才艺,一直不被列入正统的女子教育内容之中,甚至被有意地排除在正统的女子教育内容之外。北宋司马光(1019-1086)对女子教育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31)
司马光主张女子应读书,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可说是宋人的共识;但他同时也对女子读书做出明确的限制,即只能阅读《孝经》、《论语》之类的儒家经典,或观图史以自鉴,而不得学习“刺绣华巧,管弦歌诗”之类的文学才艺。
明清时期贬抑女子接受文学教育的言论仍然甚嚣尘上。如明许相卿告诫:教育女子,“勿令工笔札,学词章”(32)。徐学谟(1522-1593)甚至闭着眼睛说瞎话,指责“妇人识字,多致诲淫”(33)。清石成金(1659-?)《家训钞·靳河台庭训》说:“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耻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守分之为愈也。”(34)车鼎晋(康熙三十年进士)《女学序》说:“女子以德为本,而文词原非所尚。……苟能明事父母舅姑之义,躬井臼织作之事,即才艺无闻,亦无失焉。”(35)《昏前翼·书史》一面认为“女子固不宜弄文墨,但古之贤女未尝不读书。如《孝经》、《论语》、《女诫》、《女训》之类,何可不读”?一面却明确声称“诗词歌咏,断乎不可”(36)!戴礼(1884-1935)说“摘句寻章、簪花咏絮之事”,“非所谓学矣”(37)。更有甚者,有人还把“弄柔翰,逞骚材”、“拨俗弦,歌艳语”之类,视为“邪教之流”(38)。
要之,在明清时期,文学教育是妨害女子道德人格的罪魁祸首的看法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当时盛传于世的“女子无才便是德”(39)的俗谚便集中彰显了这种文化生态。
囿于传统观念的熏染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明清时期许多女子虽然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却自觉地扼制自己的文学才华。如海宁人汪蕙“幼娴文艺,于归后,所作尤多。以诗非妇人所宜,恒秘藏之”(40)。钱塘人王璋虽然长于诗词,但因亲人“最恶妇人作诗”,于是“绝笔不作”(41)。黄宗羲之妻叶宝林“少通经史,有诗二帙”,但有见于“越中闺秀有以诗酒结社者”,认为“此伤风败俗之尤”,“即取己稿焚之,不留只字”(42)。查昌鹓虽然对诗文“声韵之学,往往见猎心喜”,却“以非女子事,辄不敢为。偶有小咏,即焚弃之,不复存稿”(43)。桐乡人沈珮少年时娴于诗歌,但出嫁后忽自悔“才非女子所宜”,“遂自焚其稿”(44)。在她们内心中,学习吟咏诗词,即便不至于严重戕害道德人格,至少也不利于自身“淑女”、“贤妇”之类社会形象的塑造。
然而,从明末清初开始,社会上也还传播着另一种声音,即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提出异议,明确申明女子之才并不妨其德。如明末冯梦龙(1574-1646)说:“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成周圣善,首推邑姜,孔子称其才与九臣埒,不闻以才贬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45)叶绍袁(1589-1648)说:“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46)明末清初王相之母刘氏说:“‘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并反问道:“古者后妃夫人,以逮庶妾匹妇,莫不知诗,岂皆无德者欤?末世妒妇淫女,及乎悍妇泼妪,大悖于礼,岂尽有才者耶?”(47)在清代,更有一些知名文人为女子的文学之才张目。如陈兆仑(1700-1771)《才女说》云:
世之论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独谓不然。……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索,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以视村姑野媪,惑溺于盲子弹词、乞儿说谎,为之啼笑者,譬如一龙一猪,岂可以同日哉?又《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柔与厚,皆地道也,妻道也。由此思之,则女教莫诗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48)
姚鼐(1731-1815)指出:
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文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49)
然而,只要细读上述言论,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振振有词地批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见,人们也大多是从张扬女子“才德不相妨”的角度着眼的。人们坚信,只须高扬“德”的旗帜,便可以为“才”在女子人格建构上的合理性存在争得一席之地。所以明人郦琥选辑《彤管遗编》,胡文焕编纂《新刻彤管摘奇》,都明确标榜:“学行并茂,置诸首选;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学富行秽,续为一集;别以孽妾文妓终焉,先德行而后文艺也。”(50)
不仅男子如此认识,明清时期的女子也多有同感。她们肯定女子学诗吟咏的时候,往往有见于“自来篇什中,何非节孝选。妇言与妇功,德亦藉此阐”(51);“务使才与德,相成毋相反”(52)。明末清初顾若璞(1592-约1681)为其家女孩聘请塾师进行教育,“舍彼女红,诵习徒勤”,一位老妇批评她“妇道无成”,她反驳道:
二仪始分,肇经人伦,夫子制义,家人女贞。不事诗书,岂尽性生?……人生有别,妇德难纯。讵以闺壶,弗师古人?邑姜、文母,十乱并称;大家有训,《内则》宜明。自愧伫愚,寡过不能。哀今之人,修容饰襟,弗端蒙养,有愧家声。学以聚之,问辩研精,四德三从,古道作程。斧之藻之,淑善其身。岂期显荣,愆尤是惩。(53)
从母亲职责、家庭荣誉,尤其是从“四德三从”的伦理意义上,顾若璞雄辩地证明了女子文学教育的正当性。清中叶恽珠(1771-1833)更是极力倡言女子学诗的道德合理性:
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纴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独是大雅不作,诗教日漓,或竞浮艳之词,或涉纤佻之习,甚且以风流放诞为高,大失敦厚温柔之旨,则非学诗之过,实不学之过也。
所以她编选《国朝闺秀正始集》,便严加筛选,“用以显微阐幽,垂为彭范,使妇人之学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尽删风云月露之词,以合乎二南正始之道”(54)。清末侯官人陈芸(1885-1911)也说得很明白:
(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未由见。不于此是求,而求之幽渺夸诞之说,殆将并妇女柔顺之质,皆付诸荒烟蔓草而湮没,微特隳女学,坏女教,其弊诚有不堪设想者矣。(55)
尽管如此,女子“才德不相妨”的观念毕竟比“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见大大前进了一步,它理直气壮地肯定了女子文学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女子文学教育大张其目,大倡其声,从而为普及与推进女子文学教育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正如美国学者高彦颐评价顾若璞时所说的:“用母教去申明妇女教育的重要,她正沿袭着男性惯用的策略。虽然使用的是一种传统的语汇,但将妇德和女工的含义扩展到诗才,顾若璞为新女性形象做出了强有力辩护。”(56)
垂艳流芳:女子文学教育的效果
在明清时期,传统观念与社会舆论共同锻造出的多元文化生态,显性地或隐性地影响着全社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女子文学教育的“理想范型”,即“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是适当的,是合理的,是可以得到公认的,包括现实的认可和历史的认可。这种“理想范型”,既为女子文学教育实践提供了强制的规范和明确的导向,也为其提供了精致的包装和得体的标榜。在多元文化生态中理想与实践二者的互动与相生,构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展现出明清时期丰富的女子文学教育状貌。与此相关,这种“理想范型”也与教育效能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它既为女子文学教育效能提供了合理的、公认的解释,也为其提供了有效的“保护色”。于是,实际的女子文学教育效能得以在“终极意义”上被解释为符合“理想范型”,尽管它在实践层面可能千姿百态,甚至与“理想范型”背道而驰。
于是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多元文化生态,为女子文学教育的普遍推广和持续高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缘。无论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规范和导向如何,在实践的层面上,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效果无疑是极其显著的。尤其是从晚明到晚清的四百多年中,女子文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提高程度都远远超过其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甚至成为重要的“文化命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且形成文化风气,造成社会效应,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从这一时期具体的教育实践来看,女子教育,包括女子文学教育,已经逐渐纳入社会运行机制的正常轨道,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如《桐城续修县志》卷3《风俗》记载:“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57)无论是《女四书》还是《毛诗》的授读,都不仅止于识文断字,也不仅止于伦理教化,其中无疑也蕴含着文学的启蒙和审美的熏染,从而成为文学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
在教育效果方面,晚明至晚清才女辈出,前所未见,尤以江南地区为甚,这与文学教育的社会普及不无关系。如《卧月轩稿序》记载晚明的情形,说:
而近世女士固多文焉。他不具论,吾杭数十年以来,子艺田先生女玉燕氏,则有《玉树楼遗草》;长孺虞先生女净芳氏,则有《镜园遗咏》;而存者,为张琼如氏之书,为梁孟昭氏之画,为张姒音氏之诗若文,皆闺阁秀丽,垂艳流芳。宜马先生谓:“钱塘山水蜿蜒磅礴之气,非缙绅学士所能独擅。”(58)
清中叶袁枚(1716-1797)还作了一个“古今对比”,说:“近时闺秀之多,十倍于古,而吴门为尤盛。”(59)丁绍仪(1885-1884)《听秋声馆词话》卷19“清闺秀词”条记载清后期的情形,也说:“吴越女子多读书识字,女红之暇,不乏篇章。近则到处皆然,故闺秀之盛,度越千古。”(60)
我们可以通过清代女子著述的情况,来印证袁枚“十倍于古”的说法。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明清之前历代单独出版正式著作的妇女共117人,而明朝一代就有242人,清朝更多达3667人(61)。在单独出版正式著作的妇女之外,撰有零星诗文传世的女子更远远超过此数(62)。看来,即使考虑到著作流存略远而详近的客观因素,袁枚“十倍于古”的估计也并非信口雌黄,而是其说有据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说:
古今妇女之诗比于男子,诗篇不过千百中之十一,……今乃累轴连编,所称闺阁之诗,几与男子相埒。甚至比连母女姑妇,缀和娣姒姊妹,殆于家称王、谢,户尽崔、卢。岂壶内文风,自古以来,于今为烈耶?(63)
章氏对此现象不免心存疑虑,甚至痛心疾首。但他却不经意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女子教育的普及,女子写作的广泛,女子才华的揄扬,这的确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明至晚清势不可挡的社会风气,“自古以来,于今为烈”。
那么,明清时期女子接受文学教育的社会阶层情况究竟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似乎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下层女子也能够享有接受文学教育的权利,似乎已经达到“有教无类”的理想状况。清中叶李调元(1734-1802)对此言之凿凿:“武林(即今浙江杭州)女媛多能诗,不但朱门华胄,即里巷贫户能诗者亦复不少。”(64)“亦复不少”究竟是多少?李调元含糊其辞,今人也无从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李调元要传达的信息显然相当明晰:在浙江杭州,“里巷贫户能诗者”即使不说以百计,至少也可以十计,此方可谓之“不少”。
清代浙江杭州平民女子能诗的情况,可以仁和女子吴藻(约1799-约1862)为例。吴藻“父夫俱业贾,两家无一读书者”,显然出身在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但她却“喜读词曲”,自学成才,成为名噪大江南北的女词人(65)。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地区的一些佐证。比如吴江(今属江苏)女子汪宜秋(字玉轸),“父兄夫婿,皆非士人”(66),却“工诗善书”,文学水平颇高,甚至足以“卖文自活”(67)。在举家男子皆不读书的家庭里,居然能孕育出“工诗善书”的女子。
当然,吴藻的父亲和丈夫都是商人,虽属平民阶层,比之“里巷贫户”地位还是略高一些。真正出身下层平民而接受文学教育的例证,则有为时人交口称道的丹阳(今属江苏)农家女子贺双卿(1713-1736):
生有宿慧,闻书声,即喜笑。十余岁习女红,异巧。其舅为塾师,邻其室,听之,悉暗记,以女红易诗词诵习之。(68)……田家女能识字,且通文,通文且悉工,醉玉函,惊嗣叔,慑宁溪,饥渴啼笑,极眩乱而无以自持,何数数也?(69)
早在清初,荻岸山人编次《平山冷燕》小说,便塑造了扬州乡村一位杰出的农家女子冷绛雪:
禀性聪明,赋情敏慧。见了书史笔墨,便如性命。自三四岁抱他到村学堂中玩耍,听见读书,便一一默记在心。到六七岁,都能成诵。……到了八九岁,竟下笔成文,出口成诗。(70)
此外,还有身为婢女而工诗能词的例子。如明清之际邹枢《十美词纪》记载,邹枢十五岁时,其外祖母以二十五金买一婢女,名如意,年十四。如意自称:
我南城织户陆氏女,七岁鬻于顾氏家。主怜我聪颖,命我入馆伴读。主母延女师训诸姑,师姓沈,嘉兴秀水人,工诗词,尽心教我,以故诗词颇晓。(71)
又如雷瑨、雷瑊《闺秀诗话》卷4记载:
扬州西乡有农家女者,年方十五,为巨室某姓家婢。某夫人能诗,见其颖慧,辄教以吟咏。不三年而成,里中辄以才女目之。有富商某欲纳为侧室,女不从,曰:“我宁为婴儿子,不愿为小青也。”寻又议婚农家子,女亦不从,曰:“我不能为双卿。”竟不嫁,专事吟哦,十八岁而卒。(72)
清人王倬曾著有《课婢约》,文中记载:
有婢初来,年方十四,指挥未谙,约法数章。翰墨图书,只此是吾长物,牙签玉轴,从令隶汝所司。……背诵经文,私教鹦鹉,图书常令拂拭,窗几莫不明净。……丝桐在壁,凭弦渐解琴声。(73)
以上例证似乎确凿地向我们昭示,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卑如农女,贱如侍婢,都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文采斐然,出口成章。
然而,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一片阳光灿烂。贺双卿其人已是若有若无,令人将信将疑(74);才女冷绛雪更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实际状况应该是,即使在女子文学教育似乎广为普及、女子文学写作似乎如火如荼的清代,真正受到文学教育,尤其是较为良好的文学教育的,其实绝大多数还是簪缨世家、书香门第的闺秀。史载东汉末年郑玄(127-200)家“奴婢皆读书”(75),这并不意味着东汉社会广大平民女子都有机会读书学文、吟诗作赋。此事传为雅谈,不正反证这类事情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吗?曹雪芹(1715?-1763?)《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府,充溢着一派“诗礼簪缨之族”的文明气象。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又有几个丫鬟识字断文?更不用说吟诗作赋了,那毕竟只能是公子、小姐们的风雅趣事。同样,在明清时期一些著名的文学世家中,我们可以观赏母女姊妹一门风雅、骈珠联萼的景象,却很难寻觅侍女丫鬟出口成章、倚马千言的记载。
倘若仔细考察明清时期数以百计的女子诗文作品总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享有接受文学教育机会的女子中,出身贵族官宦家庭的占绝大多数,其次出身文人士子家庭,再次则出身务农或经商的富裕家庭,至于出身下层平民百姓家庭的则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如单士釐《清闺秀艺文略》一书著录清代女作家2787人,仅撰《丹白集》之莫兰心一人为“农家女”,其余则“或名父之女,或才士之妻,或令子之母”(76)。这正彰显了明清女子文学教育真实的文化生态。因此,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只能说明当时的贵族官宦、文人士子家庭女子文学教育状况,并不足以说明当时全社会女子文学教育的实际状况。
注释:
①雷良波《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先秦至晚清)》(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简略谈到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状况。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有若干章节涉及文学教育。
②《论语注疏》卷15《卫灵公第十五》,《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8页。
③《论语注疏》卷17《阳货第十七》,《十三经注疏》,第2526页。
④范晔:《后汉书》卷84《曹叔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786页。
⑤郑侠:《西塘文集》卷4,《四库全书珍本四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8页。
⑥陆世仪:《思辨录》卷1,清光绪三年(1877)江苏书局本,第1页。
⑦刘氏(王节妇):《女范捷录·统论篇》,王相:《新增女子四书读本》,上海:会文堂书局,1916年,第2页。
⑧班固等:《白虎通义·嫁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仪礼》卷30《丧服》,《十三经注疏》,第1104页。
⑩李晚芳:《女学言行纂·总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谧园刻本,第4页。
(11)《礼记·内则》长乐刘氏注。所谓“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又称“四行”,始见于《周礼·天官·九嫔》及《礼记·昏义》。又《诗经·周南·葛覃》:“言告师氏”,汉毛亨《传》曰:“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12)梁兰猗:《课女》,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12,清道光十一年(1831)红香馆刻本,第3页。
(13)范晔:《后汉书》卷10《邓皇后纪》,第418页。
(14)陈寿:《三国志》卷5《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9页。
(15)温以介:《温氏母训》,《丛书集成初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页。
(16)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
(17)艮斋主人辑:《寻乐堂家规》,窦克勤:《窦退庵遗书》,清康熙间刻求善居藏板本,第3页。
(18)陈兆仑:《汤母路太恭人传》,《紫竹山房诗文集》卷14,清乾嘉间陈桂生刻本,第23页。
(19)贺龙骧纂辑:《女丹合编·女丹合编通俗序》,彭翰然参订;彭定求辑:《道藏辑要》,阎永和增补,第243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刻本。
(20)康有为:《大同书》戊部《去形界保独立》,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21-222页。
(21)徐皇后:《内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25)蓝鼎元:《女学》卷6,《闽漳浦鹿州全集》,清光绪六年(1880)重修跋闽漳素位山房代印本,第22、23页。
(23)陈弘谋:《五种遗规·教女遗规·序》,《四部备要·子部·儒家》,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25页。
(24)许相卿:《许云村贻谋》,《丛书集成初编》,第6页。
(26)李晚芳:《女学言行纂·总论》,第3页。
(27)周赓业:《周母沈硕人传》,《蓬芦文钞》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9页。
(28)《妇学篇书后》,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55页。
(29)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夏东元编:《郑观应集》卷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30)以上论述参考刘咏聪:《清代前期关于女性应否有“才”之讨论》,载其《德·色·才·权——论中国古代女性》,香港: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258-262页。
(31)司马光:《温公家范》,王宗志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32)许相卿:《许云村贻谋》,《丛书集成初编》,第6页。
(33)徐学谟:《归有园麈谈》,陈继儒:《宝颜堂秘笈》第4册,上海:文明书局,1922年,第2页。
(34)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5页。
(35)蓝鼎元:《女学》卷首,《闽漳浦鹿州全集》,第1页。
(36)《古今图书集成》卷3《明伦汇编·闺媛典·闺媛总部·总论》,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1934年,第15页。
(37)戴礼:《女小学》卷1,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静海高毓浵铅印本,第3页。
(38)吕坤:《闺范序》,《吕新吾先生闺范图说》卷首,《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29册,影印明吕应菊重刻本,第479-480页。
(39)此语始见于明末陈继儒《安得长者言》所录时人之语,见《宝颜堂秘笈》,上海:文明书局,1922年,第1页上。明末冯梦龙《智囊补·闺智部总叙》亦引此语。清初王相注解《女范捷录》中提到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时亦谓为“古人之言”,见刘氏(王节妇)《女范捷录》卷下《才德篇》,王相《新增女子四书读本》,第25页。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对此有所考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88-202页。参见刘咏聪:《中国传统才德观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论》,载其《德·色·才·权——论中国古代女性》,第200-201页及第241-245页之注释。
(40)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7引《两浙輶轩续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6b页。
(41)(44)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2引《众香词》,第17a、18a页。
(42)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1引《馀姚县志》,第15b页。
(43)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引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26-427页。
(45)冯梦龙:《智囊补·闺智部总叙》,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11页。
(46) 叶绍袁:《午梦堂集·序》,《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47)刘氏(王节妇):《女范捷录·才德篇》,王相:《新增女子四书读本》,第25-26页。
(48)陈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卷7,第6b页。
(49)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6页。
(50)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引郦琥《彤管遗编·序》,第879页。
(51)夏伊兰:《偶成》,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第9册,卷3,清道光间嫏嬛别馆刻本,第51-52页。
(52)张淑莲:《孙女辈学诗书示》,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15,清道光十一年(1831)红香馆刻本,第2页。
(53)顾若璞:《卧月轩稿》卷2,丁丙编:《武林往哲遗著》第58册,钱塘丁氏嘉惠堂,1898-1900年,第1b-2a页。
(54)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首“弁言”,第1页。
(55)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卷首“叙”,民国三年(1914)刻本,第1a页。
(56)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
(57)廖大闻等:《桐城续修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第92页。
(58)顾若璞:《卧月轩稿》“卷首”,丁丙编:《武林往哲遗著》第58册,第5a页。
(59)《随园诗话补遗》卷8,袁枚:《随园诗话》,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785页。
(60)唐圭璋:《词话丛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20页。
(61)转引自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312页,注24。该注释还引用罗友枝《中国清代的教育和大众识字》云:“19世纪中晚期的证据证明,中国有30%-45%的男性和2%-10%的妇女能够读写。”按陆草《论清代女诗人的群体性特征》(《中州学刊》1993年第3期)统计,《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清代女诗人3671位。段继红《清代女诗人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统计该书“共收录了历代有著作成集的妇女共4200余人,其中明末之前共361人,而清代则有3800多人,又加上史梅女士辑出的未收入《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的118人,则近4000家。”史梅的辑录,见其《清代江苏方志中之妇女著作——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拾遗》(《古籍研究》1996年第2期)。黄湘金《南国女子皆能诗——〈清闺秀艺文略〉评介》,又补充胡书所不载而见于单士釐《清闺秀艺文略》的女诗人83位(《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104页)。
(62)仅以晚明而论,李圣华根据大量史料爬梳出209位女诗人,见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附录二“晚明女诗人生平、著述简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95-412页。
(6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67页。
(64)钱仲联:《清诗纪事》引李调元《雨村诗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764页。
(65)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2“花帘词”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1-62页。
(66)钱仲联:《清诗纪事》引袁洁《蠡庄诗话》,第15799页。
(67)钱仲联:《清诗纪事》引沈善宝《名媛诗话》,第15798页。
(68)史震林:《西青散记》卷2,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第39页。
(69)史震林:《西青散记》卷4,第39页。
(70)获岸山人:《平山冷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55-56页。
(71)《香艳丛书》第1集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学扶轮社排印本,1992年,第580页。
(72)雷瑨、雷瑊:《闺秀诗话》,上海:扫叶山房,1916年,第9b页。
(73)《香艳丛书》第12集卷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学扶轮社排印本,1992年。
(74)参见胡适:《贺双卿考》,《胡适文存三集》(《民国丛书》本);康正果:《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及其传达的诗意:〈西青散记〉初探》(上、下),《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2期、1996年第1期;李金坤:《贺双卿考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院报》2001年第3期,《贺双卿研究综论》,《常州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严迪昌《〈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疑事辨》,《泰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等。
(75)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2页。
(76)黄湘金:《南国女子皆能诗——《清闺秀艺文略》评介》,《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