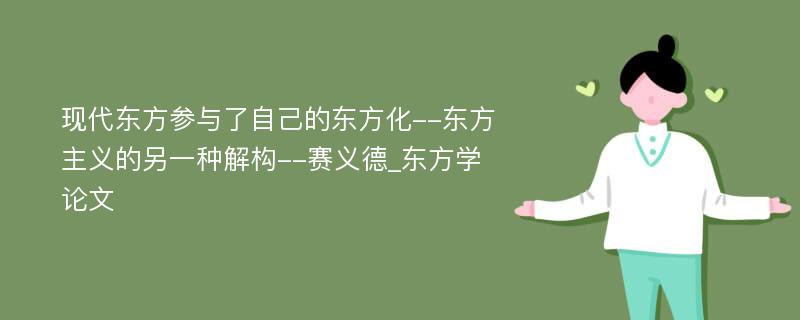
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赛义德对东方学的另一种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学论文,赛义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5-0073-05
解构东方学是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是如何参与自身的东方化的。他说,“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18页。)。
现代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的观念中,这些观念首先表现在东方人的民族自卑性、崇洋媚外等“西化”意识上。赛义德以东方人的消费模式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他看来,东西方之间的消费关系是一种一边倒的关系:美国是少量产品有选择的消费者,而阿拉伯则不加选择地消费着各种各样的美国产品——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这产生了许多后果。阿拉伯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趣味上的标准化,不仅体现在晶体管收音机、蓝布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这些物质形象上,而且体现在美国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东方文化形象上,这些形象几乎被电视观众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阿拉伯人居然以好莱坞所制造的那种“阿拉伯人”形象为标准来看待自己。
在上述的一边倒的消费关系中,东方人实际上认同了西方关于东方人的形象,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东方人把西方关于东方人的形象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默认了西方的优越和高人一等,这本身已经是在参与自身的东方化了。如果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弱势民族面对强势民族时的被动和无奈的话,那么在东方,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主动地去迎合西方的胃口,主张在东方要照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化模式。对此,赛义德写道:东方的“知识界本身助长了这一被其视为主要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现象的产物。它注定要充当的是一种‘现代化’的角色,这意味着它会为那些它大部分从美国接受而来的有关现代化、进步和文化的观念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且赋予它们以权威。……如果这里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东方学形象和学说的一种默认,这一倾向同时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交流中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简言之,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15页。)。
赛义德的这一看法与英国的新闻记者兼自由作家保罗·哈里森的观点不谋而合。哈里森遍游亚非拉等23个国家之后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之源在于殖民主义统治和照搬西方模式。在其所著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第三章《整个世界的西方化》中,哈里森详细地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比照集团行为”等形式对西方模式的全面摹仿。“有这种行为的人,照搬他希望跻身其中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抛弃自己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他说,“在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村子里,你都会发现嘲笑传统服装、炫耀地穿着厚蓝布裤子和紧身短袖圆领衫的年轻人。走进任何一家银行,出纳员的穿着都和他们的欧洲同行毫无二致。……这种情形山不仅仅反映在人们所追求的消费形式上,模仿也发展到建筑形式,工业技术、医疗系统,教育体制和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上”(注: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第35页。)。哈里森对第三世界盲目地摹仿西方的一套做法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在他看来,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就会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并且迅速地把传统文化中不管好的坏的东西都一古脑地摧毁了。哈里森在这里主要是探讨第三世界的贫困之源的,但他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赛义德所说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现代东方参与自身的东方化的第二种形式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是:东方人为了对付西方的东方学,从而炮制出一种所谓的西方学,用西方学的体系来替代东方学的体系。这样,东方人在推翻了一种旧的二元对立之后,又在东西方面前树立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正是在此过程中,东方人实现了对自身的又一次东方化——人为地主动地把自身与西方再一次相对立。对此,赛义德持极力反对的态度。他强调指出,东方学的对立面并不是“西方学”。针对某些批评家指责他在《东方学》中的“反西方论倾向”,赛义德作了强烈地反驳。他说:我“书中的观点显然是反本质主义的,对诸如东方和西方这类类型化概括是持强烈怀疑态度的,并且煞费苦心地避免对东方和伊斯兰进行‘辩护’,或者干脆就将这类问题搁置起来不予讨论”。他还说:“‘攻击西方文明’这一陈腐的公式之中得出同样概约化的信息,既过于简单化也是极为错误的”(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26页。),赛义德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他既无意为东方辩护,也不是反西方的,他纠正东方学权力话语的意图就是要超越传统的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僵化对立模式,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他并不是要人们走极端搞一个“西方学”,正如德里达解构“中心”的目的不是要使某种“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共生一样,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
在另一场合,赛义德进一步重申了他的上述立场,并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他写作《东方学》的主要目的。他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一种特殊的观念体系,而决不是试图用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我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的文化时)或敌视和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必须给予独立的批评意识,一种唱反调的批评意识多大重大性?”(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18页。)
那么赛义德所说的“西方学”是什么意思呢?在东方世界,那些强烈而僵化的自我身份认同,与西方的尖锐而恒在的对立感、敌对感、受迫害感,这些本质主义及其有关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就是与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相对应的“西方学”或“西方主义”(Occidomtalism)。它是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又为现实政治所强化、深化和僵化。它与东方学一样,是东方对西方的整体化、妖魔化、类型化建构,是东方对西方的想象视野、过滤框架、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也是东方误解、歪曲、建构西方的前结构、前见和文化传统,是“认为西方正在对付整个非西方世界”的观念体系。
“西方学”显然是弱势文化在面临优势文化的强大挑战时的本能反应,是长期处于自我封闭和超稳态结构中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遭遇另一强大文化侵袭时所采取的策略。“西方学”的主要表现就是文化自大。日本作家梅棹忠夫在其《文明的生态史观》中就指出了印度与中华文明的自大表现(注: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译:《文明的生态史观》,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6页。)。中国近现代对西方文化的典型看法是:西方文化是物质性的,是器用之学、格致之学,精神贫乏,伦理沦丧;西方人是凶恶成性、攻击性极强的食肉动物等等。这就是赛义德所说的“妖魔化”和“整体化”。比如辜鸿铭就认为,西人只知“敬天”“尚力”不“敬人”“崇德”,专重势利而不言义理,只会求知而不会闻道,因此,“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弥此祸”,就是说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注:汪澍白:《文化冲突中的抉择—中国近代人物的中西文化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2~387页。)。“西方学”的另一种表现是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实际上也是弱势文化在感到优势文化挑战和威胁过于强烈急剧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激进的自救措施,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即生于此。赛义德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说:“文化常常咄咄逼人地与民族或国家绑在一起,把‘我们’与‘他们’加以区分,几乎永远伴随某种程度的仇视他国的情绪。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是民族同一性的根源,而且是导致刀光剑影的那一种根源。正如我们从新近对文化和传统的‘回归’中看到的。与这些‘回归’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思想和道德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与多元文化观和合成文化观这样一些比较开明的哲学所体现的宽容精神水火不相容。在原殖民地国家,这些‘回归’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性质和民族主义性质的原教旨主义”(注:赛义德著,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4~165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东方学还是西方学,它们都是在建构、妖魔化、类型化对方,都是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赛义德之所以说东方学的对立面或答案不是西方学,其原因即在如此。既然东方学的答案不是西方学,那么东方学的答案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东方学的历史命运到底如何呢?赛义德反复强调应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东方化东方”,无论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还是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避免“东方化东方”的有效途径不是用所谓的“西方学”来替代东方学,而是着眼于东方学自身的“改良”上,东方学的答案就在东方学自身里。赛义德把“改良”东方学的期望寄托在知识分子的“忠诚”和“良知”上。他说:“曾使东方学这一思维形式日益获得其说服力的那些条件将仍然存在?从整体上说,这是一件极为令人沮丧的事。不过我心中总是存有某种合理的期望:东方学不要总是象以前那样几乎不受任何质疑,不管是从学术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而言”。因此,一方面,“有趣的研究最有可能产生于这样的学者之手:他们的忠诚乃贡献于从学术的角度界定的某个学科,而不是象东方学这样从经典的、帝国主义的或地域的角度界定的某个‘领域’”。“另一方面,受传统东方学训练的学者和批评家完全有可能将自己从旧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脱出来”(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19页。)。
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在历史上一直过于自鸣得意,过于偏狭,对其方法和前提过于乐观自信,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因为在不得不对被其视为与自身相异质的地区采取一种绝对对立的立场的过程中,东方学没能与人类经验相认同,也没有将这一地区的经验视为人类经验。为此他要求东方学者要自觉地对自己的方法进行批评性细察。首先,对眼前的材料的直接感受。其次,对自己的方法和实践的不断自我审察,不断使自己的研究与材料相适应,而不是与教条和先见相适应。对人和社会不管是东方的还是非东方的研究最好放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中进行。所有这些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都能对所谓东方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并能矫正其偏蔽。讨论至此,赛义德相当乐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东方学的未来前景,他说:“从积极的角度而言,我确实相信今天的人文学科正在做出不懈的努力,以为当代学者们提供新的洞见、方法和观念,完全有可能不必再依赖东方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那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型观念”(注: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421页。)。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德里克对赛义德的关于“现代东方参与自身的东方化”这一观点极为赞赏,他进一步发挥了赛义德的这一观点,提出“东方人的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他说:“而且更加复杂的,是‘东方人的东方主义’的问题,,一方面,东/西方的区别,以及作为概念和实践的东方主义都缘起于欧洲,而东方主义这个术语也几乎完全被用来描写欧洲人对亚洲社会的态度,但是,这里我愿意指出,这个术语应该引申而用指亚洲人对亚洲的看法。用以说明将成为东方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的自我东方化的种种倾向”(注: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7页。)。历史上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是欧洲等西方人对亚洲等东方人的态度,这种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实际是西方人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东方人的东方主义”。所谓“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就是指东方人对自身的态度,是东方人的“自我东方化”或“自动东方化”。“东方主义是否仅仅是欧洲人的独立创造?或者它的出现预先假定了‘东方人’的同谋?”能否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这在德里克看来是理解东方主义及其在现代性中的位置的根本。德里克认为,“东方主义尽管在缘起和历史上维系于欧洲中心主义,但在某些基本方面却要求‘东方人’的参与才能合法化”。他说,如果没有“自我东方化”东方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德里克讨论“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他实际上是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东方人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德里克认为;民族主义一旦出现就超越时空,跨越这个民族所占据的疆域而消除一切差异,在时间上回溯到某一神秘的起源而抹掉过去不同瞬间的差异,这样,全部历史就变成了一部民族进化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特点成为民族的象征,而另一些与民族自我形象不相一致的特点则作为外来的非法入侵而被扫地出门。在这种换喻的还原理论中,民族主义与现己呈现民族规模的东方主义的文化主义方法存有许多共同之处。关于东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基曾经说过,“东方主义”在亚洲被制造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在霸权化的再现中融入他们的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思想中。他还认为,民族主义思想接受以东西方的区别为基础的同一种本质主义观念,接受由超验的研究主体所创造的同一种类型学(注:谢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德里克对帕沙·查特基的这一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并认为关于“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也许是在所谓亚洲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中东南亚“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德里克指出,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是所谓的儒学的复兴。与儒学复兴密切相关的杜维明试图把儒学变成一种全球哲学(与欧洲的基督教相媲美),可以移植任何地方。近年来,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来首相马哈蒂尔都加入了反对西方的“亚洲主义”的新的大合唱就后者的情况来说,其起点显然是伊斯兰教而不是儒学,这也是与以前的泛亚洲主义相一致的(注: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在德里克看来,虽然儒学复兴(和其他文化民族主义)也可以看作是本土文化反对欧美文化霸权的一种表达,但儒学的复兴、泛亚洲主义的兴起等东南亚文化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势必会走向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这种狭隘的文化民族的发展极为不利,制造出新的东西方对抗,而且还可能酿成东方民族的内部霸权。所以,德里克指出,“我们不必夸大自动东方化,及其关于其他现代性的主张在反对内外霸权的斗争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自动东方化最终将维持甚至巩固现存的权力形态”。他说,虽然自我东方化、“自动本质化可用来动员反对‘西方’统治的事业;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通过内化东方主义的历史前提而巩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同时,它也通过压制国内的差异而促进了内部霸权”(注: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才在一次关于文化的访谈中强调,“自我东方可以大胆说一句,我们今天‘亚洲人’的东方主义问题比欧美人更为严重”(注:谢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作为当代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员,德里克对“东方主义”的批评显然具有“极端化”的倾向,比如他对新儒学的批判、对所谓“亚洲主义”的批判等在某些方面是我们所不能接受和同意的,他虽然有时也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反霸权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但这种肯定却是蜻蜓点水般的,他对文化民族主义更多的还是谴责和批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狭隘性和强调本民族自身力量的膨胀性等。他把东方社会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东方人的东方主义”相等同,把文化民族主义完全作为“东方人的东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看待的这一认识,在我们看来,仍然值得商榷。但不管怎样,德里克对“东方人的东方主义”的分析和揭示对我们理解赛义德提出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一命题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