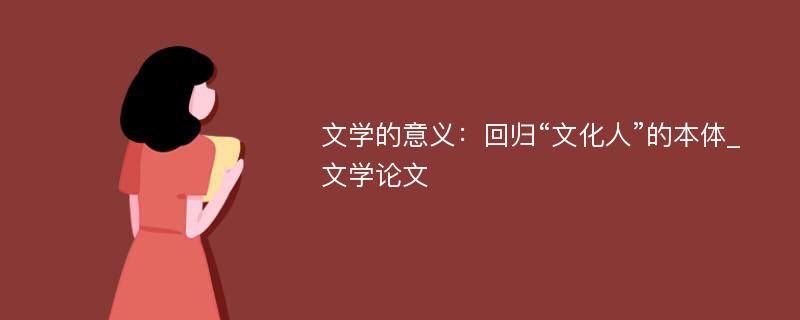
文学的意义:回归“文化人”本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人论文,本体论文,意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又是人学,因此,评价文学作品,自然而然就离不开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文化是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的集合,而文学却是反映和揭示人类的这种生存状态文化的。因此,文学意义的消解或丧失,不在于文学形式本身,而在于文学一天比一天走向文化性。文学文化性的引入,摆脱了文学单纯艺术性的形式指归,它使文学形式的目的性得到了正确矫正,也使作家们意识到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表现一般的人类文化生活,不仅在于表现一般的人生,而是要表现特定文化背景下,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文化人,而非别的什么人的悲欢离合命运。文学的文化性,使我们分析文学作品时,更加深入细致地观照到“人”作为一个“文化人”,与社会、历史和自然等因素之间的文化关系,从而对形形色色的作品形象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作出更加准确的阐释和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之所以能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行,正得益于文学作品文化性的充溢。前所未遇的开放性时代,为作家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机遇,作为文化个体,他们可以不受羁绊地用“文化”的眼光,观察我们所处的文化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文化社会中千姿百态的文化个体;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淋漓尽致地用“文化”这个复杂的艺术表现方式,塑造艺术形象,表达艺术思想。由于有了“文化”这面多棱镜,作家们对艺术形象的把握更加立体,更加血肉丰满;对文学主题的开掘更加全面深刻。正藉于此,80年代前后我国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势头。先是伤痕文学的突破,后是反思文学和新人文学的跟进,再以后,寻根文学在强化了文化人过去感文化心理的同时,开始将这种生命个体玩世的过去感升华到历史个体曾在过去感——即传统文化的高度。作家们试图从更加广阔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定位出现代中国文化人陷入重大社会悲剧中的深层文化原因。从此,我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文化小说、痞子小说、探索小说、新写实小说、陕军东征文学现象等文学群体一个接一个诞生。的确,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常的路。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笔者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20世纪下半期各阶段文学发展的文化思路,看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此辉煌的巨大飞跃。在对80年代各小说流派作了定量定性分析之后,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性,即回归“文化人”本体,是近年文学发展过程中,浸渍在小说作品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
一、文化寻根:文化人失去文化根性的文化困顿
从伤痕文学起步的新时期文学,经过反思文学的冷处理和新人文学的热处理升温,在80年代初,随着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逐渐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顿境地。由于这种“困顿”而导致的文化人文化心理的深度浮躁和迷惘,为后来寻根文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且提供了一种合理合法的现实理由。当时的情形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经过伤痕文学对自己文化心理上的文化创伤作了有效的文化理疗后,一点也没想到改革年代也同样会使人产生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新的文化创伤的产生,文化人文化心理断层上,新的文化苦恼的不断叠加和各种社会问题没完没了的积累,使得作家们不得不从民族集体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等诸文化因素中,寻找、考查、分析、解剖我们民族现代化之所以缓慢的文化历史缘由,找到阴滞我们民族前进的文化之根。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试图从文化病因上,找到治根固本的方法,为正确引导人民走向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文化思路。
韩少功对湘西楚文化原生状态的成功复述,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沈从文老先生所做的工作,他为人们认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提供了一种直观清晰的文化范式。丙崽的悲剧(《爸爸爸》),再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经常陷入一种人自体根本无法掌握、无法抗衡的文化境遇。丙崽的言行说明人类总是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话语支配下,完成着一次又一次无意义的文化循环,这种文化循环周期率似乎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文化法则。由于它,人类才在演进的历程中,血腥与美好相伴而行,野蛮与文明共存共生。我们先民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在湘西乃至许多地方,他们的文化血脉代代相因,衍化成了主宰我们这些后人集体和个人无意识思维的文化之根,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主宰我们无意识思维的民族文化劣根性,丙崽的形象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范例。
李杭育对葛川江流域吴越文化圈的“最后”揭示,旨在用“渔佬儿”这一职业的消亡,暗示人类在最终否定了大自然的同时,也必然否定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自己。“鲥鱼”的消失,从某种程度上言,体现了人类的进化法则,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最终将抛弃那些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认为那种“抛弃”实际也是一种文化退化的标志。退化与进化相互作用的文化法则,也许正是李杭育试图向人们说明的文化问题。福奎的悲剧则说明,非人性非理性的文化力量战胜了理性的文化人本体,是压抑在人类无意识文化活动中一种潜在的生命文化本能,一俟有合适的机遇,那从文化人自体魔瓶中释放出来的非理性魔鬼,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人类的文化理性打倒在地。当然,在此我们也应看到,“对岸那一溜街灯”,是福奎精神解放,获得自由,走向精神胜利的文化象征,它也是李杭育对我们的一种文化暗示。那灯,不正是一种文化希望,既昭示福奎,也昭示其它文化人继续前行。我们民族遇到的正是福奎所遇到的文化境遇。根,深植于黑暗与光明的沃土之中,而希望总是那么醒目,在远方闪烁。
寻根文学中,贾平凹的商州文化系列小说与李杭育有所不同。贾平凹的小说总是将自然的东西,当作一种文化氛围,一种达到某种文化目的的手段和藉口(而非目的),他对秦汉文化氛围下商州人文化生活状态的描述,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每一次社会变迁,都会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一种没完没了、恩恩怨怨的家族宗法斗争,至少参与变迁的相当一部分人都这么认为。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的科学性,浮躁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深刻的变革主题,而文化变革的主题下,却常常隐含着旧的东西还原自己的社会暗流和必然要求,这就是中国社会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演变成新皇帝代替旧皇帝、新宗族代替旧宗族这种文化悲剧的真正历史文化动因,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总是在原地踏步、周而复始如此循环的深层文化原因。新的东西总是旧的东西达到自己目的的文化手段,旧的力量通过新的力量,完成了自己愚昧和保守的文化对进步和文明的文化的巧妙征服,这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狡猾残酷的本质。愚昧经常将进步的文明扭曲成一种不真实的文化真理,文化和观念的进步却常常出乎意料地得出一个荒谬的结果,进步的要求在一定社会形势下,常常成为落后所找到的倒退历史的文化理由,这一切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畸型、保守、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文化诡辩的结果。
张承志的中亚草原文化系列小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探索。他将社会的两个文化点——城市和乡村,通过文化人(《黑骏马》)有效地联接在一起,利用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对文化人的潜移默化影响,指出现代都市文化和传统农牧业文化是造成现代人人格分裂的两种文化力量,受到这两种文化力量影响的文化人,在社会变革中,会不自觉地受到二者的撕扯和揪织。《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中,文化人之所以会有心理失衡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两种文化力量作用的缘故。结果,主人公们在走向草原和黄河的时候,就会有被传统道德文化力量淹没的危机;走向城市,则会有被传统文化遗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的确是由于传统文化根性过于顽固、影响太大的原因所致。
由此看来,寻根文学所潜藏的慌恐与浮躁的普遍文化情绪,实在是来自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它们的较量,促成了文化人文化心理困顿境地的形成。有根和无根的文化交织,使他们产生了进退维谷的文化烦恼。这,正是寻根文学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所在,它为我们塑造了一批陷入文化情感漩涡、失去了前进方向的文化人形象。
二、文化小说:文化人追求文化理性的适度迷惘
文化小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寻根活动。它是文化人从全面、综合、系统的理性角度,对文化寻根现象作以整体文化思考的文化标志。文化小说的意义在于使文化人打开了寻根的视域,它使文化人能从人类文化的高度,俯瞰自己,从而使文化人意识到,千丝万缕的多种文化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文化苦旅中的文化理性迷惘。
文化小说的优秀作品有这样几类:
阿城的知青部落文化系统小说,试图通过浓浓的儒、释、道文化氛围的刻意营造,表现文化人在先天性的文化压抑环境中,所能走的唯一道路。《孩子王》弥漫的是一种没有悲哀、没有喜悦、已经麻木了的文化悲苦,反叛亦无所谓,顺从也没什么,孩子们被政治愚弄了,好在他们自己不知道,当然那些极左的政治家也无意让他们知道,他们只要这些小和尚跟他们一起念政治经就行。《树王》肖疙瘩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像《孩子王》中的老杆儿一样,也走的是一条反叛道路,尽管,他的反叛不是靠文化,而是靠一种自体的淳朴天性。老杆儿的文化反叛已经失败了,肖疙瘩的体能反叛更是要失败的,虽然他曾当过侦察兵,但是,他是无法将那个政治理性社会侦察清楚的。现实中的物象“树王”,随着李立刀的起落倒坍了,支撑文化人本体“树王”肖疙瘩的信念也随之倒塌了。山上树王的死亡和人中树王肖疙瘩的死亡,象征着极左政治文化理性利斧肆虐摧残下,大自然与人类文化的双重死亡,人类的政治文化理性在毁灭了大自然之后,也必然会毁灭自然的对应物人自己。《孩子王》、《树王》告诉人们的是一种儒家式积极入世文化生活方式的失败,这种失败很彻底,不仅仅是肉体,而且触及灵魂。但是《棋王》则不一样了,王一生以棋为道,绝圣弃知,自得其乐,达到了一种物我两忘的文化境界。他采取的是道家式自觉出世的文化生活方式,在精神上他胜利了,自由了,他实现了自我文化人格上的“内圣”。至于“外王”与否,与他无关。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他自认为活得充实,活得逍遥,由于此,他躲开了灵魂的毁灭,又逃脱了肉体的死亡,他走的这条文化道路是那种年月文化人所能走的唯一一条自我文化救生之路。
王安忆的《小鲍庄》是文化小说中最具儒家味的一篇。全文以“仁义”为主线。首先,作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仁义小鲍庄”的文化环境,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原初文化性质的文化氛围。其次,作者告诉人们,仁义小鲍庄生活着一群仁义之人,这就为后来作者展开小鲍庄人的仁义之举埋下了伏笔。第三,由于以上原因,很自然地发生了捞渣救鲍五爷的仁义之事,进而,作者将此举与大禹治水联系在一起,完成了一种远古救生神话与现代救生神话的文化缝隙弥合。两种不同的文化时代,却有着一个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仁义”成了小鲍庄人亘古不变的道德法则和英雄主题。笔者以为,应将王安忆的儒家味小说与当时文化界倡导的“复兴儒学传统”的现代新儒家思潮联系起来,二者共同揭示出了这样一个文化事实,在一个道德日益堕落、良知日以泯灭的社会中,要实现现代化这个大业,我们民族只有恢复儒学的“仁义”传统,才能创造出我们民族的现代英雄文化神话。
莫言的具有齐鲁文化特色的《红高粱》家族系列文化小说,开凿了文化小说的另一种艺术形式。余占鳌集动物性、人性、匪性、英雄性为一身的复杂性格及其传奇般的成长经历,显示出了人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全部文化旅程,也揭示了人性、民族性格中一些复杂的文化层面。这多少给人一些启示,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代代繁衍的民族活力,正得益于那多姿多彩、神奇浪漫、复杂的民族文化性格。
马原和扎西达娃的作品,为我们挖掘出了西藏高原佛教文化圈中的某些文化隐秘,主人公潜意识的时空错位,灵魂与肉体的逃逸与隐遁,反映出藏族这个古老的种族与众不同、诡秘莫测的民族文化个性。生者与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对话,人的生存环境可以任意切割组合,容易使人产生人世无常的宿命论念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可以说是一篇荒诞小说。荒诞的主人公,荒诞的文化行为,得出一种荒谬的文化结果。神秘的文化人及其实践的神秘性,预言着人类在大自然中荒诞的、滑稽的、不可知的文化结局。作者有意说明,人类正是在那荒诞的岁月、荒诞的空间中辛勤跋涉的。《西海无帆船》则是人类毁灭大自然,进而又毁灭掉自身的文化寓言。叙述的神秘味、视角的怪异味、意境的混乱感,这就是马原和扎西达娃作品给人的整体印象。但是,细细究来,我们却不难发现,他们的作品,神秘中有清晰,人神鬼共存并发生关系这点是清晰的;混乱中有秩序,人类按神的或大自然的法则确定的方向发展着,而人类自己却还不知道。这些近乎于矛盾的文学内容,实际上呈现的是人世命运不确定的文化怀疑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既缘于古老神秘的文化传统过于庞大,使人产生了对这种“庞大”文化的敬畏,又缘于人类对自己、对大自然的不信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精神信念危机。由此,文化人生活在现代生活中,却对现代文明视而不见;生活在古老持久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却对传统文化茫然不知所措。从这不难看出,对于现代文明的漠视、对于传统文化的盲目敬畏和认同,也是阻滞我们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原因。
总之,文化小说的探索者通过儒释道文化氛围下文化人生命意志无意识的冲撞,袒露了新的历史时期集体文化心理的适度文化迷惘。这种迷惘由于既表现为对旧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文化传统、文化影响所进行的适度文化探询和文化情感观照,又表现为对新的文化环境、氛围、类型和观念的适度的怀疑和不信任,因而,很容易地使文化人陷入了失路英雄穷途而哭的文化悲伤。文化迷惘是时代发展文化积淀到一定程度,文化人集体与个体文化心理的必然产物。它在文化小说中的自然流露,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从形而上的理性层次,对我们民族的原初文化形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解剖。它会使我们从原有的文化迷谷中,找到现代文化人前进的文化突破口。当然,它也注定可能有一部分文化人钻进了为文化而文化的死胡同,消融了自己的文学使命与文化生命。
三、先锋文学:文化人寻求文化出路的种种尝试
如果说,寻根文学、文化小说是从历史性主题话语中寻找现代性文化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嗣后产生的探索小说、痞子小说、新写实小说,则是从前卫艺术的先锋视角和文学话语中,对以前的文学类型进行了全面的颠覆、消解和突破。
1.探索小说:指向文化悟性的多元思索。探索文学肇始于80年代初中国文坛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规模译介和认同,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可视为其开端。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学探索,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远较后来的探索小说要幼稚简单一些。意识流小说的贡献在于作家们实现对极左政治理性思维的全面文化突围,并且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着力挖掘生命意识的文化心理涌动与跳跃,着力挖掘生命个体命运在与民族集体文化命运的冲撞中,心灵深处所产生的某些文化隐秘。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处在我国社会文化解冻末期客观小说向主观文学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这就决定他们的作品必然有意疏离70年代的政治功利型文学——即“主题先行论”文学模式,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又无意深入西方文学的现代派图式,无意于步其后尘,他们的作品中较少梦想、幻想、错觉、癔语、甚至某些变态心理就是明证,这种情况恰恰与后来的探索小说相反。
探索小说的第二阶段是作家们对荒诞小说、垮掉一代小说的依附和认同。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被认为是此阶段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中国现代派小说。一群不安分守己的艺术学院学生,对传统经院式教育玩世不恭、离经叛道式的文化集体反抗,通过喜剧性的手法被揭示出来。《浪漫的黑炮》是张贤亮小说中的一篇荒诞小说,一只黑炮的丢失,引出了一场滑稽可笑、荒唐不堪的风波和闹剧,人们心灵上所覆盖的文化阴影通过艺术变形的手法,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彻底的表现。这样,作者在曲折地反映出那个荒谬不堪的文化时代的同时,也表露出文化人对那些极左政治文化权威既蔑视、又怀疑、也无奈的不信任感。荒诞小说正是用怪异、怪诞的艺术形式,挖掘出一些严肃深刻的文化主题。由于此,它也就落下了用喜剧性的表现手法表达严肃的社会问题的美名,它的艺术探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探索小说的第三阶段是一批年轻作家对象征主义文学方式的引进和开拓。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染的《世纪病》等作品,在完成了对市井文化的艺术还原后,也完成了对当代文化人市井文化心态的还原。这一阶段的探索文学作品语言粗俚,极尽调侃之能事,道出了一部分文化人不安分守己但又无法反抗现实的文化浪子心理,这些文化人因觉悟而麻木,因不满而堕落,强烈的文化觉悟与行为反差,形成了他们中国味十足的文化荒原心理。
探索小说的最后阶段是作家们对结构主义、符号学、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的钟情和移植。余华和格非是玩结构和符号的好手,《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褐色鸟群》,还有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把主人公的命运幻化为玻璃窗户上的蒙蒙雨,明晰而模糊。这类作品情节看似简单,实则扑朔迷离,其结构回环较多,但却方式单一,人物形象皆为文本符号,主题意义的确定和表达飘忽不定,且语焉不详。陌生化、神秘化是这一阶段探索小说的主要文学特征,由是本阶段的文学作品无端生出几许文化的忧伤、迷惘气息。
2.痞子小说:拯救文化知性的潇洒堕落。繁华的社会势必也会污染一批浮夸的心灵,王朔的的流氓痞子系列文化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放浪形骸、大胆妄为的社会流氓痞子形象。在作者笔下,主人公要么《一点正经也没有》,要么《玩的就是心跳》,要么《过把瘾就死》,要么叫人《千万别把我当人》,简直是一群《玩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是王朔系列痞子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作品主人公迷途知返,良知发现,完成了由堕落到觉醒再到行动的自我文化道德赎救。它告诉作家、评论家和读者,不要将自己关注的目光总停留于普通的社会人和正常文化人身上,而是应多关注一下那些人,那些称之为社会流氓和痞子的人。它还告诉我们,隐含在这些社会痞子人物背后的重大社会问题是,应怎样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去拯救那些潇洒堕落者的文化知性,我们应用怎样的文化手段,触动或唤醒潜藏在他们意识深处的文化良知。
3.新写实小说:解剖文化习性的慷慨悲歌。新写实的最大艺术特点就是写实,它“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苏童的系列传统女性小说,用一种凝固不变的叙事腔调,典雅哀婉地讲述了发生在江南那块热土上,那些深宅大院里生活女性的种种悲剧故事。与苏童小说风格相反,刘震云、池莉等人的系列公务员小说,不以历史往事、历史陈迹为自己小说的文化背景,而是以现实社会生活为自己作品的文化视域,他们采用一种不褒不贬、不夸张不修饰的零度语言,流水帐式地叙述出“单位”——这个社会文化结构单元中所发生的一些凡人俗事,通过对那些琐碎的生活现象的记述,他们揭示出了现实人生中人们普遍遭遇过的那种社会困境。刘震云和池莉的小说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深厚文化传统的社会里,一切似乎早已约定俗成,巨大的文化陋习惯性,已将人们庸俗得不能再庸俗的文化行为,衍化成了一种身不由己的落后野蛮的抑或是愚昧的潜在社会本能,一俟人进入社会,那些可怕的文化陋习就发挥作用,并且毫不留情地将人的本性吞噬掉,很少有人能逃脱这种落后文化习惯的约定和规范。由于新写实小说是如此严格地写实,将作家和作品主人公的情感冷缩为零,因此,零度状态下所产生的种种人生悲剧,更容易使我们体察到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文化悲苦。这是一种不用声音表述就能震撼人心的慷慨悲歌,因为无语,它在探索文学的作品系列群体中,才显得有些孤傲寡合和与众不同。
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文化性探索是有益的,它使我们明白,文学意义的存在与丧失,的确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也告诉我们,文化性充溢于文学全体,文化性囊括了一切文学的属性,因为有了文化性,文学才具有了别一种价值意义,文学探索才具有了别一番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