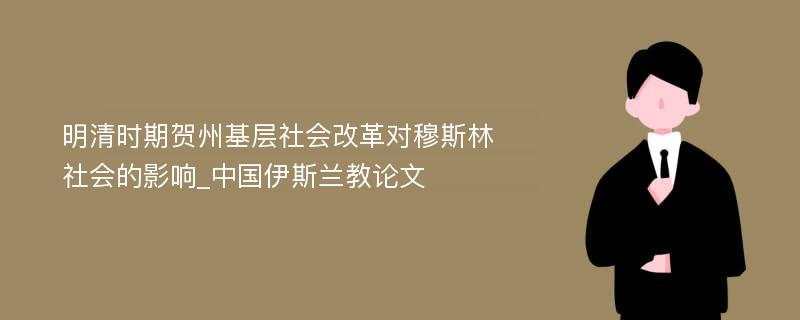
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变革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社会论文,明清论文,基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中国西北伊斯兰教派与门宦方面的论著非常之多,成果也十分丰厚,但仍有未尽之言,如关于教派与门宦何以大多创建于明清之际河州的问题,多数论著往往以人口相对优势、生活贫困、苏菲教团传入以及经堂教育影响等为解答,而对于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的变革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正是由于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自身的一系列变革,才使得各方面的因素在河州产生了更适合教派与门宦创建的环境。那么,明清之际的河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又对河州穆斯林社会以及河州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正是从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中,试图探求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变革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进而从河州穆斯林社会的变迁中为中国西北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创建提供一个历史的诠释。
一、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的变革
明代河州在成化十年(1474)前基本属河州军民指挥使司(河州卫)管辖,此时的河州卫是一个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成化十年,巡抚督御史马文升奏改河州卫原治四十五里为河州,军民分治,州隶临洮府,卫仍为军民指挥使司①。与明代河州的军政机构相比,明代河州的基层社区组织相对稳定,大体由三大类组成:一是里甲,二是土司,三是屯寨。而这三种组织中里甲制的革除、土司势力的削弱以及穆斯林掌教参与基层社区管理应当是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区中最引人瞩目的变革。
(一)河州里甲组织的革除
明代河州里甲组织,据嘉靖《河州志》卷2《地理志·里廓》载:“原额四十五里。嘉靖丙戌,知州张宗儒因人丁消乏,奏攒三十一里”。里设里长,里下为甲,甲设甲首,这与内地里甲制并无二致,但内地里长是择老成者为之,不拿俸禄,不世袭,而明代河州里甲制却保留着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里长、甲首的世代相袭,具有浓厚的部落酋长性质。这一点在康熙《河州志》王全臣呈报于清廷的“详文”中有明确记载,其云:“此旧俗相沿,有里长户、甲首户等名色。里长户世为里长,甲首户世为甲首。其甲首户悉听里长管辖”②。明代河州基层组织中不仅里长、甲首可以世代相袭,而且中下层军官、军户,以及土司、教坊掌教等均为世袭,所以说世袭是明代河州基层组织的一大鲜明的特征,而里长、甲首的世袭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
河州穆斯林自元代大量迁入后,分布在河州四乡,他们或聚族而居,如撒拉族;或散落在番寨部落中,如河州珍珠族韩土司属下的他班的族中有“土户六户,回民七户”;马圈岭族中有“回民八户”;扎麻族中有佃户“回民十三户”③;但更多的则是编户在里甲之中,与当地各民族交错居住在一起。
明代河州回族居住的里甲,由于穆斯林掌教的存在,在社区权力构成上存在着二元结构,即社区权力与宗教权力,而国家权力由于世袭里甲的阻隔,很难向县以下的乡村纵深发展,乡村社区基本上处于国家权力的真空状态。而明代河州伊斯兰教在遵从苏菲派的各家门宦尚未创建之前,又是一个看似统一,实际却十分松散的宗教体系。各地实行的是单一教坊制,一个教坊,一个清真寺,教坊之间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各自独立,各行其教。因此,当这种松散的教坊组织面对着一群独断专行、欺上瞒下、骄横跋扈的里长、甲首时,其权力的二元结构则呈现出极其的不对称。
清朝河州知州王全臣针对腐朽落后的里甲制,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保甲制、创建会社制、革除里甲制。康熙《河州志》卷2《田赋》载:“全臣筹画再三,乃令四乡先立保甲、会社,或二、二十村庄连为一会,每会择其老成者举总练一人,社长或三、四人,饬令稽查盗贼,巡警地方,迨居民成听约束矣”④。清代河州保甲的职责是“立保甲以查地亩……地亩即清,乃革除里长”⑤。虽然在清查地亩之初,总练、社长等亦参与其中,但“不过权宜之计”,其主要职责仍然是“稽查盗贼,巡警地方,迨居民咸听约束矣”。王全臣新建的保甲究竟有多少,尚不得而知,但变革后的河州共有99会,每会下辖若干社,大会有辖12社者,小会仅有2社⑥。会的首领为总练,社的首领为社长。会社原本是明初以米普遍实行于北方民间的互助组织⑦,在这里被王全臣加以改造,可谓是一大创举。
世袭里甲制的最大弊端在于封闭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而会社、保甲制的最大功绩恰恰在于开放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王全臣创建的会社、保甲制革除了河州基层组织的世袭制,打破了基层首领们网织多年、一手遮天的传统权力结构,使得河州基层社区组织从传统的羁縻制过渡到国家化的基层社区组织,而国家权力正是借助于这一新的基层社区组织得以顺利地进入社区。国家权力进入河州基层社区后,基层社区中国家权力的真空状态基本结束,新的权力结构随之形成,这就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社区权力、宗教权力的三元结构。新的三元权力结构较之里甲制下那种封闭、半独立状态的二元权力结构更具开放性,而百姓对于传统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大为减弱,其所受到的剥削和欺榨大为减轻,正所谓“革除里甲,令民自封投柜”,“百姓之输纳,争先恐后”,“欢然如拨云雾而覩天日矣”⑧。康熙《河州志》在评价王全臣之政绩时刻意强调:“夫后之见志者,以庶事之中其最者,清地均粮,革除里役而已”⑨。王全臣率先并彻底地在河州地区进行了变革,而正是这些变革为清初河州伊斯兰教派、门宦的创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土司势力的衰弱
清初,由于统治者集中全力与南明政权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余部作战,对甘青一带少数民族无暇顾及,在政治设置方面亦无多大变更。甘青各家土司照旧任职承袭,一如明朝。这种局面维持了八十年左右,到雍正时发生了变化。雍正即位之初,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乘朝廷变故,发动武装反清斗争。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打败罗卜藏丹津,并以《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为基本准则,开始在甘青藏族、撒拉族中实施改革,这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部分藏族以及撒拉族中确立千百户、设置乡约。河州部分藏族部落确立千百户、设置乡约至迟在雍正四年就已实施。雍正三年十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议:“凡切近河、洮、岷州内地番人与百姓杂处者,向通汉语。自归诚后已令改换内地服色,毋庸设立土千百户,但就其原管番目,委充乡约、里长,令催收赋科。久则化番为汉,悉作边地良民。其去州县卫所较远之部落,现在有地耕种,令按亩纳粮”⑩。此奏议得到雍正皇帝批准。翌年,青海都统、办事大臣达鼐、西宁总兵官周开捷等在河、洮等处招徕安插番人,“遵照部议,委以千百户、乡约,并饬地方营汛官弁会查户口田地,定其赋额”(11)。此后,河州境内各中马番族除珍珠族等少数未设乡约外,大多设有乡约,如鸿化、灵藏、癿藏、沙马、老鸦等族(12)。
在强化对河州中马番族管理的同时,对撒拉族的管理体制也相应地作了一系列调整和加强,主要有:“查田定赋”和封授两个撒拉族土千户。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曰:“至撒喇回民,虽系土目韩炳、韩大用所辖,而系外委土司,职守轻微,回民奸悍者多不服。今请将韩炳、韩大用二人,各给与土千户号纸,令分辖回族,则凡不法回民,既畏营员,又见韩炳等系奉旨设立之土职,自必共相惊惕。将来编查户口、输纳钱粮等事,亦易办理”(13)。奏折上报,清廷准奏,同年六月,兵部正式封授韩大用、韩炳为“保安堡撒喇土千户”。
清政府对于甘青土司调整后,国家权力虽然并未直接深入到藏族、撒拉族部落中,但却极大地削弱了土司权力,使得土司对属民的统治明显松弛。明末清初之际撒拉族中之所以能够出现众多传教者的身影,以及苏四十三等人甚至提出打倒土司的口号,均反映出土司难以统御属民的事实。
(三)穆斯林掌教参与基层社区管理
穆斯林掌教参与基层社区管理是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政府为强化对甘青少数民族管理而逐步采取的措施之一。河州番族设置乡约后不久,清政府即在甘肃回族中进行了类似设置。《清世宗实录》卷112雍正九年刑部覆议甘肃巡抚许容条奏曰:“回民居住之处,嗣后请令地方官备造册籍,印给门牌,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除设立牌头、甲长、保正外,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人户多者,再选一人为副,不时稽查,所管回民一年之内并无匪盗等事者,令地方官酌给花红,以示鼓励。应如所请,从之”。许容条奏中的有些内容早已在河州实行,如保甲、会社制等,有些却在刑部覆议后实施。以掌教稽查所管回民有无匪盗等事宜,实际上是将穆斯林社区“稽查盗贼,巡警地方,迨居民咸听约束矣”的职能从总练、社长名下部分地转移到掌教一边。掌教虽不是乡约,但清政府试图以掌教承担乡约职能、最终过渡为乡约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反清斗争后,清政府在河州穆斯林社区普遍推行乡约制,正是这一意图的纵深与强化。
同样是加强管理,但在河州中马番族中设置乡约与在河州穆斯林社区中以掌教稽查所管回民有无匪盗等事宜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却截然不同。前者显示的是清政府借助世俗力量对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土司与宗教势力的打压,其目的是加速政教分离。后者则是清政府借助非世俗力量,提升穆斯林掌教地位,发挥伊斯兰教的教化作用,它显示的是清初统治者给予河州伊斯兰教以一定程度上的重视。
清初统治者之所以对河州穆斯林掌教如此重视,是基于如下考虑:1.明朝对于河州穆斯林的管理是以羁縻管理为主,直接管理为辅;以里甲、土司管理为主,宗教管理为辅;清朝初年,随着里甲的革除、土司势力的衰退,清朝政府逐步从羁縻管理向直接管理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穆斯林掌教在穆斯林社区管理中的作用渐渐凸现出来,其号召力越来越大,其被穆斯林认可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世俗政权以外的伊斯兰教,并将依靠的重点放在掌教,而不是里甲、土司身上。应当说这是清政府通过掌教第一次将统治触角直接深入到河州穆斯林社会之中,对于长期处于羁縻状态下的大多数河州穆斯林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触动。2.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穆斯林社区中的宗族职能十分弱化,大多被宗教职能所取代,因此,政府利用惯以凭借的传统宗族势力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基础基本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穆斯林社会,故清政府只能以穆斯林掌教扮演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推行教化的重要角色。3.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使得传统儒学对穆斯林基层社区的渗透难以深入,政府通过文化上的相互渗透以整合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区的途径受到阻碍,同时,地方共同体的宗教神明与国家认可的正统神明也无法对称,难以形成以国家正统规范神明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祭祀圈,从而难以在文化上与国家权力达到高度一致,因此,只有在两种文化圈中寻找出一个合适的载体才能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地方社区,而河州穆斯林掌教作为宗教与地方绅士的代表恰恰是担负这一职责的最佳人选。4.如何处理好穆斯林基层社区组织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始终是河州基层社区的一大难题,而河州穆斯林掌教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充当着宗教与基层社区的桥梁与调节器,是两者达到统一的重要中介,因此,河州穆斯林掌教的影响与作用在基层社区的构建中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赋予穆斯林掌教以一定的社区行政管理职能,这在河州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清初统治者已清楚地看到伊斯兰教在河州穆斯林中的巨大影响,并迈出了第一步。与明代将伊斯兰教排斥在基层社区管理之外相比,这是清初统治者的一大进步。它清晰地表明清初统治者对于如何治理甘青穆斯林基层社区的理念以及围绕这一理念而形成的一整套治理政策的初步建立,这就是将宗教管理引入社区管理,以行政管理与宗教管理相结合,共同构建河州穆斯林社区管理体系。在这一管理体系中,掌教与保正、总练一道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它既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又与政教合一相去甚远,是清初统治者在河州地区创建的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纵观有清一代,统治者虽然在对待穆斯林政策上有过多次调整,但在如何治理穆斯林基层社区的政策上却始终坚持着这一具有特色的管理理念。
二、河州基层社会的变革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设立保甲制、创建会社制、削弱土司势力以及以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稽查所管回民社区有无匪盗等事宜,虽然仅仅是一些基层社区的变革,但它为河州穆斯林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新的穆斯林基层社区的建立,为河州穆斯林的交往铲除了藩篱
明代河州穆斯林社区中的里甲是一个封闭性极强的乡村组织,在这一组织中,里长的权力因世袭而被高度强化。与此相应的是,明代河州穆斯林社区中的教坊也是一个世袭掌教制下的封闭性极强的宗教组织。教坊中的穆斯林以清真寺为中心,以自然村落为活动范围,教坊与教坊之间、不同教坊中的穆斯林之间很少往来,不存在组织上的联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固然有伊斯兰教教坊制度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半部落化的里甲组织,以及来自该组织中行政权力的强力束缚极大地阻碍了这种交往。中国两北伊斯兰教从教坊制转变到门宦制大多经历了一个非世袭的过渡,如在早期伊斯兰教门宦创始人马宗生、马守贞、祁静一、马来迟、鲜美珍、马明心等身上,我们很难看到“始传者之子孙世世为掌教”的宗教世家背景,但最终均过渡到了道统传系。完成这一过渡需要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有两点必不可缺:一是世袭教坊制的废除,二是穆斯林有自由选择阿訇的权力。一般认为,明末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使得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但实际上,经堂教育只是在废除教坊世袭的形式上发挥了出色的作用,而对于穆斯林有权自由选择阿訇的问题,经堂教育的影响十分有限。就明末清初河州穆斯林而言,真正解决穆斯林有权自由选择阿訇的问题,主要应归功于新三元权力结构下保甲、会社制的建立。保甲、会社制度建立后,世袭、封闭、保守、半部落化的里甲组织被打破,新的穆斯林基层社区的建立,为河州穆斯林之间的交往铲除了藩篱。穆斯林所受到的来自社区权力的强力打压、羁绊与种种限制大为减弱。此时期河州穆斯林之间的交往空前活跃,各教坊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掌教的活动比以往更具流动性。穆斯林可以走村串乡寻求贤师圣德,掌教亦可以跨府越县传经布教,而这一切是受到国家权力保护的,如乾隆十二年,河州回民马应焕因不满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与老教争夺教徒遂进京向官府表达了自己的愤恨与担忧,官府非但没有禁止花寺门宦的传教活动,反而将马应焕“拟充军”。在官府的支持下,“马来迟与其子国宝遂往来行教。韩哈济者,撒拉十二工之总掌教也,师事之。于是十二工皆前开之教矣”。这表明国家权力对于破除河州穆斯林教坊之间的藩篱,扩大穆斯林之间的交往以及所谓“异端”、“邪教”都给予了积极有力的正面支持。同样,当马来迟与马明心在循化因传教争夺教徒而发生冲突之前期,清政府亦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对各门宦的传教权力给予了平等的认可,并“饬令撒拉尔十二工各举一人充当掌教,其新寺三座分开礼拜,以杜争端”、(14)。马通先生《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载,据1950年临夏社会调查,清康、乾以来河州穆斯林朝觐者年年都有,每批十多人,甚至二三十人,有男有女。仅八坊、阳哇山、癿藏、何家和东乡等地穆斯林就有百余人朝过觐,有“哈知”称号(15)。清代河州地区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穆斯林得以前往麦加朝觐,固然有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的因素(16),但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仅仅是促成清代河州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间接原因,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保甲、会社制的建立使得河州穆斯林对内、对外的交往相对自由。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持,正是由丁保甲、会社制的建立,才使河州穆斯林拥有更多的传教与拜教的自由。而相对自由的传经布教和相对自由的求师拜教,恰恰是伊斯兰教派门宦得以创建的十分必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当河州穆斯林拥有相对自由选择阿訇的权力时,它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清真寺对阿訇的选聘,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导致了河州伊斯兰教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对于河州伊斯兰教的学术交流,以及伊斯兰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清朝初年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活动中心之所以能够从长安转移到河州,这与当地伊斯兰教具有宽松而热烈的学术环境和众多拥有相对自由选择阿訇权力的教徒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讲,清初伊斯兰教派门宦对河州穆斯林社会所进行的重新整合,正是在基层组织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没有基层组织的变革,河州伊斯兰教派门宦的创建是很难想象的。
(二)穆斯林掌教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使得河州穆斯林社区出现了半职业化的管理阶层,河州穆斯林掌教的地位因此大幅提升
雍正九年,清政府在河州实施“以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后,这部分掌教与穆斯林社区中的保正、总练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半职业化的穆斯林基层社区的管理阶层。我们这里之所以将其定性为半职业化穆斯林基层社区的管理阶层,原因在于:从政治上讲,他们虽系管理者,但仅获得准官方资格,尚未跻身于清代正式的官僚体系之中,仅仅由政府发证认可。从职业上讲,掌教仍然以宗教职业为主,稽查所管回民有无匪盗等事宜只是兼职,并且是与总练共同执掌这一职能。在保正、总练与兼职掌教中,后者的政治色彩最淡。从职业报酬讲,保正、总练只获得部分报酬,另一部分报酬还得靠自己从事劳动或从其他方面获得,而掌教甚至连部分报酬都不享受,他的经济来源主要得力于清真寺的支持。从工作时间讲,他们只是将部分时间用于公务,其他时间或从事劳动,或从事宗教活动。而我们之所以将这些赋予了部分行政职能的掌教与穆斯林社区中的保正、总练称之为新的管理阶层,是因为这一管理阶层已基本脱离了世袭的羁縻性质,正在向国家化、社区化、民族化的管理阶层演变。
河州新的半职业化穆斯林管理阶层虽然成长于河州穆斯林基层社区,其活动范围也在社区之内,但对他们的评价以及对他们的任命与考核权却不在社区,而是在政府手里;他们的工作内容是由国家赋予的,被列入政府工作日程;他们享有政府的部分津贴和政府给予的一部分特权,如王全臣在计算赋税额度时就曾提到:“通盘合算,除绅衿享优免外,每粮一升派银五分”(17)。所有这些使得这一半职业化的穆斯林管理阶层因此带有更强烈的官方色彩,而所谓国家权力得以顺利进入穆斯林基层社区,正是借助于这些更具强烈官方色彩的半职业化管理阶层之手实现的,但同时正是由于国家权力是借助于这些半职业化管理阶层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国家权力进入河州穆斯林社区的有限性。
在河州穆斯林基层社区,掌教被国家权力赋予一定的行政职能后,便具备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辖区内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是穆斯林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另一方面他又与总练一道负责稽查所管同民社区有无匪盗等事宜,成为国家公权在穆斯林社区的代表。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使得掌教这一半职业化管理岗位在穆斯林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掌教在河州穆斯林社区中也因此具有更大的影响,其号召力有时甚至超过保正与总练。所以说,国家权力的进入构成了河州穆斯林掌教地位提高的前提,而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力的结合又为河州穆斯林掌教地位的大幅提高提供了上升通道。
河州穆斯林掌教地位的大幅提升对于河州穆斯林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明清之际的河州,穆斯林民族经济、人口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必然要构建民族化的宗教组织联系。教坊虽然也是民族化的宗教组织,但它的水平很低,影响范围十分狭小,内部也缺乏密切的组织联系,因此,河州回族社会的组织化,在宗教上必然表现为突破教防制。突破教防制除了保甲、会社制的建立外,更需要新的宗教力量和期盼有权威和号召力的经师出现,而“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恰恰为在河州穆斯林基层社区中建构这种新的宗教力量,以及有权威和号召力的经师出现提供了最佳人选。
康熙年间,河州穆斯林掌教地位的提高,极大地活跃了宗教活动,丰富了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提高了清真寺在回族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带动了河湟一代穆斯林的交往。有学者曾将清真寺在回族中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增强,以及伊斯兰教学术活动的相当活跃作为伊斯兰门宦创建的前提条件之一(18),是不无道理的。而此时期河湟一代伊斯兰教门宦名下的教徒动辄数万乃至一二十万,也恰恰为河州穆斯林掌教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从这一点讲,河州穆斯林学教地位的提高,为伊斯兰教在河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时间,为经学教义的自由交流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氛围,而这样宽松的学术氛围对于西北伊斯兰教派、门宦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三)明清之际河州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催生了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
在讨论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的身份。在明清之际的河州穆斯林中,有怎样的资格才算是知识阶层?按照传统规矩,至少得考取生员,有了功名者才可以跻身知识阶层。但明清之际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并非如此。河州地处中国西北边荒,土地贫瘠,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更是瞠乎其后。观嘉靖《河州志》,自洪武至嘉靖末近二百年间,河州考中的进士仅五人(19),且多为江南戍边后裔(20)。清代封疆大吏左宗棠曾如此评述说:甘宁青地区“汉蒙回番杂处其间,谣俗异宜,习尚各别。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创或因,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然而,上述所指仅限于明清时期河州的汉族,此时期河州穆斯林的文化与汉文化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即非主流文化特征。明清时期河州穆斯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其通经达儒的水平不仅远不如内地,即使在本地也略逊于当地的汉族,鲜有科举入仕者。所以,明清之际河州穆斯林知识分子中虽然也有一些汉文化修养相当不错的,如祁静一等,但他们并不以科举进士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在经堂,而不是学堂。科举进士在河州伊斯兰文化中并不被看重。因此,所谓明清之际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应当是指具有一定伊斯兰经学修养的群体。
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出现于明清之际,其标志性事件应当是世袭教坊制的被取代。教坊制下的经师是通过口传心授培养出来的,他们分散在各自教区内,互不往来,对社区产生的影响有限,故这些人只能是具备了宗教知识的个体,还称不上是一个知识阶层。明清之际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的出现有两大原因,经堂教育的倡兴是其产生的外部原因。经堂教育固然培养了众多职业宗教人员,但如果世袭教坊制难以废除,则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职业宗教人员很难被教坊聘用,因此,世袭教坊制的废除与否便成为新的穆斯林知识阶层能否形成的内部原因。在河州,保甲、会社制度建立,掌教普遍参与穆斯林社区行政管理后,相对自由的传经布教和相对自由的求师拜教成为可能,而世袭教坊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新的掌教聘用制所取代。所以说河州保甲、会社制的建立是催生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的内部原因,而两者结合,为当地造就了一大批值得尊敬的伊斯兰教名师、学者。
明清之际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脱离了主流文化后,其官方认同的仕途也因此被阻断,其政治地位很难伴随政治与文化的运动而在社区以外有所上升,但其经济地位却因宗教活动而呈现出强烈向上流动的趋势,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正是由此走向富裕阶层,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交替消长,当视作明清之际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的基本模式。
经受过经堂教育的河州穆斯林知识分子大量回归社区后,充任了职业宗教者或社区半职业化的管理者。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都成长为新兴的社区精英,少数人甚至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精英。大量穆斯林知识分子进入社区,为穆斯林基层社区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一,穆斯林知识分子充任社区半职业化管理者,这对于普遍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其二,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基层社区的影响,为社区带来了极强的凝聚力。其三,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大量回归,为普及伊斯兰教,推动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四,西北伊斯兰教派门宦的创建与河州穆斯林知识分子积极的创教活动是分不开的,其功绩是有目共睹的。清代初期苏菲学派之所以能够在河湟一带广泛传播,正是这些穆斯林知识分子长期卓绝的传教活动的结果。从这一点讲,明清之际河州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以及经堂教育的倡兴,催生了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而河州穆斯林知识阶层的形成又成为西北伊斯兰教派门宦创建的关键因素之一。
注释:
① 《明宪宗实录》卷123;[嘉靖]吴桢:《河州志》卷1《地理志》。
② [康熙]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③ [乾隆]龚景瀚:《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
④ [康熙]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⑤ [康熙]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⑥ 《续修导河县志》卷2《地理志》。河州在民国初曾一度为导河县,故《续修导河县志》亦为河州地方志之一种;《续修导河县志》卷2《地理志》载:“自前清光绪四十六年丁亥,知州仲山王公清丈地亩后,改村里为会社”。按光绪年号只有三十四年,没有四十六年,故此处光绪四十六年乃康熙四十六年之误。
⑦ 《明世宗实录》卷99嘉靖八年、卷239嘉靖十九年七月戊戌;万历《大明会典》卷20《户部·读法》、卷22《预备仓》;王廷相:《俊川奏议集》卷3《乞行义仓疏》,《四库存目·集部》第53册,第466—471页;[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弘文堂1960年版,第40—41页。
⑧ [康熙]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⑨ [康熙]王全臣:《河州志》张祖谆序。
⑩ [乾隆]龚景瀚:《循化志》卷1《建制沿革》。
(11) [乾隆]龚景瀚:《循化志》卷8《回变》。
(12) [乾隆]龚景瀚:《循化志》卷5《土司》。
(13) [乾隆]龚景瀚:《循化志》卷5《土司》。
(14)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18。
(15)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87页。
(16) 马祖灵主编:《甘肃宗教》,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89页。
(17) [康熙]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18) 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9) [嘉靖]吴桢:《河州志》卷2《选举志·科第》。
(20) 明代河州进士中有马应龙者,“其先凤阳人也”,这在《通议大夫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马公墓志铭》(嘉靖《河州志》卷4《文籍志下·记铭》)中有明确记载。陈龙编著:《临夏人物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将马应龙的族属定为回族,不知何据。临夏民间素有“十回九马”之说,但马应龙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