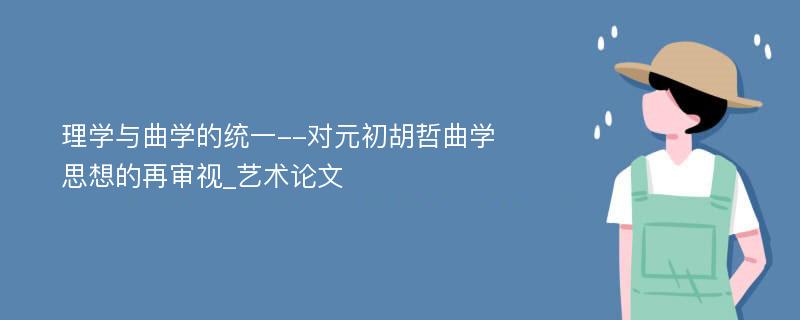
理学家与曲学家的统一——元初胡祗遹曲学思想的重新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重新审视论文,学家论文,思想论文,元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I237·1
13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古典文艺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并吸收当时多种说唱、舞蹈和音乐形式之长而诞生的北杂剧,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磨练,至此已进入成熟阶段。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舞台表演,都出现了卓荦冠群的大家。关汉卿和朱帘秀,便分别是各自领域中的翘楚。戏剧艺术的成熟,呼唤着舆论界给予应有的承认;由成熟向艺术高峰挺进,也需要学术界加以理论上的总结和指导。胡祗遹有关元杂剧艺术的系列序跋题赠,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了。
胡祗遹(1227~1295),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幼年丧父,八岁金亡入元。成年后因学问渊博,“见知于名流”。中统元年(1260),张文谦以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荐之为员外郎,从此踏上仕途。至元年间,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后因忤权奸阿合马而出为太原路治中,升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元灭宋后,历任至江南浙西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厉士风”(注:《元史》卷一七○本传。),政声甚佳。
作为元代前期的高级官吏,胡祗遹不同寻常之处是有着较高的文化学术修养。在艺术方面,书法造诣精深,“自成一家”(注:刘赓《紫山大全集》序。);在传统经学方面,曾撰有《易经直解》(注:参见王恽《紫山先生〈易直解〉序》,《秋涧大全集》卷四三。);在理学著述和诗文创作方面,著有《紫山大全集》六十七卷。惜全帙久已散佚,今存者为清修《四库全书》重编二十六卷本。《四库全书总目》论其学术渊源和创作特色如下:
大抵学问出于宋儒,以笃实为宗,而务求明体达用,不屑为空虚之谈。诗文自抒胸臆,无所依仿,亦无所雕饰,惟以理明词达为主。
认为他在崇尚风化词藻的元代文坛上,堪称“中流一柱”。此外,在新兴文艺样式散曲的写作上胡氏也颇有创获,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风格如“秋潭孤月”。所作今存十一首,散见于元明编刊的散曲集和笔记杂著中。
胡紫山染指于元曲创作,既是时代风气使然;就其本人而言,也非孤立现象,是与他对元曲的另一主要形式——杂剧的态度相辅相成的。从生平交游来看,他与元剧大家白朴(1226~?)为故友旧知(注:白朴至元二十六年(1289)与胡氏、王恽重逢于广陵,作〔木兰花慢〕词表达“恨一樽不尽故人情”,见《天籁集》卷下。),与关汉卿在创作上互通声气(注:关氏《调风月》第二折〔五煞〕:“你又不是‘残花酝酿蜂儿密,细雨调和燕子泥’。”系直接引用胡氏〔中吕·阳春曲〕小令《春景》首两句。),对杂剧艺人朱帘秀、赵文益等也颇器重(参见下文);从艺术观念来看,他对新兴的北杂剧有着较深刻的体认,所撰有关杂剧及相关曲艺样式的序跋歌咏,是元代前期戏剧学最为珍贵的文献。胡祗遹通过对戏曲曲艺演员的赠诗作序,表达了较为系统的戏剧及表演艺术观念。
一、胡祗遹非常重视戏剧艺术反映生活的广泛性:“杂”。元杂剧之所以能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是因为它善于博采前此伎艺的众家之长。最为主要的是两个方面:在表演形式上,主要吸取宋金杂剧院本的精华;在音乐体制上,直接滥觞于说唱诸宫调,因此而赋予了元杂剧表演故事性和长篇叙事性的艺术特征。作为叙事性文艺样式,戏剧应该从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汲取多样化的题材,反映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各种生活。胡氏在向戏剧女演员宋氏解释“杂剧”定义时,对此有很好的说明:
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友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巫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
——《赠宋氏序》(注:《紫山大全集》卷八。
按: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从该序内容和朱宋易讹等多方面论证“宋氏”应当就是“朱氏”之误,见《戏剧论丛》1957年第二辑。)这里没有朝廷法令什么准演、什么禁演的律条,也没有腐士酸丁什么“只看”、什么“徒然”的箴规,所有的只是元代前期特有的理论倡导的宽宏与戏剧实践的博大之间绝好的配合。尤其是“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的结语,既是对元剧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戏剧艺术潜能的由衷赞美。
二、胡祗遹非常重视戏剧欣赏心理调节的泄导性:“宣”。戏剧艺术的作用,固然贵在它能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不同领域中的各种人物,以便观众认知社会、感悟人生。但如果仅仅如此,戏剧则等同于教科书了。它之能令普通观众“谛听忘倦,唯恐不得闻”(注:胡祗遹《黄氏诗卷序》,《紫山大全集》卷八。),则应有其特殊的艺术功能在。胡紫山在其《赠宋氏序》开篇,以小品文的精彩笔法,对此进行了生动描述:
百物之中,莫灵莫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鸡鸣而兴,夜分而寐,十二时中,纷纷扰扰。役筋骸,劳志虑,口体之外,仰事俯畜。吉凶庆吊乎乡党闾里,输税应役于官府边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颦心结,郁抑而不得舒;七情之发,不中节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时安身于枕席,而梦寐惊惶,亦不少安。朝夕昼夜,起居寤寐,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无疾而呻吟,未半百而衰。于期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皞皞,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
乐以宣郁,在胡氏的艺术思想中并非偶尔言之的闪念,而是一种明确的美学观点。他在词作〔木兰花慢〕《赠歌妓》里,也曾以“日日新声妙语,人间何事颦眉?”(注:《紫山大全集》卷七诗馀。)赞扬演员新奇绝妙的演唱艺术能化解观众的百转愁肠,艺术欣赏能够冲淡他们的郁闷心情。涉世艰难,生存不易,精神紧张,筋骨疲惫,人生常苦辛,欢适有几时?以高级儒士和上层官吏而提出生活“愁苦”说,是其体贴世情处,也显示出他对生命、人生的独特体味和咀嚼;而把生活愁苦与排遣需要相联系——“少导欢适”,并进而提出戏剧源于对苦难人生的心理补偿、欣赏戏剧可暂时排解人心的苦闷疲劳,此即所谓“少导欢适”、“宣其抑郁”之说。这是胡氏对元代戏剧学乃至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贡献,是一个至今仍有其学术和实践生命力的戏剧美学命题。笔者有一篇旧文曾认为元代曲家“都没有提出戏曲的娱乐功能”(注:《元人戏曲功能论初探》,《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从上述引文来看,显然是失察之论了。
三、胡祗遹非常重视舞台演出表演技巧的艺术性:“美”。在戏剧说唱的各种表现手段中,论者看重的是演唱和说白,即所谓“女乐之百伎,惟唱、说焉”(注:《黄氏诗卷序》,《紫山大全集》卷八。)。这句话似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说、唱是最为重要的表演手段,二是指其表现技巧最难掌握。唯其最为重要,又最难掌握,他才紧接着提出了表演艺术“九美”说,即九项艺术原则:
一、姿质浓粹,光彩动人;
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
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
四、语言辨利,字真句明;
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
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
七、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
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
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
“九美”涉及到演员的自然条件、气质风度、才学修养、唱念功夫、表现技巧等多方面的美学要求。“近世优于此者,李心心、赵真、秦玉莲”一句,说明这九条原则,并非论者随口所言,而是对前此戏剧说唱伎艺的总结(注:此文开篇“女乐之百伎”应已包括戏剧在内;据《青楼集》载,赵真真《冯蛮子妻》“善杂剧,有饶梁之声”;秦玉莲“善唱诸宫调”。)。“九美”说与胡氏《朱氏诗卷序》“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注:均见《紫山大全集》卷八。)的“内外”说和《优伶赵文益诗序》的“耻踪尘烂,以新巧而易拙”(注:均见《紫山大全集》卷八。)的“新巧”说,共同构成了对戏剧表演之“美”的系统认识,在中国戏剧表演学史上,是最有价值的早期专论。
以今人的眼光审视胡祗遹有关戏剧的序跋歌咏,其价值自然是无庸置疑的;其理论内含,笔者在有关文章中也曾予以展开评述(注:见《元人戏曲功能论初探》和《元人戏曲表演论初探》,后者连载于《戏曲艺术》1987年第3、4期。)。但是,作为一个肩有振兴教化之职的地方长官和倡导学风之责的理学之士,与艺人唱和题赠、交往甚密,在旧时正统文人的脑海里,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如清人便曾直接了当地指责《紫山大全集》:
编录之时,意取繁富,遂多收应俗之作,颇为冗杂。甚至如《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诸篇,以阐明道学之人,作媟狎倡优之语。其为白璧之瑕,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潜者(注:此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集序》:“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播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而附纠其谬于此,亦足为操觚之炯戒也!
——《四库全书总目·紫山大全集》提要
我们今天阅读这段文字,一方面固然感到顽固迂腐的四库馆臣所谓“附纠其谬”的可笑和文艺观念的落后;另一方面也庆幸他们能“姑仍其旧”、手下留情,录存了一批珍贵的元初戏剧学文献。同时,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胡氏所撰有关文字,即使是在古人的思想范畴内,是否即为“媟狎倡优之语”,其写作意图是“应俗”还是“励俗”,是否有违“阐明道学之人”的思想意识。探讨这个问题,不能无视《紫山大全集》卷十二中的这样一篇重要文论:《礼乐刑政论》。
胡祗遹这一论题,出自儒家经典著作《乐记·乐本》:“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然胡氏此文,名为论礼、乐、刑、政,实则为主论“乐”的社会作用。他首先指出“礼立矣而和之以乐”,认为乐可以从感情上谐调下至“匹夫之贱”、上至“天子之贵”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使一举一动,既合于礼制,又顺乎自然;其次,提出了“乐以成德”,认为乐有助于成就人的道德修养,对人的思想品德有感染熏陶的作用。这两点,分别渊源于《乐记·乐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和《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安国注“成于乐”为“乐所以成性”),不为新见;并由此化用《乐记·乐本》的成句,得出“故曰‘审乐以知政’,因以知国祚之兴亡”的论断,也就顺理成章了。
“乐”既然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存亡、安危、治乱和贤愚贵贱的伦理道德教化,作为身兼执政之官和理学之士的胡紫山,他所看到的现实却是令其大失所望的。在另一篇类似的文章里,胡氏曾痛心地述说道:
仆自入仕临民,伤礼乐之消亡,哀民心之乖戾。为政者直以刑罚使民畏威而不犯,力务改过于棰楚之下,杖痛未止,恶念复起。条法责吏曰:“词讼简,盗贼息。”何不思之?甚也,礼乐教化既已消亡,休养生息、安宁富庶、学校训诲又不知务。民生日用之间,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愁苦悲怨,逃亡贫困,冻饿劳役。居官府者,晏然自得,而以为治民抚字之功,可哀也哉!
——《紫山大全集》卷十三《礼乐论》
胡祗遹对当政者一味以严刑酷法震慑百姓,而不知用礼乐教化安抚百姓(这正是元初统治的特点),十分不满。认为这样造成了民众的“愁苦悲怨、逃亡贫困、冻饿劳役”,原因即是《礼乐刑政论》所云“道德礼乐既废,所谓区区之刑政,亦从而废”。加之“曰刑曰政,亦无定法”,政策刑律又无一定之规,其结果必然导致道德沦丧,法律混乱,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所谓“善人瘖哑,凶人日炽,暴官污吏,顽弟逆子,戾妻僭妾,强奴悍婢,市井无赖,日增月盛”的社会现象,在元杂剧尤其是公案剧中早已是屡见不鲜了。这不能不说是对元朝前期蒙古统治者只知崇尚铁血腥风、野蛮落后的暴戾手段的一针见血的批判,亦是其产生杂剧艺术宣泄说、忘倦说的社会认识根源,虽然这是出于传统理学家和有远见政治家的立场,目的在于恢复中原儒家的礼乐教化文化。
那么,由谁来光复乐以和礼、乐以成德的教化呢?腐儒俗士是不行的,“礼乐固非庸儒之所能复”,因为他们根本认识不到“乐”的重要作用(清代四库馆臣亦属此类人),只能加速此道的堕落和毁灭。试看下面两段论述:
古之君子,燕居养德,假物之善鸣者以宣道,纯粹和平之气;今之“君子”,随俗进伎,以妩媚哇淫之欲,快耳而称口:噫!其于乐以成德也,不亦远乎?
——《紫山大全集》卷二四《语录》
今之老师宿儒,礼学、乐学绝口不谈,并以所假之器略不考较,一听于贱工俗子,是将古人之饰文末节,复不能举明而并绝之也!
——《礼乐刑政论》
要弄清这两段话的含义,首先要理解其中主要词语的基本所指。上段“物之善鸣者”与下段“所假之器”同义,在古为“金石丝竹”之类(注:《乐记·乐论》:“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乐记·乐象》:“金石丝竹,乐之器也。”),在元代则为包括戏剧在内的各种文艺样式。上段的“道”是指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礼义道德,“欲”是指流于纯粹感官欲望的自然情感。两者的关系,古人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注:《乐记·乐象》。)下段的“乐学”,则是包括乐以“和礼”、“成德”、“宣道”、“知政”在内的儒家经典文艺美学思想;而所谓“饰文末节”,则是指“乐”的形式美及其表现的有关规律(注:《乐记·乐论》:“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乐记·乐象》:“文采节奏,声之饰也。”《乐记·乐情》:“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在元代则应包括唱念表演、声韵格律等戏剧艺术规律。
如果上面的解释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本文认为胡祗遹的有关论说,针砭的是这样的现象:当今的有学有道者,对“乐学”之精粹不加研讨论究,对有关文艺样式的社会作用和艺术规律更是避而不谈;而将这有关教化政治的大事听任艺人优伶随意表现,在内容上只求以“妩媚哇淫”之欲“以助淫荒”,在形式上不能发扬光大,反而使之走向末路。
正因为不满于如此的文艺现状,他撰《礼乐刑政论》、《礼乐论》等以探讨“乐学”,撰《赠宋氏序》、《黄氏诗卷序》等以论述“乐”之“所假之器”的社会功能和“饰文末节”的艺术规律。他是自觉站在那些仅把戏剧当作遣兴娱宾之具而无视其深刻内容的今之“君子”的对立面,以“古之君子”自任,一方面借论戏剧以“宣道”,一方面对戏剧艺术规律加以总结“考较”,这就是其撰写戏剧序赠歌咏的内在目的。“宣道”不仅表现在经常化用《乐记》“先王之制礼乐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注:《乐记·乐本》。)的成句,提出“圣人所以作乐”、“乐音与政通”(注:《赠宋氏序》。)的观点;他对戏剧反映生活之“杂”的肯定,对戏剧表现“五方之风俗,诸路之音声,往古之事迹,历代之典型,下吏污浊,官长公清……居家则父慈子孝,立朝则君臣圣明”(注:《朱氏诗卷序》。)的赞赏,也都是《乐记·乐本》“审乐以知政”、“乐者通伦理者”之论在与元初戏剧实际相结合后而作出的独特阐发。“考较”则表现为集中体现在《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中的对戏剧表演学的精彩总结。
明白胡氏戏剧序赠之作意在“励俗”而非“应俗”,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这样一段议论:
人之知见志趣,赋分既定,苦不可移,小不可使之大,近不可使之远。……居官者不以政治勋业、致君泽民为乐,而日与优伶女妓、酒色声乐为娱,其位则卿相,其志趣则伶伦也。
——《紫山大全集》卷二六《语录》
乍看起来,此段语录对优伶的态度与论者自身有关演员的言行甚相矛盾,故向来不被论胡氏曲学者所征引。但是,当我们弄清其乐学思想体系,也就不难理解有关提法了。这里的“居官者”,也就是只知“随俗进伎”的“今之君子”,他们与优伶交往,只是以“酒色声乐为娱”,只图“悦耳娱心,以助淫荒”(注:《礼乐刑政论》。)(高安道〔般涉调·哨遍〕《嗓淡行院》所咏“抱官囚”,便是此等人物,他观剧心理十分阴暗,“倦游柳陌恋烟花,且向棚阑玩俳优”,看戏成了嫖妓的临时替代,用一“玩”字已道尽其行为之龌龊);这里的“优伶”,也就是所谓“贱工俗子”,他们所进之伎,只能是以“妩媚哇淫之欲快耳而称口”。按照胡祗遹的观点,“其与乐以成德也,不亦远乎!”当然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而胡氏与优伶的交往,目的在宣道观政、考较伎艺;胡氏交往的优伶,则为演艺“心得三昧,天然老成,见一时之教养,乐百年之升平”(注:《朱氏诗卷序》。)的一代名伶。他们“颇喜读,知古今,趋承士君子”,于所学“已精而求其益精”(注:《优伶赵文益诗序》。),也就是与乐之“所假之器”勤于“考较”了。这样的艺人,套用胡氏的话头,便是“其位则优伶,其志趣则卿相也。”对位在卿相而志趣优伶者予以抨击,对位在优伶而志趣卿相者加以褒奖,在倡导教化的理学家看来,两者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四库馆臣认为这便属“媟狎”之举,即使是置于传统理学范畴内来考察,也实在是曲解了胡紫山,起码也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论。
本文论述胡氏对戏剧的评说实以理学家的身份为之,并不只是要指出清人评价的失误,更无意于贬低胡氏戏剧理论的价值,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元代前期这个传统文化中断、新兴文艺突起、博学大儒无心于此、才人文士只求自娱的特殊时代,对新兴戏剧艺术功能的概括和社会地位的肯定,原来就不是一件易事;借助儒家传统美学思想予以归纳总结,或许是在当时的历史和思想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最好选择。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胡氏对元代戏剧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以传统《乐记》的美学思想为基础对新兴文艺样式进行理论指导,有助于稳固其社会地位;不仅表现在从宋儒“以笃学为宗而务求明体达用”的理学观念出发,成功地总结了元杂剧内容的充实性和反映的广泛性等艺术特点;还在于他的阐述抓住了元剧的叙事性、表演性和人物塑造性,由此而提出的戏剧美学思想和原则,就势必会丰富中国古典戏剧学的理论建树。同时,作为一名优秀的学问家和理论家,他所做的工作也不可能只是简单重复前人的言论,如所提出的“作乐以宣其抑郁”说,就不仅仅是乐可以“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注:《乐记·乐施》。)所能包容的:这其中对“莫愁苦于人”的喟叹,可以看到宋金灭亡、元朝建立过程中残酷的战乱兵燹在人们心理上留下的沉重阴影,是一种苦难时代的独有感受;而对“莫灵莫贵于人”的讴歌,则体现了封建士子在元代社会里拯世济民的理想难以实现、转而追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心灵轨迹,也叠印出这样一种时代特征:伴随着市民意识的逐渐觉醒而来的对普通民众人生价值的关注。
胡祗遹逝世后,其友王恽曾这样评价他:
材超卓而不凡,气正大而不替,可以挺公论而励衰俗,激清风而作士气。
——《秋润大全集》卷四三《紫山胡公哀挽诗卷小序》
当这一切具体化为较强的现实批判精神、较深的传统美学修养和较高的艺术理论造诣,并与明确的戏剧研究目的相结合时,便造就了胡祗遹元初戏剧学第一人的历史地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