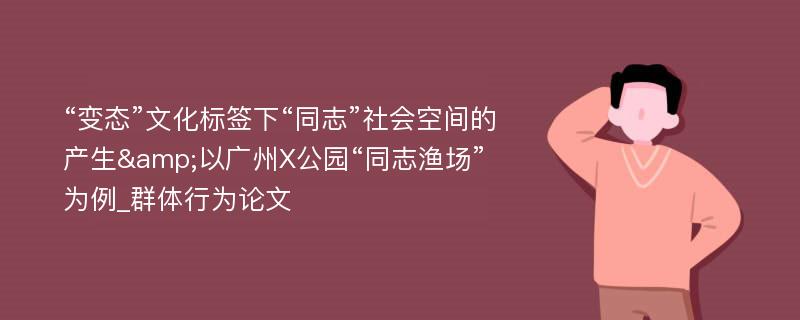
“非正常”的文化标签下“同志”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广州市X公园“同志渔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志论文,渔场论文,广州市论文,为例论文,非正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06-20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4)03-0035-09 1 引言 性少数群体(sexual minority)对城市空间的利用是城市研究中的新兴话题。性少数群体特指在性取向与性认同方面与主流的异性恋文化相异的社会群体,通常包括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与酷儿一族,即统称的LGBTQ人士。这一群体,由于受主流文化的歧视与排斥,常需要利用边缘的、在惯常生活与工作场所以外的城市空间[1,2],通过特殊的空间实践来实现群体内部的社会互动,寻求发生性接触的机会,并形成特有的亚文化[3]。本文从空间的社会建构这一视角出发,探讨男同性恋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占据、使用与体验。西方学界对同性恋群体公共空间的研究,始于Humphrey对美国的“茶室”(tearoom)性关系,即公共洗手间中男同性恋者短暂、匿名的性接触的社会学研究。Humphrey提出,特定的城市空间会被性少数群体赋予特殊的用途与意义。在这一空间中,同性恋者之间会形成特定的交往与邂逅的法则与规范[4]。Chauncey在研究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纽约男同性恋的社会空间后指出,性少数群体由于受到主流社会规范的约束,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空间中很难显露出真实的性取向。因此,其私密的性欲望与情感需求往往需要在公共的城市空间中才能得到实现[5]。公共城市空间由于汇聚了不同背景的人群,往往能够掩盖特定群体的性取向,营造出一个半隐秘的交往环境[6,7]。在大陆同性恋群体的话语体系中,这一类城市空间常被称之为特定的“场所”、“点儿”、“渔场”或“飘场”,包括公园、公共洗手间、酒吧、会所、桑拿以及一些特定的聚会地点。 目前英文圈学者对于性少数群体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关注此类空间中边缘的性身份所得到的表达和展演。其观点倾向于强调性身份得到的暂时解放,以及对于“异性恋至上”的社会规范的抵抗。然而,城市空间极少能够被单一的文化意涵或文化意义所垄断。本文认为,尽管性少数群体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霸权性的空间秩序,但异性恋至上的社会规范与意识形态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空间的生产、影响空间中的社会实践,甚至限定性少数群体文化认同的边界。同性恋身份之所以处在社会文化结构之边缘,往往并非受到暴力的直接压迫,而是因为异性恋的生活方式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社会规范,统治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8]。在这一背景之下,同志群体的空间实践与空间的文化意义是否会受到“非正常”这一文化标签的影响与建构?同志群体的空间实践是否会反过来再生产他们对于“非正常”的文化身份的体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关注此类空间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性少数群体的城市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实现情感需求与性欲望的空间,亦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空间,即不同的社会关系不断生产与重构的空间。在此类空间中,性少数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复杂多元的。他们之间,不仅会存在性的层面的关系,也会存在其他领域,例如经济、文化层次的社会联系。他们之间存在情感的依赖,但亦有潜在的不满、矛盾以及冲突。从这一观点出发,本文将以同志内部的以及同志与异性恋“他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为切入点,分析性少数群体公共空间的生产。 2 “非正常”的身份标签下性少数群体的社会空间的生产 英美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研究对性少数群体,特别是“同志”①群体的城市空间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同志对于城市空间的占有与利用,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同志自发集聚的居住社区以及相应的消费空间。其主要特点在于依赖经济实力较高的同性恋者,通过资本的力量,实现性少数群体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权。Manuel Castells(1983)对于旧金山Castro同性恋社区的经典研究,显示同志可以通过集中购买某一城市社区的住房,来建构一个“乌托邦”一般的、相对独立的生存环境与消费空间[9-12]。第二类空间,在英文中亦被称之为“巡弋(cruising)”的空间,主要通过同志在空间上暂时的集聚,为其提供短暂的性行为的机会。这类空间最为典型的案例包括男公共洗手间、郊野公园、天体海滩、浴池等[6,7,13-15]。第三类空间亦可称为性少数群体“表演”与“展示”的空间,即通过刻意的、往往较为夸张的表演向公众展示性少数群体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公共空间的“易装皇后(drag queen)”表演、“同志骄傲”大游行、街头夸张的造型(如光头同志文化、皮革同志文化等等),已经成为同志群体与异性恋社会进行文化互动的重要方式[16,17]。此类性身份的展演,将性少数群体的亚文化从幕后拉向台前,提高了主流社群对于亚文化群体的认知[18,19]。 很大程度上,性少数群体走向公共空间挑战了即有的社会规范对于这一边缘群体的压抑与限制。无可否认,随着社会思想观念的演变,主流文化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包容程度正在逐渐提高。但很多情况下,这种包容的前提是性少数群体的文化与身份必须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而不应诉诸于公众的视野。换言之,异性恋的文化是一种“公共”文化,而性少数群体的文化则只能是“私人”文化。这一“公私”的二元结构,实际上构成了对性少数群体另一种形式的歧视[20,21]。例如,英格兰于2003年实施的Sexual Offense Act将公共盥洗室内发生的性行为明确定义为违法行为[22],这就限制了对男同志颇为重要的公厕性行为(cottaging)。因此,性少数群体对于公共空间的占据与利用,可以有力地挑战这种私人一公共的二元分异,将性少数群体的文化从私人问题转变为公共行为,实现这一群体的平等与赋权[23-25]。另一方面,在一个异性恋至上的社会,即使在私人空间(例如家庭,住所),边缘性欲望也很难避免异样目光的规训与检视。因此,反而是很多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性少数群体密集交往的机会,并促进了集体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形成[5]。 上述观点,在目前欧美地理学与城市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试图对这一观点进行发展与补充。我们认为,抵抗空间的视角仅仅强调了性少数群体的社会空间对于主流文化价值的越轨,而忽视了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空间生产与主流价值体系之间多样的互动。它过于简单地将文化的压抑与抵抗按照公共—私密的分异划分到空间关系的地图上,却忽视了经验层面上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即同志公共空间的生产,不仅可以挑战主流的文化规范,也可能被主流规范所定义、约束和限制。换而言之,性少数群体的社会空间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而非一元的。 事实上,现有研究对于本文的观点已经有了一定的论述。例如,Fuss对于同志群体与霸权话语之间“进”(in)与“出”(out)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同志公共文化的形成,可以理解为同志“走出”了霸权的性文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霸权话语的“越轨”(transgression)往往使得霸权话语得到更为明确的建构,同志的身份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进入”了霸权话语之中[25]。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一个二元对立结构(binary opposition)中的两个概念,是互相建构,互相生产的[27]。换言之,“同性恋”与“异性恋”这一组对立概念,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表达,其结果往往并非是“异性恋”这一概念的消亡,而是进一步明晰了这两个概念间在意涵上的边界。因此,同志群体在社会空间的聚集,虽然毋庸置疑地促进了性身份的表达,但亦有可能因为对“非正常”的文化身份的密集体验,反而放大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差异,从而强化对于“非正常”标签的感知。 现有的经验研究也已指出,在“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这一宏观背景的作用下,同志对于身份的体验与表达,亦有可能被刻写上主流社会规范的强烈烙印。Lynda Johnston对于“同志骄傲”大游行的研究,和Gordon Waitt对于同性恋者运动会的研究均指出,同志在城市空间对其性身份的展示,并非只注重展现与主流群体的差异。很多情况下,性少数群体会为自身的性取向感到羞耻,而他们希望让“他者”看到的,是其对主流价值观的服从以及将自己塑造为“正常人”的愿望[28-31]。利用公共空间的同志,并非一个同质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依然处在霸权性话语的束缚与压力之下[32,33],甚至将霸权话语融合进了自我的主观性(subjectivity)的塑造中[34]。性少数群体的空间本身是置于一个社会平面之上的,主流价值观中正常—非正常的二元体系,以及主流文化对性少数群体的排斥,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结构性的制约因素[35,36]。 地理学视角对于论证本文观点独有裨益。地理学聚焦于物质空间本身,而非仅仅是空间中发生的某些社会现象。这就允许我们充分地捕捉特定地理单元中社会过程的多样性。空间通过特有的社会实践被生产出来,从而形成空间—社会集合体的独特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空间性”向“地方性”转变的过程。社会行为并非均匀分布在地理空间之中,特定的社会实践只有在特定的空间中才能实现。社会实践本身又往往会在同一空间中催生新的社会过程,使得同一空间内充满社会的张力、矛盾与紧张。因此社会空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正如本文观念所述,同志空间对“异性恋至上”的社会结构既有抵抗,也有受制和妥协。地理学的视角,允许我们以某个特定空间为单元,研究一个复杂的系统。这就避免了因仅仅关注特定社会空间的某些方面,而忽视社会群体在感知、评价空间的过程中所必然考虑到的多样化的社会过程。 主流的社会规范规范,通常被称为束缚同志的“柜子”(closet),但同志对于城市空间的占据与利用,是否必然意味着“出柜”,抑或是“半进半出”的中间状态[37,38]这有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微观尺度的深入分析。本文选择前述空间类型中的第二类,即同志“巡弋”的空间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以广州市X公园作为案例点,来论证前述的观点,即:纵然是具有解放与抵抗意义的社会空间,也有可能成为同志“非正常”的文化标签展演与作用,并施加霸权的场域。“非正常”是霸权话语建构出来的一个符号与意义的集合。在本文的分析中,“非正常”的标签在三个层次发挥作用。首先,“非正常”是主流社会强加在同志之上的一个霸权话语。第二,“非正常”亦是性少数群体不断体验、甚至认同而接受的。在X公园,很多参与“巡弋”行为的同志本身便将自己描述成“越轨”以及“非正常”的,他们的身份建构并未超脱于“异性恋至上”的话语之外。事实上,公园同志对于“非正常”的污名的内化(internalization of stigmas)[39],是公园的空间实践、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形成过程中十分关键的媒介。最后,“非正常”也体现在同志对于X公园的“巡弋”空间中的行为与现象的解读。很多同志对于同志渔场的评价,往往以主流社会的规范作为参考。同志空间中一些较为“越轨”、“放肆”或“混乱”的现象,常常引发同志的不安甚至羞耻之感,并强化了他们对于“非正常”这一身份标签的感知与体验。 魏伟[40-43]与富晓星[44,45]的开创性研究已指出,与西方文献中记录的现象类似,中国的同志群体亦可以通过对城市空间进行创造性的利用,实现集体文化的塑造。两位学者的研究引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方向。首先,他们没有仅从单纯的性行为的角度解读中国城市空间发生的同性爱行为;相反,“同志”被看作文化身份的标签,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其次,两位学者的研究都将特定空间看作同志身份形成与展演的平台,这就允许我们认识到同志对于主流规范进行抵抗的潜力,并对特定空间的亚文化进行深入解读。本文支持这一系列研究的观点,但又力图对已有研究进行一定补充。同志群体的解放与抵抗并未将空间的生产置于“异性恋至上”的社会规范之外。“不正常”的文化标签,可能是空间生产中的一个构成性元素(constitutive element)。抵抗与可能存在的妥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缺失任意一面都将限制我们对于同志社会空间的全面理解。 3 研究背景与方法 3.1 案例背景与调研方法 X公园位于广州市老城区,是广州较早建设的现代城市公园之一。X公园交通区位便利、自然环境优越,是广州市民十分青睐的日常休闲场所。上世纪90年代,广州市政府拆除了X公园的围墙,并实行入园免费。随后,X公园便成为了广州市男同志集聚的空间。在广州的同志圈中,X公园被称之为“渔场”,其主要功能为“钓鱼”,即寻找合适的情感伴侣或性伴侣。按照西方文献的定义,X公园明显属于“巡弋”类的社会空间,并不承载同志居住或消费的功能,只是提供一个日常生活以外的、暂时性的集聚场所。除了短暂的性关系之外,X公园的“同志渔场”也是一个重要的交友、休闲以及娱乐的场所。聊天、社交等功能和性关系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X公园的同志渔场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同志露天聚集场所,其空间范围主要包括公园西片的三条走廊,即所谓的“同志地带”。公园西北角和南北角的两个公共厕所,也常被同志用来发生短暂、匿名的性行为。 研究主要基于质性研究为主的田野调查。从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研究者通过与广州智行基金会合作,以艾滋病防治志愿者的身份,在X公园的同志渔场进行了深入的质性调查。研究者通过艾滋病防治的过程,和公园同志密集互动,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与友谊,从而慢慢进入他们的话语世界与主观世界。但由于研究者身份限制,只能主要关注同志群体内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重构,以及同志与公园异性恋群体的空间关系,对于同志的“欲望地图”以及性行为的观察则比较有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观察与质性访谈。首先,研究者对X公园同志的空间实践和社会生活进行了长时间的非参与式观察。观察的发现以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同时,研究者对广州本地同性恋公益组织的成员,以及X公园的同志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总量为35个,访谈时间在半小时到两小时之间,包括5位同性恋公益组织成员,以及30位公园的同志。由于访谈数量的局限性,本文与多数质性研究一样,无法完全捕捉群体中的普遍性观点(从社会学意义讲,即无法百分之百解释变量的方差)。但我们主要使用归纳的方法对访谈文本进行概括化(generalization)与抽象化(abstraction),以提炼论述的框架。我们发现,的确有一些观点是在访谈对象中较普遍存在的。而不同访谈对象之间显出个体性的,则是支撑观点所使用的实证事实与日常经验。因此,本文主要从具有较广泛普遍性意义的观点出发,提炼出基本的事实与观点,并从具体的日常经验中汲取论据,使我们的论证显得更加有血有肉。 3.2 X公园同志群体的特殊性 与魏伟在成都进行的社会学考察[43]不同,X公园的同志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在近年来出现了急剧的“向下过滤”的情况。如果说魏伟笔下的成都同志身份的解放有了很大进展,那X公园的情况则要滞后许多(这并不代表广州同志社区发展整体上滞后)。即使广州本地的同志NGO,对X公园也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失望之感。X公园同志的阶层属性,使得他们没有逾越霸权话语中正常—非正常的二元分异。X公园的同志主要以低收入的外来移民为主,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高收入、高教育阶层和广州本地人相对罕见。对于这部分同志来说,其接受的有关同志解放运动的信息较少,本身的思想深受传统家庭道德与生育道德的影响,很少对同性恋“非正常”这一标签产生抵抗。目前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同性恋人士,由于教育水平较高,且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已逐渐认同同性之间可以参考异性恋的模式实现正常的家庭生活,并展开了一系列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运动,多次向国家机构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但这样的文化倾向在X公园同志中是相当少见的。X公园的同志,90%以上都有,或曾经有过异性婚姻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本身即认为同性恋是“肮脏”的、“不道德”的、“心理变态”的。“非正常”这一文化标签是他们对于同性恋倾向的一个基本认识。一位中年同志认为: 我们同志在心理上是放不下的,放不下自己是同志,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觉得社会肯定是要歧视你的,觉得这个身份是很羞耻的。我们自己的心态就是这样不好的,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中国的同志是很压抑的,自己过不来自己的这一道槛。(访谈20111015A) 在这一背景下,绝大部分公园的同志都不敢想象同性之间可以按照情侣或家庭的模式长期生活。对他们来说,同性恋倾向是一种性欲望的表达,但很难转化为一种合法的身份认同。中高阶层同志人士对于长期的伴侣关系与同性婚姻关系的设想,X公园的同志不能理解,亦不敢认同。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想象,是一个保守的、僵化的、压抑的文化环境,且永远不可能接受同性恋作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X公园“同志渔场”的考察,有必要从同志群体“非正常“这一霸权话语入手,探讨这一话语体系对于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建构的影响。“非正常”作为公园同志共享的一个意义符号,当然可以促进集体认同的形成以及文化身份的展演。但它亦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塑造空间实践以及社会互动,甚至催生出新的有关“非正常”的体验。本文的经验研究,将首先对X公园中同志的性身份的解放进行简要叙述,以呼应现有文献中的主要观点。但是,研究的主要部分,将从三个平行的侧面出发,探讨“非正常”的文化身份与空间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4 X公园与同志身份的解放 毋庸置疑,X公园为男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身份解放的空间。X公园的氛围,整体上是宽容平和的,因此显著促进了同志的集体文化与集体认同的形成。公园的异性恋者,虽不能说对“钓鱼”的同志热烈欢迎,但歧视性的举动很少存在。这一点与魏伟对成都“漂场”的研究是契合的[40,43]。X公园同志渔场的使用者,绝大部分属于没有“出柜”的同志,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的空间中,必须恪守语言与行为的边界,防止显露自身性取向。然而,同志在X公园暂时的集聚,营造了截然不同的空间规则与行为规范。在这一空间中,同志是一个临时性的社会结构中的“大多数”。他们重新定义了空间的功能、行为准则及文化意义。“渔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同志的生活轨迹可以与“我们这种人”相交汇,将同性恋从一种个人的心理状态转化为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从而建立一种“我者”的文化归属感。X公园的同志在进入公园渔场之前,通常对于自己的同性欲望有着强烈的迷惑与不安,以为自己患了心理疾病,曾经进行过心理治疗者亦不在少数。而在公园,同志可以认识到自己并非是唯一或者孤立的: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正常,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同志。真的,在老家不敢和家人说,觉得自己有病,要偷偷看医生,看中医,让医生拿药给你吃。后来出来打工之后巧合吧,知道这地方,就来了,一过来之后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里很多这样的人吗。很多年龄比较长的人,就会和你聊天,告诉你,让你觉得你不是有病,后来就不是自己以前的想法了。(访谈20111016A) 在X公园,性身份的解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做平时不敢做的事”及“说平时不敢说的话”。做平时不敢做的事,表现在同志在渔场中敢于牵手、拥抱、亲吻、抚摸、凝视英俊的男性,甚至在厕所中发生性关系。同时,易装表演等性别文化色彩强烈的行为,在公园也较常见。而“说平时不敢说的话”,指的是同志之间聊天的话题会包括与同志文化、同志情欲以及同志交友有关的内容。可以说,X公园的渔场的确颠覆了主流社会的一些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为同志群体提供了一个暂时释放与解脱的空间。因此,X公园的同志对于“渔场”都有着强烈的依恋感与归属感。一名资深的同志“艾里斯”对X公园有着如此的评价: 没事做,我就觉得可以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离不开这个圈子,离不开这种文化。这个地方已经有文化了。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那些反串的、变性的都来这里的,因为这里有人可以认同他们。别的地方不敢的事情,这里敢做。这里有一种依恋感。关于友情、爱情都有。这里是广州同志的精神家园,一有空就想来这里,不来这里,不知道公园发生什么事,我就觉得心理很不平衡了。(访谈20111009A) 5 “非正常”标签下的同志渔场 5.1 同志渔场与“恶性循环” 尽管X公园的同志渔场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主流规范中对同性恋身份的边缘化,但这并不代表这一社会空间能够完全超脱正常—非正常的二元结构。事实上,即使是公园的同志本身,对这个“钓鱼”空间的态度也是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他们对于X园有无可置疑的依恋,但也会对这一空间中的一些现象与特点感到茫然、不安甚至厌恶。本小节将讨论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即X公园的同志空间虽然承载了重要的交往功能,却很难为同志提供长久的伴侣关系。在我们访谈的同志中,大部分都感慨,在公园中很难得到真实的情感,以及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在公园中寻找到的关系,通常很快便会终结,甚至大部分只是一夜惰性质的体验。随后,同志便需要重回公园寻找新的性伴侣,循环往复。由于同志之间缺乏长期的情感交流或接触,所谓“真爱”也自然很难通过公园的社会生活形成。对于很多同志来说,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场所,虽然能够满足生理的需要,但对于根本性地改善同志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作用甚微。正如很多受访者所言,他们在公园的主要活动,就是不断寻找短暂的性伴侣,周而复始,连他们自己都对这种模式感到厌烦;而这一交往模式多年来也没有明显变化: 公园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你感情短暂吗,就需要时不时地过来找新的朋友啊。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稍微久了,就换换性伙伴吗,因为不稳定啊,所以需要找新的刺激啊。两个男的结合起来都是很不稳定的,毕竟是不正规的吗,不知道两个男的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就容易分手吗。所以同志特别需要X公园这种地方来找新的关系,就是这种不断循环一样的。没有了,又来找,你说是不是?(访谈20110911B) 对很多同志来说,这一社会交往的特点,也成了失落与焦虑的来源,使得他们愈发认为自己塑造的社会空间是“越轨”和“非正常”的。这些忧虑之中,最突出的体现在同志倾向于将X公园描述为一个“性乱”与“滥交”的场所,因此在心理上对其产生了一定的抵触情绪。长期置身于短暂的性接触,性伴侣不断更换,使得他同志对自身的价值观与性道德产生了疑虑,认为同性恋的生活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滥交”和“放荡”。更重要的是,很多同志担忧X公园特殊的性文化会引来外界的指责与批判。事实上,即使是在广州本地的同志圈子内部,社会阶层及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志也常常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对X公园的“渔场”表达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并在道德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这些网络平台的话语,更加深了公园同志对于自身“非正常”身份的羞耻感: 在广州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说公园的人就是见了面就很容易上床的那种。有些人的嘴巴很烂的,如果你今天去了公园被人家看到,或者是自己不小心说出去了,那么第二天你认识的人就全都知道了,就说你是一个很滥交的人咯。在不进公园的同志的眼里,公园就是一个只有一夜情的地方。(访谈2011112A)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滥情”的社会空间的生产,正体现了“同性恋”如何在社会话语中被定义为一个“非正常”的文化身份。X公园的同志中存在一个悖论,即一方面希望通过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来抵抗“非正常”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同志“非正常”的标签又限制了对稳定关系的追求。首先,由于认同同性感情是羞耻的,X公园的同志中绝大部分依然倾向于和女性组成异性婚姻,这就意味着在异性婚姻之外,同志对于一段长期的同性伴侣关系的态度是十分矛盾,且非常谨慎的。第二,很多X公园的同志并非能够完全接受长期的同性伴侣关系。对他们来说,长久的同性关系与其说是身份的解放,不如说是难以承担的文化负担。一方面,同性伴侣关系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引起他人的怀疑,造成困扰与负担;另一方面,正如经典社会学理论所指出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只有通过适当社会知识的引导,人才能接受一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行为[46]。对于公园同志来说,由于其处在较为保守的文化环境中,生活中似乎没有适当的社会知识及文化指征来引导其适应、接受并认同长期的同性关系。很多同志甚至对同性伴侣关系感到尴尬与疑惑。“两个男人之间如何谈恋爱”?“同性关系中的角色如何分配,谁更‘男人’一些,谁更‘女人’一些”?这些问题都是X公园同志的社会知识很难回答的。 有趣的是,由于主流的文化框架中对同性伴侣关系缺乏明确的定义与规范,很多同志之间即使明确建立了伴侣关系,也极难将其长期维持。在一个异性恋至上的社会,主流的社会价值,规范与社会制度均是建立在异性恋生活方式之上,而同性恋则被严格地排除在主流知识之外。因此,对于公园同志来说,似乎没有一套针对同性伴侣关系的社会与文化规范,来保持伴侣关系的稳定。其结果是,很多同志难以抵御新的性伴侣的诱惑,加上结束现有关系的社会成本较低,同志之间的伴侣关系往往难以长久。在很多同志看来,公园中发展的情感关系本身即是“畸形”与“非正常”的。同志之间最为看重的是对方的样貌、身材、年纪以及金钱消费能力,而非性格、人品等在主流社会规范中较为看重的要素。同时,由于同志之间没有异性恋婚姻或异性恋伴侣关系中的文化道德、财产关系或者生育关系的约束,因此其开始与终止都很少经过慎重的考虑。公园的同志之间的情感往往被认为是“随意”和“脆弱”的。这也解释了缘何同志需要不断参与到同志渔场中来,且不断地重复短暂的性伴侣关系. 男女关系有婚姻法,有登记什么的,有程序什么的,而且还有财产的分割,小孩的抚养。但是两个男性之间本来就是非正常的,不可能也画一个框,两人之间,因为外来的因素,可能突然间就中断了。但是你正常婚姻不一样的,婚姻有伦理道德,受到管束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就算有‘红杏出墙’的问题,也不可能马上就画上句号的。但是同志在一起。让什么来约束你呢?保证你们就是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我说呢,同志之间很(复)杂。这个也体现在为什么X公园的同志显得比较滥交。(访谈20111016A) 5.2 公园舞蹈与“非正常”的文化身份 X公园的同志对于“非正常”的标签的体验,亦显著地体现在他们对公园中的舞蹈活动的参与。在X公园,普通的公园使用者会组织一些大众性、以交谊舞为主的舞蹈活动。同志则是这类舞蹈活动积极的参与者。同志缘何会参与到一项由异性恋者主导的公园活动之中?一方面,舞蹈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但另一方面,参与到舞蹈活动之中对他们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很多位受访的同志舞者对公园内边界明确的“同志地带”有着复杂的态度。他们认为,同志群体在空间上的聚集,加重了他们对于“非正常”的身份标签的体验。同志之间的亲热行为,似乎显得过于张扬,并且会吸引公园中的异性恋群体好奇、甚至是仇视的目光。再者,由于X公园在很多同志的心目中被贴上了“滥交”的标签,一些同志对公园中“非正常”人士积聚而形成的文化氛围感到不舒服。但他们又离不开公园的同志文化氛围。于是,公园的舞蹈空间成为一个替代性的,但显得更加“正常”的交友空间。舞蹈的空间汇聚了不同性取向的人群,本身不带有明显的性身份色彩。同志通过交替与女性异性恋者、男性异性恋者,以及男性同性恋者跳舞,可以很好地掩盖自己的性取向。有几位在公园的舞蹈活动中表现活跃的同志,甚至明确拒绝参与到“同志地带”的交往活动之中,而只愿意逗留在舞蹈的场地之中。因此,舞蹈的空间实际上成为了压抑的日常生活与“非正常”的同志渔场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对某些跳舞同志来说,舞蹈提供了他们在“同志地带”之外,体验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机会。虽然这种社会生活依然带有与其他同志进行社交的目的,但同伴情谊的表达,更加遵循“普通人”之间的方式。同志的舞伴既有同性恋者,亦有异性恋者,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管道,使自己以“正常人”的身份进行社会交往,而不用禁锢于“同性恋”这一身份标签。在X公园,“同志地带”通常被称为“我们的世界”,而一般休闲娱乐的空间则被看作“他们的世界”。但对于大部分同志来说,这两个世界不应是隔离的,“两个都是我的世界,都是不能丢的”(访谈20110903A)。X公园“同志渔场”的一大优点,在于“可进可出”当需要与同志亲密交往的时候,可以进入“同志地带”,当对“同志地带”中“非正常”的文化氛围觉得厌烦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普通公园使用者的文化活动之中。 在一个异性恋主导的社会氛围中,同志也需要短暂地在外人面前“展演为直男”(passing as straight)。这体现在跳舞的同志都比较倾向于选择女性,而非男性舞伴。与女性之间面对面的舞伴关系,使得同志临时体验了与异性之间较为亲密的关系。正如许多受访同志所言,交谊舞往往在不经意间被刻写上“异性恋”的色彩:一男一女搭配跳舞被认为才是“正常”的,而男女舞伴之间总有一些异性亲昵的成份在其中。与女性搭配舞蹈,使得很多同志相信,即使是同志亦可以与女性进行面对面的亲昵交往,甚至是不经意的暧昧,与“正常”男性无异(即使他们心中依然渴望男性的舞伴)。这样的体验,似乎是的公园同志暂时性地跨越了同性欲望一异性欲望,正常—非正常之间的边界。公园中跳舞的同志,都对与女性搭档感到非常坦然,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空间应有的法则,自己亦不会感觉受到压抑,有的甚至还感到有些自喜。一位经常参加交谊舞的同志如此总结这样的心态: 不可能不过正常生活的嘛。你看我是结婚的人啊,我来到公园之后你可能知道我是gay(同性恋),但是我在跳舞的时候你也不可能知道的。在同志的那几条走廊上,可以放肆一点。但是在这里,都是以一种‘直男’(异性恋)的身份,玩玩而已。没什么压抑的,没什么歧视的。其实在中国呢,大部分人在娱乐当中都是正常的心态,没什么的,正常的交流,正常的生活啊,你不用把它想的很严重什么的。(访谈20110921A) 为了实现与主流人群的“正常”交往,跳舞的同志对于自身的言行、举止都会进行严格的自我规训。在舞蹈的空间,与同性恋相关的语言、同志之间的身体触摸、具有调情性质的动作等,在同志舞者之间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同志舞者也尽量避开男性舞伴,而是倾向于女性舞伴。尽管公园的舞蹈同时被用来进行同志之间的社交,但是社交的内容通常限定在舞蹈技巧的教授与讨论,而与同性欲望直接相关的话题则是被严格避免的。当然,很多普通的公园休闲者也会对男性舞者的性取向产生怀疑,但是同志本身对于其性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这使得公园异性恋群体的怀疑很难得到明确的证实,这也令公园的同志与异性恋群体之间的空间关系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5.3 卖淫、抢劫、敲诈:同志社会关系的重建 主流社会对于同志身份的边缘化,以及同志将“非正常”的标签内化进入对于自我身份的理解,亦使得“渔场”中的社会生活显得复杂与多样。同志渔场中的社会关系,并非仅仅是“同志加战友”般的情感依托,而是同时存在不满、矛盾甚至冲突。这一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即公园同志内部的卖淫现象,以及抢劫敲诈等行为。 在X公园的渔场之中,同志之间的卖淫行为颇为常见②。此类卖淫者在同志圈中被称为MB(money boy),他们往往并非职业性工作者,也不排斥发生非金钱化的性关系。由于公园同志通常只能在渔场中寻求短暂的性关系,这便为一些青年同志提供了机会,在公园之中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在访谈的过程中,常常会有受访者向我们指认周围走动的男性中何人曾通过卖淫获取金钱。这些受访者中,购买过有偿性服务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几位年轻的受访者还被他人指认出曾参与卖淫。公园同志尽管认为卖淫行为是有违道德与社会风气的,但是对有偿性服务本身并不完全排斥。卖淫被理解为一种等价交换的行为,而正是同志“非正常”的文化身份,为这一行为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但与此同时,同志对于卖淫行为的看法也是复杂与矛盾的。对很多同志来说,卖淫行为的盛行似乎使得同志渔场愈发地偏离主流的社会规则与生活方式。由于同志身份的“非正常”,使得同性性关系倒更像一种“稀缺的资源”,因此同志渔场的社会关系也更易被金钱关系迅速占据。卖淫给渔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首先,公园的卖淫行为关注的是性体验所带来的金钱利益,因此严重地挤压了同志之间非商品化的,更为注重真实的互相吸引的同伴关系,使得公园中稳定的伴侣关系更加难以建立。第二,卖淫现象的出现,愈发使得公园同志感觉自身是一个“淫乱”、“滥交”的群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很多同志表示卖淫的行为,以及对于金钱的追求,就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如今在X公园,凡是身材、样貌或是其他特质比较突出的同志,都倾向于将同性欲望转化为金钱的来源。很多资历较深的公园同志都认为,X公园的同志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多年前相比,正变得越来越“不纯真”。大量的卖淫行为,不仅压制了同志之间以情感吸引为目的的交往,更被很多同志看作是有违社会诚信道德的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同志对于社群的公共形象的忧虑。 为何卖淫现象会在同志渔场这一社会空间中迅速蔓延?首先,这和中国近年来迅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有关,经济利益正在成为建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维度。第二,由于卖淫者利用了同志“非正常”的身份以及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金钱逻辑对于同志渔场的改造与重构似乎显得更加的迅速与彻底。最后,也是令同志最为沮丧的一点,即很多参与卖淫的同志觉得既然在一个异性恋至上的社会很难建立稳定的情感和长久的伴侣关系,那还不如利用同志的性欲望谋求经济利益,这样至少对自己在这个后改革时代的经济地位有所裨益。相反,同志社群内部的友谊、情感与信任所受到的重视反而与日剧减。 同时,由于同志对自身“非正常”的身份标签倍感纠结,因此他们更愿意向外界展示一个“文明”、“道德”以及“正常”的文化形象。而卖淫行为,使得公园同志的形象偏离了主流社会中“文明”的定义,而这更加深了同志对于自身身份的羞耻之感。很多同志认为,卖淫行为不仅会给同志群体“抹黑”,使得外界将同志看作一个性行为随意的群体,更有可能挑战公园的管理人员对于同志渔场容忍的底线,引发公权力的介入,最终导致同志渔场的终结。多位受访者都表示,由于同志本身是社会的少数群体,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应当弱化自身“非正常”的形象,对自身行为加以约束: 如果从没有偏见的角度看,正常的男的和女的,还是男的和男的,其实都有这样的行为。只不过因为你是社会上的一个小部分,所以给人感觉不是很好。最起码,如果是男女之间的卖淫,可能正常人会看得很淡,……,因为他们是主流。虽然说男的买男的,根本道理是一样,但主流人群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我们这种人毕竟在行为上还是让人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感觉。你可以不是那么主流,但是你不要张扬。就是说,你可以是同志。但是你太引起别人的主意的话,实际上会招来别人的反感。(访谈20111105C) 出于对卖淫行为的矛盾心理,很多同志逐渐不再倾向购买金钱化的性体验。于是,目前X公园的MB群体正在逐渐转向一种“强制性卖淫”的生存模式,即事先不透露自己卖淫者的身份,而是假装和公园的同志之间产生相互吸引,在发生性关系后,向对方表露自己的真实目的,索取金钱回报。这样的卖淫方式,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欺诈。但公园同志为了避免将事情影响扩大,对自己的名声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往往选择付钱以息事宁人。这种强制性的卖淫行为,使得同志渔场中的社会互动愈发显得“畸形”与“非正常”,同时也严重伤害了同志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社群的团结。 另一方面,公园同志之间原先较为和谐的关系,也受到了日益泛滥的抢劫、偷窃以及敲诈的影响。这些行为,同样是同志“非正常”的文化身份与金钱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形式与上文所说的“强制性卖淫”亦十分类似。通常情况下,一些公园同志会佯装和其他同志一见钟情,随后要求和对方发生性行为。由于顾虑到自己的“非正常”身份,同志很难将临时性伴侣带入自己家中,因此通常只能在快捷酒店发生短暂的性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同志由于自身孤立无援,往往很容易被对方偷窃或者抢劫随身财物。而抢劫者由于获知了对方的性倾向以及一些个人信息,往往威胁受害者,阻止其报警。受害的同志,碍于此类经历的“不光彩”成分,亦通常不愿向警方报案。这样的经历,公园中的很多同志都曾亲身体验,这更使得他们对X公园抱有一种日益警惕不安的心态。 当然,卖淫、抢劫、敲诈等行为亦是异性恋人群中经常发生的。但对X公园的同志来说,这些行为似有着更加突出的社会与文化意义。首先,这类行为的发生和同志的性身份息息相关,社会关系的“畸形化”实际上是文化身份在霸权话语中“非正常”的体现。其次,在异性恋的社会中,敲诈、卖淫、偷窃、抢劫往往被看作正常社会生活之外偶然的越轨行为,但这些现象在X公园的渔场中似乎时时刻刻发生着,且成为了渔场社会生活中相当主要的成分。“非正常”的文化身份是“强制性卖淫”等“畸形”的社会现象的结构性背景,而这些“非正常”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加深了同志对于“非正常”这一标签的体验。这些“畸形”的社会关系,严重地损害了同志群体内部的团结,在同志之间催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使得一个本身即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内部变得四分五裂,对于同志的赋权与解放亦会产生可想而知的负面作用。 6 结论 Leap指出,同志的社会空间具有丰富的意义,并且被刻上了社会过程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烙印。通过同志自下而上的实践,物质性的“场所”被转化为了社会的产物,一个具有一整套行为轨迹,社会关系以及文化意义的“空间”[7]。随着空间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兴起,很多学者指出,空间并非是社会现象被动的物质载体。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实践是社会过程形成中的重要维度。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生产,与相应的空间实践之间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47]。本文从同志群体的城市空间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空间的生产以及空间实践对于社会关系的建构与重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生产出的文化意义。“同志渔场”的出现,本身即是性少数群体的身份在主流文化体系中被边缘化,以及寻求自我救赎的结果。而这一边缘化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同性恋群体的空间行为与空间实践。同志的空间实践,又重新建构了同性恋群体的文化身份,以及同志内部、同志与公园异性恋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这些复杂的社会过程的结果,是新的有关“非正常”标签的社会体验的生产。 在经验研究的层面,X公园的同志渔场丰富了我们对于性少数群体公共空间的文化意涵的认识。通过对公园同志的社会空间的生产进行微观分析,研究可对英文圈文献中对性少数群体社会空间的研究起到细化的作用。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志这一群体的形成,与石墙运动后的英美国家有显著的区别。在中国,边缘的性身份相对于主流的性文化,往往不是针锋相对的关系,而是存在很大程度的协商,服从甚至是妥协[48,49]。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这种服从与妥协对于性少数群体的赋权与解放有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作用。在X公园的同志渔场,“非正常”这一霸权性的定义通过性少数群体的内化而进入自我的主观性的建构中,并催生出更多的“畸形”或“非正常”的体验,使得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更加复杂与艰难。“异性恋至上”这一霸权性的文化结构,给X公园的同志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不安甚至伤害。通过分析性少数群体的社会空间,本文希望对于我们理解亚文化群体形成与演变的轨迹有所助益,并促进我们对客观存在的文化压迫问题的反思。 ①“同志”是华语世界中对于同性恋者的一种称呼,起源于香港,与政治话语中的“同志”一词有较大的区别。本文的“同志”皆指代同性恋者。 ②X公园中亦存在大量的异性恋男性向同志卖淫,后文提到的抢劫敲诈也不乏异性恋者的参与。这一现象体现了异性恋者将“同志”的性欲望转为经济机会。出于研究篇幅所限,本文暂不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