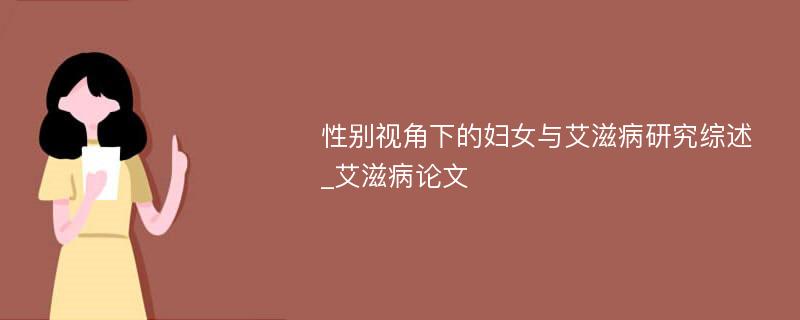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与艾滋病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滋病论文,视角论文,妇女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6)03—0028—05
一、本文研究背景与基本概念
尽管艾滋病最初是在男性当中发现的,目前男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仍占多数。但目前,女性感染艾滋病的速度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2004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估计,2004年全球3940万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有1760万,占3720万成人艾滋病患者总人数的47.31%。
我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尽管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仍以男性为主,但是,女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也在急剧上升。并且两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数量正在趋近。
表1 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的比例变化
年份 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 2004年1—9月
百分比(%)
15.3 14.3 19.4 22.7 25.4 35.6 39.0
资料来源: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第8页。
艾滋病的传播有三大途径:性接触、血液和母婴垂直传播。从全球特别是非洲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变化情况看,不管艾滋病病毒感染早期是通过何种形式传播,最终都会发展到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感染。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我国目前注射吸毒和性接触已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现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经注射吸毒传播占4.3%,经性传播占43.6%,经采供血/血制品传播占10.7%,母婴传播占1.4%。2005年新发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传播占49.8%,经注射吸毒传播占48.6%,母婴传播占1.6%。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虽然仍占较大比例,但主要是1996年以前发生的感染。性接触传播是世界上(包括我国)艾滋病在女性中传播的重要途径。经性接触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2001年是44.%,2004年上升到55%。[1]
因此,关注性别与艾滋病的问题,不仅应成为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急迫任务,也应成为它的防治方面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本文作为湖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防治项目——《师范院校潜在教师艾滋病防治IEC 技能训练与教育模式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主要对目前学术界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妇女与艾滋病问题的研究进行一个梳理,找出今后研究的可能方向。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艾滋病研究与社会性别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社会性别理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当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社会性别理论首先肯定和承认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同时认为社会性别是两性在特定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形成的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和行为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社会性别观念、规范和结构也都不同。其次,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构成,是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导致歧视性的社会性别。最后,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构成,是可以改变的,性别歧视也是可以消除的。
基于以上理论,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两性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它把女性视为发展的主体,但并不将男性作为对立面;强调一直受到漠视的女性价值,反对孤立地研究女性和女性问题,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研究男女两性的社会和权利结构、分析性别文化、性别制度和性别结构。这样既能看到男女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同时也能看到男女两性受到的不同限制和制约,了解男女两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利益与要求。从而有助于消除性别歧视,建立两性之间均衡发展的平等关系。
社会性别理论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和视角。社会性别理论要求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一切决策与学术研究中,实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主流化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社会性别意识与主流化。社会性别意识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的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重新审视和反思现存的两性关系和性别规范,将其放在是否促进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尺度上衡量,通过清理和消除两性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壁垒和障碍,扩大男女两性的选择性,促使男女两性的全面健康发展。在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社会性别意识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社会性别主流化,即将性别意识引入社会发展以及决策主流。政府要担负起促进妇女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该推行一种积极醒目的公共政策,把性别意识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建立国家及地方一级的性别平等机制,保证性别意识的政策和方案切实得到实施和有效的监督。
在中国,社会性别理论经历了引入和传播两个阶段:1993—1997年,是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阶段,1993年天津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女性与发展研讨会”上,“社会性别”一词被首次介绍到中国,引起我国学者特别是女性研究学者的浓厚兴趣;第四届世界女性大会(北京,1995)的召开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在这一阶段,通过媒体(如《中国妇女报》)的报道、相关文章的译介、理论研讨会、社会性别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社会性别理论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1998年至今是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与应用阶段。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提供的“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社会性别制度、女性社会地位等各种社会问题。随着我国艾滋病的不断蔓延,妇女与艾滋病也成为女性学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2],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
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艾滋病研究综述
纵观我国学术界的艾滋病研究历程,笔者认为,以2003年为分水岭,我国学者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艾滋病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2年是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意识到社会性别视角在艾滋病研究中的价值,开始对特定人群艾滋病问题进行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2003年至今是社会性别视角运用的发展期,随着女性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中比例的急剧攀升,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
1、1998—2002年:研究起步阶段
1998年,王金玲等人首次尝试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对性病的流行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社会财富与资源配置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商业性交易出现的重要原因。但此时,她的关注重点还是性病,艾滋病只是作为一个新的性病变种参与讨论。[3] 2001年,王金玲再次运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商业性交易中的艾滋病传播问题,指出由于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商业性交易中嫖客是艾滋病传播中的首要和主要责任者,暗娼应该定位为易感人群。[4]
同样也是针对商业性交易人群,潘绥铭运用性的网络理论,根据自己在1999年8月—2000年8月主持的一次全国分层抽样调查数据指出,那些既与性工作者有性关系又与其他性伴侣有性关系的男人是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桥梁人群;女性处在性网络的亚中心位置或边缘,更容易受到艾滋病、性病等的侵袭。是最大的受害者。[5]
此外,张北川将研究目光投向男同性恋群体,通过对男同性恋者的实证研究,揭示艾滋病传播和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关系。[6][7]
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社会性别视角进行艾滋病研究,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是艾滋病流行的深层原因,提出男性是主要责任者。但研究范围局限在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对象集中在商业性交易人群、男同性恋者、卖血人群等特定人群,缺乏对艾滋病影响的性别差异、应对策略等的探讨。
2、2003年至今:研究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手段综合化,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范围扩大化势头比较明显。学者们开始反思以往艾滋病防治政策、措施和研究中的性别误区,并对艾滋病感染原因、艾滋病影响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还提出了许多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艾滋病防治对策。
(1)对以往艾滋病防治措施的重新审视
杜洁重新审视了以往在艾滋病感染、艾滋病研究和政策中的男性视角,认为以往的研究和措施往往只针对男性,甚至将它看成男性问题,对女性艾滋病问题的重视不够,比如只将商业性交易中的女性、孕产妇纳入研究视野,忽视对一般女性的研究,或者只强调女性在艾滋病关怀中的照料角色,忽视女性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主体性和决策作用。[8] 李飏认为在艾滋病传播的头10年,大部分女性漏诊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研究和预防措施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是社会性别观念限制了女性的发言权。[9] 钱鑫从女性权利方面指出,我国有关艾滋病的政策未能充分正视和承认女性权利,如一些政策法规将儿童权利与女性权利相混淆的权利主体的错误,某些惩罚性的法律法规阻碍了对女性群体的艾滋病干预,特别是商业性服务女性的女性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10]
对以往艾滋病防治的重新审视尽管不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但三位学者提出的观点仍让人耳目一新。
(2)对艾滋病传播的性别差异的社会因素探讨
这一阶段,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把妇女放在主体的地位,充分论述了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除了生理上的易感性之外,社会性别不平等是艾滋病流行特别是在女性中流行的重要原因。其中传统社会文化对两性的期望和要求的双重性、两性社会地位(包括经济、政治等)不平等、两性获得社会支持机会的不平等等因素是学者们共同认可的原因。
龙秋霞自2002年实施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自主项目“社会性别与艾滋病”以来,一直致力于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妇女与艾滋病”问题的研究。她通过对广东省范围内艾滋病流行状况的实证调查,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存在“两低一高,两多一少”现象。即对艾滋病防治知识认知程度总体偏低,安全套使用率普遍偏低,女性被配偶或男友感染的概率较高;与女性相比,男性性观念更加开放,非婚性行为更多,婚外性伴更多,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性生活中普遍依从男性,决定性事的主动权更少。为此她提出“除了女性在生理上的、流行病学上的易感性之外,传统的性观念、性文化、以男性为中心的性行为模式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因素与女性感染艾滋病存在内在关系”。她认为强调男性在艾滋病流行和防治中的责任和提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同样重要。[11] 翁乃群和李飏都看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对女性与艾滋病关系的影响。翁乃群以泰国北部两个不同社会文化的山地族群女性为例,说明不同社会文化下的女性,受到艾滋病的伤害不尽相同。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不只是生物医学的问题,更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12] 李飏以全球视野分析女性还面临着不同地区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适当的性行为等文化适应的压力。[9] 钱鑫认为男女性权利不平等,男性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女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也是女性感染艾滋病的重要因素。她还指出性暴力是艾滋病传播的加速器,另外惩罚性的社会规范本身存在的社会性别偏差并没有给女性以平等的对待和足够的保护,也是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因素之一。[10] 张开宁认为领导岗位的女性缺席也是原因之一。[16]
杜洁则着眼于两性对比研究,认为男女两性都具有对艾滋病的易感性,男性对艾滋病的脆弱性表现在:男性由于在社会性别分工和权力结构中较高的地位,拥有较女性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力量主动进行一些行为(如买淫),或为了完成社会对自身男性角色的期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不得不从事一些高危行为(如贫困男性卖血)。[8]
(3)关于艾滋病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
由于相关的分性别数据较少,大多数学者基本没有涉及艾滋病的影响研究。尽管如此,杜洁、李飏、钱鑫还是对艾滋病影响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理论推断和探讨。他们认为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导致了男女受艾滋病影响的不同,反过来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又使得社会性别不平等更加突出。例如由于社会性别文化的双重标准,女性受到比男性更多的来自社会甚至是家庭的歧视和孤立。艾滋病的流行还使女性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角色,如艾滋病人照料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家庭经济支持者等众多角色使女性不堪重负,艾滋病还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由于所处的弱势地位,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救助机会、医疗条件等,生存状况明显劣于男性,生存期限明显短于男性。在资源短缺情况下,女童的辍学和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4)基于社会性别视角提出艾滋病防治建议和措施
学者们一致赞同在艾滋病防治和干预中注入社会性别视角。认为在各项政策、措施、办法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当特别注意到女性在原有社会性别机制中的不利地位及伴之而来的艾滋病易感性。提倡社会性别主流化,强调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
龙秋霞提出在全社会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确立性别平等意识,认为应当通过大力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普及教育、强化行为干预,发动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防治体系,提高女性的自主防范意识、倡导男性责任,加强女性抗击艾滋病的能力建设,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其弱势地位,阻断艾滋病向一般人群的蔓延。张开宁提出以“项目”的形式进行艾滋病的预防和干预,认为在项目中融入社会性别视角有助于将艾滋病应对项目划分为有害项目、无害项目、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项目和具有创新性的艾滋病项目,从而使艾滋病防治项目在增强女性权力,提高女性地位,保护女性免受艾滋病伤害发挥更大的作用。[13] 钱鑫认为解决女性与艾滋病问题的核心是女性的赋权和维权问题,指出应当保障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应当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和财产权,应当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应当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家庭暴力,应当保障女性获得平等的健康医疗保障权利。李容芳结合实践论述了社区支持功能在艾滋病防治中的特别是针对女性艾滋病防治的优势,提出艾滋病女性化防治的社区支持原则——有利、尊重、公正和社区互助。[14]
三、结语与讨论
社会性别理论为艾滋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态势也为社会性别视角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国学者从社会性别视角对艾滋病的研究呈现了如下特点:
1、与其他研究视角不同,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艾滋病研究注意到男女两性的不平等,特别突出了作为主体的女性。从研究的侧重点来看,女性与艾滋病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在审视以往艾滋病防治政策、措施,还是论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原因,或者推断艾滋病带来的影响,以及提出的对策等各个方面,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以女性为主体,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是艾滋病在女性中流行的重要因素。而且从研究者自身的性别来看,绝大多数也都是女性。
2、研究对象正由单一走向多元。在研究视角运用的初期, 学者们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商业性交易人群、男同性恋人群、卖血人群等特定的高危人群,进入发展期,除了高危人群的研究,学者们已开始把普通人群纳入研究视野(如龙秋霞)。研究对象的变化与我国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流行趋势关系密切。
目前我国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艾滋病研究仍处在发展期,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如可以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研究、现行艾滋病防治政策、措施、办法,归纳总结出更有利艾滋病防治的对策;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进行跨地区、跨文化、跨民族的对比研究、系统研究,等等。
但是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艾滋病研究要想取得更大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扩大研究的主体,即将男性也纳为分析主体。虽然艾滋病问题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男性角度出发或直接将其视为男性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将男性作为社会性别视角艾滋病研究的主体来分析。女性作为社会性别视角艾滋病研究的主体,固然有利于改善妇女环境、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抵御艾滋病的能力。但正如社会性别理论所特别强调的那样,妇女要得到真正的发展,还需要男女两性共同反思传统性别规范对两性发展的束缚,只有男女两性共同联手,才能更有效地抗击艾滋病。
收稿日期:2006—04—20
基本项目:本文由全球基金第三轮中国艾滋病项目资助,编号:GF05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