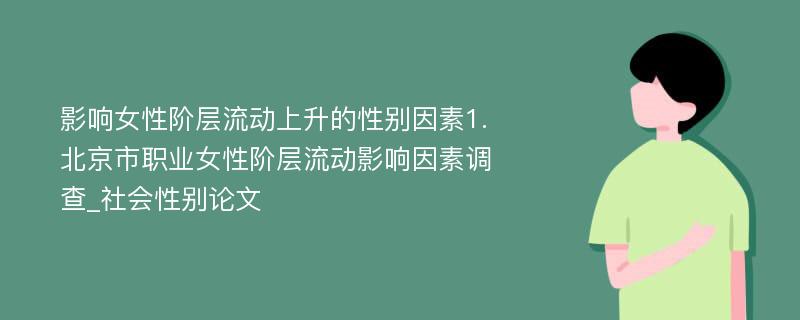
影响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①——北京职业女性阶层流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因素论文,调查研究论文,北京论文,职业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06)03-0012-05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就是指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转变的现象,上升流动即指社会地位从低向高的转变。以往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以男性群体为考察对象,未见性别分析数据。另有研究者指出,将女性群体的分层涵盖于社会整体的分层之中会忽视女性分层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构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更有必要对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迁做社会性别分析,以破译与解构社会转型中性别不平等机制的建构与运行机制。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对职业女性代内上升流动的影响因素做社会性别分析。“上升流动”指现职较前职社会地位的上升和现职内职务的晋升。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了解调查参与者② 阶层变化的状况,并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对所获资料做深入分析。
调查参与者选择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划分。具体做法是,(1)依“十大阶层”的划分,分阶层选择调查参与者。(2)依据十个阶层中各类人员所占比例,将调查参与者确定为9个阶层中所占比例最多的一类人员,它们分别是:低层行政管理者、教科文卫专业人员、低层经理人员、小企业主、党政机关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蓝领员工、第二产业非技术工人、普通农户以及下岗职工和其他失业人员。(3)为了能够了解有过上升流动经历者的主观感受(经验),尽量选择3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4)为了进行性别比较,每阶层都选择少部分男性。
(三)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在北京市海淀、朝阳、西城、宣武、东城、崇文、昌平等7个区进行。问卷主要由课题组成员进行一对一访谈方式填写,少部分由调查员发放。调查历时两年,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11份。所获样本的阶层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的阶层分布情况 (单位:人)
阶层 男性 女性总数
低层行政管理者1029 39
教科文卫专业人员
1252 64
低层经理人员 1045 55
小企业主
1117 28
机关办事人员 5 13 18
商业服务业蓝领员工 1840 58
第二产业非技术工人 2429 53
普通农户
4 23 27
下岗职工和其他失业人员1742 59
其他 8 2
10
合计 119
292 411
二、调查参与者的基本情况
调查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9.65岁,其中,男性40岁,女性39.51岁;男性年龄最大的59岁,女性年龄最大的60岁。
从调查参与者的受教育情况看,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占30%,其中受大学本科以上教育的女性占女性调查参与者的31.28%,受大学教育的男性占男性调查参与者的26.96%。男性中有30.44%的被调查者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女性中有15.86%的被调查者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调查参与者中有9.76%的女性为中共党员,男性中有12.5%的人为中共党员。
调查参与者中,已婚者329人,其中男性91人,女性为238人,女性已婚比例为81.5%,略高于男性,男性的离婚比例略高于女性。
三、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特点描述
1.女性上升流动比率低于男性。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的(45.96%)的女性调查参与者认为,自己最近一次的职业变动是上升流动,24.76%的人认为自己在最近一次流动中,阶层地位有所下降。比较男性调查参与者,14.29%的人认为自己最近一次的职业流动为下降流动,比女性低10.47个百分点;51.21%的人认为自己在最近一次的职业变动中实现了上升流动,比女性高5.25个百分点。
相关研究分析女性职业流动的变化时认为,第三产业中知识密集型行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村女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下岗女职工提供了再就业的机会。但是女性被鼓励在第三产业就业,造成了女性职业的下沉[1] (P25-29)。
2.配偶间阶层地位存在明显差距。调查发现,女性与其配偶的阶层地位存在差距(见表2)。差距最明显的是失业半失业女性群体,该群体中没有人比自己的配偶职业地位高,除11.11%的人与配偶同处一个阶层外,所有调查参与者的阶层地位均低于其配偶。数据显示,机关办事人员以下的阶层中,配偶阶层高于女性调查参与者的情况明显,而女性参与者职业地位高于其配偶的情况不明显。这从婚姻家庭的角度反映了两性阶层地位的差距。
表2 女性调查参与者与其配偶的阶层认同情况 (%)
配偶低层行政
教科文卫 低层经理 机关办事 小企业主 商业服务 产业工人
农业无业、失
其他
女性
管理者专业人员人员 人员员工 劳动者 业、半失业
低层行政管理者37.9
20.7 13.8 3.4
3.49 8.3 - -3.7
教科文卫专业人员
15.4509.6 9.6
5.88 -
- -1.6
低层经理人员 11.1
24.4 24.4
20
2.2
14.22
- -1.4
机关办事人员 17.6
17.6
5.9 41.2
5.910 -
- -1.8
小企业主
23.17.7
7.7 7.7
46.2
6.3-
- -1.4
商业服务业员工 -16.67 13.33 -23.33 16.7 23.33 -6.7
产业工人-11.11
-
5.56 27.78 33.3 11.11 - -
11.11
农业劳动者 4.55
9.09
-
4.55 13.64
-18.1840.9
-9.09
失业半失业者 2.78
8.33 5.56 2.78 22.22 11.1 30.565.56 11.11
-
合计 1.89 11.32 5.66 2.83
21.7 14.2 22.6410.4 5.7
3.77
一项对宁波市职业代内流动的性别分析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职业流动面较窄,更多是在较低职业层流动;男性职业流动的年龄区间较大,女性的职业流动的年龄区间集中在36~55岁;两性的职业地位在婚前婚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但是女性职业变动者所占的比例更多,职业变动的范围更大,职业地位的下滑更甚[2] (P101-113)。
3.在代内流动方式上,女性较男性被动。从最近的一次职业流动看,调查参与者获得现职的主要途径均为劳动人事调动和自己应聘,但女性调查参与者更依靠这两个途径,较男性分别高出2.3和3.2个百分点;而通过竞争上岗和自主创业方式来改变地位的男性调查参与者,分别较女性高出1.1和10.8个百分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调查参与者代内流动途径的获得较男性被动。
4.在女性群体中,有上升流动经验者的比例因阶层不同而差异明显。我们对参与调查的女性群体做了阶层分析,发现低层行政管理人员对自己上升流动的感知最为明显(80.8%),其次是低层经理人员(78.6%)以及科教文卫专业人员(62.2%)。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小企业主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两个阶层较其他阶层经历过更多的职业流动。但小企业主中只有41.7%人有过上升流动经验,商业服务业人员更少,只有39.5%的人有过上升流动经验。失业和半失业阶层上升流动的机会更少,只有5%的人有上升流动经验。
5.在女性群体中,上升流动的获得途径因阶层不同而差异明显。在调查所设计的7种流动途径中,低层行政管理人员和教科文卫专业人员主要依靠人事调动实现流动;商业从业者和工人主要依靠亲友关系获得流动机会,小企业主靠自己创业;经理人员和机关办事人员则主要通过应聘实现流动。
四、影响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看到,女性上升流动比例低于男性,下降流动比例高于男性;在上升流动的途径获得方面,女性也较男性被动。为什么两性在上升流动方面有这样的差异?调查参与者认为:
1.性别对女性的阶层流动具有更大的负面影响。调查问卷设计了“性别对职业、职务选择有无影响”、“性别的影响是有利或者不利”,以及“影响的程度”等问题。统计结果发现,54.3%的女性被调查者认为性别对职业选择有影响,35.6%男性的被调查者有相同的认识,女性比男性高18.7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认为“有影响”的女性被调查者中,95%的人认为是“不利”影响,而只有9%的男性认为性别给其职业选择造成“不利”影响。
可见,女性调查参与者对“性别”对职业选择的“不利”影响感受十分强烈,相关调查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2003年一项对北京市14所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当被直接问及是否同意“女性就业难于男性”时,男女两性都表示同意,但女生持“完全赞同”的比例大大高于男生(高出25.2个百分点)。在女生之间,非北京户籍的女生持“完全赞同”的比例高于北京籍女生10个百分点,而北京籍男生与非北京籍男生之间对此认识的差距却不大(只相差1个百分点)。该研究从“劳动力的性价比”的角度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指出“女牌”劳动力的“性价比”低于“男牌”劳动力,是“女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3] (P48-83)。
2.“女主内”的角色定位限制女性上升流动。性别为什么成为女性职业选择的“不利”因素?调查发现,“父母”、“配偶”、“孩子”、“工作地点离家近”等涉及到“家庭”的因素对女性调查参与者的影响均大于男性。在女性群体中,“女主内”的角色定位对女性农民的职业选择影响最大(50%),其次是机关办事人员(17.4%)和小企业主(15.4%)。问卷设计了“自我发展”以及“自我实现”等影响上升流动的因素,统计结果表明,两性均认为职业有前途、稳定和有保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在“职业有发展前途”选项里,男性调查参与者高出女性9.5个百分点,而在“工作稳定\有保障”选项里,女性被调查者则高出男性5.7个百分点。男性调查参与者对“个人爱好”的选择也高出女性4.7个百分点。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将“家庭因素”列为影响职业选择的首要因素。说明在职业和家庭发生冲突时,一部分女性会选择放弃,或低选职业,优先保障家庭的利益(或丈夫与子女的利益)。相反,对男性而言,个人发展以及组织因素是其择业的最主要原因,家庭因素对他们职业的选择则不构成主要的影响。
3.女性上升流动更需要挑战现有社会性别规范。许多女性调查参与者认为,稳定有保障且兼顾家庭是影响自己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但是,上升流动的机会往往与这些因素相冲突,即更高的职位通常意味着:不能兼顾家庭、更多的自我能力展示、更大的风险,因此,女性在面对上升流动机会时较男性的心理冲突更大。女性的这种矛盾心态,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社会分工的模式下挤压出来的一种心理态势,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着共同的表现。一些专家将女性的这种矛盾心理定义为“成功恐惧”,认为这是在男权文化的背景下影响女性全面发展的深层心理障碍。
现阶段,社会依然鼓励女性遵守职业/职务上的“男高女低”的社会性别规范,以各种“社会性回报”奖励女性选择将行为固定在那些服务他人、特别是服务亲人的行为上[4] (P175)。最重要的“社会性回报”方式就是赞扬大多数规范的遵守者,与此同时,“嘲笑”、“惩罚”社会性别规范的挑战者,从而孤立了“挑战者”,强化了女性的“成功恐惧”。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女性行政管理人员、教科文卫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在最近的职业变化中,均有半数以上的人有向上流动经验。但是,其他阶层女性向上流动的经验缺乏。
2.在争取向上流动机会方面,女性个体较男性面临更明显的社会性别因素限制,女性个体反限制的努力使个人付出高昂“代价”。
3.女性个体抗争社会性别因素影响所付出的“代价”,对女性群体具有一定程度的负警示作用。
因此,我们建议:首先,加强“女性群体”研究。本研究提示,女性是有差异的群体,但是她们更是休戚与共的性别群体,社会学研究者应对女性个体、阶层、群体间的关系做深入研究,提出可指导实践的理论解释。如陈雁研究了近代上海职业女性群体的形成,指出:对于大多数职业女性而言,家庭与孩子是职业进程的最大障碍,当家庭与职业出现矛盾时,大多数职业女性还是无奈地选择了回归家庭[5] (P346-363)。熊秉纯在台湾的家庭工厂做研究时发现,这些家庭工厂里的老板娘对工人来说,总是站在厂方的立场,扮演着监督、剥削工人的角色,极尽所能地维护资方的利益。但是很多工厂的老板是不给自己的太太(即老板娘)工资的。虽然老板娘的身份使她享受着一般工人不可能享受到、并且很令工人羡慕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但是其无偿家属劳动者的处境和身份,使得她就某种意义来说连女工都不如,因为女工至少还有一份工资,可以掌握一点经济和消费权。熊秉纯指出,女工和老板娘均单独反抗男性的压迫,但是,她们没有联合起来反抗,因为,她们有不同的角色和利益。这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女性群体的共同利益如何与阶级/阶层利益交织在一起[6] (P17-32)。
其次,鼓励各阶层女性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本研究提示,女性个体反抗社会性别因素限制的力量非常有限,且“代价”主要由个体承担,在社会上造成了“孤立的女强人”的现象,这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落后的社会性别观念。女性群体地位的改变不能靠女性个体的自我牺牲,应鼓励女性组织起来,特别是不同阶层的女性均应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吕美颐研究指出,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女性群体中出现了两个新阶层——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和产业女工。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推动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即意识到她们与男性(包括家庭中的男性)利益的区别[7] (P569-590)。
社会学家盖奥尔格·西美尔指出:“迄今为止,在妇女个人的社会学的状况里,存在着某些很奇特的东西:即她是一个女人,但她在实际上不能与其他的妇女们休戚与共,她们被禁锢在家的界限之内,促使她献身于一些完全单独的人员。”西美尔注意到,“‘妇女’的概念新近所经历过的社会学方面的进化,这种进化表现出很多一般不容易观察到的形式上的麻烦。由于妇女被迫生长到家庭的利益中,影响了她们与男人的彻底的分化。”是妇女运动让人们意识到了妇女们的存在,意识到她们在权利和利益上有别于男人[8] (P324-327)。
历史经验表明,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是妇女运动推动的结果,因此,代表各阶层女性群体利益组织的建立是推动社会性别意识觉醒的必由之路。建立这样的女性组织,不仅能推进职业领域女性的上升流动,也有助于增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推进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发展。
注释:
①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5年课题《妇女阶层上升流动影响因素》成果,课题负责人为王凤仙。
②我们称“调查对象”为“调查参与者”,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她/他们参与的结果,研究成果里包含她/他们的经验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