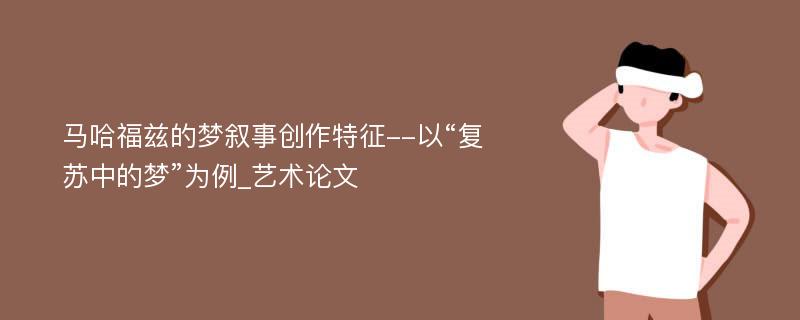
马哈福兹的梦叙事创作特色——以《痊愈期间的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马哈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拉伯小说之父”、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jīb Mahafūz,1911-2006)在回望所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是何种心境?其艺术源泉是几近枯竭还是依然汩汩流淌?其作品中表现的批判精神和实验性是有所减弱还是一如既往?特别是当他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被指控“渎神”、其本人在1994年幸免于宗教极端分子刺杀后,年逾80岁的老人是“躲进小楼”不问世事还是依然关注世纪之交命运多舛的阿拉伯世界?老作家的封笔之作《痊愈期间的梦》给出了答案。 晚年的马哈福兹在疗养期间虽病卧床榻,但并没有割断与外界的联系。通过友人的拜访聊天和秘书的读报交流,他仍抑制不住自己创作的强烈渴望,通过口授,让秘书记录了500个梦。自1998年起,这些短小、隽永、凝练、抒情、奇幻的“梦境”在埃及《半边天》文化周刊上连载。2005年埃及舒鲁格出版社出版了《痊愈期间的梦》单行本,包括其中的146个梦。该作品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也随之发行。该书舒鲁格第四版(2009)收录了206个梦,每个梦被标以序号。在编者序中,《半边天》杂志主编、著名女作家赛纳·茜碧这样评价这部散文诗般的作品:“您的梦境鞭策头脑,振奋思想,震撼心灵,记录历史,开拓文学之路,表现出对艺术的敬畏……您以电报般简洁的文字浓缩人生的收获,洞烛幽微,眼观四方,擅察新世纪文学的掌纹,以梦的闪回,将一年融于一词,将一个时代融于一行,将一生融于一句,将人生苦旅、爱恨虚幻融入交织着情感的梦境文本中,将艺术想象织入现实的梦境中,将青春的苦涩融入长者的庄严中。”①在茜碧看来,“马哈福兹的梦颠覆了作者和读者间的‘第四堵墙’②,将回忆化作昨日、今日、明日之梦,饱经沧桑,充满寓意”(《痊》:14)。可见茜碧女士对马哈福兹的封闭之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由于该作品采用了飘忽不定、混乱无序的梦境、幻觉、视觉意象、拼接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一经问世,就在读者群和评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为马哈福兹晚年作品仍具实验精神和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而喝彩;也有人觉得作品所采取的隐喻、象征、怪诞、含混的手法使作品过于朦胧和晦涩,给阅读带来了困难,这是艺术性的倒退,认为这是他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分离。③ 2000年5月,埃及《文学消息报》“园圃”栏目曾以《梦的停止便是生命的终结》为题对马哈福兹进行了专访。当埃及著名作家优素福·格依德问他为何采用梦的形式叙事时,马哈福兹坦言,梦可以赋予自己更大的创作自由度,以梦境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作品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当被问及这样写作是否是对现实的逃避和对现实主义写作的摒弃时,他苦笑地反问道:“现实是什么?”继而他解释自己用梦境表达思想的动机:梦是“我”记忆的残存和碎片,“我”将它解析、拼接起来,转译成文字,“我”在回忆,“我”在梦回,“过去我的小说直接来自于现实,而今梦境取代了现实”,“我生活在现实的梦中,也生活在梦的现实中”,“现实世界和梦世界对我来说是同等的重要”;当埃及著名作家穆吉迪·萨阿德问他“梦”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创作计划时,他回答没有,“驱逐我的梦便意味着停止我的写作”④。这些回答不仅反映了晚年的马哈福兹仍具有强烈的创作渴望,而且还表达了他要建构一种以潜意识、非理性为出发点的梦境文体的愿望,以此摆脱任何既有的写作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以更抽象、更简练,也更富有哲理的文本模式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马哈福兹冲破文类界限,采用非散文、非诗歌、非小说的梦境文体来写作并不奇怪。早在1982年他就尝试性地发表了小说《目睹梦境》,以期借助苏非主义超现实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拓宽创作之路⑤。晚年的他越来越觉得“细节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我在作品中主要表达一些哲学思考”,“思考主要集中在时间、此时、死亡等一些哲学命题上”⑥。由此,我们看到马哈福兹的艺术创作自觉地转入到内省、探索心灵自我、反映人类潜意识(或曰反理性)的写作阶段,以期更自由自在地描述不可捉摸的人物命运。 梦是什么?“梦境是心灵的剧场”,“梦是人们灵魂深处极度渴望的产物”,“梦所显示的内容是现实的象征”⑦,“梦是连接意识和潜意识的桥梁”⑧。在《痊愈期间的梦》中,马哈福兹以梦者第一人称的身份自由地运用记忆的碎片,拼接成一个个梦境,在潜意识的彼岸重构时间和空间。这些梦境短的仅仅数行,长的也不超过一页。就像视觉表现主义者那样,马哈福兹的每一个梦境犹如一个静态画面,或表达梦回故乡,或叹息天堂失落,或希冀佳丽再现,或宣泄等待焦虑。这些主题场景既是马哈福兹自传性回忆片段,又是其苏非主义倾向的流露,既反映现代人焦虑、恐惧、非我的生活现状,又讽喻丧失了人生目标和意义、割断了历史和宗教的人类在这异化和荒诞的世界里的境遇。他在评价卡夫卡的作品时说:“我从卡夫卡和表现主义作家那里,发现的是与现实平行的世界,比现实更现实。”(《自》:117)或许马哈福兹用梦境文体要表达的就是“比现实更现实”的世界。 马哈福兹在梦境中,以诗性的语言、象征性的手法来描述外部物质世界在心灵中的投影,女性象征着苏非信徒的神性之爱或最高境界,小舟象征着命运,湖泊象征着过往和人生奥义,阿巴西耶老区象征着永不逝去的童真,回家象征着“永恒回归”⑨。梦幻般的抒情性表达在作品中俯拾皆是,构成了作品的基调。例如在第192个梦中,作者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漫步: 这是一个自由的花园,恋人的泪水浇灌了园中的花朵。我徜徉于花园四处,耳际回响着爱的叹息和抗争者的呼喊。我与自己立下约定:我要借助遗忘来逃避爱和抗争。(《痊》:192) 梦者将自由、爱和抗争这些人生意义凝缩,移置于鲜花盛开的花园,抽离外部世界发生的关于爱和抗争的诸多具体因素和事件发生的过程,只留下这些事件在内心深处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心理困扰和纠结。用“恋人的泪水”、“叹息”、“呼喊”这些抒情性词汇来表现为了获得自由和爱而进行的充满艰辛和苦痛的抗争,以致必须借助遗忘来逃避残酷的现实。“在梦中,心灵几乎不存在记忆,且与清醒生活的日常内容完全隔绝。”⑩梦者欲借助梦达到遗忘。 梦回故乡是作品中重要的主题之一,为该作品抹上了明显的自传色彩。马哈福兹曾经住过的开罗老区杰玛里耶和阿巴西耶是他晚年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失去的“乐园”。在梦中他不止一次畅游于老街区,梦见昔日故人,重现失去的幸福时光: 我梦游于郁郁葱葱的尼罗河之岸。夜晚的空气潮润,月光皎洁,月亮与河水在不停地窃窃私语。我的灵魂游荡在充满素馨花和爱情的阿巴西耶老区的各个角落。我发现我的心灵在时不时地发问:你走了以后为什么没有一次在梦中光顾我,以便让我能确定那是真实的存在而非青春期的虚幻?那印刻在我幻想中的图景本来就是真实的吗?正在这时,一声旋律从黑暗的街区传来,先化作幻影,继而在第一束街灯的照射下显形,清晰可辨。让我吃惊的是,我对它并不陌生,它是我少年时常常见到的努哈西亚乐队,乐队走在出殡队伍前列,那旋律我几乎背得下来。此次幸运的是,我失去的恋人也跟在队伍后面,她容貌姣好,步履端庄,风姿绰绰。最后,她抛开出殡的队伍,惠顾于我,站在我面前以证明岁月没有白过。我受宠若惊地站起来,用全部生命的力量朝她望去,并对自己说,这是能触摸心中恋人的不可多得的机会。我向前迈了一步,张开双臂搂住她,却听见噼噼啪啪的撕裂声,随即意识到裙子轻轻滑落,很快美丽的头颅落在地上,滚进河里,像尼罗河玫瑰一样被浪花卷走,抛下我独自一人黯然神伤。(《痊》:14) 梦者的深层自我打破时空的束缚,离开此岸,飘向梦境中的潜意识彼岸,在昔日恋人的召唤下魂归老区阿巴西耶那散发着素馨花芳香的地方。似乎只有恋人的出现方能印证曾经的青春韶华,证明岁月没有白过。然而,即便在梦中,此时和过往的合一也流于虚无,梦中的过去在此时的拥抱中化为乌有。阿巴西耶区是梦者失去的乐园,在那里,马哈福兹度过了自己孩提时光,经历过美好的青春机缘。埃及著名文评家拉贾·尼高什在《马哈福兹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段奇缘:“有一天我正在踢球,突然被阳台探出的一张迷人的脸吸引。那年我13岁……我一直单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自》:122) 马哈福兹在梦中不仅回忆昔日恋人、亲朋芳邻,而且将埃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名人荟萃于梦,展开辩论,针砭时弊,评价几次埃及民族革命的得失。如在第73个梦中,作者提及1919年萨阿德·扎格鲁勒领导华夫脱党进行的反英民族资产阶级爱国运动、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青年自由军官组织”掀起的民族主义革命;在第177、第189个梦中提及华夫脱党新领袖穆斯塔法·纳哈斯和“开罗纵火案”(11)。“开罗纵火案”发生之后,从1919年伊始的埃及民众反殖民的民族主义革命实质上已宣告结束。 可见,回溯性梦境赋予了该作品自传性特征,梦者正是用梦的凝缩性和象征性,消解了时空,将过往、现在和未来融于作者主体世界的无限广阔性中,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历史风云浓缩于几句话或一个片段。人生如梦,一切如过眼烟云,岁月无声地改变一切,经过时光之筛的过滤,唯余下怅然与凄凉。此时的马哈福兹正像中国宋代文学家苏轼那样,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马哈福兹的梦不仅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桥梁,而且是揭示现代人极度的孤独感、焦虑感的有效手段,是对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混乱无序、荒诞不经的阿拉伯世界现状的隐喻性表达。梦的荒谬隐喻了现实的荒诞与怪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阿拉伯世界乱象丛生,巴以冲突不断升级,中东和平进程因拉宾被暗杀和阿拉法特身体的每况愈下而被悬置,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世界教派相残,族裔纷争。同时,现代高科技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种种物质恩惠,另一方面也使人类在强大的物欲诱惑下不再顾忌伦理道德,变得浮躁不安,急功近利。淡漠、麻木、荒谬、涣散、焦虑、疏离、不安像噩梦一样侵蚀着人类的心灵。在马哈福兹的梦里,我们不时地看到一个个小人物,他们面对都市之广,徘徊于街头巷尾(梦1),或置身于宽旷的大厅(梦4),或迷失在嘈杂的人群中(梦2),或等待于车站,彷徨无主(梦85)、或漂泊在孤船,不知所往(梦27);我们还看到一幕幕荒诞的场面:街道变成了马戏团,小丑在家迎接“我”(梦5),故人的百年华诞被布置成生前情人们的狂欢(梦52),阴翳的森林瞬间变成狼烟四起的战场(139),法庭的旁听者因语言不通而被说着“洋泾浜”的法官判处死刑(梦100);我们更看到对现实辛辣的讥讽和批判:沉醉于靡靡之音的人们对身边的受难者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梦53),刻板繁琐僵化的晋升手续使奋斗一生的小人物白忙一场(梦39),要想过上小康的生活只有结识权贵(梦34),功成名就的儿子荣归故里却遭家人拒斥(梦101),月光溶溶、令人陶醉的夜晚,畅游河中的人们因月亮的突然消失而找不到归途(梦20)。凡此种种,马哈福兹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极度异化的世界。 马哈福兹的梦境塑造了一个个压抑、孤独、焦虑、恐惧、异化的“自我”,而“等待”和“荒诞”是这类梦境不断重复的主题。譬如,在第七个梦境中,梦者等待着一趟始终没能乘上的有轨电车: 广场宽阔,车水马龙。黄昏时分,我立于车站,等待3路有轨电车的到来,我要回家,没人等我。夜幕降临,遮盖住稀稀疏疏的街灯透出的微光。我感到孤独,自问最后一趟3路车为何迟迟不来。一辆辆电车载走了站台上该载的人。我不知3路车出了什么事。喧闹的广场渐静,如织的人流渐稀,只剩下我形单影只,在空寂的广场上等待着总也不来的电车。这时,我听见轻微的声音,循声望去,看见不远处一个女子的背影,像是妓女。我更觉孤独和绝望。正想离开,3路车缓缓驶来,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别无他人。心里某种东西在暗示我不要上车,我扭转头去。不一会,3路车离开了车站。我向那姑娘站着的地方望去,她感觉到我的目光,嫣然一笑,朝最近的转弯处走去,我随她的身影追去。(《痊》:7) 宽阔的广场、形单影只的梦者、稀疏的街灯透出的微光生动地表达出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感;迟迟不来的有轨电车和黑暗中显现的女子笑容与背影增加了不可名状的神秘感和诱惑感。整个梦境就像一幕荒诞剧,剧中没有对白和交流,主题并非是回家,而是无果的等待。这让我们自然联想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马哈福兹用这一梦境表达了人类在这个荒诞世界里的尴尬处境,人和生活之间的疏离和隔绝,使这个世界成了人无可挽回的流放地。马哈福兹在梦中以反讽的手法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无意义性和无目标性。 尽管当今的世界充满了荒诞和玩世不恭,但马哈福兹并不玩世。他坦率地承认,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后,他曾一度万念俱灰,坠入玩世之渊,因为“现实看来荒谬而可怕”。但是,他又说:“不,可以肯定,我不是玩世者。你知道玩世的含义吗?简单说来,就是认为生活毫无意义。而对我来说,生活有其意义和目的。我全部的文学实践,都是在同玩世作斗争,或许我曾感到过玩世之念的蠕动,但我抗拒了它,试图分析它,然后制服它。”(《自》:7-8) 马哈福兹的梦不仅是其对个人一生的浓缩性回顾,也不止是“对埃及现代生活的哲学性反映”(12),更是其灵魂的探索和思想的超越,而指引他的灵魂之境和思想之灯便是苏非神秘主义。马哈福兹不是苏非信徒,因为他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避世,远离现实生活;但苏非思想中的智慧和哲理,其对个人灵修和人生悟道的重视,对高尚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执着叩问,还是深深吸引了马哈福兹和像他一样有良知的、崇尚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他而言,“苏非是一片美丽的绿洲,我得以在那里歇凉,躲避生活的酷热”(13)。苏非信徒对真主的不断探寻和发现,被他赋予了求索人生意义及人类最高思想境界的含意。另一方面,苏非文学中常常用想象、沉思、隐喻、梦境、幻境的方式揭示“自我”与“真主”合一或是圣贤和古人显灵的情景,将内心世界不可言喻的神性体验表达出来。这种神秘体验和文学的诗性思维十分相通,成为马哈福兹及其他一些文学家十分喜爱的文学表达方式。如,当代埃及著名作家杰马勒·黑托尼就十分肯定苏非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启迪作用:“虽然苏非文学有些朦胧费解,但是苏非的经验更接近艺术家的经验。我借助苏非文学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引人注目。苏非文学表达了内在的不安,是一种现成的形式,从中我找到了表达的自由。由此可以创造一种非同一般的艺术风格。”(14) 马哈福兹在《痊愈期间的梦》直接用“梦”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体悟诉诸笔端,其隐喻之意充满了苏非主义哲理。在梦境的框架内,叙述者“我”不断地说“我在梦中看见了……”“看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隐喻。苏非主义的“存在单一论”认为真主是独一的绝对的存在,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质,并具有“隐”和“显”两种存在形式;它也认为现实世界在其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就其本质而言,如反映镜中的影像,似梦境,为虚幻,是真主的显迹与外化。也就是说,苏非文学中对于“看见”有两个层次的“看见”:一个是有形的世界,一个是无形的世界。能不能通过这个有形的现实世界看到那个无形的真理世界,这是苏非教义中非常重视的修炼等级。苏非信徒将梦中的情景称之为“心见”或“真实”,梦幻境界是苏非信徒们精神修炼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马哈福兹在第121个梦中便隐喻性地描述了苏非主义对现世界和真理界的理解: 我在梦中看见自己行走在亚历山大的海滨大道上,向那幢大楼走去。我看见,在大楼的一个阳台上那位优雅的女士正和她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忽然大楼模糊了,景象魔幻般地融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阿巴西耶大街。我仍然向那座新楼走去,那位我难以忘怀的姑娘正从一扇窗子里看着我。走近后发现窗子里空无一人。我决定像平常一样到有轨车站上去等候,却发现整个大街既无车站的影子也无行车的轨道。(《痊》:121) 那位阳台上“优雅的女士”和窗子里“难以忘怀的姑娘”都隐喻真理或对真主的神性之爱。佳丽重现是《痊愈期间的梦》的重要主题。对于马哈福兹而言,他一直在寻找这种神秘之爱或追求真理,然而它若隐若现。“真理”的终点被设置在远处,但这一终点仍是一个幻觉,他知道那是个幻觉,可同时他又必须相信其真实性,因为只有借助它,他才能想象得更深更远,才能突破那个幻觉而不断前行。这也许正是人生的要义。 再如,第120梦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 我们去诗人们赞美的王国旅行。每一个人都选了一位向导。在向导的指引下,走过一个景点又一个景点,走过一座山,又来到一个湖,走过一处古迹又来到一个坟墓。向导说:“此次旅行只剩下水晶花园了。”他让我们稍事休息,沉思片刻,不要被即将看见的炫目的情景击垮。我们问道:“还有比我们已看到的生命和万物更耀眼吗?”向导微笑着继续前行,我们紧随其后……(《痊》:120) 很明显,在梦中,真理的追寻者向诗歌王国进发,走上神圣的灵魂之旅。在向导的指引下跋山涉水,穿越死亡和恐惧,只剩下最后一处胜景——水晶花园——没有见到。水晶花园即象征着苏非信徒中圣洁的目标,也许它遥不可及,是想象之物,虚幻而空灵。向导对我们的提问笑而不答,也许默认了我们业已经历的生命世界和周遭万物才是最美的景色。对马哈福兹而言,灵魂不断在寻找和追求至高的境界,而人生之旅中所见的一切事物和生命都是一场美好的邂逅。这里也反映出马哈福兹的积极人生观。 如上所述,马哈福兹在《痊愈期间的梦》中正是利用梦境的象征、凝缩、拼接、移置手法,引导读者从“苏非信徒”的旅程中获得更多的哲学、宗教和人生奥义,从多方面探索现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马哈福兹认为梦比现实更加具有真实性,因为它具有转换和凝缩能力,能够引领人们超拔于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之上,从新的、更深的层次理解现实。在叙述的过程中,马哈福兹不断提醒读者这是一个梦,更希望读者能够和他一起来到这个将永恒、现实、过往结合起来的世界。马哈福兹以及那些具有同样眼光看待民族文化遗产并在现代性进程中坚守民族主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其他人没有看到的真理,因而矢志远行,寻找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出路。正是这种能够看到无形的真理世界的能力,才能使阿拉伯民众重新凝聚,开创未来。这也正是作者的封笔之作为读者带来的意义。 注释: ①马哈福兹《痊愈期间的梦》,埃及:舒鲁格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页码,不再另注。译文由笔者翻译。 ②“第四堵墙”(the fourth wall)原是戏剧术语,指在镜框式舞台上,通过人们的想象位于舞台台口的一道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墙”。它是由对舞台“三向度”空间实体联想而产生,并与箱式布景的“三面墙”相联系而言的。它的作用是试图将演员与观众隔开,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而只在想象中承认“第四堵墙”的存在。 ③《〈痊愈期间的梦〉:梦帘后面观察现实的眼睛在询问发生了什么?》,http://www.elaph.com/Web/Archive/1073415357790336600.htm.2007/05/30。 ④《梦的停止就是生命的终结》,http://www.naguib-mahfouz.com/sayabout-3.htm.2007/05/16。 ⑤参见阿多尼斯《苏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沙基出版社,2006年。 ⑥转引自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⑦沙吉尔·阿卜杜·哈米德《梦、象征和神话》,埃及文化总局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⑧约翰·基欧《潜意识》,叙利亚对话书局,2010年,第86页。 ⑨这是尼采的观点,他将历史描写为一系列永不停止的重复循环,并认为,认识到这个真理将鼓励每个人细致考虑他们的决定,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是值得重复的。 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陈焕文、翟飚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1)1951年八九月间,埃及人民举行了空前大规模的反英示威运动。1952年1月26日,英美间谍机关制造了“开罗纵火案”,烧毁了许多外国企业和建筑,并以此为借口迫使穆斯塔法·纳哈斯领导的华夫脱党政府下台。埃及国王法鲁克委派阿里·马赫尔组阁,马赫尔上台后,血腥镇压反英人民运动。 (12)http://www.alwafd.org/front/detail.php?id=4706&cat=arts2007/05/26。 (13)转引自李琛《阿拉伯现代文学和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14)哲迈勒·黑托尼《落日的呼唤》,李琛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