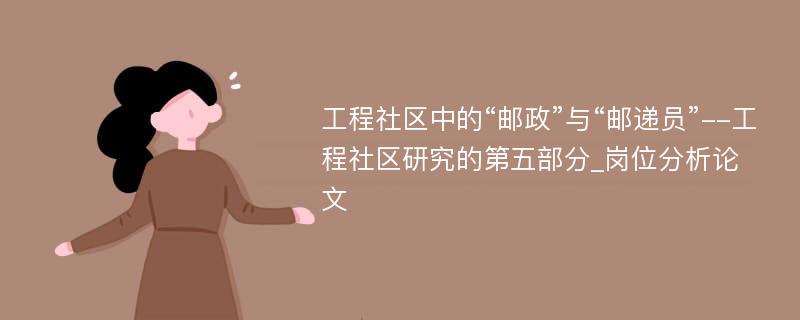
工程共同体中的“岗位”和“岗位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岗位论文,工程论文,之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0)03-0057-06
以企业和项目部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工程活动共同体(以下简称为工程共同体)是由异质成员组成的共同体。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其作为“独立个体”的本位(“本位人”);另一方面,每个个人在工程共同体内又占有一定岗位,成为了“岗位人”。于是,应该如何认识和分析本位人和岗位人的关系就成为了工程哲学和工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我的“本位”和工程共同体中的“岗位”
塞尔的《社会实在的建构》[1]出版后,“社会实在”问题引起了许多关注和讨论。《略论社会实在》[2]一文简要论述了以企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工程活动共同体也是一种社会实在或制度实在。自然实在和社会实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意图”、“承诺”和“认同”等因素,而社会实在却与“意图”、“承诺”和“认同”密切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哲学观点看,“个体”和“集体(共同体)”都是“社会实在”。而其区别是:从语言学的代词方面看,所谓“个体”就是“我”、“你”、“他(她)”,而“集体(共同体)”就是“我们”、“你们”、“他们”;从哲学方面看,与“个体”有关的基本概念是“自我”和“自我本位”,与“集体”有关的基本概念是“共同体”(本文主要讨论“工程活动共同体”)和“共同体本位”。
共同体是由个体组成的集体。个体在共同体中各自占据一个特定的“岗位”。岗位这个概念与社会学中的“角色”概念基本一致,其主要区别在于“岗位”主要用于“工作”性场合,而角色则可以广泛适用于一切场合,但这个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为叙述和分析的方便,本文把“作为自在、自为个体的个人”称为“本位人”,把在共同体中占据一定“岗位”并发挥相应功能的个体称为“岗位人”。在共同体中,各个个体都是以“岗位人”的方式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个体都是“岗位人”和“本位人”的统一。
从“来源”或“出现”过程上看,“本位人”是经过“生育过程”“出现”的,以企业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工程共同体是经过“创业”过程“出现”的,而“岗位人”则是通过“招聘”过程使“本位人”“换位”而“出现”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了分工问题[3],可是,人们往往仅从技术和生产力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理解,其实,分工便意味着不同的岗位,意味着工程共同体中的成员成为了“岗位人”。
虽然中外哲学家对“自我”和“个体”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却很少有人研究“个体”的“位格”(“本位”和“岗位”)和存在方式或存在形态问题。
由于本位人是通过生育过程而形成的,所以,“我”对于我的“本位(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可是,对于“我”的“岗位”,对于作为“本位人”的“我”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岗位人”,“我”就有进行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了。
在现代社会中,本位人往往通过企业的招聘过程而“变位”成为工程共同体中的“岗位人”。“招聘”是“工程共同体”(作为“本位”的“集体”)和“个体”(作为“本位”的“个体”)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如果“工程共同体”和“个体”可以通过招聘环节而达成“协议”,双方各自作出相应的“承诺”,一个本位人便可以“变位”为“岗位人”而“上岗”了。
在工程哲学和工程社会学中,本文人和岗位人的动态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末期以来,塞尔、图莫拉等西方学者在“社会认同”、“集体意向”、“集体接受”、“集体承诺”、“集体态度”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进展[4],但他们往往仅关注个体和共同体的“结构性关系”而忽略了“动态性关系”。
从动态观点看问题,“岗位人”在共同体中的“出场”、“在场”与“退场”就凸显出来了。
二 “岗位人”的“出场”、“在场”与“退场”
正像一个角色在舞台上有出场、在场和退场一样,岗位人在一个工程共同体中也有其“出场”、“在场”与“退场”。
(一)招聘、应聘和“角色出场”
人的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类:个体活动(特指集体之“外”的个体活动)和集体活动。在集体活动中,个体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集体的一名成员”,占有集体中的一个岗位,承担一定的岗位责任,成为了一个“岗位人”,或者说一个集体中的一个“角色”。
在没有加入企业这个集体之前,个体的存在状态是“本位人”状态。本位人是未分化状态的、具有多方面发展潜力的、具有全面活动能力的个体。许多社会科学理论,例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设和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设,往往都假定“人”(如果使用本文的术语实际上就是“本位人”)是同质的个体。
与同质的本位人不同,岗位人是异质的——即差别化的——个体。无论现实生活的观察还是理论分析都告诉我们:岗位人只能是而且必然是处于分化状态的、承担实际的特定岗位工作的个体。在共同体中,岗位人之间是分工并且合作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把企业比喻为存在于“本位人海洋”(以下亦称为“社会海洋”)中的一艘航船,又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舞台。“工程项目”便是这个舞台要上演的剧目。企业的每个成员都扮演一定的角色,而其他的本位人就成为了“舞台”下面众多的“观众”(有关心演出并且和“演员”产生“互动”的观众,也有不关心演出的观众)。
通过招聘和应聘这个环节,本位人从“社会海洋”中登船成为了企业航船上的一名船员,本位人“换位”为岗位人。成为岗位人就意味着他(她)在工程活动项目这个剧目中承担了一定的演出任务,占据一个岗位,发挥一定的功能。
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对任何岗位都有一定的要求和标准,并不是随便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合乎岗位要求和成为某个特定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任何岗位都对“在岗者”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也并不是随便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成为某个特定的角色。前者是涉及招聘和应聘双方的条件、可能性和能力方面的问题,后者是涉及双方的自由意志、目的、愿望方面的问题。
由于任何一个岗位都只是整体中的一个岗位,于是,企业在进行岗位招聘的时候,就不但需要针对不同的岗位提出不同的岗位要求,而且还必须同时提出统一的“集体目的”方面的要求。对于企业整体来说,所有的岗位目标都必须从属于企业的“集体目的”或“整体目的”。如果不能把对不同岗位的要求统一和整合为企业的集体目的或整体目的,企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企业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企业。
上文谈到本位人在一定意义上被假定为是同质的、无差别的个体。可是,一旦进入招聘和应聘这个环节或场境,本位人就成为了具体的“应聘者”(即“求职者”),成为了“差别化”的“求职者”。
不同的求职者不但有不同的能力和潜力,而且必然有不同的个人目的和要求。一般地说,个人目的和集体目的之间、个人能力与企业要求之间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必然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差距甚至矛盾、冲突的。
于是,招聘和应聘的过程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招聘者和求职者互相搜寻、选择、谈判、博弈和“制定协议(契约)”的过程。
如果通过谈判,个体方的条件、目的和要求与集体方的条件、目的和要求能够互相调和、弥合差距而求得某种契合,招聘和应聘便同时成功,一个本位人便可以与企业签约(书面契约或口头契约)而成为一个岗位人。于是,一个本位人就“变位”或“换位”而成为了一个岗位人。
应该强调指出:个体与集体双方通过招聘谈判而“完全”弥合双方在条件、目的、愿望和要求方面的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双方通过招聘谈判所达成的只能是某种“重叠共识”。
从语义分析方面看,任何重叠共识都只是而且必然是部分重叠的共识。而从谈判过程和结果方面看,尽管谈判双方不可能达成意见完全重合的共识,但谈判的成功就意味着双方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重叠,否则,谈判就要破裂,应聘者就不可能签约上岗而成为一个岗位人。
应该注意,在“招聘”谈判取得成功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况和场合下,招聘方和应聘方所达成的重叠共识的“程度”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它可能是很高程度的重叠共识,也可能仅仅是最低限度的重叠共识。
招聘和应聘活动绝不仅仅是一个认识性或知识性的过程,它同时还是一个具有经济性、社会性、法律性等多方性质或维度的过程。
招聘和应聘谈判的成功不但意味着双方达成了必需的“重叠共识”,而且同时意味着双方达成了必需的“重叠承诺”和“重叠认同”。
所谓重叠承诺不但包括招聘者对应聘者的承诺(岗位委托承诺和其他承诺),而且包括应聘者对招聘者的承诺(岗位接受承诺和其他承诺)。
在重叠认同的含义中也同样地既包括招聘方对应聘方的一定的认同,也包括应聘方对招聘方的一定的认同。
如果通过谈判而达到了所必需的“重叠共识”、“重叠承诺”和“重叠认同”这“三大重叠”,招聘和应聘便取得成功,求职者上岗,一个岗位人(或曰一个角色)便“出场”了。
一个角色出场的时候,上述“三大重叠”所达成的重叠程度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不可能取得完全重叠就意味着双方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和矛盾。而如果从双方仍然存在差距和矛盾方面看问题,“三大重叠”的非重叠部分就是“三大差距”:“共识差距”、“承诺差距”和“认同差距”。
根据“三大重叠”的重叠程度——从另一方面看就是“三大差距”的差距程度——的不同,角色的“出场”既可能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出场,也可能是平庸的出场,甚至可能是“暗藏险情”的出场。在角色出场时,不但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的情况经常出现,而且双方都有可能因为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而为岗位人的上岗埋下不良的伏笔。
(二)“在场”的岗位人和岗位人的“忠诚”问题
从招聘和应聘成功一直到解聘或辞职,这是岗位人或角色的“在岗”阶段或曰“在场”时期。
在场的岗位人获得了岗位授权,承担了特定的岗位责任。他(她)承担了做好岗位工作的义务,同时也获得了与岗位责任相应的权力。例如,门卫拥有了根据有关规定检查进出人员的权力,质量检查员拥有了不允许不合格部件进入下一道工序或不允许不合格产品出厂的权力,等等。
在认识岗位权力的性质和来源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它既不是天赋权力(天赋人权),也不是来自“本位人”的“自身能力”(虽然具有相应的自身能力是一个前提条件)的权力,它是与岗位相伴随而拥有的权力,是“岗位人”拥有的权力。
按照伦理学(特别是职业伦理学)和有关制度的要求,岗位人应该敬业爱岗,忠于职守。
“忠诚”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在中国古代的伦理学传统中,忠诚问题的焦点是对国家的忠诚、对君主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和对朋友的忠诚等。在现代社会中,除“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朋友的忠诚”之外,另外一个忠诚问题——对企业(‘集体’)的忠诚和对岗位的忠诚——被突出了。
“对企业的忠诚”和“对国家的忠诚”是两个既有类似之处又有许多区别的问题。应该承认,目前在伦理学中,对后者的研究较多而对前者研究较少,可是,前者却是一个在内容上更加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更常遇到,而且其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在现象形态上更加千变万化的问题。
首先,忠诚不但是心理和态度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行为。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思想、意识和内心状态的忠诚是只有“本人”才能够真正知道和真正体验到的,然而,他人也可以通过其行为或其他方面的表现来间接感受和推定其忠诚。
上文谈到,岗位人在通过招聘谈判而上岗时,必然达成了重叠共识、重叠承诺和重叠认同这“三大重叠”。这“三大重叠”就是岗位人忠诚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三大重叠”并不否认同时还存在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的共识差距、承诺差距和认同差距这“三大差距”,对于不同的上岗者来说,由于这“三大差距”具体状况的不同便导致了岗位人在上岗时对企业和岗位的忠诚程度出现了差别。
不同的岗位人在忠诚的程度上可能是大相径庭的。在忠诚程度上,既可能表现为无保留的极端忠诚,也可能仅仅是最低限度的忠诚,甚至会出现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而“中规中矩”的忠诚则成为了一般情况下的忠诚。
忠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但存在着“忠诚度”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忠诚行为的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和相应的忠诚行为能否被认可的问题。
在忠诚问题研究领域,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和忠诚》是一本富于启发性的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评论说:“赫希曼教授的书虽不是长篇大论,但新意迭起。经济学家一直假定,终止需求可以抚慰人们对某企业产品的不满情绪,而政治家们则倾向于在组织内部采取可能的抗议。赫希曼认为,这两种机制可以并行发挥作用,并通过分析和举证,完美地论述了二者的交互作用所具有的令人深感意外的含义。这一理论可以清楚地解释很多当代重要的经济与政治现象。赫希曼的通篇论述对很多社会和文化形态都极富参考价值。”[5]
赫希曼在《退出、呼吁和忠诚》一书中花费了很多篇幅分析和研究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退出、呼吁和忠诚”,这实际上是“组织外部的人员”在“忠诚”方面的问题。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组织内部成员”的“忠诚”问题。
上文谈到,忠诚的一般表现是“中规中矩”的忠诚,换言之,就是“思不出其岗”的“在岗忠诚”。如果岗位人出于“岗位职责之外”的“忠诚心理”和“整体性忠诚心理”而采取“呼吁”类型的行为,那就是“越岗忠诚”了。
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岗位人都遵守对于忠诚的规范性要求,于是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忠诚缺乏甚至不忠和背叛现象。
如果我们把岗位粗略地划分为管理岗和操作岗两大类,那么,对于操作岗上的岗位人来说,最常见的“忠诚缺乏”现象是消极怠工,而对于管理岗上的岗位人来说,最常见的“忠诚缺乏”现象是官僚主义。
忠诚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忠于职守,而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都损害了这个基本要求,成为了失职的表现。
每个岗位人都拥有一定的岗位权力,当出现岗位人的忠诚缺乏甚至不忠现象时,岗位人便会故意地不行使岗位权力或滥用岗位权力了。如果说贪污受贿是管理岗上的典型不忠现象,那么监守自盗就是操作岗上的典型不忠和背叛现象了。
在许多情况下,导致岗位人滥用岗位权力的原因常常是岗位人的忠心被冷漠甚至不忠所取代,规范的“岗位心”被私利的“本位心”所取代。
“重叠共识”、“重叠承诺”和“重叠认同”是岗位人上岗的前提和基础,“忠诚缺乏”甚至“不忠”意味着“单方面”地破坏了“重叠共识”、“重叠承诺”和“重叠认同”这“三大重叠”——特别是破坏了岗位人的“岗位承诺”。
岗位人处于“在岗”状态时,“本位人”并没有消失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在“本位人”、“岗位人”和“作为社会实在的集体本位”这个“三角关系”中,有许多重要而复杂的关系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这里就不能多谈了。
(三)从岗位人回归本位人:“角色退场”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占据某一个岗位。本文不讨论转岗这种情况,以下就直接讨论岗位人向本位人的回归问题。
当岗位人“离岗”,不再具有某个企业或某个项目部“成员”的身份,这就是“角色退场”,岗位人回归为本位人。虽然岗位人回归本位人的具体原因、方式和路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而言,可以分为正常方式和非正常方式两大类。
岗位人向本位人回归的正常方式是指由于常规原因或正常原因而形成的“离岗”,例如岗位合同到期、工程项目结束等等。而岗位人向本位人回归的非正常方式则是指以辞职、解职、开除等方式形成的离岗。
一个岗位人的下岗也就是一个角色的“退场”。在中国传统的戏剧理论中,不但讲究“好角色”需要有一个“好”的“出场”,而且讲究需要有一个好的“退场”。
对于一个岗位工作来说,理想的状况应该是:由于招聘方和应聘方达成了较高程度的“重叠共识”、“重叠承诺”和“重叠认同”,使得角色有一个好的“出场”;在出场(即“上岗”)后,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应该有一个好的“在场”表现;最后,应该有一个好的“退场”。
要全面达到“出场好”、“在场好”并且“退场好”的要求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岗位人都是在心怀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的遗憾(包括“出场遗憾”、“在场遗憾”或“退场遗憾”)而“退场”的。
三 从阴阳观点看本位人和岗位人关系
在本文最后,我们想运用中国传统医学和古代哲学的阴阳范畴对本位人和岗位人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和阐释。
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中医理论中,阴和阳是一对基本范畴。《老子》第42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7]29。《素问·阴阳离合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7]44传统中医根据阴阳理论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进行了全方位解释,我们则希望能够运用阴阳理论对本位人和岗位人的关系进行一些有启发性的说明和解释。
依据阴阳理论考察本位人和岗位人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要点。
(1)作为社会实在的个体是“独立个体”和“角色岗位”的统一体,是本位人和岗位人的阴阳统一体。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7]19。《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7]36准此,在统一的个体实在中,角色岗位是“阳位”,独立个体是“阴位”;本位人是“阴位”,岗位人是“阳位”。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从本位人和岗位人的阴阳统一中认识社会中的每个个体。
(2)在阴阳统一的个体中,阴和阳——即本位人和岗位人——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7]381本位人和岗位人决不是两种互不相干、互相排斥的状态,而是在岗位人状态中必然渗透着本位人的“底色”,而本位人的“社会基因”也不可能离开岗位人的“表型”而“抽象存在”。个体的“本位人基因”必然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其岗位表现,而岗位人也必然通过“岗位活动”和“岗位表现”参与对“本位人动态基因”的建构。
(3)如同医学中生理上阴阳平衡的破坏会导致病态一样,在人性和社会领域,本位人和岗位人阴阳平衡关系的破坏也要导致“异化现象”或其他“病态现象”的出现。
这里所谓的“异化现象”,既包括滥用岗位权力谋取私利和仅仅把岗位人当做工具使用之类的现象,也包括由于失业或下岗而“游离”在集体之外等现象。应该强调指出,失业现象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自我的存在价值而成为一个社会中的“游魂”,这本身便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以往学者在研究异化现象时,往往忽视了对失业这种形式的异化现象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弥补的缺陷。
在本位人和岗位人的关系上,畸形的岗位人压倒正常的本位人或畸形的本位人压倒正常的岗位人都是由于阴阳失衡而导致的异化现象。
方法论个人主义只承认本位人的存在而否认岗位人的存在。从阴阳统一的人性论观点看,其实质就是忽视了岗位人的重要性,把“本位人和岗位人阴阳统一”的个体片面地解释为“纯阴而无阳”(只见本位人而不见岗位人)的个体。而方法论整体主义只承认“集体本位”的存在而忽视了岗位人的深处还存在着一个“本位人”,从阴阳统一的人性论观点看,其实质就是把“本位人和岗位人阴阳统一”的个体片面地解释为“纯阳而无阴”(只见岗位人而不见本位人)的个体。
人性问题是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可以把“本位人和岗位人阴阳统一”的观点看做分析人性问题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例如,在“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这个个体实在中,“美国第一任总统”是一个“岗位人”,如果“华盛顿”不再占据“美国第一任总统”这个“岗位”,“纯本位人”“华盛顿”就不是“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这个“个体实在”了。同样地,在“比尔·盖茨-微软总裁”这个个体实在中,“微软总裁”是一个“岗位人”,如果“比尔·盖茨”不再占据“微软总裁”这个“岗位”,“纯本位人”“比尔·盖茨”也就不是“比尔·盖茨-微软总裁”这个个体实在了。
另一方面,一个具体岗位不可能必然与某一个具体本位人一直联系在一起。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2000年A公司由甲任总裁,B公司由乙任总裁;而在2001年,却是B公司由甲任总裁,而A公司由乙任总裁。A公司总裁和B公司总裁是两个不同的岗位,从2000年到2001年,甲和乙的岗位人身份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又必须承认甲和乙二人的“本位人”身份保持着连续性。换言之,在上述情况下,“本位人-岗位人阴阳统一”的“阳性”“岗位人”发生了变化,而在“本位人-岗位人阴阳统一”的“阴性”“本位人”并没有变化发生。这也就是所谓“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7]36
应该再次强调: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只有岗位人才是他(她)的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阳性”生存形式和生存状态。游离在集体之外的“本位人”——即处于失业状态的“本位人”——是异化状态的“强阴性”“本位人”。
如果为了解释和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走上工作岗位前的状态广义地称为“预备岗”,把退休后的状态广义地称为“退休岗”,那么,每一个个人的“大全”便都成为了“本位人-岗位人”的“阴阳统一”的“个体实在”,在这个“本位人-岗位人的阴阳统一”的“个体实在”中,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是“纯阴无阳”的,也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是“纯阳无阴”的。
“我”、“你”、“他(她)”都是“本位人-岗位人的阴阳统一”的“个体实在”。在“我”、“你”、“他(她)”的相互认知和相互关系中,在个体和集体的相互认知和相互关系中,在认知和对待个体实在时,如果不从“本位人-岗位人的阴阳统一”中认知和看待“个体实在”,那就必然要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此外,本位人和岗位人的关系还可以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进行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