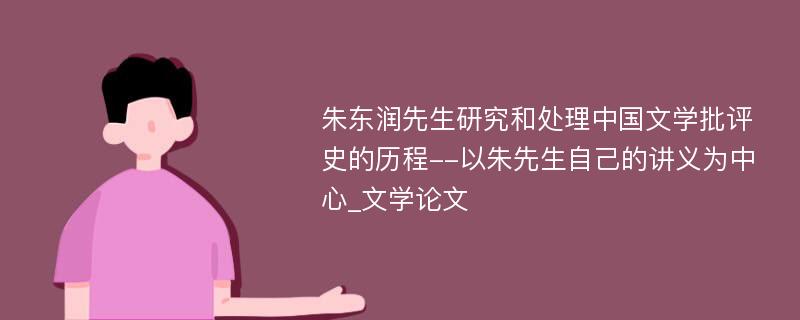
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讲义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东润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虽然时间略后于郭绍虞和罗根泽两先生的著作,但郭著1934年仅出版上册,下册则迟至1947年方问世。罗著最初仅写到六朝,1943年增订后也仅至隋唐五代。可以说,朱著是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通史。出版虽晚,但从1931年授课,1932年形成首部讲义,其后数加修订,正式出版著作也并非最终的写定本,有关情况,先生本人在《大纲》自序中略有说明。对其中原委的研究,至今也仅见周兴陆教授根据上海图书馆藏先生题赠老友郑东启先生的一册讲义,所撰《从〈讲义〉到〈大纲〉》①一文,有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笔者近因受委托编纂先生文集的机缘,承朱邦薇女士信任,得以阅读先生本人保存的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次讲义和手稿,可以较详尽、准确地梳理先生一生研究的轨迹。特撰本文,俾便学者参考了解,并纪念先生逝世25周年。
一、先生自存批评史讲义和手稿的基本情况
所见讲义和手稿计有以下若干种:
甲、国立武汉大学铅排线装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署“朱世溱东润述”,凡双面169页,单页13行,每行38字,总约17万字。卷首有题记,无目录,无印行年月。经鉴定为1932年讲义。存二册,其一颇多先生批注。
乙、国立武汉大学铅排线装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卷首无署名,有题记和目录。《绪论》前署“朱世溱东润述”。凡双面261页,单页13行,每行38字,总约26万字。无印行年月,经鉴定为1933年讲义。颇多先生批注。
丙、国立武汉大学铅排散页《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署“朱世溱东润述”,凡双面118页,单页13行,每行38字,总约12万字。卷首无题记,无目录,版页末括记:“武42二十六年印。”知为1937年讲义前半部之校样。
丁、国立武汉大学铅排线装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卷首有二十八年题记和目录,《绪论》前署“朱世溱东润述”。凡双面268页,单页13行,每行38字,总约27万字。前122页末括记:“武42二十六年印。”目录及123页后皆括记:“乐48二十七年印。”因先生于1939年1月13日方抵达乐山,故可确认此为1939年讲义。稍有先生批注。
戊、蓝格毛边稿纸剪贴1933年版讲义及新增改文稿,为1937年《讲义》增订本下半部的部分残稿。
己、上海公裕信夹工业社文件夹装订手稿,无总题,但附有1960—1961年度排课表一纸,显示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之讲义。凡毛边纸手稿双面164页,单面16行(后半为14行),每行35字,总字数约17万字。
上述讲义和手稿,时间跨度约三十年,可以反映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从筚路蓝缕的开拓中,不断完善修订、精益求精的治学探索。
二、《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1932年初稿
先生于1929年4月由陈西滢介绍,到武汉大学任特约讲师,初授英文。因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建议,自1931年起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1932年始任中文系教授。
先生《大纲》自序云:“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这份《讲义》初稿,由武汉大学校内印刷。书首有题记云:
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著一种。观其所述,大体略具,然仓卒成书,罅漏时有。略而言之,盖有数端。荀卿有言,远略近详。故刘知几曰:“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又曰:“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今陈氏所论,唐代以前殆十之七,至于宋后不过十三。然文体繁杂,溯自宋元,评论诠释,后来滋盛,概从阔略,挂漏必多。此则繁略不能悉当者一也。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震于盛名,易为所蔽。杜甫一代诗人,后来仰镜,至于评论时流,摭拾浮誉,责以名实,殊难副称。叶适《读杜诗绝句》曰:“绝疑此老性坦率,无那评文太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诸贤哪得更垂名。”而陈氏所载杜甫之论,累纸不能毕其词。此则简择不能悉当者又一也。又文学批评,论虽万殊,对象则一。对象惟何?文学而已。若割裂诗文,歧别词曲,徒见繁碎,未能尽当。有如吕本中之《童蒙训》、刘熙载之《艺概》,撰述之时,应列何等?况融斋之书,其指有歧,宁能逐节分章,概予罗列。然中土撰论,大都各有条贯,诗话词品,曲律文论,粲然具在,朗若列眉,分别陈述,亦有一节之长。此则分类不尽当而不妨置之者又一也。述兹三者,略当举隅,旨非讥诃,无事殚悉。今兹所撰,概取简要,凡陈氏所已详,或从阙略,义可互见,不待复重。至于成书,请俟他日。
可知在先生以前,仅有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一种,全书七万余字,分十二章,前三章讨论文学义界与文学批评,后九章按时代排列,仅能粗具大概。先生对此书曾有所参酌,肯定其“大体略具”,也见其“仓卒成书,罅漏时有”,并就繁略、简择、分类三端提出批评,一是详于唐以前而忽略宋代以后,二以杜甫为例指其堆砌材料而缺乏鉴别,三则指其在各代批评中喜区分文体而罗列批评。凡此诸端,虽属批评陈著,亦欲表达己著之努力目标,即远略近详,将以较大篇幅论述宋以后之文学批评史;重视简择,尽量选取各代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加以介绍;以人为目,以时代为序,以文学为批评对象,不作文体的分别论述,以免割裂之嫌。
此《讲义》初本凡分四十六章。首章《文学批评》,首举隋唐书志至四库诗文评类之成立,认为“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特别列举英国学者高斯在《英文百科全书》对批评之定义为“判定文学上或艺术上美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并借此阐明文学批评之性质、对象与分类,批评与文学盛衰之关系,以及文学批评文献之取资。此后以先秦、两汉、建安各为一章,六朝则列八章,隋唐七章,宋十六章,金元二章,明九章,止于钱谦益。
本稿多处可见凡陈著已详即“从缺略”的痕迹。如《先秦批评》于“诗言志”从略而详述季札观礼,于《论语》则云“思无邪”外另有兴观群怨说,《两汉批评》则云“司马迁之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象派之论者,既陈书所具录,兹略之”。
可以说,在初期授课基础上形成的《讲义》第一稿,先生初步完成了明以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为这一学科的成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三、《讲义》1933年增订本
从1931年初开始,先生在武汉大学新创办的《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题论文,到1935年共先后刊出《何景明批评论述评》、《述钱牧斋之文学批评》、《述方回诗评》、《袁枚文学批评论述评》、《沧浪诗话参证》、《李渔戏剧论综述》、《司空图诗论综述》、《王士禛诗论述略》、《古文四象论述评》等九篇,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此组论文可以见出先生在重大文学批评专题研究方面的深入探讨。先生晚年自述“在写作中,无论我的认识是非何若,我总想交代出一个是非来,以待后人的论定”(1970年撰《遗远集叙录》,未刊,此据稿本)。诸文皆有独到之论说,如认为司空图、严羽、王士禛三人皆脱离现实,司空论诗真谛在“思与境偕”,严倡妙悟,不过袭江西遗论,王则承严论更“汪洋无崖畔”;认为方回、钱谦益人品无取,才识各具,方论诗宗旨在格高、字响、句活,钱论诗“精悍之气见于眉宇”;认为桐城派以阴阳刚柔之说论古文始于姚鼐而成于曾国藩,对其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说论列尤详。
在专题研究深入展开、批评文献充分发掘的基础上,先生对《讲义》初稿作了两次大幅度的增订。先说1933年的修订。此本《讲义》按前述版式印出,凡得七十五章,总约26万字,较初版增写二十九章,增加九万字。卷首题记:
二十年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次讲稿,上起先秦,迄于明代。次年续编至清末止,略举诸家,率以时次,或有派别相属、论题独殊者,亦间加排比,不尽以时代限也。凡七十五篇,目如次。
始授课在民国二十年度,即1931年,编次讲稿并付印则为1932年事。“次年续编”则为1933年事。其中清代部分增写24章,为重心所在。其他部分的增改,也有一定幅度。就章节来说,此稿将首节《文学批评》改为《绪言》,将《先秦批评》改为《古代之文学批评》,将《两汉批评》分为两章,六朝部分增加范晔、萧子显、裴子野等人,宋代则增加了张戒。从内容来说,则改变初稿与陈著交集处从简的体例,如孔子诗论补入述《关雎》和“思无邪”的论述,汉代补出司马迁,以形成完整、独立的著作。
四、1937年增订本的完成与厄运
从1936年开始,先生对《讲义》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订,并于1937年秋付排。但就在这时,日军侵华规模扩大,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春,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大学也奉命西迁到四川乐山。先生的个人命运和著述工作也卷入此一风暴之中。先生在1937年末寒假开始后,因惦念已经三个多月未通音讯的家人,以及家中正在营造的居宅,取道长沙、广州、香港、上海返回泰兴老家。在家近一年,至1938年末接武汉大学电报,乃于12月2日启程,经上海、香港、河内、昆明、重庆,至1939年1月13日抵达乐山。可以确定的是,在1937年末返家以前,《讲义》第三稿的增订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但并未全部印出。《讲义》1939年本题记云:“二十五年,复删正为第三稿,次秋付印,至一百二十二页,而吾校西迁。”《大纲》自序云:“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时间,完成第三稿。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排印。这时对外的抗日战争爆发了,烽火照遍了全国,一切的机构发生障碍,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搁下,其余的原稿保存在武汉。”所叙内容是一致的。此稿文本,目前可以见到三份书稿。
其一,先生自存1937年《讲义》排印本前半部分校样两份,均无题记,署“朱世溱东润述”。均仅118页,至第三十三《朱熹附道学家文论》止。版页末括记:“武42二十六年印。”我推断此为先生离开武汉时随身携归,并携入蜀中者。
其二,1939年版《讲义》。其中正文前122页版页末括记:“武42二十六年印。”卷首目录四页和123页后版页末均括记:“乐48二十七年印。”知此本拼合两次排印本而成。其中武汉所印部分,较自存校样多4页,而123页至124页为《自〈诗本义〉至〈诗集传〉》章之后半,为1937年增订时新写章节。
其三,1937年增订本最后十八章之手稿。详见下节所述。
前述及周兴陆教授《从〈讲义〉到〈大纲〉》一文,由于仅见1933年版《讲义》,其所作《大纲》定稿过程及与《讲义》的比较分析,主体其实是1937年版《讲义》前半部对1933年版删订增补的考察。他的看法是:1.《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则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2.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举钟嵘、刘勰部分论述为例。3.“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以司空图、王士禛为例。4.文献考辨更为慎重,并补充新见到的《文镜秘府论》关于八病之论述。这些都是深入研读的结论,我都赞同。
就我对1937年版《讲义》前半部与1933年版比读的结果,确认此次修订的幅度很大。先秦部分分为两章,增加了孟、荀的内容,对《三百篇》和《诗序》的论述,则融入己著《读诗四论》的心得,认为《诗序》影响后世最大者为风雅颂之说、风刺说、变风变雅说等。六朝增加了皇甫谧,唐代增加了李德裕,并增加《初唐及盛唐之诗论》,又在司空图下增加《唐人论诗杂著》部分。宋代则增加了曾巩、陆游等人,朱熹下增附《道学家文论》,另增《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一章,表彰宋儒治《诗》之创见。而各章节下内容,少数保持原貌,如范晔一章,多数则改动幅度很大,如刘勰、钟嵘等部分,几乎将原稿全部改写。
五、1937年增订本残稿之分析
对于1937年增订本全本的合璧,先生曾抱有很大期待。《大纲》自序:“承朋友们的好意,要我把这部书出版,我总是迟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的书籍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后决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略加校定,这便是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前身。”这是1944年的表述,这时抗日战争在最后决战时期,战争何时结束正未可期。1946年6月从重庆回南京途中经过武汉时,曾“顺便去武汉大学看看老朋友和寄在武汉的三只大木箱”,木箱装的是书和文稿。(《朱东润自传》第306页)
近期查检先生遗稿,发现有一叠大蓝格毛边稿纸抄写的书稿,经鉴别应该就是先生1937年《讲义》增订本的部分残稿。残稿首有目录一纸,正反两面抄写,经核对,其前三十四章与《大纲》前三十四章全合,其后四十二章目录,应即遗失的后半部的目录,惟缺写最末《曾国藩》、《陈廷焯》二目。正文则自第六十章末节“竹垞又有《寄查德尹编修书》”始,至全书之末。残稿采取以1933年本剪贴增写的方式,其中改动较多者,均就蓝格毛边稿纸上粘贴增写,若改动不多者,则仍改动于1933年本散页上。所存为蓝格毛边稿纸十六页,两面书写;1933年本散页增订稿四十五页,每页亦各分两面。总字数约八万字。残稿上已经作有部分付排的说明。应属即将完成的增订本最后部分,但仍稍存一些仓卒的痕迹。我比较倾向的判断,是先生此次修订,为逐次完成付排者。很可能在1937年末学期结束时,上半部校样已经排出,故得取到携归以阅正,第二部分已经交稿付排,故原稿未得保存。最后部分已经接近完成,尚未及付排,故得以保存。
以残稿本与1933年本《讲义》比读,可以见到如叶燮、金人瑞、李渔、方苞、姚鼐、纪昀、赵翼、章学诚、阮元、陈廷焯诸家改动较少,或仅改订误字,润饰文意。而于王士禛、吴乔、沈德潜、袁枚、刘大櫆、曾国藩诸家改动甚大,《清初论词诸家》则几乎全部重写。另新增郭麐、翁方纲、包世臣诸人的论述。
残稿本于1933年本《讲义》改动较大部分诸家,皆清代文论之大节所在。其中大多有补充文献之增加,于各家之批评亦多增新说。如王士禛,即增写“渔洋论诗,好言神韵,后人直揭其说,以为出于明人之言格调。今以渔洋之论明诗者列之于次,其渊源所出,盖可知也”。“渔洋之诗,时人亦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见施闰章《渔洋山人续集序》。实则渔洋之论,前后数变,知乎此,于渔洋之所以论唐说宋者,得其故矣。”“渔洋论诗言三昧,又言神韵。三昧二字,不可定执,神韵一语,稍落迹象。至于诠释神韵,则有清远之意,此更为粗迹矣。”皆体会有得,可补前说之未及。再如《吴乔》,改动也很大,增加“修龄论唐宋明之别,以为在赋比兴之间”,“谓杜诗无可学之理”,李杜后“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者”为韩退之、李义山诸节。《袁枚》章则增加“随园论诗言性情,与诚斋之说合,然其立论有与诚斋异者”一段。《曾国藩》一章,则增加“曾氏持论主骈散相通”、“姚、曾论文同主阴阳刚柔之说”等内容。《沈德潜》章于其诗教说亦有很大增补,则与先生在1934年12月《珞珈》二卷四期发表《诗教》一文表达的见解有关。
《清初论词诸家》,1933年本述邹祇谟、彭孙遹、刘体仁、厉鹗四家,残稿本增至八家。1933年本初述云间宋征璧(字尚木)之论,残稿本改为第一家,引其说后增按断云:“尚木此论。颇为渔洋等所不满,论词之风气一变。然渔洋等虽言南宋,未能有所宗主,去真知灼见者尚隔一层。其所自作,亦多高自期许,互相神圣,后人未能信也。”以渔洋为第二家,仍录批评云间二语,另增评南渡诸家一节。其次仍为邹祇谟、彭孙遹、刘体仁,内容不变。其六为朱彝尊,将原述朱诗文论述末一节挪至此,改写评语云:“大要浙派所宗,在于姜、张,间及中仙。竹垞同时诸人如龚翔麟之《柘西精舍词序》、李符之《红藕庄词序》,其言皆可考也。”其七为厉鹗。以郭麐为殿,则完全新写,全录如下:
郭麐,吴江人,字祥伯,号频伽,嘉庆间贡生,有《灵芬馆词话》。频伽尝作《词品》,自序云:“余少耽倚声,为之未暇工也。中年忧患交迫,廓落尠欢,用复以此陶写,入之稍深,遂习玩百家,博涉众趣,虽曰小道,居然非粗鄙可了。因弄墨馀闲,仿表圣《诗品》,为之标举风华,发明逸态。”共得《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十二则。其后杨夔生有《续词品》,亦频伽之亚也。《灵芬馆词话》论古来词派云:“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窗,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么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岀四者。”
新写部分另有翁方纲、包世臣等。翁方纲附王士禛后,阐发其“神韵之说,出于格调”之见解。包世臣附恽敬后,录其《与杨季子论文书》谓“斥离事与理而虚言道者之无当”,录《再与杨季子书》,“论选学与八家,尤足以通二者之藩而得其窽要”,又录其摘抄韩、吕二子题词,以见其“起诸子以救文弊”。凡此皆见先生于清代文学批评之补充。
残稿目录阮元下增焦循,复圈去。对焦循,1961年讲义有论述,可以作为此时斟酌之补充,引如下:
焦循是清中期的一位经学家,但是他对于一般文学,尤其是戏曲,有他特到的成就。所著《剧说》及《花部农谈》都收入《戏曲论著集成》。因为他是对于一般文学的发展有所认识,所以在《易作籥录》发“一代有一代之胜”的主张:“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辞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花部农谈》是一部特出的叙述。清朝中叶,两淮盐务例备雅、花两部,以备大戏。雅部指昆山腔,这是当时的正统;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这是当时的地方戏,不能和昆腔取得同等地位的。焦循自序说:“犁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覩其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其《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十数本外,多男女猥亵,如《西楼》《红梨》之类,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焦循对于戏剧,和王骥德、李渔以作家身分加以评论者不同。但是从这篇序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点:一、重视地方戏。二、重视元剧富于社会意义的传统。三、对于男女猥亵的戏曲,有所不满。
六、1937年增订本缺失部分钩沉
由于战乱,先生于1937年完成的第三稿增订本下半部,除前节介绍残稿部分十八章外,其他二十四章,除了出现奇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但就缺失的这部分来说,仍保存一些线索可资考索。线索一,是前述残稿首页录存的增订本目录;线索二,是先生自存手批1933本卷首目录存增订本的部分线索,部分批语也保存了增订的预想。
残稿目录第三十七章《方回》,手批本目录同,皆将1933年本第二十九章勾改至《刘辰翁》前,《大纲》复改至第三十九,在词论二章后,内容大体仍沿1933年本,但删去章末“综虚谷诗评言之”后一段,约500字。
残稿目录第三十八章《刘辰翁》,手批本目录同,此章为新补,《大纲》无。
1933年本第三十六《晁补之李清照黄升》,残稿目录作《宋人词论之先驱》,列三十九,手批本目录作《宋代论词诸家》,删黄升,补王灼,并将《沈义父张炎》合并。此为最初预想,写定时仍分两章。1939年本、《大纲》大体仍沿1933年本,但删去李清照论词下的一段评语:“易安于南唐北宋词家,评骘殆遍,抉取利病,得其窽要,似较无咎更高一着。胡仔评之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设也。’讥弹过甚,殆非公论。”
残稿目录第四十章《沈义父张炎》,1939年本、《大纲》大体同1933年本,但删去“伯时于四声之中揭出去声之要”一节约300字。
1933年本第三十八《王铚谢伋》,残稿目录列第四十一,手批本目录括去,《大纲》不取。殆去取曾有犹豫,《大纲》终决定不存。
残稿目录第四十二《王若虚元好问》,较1933年本增加王若虚。1939年本、《大纲》大体同1933年本,但删去“《新轩乐府引》论东坡词”一节约350字。
以下《贯云石周德清乔吉》、《高棅》二节,1939年本、《大纲》皆同1933年本,仅述时事云“元代以蒙古入主中原,北自幽燕,南及交广,同时沦陷,此自有史以来未有之巨变也”,改“中原”为“中国”,改“有史”为“有中国”,存寄意时政之慨。
1933年本第四十二《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残稿目录第四十五改作《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附李东阳》,手批本目录同,1939年本、《大纲》皆改题,并删去1933年本批语云东阳“重音律”一节约350字,仅存祖沧浪而重虚字的内容,寄贬抑之意。
其后《杨慎》诸本无变化。而《谢榛王世贞》节,残稿目录第四十八作《谢榛李攀龙王世贞》,手批本目录同,正文在王世贞上批:“应补李于鳞。《选唐诗序》(全)及其论元美及五唐诸家处。”又据《巵言》引于鳞语:“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潔,语深则意气激烈,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滓,蜕脱污浊之外者,诗也。”可略知欲补之大概。
残稿目录第四十九《王世懋胡应麟》,手批本目录:“另一章《王世懋胡应麟》。”1939年本、《大纲》皆未增加。1933年本批语于王世贞末引王世懋《艺圃撷余》:“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傅初盛,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然。然使诵其诗,果为初耶盛耶,中耶晚耶,大都取法固当上宗,论诗亦莫轻道。……予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我朝越宋继唐,正以有豪杰数辈,得使事三昧耳。第恐数十年后,必有见而扫除者,则其滥觞末流为之也。”知欲补世懋诗论之大旨。
1933年本第四十五《唐顺之茅坤》、第四十六《归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论〉》,手批本目录合并作《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残稿目录同,但又将王慎中三字圈去。1939年本、《大纲》仍同1933年本。增订本所作调整,一是曾拟提升王慎中,将原附带述及者列首。1933年本批云:“慎中有《曾南丰文集序》。”但终仍圈去。二是贬抑归有光。1933年本批语引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日记》批评归文之语,略存遗意。
1933年本第四十七《徐渭臧懋循沈德符》、第四十八《吕天成王骥德》,残稿目录则作第五十《徐渭臧懋循沈德符吕天成》、第五十一《王骥德附填词解》;手批本目录则前节不变,后节作《王骥德附吕天成及〈填词训〉》。凡此变化,皆执意尊王而轻吕。1939年本、《大纲》虽略存1933年本之原文,但于吕下删去论高则诚一节、评议吕论沈、汤二家语约300字,王下删去“毛以燧跋《曲律》”一节,章末谈“批评家之病”一节约460字。1933年本批语:“吕略。多应另写。”“应补论剧戏一段。”知于此节颇存不满。所谓《填词训》,当为《吴骚合编》卷首《曲论》之第一节,后人或另刊入《衡曲麈谭》,今人考定为张楚叔撰。先生认为此篇谈戏曲理论有创见,特予揭出,惜未见具体论述。
1933年本第四十九《袁宏道》,批云:“应连三袁同论。”目录及残稿目录皆作《李贽袁宏道附袁宗道袁中道》。1939年本、《大纲》仅删1933年本引中郎“记百花洲”以下百余字,无增补。手批本引李贽《藏书纪传总目前论》、《杂说论西厢记》,又云:“小修之评见《游居柿录》九七八。”“小修之说见《游居柿录》九八四。”略存欲补之遗痕。
1933年本第五十《锺惺谭友夏》以下八章,残稿目录改动较少,仅《侯方域魏禧》改为《侯朝宗魏禧汪琬》,即增汪琬一人。手批本目录同,手批云:“侯可略。应添出汪琬之说。”正文已云魏禧等“持论往往突过朝宗”,故曾拟删其一段,后未果。手批本目录另有两处变化:其一,《冯班》一节拟增贺裳、吴乔,而将1933年本中《吴乔赵执信》节删去。残稿本此节仍保留,贺裳也未补入。其二,《王夫之顾炎武》改为《王夫之附顾炎武》,残稿本目录未改。另《冯班》章手批“重写”,《陈子龙吴伟业》章批“陈重写”,《毛奇龄朱锡鬯》章批“西河可略”,又批朱“增论词说”。至1939年本、《大纲》此数章删改痕迹,仅《锺惺谭友夏》章删伯敬讥压卷一节,余皆未变。
七、《讲义》1939年本与《大纲》
先生于1939年1月13日抵达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继续开设文学批评史课程。今存1939年乐山印《讲义》,前半标明为在武汉所印,基本保持1937年增订本前半的原貌。卷首增加了目次,并有一段题记:
民国二十一年,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写定讲义初稿。翌年稍事订补,为第二稿。二十五年,复删正为第三稿,次秋付印,至一百二十二页,而吾校西迁。积稿留鄂,不可骤得,又书籍既散,难于掇拾,不得已仍就第二稿补印。排版为难,略有删节,校对匪易,不无舛夺,可慨也。二十八年,朱世溱识。
就本文第五节所揭经逐章核对的结果,此次《讲义》自124页第三十五节《严羽》以后的部分,基本仍沿1933年本的原文,仅有少数的删节,未作大的改动与增补。
《讲义》改题《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由开明书店出版是1944年的事,先生《自序》则作于1943年2月,说明在《讲义》初稿完成后,郭、罗二位的批评史陆续出版,“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先生并说明己著的三方面特点,一是“这本书的章目里祇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二是“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给以分别的叙述”;三是“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经与1939年本的篇目和部分章节核对,可以确认《大纲》就是以1939年本《讲义》交付出版的,除个别文字校订,在结构和内容上没有作大的改动。
1957年10月,《大纲》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新版,先生后记云“除了对于个别的刊误,加以订正以外,不及另加修订”。经对校,除了涉及对曾国藩事功评价等极少数的几处改动外,全书没有作大的修订。
在1943年《自序》中,先生曾很强烈地希望在收回留在武汉大学的1937年增订本后半部后再作修订,现知至少当时先生是存有1946年从武汉取回的部分章节的,仍没有补入,不知是否与1957年下半年的政治气氛有关,也可能仅因当时系务教务忙碌而无暇增补。
至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出新版,全书“基本上还保留原来的面目”。200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新版,则据1981年版付印。
八、1961年《中国文学批评史》授课讲义
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先生为中文系五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今存手书较完整的讲义。全稿目录如下:《导论》。一《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二《墨子、庄子、韩非子》、三《扬雄、桓谭及王充》、四《曹丕、曹植和陆机》、五《范晔、沈约、萧子显》、六《刘勰》、七《钟嵘》、八《萧统、萧纲、萧绎及颜之推》、九《刘知几》、十《初唐及盛唐的一些诗论》、十一《白居易及元稹》、十二《韩愈、柳宗元》、十三(原题一)《司空图》、十四(原题十五)《北宋的诗文革新》(本讲存另一稿,题作《欧阳修与诗文革新》)、十五(原题十六)《王安石和苏轼》、十六《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和陆游的创作主张》、十七《严羽诗论批判》、十八《明代的拟古主义和反拟古主义的斗争》、十九《从神韵论到性灵论》、二十《桐城派及阳湖派》、二十一《清代词论的发展》、二十二《戏曲、小说理论中的两条道路》、二十三《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文学理论:梁启超》、二十四《近代诗歌理论批评:黄遵宪》、二十五《王国维》、二十六《鲁迅的早期文学思想》。
由于在特定年代为开设课程而作讲义,本稿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开课需要,也保留了讲义未最后写定的面貌。前引原稿中的章节部分错乱,估计是学期交替的痕迹。先生在后记中说明:“这里必须知道编书的必须采用一般人共同接受的看法,但是教书的却必须把自己所得到的一点认识交给学生。”正是突出“自己所得到的一点认识”,本稿虽然有许多对《大纲》旧说的归纳和一般认识的叙述,但仍然保存许多先生当年独到的见解。
本次讲义第六章《刘勰》,先生稍后曾另外写成专文,拟单独发表,并在1970年左右所写类似本人学案的《遗远集叙录》一文中,将其作为学术代表作给予说明,认为“本来决定对于讲稿概不发表的,因为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内占有独特的地位,近十年内对于刘勰的价值,又曾经有过意外的估计,因此抽出这一讲来,提供个人的看法”。“意外的估计”何指?先生说三十年代曾有人提出“读中国文学批评,只读一部《文心雕龙》就够了”,而到五十年代后期,则有人鼓吹刘勰“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因为“他在《知音》篇所说的‘事义’,就是事物,这是他的唯物辨证论的内在的铁证”。此一观点弥漫全国,“气焰之盛,声气之广,几乎使人没有开口的余地”。先生认为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因而加以检讨。先生认为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前曾协助名僧僧祐编纂定林寺经藏提要《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在《文心雕龙》撰述中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成了地地道道的僧侣,怎么可能具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呢?在廓清时人误区的同时,先生对刘勰文学批评的贡献重新加以分析。他认为《文心雕龙》的出现是与两晋以来形式主义文学斗争的产物,刘勰提出衡断文学的标准则是复古。复古“不是回到没有文化、没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去,而是回到更朴素、更接近于自然,而不以修饰打扮为美的社会去”。先生对作为《文心雕龙》总纲的前三篇的解读,也体现这一精神。他解释《原道》的道“止是自然存在的现象”,《宗经》、《征圣》是“把当代的文学和古代的文学联系起来”,“以复古为革新”。先生特别强调《文心雕龙》下编创作论和批评论的开拓意义,“体大思精”,“真是独探骊珠,目无今古”,给予高度礼赞。与《大纲》比较,先生对刘勰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有鉴于此,我据手稿将本文整理出来,在本期学报首度发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讲义之下限为现代,增加了《大纲》未加论列的近现代文学批评的内容。对于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先生称赞他们是“比较及早有所觉悟的一群”,“抓住诗歌、小说、戏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他特别揭出梁对小说所起作用的四点论述。对夏曾佑《小说原理》,也有特别的表彰。他对王国维的分析,围绕《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展开,强调他的美学理论主要根据叔本华学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有了欲就有追求,满足了这个追求就是厌倦,不能满足这个追求便是苦痛”。他就此而认为《红楼梦》是“宇宙的大著述”,具有“人类全体之性质”。先生说:“唯有王国维才认识到典型的意义。”对《宋元戏曲考》则分析其自然说,《人间词话》则关注境界说,都是应有之说。先生认为“王国维所说的自然,不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而是他所设想的天才作者的才能。因为有了这个才能,遂能写出胸中的成立和时代的情状”。对《人间词话》实境虚境之说、隔与不隔之论,先生是赞赏的,但对忧生忧死与赤子之心的评述,则有所保留:“尤其可怪的王国维认为李后主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负人类罪恶之意,这是一般人所无从了解的。”鲁迅一章,则主要介绍《摩罗诗力说》的见解。先生认为“摩罗就是撒但,是反抗”。“既然反抗是为了生存,因此只要有压迫存在,就必然有战争”。在当时的中国是有提出反抗和战争的必要,但鲁迅所期待的则是天才诗人的大声疾呼,先生认为鲁迅“身处风雨飘摇之中”,“混乱的现象”使他产生错觉,“把偶然的现象作为永恒的现象,使他过分重视天才而看轻群众”,不免受困于时代。
九、余论
以上就目前所见朱东润先生自存批评史讲义各文本,简略回顾了从193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授课并形成讲义,迭经增订,最后出版略有遗憾的《大纲》一书的过程,可以看到先生在此一学科建设方面开拓进取的过程。相信以上叙述对于研究现代学术史当有若干借镜的意义。就朱先生本人的学术贡献来说,我以为可以有几点提出讨论。
中国传统诗文之学在被现代大学教育容纳以后,有一逐渐转变的过程,即从传统辞章之学向现代观念之文学的转变。文学批评史学科之成立,虽然可以溯源到孔子诗说或宋元以降的诗文评著作,但其著作之学术理念则是渊源自西方的文学研究史,而其研究对象则以传统诗文批评为主体。故凡批评史之研究学者,必须具备此两方面之条件,方能胜任而有成就。先生早年于传统四部之学浸润颇深,留学英国的经历让他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文学观念有深刻之认识,在从事批评史研究前曾担任英文教师逾十五年,因此具备了担纲此一学科奠基的能力。
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史,是1927年陈钟凡所著,但很单薄,还不成熟。1934年先后出版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人文书店),显示当时在此一学科研究的成绩。罗著仅述至南北朝,郭著亦仅至唐代,虽各具体系,但都还没有完成。朱先生的著作则初成于1932年,在1933年、1937年分别作了重大的修订,虽然正式出版迟至1944年,却是第一部写到清末的文学批评通史。就本文之考察,这一文本在1937年其实已经写定,在朱先生则始终感到作为讲义的不成熟,希望完成多次修订后再正式出版。尽管由于战争的原因,1937年的写定本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也因为希望全稿写定而推迟了出版,但其独立的学术意义则是无可怀疑的。特别是略远详近的编纂原则,以及以批评家个人为单元的分析立场,特别是对宋以后文学批评文献的首次全面钩稽,是朱著最鲜明的成就和特色。
朱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除了前述各项外,我认为最重要的特点,是始终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始终坚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文学批评文献则始终坚持由表及里、独特创造的选择,因而显示著作的特达精神。比如说,杜甫诗文中确实有许多评论时贤诗文的议论,先生认为不是把这些议论全部堆砌出来就尽了写史的责任,而要知道这些评价缘何而写,是否恰当,因此而作出选择。他引叶适《读杜诗绝句》“绝疑此老性坦率,无那评文太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诸贤那得更垂名”,是很有趣的例子。杜甫祖父杜审言傲睨同时文人,有“久压公等”之自负。杜甫则于同时诗文,常不免过誉,所谓“世情”,即随顺时俗而作过誉,先生认为“评论时流,摭拾浮誉,责以名实,殊难副称”,不能完全采信。这一立场,贯穿在他对历代批评家的甄选和评论中,读者当可细心体悟。
朱先生是一位治学极其勤勉,在诸多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学者。他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前中期,且结合教学而形成著作,在他自存《讲义》的每一稿中,都保存有大量的眉批和夹注,可以看到他不断发掘文献、修订旧说、补充新见的记录,这些记录又分别为下一次修订所采据。对于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则有系列论文作深入探讨。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除了当时的讲义,还有《〈沧浪诗话〉探故》等论文写出,并有《中国文学批评论集续集》编纂的设想。这一治学精神也贯彻在先生其他领域的研究探索中,如传叙文学,今存从三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讲义和遗稿即达五六种之多,值得整理总结。
注释:
①收入《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