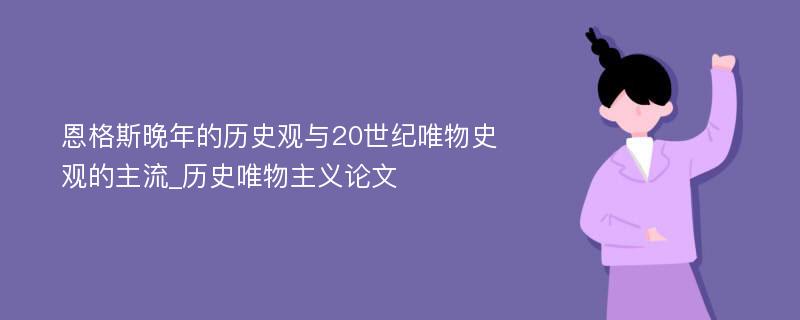
恩格斯晚年历史观与二十世纪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历史观论文,晚年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恩格斯晚期历史观占有特殊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独立阐发的理论,最能反映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倾向,而且还在于它构成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开始了唯物史观理论重心的一系列转移:从社会本质论转向社会整体化,从历史过程论转向主体活动论,从历史世界观转向历史方法论,代表了二十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
一
列宁曾经说过,随着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位。”[①]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也具有这一特点。早年,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解剖和对“原本”的批判,揭示了被种种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历史的发源地和本质,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于这一时期历史观主要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的本质,因而可以简称为社会本质论。晚年恩格斯把理论重心作了一定的调整: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上注意研究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在坚持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重点阐述经济、政治、思想因素的相互作用。一句话,把理论重心从社会本质论转向社会整体论。在九十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恩格斯概括了社会整体论的基本思想。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用交互作用论思想补充和完善历史决定论原则。如果说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是社会本质论的主要原则,那末相互作用论则是社会整体论的核心思想。晚年恩格斯反复强调,历史发展是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实现的,只有从相互作用出发,才能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理解历史决定论。第二,用“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新提法代替早年的“经济的决定作用”的用语。这不仅仅是用词的差别,而且包含有深刻的涵义,目的是吸收相互作用论思想,揭示经济决定作用实现的机制和中介。
恩格斯晚期历史观重心从社会本质论向社会整体论的转移,代表了二十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然而,第二国际理论家没有把握唯物史观的这一趋势,片面夸大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政治和观念形态的能动性,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竭力发挥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忽视的社会整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社会整体论,把总体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据此,他们重点建构了包括整体结构论、整体异化论、整体革命论在内的总体理论。总体性理论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的一种解释,又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模式,顺应了二十世纪历史唯物主义新趋势,因而值得重视。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强调总体性的同时,否认了历史决定论原则。卢卡奇用总体性否定经济因素的优先性,葛兰西把决定论看作是缺乏创造精神的早期无产阶级的一种准宗教信仰。
真正继承并全面发挥恩格斯晚期历史观的是列宁。他一方面抨击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俄国主观社会学家对唯物史观基础的否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是两个“归结法”(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捍卫了历史决定论原则。另一方面,适应新时代的特点和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他批判了俄国“经济主义”和考茨基的“生产力成熟论”,重点发挥了社会整体论。他说,人类社会是“处于经济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对社会历史要作整体研究,“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要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显然应补充对社会的法律政治的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分析。”[③]鉴于上层建筑在历史过程中作用的增大和对它研究的相对滞后,列宁把国家问题、政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到理论的核心,创立了完整的国家学说、政党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社会整体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矛盾论》提出了矛盾体系思想,分析了矛盾体系的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转化性和整体性。从矛盾体系论出发,毛泽东赋予上层建筑能动作用以新的内涵,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发展为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④]。从矛盾体系论出发,毛泽东要求立足于全局来把握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例如,只有把中国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只有立足于战争全局,才能确定战争局部的意义,因此研究战争局部的战术指挥员也必须懂得事关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是改革观、发展观。邓小平改革观是整体改革观,他在坚持以经济改革为核心的同时,又强调社会的整体改革、全面改革。邓小平发展观是整体发展观,他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做到协调发展;他在肯定部分人、部分地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的同时,又强调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他在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性的同时,又十分重视人的现代化,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跨世纪的战略目标。赋予社会整体论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
如果说从社会本质论向社会整体论的转变主要是在客观规律的层面上深化唯物史观,那末从历史过程论向主体活动论的过渡则是在更广泛的主体与客体、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关系的视面揭示唯物史观的实质。严格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过程论与主体活动论的统一。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⑤]它把社会的发展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即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⑥]正确说明了历史主体的活动及其价值。不过,在理论活动早期,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述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必然性和人的活动的受动性、非选择性,晚年恩格斯侧重于说明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把理论重心从历史过程论转向主体活动论。恩格斯主体活动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劳动本体论、意志合力论和阶级意识论。在劳动本体论中,恩格斯不仅从发生学角度论述了劳动对人类社会的根源性意义,认为劳动“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⑦]而且把劳动看作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提出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意志合力论”分析了历史过程的动力系统中的主体意志的作用,阐述了历史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必然与自由、能动性与受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规律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统一。“阶级意识论”主要揭示了无产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能动性。恩格斯把十九世纪末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工人运动长期处于自发、分散和停滞状态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工人的阶级意识淡薄,要求加强宣传、教育,使阶级斗争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相互配合,形成“向心的攻击”。
晚年恩格斯主体活动论思想没有得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解和重视。他们片面强调历史规律的强制性和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贬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历史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唯物史观变成见物不见人的机械论、宿命论。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发挥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忽视的主体活动论,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强调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客体、自然、感性,从而“自然是个社会范畴”;主张用实践本体论代替传统的物质本体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历史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认为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客体(大工业发展的产物),又是历史的主体(具有创造历史的力量)。卢卡奇等人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具有合理性,但他们用主体消解客体、用社会消解自然、用实践消解物质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列宁真正继承并发展了晚年恩格斯主体活动论思想。列宁并不象某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象考茨基一样的唯科学主义者,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规律论与主体活动论的统一,并且在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主体活动论提到首位。列宁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主体维度解释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仅承认历史必然性还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⑧]第二,阶级意识灌输论。列宁反对阶级意识产生问题上的自发论,认为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灌输。第三,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强调把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四个不同层次的历史主体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二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否认党和领袖权威的“左”倾幼稚病,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历史过程论与主体活动论是统一的。相对而言,他特别强调了历史主体在中国革命中的能动作用。第一,提出了主体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论断。他多次指出,战争是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综合国力的较量,但这些只使战争胜负具备了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主观的努力,……是决定的因素。”[⑨]第二,十分重视主体自身建设。毛泽东强调,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必须改造人本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作为中国革命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党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因而成为毛泽东主体建设理论的重点。他建构了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主要内容,以整风为主要形式的党的建设的完整理论。在新时期,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历史主体论发展为以解放思想为核心的主体解放论。
三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又是科学的历史方法论。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创立和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其中心任务,那末晚年恩格斯不仅承担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重任,而且肩负着阐明这一科学理论的方法论方面的新使命,并且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者更加突出。因为恩格斯发现,不仅涌入党内的青年派大学生把唯物史观当作公式和套语来裁剪历史事实,而且第二国际领导人在运用理论于实践时也存在简单化、教条化倾向。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如果“把它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⑩]不过,由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提到实践日程,晚年恩格斯只是从理论方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方法论性质和功能,没有就其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展开论述。即便如此,晚年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视代表了二十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面。
列宁的理论活动具有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国家环境。一是列宁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已提到实践日程。二是列宁所处的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在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个崭新的课题,在马恩著作中无现成答案,需要从俄国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方面。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认识马克思主义方法”。由此,他一方面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化为关于俄国革命的纲领、策略、方法,另一方面又注意对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方法论方面加以展开,例如,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的客观主义原则,发现历史规律的两个归结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把个人活动归结为阶级活动的阶级分析法、环节一链条法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马克思主义被归结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而社会历史理论又被归结为一种以总体性为主要原则的历史方法论。卢卡奇公开宣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即使现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马克思的每一个理论命题,也不丧失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应该说,在时代转换,科技革命和理论日益实践化的二十世纪,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性质和功能是正当的。问题是,卢卡奇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解释功能和规范功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客观上为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修正主义提供了理论辩护。
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基础上重点发挥其方法论方面并取得极大成功的是毛泽东。从内容看,毛泽东哲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毛泽东哲学是中国革命的理论总结,具有更鲜明的实践性。其二,毛泽东哲学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方法论科学,具有更突出的方法论特征。他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哲学应“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应区分其词句和实质,重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首次把思想方法论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并建构了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内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方法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来概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既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理论的提出,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功能和方法论的本质。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②③:《列宁选集》第1卷,第141、42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237、458页。
⑧:《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恩格斯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