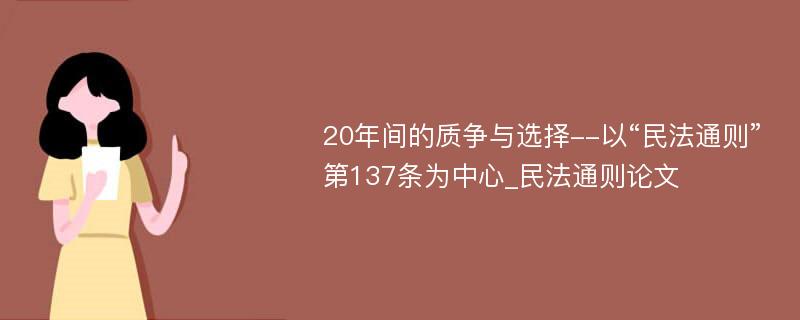
“20年期间”定性之争鸣与选择——以《民法通则》第137条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通则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法通则》第137条中“20年期间”之定性可谓“老生常谈”,① 因为在“琳琅满目”的民法学教科书中其均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它又有待给出“确定答案”,因为各种学说之争从未停止,甚至还愈演愈烈。如果对《民法通则》实施二十余年来“20年期间”定性之争作一个简单盘点,前十年主要是除斥期间说与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之竞争,而近十年来主要是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与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之对抗,最长期间限制说则作为一种新型学说还未形成足够的影响,总的来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仍居统治地位。本文对该问题如此关注还基于如下两个理由:一是“20年期间”如何定性直接关系到其在未来民法典的技术位置,比如究竟是像《民法通则》第137条那样将“20年期间”与普通诉讼时效起算规则置于同一条文中,还是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并列排在若干条文中,或是将其纳入除斥期间规则体系中;二是“20年期间”之不同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对诉讼时效制度及其精神的不同理解,于是该问题也成为我们检验和反思既有诉讼时效观念的一块试金石。本文试图对“20年期间”之定性学说进行全面盘点和系统反思,并表明自己的基本立场。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典中都存在类似的期间甚至类似的定性争论,我国诸多民事单行法也存在与“20年期间”性质相同的期间。因此,本文的分析不可能局限于《民法通则》第137条,也不可能局限于我国法的考察,第137条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分析样本而已。
一、除斥期间说:日渐式微的“先行者”
除斥期间说主要基于如下三个理由。一是“20年期间”是“为了弥补诉讼时效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设置了一个不变期间加以限制,以防止出现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导致的法律关系不稳定,因此不是诉讼时效期间。二是“20年期间”不适用中止和中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5条第2款),因此与诉讼时效期间相比属于明显的“不变期间”,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前者为可变期间,可以中止和中断,而后者属不变期间,不能中止和中断。② 于是,明显属于不变期间的20年当然应被归入除斥期间范畴。三是“20年期间”是“从当事人的权利客观上发生时起计算”,这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特殊诉讼时效期间采取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的主观起算标准明显不同,既然归入诉讼时效并不合适,那么在权利行使的两种限制(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之中,“20年期间”更应归入除斥期间。③ 目前民法学界主张除斥期间说的学者相对较少,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持这种观点,该建议稿第270条[诉权的除斥期间]规定:“从完成行为起算的20年过去后,不承认任何诉权有效。此等期间不得中止,也不得中断。”④ 与我国除斥期间说的式微不同,日本学界和实务界倒是对除斥期间说情有独钟。《日本民法典》第724条规定:“因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道其损害及加害人时起三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起,经过二十年时,亦同。”通说、判例认为《日本民法典》第724条的3年期间是消灭时效期间,但“20年期间”是除斥期间。⑤
除斥期间说充分肯定了“20年期间”与除斥期间特征的相似性,以及“20年期间”与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之间的重大差异,因此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除斥期间说存在的局限更明显。一是除斥期间说过分夸大了“20年期间”与除斥期间在“不变期间”特征上的相似性,却忽视了“20年期间”与除斥期间其他方面的重要差异,如“20年期间”适用于请求权,而除斥期间却适用于形成权;“20年期间”只是使义务人获得抗辩权,而除斥期间的效力则为实体权利的消灭;除斥期间一般较短,因为形成权对法律关系影响较大,不宜久拖不决,各国立法大多规定得较短,一般不应达到20年期限;⑥ 除斥期间从权利人可行使权利时起算,而“20年期间”则不考虑权利人可以行使权利的主观因素等。⑦ 简言之,除斥期间说陷入了“以偏概全”的局限。二是除斥期间说与现行法某些规则存在冲突。根据《民通意见》第175条,“20年期间”虽不适用中止、中断规定,但却可以延长,这与除斥期间不得延长的一般原理并不相符。⑧ 三是除斥期间说过分局限于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两分法”,将那些与诉讼时效期间不同的期间都统统“非此即彼”地直接归入除斥期间范畴,却未考虑“第三种可能性”,以至于除斥期间说的论证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对“20年期间”之定性,还不如说是对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二者差异的再次确认和解释。
考察该学说在我国产生的背景或制度环境可以发现,除斥期间说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来长期的“职权主义援引”立法和司法实践,⑨ 至少是受到了后者的重要影响。如持除斥期间观点的学者同时阐述了诉讼时效援引的职权主义特征:“无论当事人是否了解时效的规定或是否提出时效抗辩,司法机关均应依职权调查诉讼时效问题,如果原告的请求或权利适用诉讼时效,且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又没有应予保护或延长时效期间的特殊情况,就应判决对其权利不予保护。”⑩ 由于诉讼时效援引的职权主义倾向和做法,原本诉讼时效制度的“私人抗辩”效果消失了。法官主动援用诉讼时效,实质上已经使诉讼时效“除斥期间化”,并因而从根本上扭曲了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来面目。(11) 就其对除斥期间学说定性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言,既然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都成为法官可以主动援引的事项,那么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在是否允许法官主动援引上的重要差异实际上被消除了,(12) 这相当于原本会成为除斥期间学说定性重要障碍的特征差异由于相关制度的“变异”而不存在了。在某种意义上,除斥期间说在我国逐渐式微的事实可以从诉讼时效援用的抗辩模式逐渐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和制度的确立之中得到解释。(13)
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常青树”的内在困境
在“20年期间”定性问题上,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一直在我国学界占据统治地位,(14) 即使目前它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该说看来,“20年期间”与2年、1年等诉讼时效期间均为“关于诉讼时效”的期间,都是对权利人权利行使的限制措施,将“20年期间”收编于“诉讼时效期间”名称之下理所当然。(15) 虽然“20年期间”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存在的差异也同时被强调(如前者具有固定性,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而后者广泛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前者在起算上具有特殊性,从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而后者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等),但这种差异却往往被视为具体诉讼时效期间之间的“表面”或“个性”差异,与是否属于诉讼时效期间这一“本质”问题无关。然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理解和定性在理论上和规则设计中都有重大缺陷。
第一,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模糊了诉讼时效期间的内涵和边界。诉讼时效的效力在于请求权因期间届满而丧失可强制执行性,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与请求权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一方面,某个诉讼时效期间针对特定范围内的请求权;另一方面,某一请求权只能适用一种诉讼时效期间。然而,将“20年期间”作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定性却打破了诉讼时效期间与请求权的这种对应性和确定性,造成了某一请求权能够适用两种诉讼时效期间、某一诉讼时效期间能够适用于所有请求权的混乱局面。对此,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可能会提出如下辩护: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与2年或1年的普通或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并不会同时适用(前者是在权利人不知道或不应知道的情况下适用;后者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因此对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定性的质疑是陷于纯粹概念之争的“小题大作”。这一辩护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它忽视了大陆法系民法讲求概念逻辑和体系性的特征(除非我们抛弃之)。一旦用“诉讼时效期间”指称产生根源和规范目标并不相同的期间,那么这一概念事实上已经无法向我们清晰展示其真正内涵,其边界何在;二是它忽视了这种定性对法官和民众准确理解“20年期间”可能造成的困难,用同一术语指称不同的事物会大大增加他们理解的难度和成本,甚至使准确的理解完全不可能。正如德国学者魏德士所指出的:“词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和变迁性是语言理解过程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交流双方能够并且必须为词语的含义约定一个特定的范围。”(16)
第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导致“20年期间”成为诉讼时效期间家族中的异类。各种诉讼时效期间都与特定范围的请求权相连,并形成了多元层次体系,如《德国民法典》第195条、第196条、第197条分别针对不同请求权规定了3年(普通时效期间)、10年、30年消灭时效期间。同时,《德国民法典》也存在类似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20年期间”的诸种期间,其第199条规定:“……(1)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自有下列情形之年的年末起算:1.请求权在该年以内产生的,并且2.债权人在该年以内知道或者在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知道使请求权成立的情况和债务人的。(2)以侵害生命、身体、健康或者自由为依据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论它们在何时产生和债权人是否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自实施行为时、违反义务时或者引起损害的其他事件发生时起,经过三十年而完成消灭时效。(3)其他损害赔偿请求权:1.不论是否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自它们产生时起,经过十年而完成消灭时效,并且不论它们在何时产生和债权人是否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自实施行为时,违反义务时或者引起损害的其他事件发生时起,经过三十年而完成消灭时效。……”显然,《德国民法典》只是将第199条的10年和30年视为时效期间起算的限制性期间,是为防止采纳主观起算标准可能导致的对权利人无限期保护而设,或者也源于“时效开始于获知或在重大过失时未获知之时的规定会造成时间上区分的困难”的现实难题。(17) 换句话说,这些期间只与“起算”有关,与诉讼时效的“常规性期间”设定(如第196、197、198条)无关。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20年期间”不也被置于关于“起算”的条文吗?我们却硬要将其界定为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结果我们不得不通过多种方式强调该期间的特殊性以显示将其归入诉讼时效期间家族的限度,如学者们虽然主张“20年期间”为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但在期间分类上却只区分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包括《民法通则》规定的短期诉讼时效期间和各民事单行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0年期间”并未被列入。(18)
第三,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可能(也许是已经)造成对我国诉讼时效起算标准的误解,该说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我国既存在较短诉讼时效期间(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加主观起算标准的模式,也存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加客观起算标准的模式。(19)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德国民法典》提供了难得的参照标准。虽然2002年修正后的《德国民法典》在缩短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的同时将相应的起算标准从“客观标准”变为“主观标准”,但较长消灭时效期间配以客观起算标准和较短消灭时效期间配以主观起算标准是继续并存的。前者如《德国民法典》第196条:“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请求权以及要求设定、转让或者取消土地上权利的请求权,或者要求变更此种权利的内容的请求权以及对待给付请求权,经过十年而完成消灭时效。”《德国民法典》第197条:“(1)除另有规定外,下列请求权经过三十年而完成消灭时效:1.由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产生的返还请求权,2.亲属法和继承法上的请求权,3.被有既判力地确认的请求权,4.由可执行和解或者可执行证书产生的请求权,以及5.因在支付不能程序中进行的确认而变成可执行的请求权。……”后者如《德国民法典》第199条(如前所述)。我国有些学者常常提及的所谓“20年期间从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而2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则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表述,似乎更像是针对《德国民法典》“两种消灭时效起算标准并存”模式的评论,而并不适用于对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标准的描述,因为我国实际上只存在较短诉讼时效期间配以主观起算标准的模式。
最后,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甚至可能造成立法设计中的混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2年12月1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第99条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期间为三年,但下列情形为一年……前款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民法草案》第100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下列情形之一,超过三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前款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这两条规定产生了两个问题。(1)如果两个条文都是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标准的规定,《民法草案》第99条和第100条就是根本冲突的。至少从表述上看,两个条文的确都可以单独作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的规定,其中《民法草案》第99条可以视为3年普通时效期间和主观起算标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规定,《民法草案》第100条可以视为20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客观起算标准“自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的规定。然而,一个诉讼时效制度体系之内不能存在两种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方式。(2)如果立法者并非试图设定两个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标准,《民法草案》第100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实际上只能视为对第99条“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期间为三年”这一规定的补充和限制,就像《民法通则》第137条一样。换言之,《民法草案》第100条虽然使用了“诉讼时效期间”称谓,但并非真的界定了另一种诉讼时效期间,而只是关于“起算”的补充规则。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体现了一种将其与普通时效期间并列的思维倾向,在《民法草案》起草者看来,第100条只是将《民法通则》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独立出来与普通时效期间的规定并列、从而使其更符合诉讼时效期间的称谓或身份而已。
三、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破有余而立不足”的“挑战者”
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虽然早已提出,但其地位确立和影响拓展却是近些年来的事情,(20) 并已发展壮大为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的最大“威胁”。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的论证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揭示“20年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重要区别(就像除斥期间说所做的一样),如前者从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后者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前者不能中止、中断,而后者可以中止、中断。二是强调最长权利保护期限是为克服诉讼时效制度可能导致的无限期保护权利之缺点而设的制度。(21) 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的出现和壮大反映了学者们试图跳出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二分法”之外寻求“第三种可能”的努力和共识,反映了他们对“20年期间”与其他诉讼时效期间差异的重新审视和界定,即这些差异既不应视为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差异,也不应视为诉讼时效期间的内部差异或者诉讼时效期间多样性的表现,而是应当视为“20年期间”独立性和独特性的有力证明。
虽然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已经在寻求“20年期间”定性新的可能性上大有进展,直指其“克服诉讼时效制度可能导致的无限期保护权利的缺点”之意义,但该学说也有着自身的局限,“破有余而立不足”,至少是在其反对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和除斥期间说面前是如此。
第一,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虽竭力强调其与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和除斥期间说的本质差异,但却缺乏足够的正面论证。一方面,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在论证时提到的“20年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诸多差异,与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论证“本质属于诉讼时效期间,只不过特殊而已”这一观点时的表述并无多大差异;另一方面,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在论证时所进行的“20年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比较分析,与除斥期间说在论证时所进行的比较分析几乎如出一辙。(22) 如此一来,至少对于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和除斥期间说的坚定支持者而言,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是判断多于论证,缺乏足够细致的推理过程,该说除了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之外,并不比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甚至不比除斥期间说做得更多或更具说服力。
第二,“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表述本身也遭到了质疑,特别是遭到持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观点学者的质疑。如有学者指出:“将20年作为民事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限,首先是没有揭示出20年的法律本质。民事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限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而且从文义上说,民事权利的保护原则上是不受期限限制的,即便有限制,也往往长于20年。比如在我国,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等的保护就不受期限限制,而发表权、获得报酬权等的保护期限则是作者生前加死后50年。因此笼统地说20年是民事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限难免令人费解。其次,说20年是民事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限是建立在权利遭受了侵害的基础之上的,而当权利遭受侵害之后的法律保护期限在本质上就是指诉讼时效期限。很难想象除了诉讼时效期限,还有什么期限称得上是对遭受侵害之后的民事权利的保护期限。”(23) 这一质疑不无道理,作为一个广义称谓,权利保护期限既可指向法律赋权意义上的保护期限(如著作权中的发表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生前加死后50年),也可指向法律限权意义上的保护期限(如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还可指向为防止主观起算而导致时效届满被无限期推迟而设置的限制措施等。用一个如此广义和概括的称谓指称其中一种可能情形达不到清晰界定的目的。记住德国学者魏德士的提醒是有益的:“新概念就应该比旧概念更加准确地描述对象和关系,不过必须避免不清楚的、容易引起误解的新词语或定义,因为它们对法学和法律实践都是有害的。”(24)
第三,“权利保护”用语在描述诉讼时效制度时极易引起歧义。我国《民法通则》在“第七章诉讼时效”中使用“请求保护”(第135条)、“不予保护”(第137条)等表述,这种用语倒向了诉讼时效援用的职权主义倾向。可作为佐证的是,我国《民法通则》虽未像《苏俄民法典》那样明确规定法官依职权援用诉讼时效,却仍与后者一样长期保持着诉讼时效援用的职权主义实践。在诉讼时效援用的抗辩模式逐渐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并已在制度上确立的今天,“权利保护”用语显得不合时宜。在“20年期间”定性问题上,这种用语问题已成为持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说学者对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说的批评理由,即20年期间“不宜看作权利最长保护期限。因为这20年期满后,权利人接受义务人自动履行之后果仍受法律保护,并非绝对不受法律保护,因此,20年期间规定应视为最长诉讼时效”。(25)
四、最长期间限制说:立足“功能”的“新生代”
四种学说中,最长期间限制说出现最晚,(26) 也还有待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然而,最长期间限制说最为准确地界定了“20年期间”的性质——为防止主观起算标准可能导致的对权利人的无限期保护而设置的限制性措施,并且在概念表述和具体论证上更具说服力。对“20年期间”性质的界定只能从其与主观起算标准的内在关联着手,而不是从强调“20年期间”与普通和短期诉讼时效期间在固定性和起算标准上的差异等来入手。一方面,采取客观起算标准而非现行法规定的主观起算标准并不足以证明某一期间不属于诉讼时效期间范畴,客观还是主观的起算标准只是立法者根据其所理解的诉讼时效精神和时代背景而作出的技术性选择(如《德国民法典》就同时存在长短不一的时效期间及其相应的客观或主观起算标准),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界定是否属于诉讼时效期间的分界范畴;另一方面,所谓固定性,通常被理解为不适用中止和中断规定,因而属于不变期间而非可变期间,但这种固定性事实上也源于“20年期间”与主观起算标准的关联性。正是为防止主观起算方式可能导致的对权利人的无限期保护,法律设置了限制期间,又由于该期间必须考虑权利人不知道或不应知道的“无辜”情形,期间又必须很长,这种足够长的限制期间已经无法再容忍中止和中断制度的适用,因为那必将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无限期保护。仅仅强调“20年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之间所谓固定性和起算标准的差异,更多只是阐述了特征和结果,并未解释性质和原因。在此意义上,最长期间限制说更侧重从制度起源与功能角度对“20年期间”进行定性,而不是侧重强调它与其他期间的特征差异。
“20年期间”与主观起算标准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在采取客观起算标准和较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则中,并不存在最长期间限制。如《德国民法典》第199条的20年和30年都是针对采取主观起算标准的3年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而设,对于第197条采取客观起算标准的30年消灭时效期间,则并不存在相应的最长期间限制,因为客观起算标准的选择决定了不存在长期无法计算时效的困境。《日本民法典》原则上采取了较长诉讼时效期间(第167条规定的10年和20年期间)和主观起算标准(第166条规定的“自权利可以行使时起进行”)的模式,因而在“总则”编第七章“时效”中并没有关于最长期间限制的规定,倒是在债权编第五章“侵权行为”中第724条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定了特别的主观起算标准(“知道其损害及加害人时起”)和较短的时效期间(3年),相应地规定了与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类似的“20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了与日本民法类似的立场,即原则上采取较长诉讼时效期间(第125条规定的15年期间)和客观起算标准(第128条规定的“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的模式,因而在“总则”第六章“消灭时效”中并没有关于最长期间限制的规定,倒是在“债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五款“侵权行为”中第197条为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定了特别的主观起算标准(“自请求权人知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起”)和较短的时效期间(2年),与此相应规定了与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相同性质的10年期间。
就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草案或学者建议稿)而言,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总则编》对于诉讼时效起算标准采取“客观”立场,该建议稿第192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时效依以下规定开始计算:(一)时效期间自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27) 在建议稿中并没有类似《民法通则》“20年期间”的规定。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对于诉讼时效起算标准也采取“客观”立场,该建议稿第252条规定:“时效期间从可以行使诉权之时起算。”(28) 在建议稿中也没有类似《民法通则》“20年期间”的规定。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总则编》对于诉讼时效起算标准采取“主观”立场,该建议稿第245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相应地也有类似《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无论权利人是否知道起权利受到侵害,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给付义务。”(第246条)(29) 《民法草案》对于诉讼时效起算标准也采取“主观”立场,该草案第一编“总则”第99条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期间为3年,……”于是有了《民法草案》第100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只有“20年期间”与主观起算标准相伴而生且只为其存在才能解释草案或建议稿中仅仅由于起算标准的不同导致最长期间限制的存在与否。
在我国,20年期间与主观起算标准的内在关联这一直接决定其性质界定的要素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和强调,20年期间很“自然地”被界定为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以下四个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这种状况。(1)“20年期间”在我国“关于”诉讼时效的期间体系中的确“最长”。除《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第135条)和“1年”(第136条)之外,《合同法》规定的“4年”(第129条)、《产品质量法》规定的“2年”(第45条)、《环境保护法》规定的“3年”(第42条)等也都属于比较短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与这些诉讼时效期间相比,20年的确是最长的。《德国民法典》第199条的10年和30年与《民法通则》的20年性质一样,但我们可以区分出它并非最长消灭时效期间,因为《德国民法典》第197条已经明确规定了30年“真正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我国学者对修正后《德国民法典》的研究中,将第199条的10年和30年特别称为“最长期间”或“最大期间”,(30) 而不是“最长消灭时效期间”,应该有基于区分需要的考虑。(2)我国诉讼时效期间普遍很短,“20年期间”很容易给人以“设置更长时效期间以便更周全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印象,(31) 从而扭曲了“20年期间”的真正规范目标——对权利人权利行使的限制。如果说“20年期间”是为特别保护某种利益的话,那也是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在权利人不知道且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20年期间”不存在无疑对其有利,而对债务人不利。“20年期间”正是为了扭转对债务人的极端不利局面、防止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限制的失灵而设置的补救措施。正如德国学者福克斯所指出的:“对时效的起算点取决于债权人主观上知道的规定,在个别情况中可能导致时效期间在侵权行为发生很长时间后才开始计算,或者推迟的时间甚至完全无法确定。这不符合法律也应当保护债务人法律安全利益的原旨。”(32) (3)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单行法普遍对诉讼时效期间采取了主观起算标准,如《环境保护法》第42条、《产品质量法》第45条等。由于主观起算标准的这种唯一性,“20年期间”只源于和针对主观起算标准的本质特征没有得到关注,而不像现行《德国民法典》能够清晰显示这一点(如前所述)。(4)我们未能将“20年期间”与民商事单行法中的其他最长期间限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致出现认识的片面。事实上,能够称得上“最长期间限制”的并非只有《民法通则》第137条的20年期间,《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产品质量法》第45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海商法》第258条第2项、第265条对有关旅客死亡的请求权、油污损害请求权也规定了最长期间限制,分别为3年和6年。如果我们将其与《民法通则》第137条的20年期间结合起来考察,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我们对“20年期间”的诸多误解。
本文将“20年期间”以“最长期间限制”定性,还与另一事实有关,即这种类型的期间不仅出现在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则中,也出现在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则中。许多国家民法典的除斥期间规则中都有功能上类似《民法通则》第137条“20年”的期间设置,如《日本民法典》第126条规定:“撤销权自可以追认时起,五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行为时起,经过二十年时,亦同。”《德国民法典》第121条规定:“(1)在第119条、第120条的情况下,必须在撤销权人知道撤销原因后,在没有有过错的迟延的情况下(不迟延地)进行撤销。……(2)自意思表示做出时起十年已过去的,撤销即被排除。”《德国民法典》第124条规定:“(1)依照第123条可予撤销的意思表示,只能在一年的期间内撤销。……(3)自意思表示做出时起十年已过去的,撤销即被排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3条规定:“前条之撤销,应于发现诈欺或胁迫终止后,一年内为之。但自意思表示后,经过十年,不得撤销。”其第245条规定:“前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有撤销原因时起,一年间不行使,或自行为时起,经过十年而消灭。”对于撤销权除斥期间中这种明显很长的限制期间,学者们或者根本未提到这种期间及其性质,(33) 或者将其与常规除斥期间作同一对待,(34) 或者与常规除斥期间区分为“短期行使期间”和“长期行使期间”。(35)如果我们将除斥期间规则中存在的这种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而将诉讼时效规则中存在的这种期间定性为诉讼时效期间,就会导致具有同样功能的期间被作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定性,并引起我们对两种期间差异的误解和想象。在此意义上,将“20年期间”定性为最长期间限制实际上是从其原初功能的角度而非它所属法律领域所作的界定。
注释:
①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为行文简便,下文以“20年期间”指称本条后半句所指之“二十年”。
② 有些国家的民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如《葡萄牙民法典》第328条规定:“除斥期间既不中止亦不中断,但法律有此规定者除外。”
③ 参见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④ 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⑤ [日]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39页。
⑥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6页。
⑦ 参见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
⑧ 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页。当然,《民法通则》第137条确立的延长制度是否合理,可以也需要进一步考察和争论。
⑨ 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有这样的规则,《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诉法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⑩ 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
(11) 我们所熟知的所谓权利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和抗辩权发生主义,尽管视角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是依据“私人自治”模式来建构的,《苏俄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倒是有些特立独行。《苏俄民法典(1964)》第82条规定:“法院、仲裁署或公断法庭,不论双方当事人声请与否,均应适用诉讼时效。”
(12) 二者差异甚至体现于各国法典,如《日本民法典》第145条规定:“时效非经当事人援用,法院不能依时效裁判。”《巴西新民法典》第210条规定:“在法律规定了除斥期间的情形,法官应依职权指明此等期间。”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使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14) 参见陈国柱主编:《民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页;孙宪忠主编:《民法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王利明等:《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15) 有学者将“20年期间”定性为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其“规定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一章”。参见葛承书:《民法时效——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16) [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7) 朱岩:《德国新债法:条文及官方解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18) 参见尹田主编:《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9页;汪渊智主编:《民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19)参见吴庆宝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2009-2010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20) 参见徐开墅等:《民法通则概论》,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李开国主编:《中国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郭明瑞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王卫国主编:《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21) 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郭明瑞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22) 参见王卫国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23) 葛承书:《民法时效——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19页。
(24) [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
(25) 参见陈明添、吴国平主编:《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323页。
(26) 在国内学界,龙卫球教授最早提出应将“20年期间”定性为“诉讼时效计算之最长期间限制”。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22页。
(27)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28) 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29)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30) 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杜景林、卢谌:《德国债法改革:〈德国民法典〉最新进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31) 参见郑立等:《民法通则概论》,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
(32)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33) 参见刘得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林诚二:《民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86页。
(34)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5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35) [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解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标签:民法通则论文; 德国民法典论文; 诉讼时效论文; 债权请求权论文; 债权诉讼时效论文; 民法论文; 法律论文; 除斥期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