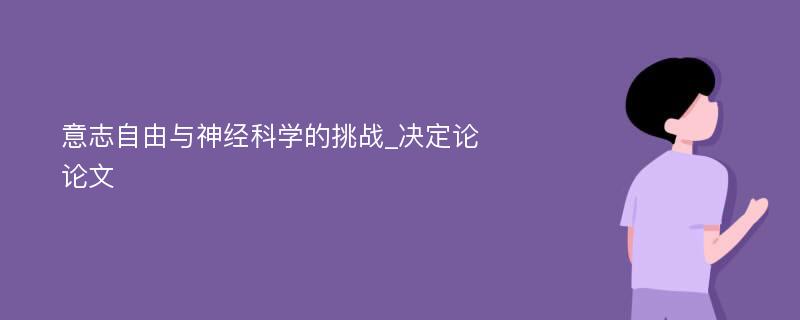
意志自由与神经科学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志论文,神经论文,科学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观念形态发展的漫长历史上,有一些观念总是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反复探究,比如“自由”、“正义”及“民主”,等等。自由是人的自我理解中的一个基础性的观念;自由的属性同理性、个体独特性等属性一起,构成了人类之所以能够超拔于自然界而成为拥有精神性禀赋的文化存在的最根本的特征。对自由的探索一直都是人类哲学研究的主导性动机,近代以来甚至构成了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里的奠基性、关键性观念。所谓自由,是指拥有行为能力的人类个体能够自我决定,意味着当事人在某一给定的场景下,有能力不受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强制,做出一种与其事实上已经做出的选择完全不同的选择。纯粹从形式上看,自由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所谓消极自由,是指行为主体能够摆脱外在因素(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强制和内在因素(身体需求、感性冲动、情感偏好)的阻碍。就政治共同体(如国家)而言,其在消极自由方面的义务是不任意、非法地干预或阻碍行为主体的自由。所谓积极自由,是指行为主体的自我决断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即能够将其意志贯彻到现实的行为之中:不仅是设定目标,而且还能选择途径、采取措施、满足需求、完成心愿。就政治共同体(如国家)而言,其在积极自由方面的义务是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帮助行为主体实现其行为自由。
从历史上看,自由的形态与地位曾在欧洲大陆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变迁轨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重视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外在的政治自由,而近现代思想家们则更关注人在其本质上是否拥有一种能够自我决断的权利这种内在的自由。古希腊时期,人们强调本体论基础上的秩序高于自由,而近现代时期,人们则强调自由先于秩序。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被理解为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作为一项特殊的法律规定,自由的观念使一部分人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部分人被称为自由人,能够基于自身意志而行动,免于外在的暴力、伤害和压迫,不同于没有自由的奴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即为自由人的共同体,他们为了自给自足的目的而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遵循得到认可的规则,基于人类最高的善而追求人生的目标。同时,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仅认可自由,而且还把自由理解为是基于理性的、以善为导向的,并且是超越了感性自然物与纯粹自发性的选择能力。
然而,从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起,经过犹太-基督教的发展,直至近代启蒙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运动,自由逐渐演变成每个个体及每种政治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的普遍需求。在近代思想家眼里,自由已不再是一种城邦中所体现的、为少数人独享的现存之物,而是所有的人基于其自然本性所应享有的天赋权利。正如康德所言:“自由(独立于一种他在的强制性的任意),只要它依照一种普遍的法则与每一种他人的自由共在,便是这样一种唯一的、原初的、每个人因其人性而拥有的权利”。(转引自Wildfeuer,S.363)在近现代这一人类自我解放的伟大时代里,自由成为改变近代以来人、道德与社会原有面貌的一面最重要的精神旗帜:对于个人而言,个性自由的运用使得当事人赢得强大的品格、高度的自我约束、发达的理智、精致的鉴赏力和思想的原创性(密尔语)。对于道德而言,“道德本来意义的功效在于出于自由和为了自由之故而设置一种目标。这样自由就全然作为意志自由而变成了道德行为的原则与标准”。(Pieper,S.165)对于社会而言,人们本着自由的精神努力冲破旧有政治、经济、观念秩序的桎梏与强迫,建构起使公民的自由空间得到保障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这其中,自由作为“近代人文主义的谋划”(H.Krings,转引自Wildfeuer,S.363),不仅构成了现代人权理念的核心,而且也成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存在的论证理由。
总而言之,自由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道德产生的前提、社会建构的原则。自由是人类文明成熟程度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正向价值的标尺。就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而言,自由又分为意志自由与行为自由。简单来说,意志自由是行为自由的基础,行为自由是意志自由的实现。在宏观的自由观念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所当然的背景之时,个体的意志自由与相应的行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这一点已成为近代以来哲学家、伦理学家的主流共识,人对意志自由的拥有也已成为几乎全球公认的人的图景中的重要特征。
但是,自由以及意志自由概念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及精神道德生活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并不意味着意志自由这一观念在自然科学界也得到了清晰的理解和普遍的认可。恰恰相反,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实验技术的精细化,科学界对意志自由是否存在的质疑却有增无减。2000年以来,意志自由问题越来越受到神经科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重视,国际顶尖的科学刊物频繁发表认知神经科学家有关意志自由的研究论文,与之相呼应的是相关内容的学术研讨会在欧美密集举行。2004至2006年间的德国,不论是严肃的学术杂志还是通俗的报纸副刊,均出现了大量有关意志自由是否存在的争论文章,认可意志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哲学家与持质疑态度的神经科学家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论战之激烈甚至被惊呼为一场自然与精神大对决的文化战争。这场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焦点为核心的争论,不仅展现了学术界内部观点和立场的正常分歧与交锋,而且还由于议题所涉内容的敏感性,触及到对人的图景的自我理解,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对社会建构及刑法制度也形成挑战。
实际上,认可意志自由存在的立场同否认其存在的立场之间的论争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而是贯穿于两千多年以来的哲学史全部发展过程之中,到了19世纪这一论争达到了一个高潮。否定意志自由存在的观点主要是在宿命论和决定论的立场中体现出来。宿命论认定人的自由选择的体验是纯粹的幻觉,人类的一切均是由命运所决定的,甚至连人自身的动机、权衡和行为也取决于命运的安排。决定论有别于宿命论,它认可人的决断会对未来发生之事产生影响,但又认为人自身的决断取决于先在的身心上的原因。在决定论看来,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有原因的,一种现象是作为原因的另一种现象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由因果的相互作用所充斥的封闭的体系,万事万物均为宇宙因果链条所构成的严密系统中的一环,世界取决于因果必然性法则的统治与支配。决定论的观念统摄着整个自然科学界,正如德国脑科学家普林茨(W.Prinz)所言:“科学喜欢一元论和决定论”。(Prinz,S.23)按照自然科学描绘的由因果链条所支配的世界图景,人的一切物质活动均取决于粒子物理学意义上的原因,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均取决于神经生理学意义上的原因,这些因果联系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得到揭示、拆解和分析还原的。于是,在这样一个因果必然性统治的封闭世界里,对于人类而言,由于所有发生的一切决断与行为都是由先前出现的事件所确定的,故人的意志自由、自我决定便无从谈起。人类个体不过是世界整体中的部分或环节,所谓“自由”不过是体现在个体对整体要求的服从上。弗洛伊德(S.Freud)早就断言,无意识的机制强烈地确定了人的行为。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F.Skinner)也断定,自由与尊严不过是幻觉,因为人类所有的行为均完全受制于基因设置,与生俱来的行为倾向的强与弱均受控于某种特定的调节机制(如奖励与惩处)。(cf.Pieper,S.164)人既然无意志自由和选择的可能,那么他就无需也无法对其行为承担什么责任,道德上的判断、称赞与批评均失去了意义。这就是所谓强的决定论的立场。
但是,即便是在决定论阵营的内部,在因果必然性是否绝对有效以及人的自由决断是否可以完全被否定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某种观念分歧。与强的决定论相对立的是所谓弱的决定论。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架构的提出要归因于休谟的经验哲学。但即便是在18世纪,休谟本人也并未认同强的决定论的立场。休谟认定人的所有的知识均来自于经验观察,有关因果性的认知也不例外。但经验观察无法证实因果必然性,因为因果之间的联系是我们给予的,它们之间的“必然性并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只能是属于我们的思想活动,只要我们将它们前后一致地相互联系在一起”。(Schweppenhaeuser,S.68)于是,在休谟看来,强的决定论所认定的“结果可以是先验地从其原因中导出”的观点,便是站不住脚的。故休谟属于弱的决定论的代表,他承认我们的道德决断并非来自于强制,而是来自于自由的决定,所以道德与自由相关。逻辑实证主义的奠基人石里克(M.Schlick)曾经骄傲地宣称,如果他的《伦理学问题》里也有一章谈论自由问题,他就会感到羞耻。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全然倒向强的决定论。在他看来,由于我们无法确认因果原则是否毫无例外地绝对普遍有效适用,故有关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论争最终也是难以决断的。(cf.ibid,S.65)
然而,2000年以来,强的决定论立场再次受到了关注并为一些神经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所强烈坚持,意志自由的存在又一次遭到了质疑,从而爆发了前已提及的有关意志自由的学术论战。而在这一事件中,著名的李贝特行为控制实验起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国神经心理学家李贝特(B.Libet)为了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证明意志自由的存在,做了一项脑神经活动实验,要求志愿的受试者在最多3秒钟的时间里,任意用手指按压按钮,并注意其意识到做出手指按压这项“决定”的时间点。结果表明,当事人的作为大脑无意识活动的所谓“准备电位”(readiness-potential)的出现,比其有意识的决定要早约半秒钟。也就是说,与我们通常认定的“人的有意识的决断导致人的行为,我们是自己生活历史的作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实验表明,首先启动的是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过程(即“准备电位”的建构),然后才有我们对决断的意识,最后才有具体的行为的落实。一句话,我们的有意识的决断不是自主的,而是取决于一种无意识的神经活动过程。我们的具体行为产生的最直接原因不是我们的有意识决定,而是无意识的大脑活动。
尽管李贝特本人并没有据此得出极端的决定论式的解释,但毕竟实验结果与他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之后,神经心理学家哈格德(P.Haggard)和埃尔默(M.Eimer)在更严格的条件下重复了此项实验,证明了李贝特的结果。这一系列脑科学实验似乎也验证了早在1900年弗洛伊德就提出过的理论:无意识的动机与体验在人的决断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尽管当事人自己并不知情。
对于这一实验结果,德国脑科学家罗特(G.Roth)、辛格(W.Singer)和普林茨均认为,实验表明无意识的大脑活动决定了人的有意识的决断,我们的意志受控于大脑中无意识的过程,这说明我们的意志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大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这取决于大脑本身生理过程的运行规律。大脑的决定结果取决于大脑的构成及处理信息的方式,这与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无关。由于我们的意志决定于大脑无意识的活动过程,最终是大脑的无意识的神经活动在做决定,而非人的清醒意识,故人的意志自由只是一种幻象。普林茨因此断言:“我们不是在做我们所愿意的,而是我们愿意我们所做的”。(Prinz,S.22)
从这一大脑的无意识的神经活动过程决定了我们的有意识的决断及行为的所谓决定论中,他们进一步得出所谓生物主义还原论的结论:人类全部的行为方式,以及感知与思想、记忆与决断、情感与评价,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均可还原为大脑中神经信号的加工过程。任何行为动机的生发、决断的权衡经过,都可以依据由自然因果律所决定的神经活动来解释,神经生物学测量手段的精确化使精神现象成为可以客观度量的自然科学的描述对象,甚至还可以因客观化而成为可操作的东西。一句话,一切精神上的东西都可还原为物质上的东西。这样,精神和意识便完全成为自然现象,人的社会特性也完全取决于其生物本质。正如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所总结的那样:“只要行为不再是基于可理解的动机和得到判断的状态,而仅仅是基于自然规则,即借助于组织上的变化、化学过程或物理上的干预得到解释,则‘自然因果性’便……取代了行为的合理性”。(Habermas,2007a,S.274)
上述脑科学家对李贝特实验结果的解释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即:人与动物及其他生物之间不复存在任何区别,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人的精神意义上的道德行为的主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可客观化的神经生理活动过程的运作,该运作是关于大脑的经验性研究的对象。于是,伦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均因无的放矢而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理由。
然而,这种对意志自由持否定立场的神经过程决定论及生物主义的还原论,与人们日常对意志自由、自主决定之客观真实存在的体验完全不符,故难以产生很大的说服力,更不用说得到精神人文科学研究者们的认同。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尽管李贝特实验的结果难以推翻,但人们完全可以对该实验结果做出另一种解读,而从这种解读中并得不出意志自由的存在受到否定的结论。
首先,有关时间差的解释。李贝特实验似乎表明我们大脑的无意识的神经活动过程首先做出了决断,然后才有我们对这一决断的自觉意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的决断是基于大脑的神经活动而进行的,但决断过程并非是大脑纯粹的无意识的活动过程。只是我们对这一决断的自觉意识与决断本身并不是同步的,我们对决断的自觉意识是需要时间的:“人们总是以某种方式仅仅感知到过去了的东西,因而不存在时间上的一比一的感知”。(Klein,S.351)也就是说,在决断与对决断的自觉意识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是决断本身与对决断的意识之间的时间差,而不是先前所说的“无意识的神经活动在先,对这决断的自觉意识在后”这种时间差。从时间差这一理据可以看出,李贝特实验只是表明了我们对决断的自觉意识与决断的出现不可能是同步的,但这种时间延迟并不意味着决断不是我们自主做出的,故从李贝特实验中得不出意志自由不存在的结论。
其次,手指反应有别于自由决断。神经过程决定论之所以认定大脑的神经活动决定了人的决断及行为,是因为根据李贝特实验的结果,先有大脑中的准备电位的出现,然后才有按压电钮的决断,最后才有按压的动作;在这里决断与动作基本上无法分开。由于按压的决断晚于准备电位,故按压者按压决断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但基于上述关于决断与对决断的意识之间时间差的理据,我们可以断定,有关按压决断(如果它真是一种决断)晚于准备电位的出现的观察应该是一种错觉,用这一错觉来否定意志自由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这不是一种错觉,那么就要看实验中的这个按压决断本身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断。什么叫决断?通常我们把决断看成是一种有意的行为,无论是长还是短,它均包含有一种权衡的过程,“该权衡以目标和可选的手段为对象,并且要关涉到机会、资源和障碍”(Habermas,2007b,S.103),故“决断也是一种选择和否定”(Wingert,S.197)。总之,“一种决断仅仅是在无论怎样瞬间和模糊的权衡的结果中成就起来的”。(ibid,S.104)由于决断是一种有意的行为,故决断本身便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在李贝特实验中,当然有决断,但它并不体现在手指按压这一动作上,而是体现在受试人员经过事先权衡,最后做出参与此项实验活动并且按照实验指令和规则完成动作的决定上。当受试人员被置于一种规定动作的程序之中,在最多三秒钟之内随时准备按压电钮的时候,所谓决断已经下出了,受试者注意力高度集中,“随着投入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种直接的先在的任务……有关这一立即实施的行为的准备电位就已经出现了。……有意识的手指按压,即‘现在’就按的最后的意识冲动,仅仅是执行行为。它仅是一种‘小部分决定’,不再有关是否,而仅有关何时……”(Helmrich,S.94)。也就是说,手指按压这一微小的动作已不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决断,而是一种类似于足球守门员扑球动作的条件反射行为,这种机械反应冲动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决断毫无关系。从实际情况来看,作为反应冲动的按压电钮的机械行为晚于与决断相伴的大脑准备电位的出现,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真正的决断已经做出了。而手指按压动作则不是决断,故李贝特实验不仅无法否认意志自由,而且与意志自由本来就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李贝特实验并不是自由-实验,而是一种反应时间-实验”。(Recki,S.46)
再次,科学研究活动本身便蕴含着意志自由。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用论据来说服别人这样一种举动,即通过论辩来让对方信服自己的观点。例如,在有关李贝特实验与意志自由的争论中,辛格就基于决定论的立场,呼吁学界“应当停止谈论自由”(cf.ibid,S.48)。辛格的呼吁意味着他试图以其脑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用理据来说服他人相信意志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之物。但辛格的呼吁与论辩均明显蕴含着一个前提,即对方可以或有可能相信他的说法,而同时也可以或有可能不相信他的说法;或者,对方本应相信他的说法,实际上却并没有相信他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恰恰说明对方一定是拥有意志自由的。因为如果没有意志自由,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则对方就只能相信他的说法。而且,就作为主体的辛格而言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意志自由,辛格自己就不会进行论辩并使用“应当”这一用法,“因为论辩——作为对论据的交流与权衡——本身就是一种出自自由的行动”(Recki,S.47)。而“应当这样做”这一表述本身,便包含着对方也有不这样做的可能性及自由。总之,“大脑研究者们对自己和对其交谈对象都是以自身洞见的自由为前提的”。(ibid)如果没有意志自由,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则科学研究活动本身根本就没有进行的可能。这表明否定意志自由者所坚持的决定论的立场,与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之间是矛盾的。
最后,李贝特实验的主角李贝特本人也没有否认意志自由。即便我们承认有意识的行为是被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所启动的,但在准备电位的形成与有意识行为的实施之间还有几毫秒时间的空隙,人可以在此时运用自由意志来否决这一行为。换言之,“尽管准备电位已经形成,但有目的的小的行为却并非一定会得到执行。因而准备电位的出现并不是说明我们在意志上无法做出别的行为并且我们已被大脑自在的先前决断决定了的合宜的指示器”。(Helmrich,S.96)
在李贝特看来,有意识的自由意志能够控制一个无意识的启动过程的实现,人的意志自由就体现在对行为实施的有意的“否决”上,这样,“无意识的准备电位的存在并不会使人失去自由”(ibid),意志自由就是在对行为的放弃上呈现自身的。尽管李贝特有关意志自由就体现在否决某一行为的能力上的观点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因为相应的否决在(他自己的)实验中并未发生,但日常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却是无处不在的。有的行为的确不可以被阻止,如呼吸,它完全遵循神经活动的程序,只要该程序运行,则我们虽可短暂停顿它,却无法长期停顿它。然而,人的多数行为却会随着意图与动机的改变而受到有意的否决。例如,看见一位明星出现,某人本打算前去与其合影,但担心受到朋友奚落而放弃了;不过,忽然又想到其母亲是该明星的粉丝,一张其与该明星的合影肯定会使其母亲高兴,于是此人又准备迎上前去与该明星打招呼;然而,后来马上又想到该明星已经非常疲惫,如此打扰有些不忍,于是最后此人还是放弃了合影行动。在极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的行为可能在反复的犹豫中被不同的动机所否定,这种情况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以否决为表现形式的意志自由的存在。
另外,所谓二阶意愿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人有像酗酒、烟瘾、暴力倾向等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一阶意愿,但人也有可能出于对自身和社会负责任的考量,而做出一个二阶意愿来阻止上述一阶意愿行为的发生,这个与一阶意愿相冲突的被有意做出的二阶意愿就是意志自由的体现。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场有关人的行为控制的神经科学的实验不仅引发了如此不同的解读和如此巨大的观念分歧,而且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乃至广大公众共同关注的交汇点,这在学术史上并不多见。当然,这种观念、立场上的分歧也绝非偶然,它是人类存在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一种折射或反映。一方面,人类毫无疑问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拥有着潜意识、内在冲动和基因设置;这种情况导致了自然科学将人的行为归溯为化学反应、神经表现、基因条件和生理活动的机制。另一方面,人又不完全从属于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不完全受制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而是一种拥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主体;这种情况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及日常心理学基于人的自由意志、基于人类所特有的感知和判断及决断能力,认为人的种种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取决于理性上可理解的动因,它们并非是预先就被决定好了的。总而言之,针对复杂多样的人的行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都试图做出自己的解析。
然而在自然科学界,有些人并不认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他们拥有一种偏见,认定只有经验科学能够证实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化学与物理学把握得到的事物才是真正现实的。普林茨说:“科学的出发点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均有其原因并且人们可以发现这些原因”。(Prinz,S.22)按照这一逻辑,人的所有的行动,不论是合乎自然因果律的自然行为,还是人的思想及自主决断等精神活动,都应当基于大脑的物理化学反应机制来进行解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最终均可还原为神经科学问题而得到处理。德国心理学与脑科学杂志《大脑与精神》(Gehirn & Geist)2004年第6期所发表的十一位神经科学家的宣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希望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解答意志自由的问题,从而使这一千百年来的哲学论争得以终结。
但是,这些神经科学家们过于乐观和自信了。应当说,像自主决断、道德选择和宗教信仰这类精神活动具有高度复杂的特性,因而难以肯定这些精神活动均可还原为神经过程。诚然,神经生物学可以高度精确地描绘某些精神现象的神经联系,特别是像颜色体验、记忆功能和疼痛感觉等感受状态;但像意愿、信仰、主张、权衡过程等精神现象却无法客观化,无法还原为大脑物质元素中点对点式的对应物。我们今天所具备的神经科学知识与测量手段提供不了这样的精神状态与神经网结之间的关联。尽管我们现在拥有了大脑扫描仪(即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出的一些决定是很难借助于这一仪器来进行判断确定的。不同于肠胃只能这样消化、肺叶只能这样呼吸,我们的大脑却绝不是只能这样决断:我们可以权衡、犹豫、选择,更可以变更我们的决定。这些包括道德心理在内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并非是神经科学可以描绘分析的,也并非是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可以显示、测量和解读的。因此,连普林茨自己也承认:“生物学家可以解释大脑中的化学和物理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但至今没有人知道,自我-体验是如何发生的,大脑究竟是如何产发出意思的”。(Prinz,S.26)德国伦理学家赫弗(O.Hoeffe)引述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的说法:“大脑是依照何种规则工作的,它是如何通过使直接的感知与早期的体验相融合的方式描摹这个世界的,大脑是如何将其内在的活动感知为‘其’活动的,它是如何规划其未来的行为的,我们对所有这一切的认识还都没有开始。再者,人们如何借助当下的手段来研究这些,这一点根本还不清楚。就此而言,我们似乎仍然处在狩猎和采集的水平上。”(Hoeffe,S.261)
有人会说,某些神经科学家试图将包括意愿、权衡、信仰、决断等在内的所有精神活动均还原为神经过程(即所谓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强的决定论)的努力,在现有的科学知识与实验条件下固然无法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技术手段的改进,这一努力将来也不可能成功。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便是在时代进步、科研条件改善的未来,强的决定论者仍然难以逾越如下理论障碍:
第一,精神活动依赖于生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但并不等同于这一物质基础。没有人否认所有的精神活动均要通过大脑的神经过程才得以实现:意识离不开其物质条件,脱离不了与自然界的关联。但“某物离开某物就不可能发生,并不意味着两者是一回事”。(Wingert,S.202)像自主决定、道德选择、宗教信仰等精神活动,并非完全因果性地取决于大脑状态,而是有着独特的活动机制,它们可以自由地做出处置,不受自然界的确定与安排。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主观上可以体验得到的“自我”的作用,而这个所谓的“自我”就是对一切意识活动进行控制与协调的主管。一个人在其漫长的生涯中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智上都会经历无数的变化,但正是由于其“自我”的存在,他总是能够保持自身心理的同一性、个体的连续性以及自始至终同为一人(即整体的人)的现实感。这个能够有意识地决断的“自我”之存在固然离不开大脑,但绝不等同于大脑,甚至在大脑中通过神经生理学的方法也找不到对应物。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并非是心灵在发怒、在受压抑或在思考,也不是心灵在编织、在建造房屋,而是人借助于其心灵在做这些事情。(cf.Buchheim,S.161)这表明亚里士多德早就清楚地将自我(人)与大脑(心灵)区分开来了,早就意识到了人的主观世界的维度,意识到了“并非是‘大脑做决定’,而是个体、行为者‘做决定’,无论如何是作为整体的人‘做决定’。我们也不会讲,大脑现在在喝啤酒或在写一本书”。(Klein,S.334)
而将所有精神活动均还原为神经过程的强的决定论,则恰恰是完全取消了人的这个“自我”的主观维度,只承认大脑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不是人之“自我”在做决定,而是大脑在做决定,这样也就将“谁-问题”(问:谁在行动?答:我在散步,我在准备跳远)置换成了纯粹的“什么-问题”(问:发生了什么?答:我身体上出现了散步的动作,我这里出现了跳远的准备)。罗特就直截了当地说:“在我看来,‘不是我而是大脑做了决定’这句话是正确的”。(转引自ibid,S.333)也就是说,自主决定并非来自于一个整体的人的自我,而是人的大脑中无意识的、并且同时是充分的因果因素做出了决定。
这一观念给我们通常理解的人的图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一图景表明,人是由其自我意识支配的,他拥有自由意志并且对其自由的行动后果承担责任。但假如按照强的决定论的立场,决定不是来自于自我,而是来自于大脑,那么我们就不能惩罚罪犯本人,而只能追究其大脑的责任。而这样又会给人类社会现有的司法制度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个体的人若是无自由的,就没有犯罪能力及责任;而没有罪责,也就没有司法。穷凶极恶的杀手便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因为他会说自己并不是行为的决策和启动者,其行为不是由他的自主的意愿,而是由他的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过程启动的,而这一物理化学性的神经活动又取决于外部物质世界的因果关系,故自己对行为后果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辛格就说:“谁都无法成为不同于他所是的东西。这一洞见可以导致一种对这些人更加人性化、更少歧视性的评价:这些人遇到这样倒霉的事,即他们带着一种器官长大,该器官的功能设计者不允许他们可以有合宜的行为。把带有问题的行为设置的人评价为是坏的或恶的,这只不过意味着是在评价这种构成了我们本质的器官之命运所决定的发展结果”。(转引自Klein,S.335)于是,现有的奠定在人的自由行为与相应的责任担当之基础上的刑法体系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强的决定论者设想“建立另一种法律体系,比如说不是奠立于罪责与责任的原则,而是奠立于这样的原则,即当事人对其伤害他人的行为必须赔偿,但无需归罪于当事人的自由和犯罪能力”。(Prinz,S.26)也就是说,侵害者应当做出补偿,但无需道歉。任何通过批评、谴责和说服教育使肇事者产生反思反省、幡然悔过之心理,从而做出痛改前非之举动的努力,均失去了意义,因为所有发生的一切均是自然界设定安排好了的,在客观世界的历史必然性面前,人难以逃脱这种无可奈何的命运。但是,强的决定论的这套谬说,不仅与既有的社会矫正理论与实践成果不符,而且也与人类社会在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反省和总结中逐步成熟、从而走向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相悖。
第二,行为的原因不同于行为的理由。如前所述,人分为自然存在的层面与精神存在的层面。就自然存在而言,人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从属于自然界的因果链条;这种因果必然性支配着人体中的生化反应、神经表现、基因配置与生理活动。人的生理活动难以逃脱因果必然规律的制约。我们身体中出现的任何生理现象都有其相应的原因,这一原因一定会导致包括该现象在内的相应的结果。像呼吸、咳嗽、流汗、做梦、打喷嚏等生理活动,均受控于自然因果必然性,我们可以暂时屏住呼吸,但无法长久。
然而,作为精神存在的人,我们却又不完全受因果必然链条的制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权衡、犹豫以及在两种行为选项上的抉择。人之所以能够因理性之故而超拔于自然界,就在于人是自身决断的作者。而这种开放性的决断并非取决于因果先定的大脑活动。“决定是常常延展的过程,带有许多的反馈和权衡回路,这些反馈与回路以这种形式是根本无法精确地在时间上予以限定的”。(Klein,S.344)换言之,决断是“自发的,不受外在强权或内在强制的影响”。(cf.Schweppenhaeuser,S.63-64)尽管决断在大脑中拥有其活动的物质性条件,但其本身却并非是依因果关系从这些条件中导引出来的,“并非是时空中为自然因果联系所支配的……原则上为神经心理学所无法解释”。(Zunke,S.210)自然科学无法提供经验性的解释,并不是我们否认自主的决断之客观存在的理由,况且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思索、权衡、犹豫、抉择的场景,时时刻刻都在证明人类拥有意志上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未决性: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改变预先的欲求,体验自身的自由。洛克为此做了一个精彩的总结:“我们拥有中断追逐这种或那种愿望的能力,就像每个人每天在自身所能验证的那样。在我看来,这里就存在着所有自由的源泉,这里就有……人们称为自由的意志的东西”。(转引自Beckermann,S.298)
人们在权衡中既可以这样决定,也可以那样选择,这表明人有意志自由,能自主决断,不受自然界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不取决于经验上可观察到的原因。那么人的自主决断又是基于什么而触发的呢?答案是:基于其意图性的结构;换言之,人在权衡与决断之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不同的、互相竞争着的理由,所谓决定就意味着对不同理由的思考和选择,人的自主行为便是出于某种理由的行动,是对理由的权衡与认可的结果。瑞逵(B.Recki)指出:“一种行动作为某种目的的实现是复杂的慎思序列的结果,该慎思要回溯到理由的原则性和情景性的信服力。”(Recki,S.45)哈贝马斯也认为:“一般而言,我所理解的意志自由是意志的基于澄明了的理由的自我约束的方式。意志自由表征着一种存在方式,即行动着的人在理由的空间里存在的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为文化上所传承下来的并且是社会组织化了的理由所刺激的方式”。(Habermas,2007a,S.270)在这里,哈贝马斯清楚地揭示出了意志自由与理由的关系,即自由属于理由的王国,意志自由只存在于能够对理由进行思考、判定、权衡与抉择的人之中。“意志自由就在于在某种行动面前停顿并且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做以及这样做或那样做的理由的能力”。(Beckermann,S.298)换言之,一种决断只有在经过行为者的权衡,通过对理由的考量的前提下,才是自由的。“一种决断若是基于一种向理由开放的过程,便是自由的”。(ibid,S.99)
那么,理由是怎样不同于原因的呢?柏拉图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说明。以苏格拉底为何不逃出监狱这一问题为例,有两种可能的回答。第一种是:因为他的胫腱、腿骨无法运动——这就是原因。第二种是:因为他要遵循国家的法律——这就是理由。由此可见,原因反映了人的身体状况,是经验科学的研究内容。而理由则“并非是可观察到的依照自然规律变化的物理上的标志……不受严格的因果解释的制约”。(Habermas,2007b,S.109)理由不同于可回溯为神经活动的过程:“理据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神经状态,而是理智性的论据”。(cf.Hoeffe,S.261)原因只是对物理世界客观状态的反映与呈现,故并无对错之分,只有真假之别。而理由则关涉到人的行为的复杂的规范维度:正确的理由意味着应当的行为,错误的理由则造成行为的失当与有害。凯泽(G.Kaiser)指出:“没有意愿就没有应当,没有根据理由的判断和行动——而不是仅仅根据原因——就没有正确和错误”。(Kaiser,S.266)
可见,原因无对错之分,理由却有对错之分;原因是自然性的,理由则是人际间社会性的。“行为理由……来自于个体的生活体验以及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交往”。(Habermas,转引自Roth,2006a,S.19)原因从属于自然界的必然性,理由则起源于人际交往社会关联的运行规则和对文化历史经验累积的反思与醒悟。原因通过科学来解释与克服,理由则依靠启蒙、学习和教育得到改善。人既有自然性亦有社会性: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与人之间在身体构造上并无本质性的差异,但作为社会中的存在,人由于个性、体验、教育、环境、生活史的不同而各显区别。
也就是说,在原因的世界,我们因从属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彼此相似;但在理由的世界,我们则因意志自由而大不相同。
回到李贝特实验。我们知道,意志自由与理由相关,关涉到出于理由的行动。李贝特实验与意志自由相关的场景或许在于,询问受试者是否乐意参与这项实验并按指令进行动作,让受试者在对不同理由的权衡中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此时,实验者要马上在受试者的权衡过程中对其神经生理活动进行观察,这才是涉及出于理由的决断过程的研究,即意志自由的研究。而手指按压电钮的动作并不是涉及理由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原本的李贝特实验与意志自由是否存在的问题没有关系,它不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关于意志自由的实验。
总而言之,包括意愿、权衡、信仰、决断在内的体现了人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活动有着复杂的特性,无法简单还原为神经过程,故神经过程决定论及生物主义的还原论经不起实践的验证。同时,我们日常的生活体验又清楚地证明了人的意志自由、人的自主决断之客观真实的存在,清楚地揭示了其不受自然界因果必然性的支配的特性。“谁要是对未来行为进行权衡,在康德看来便根本不能不把自己想成是不自由的”。(Thiele,S.39)这种情况充分展示了人的存在的复杂性,或者让我们想到了康德二元论式的解释,即人是两重性的存在:作为肉体性的自然存在,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人当然服从于机械的自然因果必然性的统治;作为纯理智性生物的精神存在,人却是其行为的绝对主体,是受理性引导的自由的行为者。“当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时,我们就不能相信逃脱了自然必然性的幽灵或神话。但当我们想把人理解和判断为个人,把其活动理解和判断为决断和行为之时,我们就必须把自由作为前提条件”。(Fischer,S.46)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人作为自然存在加以考察之时,我们体验不到自由,因为自然界受因果必然性的统治。自然世界所有发生的事物均处于一种因果必然性的链条之中。但当我们把人作为精神存在加以认知之时,我们就必须承认自由的真实存在。有关意志自由之存在的认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或者说人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一个是必然性统治的自然界,在这里人是不自由的,用康德的话说,自由在现象世界无法得到证明;另一个是自由支配的超越时空的精神世界,人作为精神存在是自由的,因为人的理性构成了一种能够自发开始行动的理念。在精神世界里,自由成为一种我们无法避免的意识内容,自由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与自己的自然性保持距离。在康德看来,两个世界的存在都不可否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可以得到人的验证,人的意志自由则可以得到人的假定,这样两者并行不悖、相安无事,仅有区别,而无冲突。“两种立场——自然法则的和自由法则的,在康德看来均是补充性的扩展物,两者均合乎人的本性”。(Thiele,S.39)这就是康德所代表的必然世界与自由世界的二元论的立场。
如前所述,神经过程决定论及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均试图超越这种二元论的立场,但它们的努力都难以成功。像罗特这样的脑科学家认定,人的行为一方面取决于认知上的权衡,另一方面更取决于某种情感机制,这些情感机制是由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活动构成的。对于人的复杂的行动,认知上的权衡只是提出建议,但最终做出决定的则是所谓“情感体验记忆”:“有关我们期望、意愿和行动的决断中的最重要的主管,是情感体验记忆。……这种记忆在其发展中始于怀孕的前几周,最高阶段则是出生后的前几个月”。(Roth,2006b,S.37-38)罗特甚至说:“在愿望和意图的产生上,无意识地工作的情感体验记忆起开启和最后的作用。它开启了我们愿望和意图的产生,它在决定是否将我们希望的东西此时此地、这样而非那样地付诸实施上起最后的作用。这种最后决断的出现同我们对该决断的意识和拥有付诸行动的意志相较早了两秒钟”。(ibid,2006a,S.13)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过去了的体验的光影下发生的”。(ibid,S.14)因而我们的行为最终并非是受理性指导,“并非认知上的权衡对于一种行为改变是最终决定性的,而是‘行动者的一种最大可能的稳定的和自身无矛盾的情感状态的维持’(起决定作用)”。(G.Roth,转引自Thorhauer,S.68)
这种轻理智抉择、重情感体验的立场,也得到了当代德性论的支持。努斯鲍姆(M.Nussbaum)就认为:“理智缺乏情感在价值上便是盲目的,对于理智而言缺乏人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方面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内居于情感之中的判断里”。(M.Nussbaum,转引自ibid,S.75)
然而,情感在价值判断上真的超越了理智吗?从对著名的电车难题的大脑实验研究中,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当问到你是否同意搬动道岔,从而使一辆飞驰的有轨电车转而冲向另一轨道上的一人,以避免在不搬动道岔的情况下电车沿既定轨道径直冲向前面的五人之时,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大部分都同意搬动道岔,让一人承担死亡风险而使另五人得救;在问及此道德两难之时,支持者的大脑反应微弱。实验表明从情感上看,大部分人认同用一命去救五命。然而,这一情感决断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因为理智告诉我们人命都是一次性的、无价的、不可逆的,个体的生命价值具有终极性,在人命之间没有可比性。故这里不可能出现五条人命相加之价值大于一条人命的结论。这就决定了不能为了营救五人之命而让一人之命牺牲,这一理智的决断所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最高尊重。这种已上升为许多国家法律规定的理性的生命原则,是人们思考、权衡包括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省的产物,并且完全超越了从所谓人类原初的情感机制中产生的心理反应。这一著名的例证清楚地说明,“人在其感受、思想和行动中并不完全是由其生物本性包括其大脑的活动过程所规定的,他的主观性和意向性(行动出于理由而非仅仅出于原因)以及他的社会性超越了他的生物本性。‘人不仅仅是其本性和其大脑功能’”。(转引自Roth,2006a,S.9)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固然不应当主张所谓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论(即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任何物质基础的精神世界),但却难以取消所谓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二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