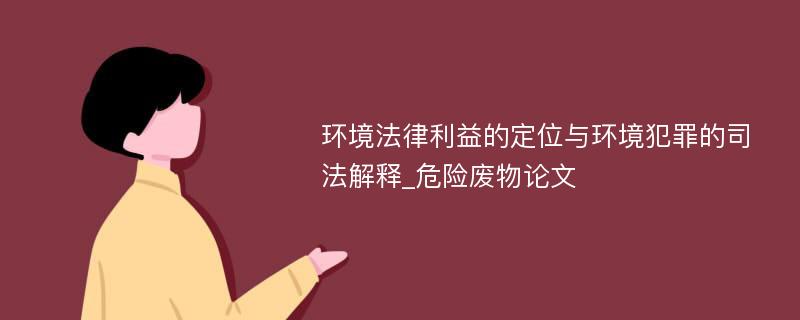
环境法益与环境犯罪司法解释之应然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解释论文,立场论文,环境论文,环境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8-0096-10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典“污染型”环境犯罪的核心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出重要修正,以“严重污染环境”取代“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损失”,原罪名也随之被调整为“污染环境罪”。修正案降低了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申明了“环境”所具有的独立价值,成为中国环境刑法立法观念转型的起点。为准确适用新罪名,2013年6月8日“两高”颁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污染”、“环境”与“严重”做出解释,其中,第1条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标准、第3条规定了加重情节的11种情形、第4条规定了酌定从重处罚的4种情节、第6与第7条规定了加大单位环境犯罪与环境共同犯罪打击力度的原则,体现出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的政策立场。据不完全统计,《解释》出台以来,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超过近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办247起此类案件,相当于过去10年立案总量,目前已移送检察机关起诉145起①。《解释》的出台,成为强化环境刑事司法功能的重要举措。加之,《解释》第5条关于“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和积极赔偿损失”可从宽处理的规定,明确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导向。然而,《解释》在力求强化环境犯罪刑法治理机制的前提下,囿于对环境法益理解与独立性认识上所存在的偏差,暴露出在基本立场上难以与立法改革方向吻合的问题,需要展开批判性反思。 一、环境犯罪司法解释之正当性分析 司法解释是对立法语义的充分说明,司法解释的目标是为了阐明刑法的立法原意,应当遵循合目的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之原则②。全面审视《解释》各项规定的内容,不难发现,《解释》中存在诸多需要正视的问题。 (一)违背合目的性原则之条款 尊重并贯彻立法原意,进行合乎立法目的的解释是司法解释之圭臬。在立法原意探寻中,立法修正过程的“回归性”分析至关重要。中国97年刑法典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因在犯罪成立条件上,固守以传统的人身、财产法益遭受严重侵害作为犯罪成立之条件,导致司法适用面过窄,大量的严重污染环境行为难诉其咎。有数据统计,2004年全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1起、2006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有3起、2008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5起、2009年仅有2起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③,但上述年度同期全国环境污染事故的数量分别为1441、842、474、418件④,显然,绝大部分污染事故是通过行政处罚途径结案的。而2007-2011年每年全国环境污染突发事故维持在418~542件之间,平均每天1~2件,行政处罚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已相当严峻。根据国际环境刑法发展趋势,调整环境刑法立法导向,提高犯罪规制能力,成为完善环境刑事治理之要略。为此,《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罪做出立法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6年解释》)的基础上,增设7种严重污染环境的新类型,下调部分情形下严重污染的判断标准,被誉为是入罪标准的降低⑤。然而,《解释》中部分条款与立法修正本意的貌合神离,极易导致立法目标难以达至的结果。具体包括: 1.限制环境要素保护范围之条款 《解释》第1条第1项将在饮用水的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污染行为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其意图在于加强对重点区域的保护,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限制性解释是否必要? 修正后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的对象是“环境”,即,由水、大气、岩石、生物、阳光和土壤等不同要素组成生态空间,可概括归类为生存型环境要素与资源型环境要素两类:前者是指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水、空气和土地要素,后者是指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矿产、林木、动植物等要素。由于后者已多数被规定于其他罪名中,因而污染环境罪中的“环境”应主要指生存环境,即水体、空气及土地要素。因立法对“严重污染环境”未作具体环境要素的区分,故可推定立法对各环境要素及其具体形态持充分保护的观点。 《解释》第1条第1项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饮用水水体环境的保护;二是针对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环境的保护。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般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还可增设准保护区。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二级保护区的长度是从一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向上游(包括汇入的上游支流)延伸不得小于2000米,下游侧外边界距一级保护区边界不得小于200米。换言之,二级保护区属于一级保护区的外延范围。水体的流动性、水系支脉的关联性,使得对饮用水二级保护区或准保护区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同样也会严重侵害一级保护区的水体环境。为调节、改善水源流量和水质,国家还在河川上游的水源地区设置了水质影响区、水源涵养区,这些区域内的严重污染,不仅破坏了本区域对下游水质的保护功能,也会加剧下游污染。即使污染的是非饮用水区域,由于水体的流动性,也会恶化其关联水系,进而最终损害人类利益。同款关于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也存在类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缓冲区在核心区之外,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外围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缓冲区或实验区因为有人的活动,理应比核心区更易产生环境污染侵害,但却未被《解释》所涵盖。 值得推敲的是,对于在饮用水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核心区之外实施的污染行为,是否适用《解释》第1条第2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规定?尽管第2项与第1项行为方式相同,但其犯罪对象是“危险废物”,对象范围小于第1项“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规定,并且在量上还有吨数限制,仅适用于符合其条件的非饮用水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非核心区的污染行为。因此,《解释》对于非饮用水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非核心区的环境保护仍基本处于“真空”地带,其关于重点区域的特殊规定,实质是变相限缩了犯罪规制的范围,与立法修正之初衷相逆,属不必要之规定。 2.设置不当前置保护条件之条款 《解释》第1条第5项效仿逃税罪及非法经营罪司法解释之规定,增加了“两年内曾违反国家规定……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行为人实施的均为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即“又实施前列行为”中的“行为”不能是犯罪行为,否则该解释规定根本无必要。对于累次实施污染环境的行政不法行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大,秩序罚已丧失有效性,进而有必要通过刑法加以调整。但是,对于两年之内以及跨越两年受到两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污染行为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并无实质差别,以“两年”作为时间限制,无端制造出司法适用的阻却屏障,降低了司法适用效果,不符合立法修正之本意。 3.与环境保护无关之条款 《解释》第1条第6项、第10项新增两种“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一是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12小时以上的;二是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这一规定源自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突发环境事件预案》中关于环境污染事件(Ⅰ级、Ⅱ级)的规定。然而,制定《突发环境事故预案》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关于涉及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变能力,为及时稳定社会秩序提供应对方案,而非如何治理环境污染或保护环境。取水中断的时间、疏散群众的人数,只是环境受到侵害后对当地经济、社会活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评价标准,而非环境受侵害程度的评价标准,将其作为严重污染环境的评价依据,理由不足,不符合合目的性的解释基本原则。 (二)违背合理性原则之条款 司法解释的合理性是指刑法的解释要合乎法理、人伦常理和社会发展需要之理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司法解释的合理性至少应当考虑环境要素的特殊性、社会一般规律性认识、法益侵害的加重程度,以及条文间的逻辑关系。就此而言,《解释》的以下内容存在合理性方面的欠缺。 1.混同环境要素之条款 虽然环境是一个综合体,各种环境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但不同环境要素在污染传播方式、污染后治理难易程度以及保护紧迫性等方面仍存在区别。如,水体、空气流动性强,受污染后危害极易在短期内传播,而土地污染的结果则具有潜伏性;水体还存在内水与海水的差别,海洋作为一种独立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同于其他水体的属性和特点;土地类型中的耕地与人类生存具有最密切联系;还有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性地带而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湿地遭破坏的原因,既有直接的环境污染,也有围海、围湖造田、河流改道等人类“合理”经济活动。因此,《解释》应当针对不同环境要素及其特点在解释对象范围上予以区分。然而,《解释》除第1条第1、7、8项分别针对特定保护区、特殊土地和森林有专门规定外,其他条款对不同环境要素则不作区分,亦未设置不同评价标准。即使在有专门规定的情形下,也存在对不同环境要素适用同一行为标准的问题。《解释》第1条第1项将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与自然生态保护核心区并列规定,但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珍贵和濒危动、植物以及各种典型的或特殊的生态系统,与水源保护区不具有同一性;《解释》第1条第7项对土地类型进行了区分,但以基本农田取代耕地概念,前者来自于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是满足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必须确保的耕地最低需求量,属于耕地的下位概念,而目前耕地污染却是最为严重的⑦;《解释》第1条第8项将森林与其他林木并列规定,但森林是独立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除了林木之外,还包括林中和林下植物、野生动物、土壤微生物及其他自然环境因子等,与一般的林木也非并列关系。 2.已定标准缺乏充分依据之条款 《解释》第1条第2、3项规定了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和污染物超标排放三倍的认定标准。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危险废物包括固体废物和液态废物,不包括废气,因此,第1条第2项指的是向水体和土地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而第3项指的是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情形。然而,《解释》根据何种理由将标准限定为三吨与三倍?第2、3项的规定属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作为抽象危险推定的基本标准,应符合公众对危险的一般认识或参考前置法的规定,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前置法中未提出危险废物或污染物的重量与超标倍数标准或其他标准。由此可能出现行为人仅处置2吨危险废物,已对环境构成实质侵害,却因不符合《解释》规定之重量标准或其他条款之要求而不构成犯罪的问题。尽管以重量和超标比例作为判断标准,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却忽视了环境犯罪及环境法益的最核心特质,存在求末舍本之弊。 3.法益侵害关系混乱之条款 人与自然之间利益休戚相关,人本身即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较之侵害生物类群或自然资源的犯罪,污染环境犯罪对人的侵害更为直接。故而,个人法益也是环境犯罪的侵害对象。无论是首倡环境法益概念的德国,还是对环境犯罪采取重刑治理政策的美国,都将个人法益规定为污染环境犯罪的选择要素。然而,从法益侵害的逻辑关系来看,仍应首先是环境法益受到侵害,其次才是个人法益。换言之,个人法益是环境法益受侵害后的加重结果,或者至少是环境法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也会产生个人法益侵害的危险,而个人法益的实际损害则应是其加重构成。然而,这样的法益侵害关系在《解释》中却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解释》第1条第11~13项,以及第9项将人身、财产法益侵害后果作为“严重污染环境”的评价标准。姑且不论财产法益与人身法益是否可以等而视之,就人身法益本身而言,将人身健康的实害结果作为评价“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实际是将环境法益与其侵害的加重结果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评价,不符合法益侵害的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一致原则,难以符合合理性原则的要求。 同时,这样的规定也造成《解释》第3条“后果特别严重”成为受害人数的简单分配与累加,极有可能出现个人法益侵害加重下的空档区。假若在一起污染事故中,导致34人中毒的结果,且其中仅3人轻伤、1人重伤,此时,就同时符合了第1条第11项(致使30人以上中毒)、第12项(致使3人以上轻伤)、第13项(致使1人以上重伤)之要求,同时存在三项并列的人身法益侵害结果,此时法益侵害已明显加重,但却因无法达到第3条第6项(100人以上中毒)、第7项(10人以上轻伤)、第8项(3人以上重伤)所规定的加重人数,而只能适用基本犯之规定。此外,从规范的形式来看,《解释》第3条第9项原本意在将第1条第12项之“致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以及第13项之“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合并为一项加重情节,即表明在同时具备致人轻伤与重伤时,存在加重的法益侵害,应当适用更高的法定刑,但第3条第9项却无端提高了轻伤人数,由3人升至5人以上,人为制造出在1人重伤且3~4人轻伤的加重法益侵害情形下仍适用基本犯法定刑的空档区。 4.对象范围不统一之条款 《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及“后果特别严重”均给予了充分的细化说明,但过度细化也导致其难以顾及条文之间的关系、对象范围不统一的问题。《解释》第1条第1项、第4项、第5项规定的犯罪对象为“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和有毒物质”,第10条将“有毒物质”范围解释为包括危险废物在内的可能污染环境的有毒物质。但是,第1条第2项的犯罪对象仅为“危险废物”。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章之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具有各种毒性(如急性毒性、慢性毒性、生态毒性等)、爆炸性、腐蚀性、传染性、反应性等危险特性的废物。显然,第1条第2项的犯罪对象范围要小于第1条第1项等其他条款。基于这样的差异规定,在第1条第1项等规定之外,排放、倾倒、处置放射性废物、未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尚无相关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的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和有毒物质3吨以上的,不属于严重污染环境,不构成污染环境罪,但是,这样的结论无法让人接受。 (三)违背合法性原则之条款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首先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解释不能超出词语最大的语义射程范围且应具有明确性;其次要尊重刑法的谦抑属性,充分考虑与前置法之间的衔接关系。《解释》中以下条款存在有违解释合法性原则的问题。 1.模糊性条款 《解释》第6条规定了单位实施污染环境罪时,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适用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表明了从严打击单位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立场。然而,遗憾的是,《解释》没有能进一步对单位罚金的具体数额、适用比例、裁量依据等做出具体的规定或说明,使得单位罚金仍处于无限额、无基准、无依据的状态,欠缺解释的明确性。 2.重合性条款 根据犯罪定性与定量的要求,污染环境罪属于“行政加重犯”,即以“行政违反+加重要素”为构造的犯罪⑧。一方面,污染环境罪所规制的行为本身具有行政不法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又具有区别于普通行为不法的加重要素,如特殊情节、特定后果以及罪过要求。在基本行为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加重要素,形成了行政规制与刑事规制的衔接体系,从而确保了刑罚处罚的必要性。然而,《解释》第1条第4项忽视了与前置法规之间的衔接性,“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之规定与《水污染防治法》第76条第7项“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或者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之规定,基本重合,根本无法从行为实施程度的角度作出归属于行政不法抑或刑事犯罪的判断,属与前置法重合的规定。 二、环境犯罪司法解释应然立场 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境”之立法修正,使“环境”本身成为了犯罪的对象,标志着“环境法益”由此成为了中国环境刑法立法的基石。然而,《解释》并未能把握这一立法修正实质的核心变化,其重点仅在于形式层面的降低入罪门槛、扩大规制范围,由此在高举加强环境保护旗帜的形式下混淆了环境法益与其他法益之关系,进而采取了简单以《2006年解释》为基础的“拼接型”解释模式,解释内容缺乏协调性、层次性,模糊了立法对环境法益的独立诉求,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环境法益之发展与体现 从世界范围环境刑法立法发展趋势看,保护环境法益已经成为环境刑法立法修正的主要目的。德国被誉为是世界上处罚环境犯罪最为严厉,及刑罚权范围最广的国家之一⑨。以德国为代表,环境刑法立法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环境刑法缺位阶段。1871年德国刑法典虽然将虐待动物、公共危险投毒、破坏安宁噪音的个别侵害环境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绝大多数环境侵害行为仍通过行政程序处理。即使有个别严重污染环境行为进入刑事程序,也按照传统犯罪处理。在1950年代部分法院还采用传统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环境污染行为,如将因水污染造成鱼类死亡解释为刑法303条毁损财物罪⑩。(2)以个人法益保护为导向的刑法立法阶段。进入1960年代后,德国在大量附属刑法中规定了环境犯罪,但认为环境刑法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本体利益,“如果人的本体利益没有受到侵害或威胁,则无刑事制裁可言。”(11)在1971年的刑法修改建议稿中,仍认为“环境保护”的概念应限于“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免受环境的危害”(12)。(3)以环境法益保护为导向的刑法立法阶段。1979年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刑法会议,确立了以刑法典集中保护环境法益的立法改革方向。德国于1980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第二十八章“环境污染犯罪”,将原来的环境附属刑法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同时强调立法目的不在于整合,而系以全新观念,重新思考环境刑法之犯罪构成要件(13),其中第324条污染水域罪完全摆脱了对个人法益的依赖,将对“水体品质作不利改变的”直接规定为犯罪行为,表明了立法对环境法益独立性的正式承认。1994年“打击环境犯罪的第二部法律”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法益保护的范围、提高了刑罚幅度,并设置了侵害环境要素的危险犯类型,表明环境法益的刑法立法保护体系逐步成型。 在国际层面,加强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也为国际协议所积极倡导。1991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将故意严重危害环境罪规定为国际犯罪。1994年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危害环境罪的决议,其第2条第4款“危害环境罪的最低限度行为要件”中规定:(1)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作为或不作为;(2)违反已规定的环境标准而对环境造成现实的和紧迫的具体危险。1997年欧洲理事会《通过刑法保护环境公约》,强调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且必要的措施在其国内立法中将所列的故意、过失导致任何人或空气、土壤、水、动植物的实质损害行为规定为犯罪。2003年欧盟部长理事会《关于通过刑法保护环境的框架决议》将对环境要素的侵害作为环境犯罪构成的最低标准。2007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通过刑法保护环境”新议案(2007/0022(COD)),对环境犯罪进行了明确界定,即故意或过失对人体健康或环境造成了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违法行为,再次清晰地表明环境法益已经成为与个人法益并列的环境犯罪侵害对象。 (二)《解释》的法益定位及其问题 国际与国外环境刑法立法实践可以看出,承认环境要素的独立保护价值,加强对环境要素的保护力度,已然是环境刑法立法发展的基本趋势,环境要素是环境法益的载体,环境要素的独立化即表明环境法益的独立化。然而,环境法益的独立化并非绝对概念,脱离了人类利益看待环境法益将毫无意义,强调环境法益的最终目的仍是保护人类利益,但这种人类利益是一种未来的、预期的利益,就现实保护而言,只能转换为与其密切联系的既存的整体环境。换言之,环境法益是人类的未来利益以及未来人类的利益,是刑法保护预期法益的特殊形式。这也赋予了环境刑法强烈的预防品质,形成了对“可能”造成环境损害行为积极干预的危险犯立法模式。然而,《解释》未能捕捉到环境刑法立法发展趋势转型中法益特征的变化,仍固守较为落后、陈旧的以个人法益或社会管理秩序作为环境刑法保护对象的基本定位。 从内容来看,《解释》较少涉及具体的环境要素。《解释》第1条规定的14种基本情节中,仅第1、7、8项涉及具体环境要素,分别是保护区、土地和林木;第3条规定的11种加重情节中,仅第2、3项涉及具体环境要素,分别是土地和林木;第4条规定的酌定从重情节中,无一项涉及环境要素。既然环境要素是环境法益的直接体现,司法解释就应针对“严重污染环境”中的“环境”进行具体说明。刑法典原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原本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处置的规定。有观点认为这样可能导致部分环境违法行为无法追究,修正案删除这一限制将使得338条的适用范围更宽(14)。然而,立法删除对象要素并不代表司法无需再进行解释。事实上,正是由于环境要素数量较多,且具有不同特质,保护手段也应有所差异,所以才无法在立法中加以列举性规定,立法删除的结果,更加强化了司法对环境要素进行具体解释的必要性。 从整体结构上看,《解释》是对《2006年解释》的全面继承,本质上仍然是加强个人法益保护的更新翻版。针对原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06年解释》对人身、财产法益侵害后果进行了具体解释,根本不涉及环境法益。较之《2006年解释》,《解释》第1条规定的14种基本情节中,仅有第1~5项是完全新增规定,其他规定均是来自于《2006年解释》,包括直接沿用的(第7~9项)以及降低原有标准后使用的(第6项和第10~13项)。《解释》第3条规定的11种加重情节,更是全部来自于《2006年解释》的第2~3条。《解释》第1、3条构成了该解释的主要内容,完全新增之规定仅有5项,仅占第1、3条全部规定的20%,因而,《解释》仍是重在保护个人法益。 从新增条款的功能来看,单纯强调对环境管理秩序的维护,仍然缺乏对环境法益的独立诉求。《解释》第1条规定的1~5种情形,仅第1项规定了对保护区的专门保护,而其他项中则无保护环境要素之特征,相反却具有强烈的秩序不法特点,如规定了超标排放标准、两年内两次行政处罚后的再违法。《解释》第3条酌定从重情节中秩序不法的特点更为明显,如规定了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拆除污染防治设施、在限期整改期间的污染行为等。尽管环境犯罪被规定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解释》以维护环境管理秩序为依据并无体系解释上的不妥,但是,环境管理制度仅是环境犯罪的外部社会关系,不具有环境法益的本质特征,环境法益只能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得到反映,即使是合乎行政管理秩序的活动,也存在侵害环境法益的可能性,因而,需要在认识层面突破传统环境刑法的狭隘理解,提倡独立的环境刑法法益观。 由于《解释》定位于保护个人法益及社会管理秩序,必然造成解释内容向这两个方面的倾斜与偏移,背离了保护环境法益之立法目的,由此产生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之诸多问题。如,基于对个人法益之过度重视,导致不区分法益侵害逻辑顺序,不考虑不同环境要素的差别;基于对管理秩序的强烈偏好,导致与前置法之间的界限模糊,出现重合性条款、与环境法益保护无关之条款以及不当限制打击范围的条款。不仅如此,以保护个人法益及社会管理秩序为出发点,还会导致对犯罪模式的认识走入两个极端:一是从个人法益的角度,直接以实害结果作为犯罪既遂条件,造成刑法介入依然滞后,风险预防功能难以发挥;二是从社会管理秩序的角度,直接将严重的行政不法行为犯罪化,却忽视了作为行为犯与实害犯中间地带的具体危险犯,进而导致符合具体危险犯条件的污染环境行为将转向处罚更为严厉的投放危险物质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实质相同的污染环境行为产生迥异的刑事处断结果,有损法律的公平性。 三、以环境法益为中心的司法解释更新 笔者认为,《解释》的进步之处在于,贯彻了严厉治理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扩大了规制范围,细化了相关评价标准,司法操作性更强。然而,因为这些变化并非建立在对环境法益全面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更多受到环境犯罪严打政策的影响,难以对环境犯罪真正发挥出长效治理功能,而对于污染环境罪中争议较大的罪过问题(15)、罚金幅度问题也未有具体涉及。因此,尽管《解释》在局部内容上不乏亮点,但立基存在偏差,背离了立法修正目的,与其进行修补,不如期待以新定解释加以替代。在重新解释时,应反思《解释》所存在的问题,兼顾其他未尽问题,全面考虑以下问题: (一)以环境法益的独立化为指导理念 环境犯罪规定在中国刑法典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表明立法者认为该类犯罪的法益为环境管理秩序,这也是目前理论界的通说观点(16)。基于环境的“公共利益”属性,由政府通过管理体系进行有序的利益分配是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但是,构建环境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在于保护环境法益,属于手段行为,违反环境保护管理秩序只是对环境侵害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从环境整体角度看,人类仅是自然环境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不管人类如何地重建了其生存环境,都仍然是生态系统中的栖息者”(17),环境的整体性与独立性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环境行政管理秩序调整的仅是立法者所希望的,而不是全部环境。“环境刑法不是只为了保障环境行政法,不是只关系着管理、分配与秩序问题,而是将人类自然生活空间里的种种生态形态,如水、空气、风景区以及动植物世界等,视为应予保护的法益”(18)。行政前置法的立法漏洞与规则缺失对于有效展开环境刑事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基于此,有观点提出,“应当将环境刑法从行政法的附属范围中提出,并将它放入主刑法之内,因为环境犯罪不单纯是违反秩序,而是与伤害、盗窃、欺诈一样可以非难”(19)。一些国家在污染环境犯罪的个别罪名中,已经取消以行政“违法性”作为成立犯罪之前提条件的要求,如,现行德国刑法典第29章“污染环境的犯罪”第330条a款直接规定“传播或泄放有毒或能产生毒性的物质,有导致他人死亡或重伤,或导致不特定多数人重伤之虞的,处……”;美国也在部分判例中表明,在没有违反许可或其他行政规则的情形下,也可能构成《清洁空气法》所规定的疏忽危险型或故意危险型犯罪(20)。显然,环境刑法已经走向了一条观念改革的更新之路,独立法益形态已经昭然若现。 《刑修(八)》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正已经为环境法益的独立化奠定了观念基础,新司法解释所要做的即是追寻这样的立法理念,紧密围绕环境法益展开合目的性解释:一是围绕环境要素进行解释,将解释的重点置于环境本身,而非行为方式手段。二是减少对环境要素的范围限制,避免出现《解释》中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要素的限制规定;三是合理协调环境法益与环境管理秩序的关系,防止出现重复性条款,减少作为前置条件的行政不法的限制要素;四是避免出现类似《解释》中与环境法益保护无直接关系的规定。 (二)合理选择污染行为的宽严尺度 “污染环境”的“环境”包括了多种环境要素,不同环境要素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其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也有所差异,应当予以合理区分。在区分时,应当考虑到环境要素本身是否具有系统性或特殊性,如对于综合生态系统的海洋、森林和湿地应当区别于普通水域、林木和一般土地,而在土地类型中,更应强调突出目前污染最为严重的耕地类型。据此,新司法解释应当根据对不同类型环境要素构成“污染”的具体情况,遵循刑法体系解释的基本原理,有针对性地选择解释“污染”行为的宽严尺度:对于流动性较强的空气、水体,应对“排放、倾倒、处置”的语义做最大限度地扩张解释,将凡是导致空气或水体质量严重改变的行为,均纳入“污染”的范畴;而对于相对固定的土地,则有必要重视扩张解释的适度性,包括污染行为,还应包括特定物的存储、利用、埋入、丢弃。在强调体系解释对“污染”行为内容与方式的扩张标准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司法解释结论表述中的遣词造语的问题,尽可能确保同一解释结论中语词内涵的一致性,以及不同前置法概念适用的统一性问题,避免出现《解释》中不同款项关于“危险废物”与“有毒物质”规定的不一致,以及以基本农田取代耕地概念的问题。 (三)明确犯罪故意的罪过形式 污染环境罪缺乏对罪过形态的直接表述,传统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21),但也有观点认为“本罪原本为过失犯罪,但经《刑修(八)》修改后,本罪的责任形式应为故意”(22)。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公布了四个典型案例作为环境犯罪的办案指引,其中三个是以过失犯罪按照旧罪处理,一个是故意犯罪按照投放危险物质罪论处(23)。这是否隐含着污染环境罪仍与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一样,均属过失犯罪?对于环境实害犯而言,或许多数情形下的罪过形态属过失,但是,对于环境危险犯而言,难以排除故意的可能性(24),而且刑法总则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既然污染环境罪无法从罪名与罪状的规定上判断出过失形态,那么司法解释就应当遵循刑法总则的要求,明确本罪的责任形态仅为故意,以避免更多的无谓争议。当然,这样会造成环境污染的过失犯罪转向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过失犯罪,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该问题已经超越了司法解释的能力范围,只能通过立法途径解决。 (四)构建具体危险犯的犯罪既遂模式 “严重污染环境”的立法规定对于犯罪既遂形态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而《解释》仅将犯罪既遂形态设置为行为犯和实害犯,缺乏具体危险犯的规定,贬损了环境刑法的犯罪预防功能,容易导致司法适用的不均衡。环境污染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非常严重,一旦结果发生,对于环境和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造成极大的破坏,应当将足以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因此,在新司法解释中,有必要将本罪的基本犯设置为具体危险犯,将“严重污染”解释为:“足以严重污染环境或导致人身健康、生命受到严重侵害危险的”。同时,在加重构成中,将加重结果具体规定为“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的或造成他人健康、生命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形。 (五)设置累进化的刑罚处罚模式 刑罚配置的累进化是指根据不同犯罪形态及法益侵害程度,配置轻重不同的刑罚,从而使得刑罚呈现出从轻至重的逐步攀升结构。刑罚配置累进化是环境犯罪治理的客观需要。当客观出现实际环境损害时或更重罪过类型时,由于法益侵害加重,预防性目标失去价值而被威慑性目标所替代,只有以增加刑罚量的方式,才能提高刑罚的威慑效果,从而进一步证明环境的价值。美欧等国环境刑法在区分法益侵害程度、罪过类型等因素基础上,设置了逐步攀升的刑罚体系,如对实害犯的处罚重于危险犯,对故意犯罪重于过失犯罪等,特别是美国还考虑到人身危险性因素,加大对环境累犯的处罚力度(25)。相比之下,《解释》的规定较为简陋,未能形成累进化的刑罚处罚模式,难以有效发挥刑罚的威慑与预防功能。基于此,新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刑罚适用的判断要素,形成具有累进惩罚特征的处罚模式。对此,应当权衡考虑到:一是区分主观罪过形式。在立法上能够区分故意与过失责任形态的前提下,对故意犯罪的处罚应重于过失犯罪。二是考虑法益侵害的危险程度对刑罚配置的影响。根据法益侵害及刑法干预的紧迫性要求,刑法介入的时间遵循从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实害犯的顺序,刑法介入时间越晚,表明法益侵害的风险或结果越大,刑罚的否定性评价程度也应当越高。若将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放在同一基本犯模式中,则应根据不同的既遂模式规定不同的裁量标准;若将本罪的基本犯规定为具体危险犯,则应区分环境法益危险与个人法益危险,设置不同的处罚标准。三是充分考虑到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因素。结合罪过形态,分别规定环境犯罪的累犯或再犯的处罚标准。 ①参见武卫政《环保公安合力打击污染犯罪 两部门发布意见》,《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日。 ②参见齐文远、周详《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③参见陈景清《恶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 考问中国环保法治体系》,《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9月10日。 ④参见环境保护部《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www.mep.gov.cn/zwgk/hjtj/qghjtjgb/,2013-01-04。 ⑤参见佚名《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降低》,《北京晚报》2013年6月18日。 ⑥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5年版,第88页。 ⑦参见佚名《媒体称我国1/6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资金超万亿》,《经济参考报》2013年6月17日;国土部《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约五千万亩》,http://news.sina.com.cn/c/2013-12-30/122729119030.shtml,2013-01-04。 ⑧参见张明楷《行政违反加重犯初探》,《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⑨⑩(13)参见郑昆山《论我国环境防治之道》,《东海法学研究》1995年第9期。 (11)参见许玉秀《环境刑法规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台湾地区1992年《环境刑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辑》,第616页。 (12)参见王世洲《德国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概念研究》,《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2期。 (14)参见王炜《刑法大幅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国环境报》2011年3月4日。 (15)对于本罪的罪过形式,学界有故意说与过失说之争,《解释》虽然没有明确涉及这一问题,但第7条关于“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超越经营许可范围”之共犯规定,或许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本罪属于故意犯罪。 (16)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版,第525页。 (17)参见雷毅《生态伦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18)(19)参见[德]叶瑟《环境保护 一个对刑法的挑战》,台湾地区1992年《环境刑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辑》。 (20)Cf United States v.Grace,504,F.3d 745(9th Cir.2007). (21)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版,第580页。 (2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995页;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第5版,第1389页。 (23)四个典型案例分别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盐城胡文标、丁月生投放危险物质案。张先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四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人民法院报》2013年6月19日第3版。 (24)事实上,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不同罪过类型是国外环境刑法的普遍模式。如,《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污染水域罪、第324条a款污染土地罪、第325条污染空气罪均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不同法定刑;美国《清洁水法》(U.S.C1319条第3款)和《清洁空气法》(U.S.C1391条)也有类似规定等。 (25)Susan F.Mandiberg,Michael G.Faure,"A Graduated Punishment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Crimes:Beyond Vind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34 Colum.J.Envtl.L.447,2009.p.454.标签:危险废物论文; 环境法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安全饮用水论文; 环境污染论文; 水污染防治法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