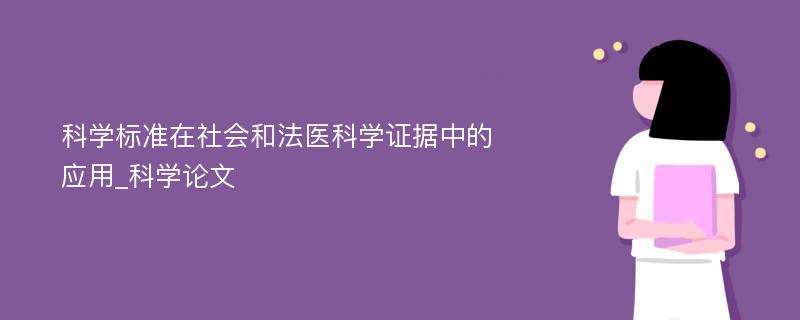
科学标准在社会和法庭科学证据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法庭论文,证据论文,标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26(2011)04-0487-05
科学的应用作为所有司法程序中争议事实之证明的一种方法,这一问题的出现(有人甚至会说是爆发)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并且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实际上科学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不过人们通常将这个问题视为仅仅与专家证人或者专家作为法庭顾问的实际使用有关,而并没有对以科学技术方法为手段取得的证据之质量和可靠性给予特别的关注。
如果谁要想为关于“科学证据”所表达的正确含义这个话题在现代乃至当前的发展确定一个出发点,那么他就可能应当参考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在1993年判决的Daubert v.Morrell Dow Pharm.,Inc.一案。布莱克蒙(Blackmun)法官在他的大多数意见中,试图将法官作为控制科学证据之采纳的守门人而去挑选证据的标准确定为“科学有效性”。抛开所谓的Frye规则(1923年确立)——根据该规则,一项证据,如果其使用的方法在相关科学领域获得了普遍的接受,那么它就是“科学的”——布莱克蒙写下了判断一项证据是否是“科学有效的”之条件:a)该理论或技术能够且已经得到检验;b)该理论或技术已经公开发表并得到同行认可;c)其实际或潜在的错误率是可知的;d)有控制该科学技术操作的标准;e)该科学技术在相关的科学领域内具有较高的接受程度。
布莱克蒙的观点受到了认识论观点的批判,因为给其带来灵感的波普尔认识论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值得怀疑的。此外,Daubert规则尽管已经适用于联邦法院,但却并没有被美国所有的州司法辖区所接受。另一方面,该学说在Kuhmo一案中也拓展适用至技术证据(而不仅仅是科学证据)。不仅如此,Daubert规则还在2000年使得《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根据修订后的规则,专家证人现在必须具备专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并且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他才能够作证:(1)证言基于充足的事实或数据,(2)证言是可靠原理和方法的产物,并且(3)证人将这些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的事实。因此很明显,《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条主要关注专家提供的证据的可靠性,强调了其必要性,强调了Daubert规则中“科学证据”必须具备实质上的“科学性”。
一些评论者说,无论如何,Daubert规则一直并且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其关注了——尽管是从一个有争议的认识论角度——用于决定争议事实的证据之科学有效性方面的基本问题。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指出,Daubert规则在强调法官控制与挑选那些真正具有“科学性”的证据的角色方面是走对了路的,尽管在这个方向上它走得不够远。尽管法官的这种积极角色对于美国对抗制结构程序来说是相当新奇的,但对于大陆法系来说就不那么新奇了。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法律体系中,Daubert规则关于证据的实际科学有效性之必要性的这类信息依然有着重大的影响,主要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说的,即这种控制还没有建立,或者曾经以一种表面化的且不具有实际效果的方式建立。
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地受到“科学神话”或者“科学主义”的影响,因为认识论者教会我们不要相信科学(用大写字母S)总能发现真理(用大写字母T),同时他们也告诉我们科学的应用并不是应对事实裁判者必须解决的所有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此外,他们认为科学是多样化的,并且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和发展,所以简单地谈及科学也许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并且他们多次重申,由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常常具有模糊性和非确定性,所以想要在科学有效的方法与非科学有效的方法之间做一个清晰明显的区分,是不容易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对于解决司法证据问题具有科学导向的方法的这些评论,不应该被推得太远,尽管他们无疑有一定的道理。
一方面,即使在事实上我们承认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并没有被准确和明显地界定,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声称可靠的方法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有关争议事实的“好的知识”。换言之,在司法背景和其他背景之下,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可靠的信息和数据以代替错误和不可靠的信息,那么为了完成建构,我们需要一些标准和规则。无论我们使用哪种标准和范式来定义我们所声称的“科学”,我们都必须证明与合理化这种标准或范式的适用,这恰好是为了排除任何实际上缺乏任何合理可接受性的伪科学。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提到科学(因为在特殊的案件中没有可用的科学或者因为任何原因我们没有运用科学),那么我们可以运用“常识”以及“理性人”的“普通文化”,也就是凭借个人的“知识储备”,而这种“知识储备”存在于任何社会成员的大脑和记忆中。实际上,事实裁判者(法官或陪审团成员)在任何案件中都必须对争议事实作出裁决:如果他不能依靠科学有效的证据,那么他将运用他自己的知识储备。但是当威廉·特文宁(William Twining)强调这样一种知识储备是一种“不明确的信念之集合,而这种集合是由一种包含或多或少的完备信息、精细模型、轶事回忆、印象、故事、神话、箴言、愿望、陈规、推测和偏见的复杂汤组成”的时候,他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他声称,在这碗“汤”中,事实和价值是不能被明显区分的,事实、幻想和虚构也同样如此。
因而,科学可能不会从本源上区别于其他更普遍的知识类型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很明显,各种各样的知识种类的可靠性程度不同,而科学的可靠性程度要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或真实或虚假的知识的可靠性程度高得多。
另一种关于科学和法律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在司法环境中科学的应用——更为普遍而重要的观点认为,科学方法和裁决争议事实的司法方法是不同的。表面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却不应被再次推向极端。一方面,科学研究旨在发现普遍的理论和规律,而司法程序则旨在发现具体、特定案件的真相,但这并不是反对在司法环境中应用科学,因为在许多案件中科学知识的应用仅仅是为了决定特定的事实(例如,有关特殊患者的医疗诊断)。另一方面,一般程序规则允许使用科学方法,且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它们普遍认同专家给事实裁判者提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是事实裁判者所不具备的。
事实上,在司法程序中规制证据采纳和提出(有时也有评价)的规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但这并不表明这些程序完全不同于其他认定事件是否实际发生的经验背景。换句话说,在司法过程中不可能达到“程序上的”或“形式上的真理”,而“真实的”或“实质的真理”仅能够在非司法环境中实现。如果能像企业那样很好地建构一套旨在发现争议事实真相的程序,那可以查明的真相在本体论上就不同于在其他不同情况下可以发现的真相。
这个问题并不解决真理的自然属性,而是解决事实问题。由于很多原因,许多程序制度都包含了很明显的非认识性规则,如排除相关证据的规则(例如为了保护有关特权的各种秘密事项)。然而,人们应该考虑到这些规则在不同的程序制度中也有所不同,即是历史、传统和政策选择的结果,因此,他们之间没有逻辑和认识上的必然联系。在这一点上杰里米·边沁(Jerermy Bentham)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理想的证据法应当仅包括相关性规则,根据该规则每一项相关证据都应当被采纳(今天边沁可能会同意非法证据的排除)。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有些程序规则是认知性的,因为它们以发现真相为目标,比如那些旨在防止陪审团自身错误的规则,或者为言词证据之陈述提供有效方法的规则(例如交叉询问,如果人们相信著名的威格莫尔格言)。
因此,很明显,有关证据和证明程序规则的存在,在本质上并没有同科学证据的应用和采纳在任何方式上存在冲突。相反,如果存在非认知性的程序规则,其结果是这样的规则应该被撤销,而认知性程序规则对科学证据的提出更为方便有效,从而有助于争议案件事实真相的建构。
至少自19世纪末以来,一些哲学家,例如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等就开始提出一般科学领域内的重要区别。根据这些区别中最著名的部分,例如在物理、化学、工程学和遗传学等“解释性科学”(即“自然的”或“硬性的”科学)和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学等“理解性科学”(即“社会的”、“人类的”或“软性的”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这不是文化或哲学上的抽象问题,但就司法环境中科学的应用而言,其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为了建构或者评价和解释特定的争议事实而使用社会科学专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公认且越来越流行,而不仅仅在诸如英国法院不得不确认劳伦斯作品《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文学价值等著名案件的审判中才使用社会科学专家。下面简单举一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其应用相当广泛:
——社会学家经常在有关就业歧视的案件中被咨询;
——历史学家被咨询有关历史事件的重构;
——当一个建筑的历史价值不得不被评估时,文艺历史学家会被听取意见;
——心理学家在一系列关于人的心理状态的大量案件中被咨询。
一般情况下,关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的证明书在司法诉讼中已经得到认可,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相关问题。
一方面,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些科学无法根据Daubert标准进行评价。Daubert标准涉及一个硬性科学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为了确定一种被称为盐酸双环胺(Bendection)的药物是否能给新生儿带来损害。因而,当大法官布莱克蒙冒险引证上述在他脑海中已经形成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有效性问题——而不是其他任何问题——来定义这些特定标准时,这些标准被硬性科学之一般定义的考虑精心地裁剪了。甚至当Daubert标准的适用扩展至技术案件时——例如Kuhmo案,社会科学仍然未被涉及。
那么问题是,虽然其中一些标准也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主要是“普遍承认标准”,该标准已经适用于Fry案件且从1923年开始被普遍适用,而且可能还适用于经过同行审核过的期刊杂志),但是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标准——如有关错误比例的知识和可测试性——却不可能适用于社会科学。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理解性科学”与大法官布莱克蒙谈及的“解释性科学”并不是一回事。在库恩主义语境下,两种科学类型的范式(the paradigms)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特别是人类科学不能适用在自然科学领域被认为是正确的亨普尔理论范式。因为Daubert标准像其他任何能够适用于硬性科学的标准一样,不能适用于具有根本不同之范式的科学,它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建立科学有效性的标准,如果成功,这些标准或许可以适用于社会科学。
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科学并没有形成一个同类的集合:它们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范式。在这样的多样性面前,要想定义一些科学有效性标准,只有考虑每一种科学的独有特征。实际上,经济统计学或社会统计学,在为了确定一栋建筑物的历史价值时,不应该采取同样的方法,相应的,也与分析一个成年人或未成年人的心智能力而使用的方法不同,此外,也与一个专家如何评价一个犯罪的文化动机,或者确定一个历史事实是否以及如何发生的方法不同。因此,对于任何种类的社会科学来说,必须考虑到这一问题不是由一种而是由若干科学可靠性决定的。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承认那些应当被适当地考虑为“垃圾科学”的方法在司法中的应用,无处不存在着危险,因为它们被剥夺了任何科学有效性,而且还缺乏对于它们的本质和它们的结论可信性之任何充分的认识分析。正如一些认识论者所言,即使承认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界限不甚明确,一个人也不应当倾向于把任何科学价值归因于对茶叶的熟悉程度或占星术,也不应当把一个虚假的通灵人当作专家证人。另一方面,一种检测某种实践的可靠性的好方法不应当是去询问那些仅仅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而获利的人。同时也应当考虑到Fry检测的普遍接受性存在着争议,因为那些从事茶叶解释实践的人将会同意在相关领域的知识中被普遍接受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的是一个独立的分析和建构一种对于任何知识之有效形式的范式都恰当的标准,并且应当能够鉴别出那些因为缺乏任何认知控制而“废弃的”的实践或方法。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大卫·凯(David Kaye)写道“这是法庭科学的黑暗时代”,主要是因为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Americ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提交了一篇题为“强化美国法庭科学——一条通向未来的路”的学术报告,写了三百多页关于所谓“法庭科学”的科学基础所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些已经不是新问题了,因为早在几十年以前,就有文章对各种法庭科学技术的可靠性提出多种质疑。但是NAS报告却尤为重要,因为它研究了至少12种法庭科学证据,除了对这些技术问题的一般讨论之外,还进一步广泛而细致地分析了每一种证据。这篇报告是关于法庭科学证据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且自从它公开发表以来,如今已经有多篇探讨其内容的学术文章相继发表,既有对其总体的评价,也有对更为常见的法庭实践的具体评价。
当然,我们无法在这里对这篇NAS报告进行总结,但是,至少值得强调的是它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这篇报告分析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所有的法庭科学,除了DNA检测之外,都缺乏科学有效性。这就是说,也包括了最常用的法庭科学技术,例如指纹对比(从1911年就开始在美国应用了)和笔迹分析,以及其他用于法庭调查的技术。此外,报告还指出,美国法庭一直以来(并且现在也仍然)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法庭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因为法官们经常会在他们的判决中承认和应用那些根本没有科学有效性的信息和数据。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形源于有关法庭科学技术可能(或不可能)的有效性之科学研究——从一个真正科学的视角出发——系统的缺乏;源于法官们对几乎所有这些技术的不可靠性的普遍忽视。尽管NAS报告只说明了美国的现状,但它所提及的总体情形其实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可能存在。
DNA鉴定技术是唯一的例外。近几十年来,它已经发展成了科学可靠性的“黄金标准”,恰恰是因为它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且这种科学研究是基于对基因的分析而存在的(尽管根据大卫·凯新近出版的书中所谈到的,这种证据并不是呈直线发展的)。此外,DNA鉴定技术还可以检测许多其他技术的潜在危机,因为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是,成百上千的错误定罪案件(通过DNA检测方法发现错误)是由各种法庭科学技术造成的,而这些法庭科学技术导致了事实裁判者的错误判决。
关于法庭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存在多种多样的问题,其中至少有两种是值得提及的。第一种问题源于这样一种事实,在很多案件中(例如笔迹分析中),结论基本上取决于两种笔迹的主观对比。如果这种对比的主观性必然存在,那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家将出具不同的主观对比的可能性就会存在,这样就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根本不同的结论:但在这样一个案件中,就无法确定孰对孰错,因为它们都是主观的,而且没有建立在任何科学的基础上。每个专家都会宣称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但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根本问题。
第二种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很多法庭科学技术的结果常常都是用“唯一性”的术语来表述的(例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写出这种笔记),因为法庭科学专家们经常用“零错误率”或“×百万分之一的错误率”(接近于零错误率)之类的术语。然而,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这种唯一性几乎不可能被证明,因为没有科学基础来为这样的结论进行证明。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一个理论上低的(或极低的)错误(或者非唯一性)的几率被承认了(尽管通常是不可知的),那么就变成了如何去决定多大的(不可知的)错误率是可以接受的问题,以作为支持一项宣告有罪或宣告无罪的判决的基础。这种科学可靠性信息的缺乏将再一次剥夺任何客观的和可信的法庭科学技术。
由于切实考虑到这些问题,NAS报告列了一个很长的建议清单,其中,在强调“建立证明法庭科学方法之科学有效性的科学基础”的研究必要性和建议“法庭科学分析可靠性和精确性的量化措施”的建立和发展时,第三条建议尤其清晰明了。此外,第五条建议强调了“关于人类观察者的偏见和在法庭讯问中人为错误的来源”的研究的可能性。而第六条提出了“为获得更高级的可测性、有效性、可靠性、信息共享性和专业检测性而去发展更高新的科学工具”的必要性。无需多言,当新的法庭科学证据获取方法被发现和采用时,这些建议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们不遵循科学有效性的标准,那么它们将不能在司法程序中被采信为证据。
这些概要式的评论说明,应用于各种证据的科学有效性标准在司法环境——一种极端复杂和令人费解的系统——中被运用。然而,尽管它极具难度,这样一个系统仍然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相信一个正确的司法判决要求对争议事实进行真实准确地建构;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将会成为构建这些事实的常规方法,那么它将决定何种方法才是真正“科学的”,以及何种手段不具有科学可靠性,这是一个公正的司法系统的首要条件。正如我试图阐述的,在科学证据这个辽阔而多样化的世界中,确实存在很多重要的区别,但是科学有效性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而法医学也不例外。
事实上,在现代司法系统中,科学有效性问题根本上是基于对法律的正确运用,我们不需要关于争议事实的任意的或者不可靠的裁决: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真实的裁决,这就意味着,当裁决是基于科学作出的时候,那它就是有效的和好的科学。
本文系第三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