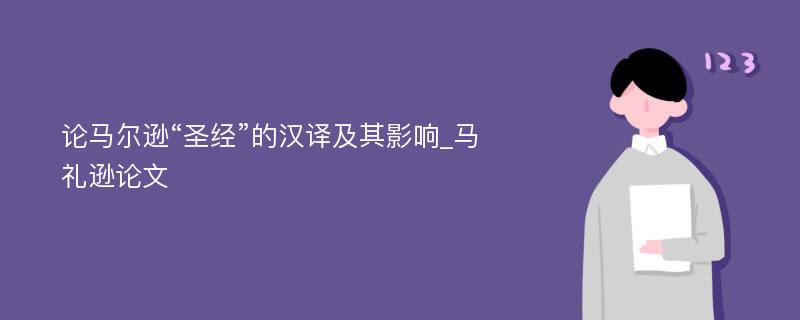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汉译论文,论马礼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督教从唐代(时称景教)传入中国,迄今已1300多年。虽然从其传入之始,便有景教徒将《圣经》经卷汉译以便广布,然而直到19世纪,尚没有出版完整的《圣经》中译本。1807年,作为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鼻祖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后,即开始了被视为他“事业的顶峰之一”[1](P18)的《圣经》汉译工作,在中国第一次将《圣经》全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因此,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2](P249)。
一、马礼逊从事《圣经》汉译的背景
《圣经》何时开始有中文译本,有论者认为,早在7世纪前半期,至少《新约》已经译成中文[3]。其依据便是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载贞观九年,叙利亚籍传教士阿罗本来长安,唐太宗命房玄龄“偬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深知正真,特令传教。”[4]因唐太宗时期佛经翻译已处于“盛行之时,《圣经》的译成汉文也更见可能。”[3](P4)这从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景教文献《尊经》可以看出,景教徒已译出《浑元经》(《创世纪》)、《牟世法王经》(《摩西五经》)和《述略传》(《使徒行传》)等30余部,这是中国第一批汉译《圣经》经卷[5]。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他们曾想把《圣经》译成中文。但是,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字不能表达《圣经》的涵义,以为最好的办法,莫如把《圣经》教训中重要的道理和圣经历史中重要的故事,编合而成一册书籍,以代《圣经》之用[3](P10)。东印度公司董事格兰特甚至断言:“没有哪种《圣经》的译作可以转译成中文,因为我了解中文的特性,不能进行任何转译,以中文翻译圣经,实际上是万无可能的事[7](P50)。”今天已没人相信这种说法,但在当时,格兰特的看法并非个别。杜拉姆城主教认为:“翻译中文圣经有两种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为经费浩大无法供应;一为除非假手天主教,基督教即使能将圣经译成中文,亦无法介绍及散播圣经于中国。”正因如此,基督教学术促进会慎重考虑后认定翻译中文圣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8](P68)。
1804年,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成立和大英博物院发现中文《新约》抄本即史路连抄本,使译经工作被重新考虑。圣经公会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正欲派传教团到中国的伦敦会。就在这年,正在高斯坡神学院学习的马礼逊向伦敦会提出请求,“愿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之布道区域中。”[9](P146)伦敦会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多,但他们预料到会有很多困难,暂时不能期望比翻译《圣经》更多的事,认为译经是使异教徒皈依的基础。马士曼在印度的传教经验也证实了这点,他说:“我们看到,如果福音在那里(指印度)扎下根,它一定是通过《圣经》的翻译和把译本送到印度各部落人的手中,无论传教士多么辛劳,他传播真理仅靠生动的语言而没有写成的著作以供他们阅读,他常会被误解,而以任何方式出版的《圣经》在他们中间传布,就会取得巨大成果,尤其当地人在阅读《圣经》时,就会加深对主的印象。”[10](P3)伦敦会由此坚信,《圣经》译成中文的工作完成后,上帝将会以某种方式为他们的事业敞开大门[10](P68)。这正是马礼逊来华后,克服一切困难,矢志不渝地从事译经的动机所在。
二、马礼逊的译经原则
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但其译经受到天主教译本影响很大,这源自他在伦敦学习中文时誊抄的巴设译本,美国宗教史家赖特烈说:“天主教的《新约》译本被介绍给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用来学习中文,它无疑影响了马礼逊本人的《圣经》翻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后来许多新教徒译本。”[11](P190)马礼逊自己对此予以承认,“我把珍藏在大英博物院的中文《新约》译本誊抄一遍,它成为我翻译和编辑中文《新约》的基础。”[12](P118)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他又提到,他的一部分翻译是根据某个不知名的人的著作,“他的虔诚的劳动保存在大英博物院里,我冒昧地改正和补充了我所需要的东西。”[13](P395)这显然指的是巴设译本。而马礼逊把"God"译为“神”,即是受了巴设译本的影响,巴设译本《约翰福音》第3章36节译为,“盖神爱世人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陨,乃得常生也。”《罗马书》第1章第一节译为“耶稣基督之仆,蒙神召为使徒,蒙择事神。”而马礼逊译本《约翰福音》第3章36节译为“盖神爱世,致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致沉亡,乃得永常生也”;《罗马书》第1章第1节译为“耶稣基利斯督之仆保罗,被召为使徒,分派事神之福音。”[14](P48)这里马礼逊不仅按史路连抄本把"God"译为神,而且用词和句式也基本相同。所以卫三畏说《新约》的一半是马礼逊翻译的,另一半是他校正了在大英博物院发现的手稿[2](P326),看来并非臆断。
同时,马礼逊在译经过程中,还注意使用一些容易引起异教徒共鸣的语词。马礼逊留意到,在中国语言中,所有那些看不见、又被人尊敬的就被称为“神”,马礼逊在翻译"God"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神”一词,认为这是中文能提供的表达"God"最通用的词。马礼逊译经不仅仅受到巴设译本的影响,据说他到达广州后,为了学会基督教的中文词汇,他曾被迫学习用中文写成的天主教书籍,并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5](P111)。据卫三畏认为,"Baptism"一词,马礼逊译为“施洗”,“洗礼”,就是沿用了天主教的翻译[2](P363)。关于“耶和华”(Jehovaho),通常译为“神主”(Divine Lord),当出现Jehovaho和"Lord God"时,马礼逊在一些情况下,用“主神”。但通常译成“神主”,可以理解成"God the Lord"或"Divine Lord",这可能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马礼逊在谈到自己的译经原则时说:“在我的译本中,我力求忠实、明达和简易。我宁愿采用常用字而舍弃罕见的经典字。我努力避免使用异教哲理和异教经籍中的术语,我宁愿被人视为俚俗不雅而不愿令人难以理解。在难懂的段落,我用我能达到的最优雅、最忠实、最不古怪的词给出教义的通俗表达。”[16](P122)他认为,任何一本书的译者都有两个职责:第一、要正确地领会原作的精神;第二、必须以诚信、明达及典雅的文笔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对第一个职责,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学者,在翻译《圣经》上比一个异教徒的译者更能胜任。至于第二个职责,自然,翻译成母语的人则较占优势。迄今看来,在一些现在仍奉异教的人中,在他们皈依前,要物色完全符合这些资格的人是不容易的。在这两个职责中,马礼逊认为第一项比第二项更重要,因为不论译文如何典雅,但倘若误解《圣经》的原义,真是得不偿失。相反,如果文字稍为拙劣,而传达意义准确无讹,则于原著无伤[12](P121)马礼逊说:“为完成此项任务,我不惮长期工作,谢绝社交,持以平静而不偏颇的判断:既不迷于新奇和古怪,也不因其为古代的经籍而固执己见。我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小心翼翼,而期望避免误传上帝神言之可怕的责任。这都是从事翻译《圣经》此类的书所不可缺少的素质。”[16](P118)
英国海外圣经公会给马礼逊提出的要求是,他的译文应忠实于原义,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并博得中国人对它的尊重[13](P442)。马礼逊对译经是极求准确,他在1808年2月给乔治·斯汤东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对我说过,根据希腊文译本,《使徒行传》中有些字句似乎不准确,等你有空时,你给我指出你发现的那些,我们一起商讨。”[13](P216)足见马礼逊态度之严谨,无怪卫三畏说,指导马礼逊及其同伴的译经原则是忠实、明达和质朴,最忠实地把《圣经》翻译成合乎中国文法的译本,使普通的读者也能理解[2](P328)。
马礼逊在译经过程中很注意文体,但他认为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式的文体不适于翻译圣经,因为即使中国的博学之士在理解他们的古代经典时,对一些难点解释往往存在异义。马礼逊说:“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真正的事实,我们将发现,若没有注疏,中国的经典被认为是无法理解的:原本文章从来没有人去读,除非为孩子学习发音,或经过老师或由以前借助注疏读过它的人解释,有五分之一的人花了几年时间阅读,尽管他们拥有注疏和老师教授之便,仍不能理解。”[13](P332)朱子(朱熹)是生活在12世纪著名的著作者,他给大多数经典或古代著作注疏,“他自己承认,由于年代久远和过于简洁,常常对文章真正的含义感到不知所从。”[13](P333)连朱熹这样的大注疏家在理解古代经典上尚且如此。因此马礼逊认为,称为“经”(King)的著作一般不适于模仿,无论是在《圣经》翻译还是其他神学著作中。实际上,在任何试图让大众广泛阅读和为大众所用的著作,都不能模仿这种文体。他认为,“博学之士的书面语与普通人的口语之间的差别,几乎像古罗马语言和欧洲现代方言的差别一样。”[1](P120)
马礼逊认为,翻译《圣经》最好的文体是根据经典注疏和《三国演义》结合而产生的文体,这种文体最适合于《圣经》翻译和其他宗教著作。经典注疏解决的主题通常是非常庄重的,因此,经常仔细地阅读它们,受之影响形成的文体很适合于神圣之物的尊严,而根据《三国演义》的模式形成的文体,则具有表达平朴流畅的特点。在马礼逊看来,《三国演义》在中国是非常受推崇的著作,采用这种文体,一方面具有经典著作的某些庄重和尊严,又避免经典的极其简洁,而使人难以理解,同时又没有了口语化的粗俗。所以马礼逊说:“就文体而言,《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可读性的作品。”[13](P330)
马礼逊抨击了中国士大夫著述所用的文体,他说:“中国有学问的人,像黑暗时代(指中世纪时期)欧洲有学问的人一样,认为每种受尊崇的书籍,应当以拉丁文书写,不能用土著方言。朱夫子(朱熹)在他的哲理论文中开始别开生面。因为新观念的传达,诚不如用浅白文字为好,中文经典式的古人辞,简略至甚,只可使旧观念复兴而已。采用这种深奥艰涩的文体翻译《圣经》,要么是取悦于有学问的人,要么是炫耀自己的才华。这无异于古埃及的祭司们,据说他们用象形文字来书写他们的经文,除了他们自己或少数人能理解外,真是难索解人;又无异兰斯的《新约》英译本(注:兰斯译本,Rhenish Version,指1582年英国天主教传教团在法国兰斯所译的《圣经·新约》英译本。),里面保留了许多东方的、希腊的、拉丁文以及许多深奥辞句,故意使一般人看不懂,这个斥责也许太过严厉,但在《圣经》的翻译中,应该承认,用浅白、简易的原则是可行的。”[1](P121)
正是为了使译本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马礼逊聘用中国学者为他校正,他的中文老师高先生,甚至梁发都是马礼逊译本的润饰加工者。
三、马礼逊圣经译本的影响
马礼逊从1807年开始译经,1810年就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全部《新约》译完,1814年出版[17](P376)。1819年11月《圣经》中文全译本译毕,1823年全部出版,取名《神天圣书》,《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注:遗书为英文Testament的中译。该词可译为“遗嘱、遗言”,也可译为“约”。根据基督教经典,译为“约”最为恰当,所以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圣经》译本都译作“约”不再用“遗诏”。)。《新约》部分由马礼逊独自完成,据卫三畏说,《新约》的一半完全是马礼逊翻译的,另一半则是他校正了大英博物院的手稿[2](P326)。《旧约》是米怜和马礼逊共同完成,所以有人又把这个译本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这些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3](P26)。
马礼逊《圣经》中译本作为中国第一部全译本,其影响是深远的。《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它的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中国严禁传教士布道的情况下,散发《圣经》译本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就成为在华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一个重要方式。马礼逊在谈到翻译《圣经》对传教的作用时说:“一个外国人的不精致的书面翻译,能够使一个当地学生很清晰地理解圣经的思想和含义,比口头表达效果要好得多。”[13](P8)伦敦会的创始人勃格博士也说:“《圣经》中译本是实现传教目标的最重要的著作,被剥夺讲道的机会是很令人痛心的。但你的翻译如果不是为你自己,起码也是为其他人在传教上奠定了一个基础。除此之外,很明显,当你完成第一部著作时,上帝会为你在中国布道敞开一扇宽广和便利的大门。尽管那个国家(中国)目前仍然对基督教真理紧闭国门,但我相信,上帝将为他的箴言和传教士提供一个突破口。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显示其重要性,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人去占领它。你的翻译就是一个重要的前奏。当《圣经》译完时,因为你和米怜能用他们的语言向中国人讲道,……你就可以满怀信心地看到中国辉煌的来日。”[13](P495)勃格博士对《圣经》中译的作用深信不疑。
马礼逊《圣经》中译本在欧洲也引起轰动,坚定了各差会对中国传教的信心。英国圣经公会在给马礼逊的信中说:“一个用他们本地的语言翻译的《圣经》全译本,除了给中国人带来难以估量的利益外,你的译本的印刷已经在那些从前如果不是对传教本身怀有敌意,也是对《圣经》的传布漠不关心的人中赢得了许多朋友,甚至同工(fellow Labourer)。当宣布中文《新约》译完时,引起了欧洲博学之士的最高程度的好奇,当有些人还在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时,他们已经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人手一本,并为他们各自的图书馆购买了它。《圣经》全译本将以这种方式产生最有力的影响。”[13](P108)
梁发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就是阅读《圣经》中译本而受影响。梁发是广东高明人,原系佛教徒,因会雕刻、印刷工艺而结识马礼逊。马礼逊《新约》即主要由他雕刻与印刷。[9](P1471)米怜前往马六甲时,需印刷工数名,梁发又随去马六甲从事雕刻印刷。梁发在雕刻中,对基督教教义渐生好感,闲暇时,“自己查察圣经,见经中严禁不洁、欺骗、拜偶等罪过,于是我想:‘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而此书之教训又得耶稣之异迹以为证明,此书必为真经无疑。’此后我遂留心听人解释圣经,而安息日读经时亦更为注意,而且求传教士为我解释。”据说最感动梁发的天良和追求真理之心的书是米怜的《耶稣传》,此书用简明的中文写成,米怜雇梁发为之雕刻,无疑,“这本有历史和地理背景并且附着详细的注解的故事,使梁发更清楚地认识了耶稣。”[9](P151)马礼逊在谈到《圣经》对梁发的影响时说:“自从梁发受洗以来,已经编成和印刷一段关于《新约》几个部分的释义。通过阅读,他发现比我们出版的任何其他书籍对他的灵魂教诲更大。……我相信他确实感到神圣真理的力量,在这个偶像崇拜的国家中,他是一个《圣经》产生效果的例子。”[13](P38)卫三畏也说中国“第一位信教者(指梁发)就是通过阅读他雕刻的印板而受影响皈依基督教的。”[18](P65)的确,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梁发逐步抛弃了原来的佛教信仰,皈依基督教,在1816年11月3日由米怜领洗,成为一位基督徒,并在1823年12月,被马礼逊封为宣教师。梁发不仅进行口头讲道,而且著述很多布道小册子,到处散发,其最著名的就是《劝世良言》。此书对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拜上帝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皮尧士甚至认为,“早期中国改正教(基督教新教又称改正教、更正教或新教)教会之所以能够发达,显然有赖于梁发之力。他所作的小书和单张是破除迷信开通思想的先锋。这位文字布道的先进,应受今日一切从事此种工作的人的感谢。”[9](P220)
《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经典,包含着基督教的教义和戒律,而且还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欧美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希伯来文学,就集中体现于基督教的《圣经》中。周作人先生说:“《旧约》就是希伯来的文学。”[19]《圣经》里辑录的色彩斑澜、优美动人的文学作品,对后世欧美文学艺术有极为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重视《圣经》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批判地加以引用。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涉及到的《圣经》人物就有80多个,而这80多个人物,被引用达300多次[20](P1)。正如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威里克夫的英译本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一样,马礼逊及其以后的《圣经》中译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作人先生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认为,圣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分为精神和形式的两个方面:精神的影响体现在“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出来。”他认为《旧约》里古代的几种纪事及预言书思想还嫌严厉,而略迟的几篇如《约拿书》就显示出“高大宽博的精神。”[19](P5)这篇故事通篇讲的是巨鱼吞约拿,但篇末耶和华所说:“这蓖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显示了上帝耶和华的宽厚仁慈。在《新约》里,这种思想更加明显。《马太福音》中登山训众的话就是恰当的例子。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第五章三十八——三十九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第五章四三至四十四),周作人认为,“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半源泉是基督教精神和希腊思想相接触[19](P5)。
圣书对中国文学的第二个影响即形式上的,也就是文体上的影响。他说:“欧洲对圣书的译本助成各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这动因原是宗教的,也是无意的;圣书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所深信的、不疑的,”周作人接着谈到圣书对新文学的影响,“我记得以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20](P7)周作人的见解可谓敏锐,近代有大批作家的创作受到基督教思想艺术的影响,而且在文学创作中,大量使用诸如“天国”、“天使”、“福音”、“十字架”、“乐园”、“赎罪”、“忏悔”等名词,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圣经》的译本的影响。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会长诚静怡(1881-1939)曾对海恩博(Broomhall Marshall)说:“关于您所问的销流广大的官话《圣经》有没有帮助国语被人用作文字媒介的问题,我相信它有。……虽然不能说官话《圣经》就是介绍中国新文字的工具,它一定曾在这件事上做过重要的角色。”[5]王国维曾说:“周、秦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21]正是在《圣经》等西典的翻译过程中,使中国汉语词汇得以日臻丰富。
马礼逊《圣经》中译本作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开近代圣经汉译之嚆矢,为以后新教徒的《圣经》中译奠定了基础。1835年,由麦都思(Medhurst)、郭实猎(Gutzlaff)、裨治文(Bridgman)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组成四人小组,重新翻译《圣经》,他们以马礼逊译本为根据而加以修订,新约部分于1835年完成,由麦都思作最后订正,1837年名为《新遗诏书》,在巴达维亚以石版印行。在以后的十至十二年间,中国的新教教会都以这册为主要的《圣经》译本[3](P29)。可见其影响之大。《旧约》于1838年完成,1840年印行,大部分为郭实猎所译。郭实猎又再修订麦都思修订的《新约》,以《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出版。这个译本后来被太平天国军队采用,在定都天京后印发,每册封面印有太平天国徽号和太平天国年历。洪秀全还将郭实猎译本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作为应试员生之参考本[22](P4)。据载郭实猎修订本,还流传到民间,马礼逊翻译的中文《新约》甚至传到伊尔库次克和其他俄罗斯城市。
标签:马礼逊论文; 圣经论文; 基督教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旧约论文; 新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