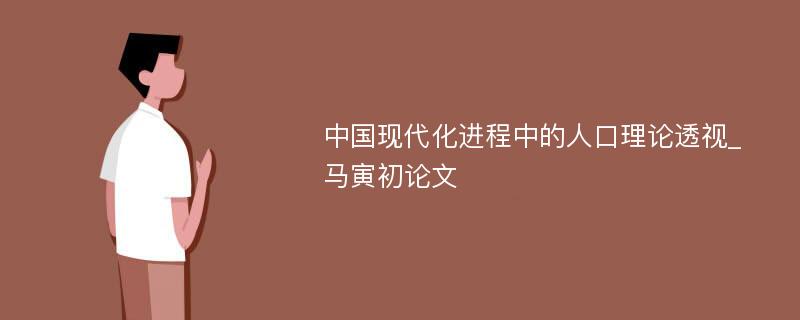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理论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透视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人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在中国有史以来生存发展问题最多的时段。反映这些问题的人口理论也就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变化、冲突和发展。清末的减民论首先对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众民论作出了断然的否定。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现代化的先行者们开始把人口问题同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第一次有了从学科意义上构建的人口节制理论。新中国诞生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抗有力地支配着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人口理论。直至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口理论才第一次能够真正地面对人口问题的现实,实事求是地支撑起现代化的基本国策。
人口问题历来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人口理论则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问题在人们思维中的抽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在中国有史以来生存发展问题最多的时段,因而反映这些问题的人口理论也就比以往有了更多的变化、冲突和发展。
一、传统社会的衰世哀呜
——清末减民论对传统众民论的否定
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传统社会全面衰败的变局下逐次展开的。传统社会的全面衰败反映在人口理论上,从一开始就集中表现为清末减民论对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众民论的断然否定。
所谓众民论,是以人口众多为追求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几千年来,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以拥有人的数量为主要决定因素的军事政治状况,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早在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留下了“多子孙甲”的愿望①。经过先秦时期的一大批主流思想家的发挥、论证和强调,众民论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普遍的共识。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②墨子也“欲民之众而恶其寡”③。孟子把“人民”列为诸侯三宝之一,指出“广大众民,君子欲之”④。荀子更是认为,人口再多,自然界也能供养——“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固有余足以衣人矣”⑤。先秦名著《管子》还颇为周详地提出过鼓励多育的政策设计,主张国家应专设“掌幼”之官主管多育。这些以众民为追求的人口理论,几乎都具体化为历朝历代推行的早婚多育的基本国策。
几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众民论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有力的挑战。虽然先秦就有老子主张过“小国寡民”,后来韩非子也曾从韩国的实际出发,对人口增长太快,货财增长太慢的反差深感忧虑,但是,这样的主张和忧虑在当时及以后的日子里,并没有得到社会与人心的多少响应。直至中国人口在清朝中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导向下爆炸性增长,从几千万上升到一亿,然后成亿地翻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道光年间突破了四亿大关。于是,人口的供养生计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给社会造成的压力日益明显。而要承受这一压力的社会,无论是从其自身矛盾的周期性规律来看,还是从其与世界环境横向比较所产生的新问题来看,都已经步入了“四海变秋色”的衰败之世。
以此为背景,传统的众民论第一次受到减民论的有力挑战。乾嘉时期的官僚学者洪亮吉忧思在先。他把人民生计日趋艰难的社会问题与当时人口的大量增殖联系了起来,提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⑥。这一观点与英国牧师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何其相似,但是它的提出却比马尔萨斯还早了五年。进而,洪亮吉又提出了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叫“天地调剂之法”,即借助水旱灾害、疾病时疫来减少人口;另一个叫“君相调剂之法”,即通过政策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及财富分配相适应。
与洪亮吉相比,一生历经清末嘉道咸同光五帝的官僚学者汪士铎对众民论的挑战更为犀利。他在1855年至1856年所写的《乙丙日记》中认为,当时“人多之害”,已经到了“天地之利穷矣”,“人事之权殚矣”,“犹不足养”的地步,因此,他主张大量减少既有人口。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他提出一整套减少人口的办法:一为恢复族诛,推广连坐,“以威断多杀为主”;二为推广溺女之法,限制生育,多生倍赋;三为实施避孕,“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四为鼓励男子外出经商,使夫妻不同房,减少人口出生率;五为提倡独身,奖励出家为僧尼;六为限制男女再婚,“男子有子而续取,妇人有子而再嫁,皆斩立决”,七为强制推行晚婚晚育,男“三十而娶”,女“二十五而嫁”。⑦汪士铎的减民论就其总体而言,就如同恩格斯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所指出的,是“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⑧它对传统众民论的断然否定,正反映出它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彻底绝望。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衰世哀鸣。然而,清末减民论的兴起,第一次把减少人口作为中国社会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第一次把减少人口的主张系统化措施化具体化,其意义和影响值得仔细探讨。
二、世纪之交的中外碰撞
——现代化先行者的人口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与日俱衰,正逢世界资本主义的恣意汪洋,中国社会日盛一日地受到这股世界潮流全方位的冲击。这一时代的特点,使得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理论明显地带有同世界对接与碰撞的特点。
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他面对不可回避的人口问题,已然放眼从世界吸取智慧,认为只要象西洋诸国那样“导民生财”,大力发展工商交运,就能解决人民生计问题。薛福成还具体提出要对国外输出劳务,向海外移民的主张,要求允许外国来华招工,认为这“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⑨。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也是从中国与英、法、德等国人口密度的对比中,来认识当时“动忧人满”的问题,他否定人口众多是造成贫困的原因,认为只要大量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农、矿、工等产业,就可满足人民生计之所需。表现了他对世界潮流所展示的新的社会制度以及新的生产关系所拥有的生产力具有充分的信心。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同样鲜明地带有中外碰撞的特征。孙中山把人口问题突出地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问题来看待。他在《三民主义》的系列讲演中,把人口问题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并列,作为民族主义的三大问题之一。他尖锐指出:中国受列强的祸害“详细的说,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人口的增加。他认为“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而近代以来,列强之“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中国)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从这一观点出发,孙中山特别抨击了当时对中国影响颇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用马氏人口论在法国的遭遇,来要求中国一些受马氏人口论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新青年,不要再中这一学说的毒。⑩孙中山“众民图存”的人口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危亡感,表达了一代爱国志士的共同心声。孙中山的忠实助手和积极支持者廖仲恺也曾著文,集中批判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源,是国家的政治和财产制度不好,绝不能归咎于“人满”的缘故。他断言“人满的患,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11)。
这些位于世纪之交的现代化先行者的人口理论不仅重新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众民论,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加入了他们所能汲取的时代内容,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把中国同世界相联系,在同世界的人口状况、人口理论的对接碰撞当中,提出自己的人口理论,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
三、动荡年代的书生之见
——人口节制理论初具规模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多灾多难的中国政治动荡,内战频发,外患临头,国家经济却仍在想方设法勉力发展,整个社会充满了紧张与失衡,到处是矛盾和冲突。一些学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专注于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先后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学的著作和论文,第一次从学科的意义上构建了中国的人口节制理论。
在这些学者中,陈长衡于1918年出了《中国人口论》一书,1930年又出了《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许仕廉于1930年出了《中国人口》一书,1934年又出了《人口论纲要》;陈达于1932年在《北京晨报》创办了“人口副刊”,1934年也出了《人口问题》一书。此外,还有吴景超等一些学者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谈论中国人口问题的文章。这些学者共同的观点,是主张节制中国人口数量。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是:
(一)陈长衡率先引用当时风行于西方的“适度人口论”,提出了“适中人口密度”论。把我国人口同自然资源、耕地、农业和城市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我国人口已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在“适中人口密度”以上,达到“人满”的程度。(12)。
(二)陈达率先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数量和改善人口的品质。认为“人口数量与人口品质处于反对地位”(13),人口数量增长太快,必然导致人口品质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数量降低,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的品质。他们主张限制人口生育,发展教育,发达科学,提倡优生,讲求公共卫生。
(三)许仕廉率先提出实行节育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治本”的办法。认为发展生产增加就业,实行移民,发展卫生,提倡优生,都是“治标”;唯有实施节制生育,才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这些学者和他们的论著,第一次使得中国的人口节制理论初步形成了规模。他们提出并研究论证的一些观点尽管在理论依据和论证方法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却具有奠基破题的科学价值。例如,“限制人口的数量和改善人口的品质”这一命题,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问题的关键,此后一直是我国人口理论所必须面对的中心课题。
但是,还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这些学者在提出和构建人口节制理论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深受西方人口理论,尤其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他们对马氏人口论中“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两种抑制”等基本观点异议甚少,接受颇多。并且,他们对人口理论的研究往往仅是从纯粹学理的范畴中来演绎的,脱离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忽略了人口问题同中国社会根本问题及其他问题的所有关联性。因此,他们所苦心构建的人口节制理论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成为备受冷落的书生之见。
四、探索时期的相生相克
——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理论风波
1949年9月,伴着中国革命胜利的隆隆炮声,中国的人口问题突然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热点。美国的国务卿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人民的吃饭问题没法解决。毛泽东即时发表文章《唯心史观的破产》加以驳斥。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中国的“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还指名斥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14)毛泽东的这些论断,为新中国的人口理论一锤定音。
随着新中国工业的起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1953年6月,国家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4年11月普查结果公布,中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必然联系,率先引起了党和国家主管经济建设的领导人的重视。1953年8月,政务院批准卫生部修订避孕和人工流产的办法,批示卫生部要帮助群众做好节育工作。1954年1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问题座谈会,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党是赞成节育的”(15)。同时,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组成了节育研究小组。1955年3月,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方式发出了第一份政策性指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提出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生育方面要加以适当的节制。同期,毛泽东也几次谈了控制人口的问题,讲到“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明确地提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16)。
在这样的背景下,沉寂多年的中国人口理论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包括二、三十年代成名的那些人口节制论学者在内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1957年前后纷纷发表文章,再谈我国人口问题。这些文章的主要理论观点渊源于二三十年代成型的人口节制理论,但也有一些明显的改变和发展:首先是对过去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所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和认错。同时也都对马氏人口论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其次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状况重新提出了“适中人口密度论”学说,修改了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结论。有人根据这一理论提出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是8亿。再次是分析了全国解放后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节制人口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办法。
这一时期重新活跃起来的人口节制理论中,最完整系统,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已成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务。他从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和自己的学问专长出发,十分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先是在1955年就曾将几年来的实地调查所得,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递交人大会议。但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被认为涉嫌马尔萨斯人口论,也就暂时压了下来。直到1957年2月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到毛泽东谈到了人口问题,于是马寅初就在会上宣读了这一发言稿,受到高层领导的肯定和重视。会后马寅初倍感鼓舞,认为“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17)。这样的认识推动他又在原有发言稿的基础上再作补充修改,1957年6月正式递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作为书面发言,并在1957年7月5日被《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标题为《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是: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马寅初估计,1953年人口普查以来,近四年的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20‰以上。对于一个人口超过6亿的国家来说,人口增殖率超过20‰就会带来各种问题,对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之间会产生一系列矛盾。因此,马寅初建议,一是要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五年计划;二是要宣传晚婚节育,并由国家采取行政和经济措施,实行晚婚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三是要实行计划生育,普遍宣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然而,在紧接而至的反右派运动中,那些热心谋国的人口理论学者均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利用人口问题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人口理论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马尔萨斯主义”的政治帽子付诸“批判”。尤其是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更是受到有组织的大规模攻击。据不完全统计,在1958年4月至1959年10月,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批判”马寅初和新人口论的文章约有200余篇。
当时的“批判”,号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武器,是以大量事实为根据来进行的。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形而上学和主观独断。首先,在理论上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甚至简单化地把主张增加人口还是减少人口当作区分两个“马”家人口理论的一条标准。其次,在思想上盲目认为只要革命胜利了,产生人口问题的社会原因也就解决了,一切人口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了,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人口问题,谁提谁就是利用人口问题反社会主义。再次,在实践上不切实际地照搬苏联的人口政策和我国“大跃进”中的浮夸事例,把这些做法绝对化为无产阶级的做法,而把与此不同的看法统统判为资产阶级的做法,一概否定。
对人口节制理论大“批判”的升级,正逢“大跃进”运动的高潮。在这个背景下,“人口越多越好”的众民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一理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借着“大跃进”的狂潮,凭着社会心理中的传统众民观念的牢固支撑,乘着“批判”人口节制理论的政治动力,急剧地膨胀起来,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系列的观点:一是在人口和人手的关系上,认为“主导的一面是手”,“口的消费量是有限的,手的创造力却是无穷的”(18)二是在人口增加和国家积累的关系上,认为“人多固然消费多,但生产更多,因而积累也必然更多”(19)。三是在增加人口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上,认为人口增加不是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甚至可能使劳动生产率获得巨大增长。四是在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上,不承认人口质量的客观存在,把人口质量论说成是来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所倡导的优生学说,来源于法西斯主义所宣扬的种族论,“是对中国人的诬蔑,对帝国主义的效劳”(20)。五是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人口政策的关系上,特别强调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主张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我国的所有的人口理论都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无不受到社会政治运动的有力支配和影响,无不是把每一个人口理论观点统统纳入到意识形态对抗的范畴之中,简单地划出阶级分野,贴上标签,对号入座。这一时期各种人口理论的遭遇也就往往发生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之中。判断的标准又绝对是从先验的意识形态框框出发,而完全忽略了从真正的实际问题出发来对每一个理论观点作一番完整准确科学客观的把握。然而,真正实际的人口问题却以其严重的程度,很快就对这一时期风波的是非曲直作出了公断。
五、实事求是的理论共识
——邓小平的人口思想和现代化的基本国策
马寅初等学者和他们的节制人口理论被整挨批以后,人口问题研究顿时成了是非之地。与此同时,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升温,尤其是“文革”动乱的兴起,党和政府从五十年代中期实际上已在起步开展的节制生育工作也受到了干扰。从而,在人口问题上压倒一切的众民论,竟然在社会生活中兑现为人口猛增的现实。从1961年至1971年,全国人口由6亿5千万多万,猛增到8亿4千多万,十年间净增人口近2亿,年平均增殖率达25.6‰,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的水平。这就是民谣流传“错批一个人,多增二亿人”的社会背景。
面对突出的人口问题,毛泽东从七十年代开始,多次讲到计划生育,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周恩来具体领导落实控制人口的工作。在强有力的领导推动下,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持续实施了强大而有效的计划生育活动。十年中全国总和生育率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了50%以上,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1年的2.6%。但是与计划生育活动大幅度推进相比较,人口理论研究显得大为滞后,适应不了计划生育实际工作的需要。
直到1978年底,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拨乱反正。1979年党中央终于批准为马寅初平反,为新人口论恢复名誉,充分肯定这一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是正确的。这一重大举措无疑是打开了禁闭多年的中国人口理论研究的闸门。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的人口理论研究进入了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特征的崭新阶段。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些领域的研究人员重新充实了人口问题研究队伍,不仅引进和应用控制论、系统工程理论等新的方法深入开展研究,而且还解放思想,冲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禁区”,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例如:展开了“两种生产观”的讨论,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口和物质资料“两种生产观”;论证了人口不断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研究了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人口规律问题;探讨分析了适度人口理论问题;甚至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提出了更切合实际的看法。
在这一进程中,邓小平的人口思想,为适应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口理论研究,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从认识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国情的角度,明确提出了人口问题。他多次指出“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中国的麻烦就在于人太多”(21)。他还说:“我们难就难在人口太多,而且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22)正是从这个实事求是的认识出发,邓小平总是从总体战略的高度指出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对我国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他提出对中国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邓小平在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时,处处考虑到了要把各项总量指标用人口数来均分。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经常用人均观念来论述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他还高度重视人口的质量问题,他从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多次强调要提高人的素质。
邓小平的人口思想使人们面对现实,越来越认识到人口过多并不是好事情,从而敢于正视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的状况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压力和不利因素,明白了人口过多已经拖了我国现代化的后腿。
实事求是的态度终于使人们在人口问题上达成了理论的共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这一共识已经具体化为党和政府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支撑起了一项现代化的基本国策。1980年《新婚姻法》规定了计划生育的要求。1982年,计划生育的条款载入了国家宪法。同年,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运用国家的力量把人口增长与国家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使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利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积极地走出一条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科学的人口理论在这条现代化的道路上获得了充分展开的广阔前景。
注释:
①见《殷墟书契后编》卷下十四叶一断片。
②《礼记·亲见下》。
③《墨子·辞过》。
④《孟子·尽心上》。
⑤《荀子·富国》。
⑥《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
⑦以上引文均见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8页。
⑨《庸庵文外编·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
⑩《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8、630、629-630、628页。
(11)《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页。
(12)陈长衡《中国人口论》,1918年版,第54页。
(13)陈达《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30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新版第1510、1511、1512、1511-1512页。
(15)《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1页。
(16)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17)见马寅初《新人口论》。
(18)见195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19)(20)见1959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
(21)(22)转引自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人口与计划生育》(双月刊),1994年第1期,第4页,第3期,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