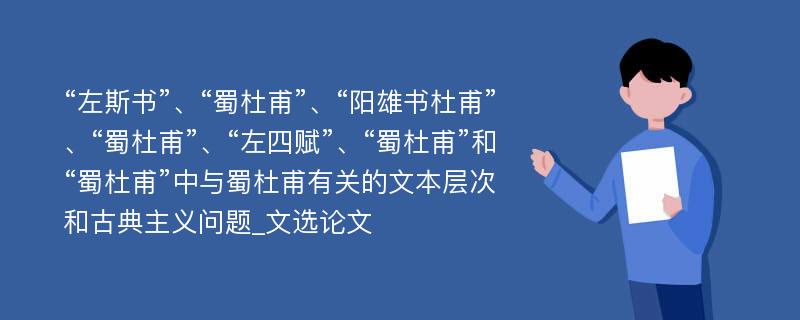
文本层次与经典化——《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层次论文,文本论文,经典论文,注引扬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5)03-0102-06 《文选》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校勘、训诂、编纂、传播等方面,无论是对正文文字还是注文文字的解读,都限定在单一的某一个文本层面,较少有对正文、注文以及二者形成的综合文本的考虑,尤其缺乏对这三种文本造成的阅读与审美体验的分析。 《文选》选家、注家,对所选文本、注本皆有不同的学术考虑。如《文选》选用左思《蜀都赋》,有选家的学术与政治考虑,也有现实社会的需求。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十余条,其文字与扬雄赋原文存在差异,说明《文选》注者在引扬雄《蜀都赋》时对正文文本、注文文本皆有注家之考虑。通过分析注者对引文文字的处理方式,还可以看出选家、注者不同的学术态度导致的文本层次、文本世界与其多系统性问题。 一、《文选》弃扬雄《蜀都赋》而录左思《蜀都赋》之分析 刘咸炘《文学述林》称:“京都之体最后,而乃以为首,此盖文士之见爱其篇体广博耳。”[1]“京都”之内,左思《三都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之后,可见选家对左思《三都》之重视。然在班固、张衡之前,早有扬雄《蜀都赋》,《文选》未录扬雄《蜀都赋》,而收录了左思《蜀都赋》,其原因值得探究。 扬雄《蜀都赋》,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与扬雄本传,亦不见于《文选》、《隋书·经籍志》。后人多以其晚出而怀疑并非扬雄手笔。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后汉书》李贤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皆曾引扬雄《蜀都赋》,北齐司马子如曾注扬雄《蜀都赋》。此证南北朝时期,扬雄《蜀都赋》流传甚广。 扬雄《蜀都赋》为单篇文章,《汉书》、《隋书》未著录,尚可理解。萧统《文选》不录,就值得思考。扬雄《蜀都赋》约成于汉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2]257,班固《两都赋》约成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2]399,张衡《二京赋》约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七年(105年)[2]455,扬雄《蜀都赋》成篇时间,较之二者已逾百年之上。《文选》选录了更晚的左思《蜀都赋》,而未选扬雄《蜀都赋》,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作品时代延续性的原因。班、张京都赋,皆写两汉都城长安、洛阳,左思所写,则是紧承两汉之后的三国京都,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地理上具有广泛性,而扬雄笔下的“蜀都”,并非“近汉之世”的京都。第二,政治上的考虑。《文选》选择作品,以京都为首,显然具有政治考虑,而扬雄《蜀都赋》中的成都,政治中心的地位不高,故此赋政治意蕴不浓。而班、张、左京都赋则不然,尤其是班固赋后《白雉诗》,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第三,历史正统观念的考虑。左思《三都赋》写魏、蜀、吴京都之繁荣,实为夸耀西晋之正统,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3]进一步而言,南朝诸代皆承晋绪,萧统《文选》选择京都赋作品,为避免不必要的历史误解,自然会避开将扬雄《蜀都赋》列于《选》首的情况。第四,文学上的思考。自东晋李充确立甲、乙、丙、丁四部之别,集部意识逐渐明显;南朝刘宋时期立儒学、文学、史学、玄学“四学”,文学独立于儒学的意识逐渐清晰,至萧统编选《文选》时期,会更多注意作品的文学性。扬雄《蜀都赋》主要是对山川、河流、物产、民俗等的概括性介绍,文学色彩较弱于左思《蜀都赋》,左思《蜀都赋》的文学色彩尤其是骈俪句式的特点,远远重于扬雄《蜀都赋》。 综合起来说,《文选》对不同体裁的文章篇目有所考虑,对同一体裁同题篇目之取舍亦有历史与文学思考。除此而外,《文选》取左思而弃扬雄,还有对左思《蜀都赋》文学影响较大与“厚今薄古”的人文思考。 左思《蜀都赋》的流行,有很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按照《世说新语》记载,左思《三都赋》初始并不为人所重,后张载建议他访皇甫谧作序,方为人所知。《晋书》的记载更为详细:左思《蜀都赋》初成,“时人未之重”,左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就请当时著名的三个学者为《三都赋》作序或注,皇甫谧“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刘逵对《三都赋》吹捧过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其置于司马相如、班固与张衡赋之上:“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4]2376第二,认为左思赋乃“近世”“明物”之作,将其比拟于胡光、蔡邕之作,“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4]2376其后,卫权“为思赋作《略解》”,张华将其比作“班张之流”。这五个学者,可以说是西晋文学翘楚,经其推荐,《三都赋》遂“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而陆机与陆云论左思《三都赋》,并读赋后“绝叹伏”。诸如此类的文学造势,是左思《三都赋》迅速被社会所知的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刘逵对“中古以来为赋者”的否定,以及对左思《三都赋》为“近世”“明物”之作的肯定,其中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左思《三都赋》属于“近世”即晋代之新创作,较“中古”辞赋家成就为高。第二,与汉赋“明物”相比,左思《三都赋》具有“明”“近世”之“物”的作用,尤其是“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直接提出了左思《三都赋》在“明物”上的新突破。刘逵对当时“贵远而贱近”的文风提出批评,认为左思《三都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是“近世”之作,明显具有强调“厚今薄古”的政治色彩。这种对左思《蜀都赋》文学影响与历史定位的评价,不能不对《文选》编者产生深刻影响。 本来,《文选》选左思而舍扬雄之后,左思《蜀都赋》作为《文选》中一篇,与《文选》整个文本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唐代六臣注《文选》,又引扬雄《蜀都赋》文字,将其胪列于左思《蜀都赋》文字之下。这在扩大读者阅读眼界的同时,又将包括扬雄《蜀都赋》在内的一个个独立文本引入《文选》正文文本之下,割裂了读者对《文选》正文文本的完整认识。但毋庸置疑的是,注者为了保护《文选》正文文本的完整性与主体地位,会在有意无意间对注文文本的文字进行相应的处理。 二、左思《蜀都赋》注对引文的处理方式与文本考虑 左思《蜀都赋》注引同题赋作材料,能体现注者对选者的文学、史学考虑,尤其是选者当初的取舍之心。《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说明注者认为左思《蜀都赋》与扬雄《蜀都赋》具有一定的文学联系。通过比较注者所引扬雄《蜀都赋》与左思《蜀都赋》的文字异同,可以总结出注者对二《蜀都赋》不同解读的文化心理、注文带来的文本局面的改变以及二者造成的文本层次问题。 就《文选》而言,至迟从中唐以降,读者见到的《文选》,已不是白文本的《文选》,而是有注文的《文选》,即在文本上是正文、注文混一的《文选》。这种情况下,注文势必对正文传播发生作用,但正如陆机所言“为文之用心”,注家对引文的处理方式,在后世研究者眼里也会体现出一定的“为注之用心”。这就是说,注者对注释中的注文多有改造——尤其是对注中引书文字,皆有据正文文意而改变注文文字之事。例如《文选》赋作中引《尔雅》,李善注多据辞赋文意顺改《尔雅》之字:李善注《鲁灵光殿赋》“规矩应天,上宪觜陬”之“觜陬”,引《尔雅》作“觜陬之星”,《尔雅·释天》作“娵觜之口”,此即李善据“上宪觜陬”文意改“之口”为“之星”①。这种改变,对于正文、注文之关系,具有一定意义。下面,笔者尝试对李善注与其他注者处理注文的方式,进行详细分析。 1.故意弱化注文文本地位,以保持阅读者对正文文本的注意力。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文选》五臣注:“江水分为二,故云带二江也。”②李善注引扬雄《蜀都赋》:“两江珥其前。”③扬雄《蜀都赋》作:“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④“两江珥其市”,张震泽解释为“两江旁贯其市如珥”,意思与“带二江之双流”同,但左思此言,显然合扬雄“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之意。这是一种“合并文意”的处理方式。左、扬赋中,“带”与“珥”对、“双”与“两”合,但左思“双流”,本来对应扬雄“九桥带其流”,注者却并未引用。这种故意“合并文意”的处理方式,显然是避免引入注文后使得读者对注文阅读界面的扩大,分散对正文的注意力,有弱化注文地位的倾向。 左思“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注者作“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录扬雄《蜀都赋》:“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卢池,澹漫波沦。”⑤《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文苑》同。可知注者属于直接引用。扬雄属概括性介绍,故涉及四个意象: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左思描写较为具体,并以对偶形式表现出来,意象也只剩下了盐泉井、橘柚园,但在扬雄方位词“西”基础上,增加了“家”、“户”,显得文学性更强。在这个文本层次中,注者引扬雄《蜀都赋》,只截取了几个孤立的描写对象,远不如左思正文之文采斐然,反衬左思《蜀都赋》文字之华美。根据谢灵运的看法,左思的表述具有骈文色彩,比扬雄的表达生动,如谢灵运《山居赋并注》:“橘林,蜀之园林,扬子云《蜀都赋》亦云橘林。左太冲谓户有橘柚之园。”其文采高下立判。 从此处正文、注文的不同文本层次看,注者引文,有时候是为了反衬正文文本的文学性,提高读者对正文文本文学意义的认识。这个时候,注者有弱化注文地位、故意抬高正文文本的倾向。 2.通过“截取关键词”,故意使得注文趋同并嵌合正文文字。左思《蜀都赋》:“其间则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文选》刘注引扬雄《蜀都赋》:“瑕英江珠。”不看扬雄《蜀都赋》原文,读者完全可以认为二赋文辞一致。但左思的“江珠瑕英”、《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瑕英江珠”,在扬雄《蜀都赋》原文则为:“于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显然注文对原文进行了“截取关键词”。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注者对正文文本的特殊考虑,以及对注文文本的特殊处理。注者有故意改易注文文本,以嵌合正文文本的倾向。 3.通过比较注文与正文文字差异,突出正文文本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左思《蜀都赋》:“其树则有木兰、梫桂。”《文选》刘注引扬雄《蜀都赋》曰:“树以木兰。”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蜀都赋》:“树以木兰,扶林禽,爚般关,旁支何若,英络其间。”《文选》注引扬雄赋,直接引用原文字,与左思表述相比,少了“梫桂”。在左思《蜀都赋》文本增益文字的情况下,注者直接引用了扬雄赋原文,还是照顾到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 4.缩小读者与注文文本的“接触面”,以消解注文原本的“经典化”,反衬正文文本的主体地位。左思《蜀都赋》:“黄润比筒,籝金所过。”《文选》注:“籝,幐也。《韦贤传》曰:黄金满籝。”《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与扬雄《蜀都赋》一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藕细布,一号郁林布,比蜀黄润,古称云‘筩中黄润,一端数金’。《淮南子》云弱緆,细布也。《汉书》云:白越即此布也。”左思《蜀都赋》与扬雄字异意同,显然借用、化用了扬雄《蜀都赋》的文字与文意。 如果仅仅看这两句话,我们会误以为左思只是化用了扬雄《蜀都赋》中的文字表述,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左思对扬雄的借用还不止于此。左思《蜀都赋》:“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在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蜀都赋》中则为:“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筒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扣器,百伎千工。”扬雄在“筒中黄润,一端数金”后,总结“雕镂扣器,百伎千工”;左思则先说“伎巧之家”,与扬雄相比,是将类似的表述提前至“黄润比筒”之前,并将扬雄仅有的两句话,铺衍为骈文句式:“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说明,左思《蜀都赋》不仅借用了扬雄的词句,还袭用了扬雄《蜀都赋》的文章结构与思路。注者省略完整的句子,仅仅保留关键词句“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显然模糊了左思与扬雄《蜀都赋》的雷同,造成了左思仅仅截取、化用扬雄词句的假象。从文本层次看,与扬雄《蜀都赋》原文相比,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的注文文本,有不断缩小文本“面积”,以突出左思《蜀都赋》文本地位的意图。 5.集部从经、史、子部中独立出来之后,注者有强化正文文本文学性的意识。结合注文与正文文字异同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通过注文、正文之意同字异,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学风格。左思《蜀都赋》:“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蜀都赋》:“尔乃其俗,迎春送腊,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干池泄澳,观鱼于江。”《古文苑》卷四:“尔乃其俗,迎春送暑,百金之家,千金之公(注:言中产之家,贵重之人,莫不毕出游遨)。”⑥《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作:“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除了“终冬始春”与“迎春送冬”相比,二赋似乎没有相同之处。但注者引扬雄《蜀都赋》却增加了一个“百金之家,千金之公”,显然是为了对应左思的“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这里不仅仅体现的是左思对扬雄赋的如何袭用或改变,也体现了不同时代汉赋写作的差异。扬雄时代的赋重“赋神”(即重知识化、信息化之“体物”),轻世俗风情之场景描绘;魏晋六朝赋重“赋情”,故文辞骈俪排偶、描写细致入微。读者会从注文、正文之表述差异,体味不同时代辞赋风格。 第二,注文与正文形成对比、互动关系,保证读者阅读进程,同时为读者提供动静结合的文学“画面”。左思《蜀都赋》:“若夫王孙之属,郄公之伦,从禽于外,巷无居人。”《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曰:“若其渔弋郄公之徒,相与如乎巨野。”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若其游怠渔弋,卻公之徒,相与如平阳,濒臣沼,罗车百乘,期会投宿,观者方堤,行船竞逐。”选者倾向于介绍左思笔下成都王公贵族的“从禽”游猎之乐,以“巷无居人”说明观猎者之众。《华阳国志》卷三:“郄公从禽,巷无居人。”亦说明此风之盛。游猎者与观猎者构成了一副静态的“游猎图”。《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若其渔弋郄公之徒,相与如乎巨野”,说的是“渔弋”之乐,即捕鱼、游猎之乐,此“渔猎图”比左思《蜀都赋》“游乐图”更增层次感与动态感。尤其是左思“巷无居人”,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括,远不如扬雄“罗车百乘,期会投宿,观者方堤,行船竞逐”说得形象而生动,更不如后者文学色彩浓厚。与《艺文类聚》引扬雄《蜀都赋》“若其游怠渔弋,卻公之徒,相与如平阳”比较,《文选》注引删除了表达渔猎心情的词汇“游怠”,删除了表示捕鱼地点的“沼”。注者如此处理,一方面是尽可能使得注文文字与正文文字高度近似,以免打断读者的阅读进程;另一方面,也有弱化注文文本地位的考虑,以免注文反客为主,影响读者对正文文字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艺文类聚》引此段,与注文亦有不同:“设坐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郄公之徒,相与如平阳。”这是将前文成都富豪饮宴的场面,与后文渔猎场面合并一处。这样处理的原因,显然在于类书编纂者的意图,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场面描写的凡例,而非专注于具体细节的文学描写。如此,原始文本就在不断被“碎片化”基础上,使得其文本系统不断复杂化。 从《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的内容,可以看出注者对左思《蜀都赋》文本的学术考量:考释名物,文学修辞表达的方式(彭门),相关的文化习俗(迎春送冬),生活现状(渔弋)。这体现了注者的文学修养和学术思想,以及注者使用注文与正文形成稳定关系的学术设计。这虽然可能会产生有悖于选者或作者原意的效果,但却不妨碍注者与后来的阅读者产生更多的文本感受、阅读体验与审美愉悦。 以上所谈,主要是笔者浅见,未必完全符合注者原意。然而,将《文选》与注释文字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性文本看,以上的分析也符合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和研究规则。例如将《文选》与注释文字作为不同层次的文本研究对象,就会看到《文选》注者引扬雄《蜀都赋》与选者选用左思《蜀都赋》,造成了文本面貌的改变。选者最初选用左思《蜀都赋》,给阅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阅读视野的限制,还有阅读误区与判断错位——即阅读者会误以为文学史上《蜀都赋》仅此一篇,或者误以为左思《蜀都赋》写得最好、地位最高。注者将扬雄《蜀都赋》引入之后,相当于在一个完整的田野上划分出一个个独立的“隙地”,部分程度上改变了选本的原貌与设想:左思《蜀都赋》中,穿插扬雄《蜀都赋》,为阅读者呈现出正文、注文两种不同的文本。这可能又会给读者带来另一种误读,即认为正文文本是借用了注文文本的文字与思想,是简单的模拟,而非新创。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三、注文文本造成的文本层次与“经典化” 选本、注本构成的不同文本世界,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冲击与阅读体验。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又说:“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5]结合鲁迅先生的说法,可知《文选》文本的影响力大致有两个向度:第一,蕴含着选者的文学观念。第二,限定了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判断。更进一步分析,《文选》文本,其实具有两个阅读程序,即选者初始阅读后的判断与选择、读者在选本基础上的二次阅读与再认知。这样看的话,选者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本世界,而选本阅读者面对的是高度“浓缩”的文本世界。文本世界的不断缩小,会影响阅读者的欣赏范围与价值判断。或者说,阅读者受到了选者文学思想的影响,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认识,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但随着选本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种片面性也会受到文学内在规律的作用而得以补偿。注释文献,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文选》中注释文字的出现,丰富了单一的选本世界,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选本、注文以及二者重新组合而成的文本世界。选本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限制,在注文中得到了相对全面的补充;二者结合而成的新文本,就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这就是说,选本正文、注文形成的不同文本世界,扩大了阅读者的眼界,改变了最初读者对选本正文可能产生的误读。 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给人们带来的首先是视觉上的层次感。正文文本与注文文本,会形成不同的“阅读层次”。《文选》左思《蜀都赋》注,通过不同方式引扬雄《蜀都赋》,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本世界:左思《蜀都赋》正文大世界、扬雄《蜀都赋》注文小世界,以及二者合成的新的文本世界。读者在阅读左思《蜀都赋》时,会自然而然形成对这三个文本世界的不同关注,从而获得不同的知识信息、文本感受与审美体验。对于更高层次的读者来说,可能还会进一步产生对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的回忆、联想与联系。这就在看似简单的文本阅读中,形成了三至四个不同的文本世界。左思《蜀都赋》属于正文,给人以辞赋“明物”之意义与文辞华丽之美感;扬雄《蜀都赋》属于注文,给人以知识补偿性解释的作用。二者形成的综合文本,形成了程度不同的“经典化”。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则与这三个文本世界保持了一定距离,显得貌似质木无文,成了一个不断被引用的“资料库”。 这种情况的出现,文学意义是明显的。一方面,扬雄《蜀都赋》引入左思《蜀都赋》注后,出现了明显的“去经典化”现象。为了避免注文弱化正文,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时,大量采用了故意弱化注文文本地位的方式,以保证读者对正文的关注和正文文本的“经典性”。从这个意义说,注文文本具有不断“碎片化”、“经典消解化”的倾向。以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为例,与其原始文本相比,《文选》中的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存在截取、节录、直接引用或化用等不同方式,使得注本扬雄《蜀都赋》与正文左思《蜀都赋》在文字、意义上具有了很大的趋同性,从而保证了阅读者可以很快把握正文文字的出处与含义。对于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来说,虽然这种文本事实上已经是被“碎片化”的次生文本,但对于不熟悉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的读者而言,注文中的扬雄《蜀都赋》,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完整文本。由于左思、扬雄《蜀都赋》篇幅都较长,如果阅读者在读左思《蜀都赋》的时候,再回头读扬雄的《蜀都赋》,就很容易产生阅读疲劳。如此,注文中的扬雄《蜀都赋》,就成了读者了解其文本内容与意义的主要渠道。而左思《蜀都赋》正文文本的遮蔽作用,会逐渐消解读者对扬雄《蜀都赋》完整文本的阅读欲望。长此以往,扬雄《蜀都赋》就不断被“去经典化”,并逐渐远离文本中心,成了文学文本注文、类书引文的材料来源。 另一方面,左思《蜀都赋》出现了不断被“经典化”的倾向。《文选》选家将左思《蜀都赋》从大量辞赋作品中选择出来的时候,第一次缩小了读者的眼界,但却使得左思《蜀都赋》文本具有了“经典”意义;扬雄《蜀都赋》被引入左思《蜀都赋》后,又一次衬托、提高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这就是说,一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必然同时伴随着其他“经典作品”的“去经典化”。另外,这种“选本”中的“注本”,又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选本”,造成了“选本”中有“选本”的文本面貌,使得文本的层次更趋复杂,给阅读者带来了更多、更新的阅读喜悦与审美体验。 当然,注文文本的负面作用也是存在的。注家对引文各种复杂的处理方式,有遮蔽正文与注文血肉联系的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正文与注文引文、正文作者与注文引文作者之间联系的完整性。从注家作注的目的——疏通证明来看,对引文的种种节略处理,恰与其目的相悖,至少是部分相悖。由于这个矛盾,注家对注文引文的处理,尽管有利于正文的传播和正文的经典化进程,但这种积极作用是以割裂引文与正文的鲜活联系为代价的,因而注本就包含着消极性,是扭曲的。注文对正文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消减。另外,注文文本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滞碍了读者的阅读进程,打断了读者对正文的持续性关注和连续性思考。尤其是较为繁复的注文材料,会迟滞读者对注文的阅读并使其恋栈于注文文本,从而分散读者对正文的注意力⑦。 综上所述,《文选》选用左思《蜀都赋》、舍扬雄《蜀都赋》,将扬雄《蜀都赋》“逐”出了“经典”位置,客观上突出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然而,《文选》注者在左思《蜀都赋》中引入扬雄《蜀都赋》后,一方面突出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与“主体文本”价值;另一方面也建构了扬雄《蜀都赋》等不同的“次生文本”,丰富了整体文本的层次性与系统性,并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本世界与阅读体验。进一步而言,注文性质差异,呈现出文学、经学、史学、子学文本共存共生的文本层次与世界,客观上起到了类书的作用,甚至是一部经、史、子、集经典作品的“缩微版”。这对于研究集部独立之后,如何从经、史、子学中汲取文学素材与营养,成为独立的门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研究思路。同时,本文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推广至经、史、子部典籍,为深入挖掘四部典籍中的文化价值提供借鉴。 注释: ①更多例证参见窦秀艳《雅学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本文使用的左思《蜀都赋》正文,主要采用了《文选》李善注本的文字。左思《蜀都赋》注释文字,参用了中华书局1977年李善注本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五臣注本,余不一一赘注。 ③《艺文类聚》卷六十一、宋章樵注《古文苑》卷四、明杨慎《升庵集》、明郑朴编《扬子云集》、张震泽《扬雄赋校注》中录《蜀都赋》皆作“两江珥其市”。严可均《全汉文》引扬雄《蜀都赋》作“两江珥其前”,注云:“本作‘两江饰其市’,《艺文类聚》六十一亦如此,今从《文选·蜀都赋》注、《水经·江水》一注改。” ④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本文使用的扬雄《蜀都赋》,皆用该书,不再一一赘注。 ⑤谢灵运《山居赋并注》:“扬雄《蜀都赋》云:‘铜陵衍。’”与各书不同。如果不是谢灵运改易了扬雄的文字,则扬雄《蜀都赋》或另有版本流传。 ⑥宋代诗人刘攽、苏辙、陈造、戴复古等人的诗中,皆有“迎春送腊”典故。 ⑦此方面分析得到了梁临川先生的指教,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