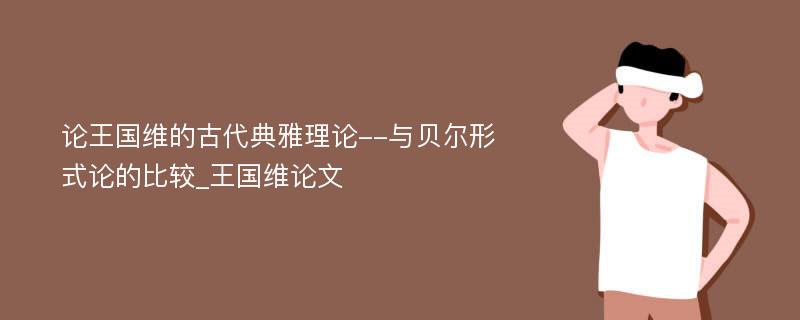
论王国维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尔论文,理论论文,古雅论文,形式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氛围进行中西美学、中西艺术对话和融通的中枢,而他极富美学品格和美学价值的古雅理论就是这一中枢的关捩。尽管古雅理论与克莱夫·贝尔的形式理论从渊源到内涵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理论界、艺术界舍近而求远,把“有意味的形式”推崇到作为现代艺术旗帜的高举与对“古雅”的冷漠、忽略甚至讥讽,形成了鲜明的反照。这,不只是知识认同的失误和理论选择的偏差,更是理性导向的失误和偏差,在王国维的古雅理论与贝尔的形式理论的互为参数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加明了地把握这一点。
1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主要依叔本华的意志本体论、悲剧人生观以及建立其上的被誉为“人生之花”的艺术哲学,提出优美、宏壮(壮美)的两个审美范畴,并对它们的美学性质、人生价值和创作渊源作了系统概括。随他对西方哲学、美学领悟的加深和中国美学、艺术奥秘的自觉,又在1907年提出与优美、宏壮并列的艺术审美范畴——古雅。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开宗明义:
“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汗德(即康德——引者注)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下,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
艺术天才论在西方美学、艺术理论上,由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渊源而流长,自康德提出“天才替艺术定规则”理论以后,席勒、叔本华、尼采等便揭去了艺术与天才之间的层层纱帷,艺术是天才的产物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学观念。王国维极力推扬艺术天才论,但其沉潜的理论根柢不是康德的天才论而是叔本华的天才论。他认为,“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出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问题。叔本华论此问题也,最为透辟。”[②]王国维吸收叔本华意志——理念——表象的哲学演绎公式,并援引《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艺术出于“先天”的“最为透辟”的观点,确信艺术对“理念”的认识和传达均是天才的任务。天才以其纯粹主体洞察对象的纯粹形式,从而创造引导人们在对它观照的审美境界暂时解脱苦痛的艺术。王国维把美、艺术美分为优美、宏壮两种,它们与康德美在无关利害的形式吻合,具体而言,优美“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其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没于此”;壮美之“形式越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不大利于吾人,而又觉非其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天才的艺术之所以被王国维标举为“最神圣最尊贵”[③]的,就在于它们作为无关利害的纯粹形式,以不同的审美心态在“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审美境界,解脱人们的利害、苦痛的审美价值或人生价值。这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对康德、叔本华的美学观、艺术论的膺服解读。
但是,王国维因“疲于哲学”而“移于文学”,由美学的理论探讨而艺术的美育实践,把探究的视点聚焦在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他对原来坚信的叔本华、康德的艺术天才论及审美范畴论开始动摇,觉得它们不能说明艺术美、艺术价值和艺术创作的全部事实,突出表现为三点:其一,从艺术性质看,既存在非利用品的真正艺术品,同时也存在“决非真正的艺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的艺术品”,即不是真正艺术品亦非真正利用品但又有真正艺术品性质的作品。其二,从创作主体看,既有创造真正艺术品的天才艺术家,也有能创造出与天才的真正艺术品相媲美的艺术的非天才艺术家。其三,从艺术价值看,天才创造的真正艺术品能慰藉人们的情感痛苦而走上解脱之道,有些并非真正艺术品,也具有同样的审美功能和人生价值。因此,王国维所依叔本华和康德的审美范畴论和艺术天才论,把天才洞见及创造的美和艺术划分为优美、宏壮的两大审美范畴,再也囊括不了艺术世界的全部事实。他对艺术世界优美、宏壮之外的艺术审美事实“无以名之”,遂从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中找到“古雅”范畴,作为这些并非天才所制作而与天才的制作具有同样人生价值的艺术品的审美特征和审美内蕴的范畴概括。
古雅,原是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的一项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王国维在《中国名画集序》中说:“三代损益,文质尚殊,五方悬隔,嗜好不同。或以优美、宏壮为宗,或以古雅、简易为尚。”王国维在以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对所吸收的西方美学思想的深刻反思中,自然以谙熟的这一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的合理内核去救偏、修正、充实西方美学,尤其是康德、叔本华的艺术天才论和审美范畴论,因此,其“古雅”已不再是传统的“古雅”,也不是康德、叔本华的“形式”,而在中西美学、中西艺术的合璧中被赋予丰富的美学内涵。王国维从对西方美学的艺术天才论和审美范畴论的救偏出发,把康德以及叔本华的“美在形式”说广泛用于艺术及其审美特性的研究,由“形式”推及“古雅”,并以此作为把握、界定艺术的本质审美特征之一,从而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完成超越优美、宏壮两大审美范畴的古雅理论建构。
无独有偶,在王国维建构古雅理论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发表六年后,英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出版了《艺术》[④]一书。他以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法国风起的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艺术为材料和印证,将康德“美在形式”的“形式”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并用以作为艺术的基本界定和审美的本体属性。王国维和贝尔都不把艺术看作固定不变的实体,而以含有特定“意味”的形式来把握艺术及艺术美。这似乎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东、西双方不同文化氛围对艺术及艺术美的共同美学追求。以古希腊摹仿论为精神支柱的西方古典艺术,发展到十九世纪,其再现、描述、写实的程度已是登峰造极。于是,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用,便发生了印象派。莫奈、马奈、雷诺阿等印象派大师一反再现、写实的传统,旁若无人地摄取光、色效应入画,将康德“美在形式”说落到艺术的实地,在对传统的古典绘画的毁灭性冲击中,走进现代艺术的历史领域。而高庚、凡·高、塞尚等后期印象派的崛起,则突破早期印象派对虚浮的色、光追求,更加注重“意匠”“意味”,注意色、光、线及其组合等形式的内在意蕴。贝尔在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绘画的启示下,承康德的“形式”而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口号,既是贝尔对西方古典艺术重新估价的标准,也是现代艺术阵地上高高飘扬的战旗和不懈的美学追求。中国古典艺术向来讲究“神韵”、“笔情”、“墨趣”、“意境”、“匠心”、“写意”,其中山石水木云烟花草因“隐然咏怀”便蕴涵了无限的生命和永恒的情趣。中国古典美学的这一内在精神直接引发了西方印象派及后期印象派的崛起,也深深渗入贝尔的形式理论中。而这一传统的艺术精神,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曾多次的断裂。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字狱的盛行和桐城派的推波,美学观念和艺术实践的形式主义浮艳之风日益滋靡,及至王国维时代,则艺术领域的每一角落都充斥了这种形式主义的色彩。王国维针砭时弊,在用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精神对吸收的外来美学观念和当时的艺术实践的深刻反思中,提出“古雅”范畴以探究艺术及其形式美的深层意蕴,展开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本体追求。
因此,王国维的“古雅”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渊源,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美在形式论,而中国古典艺术及受其影响而崛起的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艺术,则是它们诞生的催生剂,但引发它们诞生的原始酵母,则是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的“写意”、“神韵”、“意境”、“情趣”、“匠心”等内在精神。
2 “古雅”作为与优美、宏壮同等的艺术审美范畴,因拥有“美之性质”或“美之公性”而挤入王国维的美学视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术之公性,优美与宏壮然,古雅亦然”。王国维“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术之公性”这一美学命题,无疑包涵了“古雅”与优美、宏壮相同的审美属性,具体言之,则:
首先,从命题的字面义看,“古雅”与优美、宏壮一样,不涉及道德实践的功利和物质实践的实用。“虽物之美有时亦供吾人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矣。”
其次,从命题的深层义看,“古雅”与优美、宏壮一样,它作为审美对象使其主体在纯粹愉快的审美境界,暂时摆脱人生的苦痛和意志缠绕。“吾人之玩其物也,无关利用故,遂使吾人超出利害之范围外,而惝恍于缥缈宁静之域。”
再次,从命题的引伸义看,“古雅”与优美、宏壮的审美特征最后都归结为“形式”。“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无疑王国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的“形式”,来源于康德“美在形式”的“形式”。但并非只此,“美之知识,乃‘实念’(即叔本华的‘理念’——引者注)之知识也。”进而,王国维把康德的美在“形式”与叔本华的美在“理念”融二为一,“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因此,王国维的“形式”,是“理念”或“实念”显现的“形式”。美在形式说是王国维系统讨论古雅理论的基石。
“古雅”,与优美、宏壮有共同的审美特征即“公性”,但它作为独立的艺术审美范畴又有什么独特的审美属性,王国维又是怎样界定它的审美规定性的呢?对这一问题,王国维是在与优美、宏壮的比较中作出思辩性回答的。
其一,优美、宏壮兼存于自然和艺术,而“古雅”仅存于艺术。优美、宏壮作为意志直接客体化的“理念”的呈现,存在于自然界,它们经天才直观而进入艺术系统,仍具有优美、宏壮的美学品格。而“古雅”,则是天才艺术家在没有天才光临的时候或非天才艺术家凭人力修为在艺术创作中缔结的纯粹形式,它不可能游离艺术而存在。
其二,优美、宏壮作为“物”存于自然和艺术,就与功利、实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惟天才凭其秉赋才能脱离它们的利害、功用束缚,而在审美直观中洞见其美的纯粹形式,并且天才的审美欣赏及判断是共同的,为非天才的范示。因此,优美、宏壮的欣赏力、判断力既是先天的、天才的,又是必然的、普遍的。“古雅”的存在范围和存在方式与优美、宏壮不同,它以纯粹形式呈现于艺术,而一般“中智以下之人”凭其人力修养就可以欣赏它、判断它,且依人力修养程度的差异而对它的欣赏、判断会有不同的特色。因此,“古雅”的欣赏力、判断力既是后天的、经验的,又是特殊的、偶然的。
其三,优美在“无我之境”的“静”中使“人心平和”,宏壮在“有我之境”的“由动之静”中“起人钦仰”,从而实现它们的审美价值或人生价值。“古雅”呢?其纯粹形式既使“人心休息”与优美相通可不及优美,又回唤起“钦仰之初步”的“一种惊讶”而与宏壮相通可也不及宏壮。王国维由此断定,“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称之为“低度之优美”和“低度之宏壮”。同时,对无论自然还是艺术的优美,宏壮的欣赏和创造均属天才的专利,不及天才的“中智之下”的众庶是无力问津的,但他们可以通过人力修养来欣赏、判断、创造“古雅”的艺术作品,并在创造和欣赏的审美境界获得人生苦痛的暂且解脱。王国维深知天才何其少而众庶何其多,认为“古雅”是审美教育普及的津梁,极力标举它对众庶的审美价值或人生价值,就将“古雅”列为其救人救世的美育医方的一味良药。王国维由此断言,“自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
“古雅”与优美、宏壮在“美之公性”之上的独特审美特质,使其成为与它们相并的艺术审美范畴。它的确立,从根本上弥补了康德以来西方美学艺术天才论和审美范畴的缺陷,同时,也在艺术审美价值的理论深度和实现广度上,为优美与宏壮架起了一道桥梁,为众庶走向审美找到了一座津梁,从而在与优美、宏壮的比较中,确定了“古雅”作为艺术审美范畴的合法位置和人生意义。
王国维的艺术审美范畴有优美、宏壮和古雅,或者说,他以优美、宏壮、古雅三个并列范畴来阐述艺术的审美特征。而贝尔只用“signfinicant form”唯一范畴来概括艺术审美特征的全部内涵。但是,王国维与贝尔阐述艺术审美特征、确定艺术审美范畴的基点,均是艺术的形式。由此,王国维从自然与艺术关系的角度,把艺术形式分为“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两种:
以自然但经过第一形式,而艺术则必须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
可见,王国维就自然与艺术同“理念”或“实念”的关系而言,以优美、宏壮的自然之美为“第一形式”,称优美、宏壮、古雅的艺术之美是“第二形式”;就艺术的审美范畴而言,源于自然的优美、宏壮属“第一形式”,表出自然中固有的优美、宏壮的“形式”或艺术家所自创造的“新形式”的“形式”属于“第二形式”。王国维在西学或新学熏浸下形成的逻辑思辩显示充分,从自然与艺术的关系切入,在艺术的审美范畴内部展开了对作为“第二形式”之“古雅”的理论探究。同样,贝尔也立足于自然与艺术、现实与艺术的关系来建构其形式理论的,不过他是从对两者的否定论证中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的。
“古雅”作为艺术审美范畴的“第二形式”,它比康德的纯粹美更纯粹,“可谓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王国维说:
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其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由此可知,王国维对作为艺术审美范畴的“第二形式”之“古雅”的分析,实际上有两个系统或两个层次:美者愈增其美与一种独立之价值。
3 古雅的第一层次系统就是表“自然中固有之形式”的“第二形式”。它与王国维从自然与艺术同“理念”的关系入手所划分的“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相联系,自然中“理念”显现的优美、宏壮作为“第一形式”,一经艺术家直观便唤起优美之情与宏壮之情,凭依“古雅”之“第二形式”复现于艺术,使自然中优美、宏壮之“第一形式”因艺术的“古雅”之“第二形式”而“愈增其美”。王国维说:
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在于形式固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情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等……戏曲小说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对文章之方面言之,则为材质,然对吾人之感情言之,则此等材质又为唤起美情之最适之形式。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
此段陈述阐析了艺术领域的“材质”、“美情”、“形式”的思辩关系。其“材质”就是“理念”显现的优美、宏壮,即艺术原型之“第一形式”;其“美情”,就是“第一形式”之美的对象唤起的优美之情和宏壮之情;其“形式”,就是复现优美、宏壮之“材质”,媒裁优美、宏壮之“美情”的“第二形式”之“古雅”。自然状态的优美、宏壮之“材质”及其唤起的“美情”,经“第二形式”之“古雅”,使“美者愈增其美”。在艺术领域就此点而言,“材质”、“美情”与“形式”,优美、宏壮与古雅,“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是融然相一的,可通俗地解读为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王国维说:“优美及宏壮必与古雅合,然后得其固有之价值”,“古雅之原质为优美、宏壮不可缺之原质。”因此,“古雅”之“第二形式”实则是融浸“第一形式”“材质”及其“美情”的“形式”。
似乎有一个矛盾,“中智以下”的众庶凭其人力修养而欣赏、创造“古雅”,可“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的优美、宏壮,只有天才方可洞见并予以艺术的复现。如此,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出现了。其实,王国维否定众庶对优美、宏壮的欣赏和创造,但并不否认天才对“古雅”的作为,更何况“真正之天才,其制作非必皆神来兴到之作也。以文学论,则虽最优美、最宏壮之文学中,往往书有陪衬之篇,篇有陪衬之章,章有陪衬之句,句有陪衬之字。一切艺术莫不如是。此等神兴枯涸处,非以古雅弥缝不可。”王国维由此认为,只有天才艺术家创造的“古雅”之“第二形式”,在与“美情”“材质”“第一形式”的浑融相合中,才真正使自然中固有的优美、宏壮更加“美且壮”,即“美者愈增其美”。
王国维的“古雅”与贝尔“有意味的形式”,旨在对艺术形式的本体探求。王国维强调“古雅”之“第二形式”对艺术形式的本体作用,“即同一形式,其表之也各不同;同一曲也,而奏之才各异;同一雕刻绘画也,而真本与摹本大殊。”贝尔也认为,“一件艺术品不可能被丝毫不差地仿制出来……因为支配艺术品创作的东西不再支配复制品的制作。”而“神秘地支配形式创作的东西”就是“艺术家创造的形式表达了某种特殊的情感。”贝尔进而把艺术本体归结为“有意味的形式”。“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组合,这些审美地感人的形式,称为‘有意味的形式’。”他有“有意味的形式”之“形式”确立为“审美情感”,从而在审美情感与艺术形式之间架起的符号性关系,使其颇具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王国维的“材质”“第一形式”“美情”与贝尔的“审美情感”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它们复现于艺术之中,成为“古雅”之“第二形式”的内在意蕴。
但是,贝尔是从否定艺术的再现与对其摹仿的切口来探讨“有意味的形式”的。他在主体与客体,艺术与自然割裂之中片面夸大主体“审美情感”的作用,“唯有艺术家的敏感才能知觉到它们纯形式的意味”,而自然美、社会美不可能产生“有意味的形式”,虽然贝尔也曾提出第二个假设——“有意味的形式”是对某种特殊的现实情感的再现,但他在“远远不敢说有多大自信”的疑惑中,又以再现往往是艺术家低能的确信予以否决,从而以为再现、记述事实、描述故事情节都不能唤起审美情感,甚至把能够暗示和传达思想、信息的形式一概排斥在“有意味的形式”之外。如此,不仅“有意味的形式”之“意味”——审美情感成为无源之水,而且艺术与社会、生活、现实的审美双向流程被阻滞,最多只能容纳艺术影响生活而不受生活影响的观点。王国维从自然与艺术的密切关系入手,从自然之“第一形式”进入艺术因“第二形式”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异来探讨“古雅”的奥秘。“古雅”之“美情”是自然中优美、宏壮之“第一形式”唤起的审美情感,“第一形式”“美情”与“第二形式”“古雅”就是自然的优美、宏壮的“攫捕”和“表出”。因此,王国维在自然与艺术、“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的审美双向流程中,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描写“人生全面之知识”,参与社会作用的。“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独之生活,而在家庭、国家及社会中生活也。”甚至艺术作品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学家论世之资者不少。”
王维“古雅”之“第二形式”的第一层次系统,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在同一理论格局下,呈现了中西两种艺术形式本体的审美范畴的不同价值基点和审美取向。但随王国维“古雅”由第一层次系统向第二层次系统的转换,则“古雅”之“第二形式”与“有意味的形式”几乎走向美学底蕴的趋同。
4 王国维在康德的纯粹美和叔本华的音乐美的理论导向下,走入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的传统精神,从而在中西美学、中西艺术对话中开始“古雅”之“第二形式”的第二层次系统的探求。康德无论什么现实内容都不能降低其独立美学价值的希腊风格绘画和无标题幻想曲的纯粹美,给王国维以极大的启迪,在叔本华最高艺术类型的音乐是蕴含“精髓”的“普遍形式”的直接引发下,王维指出:
茅茨土阶,与夫自然中寻常之景物,以吾人肉眼观之,举无足与优美宏壮之数,然一经艺术家(若绘画,若诗歌)之手,而遂觉有不可言之趣味。此等趣味不自第一形式得之,而自第二形式得之者无疑也。
表明艺术“古雅”之“第二形式”,不仅能表出自然固有的优美宏壮之“第一形式”及其“美情”,还能表出自然本无的“所自创造的新形式”及其“美情”,还能表出自然本无的“所自创造的新形式”。将自然中本无优美宏壮可言的茅茨土阶等寻常之物纳入艺术并表出之的“第二形式”,自然不是“古雅”第一层次系统以“材质”“第一形式”“美情”为内蕴的形式,而是涵养“趣味”的形式。与康德的自由美和叔本华的音乐美一样,王国维蕴涵“趣味”的“形式”,不依其自然、社会、此在的现实内容,但具有给人以情感愉悦、痛苦解脱的独立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这就是王国维“古雅”之“第二形式”的第二层次系统。
在“古雅”的第二层次系统,“趣味”是其“第二形式”的内核,也是“古雅”由第一层次系统进入第二层次系统的关键。“趣味”是中国古典美学对古典艺术凝呈的主体心灵结构人格的审美概括。华夏民族“神与物游”的审美模式,决定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既缘于客体又超越客体,是对主体路履的和理想的心灵人格的反观和体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古典艺术的深层意蕴,就是主体心灵人格的内在美的物化结晶。中国古典艺术的这一内在精神,在书法、山水画、山水诗等民族特色浓厚的艺术式样中显得分外明著。中国古典美学依其个性,把物化于艺术的人格之美概括为“笔”“情”“墨”“神”“韵”“味”等,王国维将这些反映中国古典艺术的内在精神的美学范畴,统称之为“趣味”。“越味”与“材质”“第一形式”“美情”的差别,表明“古雅”的第一层次系统与第二层次系统,是在同一格局中并立的两大支柱。由“材质”“美情”到“趣味”、由第一层次系统到第二层次系统,说明王国维美学历程的基点在由西学走向中学中自觉融汇中西美学精神,也说明王国维对艺术形式的本体探求在自然与艺术的关系中,由外在自然走向内在心灵从而在心灵中寻追艺术的奥秘。
其实,王国维从中国古典美学中选择“古雅”这一审美范畴,以表达其特定的艺术审美内涵,与“古雅”之“第二形式”的第二层次系统有直接渊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沉淀于“古雅”范畴的审美内蕴,在第二层次系统得以集中体现。先从“雅”的本身义看:其一,雅的人格,即所谓“人格诚高”的“德性”。王国维深得中国古典美学、古典艺术突出人格意蕴之三昧,认为“苟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有也。”屈原、杜甫、陶潜、苏轼等“人格自足千克”,艺术也随之千古流芳。美学、艺术即人学。诚高人格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两大类型——伦理人格和自然人格,它们超越现实苦难而为人类的悲剧命运寻找解脱的宇宙情怀,就是“趣味”的渊源。其次,雅的修养,即“学问诚高”。“古雅”的欣赏、判断、创造是后天的、特殊的,其诸种能力由修养得之。艺术欣赏和创造的修养之诚与博,是“雅”的人格凝呈为“趣味”的中介。再次,雅的风格。“雅”的人格物化为“趣味”,寄托于特定的艺术形式,化作“雅”的艺术风格。“雅”的自然人格和伦理人格决定“雅”的风格或“趣味”有“恬雅”和“高雅”两种,前者淡泊玄澹,后者温柔敦厚。最后,雅的价值。“雅”的艺术使人们离功用利害,脱苦痛而得“暂时之和平”。“恬雅”之淡泊玄澹导人以与优美之情相似的“人心休息”而解脱,可称为“低度之优美”;“高雅”之温柔敦厚给人以宏壮之情的初步之“惊讶”达解脱,可称为“低度之宏壮”。“雅”的本身义,就是王国维“古雅”第二层次系统的美学内涵。“雅”的人格到“雅”的价值,终归指向情感痛苦的暂时解脱、命运悲剧的审美拯救。这是王国维为拯救人生悲剧命运而由哲学移诸美育、文学的内在机制所在,就是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论述了“古”对“雅”的引伸义或象征义。
“古”之遗物与“雅”的艺术在审美价值即人生价值上的沟通,是它作为“雅”的象征义或延伸义而缔结“古雅”美学范畴的内在机制。古代的遗物,甚至曾经以功利、实用、道德为目的的物品,诸如钟鼎、书法、秦砖汉瓦、典章书籍等,经历史的推移便与审美主体有了时空的距离,原有的功利、实用等目的被历史的运转和时空的阻隔而淡化即“雅化”,只以单纯的形式呈现于主体的审美视野,引导主体进入审美境界以得情感的纯粹愉悦。“古”之遗物,通“雅化”的机制,就与“雅”之艺术具有了同样的审美功能。
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沉积于“古雅”的审美意蕴与王国维“古雅”第二层次系统的审美意义的吻合,可把第二层次系统看作是“古雅”之“第二形式”的本身义,而第一层次系统因在审美价值、人生价值上与第二层次系统相通,可将它视为“古雅”之“第二形式”的延伸义或象征义。
“古雅”的第二层次系统,是西方美学的形式说与中国美学的趣味说的融汇,它作为有“趣味”的“形式”与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相符。他们分别把有“趣味”的形式与“有意味的形式”视为艺术的终极实在。“趣味”较之“材质”“第一形式”“美情”,与贝尔“意味”的距离几乎达到无间的程度。“趣味”和“意味”均源于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灵,衍生成艺术本体的形式内核。
王国维“古雅”的第二层次系统走向与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相合,逐步丧失了第一层次系统所强调的艺术与自然、生活、社会沟通的合理因素,而“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迷失和现实偏颇也在“古雅”之上逐渐显示出来。“古雅”的有“趣味”的“形式”对蕴含“材质”“第一形式”“美情”的“形式”的否定,将本可以萌生现实主义大潮的艺术创作导向中国传统美学的搜括内心的写意和表现。贝尔“有意味的形式”以匠意否定写实,以表现否定再现,以原始艺术的抽象性否定古典艺术的描述性,是西方现代艺术全面反叛古典艺术,从而扭转西方艺术乾坤的美学旗帜。在中国当代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中,随处可听到贝尔这面旗帜飘展的凛冽之声。而王国维的“古雅”呢,仍躺在被抹上政治批判阴影的故纸堆里酣睡!
王国维的古雅理论,是中西美学观念、艺术实践会冲、融汇的产物。正是如此,其中西美学融汇基点的西学和中学的差异,使“古雅”之“第二形式”在同一格局下具有两个几乎是内在否定的层次系统。其实,这种美学、艺术理论的相悖,是中西文化融汇的时代精神的凸现。若仅以第一层次系统的现实主义否定第二层次系统的表现主义,或以第二层次系统的人文精神否定第一层次系统的科学精神,都是片面的;若只揭示两个层次系统的内在矛盾而简单地抛弃,则更是有害。古雅理论与有意味的形式理论,这两朵中西美学观念、艺术操作融汇绽放的美学之花何等相似,但“有意味的形式”所受礼遇之“热”与“古雅”所受冷嘲之“惨”,该是启迪我们重新考虑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的时候了。
注释:
①以下王国维引言出自该文者,不另注。
②王国维《从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④以下克莱夫·贝尔的引文均出自该文,不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