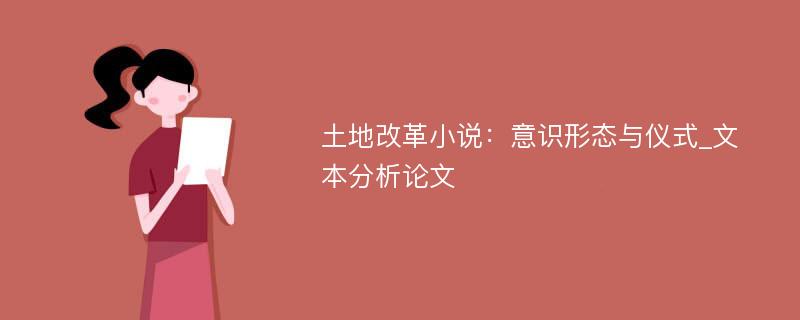
土改小说:意识形态与仪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仪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6)02-0064-05
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1] (P61)作为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另一方面,文学又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它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在文学研究中避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的错误。同时,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中,我们还会发现,意识形态的隐秘性和文学的情感性也形成了混生、互动的关系。
一、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
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实证主义的二元论传统。例如,认为文学只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社会现实因此具有了绝对的中心地位,它永远是真实的,而文学才有或真或假的可能性。因为文学总是第二位的,它是外在于我们的实践过程的,是无关宏旨的,虽然它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詹明信指责这种二元论的做法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坚守的有关客观性和绝对真理的基本概念”。这种观念下的文学自身“就成为意味深长的意识形态活动,成为某种具有近乎神学意味的资产阶级总体思维对确定性的渴望在美学上的对应之物”。[2] (P83)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理论,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意识形态从被社会存在机械决定的论调下解救出来,承认这种决定必须经过文学文本等中介的重要作用。文学文本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参与建构新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提出了新的文本概念,它“至少具有一种策略上的优势,可以从认识论和主客体对立中切入,将两者都中性化,并且可以把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自身作为读者的位置和作为阐释的精神行为上。”这样就可以将意识形态文本化,并且把它放回到特定的情境中,像人类学家那样,对原来作为“制度”的实践、习俗和礼仪进行解读,获得新的明晰性。[2] (P55-56)
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深刻地指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机制,并且文学经由价值观、意识形态,最终指向政治权力。他说:“我们迄今所揭示的,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3] (P34)巴利巴尔和马歇雷也指出:“文学不是虚构,不是描写真实的虚构形象……文学是通过某一复杂过程对某一特定现实的生产——这个现实并不是一个自治的现实,而是一个物质现实……因此,文学不是虚构,而是虚构的生产,确言之,是虚构效果的生产”。[4] (P47)
但是,伊格尔顿充分意识到文学的审美激情与权力、习俗既和谐又尴尬的矛盾关系:“审美自始就是一个矛盾的双面概念。一方面,它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力量,主体通过感性律动和兄弟情感而不是外加的律法联结成群体,每一个个体维护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但是和谐地融入社会。审美为中产阶级的政治追求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范式,典型地表现出新的自主和自决形式,改造了律法与欲望、道德与知识之间的关系,重铸了个体与集体的联结,以习俗、情感和怜悯为基础修正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审美是马克斯·霍克海默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权力插入被支配者的内心深处,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政治霸权方式。然而,如果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对身体快感和冲动加以殖民化而赋予它们以新意,那就很可能把它们突出和强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作为习俗、情感、自发的冲动的审美完全可以护卫政治统治,但是这些现象令人尴尬地接近激情、想象、感觉,而它们却并不总是配合得很好。”[5] (P52-53)
为了进一步分析文学文本中这些盘根错节的意识形态关系,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六个基本操作范畴:1、一般生产方式。2、文学生产方式。3、一般意识形态。4、作者意识形态。5、美学意识形态。6、文本。其中“一般生产方式”指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由文学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组成。每一文本都以其特定的规约暗示它应如何被消费,它如何、由谁及为谁而生产意识形态的密码。“一般意识形态”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括伦理价值话语、艺术表现话语、宗教信仰话语等。“作者意识形态”是指作者以特定方式被置入一般意识形态之内所产生的后果。“美学意识形态”是指文学理论、批评、实践、传统、规约、文类、技巧等。[6] (P236-237)
文学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之下的生产,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文学与意识形态不是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意识形态也是纷纭纠缠的“场”。例如丁玲,她的写作就是自觉地遵循意识形态的轨道的。她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7] (前言)因此,有学者认为,丁玲的写作是“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缺失”。[8]
然而,在文学作品内部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是很困难的,因为,一方面是文本内部的复调性,各种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隐身性,它总是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现,使人难以察觉,它实际上往往以无意识的形式运作。因此,对文本和意识形态两者,都必须采用阿尔都塞的“征候式阅读”方法:“对一个作品进行征候式阅读,就是要进行双重阅读:首先对显性文本进行阅读,然后,通过显性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失误、歪曲之处、缄默和在隐(这些都是某个问题要被引发出来的征候),产生隐性文本并对隐性文本进行阅读。”[9] (P161)必须摈弃对作品统一性的迷信。[9] (P162)
二、文本意识形态与仪式
文本意识形态不同于作者意识形态,它是文学文本以叙事的方式所呈示的观念系统和符号秩序。作为叙事的作品,文学文本所描写(深描)的对象主要是人的行为,并且往往是程式化了的。这种行为在人类学中称为仪式,它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0] (P1)在现代,叙事文体的主要形式是小说,而在古代则是神话。仪式与神话都是神圣叙事,只是在形式上,前者是行为,后者是言语。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暗示了神话与仪式之间的同源关系。而神话与仪式又通过象征,共同指向符号秩序、信仰或意识形态。正如利奥塔所指出的那样:
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讲述了某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业绩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的牵涉到现存社会的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11] (P43)
叙事与社会行动中的仪式是互为表里、互相循环的。它们的“共谋”达成了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自然化和崇高化。福柯早就洞悉了体制在话语中的“自然化”与在仪式中的“崇高化”之间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以求从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须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可怖和邪恶之处。体制对于这一常有的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似乎是为了使其在远处亦能更为容易地辨认。[12] (P2)
而心理学家荣格把叙事、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混生、互渗、同构,并进一步归结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他指出:“个体无意识的绝大部分由‘情结’所组成,而集体无意识主要是由‘原型’所组成的……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相符;在比较宗教学领域中,胡伯特(Hubert)和毛斯(Mauss)把它们定义为‘想象的范畴’。”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它们是本能行为的模式”。[13] (P104-105)
韦伯以为现代社会中神话、宗教、礼仪和传统都已经衰败,但是,实际上,现代世界中存在着“对神话的渴望”,神话已经侵入了看似理性的观念系统。[14] (P124)意识形态也是与礼仪、典礼等混生互渗的观念系统之一。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仪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逻辑,人类对象征和象征体系的依赖,决定着他的生存能力,只有通过某种仪式形式,动机(motivations)与情绪(moods)及关于存在秩序的一般观念才能相互支撑和协同。生存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只有通过象征形式才能融合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15] (P101-143)意识形态也同样如此,它是通过象征形式来表现意义的一种模式。它并不会凭空凌云,而是深入到人类的“礼仪、神话、戏剧、人际交往、俗谚俚语”等符号之中。[16](P132)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往往也是通过仪式或者仪式化的描写进行再生产的。不过,在文学的叙事中,意识形态与意识的共通性与其说是“本能行为的模式”,不如说是情感上的激越或者温柔。无论是统治的还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情感的“征用”如出一辙:
仪式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人们从他们所参与的仪式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统治者努力设计和利用仪式动员民众的情感以支持其合法性,并激发起群众对其政策的热情。而作为象征,仪式对于革命群体也同样是重要的,革命同样需要引发强烈的情感以动员民众造反(David Kertzer,1988)。[10] (P2)
不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实践,我们似乎是通过相反的路向和人类学汇合的。文学批评历来都不缺乏宏大叙事,不缺乏豪言壮语,只是这种豪言壮语日益叫人生厌,变得“危乎高哉”了,对小说叙事中仪式的发现,使批评的“脚”落在了实地。而另一方面,人类学又在反思自己过于“脚踏实地”的传统,过于沉湎于文化遗产、原始部落的考察。人类学正力图超越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小传统的局限,返身省视现代社会,“通过仪式的研究,观照现代政治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强有力的进入及如何进入的过程,可以使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10] (P5)
三、土改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和仪式
人类学通常将仪式分为3种:1、一年的例行节日和活动。2、“通过礼仪”或人生礼仪,如诞生、命名、成人、结婚、丧葬等。3、状态礼仪。有学者又把“通过礼仪”细分为三个阶段:分离礼仪(以使人离开原来的地位和状态为目的)、过渡礼仪(以实现向新的地位和状态的过渡为目的)和统合礼仪(以使过渡到新地位和状态的人再次进入社会为目的)。[17] (P157-158)
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进行意识形态生产时,就有类似通过仪式三阶段的情形。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和初次发表的时代,有两种相互抗衡的“一般意识形态”,即国民党政府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代表的“革命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双方主要纠结于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秩序。作者创作时的意识形态意图是,让农民完成一次意识形态上的“成人仪式”。这是一种“革命的启蒙”——使“落后的”农民摆脱蒙昧的状态,进而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工作队在暖水屯的两次群众大会,是作品中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中心仪式。在革命以前的乡村社会中,仪式化的大型场合是非常少的,宗族会议可能是最重要的,此外就是求神拜佛、红白喜事。工作队召集会议本身就是一种事件。会议不是单纯的人群的聚合,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社会空间的建构仪式。工作队在暖水屯召集的两次群众大会,实际上就是革命意识形态对乡村意识形态强行介入、颠覆国家的地主意识形态、重新整合乡村意识形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格局的重要仪式。仪式与典礼不同,仪式几乎总是伴随着状态转换;而典礼是一种延续,是确认性的,是认可规范、秩序的方法。[18] (P515)同时,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也应该看到,仪式是可以转变为典礼的。当一种新革命意识形态秩序得以确立、取得主导地位时,原来具有反叛性的诉苦、斗争大会仪式就会转化为没有冲突和悬念的表演典礼,变为对新秩序的欣赏和陶醉。
暖水屯的第一次群众大会由年轻的农会主任程仁主持,但是,程仁的打扮和举止,显然还不能适应一个在公众面前演讲的领导者的角色要求。他在旧的权力场域(field)中已经被规训出“沉默”和“腼腆”的惯习(habitus),这是结构化的权力位置空间在他身体上的渗透和积淀。[19] (P19-24)
在这个会议中,程仁连接了革命意识形态和乡村意识形态。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过去国家对乡村的统治,往往要借助于生活在农村的乡绅来进行。现在,革命的意识形态则是由农村中某个能干的中青年农民来承载。一方面,他们思想意识比较先进,并且苦大仇深,有革命的积极性,热切地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地方背景,理解地方的习俗,有农民的意识形态,易于被农民们所接受。他们在内心把革命和农民进行“化合”反应,一方面避免革命“硬来”,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又防止农民“乱来”,不讲政策,自私自利。
革命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乡村的,它和“草根社会”的原有意识形态秩序不尽相同,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一些缝隙。然而,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原因错误地归到一位知识分子——会议上掌握主要话语权的工作队负责人“文采同志”身上。文采同志在这个场合固然没有贴近农民的语言,感到失语的痛苦。但是,作者似乎快意于他的窘迫,以此调侃甚至揶揄知识分子。作者陷入了“群众语言”的拜物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她还没有像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那样,让方言俚语在叙述语言中泛滥成灾。“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0] (P443)革命的话语必然不同于农民的话语。正因为如此,在暖水屯,才需要程仁、张逸民等“积极分子”作为意识形态的翻译者和桥梁。
我们大概不能天真地相信作品中关于农民高涨的积极性的说法。从政治局势来说,当时“暖水屯”一带的形势是“内战逼人”,中秋节刚过,工作队即开始撤退,“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7] (重印前言)从中共中央的政策来看,“暖水屯”实际上并不具备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在革命政权不是很稳固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本来就有冒进之嫌。所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的确不是很高。他们更倾向于服从旧的秩序。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在这里,我们的确注意到被压迫集团和它的主人一起全力投入于合法化过程,说服自己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就应该受苦,别人也如此,别的选择可能更糟糕。被压迫者进行的这种合理化可能不会扩大他们的利益,但肯定会增进统治者的利益。”[21] (P88)因此才会有下面的情形:
他们大半听不懂,有些人却只好说:“人家有才学,讲得多好呀!”不过,慢慢的也感觉得无力支持他们疲乏的身体了。由于白天的劳动,又加上长时间的兴奋过度,人们都眼皮涩重,上边的垂下来了,又用力往上睁,旁边的人也拿肘子去碰他。于是有些人悄悄地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坐到后边的台阶上,手放到膝头上,张着嘴睡着了。[7] (P82)
接下来,村干部对要退席的农民说:“你走,你走!门口还有民兵呢。”一个小民兵也嚷:“谁吵就把谁绑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只是由于文采同志说得不精彩和会议时间太长(“六个钟头的会”)造成的,但是,会场上的强迫暗示我们,新意识形态之于农民们,还有待灌输,有待产生和塑型。政权的更迭也许在一夜之间可以实现,但是,意识形态却是柔性的、绵延的,它的演替只能是渐进的。
在另一部描写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工作队的萧队长对意识形态转换的困难认识得也很清楚:
群众并不是黄蒿,划一根洋火就能点起漫天的大火,没有这样容易的事,至少在现在。我们来了几天呢?通起来才四天四宿,而农民却被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了好几千年,好几千年呀,同志![22] (第一部第8节)
正因为工作队认识到了意识形态转换的艰巨性,他们采用了更为高明和有效的方法,重建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态,那就是诉诸情感的“算账”和“诉苦”。算账和诉苦这两种新演化出来的仪式,使农民从“自为的”日常状态中觉醒过来,启发他们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再解读,“发现”或者说生产被压迫的“事实”。农民们最强烈的情绪——复仇被动员了起来。《暴风骤雨》写道:
刘胜起身走到台前,对大伙说:“韩老六是大伙的仇人,工作队听到了屯子里人诉苦,都说韩老六压迫了大伙,剥削了大伙,昨儿下晚把他叫到工作队,今儿咱们要跟他说道理,算细账。”说得很短,结尾他说:“你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大伙别怕。”
下面,李振江在人群里说道:“对,大伙别怕。”……[22] (第一部第8节)
更新的也更加激烈的仪式——“斗争会”与之相伴相生。斗争会发明了“喊口号”的技术,它把个人的情感扩散为集体的,又把集体的情感灌输给个人,同时又产生剧场中“叫好”的效果,把观众变成了演员。斗争会,同时还是对地主的羞辱仪式(殴打、谩骂、丑化都是少不了的技术),[10] (372)使地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臣民,完成乡村的权力关系的倒置。《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斗争会的场面是完全戏剧化的:
“你还想吓唬人!不行!这台上没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给全村父老跪下!”他用力把钱文贵一推,底下有人响应着他:“跪下!跪下!”左右两个民兵一按,钱文贵矮下去了,他规规矩矩地跪着。于是人群的气焰高起来了,群众猛然得势,于是又骚动起来,有一个小孩声音也嚷:“戴高帽子!戴高帽子!”……高的纸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7] (P296-297)
对地主的斗争和地主公开认罪的仪式成为热闹的“公共景观”和公开表演的“戏剧”。[23] (P8-9)这种“斗争”通过制造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作用于肉体,是一种身体暴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仪式又作用于精神,成为传播表象和符号的游戏。[23] (P111)又如,钱文贵的认罪状(“保状”)中称村民为“诸亲好友”,遭到斥骂,又改称“穷大爷”,最后终于找到了“翻身大爷”这个更加“贴切”的符号,重新标示了新的政治地形图。此前多次描写的佃农向地主讨要“红契”(地契)的运动,初看起来也叫人费解,因为革命政权完全可以直接废除旧的地契,另颁新的地契。事实上,小说的结尾也正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符号斗争,地契这个符号集中地代表了旧的土地所有制度,所以才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只有让地主交出地契,才能表明土地革命在符号上的“名正言顺”。
总之,在文学的叙事之中,意识形态、仪式互为混生、渗透关系,同时它们之间也会显现缝隙,这是任何一部作品都难以避免的。或者,有时这种效果就是作者刻意追求的。文学作品因此也就有了反复解读的魅力和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