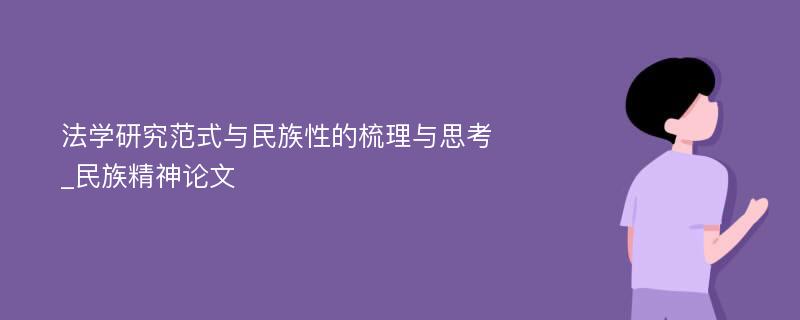
法律与民族性格———种法律研究范式的梳理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律论文,范式论文,性格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文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205(2010)06-0003-(009)
一、导论
自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1]255民族性格差异问题开始被那些游走于各个民族之间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官等人士敏锐地观察和感受到,随后又引起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领域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和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等学科中,民族性格(或曰国民性)乃是其学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范畴。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看来,正像一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性格一样,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的群体性格。在《文化模式》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普埃布罗人、夸扣特尔人和多布人三个原始民族的文化和性格,并把这三个民族的文化和性格分别称为“阿波罗型”、“狄奥尼斯型”、“妄想或偏执狂型”。她认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2]36在人类学、心理学那里,民族性格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反复出现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经常把民族性格范畴作为分析或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3]476-477[4]2-4例如,在理解民族的概念时,学者们都会强调民族性格或共同心理这一重要因素。斯大林曾给民族下定义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5]64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将民族性格问题引入到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思考之中,把民族性格的改造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运动。[6]
在法学领域,从民族性格出发考察、解析某一民族法律的独特性或不同民族法律的差异性,乃是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而为的事情。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孟德斯鸠、黑格尔、萨维尼等人都讨论过法律与民族性格(精神)问题,认识到它对法律所可能产生的多重影响。托克维尔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法律与民族性格问题,却非常成功地从美国人性格的角度揭示了美国民主和法治背后深厚的心理文化基础。20世纪以来,以民族性格为根据解释不同民族法律的差异性乃是法学领域、特别是比较法和法律史领域一种常见的学术进路。在法学领域之外,一些专门研究民族性格的学者也在讨论某个民族的性格时经常论及民族性格对国民政治法律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本文把近代以来法学和非法学领域所存在的这种法律研究或解释模式称为民族性格范式,并试图在对这一研究范式及其应用情况的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这一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及其限度进行简要的评判。
二、民族性格范式的理论奠基
在18、19世纪的欧洲,尽管当时的思想家们经常高谈阔论各个民族的不同性格,但在核心概念的使用上他们仍偏好使用“民族精神”这一术语。特别是在当时的德国,民族精神一度成为整个思想界一个相当时髦的概念,并被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精神学说”。[7]5但从术语的日常使用上,当时的思想家往往在交叉、甚至等值的意义上使用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意识等术语。因此,本文把他们关于法律与民族精神的论述视为民族性格范式的理论奠基工作。
孟德斯鸠是最早对法律与民族精神(性格)的关系进行专题性讨论的思想家,可以说是法律研究中的民族性格范式的开创者。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描述了东西方各个民族的性格,诸如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英国人、西班牙人等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气候是决定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在法律与民族精神(性格)的关系上,孟德斯鸠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必须顺应或符合民族精神(性格)。他指出,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职责,因为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他举例说,假如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性喜交际,心胸豁达,热爱生活,有风趣,并善于表达思想,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企图用法律去束缚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免抑制他们的品德。[8]305他也反对用法律去改变与民族性格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法律是一个立法者所创立的特定制度,而风俗习惯则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一般制度。因此,不能用法律去改变风俗习惯。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专横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用风俗习惯来改变风俗习惯。[8]310
不过,孟德斯鸠也意识到,法律反过来也有助于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形成。他认为,虽然一个民族的性格、风格、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而产生的,但也同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英国为个案分析了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对英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他指出,在这一国家里,法律的制定并不厚甲而薄乙,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君主,所以这个国家的人与其说是同胞,毋宁说是同盟者。政制让每一个人都参与政事的管理,使每一个人都有政治的兴趣,所以他们许多的言谈都是围绕着政治的。[8]328
在民族精神一语曾经风行一时的德国,黑格尔、萨维尼等人都论述到了法律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强调民族精神对法律的决定性影响。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民族精神是人类向世界精神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贯穿于民族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指出,民族的宗教、政体、伦理、立法、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9]87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分析了民族精神对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影响。他认为,民族精神贯串于一个国家所有法律之中,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取决于民族精神。他举例说,拿破仑所给予西班牙人的国家制度,比他们以前所有的更为合乎理性,但对他们来说则是格格不入的,结果碰了钉子而回头。[10]291由此他强调,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否则国家制度只能在外部存在着,而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10]291-292
在反自然法学的过程中,萨维尼不仅深化了法律与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而且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法学的中心舞台。在我看来,萨维尼对民族精神(性格)与法律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法律从一产生起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是由民族精神所决定的。萨维尼提出,就像语言、行为方式和政制一样,法律从有史可查的远古时代开始就已秉有为一定民族所固有的特性。而且,法律、语言、行为方式等现象并非各自孤立存在的,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倾向的具体表象。将其联结一体的,乃是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即民族精神。[11]7第二,法律与民族的存在和性格的有机联系同样展现于法律的历史发展过程。萨维尼指出,法律就像语言一样,并无决然断裂的时刻,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之中。此种发展,如同其最初的情形,遵循同一内在必然规律。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11]9
三、托克维尔对民族性格范式的推进
法律人出身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831-1832年期间到美国进行为期9个月的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部广为流传的不朽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不仅是一部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研究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经典著作。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外国人解读美国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就连以国民性研究著称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称赞,托克维尔是一位聪明而敏锐的观察家。[12]32-33不过,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仅在少数几个地方使用过国民性或民族性格一词。在考察英裔美国人的来源时,他认为民族的偏见、习惯和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构成了所谓的民族性格。在分析多数暴政以及陪审制对美国人的影响时,他几次使用了“国民性”一词。例如,他认为,陪审制度对美国人国民性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影响是,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种思维习惯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13]316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书中更为经常使用的一个与国民性较为接近的词语是“民情(moeurs)”。托克维尔对民情做过多种解释:(1)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13]332(2)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13]354(3)人们的习俗、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总体。[13]357-358托克维尔反复强调民情的重要性,认为民情是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的因素。[13]354-359
或许受那个时代学术风尚的影响,托克维尔也习惯于用××精神来概括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通过与法国人、英国人、墨西哥人等相比较,托克维尔相当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美国人(特别是英裔美国人)的诸多精神,诸如宗教精神、爱国精神、自由精神、乡镇精神、公共精神、共和精神等。作为一个法律人,托克维尔敏锐地认识到国民性格与政治法律制度、法律家阶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花了很多的笔墨来分析国民性格与各种制度、法律家阶层之间的关系。经过对托克维尔的相关论述进行仔细的梳理之后,我把他的核心观点与分析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国民性格是支撑政治法律制度的心理文化基础。对于美国的乡镇自治制度,托克维尔极为强调支持和鼓励该制度的乡镇精神。[13]74这种乡镇精神表现为乡镇居民依恋、热爱乡镇生活,积极参与乡镇管理。托克维尔分析说,乡镇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13]213对于美国的结社自由制度,托克维尔则试图从美国人的自治精神加以解释。托克维尔强调,美国人相信这一学说,即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13]72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困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即使面临某些公共问题时,人们也愿意通过自愿组织或结社的方式以私人力量加以解决。[13]213托克维尔描述说,美国人不论年龄有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刻刻在组织社团。他把法国、英国、美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自己组织社团。[14]635-636
其二,政治法律制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国民性格。在讨论美国社会从民主制度获得的益处时,他分析了民主对美国人公共精神、权利观念、法律意识形成的作用。[13]263-276对美国人的公共精神,托克维尔感到仰慕不已。他描述说,美国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13]105他追问道,每个人为什么象关心自己的事业那样关心本镇、本县和本州的事业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社会的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3]270也就是说,民主激发出了美国人的公共精神。在论及权利观念时,托克维尔提出,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没有权利观念。但是,用什么办法能使人们养成权利观念呢?这就是让所有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在美国,由于人人都有自己的财产需要保护,所以人人原则上都承认财产权。成年人都有政治权利,所以他们把政治权利看得很高。托克维尔指出,正如财产的分配使成年人都具有财产权观念一样,民主政府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每个公民。关于美国人对法律的尊重,他指出,美国所有的阶级都对国家的现行法律表示出巨大的信任,以一种爱父母的情感对待现行法律。不管一项法律如何叫人恼火,美国的居民都容易服从。托克维尔分析原因说,这不仅是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人的作品,而且因为这项立法也是本人的作品。他们把这项立法看成是一份契约,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的参加者。[13]275-276
其三,强大而有权威的法律家阶层能够型塑国民性格。在考察美国是如何克制多数的暴政时,托克维尔对美国法律家阶层的作用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根据他的分析,美国法律家阶层不仅是克制民主弊端的最强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把法律思维习惯带给全体人民。关于前者,托克维尔指出,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律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律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谨慎的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13]309关于后者他解释说,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律家,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陪审制度更把这种习惯推广到一切阶级。这样,法律家的精神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了学校和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最低阶层,使全体人民都沾染上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趣味。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所有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13]310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托克维尔的美国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孟德斯鸠所开创的民族性格范式。特别是他关于法律家阶层对国民性格的影响的分析,构成了他在法律与民族性格研究上的独特理论贡献。
从170多年前托克维尔对美国人国民性格的研究,我们也能发现美国法律制度和法治模式成熟发达的重要原因。和英国、法国等欧洲老牌帝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西方国家。从1607年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到弗吉尼亚算起,至今不过是400年的光阴。但是,美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发展出一套富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和一种堪称典范的法治模式,并在二战以后一跃成为西方法的精神领袖。[15]美国法律制度和法治模式不仅被许多非西方国家大量借鉴或移植,也被欧洲国家广为效仿或接受。[16]如果要分析美国法律制度和法治成熟发达的原因,国民性格无疑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正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人身上的那些国民性格,如自治精神、公共精神、共和精神、权利观念、契约观念、法律意识等,构成了美国法治最为根深蒂固和牢不可破的精神文化基因。
四、比较法和法律史对民族性格范式的运用
进入到20世纪以后,比较法和法律史成为民族性格范式在法学领域应用的最主要场所。比较法学者和法律史学者纷纷从民族性格角度解释不同民族在法律思维方式、制定法风格、法律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一)民族性格对法律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比较法学者看来,作为一个民族的法律精英,法律家的思维方式必然深受本民族的思维习惯、风格的影响。即使同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西方各民族,也在思维方式、习惯和风格上表现出各种具体的差异,从而导致法律家的法律思维方式各有特色。苏格兰著名法官库珀曾在一篇论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的文章中分析了这两大法系在法律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他说,大陆法体系不同于普通法体系,犹如理性主义不同于经验主义,或演绎推理不同于归纳推理一样。大陆法法律家的推理自然地从原则到个案,普通法法律家则从个案到原则。大陆法法律家坚信三段论法,而普通法法律家则信奉先例;当遇到新问题时,前者暗自思量:“这次我们该怎么办?”而后者则大声询问:“上次我们是怎么办的?”前者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思考问题,后者则从救济的角度思考问题。前者主要关心法律规则的原理,而后者主要关心法律规则的谱系。前者的天性是追求体系化,而后者的工作规则是现场解决。[17]470-471
很多西方学者都习惯于从民族的性格和刻板印象那里寻求对普通法与大陆法法律家思维方式的差异的解释。关于英国人的一种刻板印象是,英国人习惯于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英格兰人解决问题的典型方法不是使用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像一条寻找地下菌块的狗那样绕着它嗅,确定关键所在以后再寻找答案。这种方法是经验主义的,符合实际的,只相信常识的。”[18]209一则英谚说:“不到桥边不想桥对面的事。”早在19世纪末,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以此来解释英国的判例法传统:英国人是经验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只有体验过的东西(经验)才有力量。因此,理论上的先验论和抽象的规范对他们没有什么力量。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个数百年来生活在海洋上和航船上的民族,英国人确信生活的航程完全不同于计划的预见。这种确信使他们觉得,同制定法相对立的判例法对英国人是适宜的。[19]133-134
在20世纪上半叶,法学家庞德从英国人的心态来解释普通法学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普通法法律家富有特性的学说、思想和技术的背后,有一种重要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习惯于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观察事物,相信的是经验而不是抽象概念;宁可在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每个案件中似乎正义所要求的从一个案件到下一个案件谨慎地行进,而不是事事回头求助假设的一般概念;不指望从被一般公式化了的命题中演绎出面前案件的判决……这种心态根源于那种根深蒂固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习惯,即当情况发生时才处理,而不是用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公式去预想情况”。[19]158
在20世纪下半叶,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也认为,欧洲大陆法与英美法在法律思维方法上的区别根源于国民性格不同。欧洲大陆人喜欢事先做计划或规划,因而在法律方面倾向于拟定抽象的规范或体系。他们带着先验的观念走向生活,并且在演绎思维中发挥着其特有的才能。而英国人却是“即席创作诗人”,他们只是在实际生活要求自己作出直接判断时,才开始判断。[19]133由于英国人注重实际的经验主义和从案件到案件循序渐进的习惯,他们把通过制定适用于整个生活领域的一般法规来预先规定相似案件的结果,看作是危险的和不自然的,而奉行的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信条。[19]468
(二)民族性格对制定法风格的影响
比较法学者对不同国家的制定法——特别是法典——的比较研究揭示出,不同国家的制定法在行文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制定法风格的形成,与民族的精神气质、思维习性、语言风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与单个文学家、艺术家创作的作品相比,国家制定法作为集体创作的作品,更能体现民族的精神气质、思维习性、语言风格。茨威格特和克茨对《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这两部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民法典的风格进行了比较。《法国民法典》文体简洁凝练,行文流畅明快,语言通俗易懂,堪称语言文体的杰作。法国大文豪司汤达为了获得其韵调上的语感,每天都要读几段民法典条文。另一位作家保尔·瓦莱利则称民法典为“法国最伟大的文学著作”。《法国民法典》的通俗性,使其深受法国民众的喜爱。[19]169
与《法国民法典》相反,《德国民法典》一向以精确的概念、抽象的语言、严谨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而著称。后者被称为“优良的法律计算机”、“不寻常的精巧的金缕玉衣”、“具有最精确、最富有法律逻辑语言的私法典”。但其令人望而生畏的官牍文体、复杂的句子结构以及古拉丁语的使用,不仅法律的门外汉,甚至外国的法律专家,都难以理解。在德国,没有任何人会像法国人那样对他本国的民法典怀有热爱或心心相通的情感。即使是德国的法律家以这部法典那无可否认的技术质量而感到骄傲,亦不过是一种冷漠的、几乎是迫不得已的承认而已。[19]268-269《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的这种差异导源于德国人追求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精神气质。茨威格特和克茨指出,德国的理性法学者总是以严谨的、逻辑数学的演绎从最一般的、有牢固理性法基础的基本原理中获得最具体的个别法律规定,以至于其法律制度就像是完全艺术化分类的、系统而明确设计的建筑。[19]254
郝铁川分析了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制定法的影响。模糊思维方式导致制定法过于笼统、原则。模糊思维的特点是,用词多歧义,没有明确界说;立辞多独断,缺乏详细的论证。这种模糊思维对当今中国立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文字表述过于笼统,用词含糊、不明确,用词不合逻辑,用语有失协调统一。崇尚语言文字简约的思维方式导致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方针,法律法规的条文数量少,法律规定过于简单,法律的可操作性差。[20]213-226
(三)民族性格对法律发展方式的影响
在比较法学者看来,各个民族的法律发展的过程和方式,必然要受到长期积淀而成的民族性格和集体偏好的影响。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法国政体和宪法变动之频繁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法国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次革命、政变、风暴,产生过一个君主国、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法国共颁布过15部宪法,颁布的年份分别是:1791、1793、1795、1799、1802、1804、1814、1815、1830、1848、1852、1875、1940、1946、1958。法国史学家戈德肖指出:“法国无疑是经历宪法数最多的国家:在180年间总共实行过15部宪法,即平均每12年一部”①。法国宪法不仅更替频繁,而且内容多变。虽然大部分宪法名义上都是对前一部宪法的修改,但实际上两部宪法在体系和内容上差异甚大,往往给人以面目全非的印象。[21]99-100德朗德尔认为,“从1789年到1871年,法国可以说是世界惟一的宪法实验场。八十一年中,它实行过多种多样的政治体制,这在任何其他民族的历史上是找不到的。②”学者马胜利认为,法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频繁变动与法兰西民族的激进主义传统相关。与英美人不同,法国人似乎永远不满足现状,热衷于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愿望。法国是革命的摇篮。1789、1830、1848、1871年革命构成了法国的革命传统。直到20世纪,革命依然是许多法国人,如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毛主义者的理想。[22]112-113
英国法则代表了一种与法国法截然不同的法律发展方式。正如何勤华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法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持续性、渐进性等特征。[23]67-69保守性主要表现为在中世纪时期形成的某些古老的法律概念、分类和制度仍然延续至今,如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类。持续性表现为英国法一直按照自身的传统和逻辑自主发展,没有受到明显的外来干扰。渐进性表现为英国法一直是缓慢而平稳地向前发展,没有经历过法国法那样的剧烈变化。英国法的这些特点在其宪法上充分展现出来。作为一种不成文的宪法,英国宪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缓慢地生长和累积起来的,由一系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宪法性文件和惯例构成。中世纪时期的一些宪法性文件或惯例在今天仍有效力,如1215年《大宪章》。在英国思想家柏克看来,英国宪法的种种优点来源于其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吸收了许多人、许多代的智慧和经验。他唯恐被鼓动家、尤其是不慎重的理论家们的任性和激烈的不妥协态度所毁坏。[24]1正如有的论者所分析的那样,英国法的这种发展方式无疑与英格兰民族的保守主义性格有着直接关系。[25]英格兰民族是一个尊重传统、比较保守的民族,英国也是世界上的保守主义思想传统的发源地和根据地。
五、非法学学者对民族性格范式的运用
在法学领域以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很多学者,特别是民族性格研究者,也经常运用民族性格范式来解释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本部分以林语堂关于中国人民族性格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人民族性格与日本法的分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一)林语堂对中国人性格与传统法文化的分析
自近代以来,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的传教士)和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特殊性,写下了大量研究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文章或著作③。其中,中国学者林语堂于1934年用英文所著的《吾国与吾民》是一部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Buck)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称赞它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26]8在该书中,他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生活的诸多特征。例如,他把中国人的性格概括为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八项。林语堂在描绘中国人性格和心灵的特征时,也论及到了中国人性格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联性。
一方面,林语堂看到了民族性格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行为模式、纠纷解决方式的深刻影响。这体现在他对遇事忍耐、注重情理、乡属精神等性格的社会影响的分析上。关于遇事忍耐的性格,林语堂指出,中国人的忍耐有如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比。忍耐的品质是整个民族适应周围条件的结果,如过分稠密的人口和经济上的压力导致人们只有狭小的生存空间;也是家庭制度的产物,因为大家庭是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在林语堂看来,这种品质对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意识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说,这种品质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也是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已经被提前征收了今后三十年的赋税,但是他们除了私下在家里发出几声别人似能听见又听不见的咒骂外,再无任何有力的反抗。他批评说,我们屈服于暴政和敲诈勒索,犹如小鱼投入大鱼之口。或许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小一些,我们的苦难就会少一些。然而这种对污辱的承受力被赋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伦理学谆谆教诲为做人的重要美德。[26]59
关于注重情理的性格,他认为中国人的心灵不同于西方人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更重视情理,而西方人更重视逻辑。对西方人来讲,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得通,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讲,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还必须合乎人情。而且,合乎人情比合乎逻辑更为重要。[26]100-101林语堂认为,这种追求情理的精神与对逻辑的反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是一种机械的东西,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他说,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不可能。与其受治于法治政府,中国人宁愿赞成贤人政府,因为贤人政府比较近人情和有伸缩性。[26]121-122
关于乡属精神④,林语堂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人的基层生活。这和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人基层生活时所说的“乡镇精神”形成鲜明对照。两个术语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所指迥然有别。林语堂认为,乡属精神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从热爱自己的家庭,发展到热爱自己的宗族,再到热爱生我养我的土地,于是一种乡土之情油然而生。这种乡土之情可称为“同乡观念”。这种观念将来自同一村镇、地区、省市的人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建立起学校、商会等公共事业,从而使一定程度的社会合作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乡属精神使得本乡的人民发展出一种村镇自治体。不过,这种村镇自治和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的乡镇自治很不一样,它并没有由居民选出来的市长或议员,而是一种年长者和绅士们的统治。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长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的依据并不单单是公理,而是人情与公理兼顾。没有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使公正的判断更为可能,而判断公正就使人心服。95%的乡村纠纷都由长者们解决的。民众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衙门,常以平生未进过衙门上过公堂而自夸。只有当遇到刑事案件或分家析产纠纷,双方为了面子一决雌雄时,才会迫不得已把案子送往衙门。[26]207-208,[27]175-177
另一方面,林语堂也认识到法律制度在民族性格形成中的作用。这体现在他对中国人消极避世性格的成因分析上。很多研究中国人性格的学者都批评说,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不愿意参与公共事业。林语堂以两个不同的母亲对儿子的叮嘱揭示了中国人的消极避世性格。在一部英文经典小说里,母亲对儿子的嘱咐是:“抬头挺胸,爽直地回答别人的问话”;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告诫是,“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林语堂认为,消极避世并不是中国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说,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到了25至30岁,他们则变得聪明起来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消极避世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或者说爱管闲事,容易惹祸上身。[26]60-61,[27]41-42
(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性格与日本法的分析
日本国内外研究日本人民族性格的著作很多,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在二战快要结束之前,她受美国政府之委托,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开始研究日本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由于战争仍在进行,她无法采用文化人类学家常用的实地考察方法,而是依靠访问日裔美国人、观看日本的影片戏剧、查阅日本研究文献等方式进行研究。她的研究,不仅为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成功地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学者祖文江孝男称赞说:“尽管本尼迪克特一次也没有来过日本,然而,她却巧妙确切地抓住了日本自己并没有察觉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许多特点。”[28]120尽管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很少直接论述法律与民族性格的关系,但她对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分析涉及到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而且,千叶正士等学者关于日本法和法律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深受本尼迪克特的影响。他曾把本尼迪克特所描述的几项国民意识和观念确定为日本的非官方法律原理。[29]78-81
关于尊崇天皇的意识,本尼迪克特认为,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令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的态度。尽管在封建时代,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在日本的现代体制下,天皇也无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但天皇却是所有日本人尊崇和拥戴的对象。她在《菊与刀》一书引用日本战俘的话来揭示日本人的这种观念。对他们来说,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12]23-24二战后日本的情况表明此类说法不假。千叶正士把天皇崇拜确立为日本非官方法律原理之一,而且认为天皇崇拜的影响不限于精神领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官方法律原理。天皇仍然占据着一个宪法职位,尽管只是作为国家和民族团结的象征(《日本宪法》第1条)。[29]105
关于情义观念,本尼迪克特指出,情义是日本所独有的范畴,是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概念和准则,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情义又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观念。她试图通过区分“情义”与“义务”来解释情义的含义。义务是指个人对直系亲属(父母、祖先、子女)和对国家(天皇、法律、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义务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理应履行的。情义则是指个人因处于某种关系或环境之下而不得不尽的各种责任,例如,从某人处得到恩惠,必须报答恩情。本尼迪克特把情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包括对姻亲属、上司、同事、恩人等应尽的责任;一类是对名誉的情义,即为洗刷自己的污名或确立自己的声誉而应做的事情,如自杀、复仇。[12]66与本尼迪克特的分析相呼应,千叶正士把情义视为是日本的非官方法律原理,把情义关系理解为日本的非官方法。他分析说,由于情义给日本人之间如此频繁的礼物交换提供了最主要的理由,因此当公务员从与他们有特殊关系的人那里接受礼物时,只要是根据“社会常识”礼物被衡量为是合乎情理的,就不会认定为是受贿行为。[29]112-113
关于等级观念,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对秩序、特级制的信赖,有如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⑤。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日本人的家庭生活的核心。每个日本人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再将其所学的这种习惯运用到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12]31-40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到惩罚。[12]66这种等级制习惯是与集团意识、各安其分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在其所属的集团中都有确定的位置,并要根据这种位置的角色要求做出行为。千叶正士也把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和习惯概括为一种非官方法律原理,即“地位秩序”原理。[29]101、104-105
关于耻感意识,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概括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并对这两种文化的区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第一,在罪感文化中,有过错的人可以通过忏悔、赎罪等方式减轻内心重负,获得心灵解脱。而在耻感文化中,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得到解脱。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自寻烦恼。第二,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罪感文化则依靠内心的服罪来做善行。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如受到外人的嘲笑、讥讽、排斥,或者至少要感觉到有外在地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第三,耻感意识更为重视个人行为对个人名誉的影响,罪感意识更为重视个人行为的正义与否、善良与否。对于日本人来说,名誉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名誉,甚至可以不顾事实,不讲善恶。传统的日本人往往用复仇或自杀的方法来洗刷耻辱,保全名誉。耻感意识对人的行为的约束靠外部力量,罪感意识对人的行为的约束靠内心良知。[12]154-155耻感意识也对日本人的法律意识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菊与刀》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一个孟德斯鸠式的结论:法律不能改变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她告诫美国政府说,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迫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度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有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以及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12]217
应当承认,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国民性格和意识的分析为日本法与西方法的差异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在所有非西方的民族中,日本常被公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在法律方面,日本通过大规模地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也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法制现代化。不过,如同很多学者所言,尽管日本法在国家制定法层面已跟西方法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但其现实运作却与西方法的实践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气质、国民性格的不同。正如日本学者野田良之所言,继受西欧法的日本人依靠西欧法实现了近代化,但这并不表明日本人变成了西欧人。运用法律主体乃是具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日本人,因而,日本法从国家法到生活规范都具有不同于西欧法的性质。[30]87
六、民族性格范式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到目前为止,本文主要在介绍学者们关于法律与民族性格的各种观点,而没有对民族性格范式的有效性进行追问与评论,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对民族性格范式的态度与立场。本文最后一部分要完成这一未竟的理论任务。对于民族性格范式,日本比较法学者大木雅夫明确表达了否定性意见。在他看来,关于国民性差异的许多说法,如西方人是合理主义者、东方人是非合理主义者,西方人重物质、东方人重精神,无非都是任意臆造出来的东西。他认为,提出国民性作为解释的理由,实际上不啻于未作任何说明。因此,他反对用国民性或民族性格去解释各大法圈法律思维的差异。[31]120-121大木雅夫的批评道出了很多学者对民族性格研究的不满意见,即有关民族性格的诸多论断往往是一种印象主义的甚或武断的描述,而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不过,民族性格研究的方式及其结论有问题,并不说明民族性格研究本身没有意义,也不能说明民族性格对法律差异没有解释力。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注重对民族性格进行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一方面借助科学的取样技术保证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又精心设计衡量民族性格的指标体系、评价尺度。通过这种系统而周详的分析所获得的对某一民族的性格描述是相对较为可信的。[3]486-487
如果民族性格的描述是较为可信的,用民族性格来解释各个民族的法律差异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有意义的。和语言、习俗一样,法律乃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演奏的艺术作品,因而必然烙上民族性格的深刻印记。作为民族性格构成要素的心理特征、情感偏好、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必然在一个民族的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中体现出来,形成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样式。因此,就像可以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因素去解释各个民族的法律差异一样,我们也可以用民族性格去解释各个民族的法律差异。[32]而且,在某些方面,例如,人们对待法律和诉讼的态度、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等,民族性格具有其他解释因素所不具有的独特的解释力。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民族性格的解释力是有限度的。如果试图把民族性格作为解释一国法的所有特征的万能钥匙,那只会做出很多牵强附会、乃至十分荒唐的解释。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国法强调公、私法划分的原因在于法国人崇尚理性的性格。[33]这种解释显然很牵强。公、私法的划分并非法国人的创造,而是来自于罗马法学家。法国法不过是承袭了罗马法的这一传统。其次,在解释各个民族法律的差异性时,民族性格并非自足的、终极的因素,而往往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民族性格的形成本身是各种社会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综合作用的产物。在一个民族法律文明成长和演变的过程中,民族性格是和其他社会因素一起共同型塑该民族法律文明的特质的。因此,即使在民族性格发挥重要影响的法律领域,也不能孤立地理解或片面地强调民族性格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06-17
注释:
① 转引自马胜利:《法兰西民族的激进主义传统》,《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8页。
② 转引自何勤华主编:《法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③ 关于中国人性格的各种观点的摘编,参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格(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郝志东、沈益洪的中译本译为“乡村精神”。参见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页。
⑤ 后来,赖肖尔也有类似的观点:“对于日本人来说,根据等级确定人际关系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对于美国人来说,不管年龄和地位如何,都试图做到一视同仁是合乎情理的一样。”[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1页。
标签:民族精神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法律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法国生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