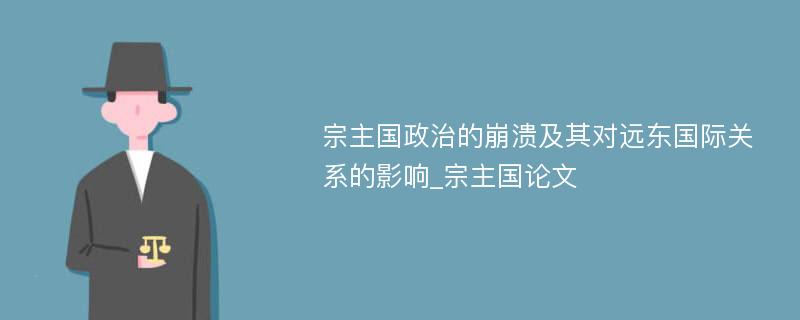
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其对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以来,乃至更早以前,中国同周边的大多数国家一直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宗藩关系,或称藩属关系。有时也叫朝贡关系,或朝贡制度。宗藩政治无论是作为一种国际关系,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历史地客观地总结和评述这一制度,研究和了解它是如何被瓦解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宗藩政治的出现与中国封建政治的发生发展有关。《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意思是说掌握天下的君主,应“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王也”。到了周代,则出现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治格局,周天子将其亲戚分封各地,以屏藩中央。秦代,秦始皇在内地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在边远地区实行“属邦”的管辖制度。汉代,因避刘邦之讳而将“属邦”改为“属国”。此后,随着中华各民族的不断融合,日渐形成同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
宗藩包括藩部和属国两部分。藩部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新疆、蒙古、西藏等,其疆域包括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其行政系统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内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染指。属国的领土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它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和政治制度,它们同中国保持着一种从属的关系。根据《大清会典》所列属国表、赵尔巽所撰《清史稿》、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书记载,鸦片战前,与中国有从属关系的国家主要有:安南(即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即泰国)、南掌(即老挝)、高丽(即朝鲜)、琉球、苏禄(即菲列宾)等。
宗藩作为一种带制度化了的政治,它具有以下的性质和特点。
一、它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学说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运用,是三纲中封建君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作为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是一种以大字小、以小事大的封建政治关系。对属国来说,尊奉中国为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取得中国的承认和保护,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而对中国来说,则以属国为屏藩,维护天朝的安宁。
二、它是从“中国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大一统关系演化而来的,是一种封建的政治联盟。宗主国与属国疆域分明。对中国来说,既不利其土地和人民,也不干预其内部行政。它们的关系是“从属但没有控制”,彼此“是兄与弟的关系,它不总是一种肯定的、一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接触大部分只是仪式”。“在理论上,且一般地在实践上,中国并不设法通过这些方式来直接干预这些属国的内政”,只要“照儒家的模型一道生活,并履行他们的义务,遵行有关的礼仪制度,这些国家大部分是自主的”。(注:克莱德:《远东》,第240 -241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229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若属国发生内乱或遭到外来侵略,则行字小存亡之道,维护属国的安危,以尽其对属国的义务和责任。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掠夺和战争上,中国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
三、它是一种自然的“礼节仪式的关系”,“儒家化了的国家关系体现”,通常是通过朝贡制度来体现的。朝贡既是一种外交礼仪制度,也是一种通商贸易制度。属国向中国朝贡有时间、路线、人员数量等具体的限制和规定。如:琉球,规定每3年朝贡2次,路线从福建登陆,经福州前往北京;暹罗每3年朝贡1次,路线经由广州前往北京; 朝鲜每4年朝贡1次,路线须由陆路经山海关,再到北京, 每次朝贡人员不得超过100人,其中包括1名正使,1名秘书,3名译员,24名保护贡品的护送人员,30名侍从人员。在公文往来上所有属国须应用中国的礼节和中国历书的时间。越南每4年朝贡1次;尼泊尔、锡金每5年朝贡1次;苏禄每5年朝贡1次;缅甸每10年朝贡1次;南掌每10年朝贡1次。
四、在近代以前,中国是东亚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宗藩政治在文化方面所体现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向慕钦佩,因此它又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为纽带的东方国际社会秩序。它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前期各国的附庸国和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封建主义时代,封建主是附庸国的宗主,封建制度消灭后,宗主权成为宗主国对附庸国在国际上的权利,在国际上,附庸国主要是由宗主国来代表它。但中国同其属国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在国际上,它不代表属国,属国在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藩属的同时,可以自由地、以一个主权国家身份同外国签定条约,这在琉球、越南、朝鲜等国的外交关系中表现得极为清楚。“琉球与朝鲜两国不仅在内政上是独立的,且有与外国缔结条约之权。”(注:胡特生:《世界政治中的远东》,第80—8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73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二)
1840—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打开中国门户的第一步,随后西方资本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了中国。战争的失败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亚洲,同时也对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绵延已久的宗藩政治在战后不到半个世纪也就迅速瓦解,直到最后崩溃。
宗藩政治的动摇首先同外国资本主义对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不断发动侵略、迫使清政府接受西方的“国际新秩序”有关。西方的所谓国际新秩序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原则。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强迫中国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各种权益。1861年后西方国家使节开始常驻北京,1873年(同治十二年)6月, 外国驻京公使首次入觐,1877年中国也一改千年来只有属国遣使来华朝觐的惯例,首次向外国派驻使节。六、七十年代中外关系的这一系列变化,俨然将中外关系划为前后、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对宗藩政治形成了冲击。
西方对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的侵略与对中国的属国的侵略几乎同步。列强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属国发动大规模侵略。通过夺取中国的宗主权,将中国的属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直接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宗藩政治从此遭到了破坏。
中国同属国的藩属关系首先遭到破坏的是琉球国。琉球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国隔海相望,北面与日本相邻。自明朝洪武年间,就接受中国的册封。1646年(顺治三年)后,作为中国的一个属国,一直定期朝贡,并在福建设有琉球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4月, 日本借口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渔民一事,悍然出兵台湾。“究其目的是欲吞并琉球。”(注:胡特生:《世界政治中的远东》,第80-8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73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在美国的调停下,中日签订协定。协定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是“保民义举”,等于是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同意撤退在台的军队,中国则向日本支付白银50万两。协定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对中国来说,“这种和解注定了中国的命运,……比起这种准备付款甚至更有意义的是中国轻易地放弃了琉球群岛,这个地方曾进贡有五个世纪之久。”(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0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协定签订的次年,日本公开改琉球国为日本的一藩,1879年又将它改为冲绳县,列为日本的一个行政单位。琉球国王秘密遣使来华求救。维护对琉球的宗主权,保护属国的安危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清政府就此训令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日交涉。何氏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复辩论,若不听从,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廷旨将何氏三策发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复议。李鸿章以何氏上、中两策皆小题大做,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中国受其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护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亦且无谓。”(注:吴汝纶辑:《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八卷,第4-6页,光绪刻本。)李氏从受贡无大利这个自私的观念出发,竟采取了消极的放弃论。此后中日虽经交涉,终于不了了之。1881年中国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宗主权。
琉球的丧失,是中国“所有朝贡的属国一个一个的相继被割去的一个序幕”。(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01 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清政府这种听任别国吞并一个属国而不拼力相争的作法,也给其他属国心理上投下了宗主国无力保护的阴影。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国对属国的“宗主权的主张是虚无渺茫和做样子的,而不是认真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5 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因此,它加速了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蚕食和鲸吞中国属国的步伐。
日本吞并琉球之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相继夺取了中国对越南、缅甸、暹罗、尼泊尔、锡金等国的宗主权。宗藩政治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越南古称交趾,汉唐以前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地一直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唐调露年间,唐政府设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交州,安南之名由此而来。唐末,藩镇割据,安南地方势力遂趁机自立为王,脱离中朝。清代,越南同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始终保持稳定的宗藩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18世纪以后,法国向东方推行殖民扩张的政策。鸦片战后,法国借口传教士多次在越南被杀为由,派遣远征军到越南勒索赔偿。这些为法国资产阶级侵略越南提供了“机会和借口”。1858年法国利用参加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武力,联合西班牙,发动侵越战争,1862 年2月强迫越南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夺取昆仑岛、西贡、下交趾三省。1873年法国对越南再次用兵,次年3月, 又迫使越南签订《法越和平联盟条约》(又称《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宣称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法国管理越南政府对一切外国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在内。根据这个条约,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越南国王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危险,于是秘密地遣使北京,希望清政府予以帮助。1876年越南循例派遣使臣向清政府朝贡,公使在京没有去拜访法国公使。1880年又照例派使朝贡,“向中国乞师反抗法国侵略”(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1883年7月国王阮福映去世。8月,新国王与法国正式签订《顺化条约》, 接受法国保护。“法国代替了中国——以一个压制者代替了一个无权之王,而作了越南的大君主。”(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 38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越南与中国的两广、云南毗连,法国侵占越南直接关系到中国本土的安危,捍卫越南的宗主权与保卫宗主国的安危相一致。《顺化条约》签订不久,中国就越南问题同法国展开交涉。但交涉一开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又一次采取消极退让的方针,他在同法国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时,对条约中的“每一个重要论点都对法国屈服”,完全屈从了法国的要求,“甚至超出了慈禧太后的愿望”。(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他的作法遭到主战派的强烈反对,简明条约未被清政府批准。在清政府看来,“在南方边境上有一个专横的欧洲强国作为邻居以代替软弱的越南人是不愉快的,抛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不论它是怎样虚假,是更不愉快的,而最不愉快的乃是认定中国自己的虚弱无能,没有打仗就承认失败。”(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当时中俄伊犁交涉已进入最后阶段。中俄伊犁交涉的成功,增强了中国对法交涉的信心。在主战派的支持下,清政府决定对法开战。战争后期取得了谅山、镇南关大捷。由于法国侵占越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西方东扩的意图,此后,英、美、俄等国对清政府频频施压,结果清政府最终还是把对越南的宗主权让给了法国。
越南的宗主权丧失后,随之又带来暹罗、南掌、缅甸三国宗主权的丧失。暹罗在中法战争爆发不久就宣布停止向中国朝贡,南掌也于1893年被法国兼并,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缅甸自元代起就是中国的一个属国,每10年遣使经八募、腾越前往北京朝贡。1862年下缅甸被纳入英属印度的控制之下。中法战后第二年,即1886年,英国担心法国势力扩张于己不利,将上缅甸合并到英属印度,至此缅甸完全落入英国的控制之下。同年7月24日,中英在北京签订有关缅甸的条约, 中国承认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权,同意“英国在缅甸当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而英国作为一种让步,仍允许缅甸“每10年向清政府循例进贡”。1895年缅甸依约向清政府派遣了贡使,进贡了方物,然而这也是它的最后一次。此后,这种“遣使进贡一事”,便被“丢进了人们忘却的古物储藏室”,(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41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连这点虚假的宗藩关系也不复存在了。
越南、暹罗等属国的丧失,还涉及到以西的尼泊尔、锡金。尼泊尔、锡金自1790年起就是中国的属国,按期朝贡不绝。它们最后一次朝贡是在1882年。1890年中英签订《印藏条约》,同意尼泊尔、锡金归英属印度管辖。1893年12月,赫德的弟弟赫政代表清政府同英国立约,承认尼泊尔、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至此,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属国全部丧失。它们的丧失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殖民侵略扩张的深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中华国际秩序开始崩溃,它直接加深了东亚地区的社会政治危机。
宗藩政治瓦解的标志是中国对朝鲜宗主权的丧失。
朝鲜古称高丽,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早在关外时期的崇德年间,就是清朝的属国。清朝入主中原后,中朝的藩属关系完全确立起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它是清朝属国中最重要的一个。
朝鲜又与日本隔海相望。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入侵。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向海外扩张的道路上,最早提出了“征韩论”。1876年1月,日本派遣海军到朝鲜。2月,强迫朝鲜签订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条约规定“朝鲜为自主国”,第一次对中国的宗主权提出了挑战。此后,日本不断向朝鲜渗透。为了维护对朝鲜的宗主权,同时也是为了抑制日本及沙俄对朝鲜的侵略企图,清政府曾以儒家的“以夷制夷”的方法,引导朝鲜参与国际社会活动,同美国等众多西方国家立约通商。然而“当时西方列强中没有一个国家(尽管它们与朝鲜订有条约)准备维护朝鲜独立的事实和原则,这就为日本这样作(指侵略朝鲜)开辟了一条道路”。1884年12月,日本在汉城一手制造了反对中国的“甲申政变”。次年4月, 在中日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中,日本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此后中日在朝鲜由外交对抗发展到军事对峙。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国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入朝平叛。“在行动上一直丝毫不苟地遵守着它作为一个宗主国所具有的责任”,目的“主要是不要给朝鲜政府招致麻烦,维持朝鲜的现状。”(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655页, 三联书店1958年版。)但日本带着它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趁机派重兵入朝。东学党起义失败后,日本拒绝中国同时撤兵的要求,并抛出一项有26款的改革朝鲜内政的纲领,限10日内决定并付诸实施。日本的所谓“改革”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此时它已下决心,要“雪除1884年的耻辱”(大隈重信语),“要实行侵略以期建立它在国际间的地位”。当中国以日本既认朝鲜为自主国,不应干预朝鲜内政答复后,日本遂采取军事行动,一手挑起侵略战争。1895年4月,中日议和,《马关条约》签订, 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至此,绵延数世的宗藩政治彻底瓦解。
(三)
宗藩政治在鸦片战后不到半个世纪内遭到瓦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西方资本殖民主义冲击与摧毁的结果。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及其属国所受到的种种苦难乃至变化均来自西方的冲击,以及日本的殖民侵略。一方面,19世纪上半叶,欧美主要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迫切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迫切需要殖民地,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东方各国首当其冲成为其主要掠夺对象。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及其属国还停留在中世纪,“在一个狂热的、技术的时代里,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是绝对地不足以应付的。”(注:伯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第39—40页,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327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西方资产阶级要按照它们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要将它们的殖民政治制度移植到东方,因此它们在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同时,亦通过战争剥夺中国的藩属国,使它们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置于西方的控制之下。这就是鸦片战后的二、三十年内中国先后丧失越南、暹罗、缅甸、南掌、尼泊尔、锡金等属国宗主权的原因。后起的日本对殖民地和市场表现了更大的贪焚欲望和急不可待,而邻近的琉球和朝鲜则首先成为它掠夺的重要目标。琉球和朝鲜的宗主权的丧失直接源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
其次,宗藩政治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同清政府的衰败以及它对属国的政策失误有关。对外战争的失败,连年的农民起义,使清政府疲惫不堪,元气大伤。在经历了农民起义大风暴的震撼和西方列强的严重打击之后,清政府推行了重内轻外的政策,把农民起义视为“心腹大患”,而将西方侵略看成是“肢体之患”。他们不谙世界大势,没有意识到由西方侵略所造成的“变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不去多费心思来估计他们自己衰弱的原因或西方强盛的根源”。(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27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在1864-1894年的30年中,“清政府完全可以进行内部整顿,努力使她和受她支配的国家(指属国)在国际上立于平等地位,可是时间过去了,并不见有效改良或者更新的信号,在陆军方面,在建立海军方面也花了些钱,可是在行政改良方面却一无表现。”(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7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仍循着传统的思维,恪守“内中华而外夷”的思想,迷恋“天子居中,四方来朝”的往昔岁月,在历史的巨大惯性和惰性的轨道上滑行。在清政府那里,兴办洋务的一个最大目的是维护传统秩序。对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身上的那些条件,诸如政治上、经济上的治外法权、行政权、协定关税权等,一件也未努力加以修改或争取废除过,对于西方列强无休止的勒索要挟,仍旧采取逆来顺受的作法,与邻近的日本举国上下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政治上表现了毫无作为。此外,吏治腐败,贪污盛行,最高统治层争权夺利。清政府如此腐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只能是日益加深了。
清政府既不能保护自己的本土免于外患,自然无法给属国以有力的保护。它虽不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宗主权,但在处理属国的外部事务上,常常摇摆不定,以至严重损毁了作为一个宗主国的“正当合理的地位”。如在朝鲜的政策上,清政府一再表示朝鲜是自己的属国,但实际上则尽量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在西方看来,中国是对朝鲜未尽责任。1866年法国因一名传教士在朝鲜被杀,要求赔款时,清政府软弱地拒绝了一个被“公认为是它属国的臣民所犯行为担负的责任”。同样的,1871年1 名美国捕鲸船员在朝鲜海岸被杀,美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清政府竟要求美国人自己去惩办。为了抵制日、俄势力,李鸿章援引“以夷制夷”的作法,引导朝鲜与欧美各国通商立约,清政府这样做,无疑是向世界各国表明自己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1876年日本派遣军舰到朝鲜,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明文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这一规定无疑是要废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直到这时,清政府才发觉自己的错误,力图挽回,要朝鲜国王在每一个条约中附上自己是中国的属国的有关条文。然而各国完全置这种似是而非的作法于不顾。对于朝鲜究竟是独立国还是藩属国,各国仍“采取最适合于它自己利益的看法”。(注:庄延龄:《中国,它的过去与现在》,第340—34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671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在中法有关越南问题的交涉上,清政府同样表现得极为软弱无能。李鸿章从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一开始,就误于“柔、忍、让”三字(注:《曾纪泽致郭筠仙侍郎函》,《曾纪泽选集》第二卷,湖南出版社1984年版。),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认为中国兵力一向单薄,滇防有名无实,海军又少,切不可与法国开战,甚至认为法国吞并越南,对于中国只是伏边患于未来,目前还构不成对中国的威胁,主张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注:参见《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上)第8页,1926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没有打仗就承认失败,这就是李鸿章所做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就此批评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的主张是虚无渺茫和做样子的,而不是认真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4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法交战的后期,形势对中国抗法非常有利,然而清政府却乘胜收兵,在稍后的谈判中,反而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致使对越南的宗主权完全丧失。
属国的存亡毕竟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中国的安危,支持属国抗击外来侵略同维护对属国的宗主权是一致的。在日本侵朝问题上,清政府采取了一种先前未曾有过的积极干预政策来“代替宗主权的消极行使”,动员全国的兵力、财力同日本相角,以尽自己保护属国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造成了对朝鲜宗主权的丧失,而且直接动摇和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加重了中国的危机。
再次,宗藩政治的瓦解还同属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冲击后所引起的对宗主国——中国的背离倾向分不开。
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着东方各国改变传统的封建制度。它们在对东方进行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既有坚船利炮到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技术,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乃至民权、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这些如同酵菌一样,不同程度地催化着东方各民族,并由此引起种种社会变化,对传统的东方国际社会秩序造成震荡。朝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明治维新的日本影响下,特别是在与各国立约通商之后,在士大夫官僚中出现了一股要求改革、学习西方的政治倾向,以金玉钧为首的开化党,希翼摆脱宗藩地位而求国家自主,无疑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力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为求摆脱藩属地位,结果却染上了亲日反华的色彩,成为日本向朝鲜侵略扩张的一股政治势力,因此遭到朝鲜国内广大人民的反对。这种亲日反华倾向,终于酿成了1884年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
四,宗藩政治的瓦解还同宗藩政治本身的弱点有关。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以朝贡为形式的宗藩政治是一种自然的、不成文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到了近代以后,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着中国和这些属国“发展他们的野心时,就显得十分无力,难以抵挡列强的奴役和掠夺”。(注:兴登:《中国与日本的主要问题》第95—96页,林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233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因此, 它的瓦解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四)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了惨败,并失去了朝鲜。因为朝鲜是当时中国的最后一个属国,因此,它的丧失,标志了宗藩政治的彻底瓦解。
宗藩政治的瓦解对远东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甲午战后,先前中国的属国至此完全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国际新秩序,相继沦为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西方、日本在夺取这些国家时,虽然标榜“承认它的独立”,如法越《西贡条约》中曾规定“法国承认越南的完全独立”,可是事实上,法国在从中国手中夺取对越南的宗主权后,它只是“借政治的、和平的,和行政的行动去扩展和加强它在越南的势力”,并进一步将其侵略势力伸进中国的西南地区。在1895年4 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本曾“允许朝鲜独立”,但其真实意图是为了抵制沙俄势力向朝鲜的扩张。10年之后,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击败了俄国,不仅控制了朝鲜,而且在稍后不久,便正式吞并了朝鲜,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当初允许朝鲜“独立”完全是一个骗局。非但如此,战后,日本还将其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在西方列强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辽东半岛。此后它对中国的侵略再也未停止过,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被坚决挡住而折回”。(注:赖德烈:《中国近代史》第85—8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66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宗藩政治瓦解后,作为远东国际关系的替代物,日本在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推行殖民侵略扩张中,为了独占中国,称霸亚洲,曾先后提出过“亚洲解放论”、“泛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论”,企图取代宗藩政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他们以亚洲的主宰自居,从狭隘的黄、白人种观念出发,把日本以外的所谓欧美白种人说成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提出要把亚洲各国从欧美的殖民统治奴役中“解放”出来,以掩盖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奴役。它们的所谓“解放”论,就是改由日本独占。所谓“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国任由日本宰割。日本的一位历史家对日本的这一政策解释得十分透澈:“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资源缺乏,需要向外发展,日本的大陆政策乃是命中注定了的,不采取这种方向,日本只有灭亡。日本必须确保朝鲜,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注:佐野袈沙美:《中国现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52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亚洲解放论”、 “大东亚共荣论”就是这种殖民侵略的外包装。
为了掩饰“大东亚共荣论”的侵略本质,日本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还常常将它同中国的宗藩政治进行所谓的比较,以之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所犯下的罪行。宗藩政治虽说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东方国际政治,然而同日本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大东亚共荣”政治毕竟有着重大的区别。
首先,宗藩政治是一种建立在儒家伦理观点上的国际秩序,多少世纪以来,它之所以为日本除外的东亚各国所接受,“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名义上的上国地位为属国人民保留了最大的自由和对于他们的钱袋的最小损失。中国一贯乐于容许自治,包括征税在内。中国容许把自治作为一种内核,如果能够以朝贡和名义上臣服的饰金外壳来满足它的帝国尊容的话。”(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 1958年版。)她不干涉属国的内政,没有对属国的骚扰,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她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权利和义务。属国虽同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们不受干扰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是通过一种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在文明、文字和领土方面都代表了更自然的关系。”贡使派往北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有经常性、连续性和一种远为深刻的义务感”,“进贡本身”只是“一种藩属的标志”。(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政治其本质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殖民政治,是对东亚各国的武力征服和疯狂的掠夺。这种“共荣”是用刺刀和枪炮建立起来的对东亚各国人民的“军事暴力统治”,是一种违背人道的法西斯暴政。
其次,宗藩政治存在久远,它是以东亚各国向慕中国历史文化为前提条件的,彼此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作为基础。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政治却没有这个基础。“中国为什么能够远久地得到它的属国的极度尊敬的另一原因,是它的灿烂的文学可以同样地通过朝鲜文、越南文、日本文或琉球文使人读到,这对于蛮夷们的思想引起了感召,就象衰微的罗马对于欧洲的野蛮人仍旧有着一种半宗教的迷惑力一样。……一句话,中国与罗马一样,是在道义上毁灭不了的。”(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政治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血腥地杀戮,残酷蹂躏。它是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的“罪孽渊源所在”。它不是亚洲各国自然形成的政治联盟,在亚洲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它在1945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破灭是毫不奇怪的。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东亚各国早已摆脱资本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并选择了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一贯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然而日本“大东亚共荣”政治的幽灵时不时出现,这就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历史证明,凡是腐朽反动的东西,终究是要灭亡的。
来稿日期:1999年6月9日。
标签:宗主国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朝贡贸易论文; 历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清朝论文; 远东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中华帝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