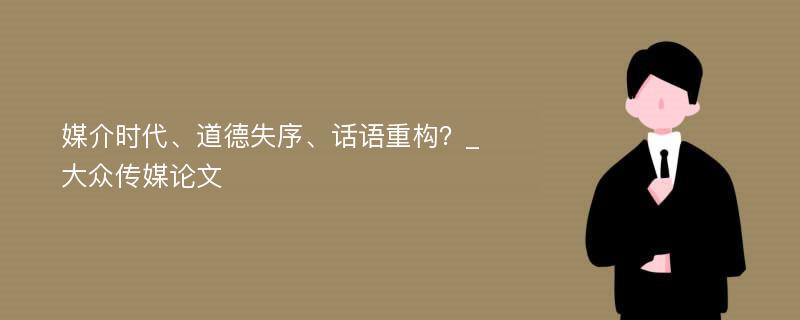
媒体时代、道德失序、话语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话语论文,道德论文,媒体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是从“毫无疑问”开始的,但,“无疑”还是“有疑”却因人而异。我读了《艺术百家》2006年第2 期上贾磊磊先生的《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道德失序与话语重构》,却感到有问题存在,而且就在题目上。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谨把我的疑问和不同陈述于下,以与贾先生商榷和交流。谢谢!
需要说明,我并非把贾文视为电影批评的文字,事实上,该文所涉及的批评状况远不止影评界,其他评论领域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大体如此。在我看来,该文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专业意义,实际上,它是从电影批评的角度对刻下文化现状做出的文化发言。因此,专业也许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在专业之外或专业之后的文化态度,这一点才构成本文的关注。
一、什么是“媒体时代”?
“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道德失序与话语重构”,这个题目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注意,“媒体时代”、“道德失序”、“话语重构”。按照顺序,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什么是“媒体时代”,或,什么又不是媒体时代?因为在我看来,媒体时代由来已久,非自今日。早在电影产生以前人类就进入媒体时代,而电影本身也就是媒体。具体地说,在东方,自从11世纪毕昇的活字术,在西方,自从15世纪古腾堡的印刷机,人类就开始进入印刷传播的媒体时代。当然,贾文中的“媒体时代”没有延伸得那么远,它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含义。比如文章开头:
毫无疑问,中国的电影批评随着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艺术批评曾经还是一个令人仰慕和崇敬的文化殿堂,如今大众传媒的商业取向使媒体上随意的吹捧与无端的指责处处可见,艺术批评已经成为一个可以随意进出的“庙门”。
这样便可以明白,作者的“媒体时代”主要是指“艺术批评”之后的“大众传媒”的时代。这就关系到文革结束后所谓“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变迁。从时间一维,大致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轮廓性的梳理:(一),被人仰慕与崇敬的“艺术批评”的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二),90年代以来,市场启动,各种纸媒兴起,便开始进入作者所谓“大众传媒”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分流使得带有专业性质的艺术批评产生了危机,因为以前偌大的“文化殿堂”只响彻它一家的声音。现在,声音频道增加了,声源不同了,它的听众被分解了,因而它原有的文化份额也减少了。(三),待及世纪之交网络世界的出现,即2000年前后, 文化格局更是风云色变。网络媒体以其“后”声夺人的气势,不仅争抢纸面媒体,更把所谓艺术批评挤向文化边缘。在众声喧哗的网络庙会中,各种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艺术批评的声音如果不是常常被遮蔽,也已类同于文化断弦。
但,尽管如此,作者“媒体时代”的命名在我看来依然是不合适的。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当你拥有一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教书;当你拥有两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流行。书籍、大学、学术杂志也是信息媒介。我们不应该把只要是自己不能接近或不愿意接近的渠道都称为大众传媒。”(福柯《权力的眼睛》第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书籍、杂志也是媒体时代,是知识分子的媒体时代,那个时代,整个大众都在倾听知识分子或学者专家的声音,包括批评和电影批评。然而,19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逆转,除了大量纸媒和电子媒介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这些媒介在生产内容上发生了“范式转型”,它从以往的“知识生产”或“精神生产”摇身一变为“消费生产”或“娱乐生产”。正是在这一关键上,80年代和90年代才被区别开来,造成这一区别的,不在于80年代是“艺术批评”时代而90年代便堕落为“大众传媒”的时代,不是的。大众传媒始终存在,就像“艺术批评”也始终存在一样。但,可以注意的是,不是“大众传媒”本身而是这个命名只有在90年代才会出现,而且它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暗含了一种出于精英立场的贬义(比如在本文中,它是和“商业取向”联系在一起的)。
“大众”、“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一个同构性的概念系列。然而,就这个系列中的“大众”概念而言,它不是孤立的,是和“精英”对举的,如果缺少对方,它自己就失去存在的意义。那么,为什么80年代不存在这样一个对举呢?很简单,在80年代的文化格局中,只有“大众”而无“大众文化”。80年代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时代,除了体制的控制,几乎就是知识分子的“一言堂”。知识分子通过纸质媒体向大众说话,对大众进行文化启蒙。而大众作为启蒙的客体,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它发不出也无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针对80年代的文化宴席,大众因其文化上的缺席或不在场,也就无需作出“精英”与“大众”的区分。
90年代不然,媒体的转型和娱乐生产的出现,使大众文化迅速形成,原来那个整体性的文化空间分裂了,它至少分裂为承袭80年代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以娱乐为其表征的“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不但在价值取向上二元对立;而且大众文化跑马圈地,不断从精英文化那里扩大自己的文化版图。这样一种文化倒转,“精英”与“大众”的区分方才成为必要。媒体不是自己的了,那就称它为“大众传媒”吧;精英时代过去了,那就称它为“媒体时代”吧。看起来是描述性的称谓,但它潜在地显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即,非大众的精英身份。虽然文章中并没有“精英”字眼出现,但一遍读过,谁又能说它不是从精英立场作出的文化檄文。文章一开头就见出了它的价值取向,比如,属于精英形态的“艺术批评”是“令人仰慕和崇敬的”,而“大众传媒”因其“商业取向”,则是“随意的吹捧与无端的指责”。
尽管贾文描述的现象有其相当的真实性,但,正如福柯所说,不应该把自己不能接近或不愿接近的渠道都称为大众传媒,何况自己在80年代也媒体过大众。福柯接着说:“我们是否可以为纤弱的学者划出保留地,一个‘文化公园’,他们受到大众传媒的凶猛袭击的威胁,而其他地盘可以成为次等产品的巨大市场?”(引同上)福柯的话如同一种讽刺,当学者以为只有从自己的“文化公园”中发出的声音才是艺术批评,而来自“巨大市场”的文化生产只能产生“次等产品”,这种指责如果发生,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自信,毋宁说是文化“纤弱”的疑似。
二、何为“道德失序”?
如果“媒体时代”在未曾分析的情况下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个价值中性的谓称,那么“道德失序”这个词立即见出作者对媒体时代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化状况的态度。问题是“道德失序”失的是什么“序”?为什么“失序”就一定是道德贬义的?
很奇怪,作为自己文章题目中的关键词,作者并没有用篇幅去展开,至少我不知道,在明确的意义上,作者的“道德失序”指的是什么。只是在这样一个段落中,它的最后一句,尽管只是短短一句,方才让我推理出作者在“道德失序”后未曾说出的文化逻辑。
大众媒体把艺术的趣味标准置于艺术的价值标准之上,并以观影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取代了艺术价值原则。电影批评在电影商业化的运作体制中本身就容易受到公众的质疑,加之诸如此类不负责任的批评言论更使电影评论的“公信度”越来越低。互联网上电影批评的极度泛化带来的是一系列学术规则的废弃和学术尊严的失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电影批评的自律性,坚持艺术批评的专业化导向,坚持电影评价的美学取向,已经成为电影艺术批评应当恪守的基本职业道德。
依然是对“大众传媒”的责伐。只是让我吃惊的是,就批评而言,无论电影还是其他,艺术趣味的标准难道不高于或不先于艺术的价值标准吗?这里并不排斥价值,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艺术品,我们衡量它的第一个标准是且只能是“艺术的趣味标准”即作者接着说的“审美趣味”。一个艺术品首先是一个审美对象,如缺乏审美趣味的话,它再有什么价值,我们还会视它为艺术品吗?同样,“以观影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取代了艺术价值原则”也存在类似问题。笔者不敏,就作为“个人”的观影者而言,他或她的审美趣味为什么不比所谓的艺术价值原则更重要?欣赏是个人的事,批评也是个人的事,它可以从某种艺术价值的原则出发,也可以恪守个人的感觉和趣味,这是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它们可以并存,更何况两者又未必天生对立。而且,说到底,任何艺术价值原则,最初不都出自个人吗?在作者所称举的电影评论体系中,比如从明斯特堡、卡奴杜、爱浦斯坦、德吕克、爱因汉姆、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巴赞、克拉考尔一直到米特里,那些今天看来是堂皇的艺术价值原则,无不来自这些“个人”及其他们的“审美趣味”。为什么大师们能“个人”,大众传媒就不可以“个人”?安知在大众传媒的无数“个人”中,就不能诞生出未来的、新的艺术价值原则?艺术价值原则并非神秘之物,它不过是个人话语经过长时间的批评博弈从而形成的“交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大家乐于认同的“原则”。但任何艺术的原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同时也不断接受来自新的个人话语的刷新。
至于从“电影批评在电影商业化的运作体制中本身就容易受到公众的质疑”,到“互联网上电影批评的极度泛化带来的是一系列学术规则的废弃和学术尊严的失落”,由于语涉大众传媒的两个时段,这里不妨稍作陈述。精英走失后的1990年代,是大众传媒形成的第一段次,它以纸媒和两电(电视电台)为主。当它一旦从人文知识分子那里易手,便形成了以娱乐消费为表征的大众文化。可以看到的是,“大众”在“大众文化”中和在以往的“精英文化”中,它的文化地位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启蒙格局中大众是压根没有文化地位的“大受众”,那么,在媒体主导的大众文化中,大众正在成为该文化的参与。因为现代娱乐生产的流水线就是强调参与、注重互动、共臻狂欢。从早期各种电视游戏到超级模仿秀再到近期的超级女声,不难看出大众在这两种文化中的价值位移,即在文化叙事上,大众的语法地位从宾语逐步转移到主语。当然,这不排除大众依然受到媒体掌控者的操纵。
真正的变化更发生在大众传媒的后一段次,这便是世纪之交因特网的出现。如果在电视电台之类的大众传媒中,大众尽管可以参与,但还需要某种许可(哪怕就是报名也要征得同意);那么,网络的出现真正给大众提供了一个文化参与的平台,它没有任何准入证,只需要鼠标和键盘。在因特网上,不需要任何审查,你便可以开通博客使自己成为一个作家,同样,你也可以通过BBS上的发贴和跟帖, 使自己成为一个评论家。于是,大众第一次可以和专家平起平坐,第一次可以摆脱你讲我听的课堂方式甚至和专家展开辩驳。这样一种文化民主和多元,使得世纪之交的因特网文化,在文化性质上远远超出80年代的精英文化和90年代的娱乐文化,也使得文化精英们比之以往纯粹的娱乐文化他们更不适应刻下谁都可以发言包括胡乱发言的网络文化。即以贾文而言,它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明显倾斜在网络媒体上。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文化弊端和文化优势几乎同样明显,而且密不可分(就像一个人不会说谎就不会说明真相一样),这更给精英们提供了道德抨击的口实和机缘。至少,精英们首先不满的是,艺术或批评的门槛被网络大大降低了,比如,该文就声称“在现实生活里,一名司机要开车需要考驾照;一名商人要经商需要申请执照,一名学生需要考试才能毕业,几乎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需要一种相互认可的核准制度才能有效。而在互联网上所有的这些制度、规则、政策都是无效的。”于是,人人成了作家,人人成了批评家。也于是,作家贬值了,批评家贬值了,被贬值的还有只能由作家和批评家来体现的学术文化。
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作者提出了他的“三个坚持”,“坚持电影批评的自律性,坚持艺术批评的专业化导向,坚持电影评价的美学取向,”并把这“三个坚持”视为“电影艺术批评应当恪守的基本职业道德”。这时,只是在这时,作者“道德失序”的文化逻辑才浮出水面。不妨把“三个坚持”中的第二个坚持单挑出来,意思就极为显豁了。亦即“坚持艺术批评的专业化导向,已经成为电影艺术批评应当恪守的基本职业道德。”如果再反过来看,可能更有意思:不坚持这种“专业化导向”,则就有违电影艺术批评的基本职业道德。
“道德失序”原来如此!
不过,这是一种什么文化逻辑呢?专业化导向即专家导向,莫非只有专家才能从事高雅的艺术批评,而大众染指就是批评本身的道德失序?也莫非即使大众染指批评也必须恪守由专家制定的专业化导向的“游戏规则”,否则就是失德?实实在在不知道,在一个多元存在的批评形态中,专业化和非专业化不过是不同的选择,它们和批评的职业道德有什么干系?因此,这里的“道德”在我眼中是一个伪词,还需要找到它真正的所指。我们知道,作者所谓“艺术批评的专业化导向”,其所指正是1980年代那种“传统的艺术批评”时代,那个时代的艺术批评是精英们的作业,大众只有聆听的份,因而那个时代的文化秩序是“令人仰慕和崇敬的”。90年代大众不再倾听精英的声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娱乐,因此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原有的文化秩序为之一变。迨至世纪之交,大众们不仅需要娱乐,进而还需要在文化上发言,甚至他们的声音在分贝上还压倒了精英,好一个喧宾夺主乱了套的文化秩序,这不是反了吗?如果一个精英以1980的文化时代为比较,这不是“失序”是什么?不过这种失序不是什么“道德失序”,而是“权力失序”。在法国利奥塔尔那里,“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第14页,三联书店,1997)根据这种知识社会学,知识即权力。80年代知识精英们文化通吃也就是权力通吃,今天他们手中的专业知识的权力不足以掌控网络时代的文化秩序了,因此,失序无非就是专业权力的失落,而“坚持艺术批评的专业化导向”,也不过是要恢复已经失落的专业知识的权力,至于“道德”,何妨是权力的一件合法化外衣。
我们今天面临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努力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时代。就电影批评而言,根据贾文的描述,至少存在着三种样态,即以精英为主的“专业批评”、商业宣传或炒作为主的“传媒批评”和以网络为主七嘴八舌的“大众批评”。其中第二种批评形态严格地说不算批评,因为正如作者所说:“有些所谓的电影评论其实不过是‘照搬’了制作单位提供的宣传材料”。如果把这种批评汰去,从以往的“专家批评”到今天的“大众批评”,无论如何,是一种文化转型,亦即是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知识精英其实是认同文化多元的,如果在专业知识的范围内,你说一种观点主宰好,还是不同观点并存好,我相信,没有人不支持后者,因为后者就是多元。而知识精英们所以认同多元,完全可以从以上“知识/权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那么这种观点无疑就是一种权力,它同时也就压制了不同于它的其他观点的表达权利。这样的文化格局显然是知识精英无法接受的。但,知识精英为什么能接受专业批评内部的学术多元,却不太容易接受批评本身的形态多元呢?这依然可以从“知识/权力”的角度去索解。表达作为权利,当它获得之后,以其知识的外衣,很容易从“权利”滑向“权力”。事实上,1980年代的知识精英获得发言权后,无论在文化心态上,还是文化现实上,都已经权力化了。这时它对它自身之外的其他权利很自然地会产生排斥。因为文化多元毕竟是对一元权力的解构,而这种解构会损害它既有的文化利益。
因此,当文化多元是个复合概念时,它不仅指专业批评内部的不同观点,同时也指的是专业之外不同批评形态的存在,这时,文化多元的问题就真正地放在了精英面前,并对其形成考量,它在考量精英们在多元问题上到底能走多远。然而,我们看到,面对刻下这种多元纷呈的批评格局,作为专家批评的贾文,它的态度或评价是“道德失序”。
三、重构“谁”的话语?
在互联网上我们看到了人们从语言狂欢发展到语言的暴力,从语言的暴力升级到语言的杀戮,从语言的杀戮演变为语言的灾难!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别人进行攻击,越尖酸刻薄越能获得满堂的喝彩,越是穷极无聊越是有人趋之若鹜。
是的,这的确是因特网的一种现实,但,更准确地说,是现实一种,它并非网络现象的全部。网络批评是一个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所在,然而这也是它勃勃的生命力之所在。别的不说,今年网络上点击率如此飙升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看似“恶搞”,但其实是一种别具形态的电影批评,它以影像批评影像,几类拓展出一种新的批评类型,以至谁都不能轻易低估这种批评方式的发展潜力。但,离开因特网,它是可以想象的吗?针对《无极》这种没有文化自信的电影(否则它也不需要从大陆从香港从韩国从日本堆集那么多的明星,以至叫人到底是看明星还是看电影都闹不清),“馒头”以滑稽模仿的方式复制出原电影背后的文化荒诞和价值虚无。面对这样一种极具颠覆效应的批评,原电影导演震怒地要把“馒头”告为侵权。此举即在因特网上引起了潮水般的反对,其中不乏贾文上举的那些现象,但,同样也有不少话糙理不糙的精彩之语,切中肯綮。总之,以网络为背景的大众批评是一个正在生长中的批评形态,它的两面性都很突出,一味的否定或相反,肯定都嫌简单。
但,贾文的否定显然是为了有所肯定,所谓“不破不立”是也。正是在对上述病理揭示的基础上,我们终于看到了题目中的目标所指:话语重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指明:首先,重构的对象是谁?根据题目,重构的对象是电影批评,但这并不确切。因为刻下的电影批评不是铁板一块,至少可以两分为专家批评和网络上的大众批评。很显然,专家批评不在此列,因为上述问题都集中在大众批评上。那么,问题二,大众批评本来就有它自己的话语(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现在要话语重构,那么,它重构“谁”的话语?
为了重构话语,贾文在全文的第一部分便用标题的形式梳理了伴随电影百年历史所形成的电影批评,它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从理论模式到表述形态,从社会功能到阐释原则,从评述视点到评价标准,都形成了自己的专业规模。以至这样一种电影批评的历史格局,“为我们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划定了一种无形的历史‘律令’。”显然,这个“我们”包括所有染指电影批评的人,但它不包括专家,或者专家本来就是这样从事电影批评的。于是,在“我们”中剩下来的就是网络上的大众了,这是在为大众批评设立“铁门限”。它以“历史”的名义出现,又以“律令”的威权提出。然而,这个“历史律令”望之俨然,即之则裸,一种未加掩饰的权力赤裸。“律”束约也,“令”听从也。接受谁的束约?又听从谁的指令?连同以上重构谁的话语?在大众和专家的两造对立中,这个“谁”不是专家又是谁?
于是,情况就很清楚,贾文对“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很不满,准确地说,作者不满的是当下批评格局中的网络批评,它的出现以及它事实上的不良使电影批评“道德失序”。因而,贾文呈现出来的逻辑是,通过“话语重构”,亦即用专家的专业话语来重构大众话语,从而使整个影评走上以专业话语为主的整饬的学术批评道路。这样的动机未必没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可能没有意识到,面对一个多元的批评格局,试图用某一类话语(哪怕它是学术的)去“一律”其他不同于自己的话语,都将导致语际本身的不公平。这里不妨再度援引一次利奥塔尔,在他那里,知识精英们经常“用一个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贾文以上关于电影批评形成的描述正是如此,这其实是在“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由于这种话语是一种“元叙事”,因而它对其他话语便形成了知识统治。我们知道,利氏本人是反对“元叙事”的,他在解释“后现代”这个概念时,就简洁地把它说成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同前书,第1—2页)
当贾文试图用在历史中形成的以专业形态出现的电影批评的“元叙事”来整合刻下电影批评,实际上也就是用它来“通约”网络上的大众批评时,像利奥塔尔一样,我不得不对这种“元叙事”表示谨慎的怀疑。因为,一个批评格局如果是多元的,它们应当有各自的“元叙事”,而彼此都不必企图用自己的“元叙事”去化约对方。当年白居易在杭州“书天竺寺”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是的,因为网络的出现,大众批评才从专业批评的“山门”中破缝而出,由此形成了批评的两个“山门”。这是多元之始,是好事。为什么偏要把专业批评的“元叙事”扩张到大众批评,使得好不容易分出来的两寺重新归为一寺?既如此,“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峰云起北峰云”。两涧水流成一条,两峰云并作一朵,这数量的递减,岂非向一元倒退?相反,让它们保持各自的差异而存在,它们的关系便是“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钟声相闻、花影交映:互文的景观很美好。因此,“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殊不知,吾师之“道”即多元之道,只有多元,方能臻至“落纷纷”的境地。
明确地说,我并非反对电影批评中的专业话语,我反对的是专业通吃。贾文的电影批评是一个囫囵的概念,它事实上包含了不同的批评形态。对此,与其用精英的学术话语重构大众批评,不如让它们彼此区别得更明显。就像它们可以互相汲取,但不宜互相取代。现在的情况是,大众批评并没要取代精英批评,后者始终保有自己的“文化公园”,尽管这个公园的游客已经光顾很少。也正因为这样,精英们不甘固守,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游戏规则”要大众和自己一道游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一厢情愿。在我看来,“重构话语”不过是要重构自己的专业权力。难以想象的是,大众批评果真恪守它的游戏规则,我们还会有点击它的乐趣?大众批评来自大众本身,它不拘一格,率性而真,带有一定的文化草根性,同时极具感性的文化创意。以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你能想象这种批评会出自专家之手和学术之门?因此,我的看法是,精英的归精英,大众的归大众,让它们遵循各自的“游戏规则”去游戏。此正如利奥塔尔所说:“语言游戏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体制,这便是局部决定论。”(同前书,第3页)局部决定论可以有效地避免知识权力的意志,它如果建立体制,也是局部的,比如以学术“元叙事”出现的精英批评就局限在专业体制的范围内,它不必去干涉大众批评的语言游戏,也不必大一统地把自己的学术“自律”用以律他。
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想到今春网络上韩寒/白烨的博客论战与这里的问题相似。白烨认为: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因此白烨认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令白烨想不到的是,韩寒对那个所谓的文坛并不买账,他说:“部分前辈们别凑一起搞些什么东西假装什么坛什么圈的,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韩寒的话很尖锐,如果“祭坛”和“花圈”显得太过的话,那么,文坛或文坛中的圈子不是别的,肯定是个权力场,在这里可以利益与共。可是,白烨以暗示的方式招安,韩寒却不买账。转换到这里,贾文以大度的方式把网络批评也纳入到电影批评之内,而且给了它那么多篇幅;但其实大众批评才不介意自己是否属于电影批评,它连影评的票友都不必,更不想往那个“文化殿堂”里面挤。它所需的就是一个表达的平台,在此能够痛快地让自己表达自己,哪怕是宣泄(当然不应语言暴力)。学术不学术,就像文坛不文坛,关它何事。因此,这篇谈电影批评的文章,私以为涉面广杂,不若还是缩小范围,针对精英自己的批评为好。看看有什么良方妙策能够重构自己(而不是重构别人),以自己的声音重新吸引大众(而不是要大众和自己的声音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