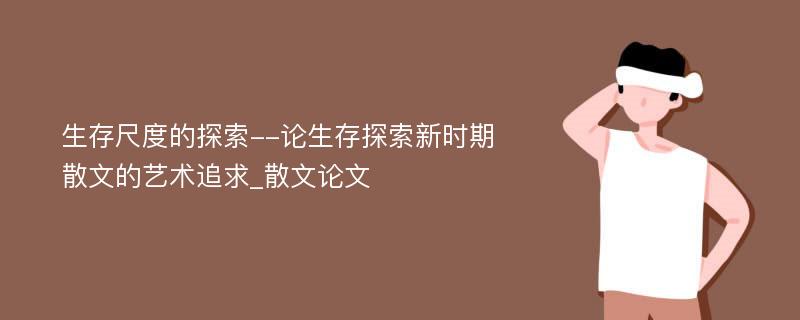
为生存探寻尺度——新时期生存探索散文艺术追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尺度论文,散文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人都有一个特殊的情怀,那就是关心家国胜过关心自己。文学家往往也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把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当作一种表达家国情怀的神圣事业。这项事业是专门敬奉神灵歌颂英雄的,平凡人生在此没有生存和空间的摆放,解放后的17年散文创作,将此推向了极致。然而,上世纪90年代,散文创作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以史铁生、贾平凹、刘亮程为代表的一批散文作家,以边缘生存者的姿态,关注平民百姓的当下生存。在散文创作中自觉减弱了家国情怀,增强了对于个体生存的思考。作家自觉摆脱了经营立场,放弃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位置,让自己站在普通生存者的位置上,用散文创作探索平凡生存者如何摆脱人生困境,思考普通生存者怎样才能活得具有价值与意义,他们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创造了属于这一时代的“有意思”的散文形式。
生存无非是一个不断突破个人在被抛境遇中已有的各种局限和束缚,向着自由之路不断迈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生存者都双脚紧蹬大地两眼巴望蓝天,他越望见蓝天的高远,就越觉得大地是一种局限,他越感受到大地的局限,就越向往蓝天的高远。这一境遇激发人们顽强地挣脱局限,执著地追求自由,竭力用自己的生存勇气克服各种屯蒙险阻,不屈地走向自由之路。人对局限的每一次克服,向自由的每一次靠近,都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幸福和快乐的享受,因此,人克服局限,奔向自由的过程又是感受幸福和快乐的过程。史铁生在《答自己问》一书的代序中这样写道:“残疾是什么呢?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1](P217)
关怀个体生存,呵护个体人生的作家,把写作当作自己作出艰难的人生困境,获取生存自由的人生实践,他们通过构建“有意思的文学形式”来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也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活动能够得到自我认识,并且为他们的自我实现有所帮助。他们知道,向死而生的凡人从来都把自己的生存历程当成一个追寻生存意义,创造生存价值的历程,人不愿意在混沌中混迹,不愿让人生失去价值与意义,一旦人生失去价值和意义,人对自己在生活世界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无票乘车的惶惑和焦虑。所以,早在古希腊时期,哲人们就提出,一个清醒的生存者首先应该关心自己,只有关心自己的人才能实现自己,为此必须认识自己。然而,人怎样才算认识自己了呢?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认为,关心自己的人必然关心如下三个问题,希望搞清如下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希望什么?中国新儒学的大师牟宗三则提出,关心在即的人必然关心如下四个问题,渴望搞清如下四个问题:(1)我应当做什么?(2)我可希望什么?(3)我能知道什么?①我能以“识”识是什么?②我能以“智”知什么?(4)人是什么?进行生存探索的作家们认为,为平凡生存着探寻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途径,帮助他们更好地关怀自我,既是中西哲人们的责任与使命,更是作家们的责任和使命。因为,文学是人学,人生的课题,自然也是文学家进行审美之思的对象。文学家都以为人类关心自己认识自己探寻管道和尺度为使命,以自己的文学能解决部分人生问题,让人觉得自己在世界中的生存有理由,活得坦然为荣耀。
二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严肃散文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为生存寻找理由,让人生活得坦然的活动。史铁生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1](P217) 史铁生对文学创作的上述思考,他在《我与地坛》等作品中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在90年代的生存探索散文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不仅探索和回答了残疾人关于物质与精神,苦闷与快乐,自杀与写作的问题,而且,对我们每一个关心自我、渴望认识自我的平凡生存者,解决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贾平凹90年代的散文创作,也以自己的平凡人生经历为对象,进行认真的生存思考与探索。这些思考与他自身的生存状况直接相关,是他真切的人生体验和思考的结晶。他对自己的散文有这样的评价:“早期的散文是清新,优美,但那时注重文章的作法,而那些作法又是我通过学习别人的作法而形成的,里边可能有漂亮的景物描写,但内涵是缺乏的,其中的一些看法也都是别人已经有过的看法,这是我后来不满意的。后来的散文,我的看法都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些觉悟,所以我看重这些。”[2] 贾平凹这个阶段对生存的思考、看法以及表现在散文中的“意思”,常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正如有人评价他散文创作时说的:“对佛禅的虔诚已成为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的贾平凹身上精神品格的一种‘原始’显现。‘原始’的宗教对宇宙自然生命灵魂的另类阐释,那种带有‘史前文明’特色的认知观,使得它在现代社会里成为人类文明文化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一个构成,并因此成为文明时代一些‘最现代’的文化人的最后精神归依,如牛顿如托尔斯泰如林语堂。”[3] 贾平凹生存思考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超脱,超脱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贾平凹选择进入禅境。禅给贾平凹带来了观察天地自然的新眼光,带来了体验世界人生的新精神,为他解除家庭变故的痛苦找到了一剂良药,为他摆脱世事纷扰的疲惫找到了一席憩息之地,为他进行文学创作更新了一支笔。
生存探索阶段,人们口口相传的流行话语是“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害怕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害怕有病。”[4](P256) 这话特别适合于一个商品意识日渐浓郁的社会。用商品意识来思考,生存所需的一切都需要用钱去买。有钱,虽然不一定能买到所有想要的东西,人起码有一种买主的尊严,觉得腰杆硬,心里踏实。没钱,一样东西你都别想据为己有。囊中羞涩,你只能望货兴叹,一腔悲酸,这是常识。吃五谷生百病,有病,人就会身心疲乏,无精打采,饱受身体疼痛、精神寂寞的折磨,这也是常识,更是人人都怕的经历和遭遇。人活着都想活得富裕活得健康,富有能使人产生良好的生存感,健康能使人充满活力地克服各种局限和束缚。富裕健康的人生使生存者在为自由奋斗时更加信心十足,这也是常识。然而,常识不等于正确。因为,贫穷也许会增加人们追求自由之路的曲折,疾病也许会缩短人们向死而生的途程,他们无疑都是限制人生自由的绳索,然而,克服怕的观念,与其进行斗争的过程,何尝不是人们获取自由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当然,人不是神,贫病交加的时候,都难免会消沉、悲观,甚至产生虚无感。但是,无钱时就自卑自贱,一有钱就自我膨胀;无病时怕得病,一有病就想到死,则是一种更可怕、更让人不自由的病。如何战胜这种病,使人的精神获得更大的自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末期,贾平凹因肝病而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住院治疗生涯。开始,他曾为此而忧愁郁闷,因为这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名人所具有的热闹生活,更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人际交往,他孤独地躺在病床上,觉得自己仿佛突然被世界抛弃了。“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4](P155-156) 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正是禅的人生观念把他从病的痛苦与孤独的忧虑中解脱出来,让他轻松自如地进行生存和写作活动。
人的生老病死,荣辱浮沉,是任何一种学说都必须面对并做出回答的问题。深受佛教影响的叔本华认为,痛苦是人生的宿命,因为人生而有欲,不能实现就感到痛苦,一旦实现又觉得无聊。慧能禅师则一反佛教的悲观宿命论,提出智慧化解说,认为智慧为苦闷的人生透出一口畅快的活气。他指出,智慧因烦恼而生,但这由烦恼而生的智慧终将化解烦恼。人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智慧,具体表现为人的悟性。悟性是生命之光,它能照亮人生中被遮蔽的黑暗角落;悟性是生命之水,它能清洁精神中沾染的尘埃;悟性是药,它能解除人心灵中的病痛。有了悟性,人就敢于直面生老病死,不以钱财的多少、寿命的长短为尺度来衡量生命是否完满,而以人生过程是否圆融无碍来衡量生命的价值意义。基于此,慧能禅师提出了“三无”(即“无念”、“无相”、“无住”)观,指出人如果能够破执著为洒脱,本心就会空明,就不会对外物生欲起念,无挂无碍的自由本性(即佛性)就会显现出来。所谓“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5](P15) “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5](P15)。由此看来,人生最可怕的病,不是形体畸变,而是精神蒙垢;反之,人生真正的健康不在于四肢发达,而在于心灵澄明。
接受禅学的影响,贾平凹从肉体的疾病和精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因此不再视病为可怕的灾难,而是在病中省悟,并且在病中悟出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病成了他参禅、参悟人生的一种形式;病使他“把一切都放下了”,使他的身心更轻松,精神更自由,生活更洒脱。于是,他用笔记下了对于人生新的领悟,作为对待人生的新态度,衡量人生的新尺度:
生的苦难与悲愤,造就着无尽的残缺与遗憾,超越了便是幽默的角色……[4](P163)
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4](P372)
把生与死看得过分严重是人的秉性,这秉性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感情,其实,这正是上帝造人的阴谋处。识破这个阴谋的是那些哲学家,高人、真人,所以他们对死从容不迫。[6](P107)
贾平凹在散文中追求这种破执著为洒脱,由迷途到彻悟的人生境界。他的这种人生思考与探索,不仅对解决自己的生存困惑,衡量自己人生是否圆融无碍,而且对解决与自己同样执迷的读者的生存困惑,衡量他们人生是否圆满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贾平凹后期散文的忠实读者都有这样的感觉,读他的散文作品能让人醒悟人生是一个庄严高尚、幸福快乐的过程,他从来不会屈服于现实的挑衅与烦扰,不会因外部施加的创伤而痛苦,他的自由心态和洒脱情怀能够战胜严酷的现实,把所有外部挑战和影响都当作自己获得解脱和自由的机会。
90年代对生存思考相当用力,而且很有代表性的另一位作家就是刘亮程。有人说他是“中国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生存散文到他这里应该说划上了一个句号。世纪末的中国,到处都在喧嚣科技理性,炒作商品意识。科技理性要求人们工作讲求效率,用最少的时间干最多的事。办事讲究效益,花最少的精力,获最多的回报。商品意识提醒人们,这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货币、货物;只有一种关系,买与卖。从这个角度来讲,工作效率高,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里,能生产更多的货物,卖到更多的钱;办事效益好,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里,能赚到更多的钱,买到更多的货物。工作效率高,办事效益好,证明此人生存本领大,应该在整个社会的中心吃香喝辣,受人尊敬和爱戴。反之,工作没效率,办事没效益,赚不到足够的钱,买不到足够的货,证明你缺乏生存本领,只好在社会边缘风餐露宿,遭人白眼和轻贱。这是从社会中心发出的声音,它犹如响雷,隆隆传来,压制并掩盖了其他各种声音,使每一个当下的生存者的耳膜都无法回避它的有力撞击。然而,中心并不等于正确;声大并不等于曼妙动听,悦人心意;有力也不等于“有意思”,更不等于有益人生。边缘也不等于错误,声小也不等于缺乏乐感,更不等于没有意思。再说,边缘生存由于远离中心,所以能够看清中心生存者的形象和边界;边缘声音由于不同于中心发出的声音,所以能够克服中心话语独白,形成多音齐鸣。因此,坚守边缘位置,倾听并传达边缘声音,对于救治中心生存的缺陷,对于形成多音齐鸣的社会和谐乐章,都有重要的意义。
刘亮程就是这样,站在社会的边缘,悬置了科技理性和商品意识所倡导的效率和效益观念,为自己构建了挣脱名利,回归自然的《一个人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他专注于倾听大地和天空所发出的和谐之音:“每天早晨,他和人们一起扛着锄头离开村子,没人知道这一天里他都干了些啥。天黑时他又混在收工的人群中回到村里。其实,即使他躺在家里睡上一年也没有人管。但他不这样,他喜欢躺在草中,静静地倾听谷物生长的声音,以及人和牲畜走动的声音。人寂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听到远远近近许多事物的声音。他们组合在一起,成为大地的声音,天空的声音。一个人在荒野中,静静地倾听上一年、两年,就会听上瘾,再不愿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他明白了大地的和声并不缺少他这一声。”[7]
在一个人人心中只有货币、货物的年代,哪怕是谈论声音,人们也会问,它值钱吗?如果值钱,能换来紧俏的货物,哪怕它是从蠢驴的口中叫出的噪音,都会有人拍手叫好。如果不值钱,不能换来生存所需的货物,即使是天空或者大地所发出的和声,也难免遭到“常人”们的轻视。然而,被叫好并不意味有意义,受到轻视并不等于他没有价值。刘亮程执著地用耳倾听天空和大地发出的和声,用笔向人们传达这种声音。这声音净化了他的心灵,和谐了他的人格,使他在人们都拼命追求最大工作效率,最大经济效益的年代里,以一种诗意生存者的洒脱心态去生存,以一种诗性的方式为“在大地上”“在蓝天下”的平凡生存者探寻生存的尺度。他相信,这声音也同样可以净化其他生存者的心灵,洒脱他们的精神,召唤他们诗意的生存。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提醒人们,天空和大地的声音,虽然不能兑换成货币,不能买来实用的东西,却是衡量人们是否完满生存的尺度,是任何一位追求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人须臾不可缺少的元素。
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诗人(即作家)首先是一个诗意的栖居者,他栖居的特点就是保护和保存每一物,使它们始终能够和平自由的生存。“保护本身不仅在于我们不伤害我们所保护者这个事实,真正的保护是某种积极的事情,当我们实现把某物留于其本性中,当我们特别的把某物送回到它的存在,当我们在真正的字面意义上让某物自由,使其入于对和平的保存,这时真正的保护就发生了。栖居,即被置于和平,意味着始终和平的处于自由,保护和把每一物都庇护于他们本性中的自由氛围中。”[8] 其次,他更是为人类寻找生存尺度的人。只有当他真正采纳尺度时他才算是作诗(即创造文学作品),有了这种尺度,凡人才得以度量自身的存在,凡人的生存才真正有了明确的方向——诗意生存的方向,才能按照自己的本质去生存。度量的基础是采纳尺度,然后把这一尺度用于度量活动之中。诗意生存的尺度就是: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引导自己。它要求天地神人和谐相处,形成完美的四一体。在这四一体中,凡人能够平和地接受大地,让他自如地开花结果,伸展为岩石和流水,生长为植物和动物,绝对不用自己的意志去征服它改造它;坦然地接受天空,让日月自行运转,四季自行变化,昼夜自行交替,绝对不用自己的意欲去干扰她;期待诸神自然的来临,让诸神自行地显露和隐蔽,绝对不为自己制造神和偶像;引导自己,让必有一死的凡人勇敢地承担死亡,使自己的死,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中无愧于人自己。
本真的诗(文学)是那些善良纯真的人作(写)出来的,也只有他们才能为凡人采纳诗意的生存尺度,因为他们怀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急欲一定施人的志向,在为自己寻找生存尺度的时候,把那对自身具有测量意义的尺规拿出来与众人分享。刘亮程在为自己建造对抗技术世界的审美世界时,也为所有不堪科技理性干扰的平凡生存者建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它和贾平凹一样,用一颗淳朴的心在为自己寻找审美生存尺度时,也为所有平凡的生存者找到了一种诗意生存的尺度。
寻找生存尺规测量自己的生存是否完满、是否有价值的行为,是一项与人类生存相始终的事业。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生存者,这项事业就会继续进行。正如人类每一项事业都会随着具体的环境来操作,都会围绕不同的目的来进行一样,不同生活世界的尺规采纳者,也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同类,为了在既定境遇中更加幸福高尚的生存而寻找到不同的生存尺规。只有那些从既定境遇出发,又超越既定境遇的尺规,才是适合所有凡人诗意生存的尺规。只有采纳这种尺规的文学作品才是具有长久效应的杰出作品。这并不是说某位作家能为人类找到一种保治百病的生存良药,而是说只要作家用善良纯正的心所采纳的生存尺规对人类的生存能起到较为久远的测度作用,他就具有让人诗意生存的功能。中国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从巴金采纳的说真话、有忏悔意识开始,到余秋雨采纳的有文化与文化观念,都是努力寻找生存尺规的表现。90年代以贾平凹、刘亮程为代表,采纳的超越功利洒脱生存尺规,更具有现实人生的具体针对性。表面看来,这些尺规几经变化,然而,其核心都是作家自己真诚地邀请所有的凡人一起诗意生存。我们不能说90年代作家的探索已经相当完美,但是,完全可以说,他们的创作已经走在了为凡人真诚寻找测量生存尺度的路上。
总之,90年代中国散文创作中的生存探索空前活跃,读者对散文的阅读和关注也空前踊跃。面对散文创作的这种盛况,理论界、创作界和读者们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林非认为,90年代散文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日益宽松的环境,自由和民主气氛大大加强;作者和读者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电视的普及,通俗的消遣方式充斥了文学作品。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太多,不愿意再花长时间去读长篇文学作品,于是便选择了短小精悍的散文;加之,中国是历史上的散文大国,大家对散文有很深的感情。曹文轩认为,散文的走俏应该感激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叙事的时代,一个散文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再以激情作为大美、至美,这是散文生长的最佳环境。现在诗歌不走俏,并不是质量差,乃时代使然。我们认为,上述诸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跟风之后,当代中国人的热情渐衰理性渐长,不愿意再被人用空洞的口号忽悠,不愿为幸福的允诺而热血沸腾。他们要活得清楚明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90年代的散文创作,积极进行生存探索,极力为平凡生存者寻找生存的尺规,正好适应了平凡生存者关心自我,即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人生要求。他们一改当代散文空洞浮泛的抒时代之情之风,在创作中注入了更多的知性因素,作品更贴近现实的平凡人生的需要,更具有呵护个体存在者生命的作用,因而更受普通读者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