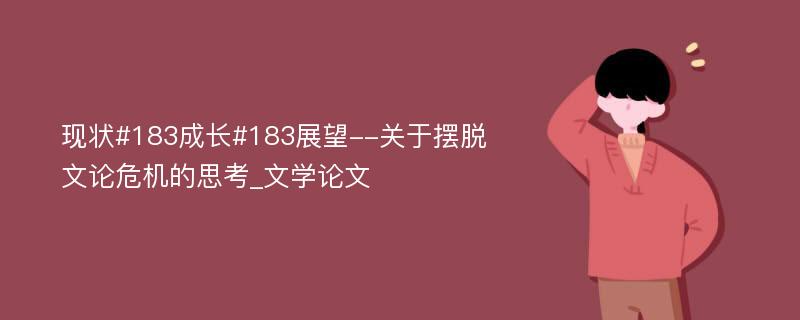
现状#183;生长#183;期待——关于文学理论摆脱危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生长论文,现状论文,危机论文,期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3-0022-04
现状
虽然没有谁不合时宜地大喊大叫“狼来了”,作为基本原理的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危机却已迫在眉睫。文学理论不再是人人向往、人才济济的显学,而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
近10年以来,作为基本原理的文学理论的科研与教学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这方面的论文数量虽多,但质量一般,予以人深刻启迪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无非是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相提并论;自从由童庆炳先生主编、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面世以来,虽然又有若干种同类教材问世,但内容大多陈旧不堪,或者旧瓶装新酒,或者新瓶装旧酒,总之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在高校的实际教学中,依笔者粗浅之经验,虽然任课老师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无法像某些“热门”课程那样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提高其学习热情。这固然与本课程的性质有关(较为枯燥乏味的理论课),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不足——不仅停滞不前,且有萎缩之势。
文学理论的衰退有其历史根据:在政府建制不全、功能尚未完善的年代里,文学理论常常是图解、贯彻抽象文艺理念的工具,是文艺斗争的战场。建国以来,几平每一次政治斗争都始于文艺论争。既然涉及文艺论争,自然离不开文学理论的论辩。于是文学理论之剑越磨越亮,寒光闪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律的完善,政府机构的健全,文学理论的政治功能,工具属性已经微乎其微。文学理论已经开始摆脱僵化思想观念的束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失去它本不该有的“腾腾杀气”和“勃勃生机”。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于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也是难得的契机。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恢复文学理论的本来面目——文学理论是有关文学的理论,疑聚的是有关文学的智慧;它不是对政策的图解,更不是斗争的工具。但过去恰恰在这方面暴露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缺点。长期寄生于政治话语、政治斗争之中,使得文学理论的从业者失去了真正的专业特色;专业术语的引入,纯粹理论体系的建构尚需时日。
生长
文学理论还能“生长”吗?它的“生长点”在哪里?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贡献于此。
第一,文学理论的生长点不在文学之内,而在文学之外。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特别是在分工不够明确的早年,文学理论家绝大多数来自文字理论之外。近代以来,情形有所改观,但真正激发文学理论之活力的,还是来自文学领域之外。现实主义文论来自朴素的实在论,"realism"这个单词本身就首先是哲学用语;浪漫主义文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自不待言的,康德—柯勒律治的师承关系尤其可以表明这一点。
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延伸;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也是如此。即使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这些所谓一心一意寻找“文学内部规律”的“内部批评”,也深受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是由文学理论的性质决定的:文学是一种旨在传达人的情感、欲望的精神产品,它虽然包含着思想、观念的萌芽,在某些时代也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或“图解政策的小喇叭”,但从总体上看,它与思想、观念较远。只有借助于“文学”之外的思想、观念才能解剖文学文本,描述其特征,总结其规律。
概而言之,文学理论来自广义上的文化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肯定下列现象——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出于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失望,胸怀拯救文学理论的远大志向(当然也有耐不住寂寞的惆怅),而毅然“出走”,奔向了“文化研究”的快乐王国。这是一种溯本求源的伟大理想。当然,大而无当、空洞乏味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种学风具有极强的感染性。
第二,文学理论的生长点不在理论之内,而在批评之中。
理论与批评密切相关,但又存在巨大差异:理论是一种思辨活动,批评是一种实践活动;理论旨在疏通学理,批评旨在褒贬作品;理论指导批评,批评丰富理论;批评以理论为前提,理论以批评为源泉。在理论界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一旦付之行动,却大谬不然。正如齐泽克所言:“在这里,回忆一下拜物教式的否认公式是多么有趣:‘我很清楚,但是……’”[1]。换成我们的话说,在意识的层面上我很清楚——批评乃理论之源,但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好像这两者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说,理论的批评化势在必行。停留在概念的玩弄上,停留在观念的冥想上,停留在“能指的嬉戏”上,就会枯萎。一旦失去了解读文本的力量,就无法面对活生生的文学世界,都无异于“自取灭亡”。
第三,文学理论应该是“复数”(theories of literature),而不应该是“单数”(theory of literature)。
这倒不是说盲目追求单纯的数量,比如出版多少种理论教材,发表多少篇理论文章。一个土豆是土豆,一袋土豆依然是土豆。据说某种学科的公共课教材一共出版过300余种,但它依然是“单数”而非“复数”。目前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也有几十种之多,但真正有新意者寡,其中不少还是“职称著作”、“博士点著作”(专门为晋升职称、申报博士点而出版的)。
这里所谓的“复数”是指: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理论框架与范例文本而精心创造的成果。学术立场虽然与政治立场、伦理立场有关,但又与其存有本质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可能对“文学”有不同的看法,只要这种看法能够自成一家之言,又能“吾道一以贯之”,就可以独创体系。比如,我完全可以是一位“形式主义者”,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思考文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对于文学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表现这种内容的方式;甚至认为,离开了形式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形式创造下内容,因而创造了文学。在西方,有关文学的看法千差万别;但在中国,无论怎样的千变万化,最后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的意识形态。这话固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所有的文学理论体系都立足于这个基本假定之上,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显然是不正常的。
不同的学者还可以拥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可以用经济基础—上层建构的模型研究五花八门的文学问题,可以运用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模型探讨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开创属于自己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我们当然不必作茧自缚般地局限在这些来自西方的模型之中,通过解读中国古代文论,进而确立属于自己的理论模型(如“理”—意—文,物—意—文的理论模型),也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第四,文学理论应该是“变数”(variable),而不应该是“常数”(constant)。
文学是日新月异的,甚至是一日千里的,理论也不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理相信人人都懂,但理论的更新速度实在太慢。落实到教材的编写上(教材是保留、传播既有研究成果最为有效的手段),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五,摆脱黑格尔主义的陷阱,去除其幻觉,乃当务之急。
比如一说到文学理论研究,就要寻找什么“逻辑起点”、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主张有坚实的理论立场,而不主张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许多理论体系并没有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却照样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例,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为精神分析理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就在于它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无意识领域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此举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掩藏着以本能、欲望(“力比多”)为核心的无意识。在信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朴素实在论者看来,这个基础是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无意识,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无法用尺子量,无法用磅秤称。但这并不影响精神分析学说大行其道,虽然它既没有科学的实证性,也没有哲学的思辨性,仿佛在讲故事,仿佛在说闲话,要命的是,却与我们的生活体验、感受大体相通……
一个学科的成立,与其“理论基础”是否“坚实”无关。关键在于,这个“理论基础”是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是否具有“延展性”。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应该抛弃的“迷思”(Myth)。社会科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它不需要像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那样,一味执著于寻求毫无异议的“公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寻求一个毫无异议的“公理”,难于登天。或许,“异议性”是社会科学的根本之所在。
之所以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因为自然科学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烈,二是因为我们受一个隐喻的制约而不自知。这个隐喻便是“理论大厦”——仿佛理论必须成为“大厦”才有出息。既然是大厦,自然要有“基础”,而且还必须是“坚实的基础”,否则“大厦将倾”,谁来负责?“理论基础”固然如此,“逻辑起点”之类的陈词滥调又何尝例外?
第六,应该把“理论”的功能与“教学”的功能分离开来。
“理论研究”与“实际教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这两种功能面对的“对象”不同。前者面对的“理想受众”是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同行,目的在于与其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后者面对的“理想受众”是与自己水平相去甚远的学生,目的在于向其传授基本的文学知识。
正如陈平原所言,“论文不是教科书”。他认为,许多学者把教科书当成写作的范本,把教学当成研究的楷模。教学的特点是一二三四、ABCD地罗列,以期把观点铺陈在一个平面上;研究的特点是“单刀赴会”,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比如,告诉你杜甫诗有四个特点,一、二、三、四,中国农民战争有五大特征,一、二、三、四、五,这是平面罗列,不必深入研究,这是教科书。论文是找到一个问题,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说形象点,做学术论文,研究要单刀直入,切忌贪多求全,四面开花。”[2]这虽然是就博士论文的选题、写作而言的,对一般的理论研究也不乏启示性意义。
研究不是教学,教学亦非研究,但现在的情形是,两者浑然不分,研究的教学化倾向尤其严重。长期在高校教学的业内人士更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他对自己面对的“理想受众”要么是浑然不知,要么一律将其定位为自己的学生。学术研究的教学化,学术著作的讲稿化,就是这样造成的。
期待
窃以为,文学研究离不开“五个一”,理论创新也离不开“五个一”:一个坚实的学术立场,一个切实有效、富有启示性的问题,一个有效的理论模型(或理论框架),一个出类拔萃的个案分析,一个新颖独特的结论。
比如,没有学术立场,就没有学术研究的根据地,就没有思想的资源、方法和动力。所以寻求立场的过程,也是寻求学术根据地、方法和资源的过程。但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大多数学者没有学术立场,跳来跳去,指着公鸡说:优点是打鸣,缺点是不下蛋;指着母鸡说:优点是下蛋,缺点是不打鸣。结论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比如,我们现在还缺少“问题意识”,“问题框架”(problematic)更是无从谈起。一部论著洋洋洒洒数十万言,你不知道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材料罗列甚为详细,真知灼见一点也无。读来昏头昏脑,想来糊里糊涂。如此做法,文学理论是“生长”不起来的。但我们期待着文学理论的“生长”。当然也不能揠苗助长。
